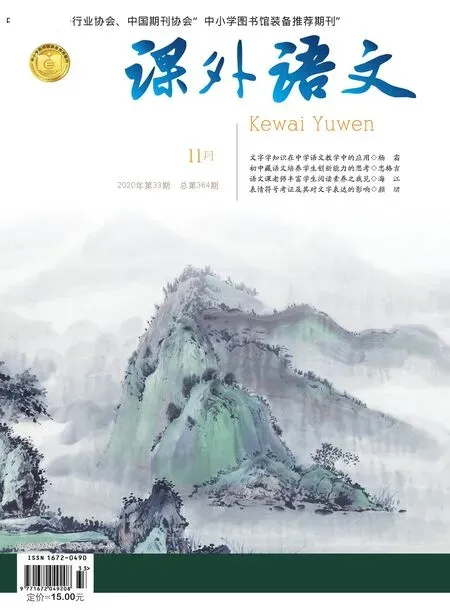浅析舒婷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阙 培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在文学领域中,最能展露诗人心灵情感的文学形式是诗歌。作为朦胧诗派的主将之一,舒婷突破了“民众千百年来不谈自我”的精神弊病,从女性独特的视角出发,探寻了女性存在的生命意义及其价值,展示出了女性高度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舒婷的女性意识构建不仅仅致力于在个人层面的努力上,更是深入到社会中,上升到国家和民族之上。在舒婷眼中,男女两性的关系是可以调和的,唯有相互尊重、相互支持,才能达到两性的自由平等与共存。舒婷的诗歌在女性文学创作上具有开拓性的作用,诱发了文人志士对女性文学高昂的创作与研究热情。
一、细腻的女性情感
情感是连接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舒婷一直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可以做到心灵相通的。所以,她以诗歌为凭借,以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沟通,在诗歌中宣扬自己的善良、积极与乐观。作为一个拥有先进思想的女性诗人,她那温婉有力的笔触书写着对爱情观、命运观与责任观的深刻见解,用诗歌语言重塑着两性之间彼此理解、互相尊重的相处方式,于此之中呼唤女性意识的回归。
(一)突破传统枷锁的爱情观
在舒婷的作品中,《致橡树》可谓是爱情诗的经典之作,她的创作旨在通过率直坦荡而又富有魄力的字句,表露出新一代女性的爱情坚守。平等、自由、独立是舒婷爱情诗的精神旗帜,这并不是要与男权一争高下而喊的宣战口号,她所做的努力不过是想重塑男女平等的价值观。“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诗人在此主要运用了四种客观事物,通过“炫耀”和“重复”二词,大胆地否定了“凌霄花”与“痴情鸟”在爱情中虚伪一面。后面又通过“常年”与“衬托”,对“泉源”和“险峰”不顾自身、为爱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做了裸露的批判。舒婷引入“木棉”的形象,倡导着女性应该告别攀附姿态,成为一株独立而有性格的“木棉”。像“木棉”树主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共同“分担”痛苦共同“分享”幸福。“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要有自己的根基”,这才是新时代女性对坚贞爱情追求的底线和思想认同。在《神女峰》一文中表现的是舒婷对封建传统落后观念的无情揭露,更是让世人深刻认识了“从一而终”这一落后的思想观念。封建观念中的“从一而终”是对女性的道德绑架,是禁锢女性精神的牢笼。另外,舒婷作为女性,对“神女峰”保持着钦佩和慨叹,同时又吐露了动人神话背后隐藏的肮脏与落后。所以她认为展览千年的荣誉,实际比不上与相爱之人的一晚倾诉。她立足于每个人应该拥有的生命自由的权利,给传统黑暗的男子霸权重重一击,她试图用对比式的文字张力拉响女性心中的警铃,给予她们挣脱枷锁的动力和奔向幸福的鼓励。与“神女峰”相通,惠安女子同样是遭遇悲惨命运的牺牲品。《惠安女子》一文中“你成为风景,成为传奇”,“传奇”二字本身具有神圣化和妖魔化的性征,惠安女子的真实情感埋没在“风景”之中,惠安女子卑微的命运禁锢在“传奇”之上。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女子遭遇的注定是不被理解的爱情,预示了悲惨的结局。总的来说,舒婷在爱情观的建立上离不开对前人爱情悲剧的深刻剖析与反思,还离不开对新时代女性的殷切期盼,舒婷于“悲剧残骸”之中去反思并获得前进的力量,为新时代女性树立了榜样,不断唤起女性深层心灵的觉醒。
(二)实现自我价值的命运观
舒婷主张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女性也不例外。女性不需要遵从封建节烈观,她认为“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都是畸形的精神绑架。舒婷并非要给女性宣扬叛逆的心理,女性自我价值的提出是要求女性从此刻起拥有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认同。“神女峰”作为男权社会的偶像,其精神禁锢了女性的自由意识,神话化的道德楷模促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牺牲者,女性的独立人格被极大地扭曲掉,女性的存在只是一个符号,从女性身上看不到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此情况下,舒婷喊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痛斥了对女性实施迫害的是“人”而不是“神”。封建节烈观的肆意,助长了对任何生命的漠视,尤其是出于社会较弱层面的女性,长此以往成为习惯。《神女峰》表达了舒婷对女性灵魂与肉体统一的呼唤,她在批判传统节烈观之余,更为直白地表明了现代女性应该受到尊重、关怀和平等对待,她们应该享有对生命本真的体验,以此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总的来说,舒婷看到了生命的可贵,痛斥了“杀害”本真生命的落后观念,鼓励女性到现实生活中去创造价值,实现自我。诗人站在人的高度上对生命意义进行审视,为的是呼唤女性重拾信心,为梦想拼搏,享受真实自我的生命体验。反映出现代女性想要挣脱男权文化的束缚,获得自我意识,就必须努力提升自我价值的必然性。
(三)人道主义的责任观
舒婷敏感地记录了处于文化转型时期女性的精神流向,她看到女性并没有仅仅局限在“一家之中”,而是走出来主动肩负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她的笔触书写着女性主动承担保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责任意识,例如,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之中,诗歌中随处可见新旧生活意象的对比,烘托出旧事物的凄凉与黯淡。在对比中透露了作者对祖国“满目疮痍”状态的深切悲悯,同时又表达了对即将破壳而出的新事物的期许,诗歌的情感指向对祖国明天的美好希望。除了对自己责任意识的要求,舒婷还不忘主动分担朋友的忧伤和困苦。一句“兄弟,我在这儿”,一句“假如你感到孤单,请到窗口来和我会面”,都体现出舒婷乐于助人、理性和善的一面。她将自己比作“顺帆的风”陪伴友人浪迹天涯,吐露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觉悟。她对朋友的信心和勇气的鼓励不曾停歇,她愿意分担,负责地参与讨论。除了对周围人物进行事无巨细的关心照顾之外,舒婷寄希望于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指引一代又一代的新青年拥有人道主义的责任观。其对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书写不仅仅是舒婷个人意识的体现,她代表了千千万万的青年和女性,重新审视了人类世界想要维持和谐发展的精神导向。因此,她将女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为范例,为的是吸引更多新时代的女性投入到唤醒人道主义责任观的使命中来,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实现女性意识的觉醒。
二、独特的女性意象
意象在诗歌中的应用绝非偶然,它潜藏了作者主观与客观的情感体悟。舒婷在诗歌中运用的意象极具个性,并且她有意筛选与新时代女性角色相适应的意象进行描写,可谓新奇独创。舒婷笔下突出女性意象的独特意象主要包括了三大类:“海”“泪”和“树”。
“海”这一意象给人的感觉是广阔而神秘的,看似与女性角色不沾边,实则其中的深刻意义是值得深思的。舒婷对“海”的情感与旁人不同,这与舒婷从小生活在海边有关。她常借助于“海”这一意象,诉说着心灵的迷茫与忧伤,同时也表现出对生命的渴望与追求。在《海滨晨曲》中,她以“忠实的女儿”的身份奋力“奔向大海”,展现出女性自由坚强的生命律动。而后又通过“飓风”与“狂涛”等自然环境的描写,映衬出女性的英姿飒爽。同样还体现在她渴望做一只“疾飞的海燕”,在大海的浪潮中拼搏翱翔。在《会唱歌的鸢尾花》中舒婷更是借“永远清醒的大海”,深刻地领悟到自己必须在兴风作浪的爱情海洋中坚守自我,时刻保持清醒的思想状态,才能迎接变幻莫测的挑战。“海”的广阔和神秘映衬了以舒婷为代表的新一代女性笃定的自我定位和人生思考。舒婷借助“海”的意象传达出女性应有的坚强,也不乏透露着对美好生命的追求。她用“海”来反衬了女性不惧困难的一面,因此“海”这一意象在反衬之中升华了女性意识的内涵。
舒婷作为当代女诗人,无论在性别角色还是社会阅历上都能与众多女性保持情感共鸣。“泪”的意象符合女性的形象特征,代表了破茧成蝶的痛思过程,也预示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舒婷常常会用“泪”来概括自己对爱情和命运的体悟。“泪”的作用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一代人的呼声》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挂着眼泪的笑涡”如何不是交织着痛苦和愤恨,如何不饱含着对命运的不甘,于挫折中重拾对生活渴求。舒婷在有的诗歌中更是将“海”与“泪”意象联合使用,“海”的硬气与“泪”的妥协相互碰撞,显示出诗人对过去与未来的理性思考,代表的是对过往的宽恕,也是对自我救赎的笃定。诗人对女性命运的揭露还体现在《碧潭水》中,表现出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带来的社会舆论。这里的“泪”实际上是历史与现实的争辩,诗中的“他们”决定了女性的地位和命运,“她们”又从未被尊重和平等看待。诗人言辞尖锐,在以“泪”还“泪”之上,揭露了女性悲痛的过往经历,也进一步唤醒了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树”这一意象作为人格的象征很早就有详细论述。“散木”“松柏”“枣树”等被文人志士赋予了生命意识,作为了人格化的象征。舒婷在其作品中有不少对于“树”形象的塑造,旨在通过塑造“树”这一形象告诉女性应该撇开柔弱依附的角色定位,变得独立自强。她在《悼》中将树作为人格化的象征,描写了“树”在实现自己的“路标”梦想上所做的努力,以及给世人展现出来的对自我价值的向往与渴望。她诉说着对大地包容性的感恩,展示了昂扬向上奋力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她的诗歌中的女性意识并不是一种绝对解放的女性意识”,《致橡树》这一经典名篇升华了“树”这一意象,舒婷有意将女性的尊重道德与开放自立的特征结合起来。比如,“橡树”和“木棉”都是大地之子,他们都依附于大地的滋润与恩惠。然而区别于以往的单纯付出角色,“树”给予了大地和周围的事物以恩惠,“您养我大,我伴您老”不就是“树”形象的深刻内涵吗?借助“爱”这一媒介,通过“树”这一意象,体现出女性意识在觉醒途中的良性发展。
三、崭新的女性语言
新诗具有语言口语化和形式自由化的特征,“我手写我口,作诗如作文”在舒婷的诗歌体现得淋漓尽致。“诗是理智指导下的情感的江河,是智慧与情感的共同丰富与延伸,最有价值的诗篇总是能把过去和未来集中于一身,表现出对人生的严肃思考与追求”。舒婷所用的语言鲜明自由,富有思辨性,正是其人生智慧和情感体悟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在《致橡树》《惠安女子》《神女峰》《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一代人的呼声》中我们随处可见舒婷鲜明励志的语言,总的来说体现在舒婷诗歌语言的思辨化和自由化上。一方面,在诗歌中有绝大部分关联词和否定词的运用,极大地体现了舒婷诗歌中女性语言的思辨之美。“与其”“不如”在《神女峰》中的运用,表达了对真相的揭露和对传统观念的不屑,体现出诗人高举否定的旗帜,对女性追求平等自由人格的号召。《致橡树》中的“绝不”“不”“不止”,这一系列带有强烈情感词语的运用,写出了新时代女性学会说“不”的进步一面。形成了她们平等、自由的爱情独立宣言,构成了女性自我价值的强烈认同感和保护欲。另一方面,舒婷诗歌中的女性语言还有自由化的特征,表现在话语体系和情感表达上的自由。在话语体系上,她所描绘的女性语言大多形式自由,更多的是个人意识和情感的自然流露,也就无心辞藻的修饰了。在情感表达上也相对自由,她在《致橡树》中先否定,但不止于“否定”,最后也会明确提出自己的爱情观念:独立、平等、尊重、支持。她利用亲切的口语化语言和丰富的意象给人们带来了思考,鼓励了新一代女性对自由人格这一精神内质的追求。女性的话语方式虽然一直受男权的影响,但是舒婷在语言的润色处理上的用功,让我们读到了构建平等两性关系的必要性。
四、结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权思想占据了社会的中心位置,女性思想被局限、被控制和干预。舒婷敏锐的观察力促使她开始关注人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她通过情感、意象和语言三大方面展现出对传统封建观念的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女性在自由、独立和个人智慧等方面应该突破的难点。另一方面,舒婷遵从儒家“和”的精神,以温和理性的方式期盼男女两性能结束对抗,达到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这一点不仅否定了女性“特立独行”的偏颇之言,而且展示出舒婷在处理人与人关系时的“中庸”思想,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温婉与理性。总之,舒婷的出现拉开了新时代女性意识的大门,成为新时期女性解放的宣言,既是对过去的救赎也是对未来的期望,这种文化与精神共存的体悟也正是舒婷诗歌历久弥新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