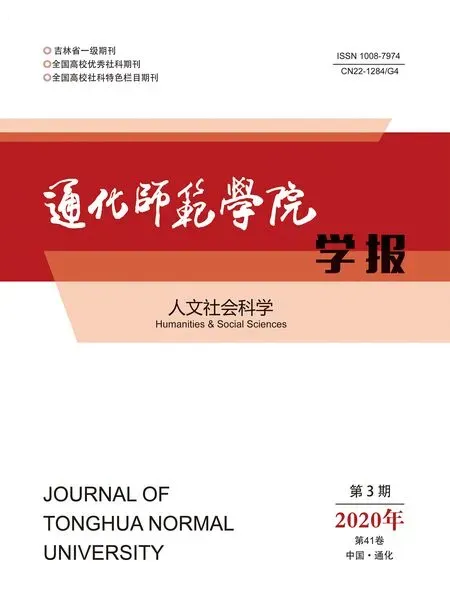从外来器物等看草原丝路辽西段的历史作用
叶立群
中国古代历史上,共有四条通往西方的商贸大通道,即“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南丝绸之路”。其中的“草原丝绸之路”经历史变迁,其主体位置位于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欧亚草原地带,由蒙古高原向西穿越南西伯利亚、中亚北部,向东抵达喀尔巴阡山脉的草原地带;向东则经中国东北深入东北亚地区。在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段向东北亚延伸的过程中,在多数历史时期与中国东北部重要的交通廊道——辽西走廊高度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价值和形态的辽西段草原丝绸之路。
众多周知,中华文化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吸纳异域的文化因子,使自身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历史上,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同样发挥了上述作用,它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吸纳外来文化因子。多年来,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陆续发现和出土了大量外来器物和带有外来文化元素的器物。其中,既有中国文化在由东向西输出过程中接受、带回的西方文化器物和文化元素,也有西方人对华输出的器物和文化元素。考察这些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比较清晰地了解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其在商贸往来和文化交融等方面所体现的独特价值和深远影响。
一、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
近年来,经众多学者的考证与研究,草原丝绸之路的沿革特别是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已经逐渐较为清晰地呈现。考古学研究发现,早在距今8000年前,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草原先民就与中亚及西方有着密切交往。公元前10世纪,随着北方游牧民族对马的成功驯养,东胡等游牧民族开始频繁地活动在横贯欧亚大陆的草原上,交通往来。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将河西走廊打通后,沙漠路线成为通向西方的重要道路,但北方原有的草原路线并未消失,匈奴人仍与西域频繁交流。公元4世纪至5世纪,即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进入历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期。关于入华粟特人在华商业活动的研究表明,草原丝绸之路南部路线已经抵达了黄渤海沿岸,“这条从河西经包头、呼和浩特、大同,通过河北北部进入内蒙古赤峰,到达辽宁朝阳的中西交通路线,可以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段……粟特人经常取此道通商。”[1]随之,在中国境内,“以平城(大同)为中心,西接伊吾,东至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了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平城和龙城(营州,今朝阳)是这条路线上的两个明珠。”[2]北魏中心政权南迁后,北方草原民族柔然、突厥等逐渐控制了草原丝绸之路,成为沟通西方与中原地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力量。这一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境外向西延伸的路线有两条,一是由亚洲中部的内陆河——锡尔河出发,经由咸海北岸西延;另一条由中亚阿姆河出发,经由咸海南岸西延。二者在乌拉尔河口汇合后,越过伏尔加河,沿着顿河和黑海北岸,抵达君士坦丁堡。唐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漠北草原后,进一步畅通了境内的草原丝绸之路。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随着辽王朝的建立和对回鹘诸政权的征服,辽在对外关系中特别重视与西域地区的联系,草原丝绸之路进入第二个繁荣期。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北线,“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行至辽西京(今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今河北宣化),又分为两路:一路正东行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东南行至辽南京(今北京市)。”[3]蒙元时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第三个繁荣期,也是鼎盛期。实现了草原丝绸之路南路与北路的畅通,在欧亚大陆北方形成了四条大道:从蒙古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道路;南西伯利亚各部间的交通路线;从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欧洲的路线;从中原内地通往中亚的道路[4]171。法国史学家格鲁塞所说印证了这一盛况:“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5]278元末明初,草原丝绸之路走向衰落,占据中国北部的“蒙古与文明国家的贸易,当时几乎完全停顿了。商路荒废了,商旅往来绝迹了”[6]199-200。清代后,草原丝绸之路虽有一定的恢复,但再未现往日盛况。
辽西,是一个独特的文化地理空间,因其重要的区域位置、特殊的人文历史环境,使其在民族融合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古代文明起源和文化一体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处于辽西地域、连接中原和东北亚重要通道的“辽西走廊”,是中国历史上文化传播、经贸往来、民族迁徙的重要通道。早在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的大凌河、老哈河流域已现交通廊道雏形,成为中原汉人及周边少数民族迁徙、南下和东西往来的重要通道。汉魏后,辽西古廊道逐渐发展、更趋成熟。研究表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廊道是联通中原和东北的最重要通道,具体路线有三条,一是从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境内),到平刚(今凌源境内),至柳城道(今朝阳);二是由卢龙,到平刚,至柳城道;三是由无终(今天津蓟县境内),到平刚,至柳城道。辽西走廊傍海道,是经由榆关(今河北抚宁境内)到锦州的傍海通道,这条通道虽古已有之,但利用率较低,在辽金后得到进一步开发,明清时期始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7]。同为“历史的地理枢纽”,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往往是重合的,“连接东北与中原的辽西走廊;连接东北与蒙古乃至中亚、西亚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8],二者在丝绸之路向东北亚延伸的过程中,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内实现了高度重合和交汇。以辽西古廊道为骨干的交通网络,也就成为了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的重要通道。在文化交流与商贸往来过程中,以草原丝绸之路和辽西走廊重合、交汇部分为核心的区域,必然会向周边进行辐射,形成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地理空间。这个文化地理空间,即当代学者所论定的“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9]因此,笔者认为,对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进行文化考察,其范围应界定为大致在包括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和河北东北部在内的辽西文化区内。
二、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
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的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最早源于新石器时代,与玉石之路、青铜之路有着密切联系,并贯穿着草原丝绸之路繁荣、通畅的各个历史阶段。此类器物和元素较多,以下为具有代表性的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
红山文化陶器几何纹饰。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彩陶图案最具代表性。具有中亚、西亚文化特征的几何纹包括菱形方格纹、等腰三角纹、直角三角纹、大三角勾连折线纹等。苏秉琦论断,红山文化彩陶罐,“绘有来自中原的玫瑰花,中亚大陆的菱形方格纹和红山本土的龙纹等三种图案,是欧亚大陆汇合点迸发的火花,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10]226
夏家店下层文化红玛瑙珠。出土于今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村。虽然有学者提出过这种珠子系由夏家店人首先制作的观点,但多数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红玛瑙珠,系由西亚、中亚自西向东传播而来。主要论据为两河流域、印度河谷、中亚地区发现的此类珠子,普遍要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500∼600年。
在距今4000年左右,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等青铜器文化中心,影响了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发现于巴林左旗的羊首曲柄短剑,发现于敖汉旗的铃首曲柄短剑,都受到了米努辛斯克文化青铜器的影响。
北票、朝阳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头饰。辽西地区出土的三燕时期金步摇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一件金步摇冠饰、朝阳市朝阳县田草沟出土的三件金步摇冠饰。这种冠饰的基本形制为花树的形式,由山题牌座、枝干和叶片组成。专家认为,这些3—5世纪的金步摇头饰,与阿姆河宝藏大月氏金冠形制极为近似,应源于阿富汗席巴尔甘大月氏金冠,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经北方游牧民族传入的。[11]49后来,金步摇经辽西,传往朝鲜和日本。
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形玻璃注等玻璃器皿。造型独特的鸭形玻璃注,极其罕见。鸭形玻璃注口如鸭嘴状,长颈鼓腹,拖细长尾,整体为鸭形。为淡绿色玻璃质,半透明,质光亮。采用了吹管法成型、粘贴法组成细部图案等复杂工艺完成制作。鸭形玻璃注重心在前,腹部充水过半时,加重后半身,才能放稳。由于其材质是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的钙钠玻璃,公元1世纪产生于罗马帝国的吹管成型法当时在中国尚不成熟,其成型与热敷玻璃条、造型及装饰亦属罗马玻璃系统,专家于20世纪80年代得出的研究结论一直为学界所认同,即鸭形玻璃注和同时出土的玻璃碗、玻璃杯等器物,均产自罗马,经由草原丝绸之路到达辽西。[12]427-428
朝阳北魏墓出土波斯银币。银币共两枚,出土于朝阳经济开发区石筑墓葬。埋葬时间为北魏中段晚期,为卑路斯银币,系与中国北朝年代相当的波斯银币。卑路斯银币与同时期的沙普尔二世银币、阿尔达希尔二世银币、伊斯提泽德二世银币、卡德一世币、库斯老一世币等,多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如吐鲁番、西宁、武威、大同、固原等地。朝阳为此时期波斯银币发现的最东端地区。此前,曾在朝阳银河社区唐墓发现了一枚波斯金币,但其输入年限比北魏墓发现的波斯银币要晚两个多世纪。
敖汉旗唐代墓出土的波斯金银器。出土的金银器包括器皿、带饰等饰品,其中的银执壶、鎏金银盘、椭圆形银碗为典型的波斯器物。其中的银执壶口径一侧有鸭嘴形流,另一侧有曲炳,炳部和口缘相接处有鎏金胡人头像,底部饰一周连珠纹;鎏金银盘浅腹,高圈足,盘心为老虎纹浮雕;椭圆形银碗,浅腹,碗口呈不规则椭圆形。[13]145夏鼐研究认为,此三件为东来的波斯萨珊朝输入品。[14]290从纹饰和器形特点考察,为萨珊帝国东部制造的,输入时期应为安史之乱前。
同一墓地出土的银杯,从形制和风格看,应产自粟特人区域,后传入辽西。
阿鲁科尔沁旗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鎏金“孝子图”银壶,克什克腾旗二八地一号辽墓出土的“大郎君”银壶。两器物的形制相似,为敞口,竖颈,折肩,圆腹,圈足,造型与突厥同类器物相似,应为仿俄罗斯米努辛思克盆地西部、濒临叶塞尼河上游地区的突厥折肩金杯而制,嵌文和纹饰为中国式,联珠纹装饰采取了萨珊王朝银器制法。[15]332上述两件器物,应为当时东西方频繁往来交流的产物。
赤峰市元宝山区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团龙戏珠纹银高足杯。据当时的发掘报告,高足杯“锤铸,口足的周缘有波状夹粒纹的图案,杯心有团龙戏珠纹”[16]1070。查遍有关唐代早期金银器的资料,未有此种形制的高足杯。但在中亚巴拉雷克(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铁尔梅兹市西北约30公里处)6世纪上半叶的壁画中,人物手中的高足杯与此极为相近。因此,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大营子辽驸马墓出土的鎏金团龙戏珠纹银高足杯,应为由中亚经草原丝绸之路传入辽西的器物。
朝阳市姑营子辽耿氏墓出土的玻璃带把杯、浅玻璃盘。玻璃带把杯1件,为伊朗伊斯兰早期流行样式,与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保存的10世纪尼沙布尔产的黑地白彩鸟纹把杯等样式相同,应为伊朗10世纪产品。浅玻璃盘器“壁作出凹凸均匀之编织纹(暗花),酷似柳条筐萝纹样”[17]。其纹饰是用有模吹制而成的,非同时期国内制作工艺,且国内同期此类制品无纹饰。根据上述特征,应与同时出土的玻璃带把杯同为伊朗产品。
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玻璃器。玻璃器共七件,玻璃带把杯两件、磨雕四棱锥钉纹玻璃盘1件、刻花玻璃瓶1件、乳钉纹玻璃瓶1件、高颈水瓶2件。其中玻璃带把杯与耿氏墓出土的带把杯形制、材质、年代相同,应同为伊朗10世纪的产品。磨雕四棱锥钉纹玻璃盘应为公元10世纪或11世纪初拜占庭的玻璃产品。刻花玻璃瓶应为伊朗9—10世纪的产品。乳钉纹玻璃瓶应为8—10世纪埃及或叙利亚的产品。高颈水瓶很可能是9世纪后中亚的产品[18]。
陈国公主墓中,还发现产自阿拉伯地区的琥珀、玛瑙等[19]。
朝阳北塔出土辽时期的执壶。形制与传统的胡瓶相似,淡茶色,饰有金盖,瓶内底部有一小瓶相连。与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保存的10世纪的波斯玻璃执壶极其相似,据此可判断执壶产自伊朗[20]。
在距辽西不远的法库县叶茂台早期辽墓出土了器形和纹饰较为特殊的绿色透明玻璃方盘,经考证,其极有可能产自伊拉克或埃及[21]。
辽代壁画、雕刻等所反映的外来物产和文化元素。主要有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的壁画,其中有源自西域的驯豹场面;巴林右旗辽庆州白塔第一层的驯象砖雕,画面有西域人驯象场面;敖汉旗宝国吐乡1号辽墓的辽代《马球图》壁画,画中运动员戴西域人所习见的帽饰;赤峰北部辽庆州释伽如来舍利塔塔身浮雕,有卷须深目隆鼻的胡人牵引狮子的形象,敖汉旗北三家1号辽墓壁画中,发现有一只雄健的狮子后踞蹲坐在一只大鼓之上,狮子形象来自古代中亚、西亚;赤峰发现的辽代鎏金银马盂,腹部两侧堑刻有相同的装饰纹样,刻有菱形图案和头生芝草、安祥伏卧的神鹿,这种纹饰同样来自西亚[22]。在敖汉旗羊山1号辽墓中壁画还发现绘有西瓜等来自西域的水果[23]。
元代,现未在辽西发现典型的外来器物,但带有外来文化元素的器物较多,如敖汉旗元代窖藏金银器,其纹饰等带有西方文化元素。赤峰翁牛特旗等地发现的元青花瓷器,其青花颜料为西方产品,系通过丝绸之路运至中国。[24]154在赤峰地区发现元代伊斯兰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质墓碑等[25]。
三、从外来器物透视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的历史作用
历史上,有部分文献反映了草原丝绸之路到达辽西或经由辽西向东北亚延伸的信息,上述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的出土和发现,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辽西作为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段东部枢纽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商贸往来和文化交融的独特风貌,及其所产生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一)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历史悠久,是较早参与中西交流的区域之一。这种交流,对于辽西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源头及其发达的早期文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辽西是人类早期活动的地区之一,曾发出照亮中华大地的第一道文明曙光,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26]。被誉为中国北方上古时代文明中心的红山文化,“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年”[27]。属于早期青铜器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国北方青铜文明较为重要的代表。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既是‘彩陶之路’的东端,又是‘玉石之路’的起点,是沟通东西方‘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汇点”[28]。红山文化及兴隆洼文化时期,草原先民在同西方及中亚地区的交往中,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所吸纳的外来文化元素,如中亚大陆的彩陶纹饰、石雕女神像和岩画所反映出的原始崇拜等,对于先民原始崇拜和中华礼制文化的形成,审美意识和艺术精神的觉醒,均产生了重要作用。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约3500∼4000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拒马河,主要分布于今赤峰、朝阳、锦州、承德、张家口等地区,是早期发达的青铜文化。该文化在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居住习俗、城堡建筑、艺术形态等方面,均有着独特的表现。夏家店下层文化及中国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则代表着中华文化基因中的另外一种形态。从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所发现的外来器物和来自西伯利亚的青铜文化元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意义层的结构,使文化内涵得到拓展,文化精神得到丰富。先进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辽西早期文明发达的重要见证。
(二)辽西段是草原丝绸之路东南段东端的重要枢纽区域,既是商贸交易地,也是集散地与中转站
从上述外来器物、文化元素和相关文献记载看,辽西段不仅是草原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且在很多历史时期具有交通枢纽和商贸交易集散地、中转站的功能。
在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发现的上述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在东北亚的国家和地区,相同或相似形制的器物和文化元素均有所发现。如三燕时期的金步摇,在朝鲜和日本均很快出现;辽北法库叶茂台辽墓来自于伊拉克或埃及的玻璃方盘,是外来器物经由辽西向东北腹地传播的结果;日本新泽千冢古墓出土的产自古罗马、波斯的玻璃器,与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外来玻璃器极为相似;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发现的部分金器,与辽西外来金器具有相同的形制、工艺和纹饰等,专家判断,这些外来器物应为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传到日本、朝鲜。
根据现有的研究,“中国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经额尔济纳、河套、呼和浩特、大同、张北、赤城、宁城、赤峰、朝阳、义县、辽阳,东经朝鲜而至日本。这条路线是连接西亚、中亚与东北亚的国际路线。朝鲜和日本发现的4世纪以来的西方金银器和玻璃器等,有一大部分可能是通过这条横贯中国北方的草原之路输入的”[29]。以辽西为集散地和中转站,既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对营州(今朝阳)、辽中京(今赤峰境内)的城市定位所决定的,也与辽西地区的交通地理地位、功能有着重要关系。十六国时期至唐代,营州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金时期同样有着重要地位。今赤峰地区是辽的发源地和政治中心之一,辽中京、辽上京均在赤峰境内。在交通地理上,辽西走廊是东北亚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历史久远、使用率颇高的交通廊道,其在多数历史时期内,是陆上通往东北亚腹地、连通东北与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
(三)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既是民族文化熔炉,也是中西文化交融地,在中国这个复杂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的核心区域——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0],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文化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活的民族主要有古商、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靺鞨、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他们与长期居留或迁入辽西的汉人一道,共同创造了辽西的历史与文化。辽西也成为民族文化熔炉。
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作为民族熔炉的辽西,也是中西文化交融地,中西文化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在辽西实现了碰撞与融合。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的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明证。在物质文化层面,从上述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来看,与西方的交通与贸易往来,极大地丰富了辽西的物质文化,仅已发现实物和图像的就包括金银器、金银饰品、玻璃器、琥珀饰品、玛瑙饰品、服饰、瓜果等。史料记载的更多,在此不做赘述。在精神文化层面,外来器物和文化元素的传入,特别是宗教文化、科技文化和审美文化等元素的传入,对于辽西区域的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文化的传播、交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佛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在辽西的传播,其与当地民族文化的交融,对于各民族精神世界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西方科技文化传入后,辽西以兼容形态予以吸纳,并改变了民族文化心理。西方器物造型、纹饰、驯兽文化、马球文化等所承载的审美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辽西各族民众的审美心理,并影响了他们的艺术创造。
按照许倬云的观点,中华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31]7,是“多元一体”浑融构成,其最为基本的构成元素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融汇与整合,中西文化汇融和合后产生的文化因子也被注入了这个复杂共同体中。草原丝绸之路辽西段,既是民族文化熔炉,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碰撞最为频繁、强烈并实现了深度融合的区域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融地。因此,这里所生成的独特的文化形态,在中华民族这个复杂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