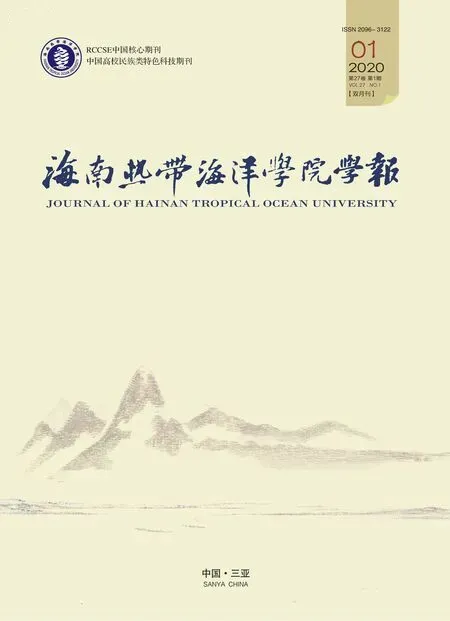六朝隋唐文学中的鲸鱼意象谈略
王 星,夏增民
(华中科技大学 历史研究所,武汉430074)
引 言
学界关于鲸鱼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鲸鱼的自然属性、文化意蕴和象征意义三个层次。其中,关于鲸鱼生物学上(自然属性)的研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兹不过多赘述。文化史学者对古代鲸鱼问题关注颇多,杨秀英及其硕士研究生沙大禹[1-3]曾对鲸鱼的历史称谓、分布及其形象变迁做过系列研究,晏新志[4]、陈敏学[5]则从鲸鱼与阴阳数术、灾异感应的角度入手,考察了鲸鱼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相较于鱼意象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成熟,学界对鲸鱼意象的关注起步较晚,吴振华[6]《论韩愈诗歌的鱼意象与钓鱼诗的文化内涵》一文,是较早对韩愈诗中的鲸鱼意象进行分析的文章,随后龚慧兰[7]《现世与理想的双重关注—论李贺诗歌鱼意象的深层含义》、田文青[8]《论唐诗中的鱼意象》、余红芳[9]《唐诗动物骑乘意象研究》等文均或多或少涉及唐诗中的鲸鱼意象。然上述研究并不专门针对鲸鱼意象,只是在各自研究内容之下偶有论及。系统考察唐诗中鲸鱼意象的是景遐东、刘逸飞[10]《李白诗歌中的鲸意象及其影响》和张丽莎、路成文[11]《论唐宋诗中的鲸意象——以李白、杜甫、陆游诗为个案》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以李白、杜甫等诗人的鲸鱼书写切入,重点考察了鲸鱼意象在诗人诗作中的占比情况,并进一步探讨了鲸鱼的具体象征意义。总体而言,学界关于鲸鱼意象的专门研究还是较少,对鲸鱼意象在中古文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亦缺乏通融性的认知。鉴于此,将鲸鱼意象放在中古文学(诗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系统梳理鲸鱼意象的流变,重点考察流变过程中的关节时间、要素,及其与中古文学演进之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有“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有几千里也”句,崔撰(今可见《庄》注中最早的一家)云:“鲲,当为鲸。”[12]3其稍后的郭象释“鲲”时则言:“鲲鹏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放、无为、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12]3唐人成玄英[12]3疏该句时引用了东方朔的《十洲记》和郭璞的《玄中记》。《十洲记》和《玄中记》中所记的“大鱼”与鲸类似,然“鲲”、“大鱼”到底是否为鲸,已然成了一段学术公案。实际上,抛开《逍遥游》不论,从先秦至明清,鲸鱼一直反复进入文本书写之中,特别是中古时期[关于中古,历来众说不一。本文所言的中古,专指魏晋至隋唐这一历史阶段。当然,文中有些探讨可能会推延到先秦秦汉及宋代,这视具体情况而定,当不全受“中古”拘泥。],其不仅成为文人笔下的一种典型意象,更参与塑造着时代文学的品性:鲸鱼或被实写,或被虚写,在社会思潮转关之际,敏锐地反映着文学走向,有时甚至成为涤荡、扭转前代文学风尚的“开山之斧”,在塑造新的审美范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魏至盛唐鲸鱼意象的演变
史书上有关鲸鱼的记载,最早见之《左传》,其卷十九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13]365杜预注曰:“鲸,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吞食小国。”[13]370鲸鱼是“不义之人”的代名词。《史记》卷六载始皇连弩射鲸事言:“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卜博士曰:水神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赍捕巨渔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14]263所谓“鲸,海大鱼也”[15],始皇射杀的“巨鱼”很可能就是鲸鱼,此处“巨鱼”也是邪恶的象征。秦汉以前,鲸鱼基本以负面形象存在于时人的观念之中,再如《淮南子》卷六所载:“昼随灰而月晕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鲸鱼“死于海边,鱼之身贱也。彗星为变异,人之害也。类相动也。”[16]鲸鱼与彗星出没同被人们看作是不祥的征兆。
(一)魏晋时期
就文学发展而言,魏晋是鲸鱼书写的第一个密集时期,此阶段,鲸鱼意象紧承先秦秦汉的典故、传说,多以此指代乱臣贼子。与之相关,“斩鲸”亦自然成为袚除谗逆,标榜功业的象征。如汉末《魏鼓吹曲十二曲?其三》所歌:“获吕布。戮陈宫。芟夷鲸鲵。驱骋群雄。囊括天下运掌中。”[17]《宋书》释此民歌的产生背景时言:“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18]644时人将吕布比作“鲸鲵”,曹操“芟夷鲸鲵”,故而“驱骋群雄”。类似的民歌还有《晋鼙舞歌五首·其三·景皇篇》云:“钦乃亡魂走,奔虏若云披。天恩赦有罪,东土放鲸鲵。”[18]631景黄帝即司马师,此诗反映的乃是司马师平定淮南二叛事。正元二年,镇东将军毌丘俭及扬州刺史文钦起兵反魏,司马师大败叛军,“亡魂”指在奔逃途中被射杀的毌丘俭,而文钦最终逃到了吴国,故此诗将其比作“东土鲸鲵”。
值得注意的是,鲸鱼在汉代也被美化过,其幽潜海底的特性曾被用来象征隐逸、高洁的情怀。最为著名的,如贾谊《吊屈原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19]“鳣鲸,亦大鱼也,以喻贤人。蝼蚁,小虫,以喻谗佞人也。言大鱼横于江湖之中,一朝失势,止于平陆,而蝼蚁所制。盖贤者失位,遭谗佞之所害。”[20]3鲸鱼与蝼蚁对喻并非贾谊原创。《庄子·杂篇·第二十三》庚桑楚谓弟子曰:“吞舟之鱼,砀而失水,则蝼蚁能苦之。”[12]772《文子·下》引老子曰:“鲸鱼失水,则制于蝼蚁。”[21]《战国策》卷二载齐人说靖郭君曰:“君不闻海大鱼乎?荡而失水,则蝼蚁得意。”[22]然而,春秋战国时期,鲸鱼与蝼蚁的关系仅用来说明“势”的某种变化,并不掺杂任何褒贬意义。贾谊借用鲸鱼失水而为蝼蚁所食的故事,赋予鲸鱼高洁的品性,以失水之鲸自比,抒发自己谪贬长沙的怨愤之情。贾谊笔下,鲸鱼具有了正面象征意义。王褒《九怀·其二·匡机》亦云:“鲸鲟兮幽潜,从虾兮游渚。”这里“鲸鲟”指“大贤”,“从虾”指“小人并进在朝廷也”[23]。遗憾的是,汉以后,鲸鱼的正面形象并未出现过在魏晋时期的诗歌中。究其原因,如果我们将此种现象与屈原在汉代的遭遇联系起来,则答案就不言自明。汉初,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称赞屈原“蝉蜕浊污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4],司马迁在《史记》中亦惋惜屈原“以彼之材,游诸侯,何国不容”[14]2503。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特别是至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以后,儒家“诗教观”得到了空前强化,班固在《离骚序》中就云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24]。扬雄虽然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然亦批评其没有做到“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25]。与屈原一样,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以鲸鱼自比,实际上也是“露才扬己”,违背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故汉以降,自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来,隐逸、高洁的鲸鱼意象自然就被士大夫过滤出来。
(二)南北朝至隋唐初年
魏晋时期的鲸鱼书写并不成熟,这主要体现在:(1)与鲸鱼相关的诗歌数量较少,没有形成集群效应;(2)在这些诗歌中,鲸鱼仅作为某种象征意义出现,大多是虚写,无直接、专门的实在书写;(3)鲸鱼的象征意象单一。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大量出现,直接促使了鲸鱼书写在以上三个方面得到突破。
《史记》卷六载始皇“夜出逢盗兰池”,张守节引《扩地志》云:“兰池陂,即古之兰池……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逢盗之处也。”[14]251始皇以后,皇家苑囿多有在池中“刻石为鲸”的习惯,如《三辅黄图》载汉武帝时的昆明池“有豫章台及石鲸,鱼长三丈,每至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26],又载“建章宫北有池,以象北海,刻石为鲸,鱼长三丈”[26]。因昆明池始为武帝“修习水战”而建,后又演变成帝王巡游的重要景观,故其往往成为表现帝王功业、颂美盛世的重要象征。相应地,石鲸亦被后人反复摹写。如梁朝刘孝威《奉和六月壬年应令诗》“雷奔石鲸动,水阔牵牛遥”[27]卷九十八、陈朝周弘正《咏石鲸应诏诗》“石鲸何壮丽,独在天池阴”[28]、隋朝薛道衡《从驾天池应诏诗》“曲浦腾烟雾,深浪骇鲸螭”[27]卷一百十八、唐初李世民《冬日临昆明池》“石鲸分玉溜,劫烬隐平沙”[29]等。除了应诏诗多以石鲸起兴,此时期,几乎所有有关昆明池的诗作都会吟咏石鲸,再如梁朝戴皓《煌煌京洛行》“铸铜门外马,刻石水中鲸”[28]卷四十二、陈朝江总《秋日游》“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鲸波”[28]卷九、隋朝元行恭《秋游昆明池诗》“池鲸隐旧石,岸菊聚新金”[30]140。《初学记》中有“昆明池”条,在其所辑录的诗歌中,“刻石”已成为固定的“事对”[30]149。《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石第八”下“鱼”条亦有“昆明池刻石鲸鱼,雷雨则鸣吼”[31]卷二,又“昆明池第五十”有“牛女石鲸”条:“汉武帝于池中置二石人相对,以像牵牛织女,又刻石为鲸鱼,每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31]卷二。《初学记》和《白氏六帖》均为唐人作诗查检的常备书,“石鲸”作为稳定的“事对”被唐人所承认,也从侧面说明了此前咏石鲸诗的繁荣。
南北朝至唐初出现的大量咏“石鲸”诗,表面上看描摹的对象是鲸的模型,但实际上,在这些诗作中,鲸鱼的外形、特性以及相应的象征意义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因而至少是“想象的真实”。此外,此时期的“石鲸”摆脱了以往鲸鱼意象的单一面孔,或被用来象征帝王气象,或指代京洛华贵,或以石鲸寥落来抒发历史兴亡之慨,鲸鱼的象征意义更加多元,这也为盛唐、中唐鲸鱼意象地进一步发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盛唐时期
杜甫《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一诗中有“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句。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云:“刘禹锡诗:华茵织斗鲸,知唐时锦样多织鲸也。”[32]唐人织锦多用鲸鱼图样,盖因“鲸鱼起而魑魅走,高枕上风涛涌而形神清”[33]。从这个小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唐代,鲸鱼与时人生活紧密相关。这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此时期的鲸鱼书写无论在数量,还是在意象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较南北朝时期均有巨大飞跃。由于此时期鲸鱼书写的诗作太多,为方便观览,我们兹统计书写次数在六次及以上的诗人诗作,如附表所示。有唐一代,诸如“李杜”“韩柳”“元白”“皮陆”,几乎所有大家文集中都有鲸鱼的身影,特别是“李杜”二人,分别以书写次数26和16次登顶鲸鱼书写的第一、二位。实际上,如果我们将统计标准下降至3次及以上,则张祜、皮日休、温庭筠、陈陶等人亦会榜上有名,如果下降至2次及以上,则需要统计的诗人诗作将更数不胜数。不仅在数量上井喷式爆发,此时期的鲸鱼意象也被时人系统、全面地挖掘出来。如李白《赠张相镐二首·其二》[29]卷一百七十、杜甫《观兵》[29]卷十八、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29]卷四百五十等诗继承前代文学传统,以鲸鱼象征乱臣贼子;杜甫《赠翰林张四学士》[29]卷二百二十四、元稹《胡旋女》[29]卷四百一十九、贯休《观李翰林真二首·其一》[29]卷八百二十九等诗以鲸鱼游泳跳跃的姿态象征人轻盈、潇洒的体态;杜甫《戏为六绝句·其四》[29]卷二百二十七、《八哀诗·其五·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29]卷二百二十二、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29]卷二百四、韩愈《刘生诗》[29]卷三百三十九等诗以鲸鱼象征雄健的笔力、险怪的文风。他如“掣鲸”“骑鲸”“鲸吸”“鲸吞”“鲸隔”“鲸牙”等亦已成为固定意象,被反复应用于诗歌之中。前文已述,贾谊在《吊屈原赋》中以鲸鱼象征隐逸、高洁的情怀,而后人因儒家“诗教观”的束缚,并未将其纳入文学传统之中。入唐以后,李白《杂曲歌辞·枯鱼过河泣》“作书报鲸鲵,勿恃风涛势。涛落归泥沙,反遭蝼蚁噬”[29]卷二十六、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29]卷二百一十六、元稹《虫豸诗》“时术功虽细,年深祸亦成。攻穿漏江海,噆食困蛟鲸”[29]卷三百九十九、白居易《寓意诗五首》“君为得风鹏,我为失水鲸”[29]卷四百二十五等诗都沿着鲸鱼与蝼蚁的典故进行了深入书写。其中,杜、元、白三人诗中鲸鱼的象征意义更是与贾文如出一辙,《杜工部草堂诗笺》释“蝼蚁”与“鲸鱼”时即言:“蝼蚁,物之微者,甫自喻鲸鲵,大鱼偃蹇沧海,理之常也。甫志在于致君泽民,其志甚大。复自责我诚蝼蚁小辈,但可自求其冗,何敢过拟大鲸而偃蹇于沧溟哉。”[34]其有意接续前代文学传统的意图十分明显。唐人从文学书写的现实需要出发,把鲸鱼当作特定的意象进行生发、运用,连“鲸鱼”与“蝼蚁”这种长时间被摒弃在文学传统之外的意象都可以被重新发掘,此时期鲸鱼书写的完美程度可见一斑。从某种意义上讲,唐人颇有“为文学而文学”的意味。
二、 鲸鱼意象与中晚唐险怪文风
诗歌发展到贞元、元和年间,风格多种多样,流派层出不穷。其中,以韩愈、孟郊、贾岛等人为代表的“韩孟诗派”,追求震荡光怪、瘁索枯槁的审美境界,形成了崇尚险怪的创作倾向,对后世影响极大。如果我们从鲸鱼书写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晚唐文学,则会发现鲸鱼意象是建构“韩孟诗派”险怪美学特征的核心意象之一,在塑造新的审美范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不只是“韩孟诗派”,整个中晚唐均有追险求怪的诗歌创作风尚。
(一)“韩孟诗派”笔下的鲸鱼意象
鲸鱼首先大量出现在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中,“韩孟”、“元白”、刘禹锡等人踵续前贤,继有一众关于鲸鱼的诗作出现。中唐诗人笔下,鲸鱼意象一方面继承了盛唐的文学传统,象征意义复杂多元。另一方面,鲸鱼深潜海底、常人不易得见的生活习性,与中唐文学对险怪意象的渴求一拍即合。鲸鱼对险怪文学的塑造,就集中体现在韩孟诗派诗人的诗歌创作中。
韩愈现存十四首鲸鱼诗,韩氏笔下,鲸鱼是营造怪奇刺戾意境的重要意象。如《刘生诗》“青鲸高磨波山浮,怪魅炫曜堆蛟虬”[29]卷四十八、《送无本师归范阳》“鲸鹏相摩窣,两举快一啖……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澹”[29]卷三百四十、《调张籍》“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29]卷三百四十。宋人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卷五释《调张籍》诗曰:“以喻得二子(李杜)之奇怪刺戾也。”[35]。清人方世举《韩昌黎编年笺注诗集》卷九同释此诗云:“魏泰云:髙至于酌天浆,幽至至于拔鲸牙,其思颐深远如此……‘拔鲸牙’,以喻沈雄汗漫。”[36]上引三首诗作,或可看作是韩氏的文论,韩氏“思颐深远”,以鲸鱼来形容他人(刘生、无本、张籍)“怪魅”“奸怪”的诗歌风格,其诗本身亦险怪起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即将《调张籍》诗与《送无本师归范阳》相联系,认为韩氏能将险怪意境描摹得如此纯熟,“盖作文以气为主也”[37]。除了韩愈,孟郊也作有两首《戏赠无本》诗,其一云:“文章杳无底,斸掘谁能根……拾月鲸口边,何人免为吞。”[29]卷三百七十七“拾月鲸口”既用来形容无本险怪的文学创作风格,又同时营造出孟诗怪奇刺戾的意境。
“韩孟诗派”诗人借鲸鱼意象来营造光怪枯槁的审美境界,还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联句诗中。如《城南联句》“惟昔集嘉咏,吐芳类鸣嘤。窥奇摘海异,恣韵激天鲸”[29]卷七百九十一、《会合联句》“狂鲸时孤轩,幽狖杂百种。瘴衣常腥腻,蛮器多疏冗”[29]卷七百九十一、《远游联句》“观怪忽荡漾,叩奇独冥搜。海鲸吞明月,浪岛没大沤”[29]卷七百九十一。《城南联句》为韩愈与孟郊共同创作,《会合联句》为韩愈、孟郊、张籍及张彻等人共同创作,《远游联句》为韩愈、孟郊及李翱共同创作。“恣韵激天鲸”“狂鲸时孤轩”“海鲸吞明月”应分别指诗歌创作中的声律、意象和构思等问题。“激天鲸”当指诗律的不求法度。《尔雅翼》云:“蒲牢者,大声如钟,而性畏鲸鱼,食于海畔,鲸鱼或跃,蒲牢辄鸣,故铸钟欲声大者作蒲牢形其上,斫撞为鲸形。”[38]鲸鱼在古代,常与声音相联系。结合上下文来看,《远游联句》中的“狂鲸”和“虎豹”“蛟鼍”“幽狖”等动物一致,均是险怪意象的铺排;“观怪”“叩奇”所言正是诗歌创作中观览、构思的过程,所谓“海鲸吞明月”与“思壮鲸跳渤澥宽”大致相同,当指作文构思之敏捷、想象之跳跃。联句诗体现的是一群人的诗歌创作追求,“韩孟诗派”诗人多次以鲸鱼入诗,且鲸鱼意象指向怪奇审美趣味的象征意义明确、集中。
(二)“韩孟诗派”以外的鲸鱼“书异”
元稹被贬通州期间,曾作《书异》一诗,全文如下:
孟冬初寒月,渚泽蒲尚青。飘萧北风起,皓雪纷满庭。行过冬至后,冻闭万物零。奔浑驰暴雨,骤鼓轰雷霆。传云不终日,通宵曾莫停。瘴云愁拂地,急溜疑注瓶。汹涌潢潦浊,喷薄鲸鲵腥。跳趫井蛙喜,突兀水怪形。飞蚋奔不死,修蛇蛰再醒。应龙非时出,无乃岁不宁。吾闻阴阳户,启闭各有扃。后时无肃杀,废职乃玄冥。座配五天帝,荐用百品珍。权为祝融夺,神其焉得灵。春秋雷电异,则必书诸经。仲冬雷雨苦,愿省蒙蔽刑。[40]
元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方人,难以习惯南方气候,此诗展现的全是让元氏感到惊异的气候现象。元氏用“喷薄鲸鲵腥”来形容当地雨水腥臊的气味,“鲸鲵之腥”与“泽蒲尚青”“皓雪满庭”“水状怪形”等现象一道,成为其表达“异”的一种重要意象。此诗无论在情感抒发还是在书写策略上,均与曹植《盘石篇》如出一辙。《盘石篇》作于黄初四年(223),曹氏迁雍丘之时,全诗围绕“我本太山人,何为客海东?”展开,运用大量笔墨来渲染“太山人”至“海东”的种种不适:“蒹葭弥斥土,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蚌蛤被滨涯,光彩如锦虹。高彼凌云霄,浮气象螭龙。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呼吸吞船欐,澎濞戏中鸿。”[27]卷二十七清人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评此诗即言:“起四句一篇之意已出,后乃极力写之,‘蒹葭’以下,其地之物则如此……我独何为而在此地乎?不极写,令荒异感之怀不尽欲。”[41]曹诗异域书写中,鲸鱼亦占据大部分篇幅。元氏之诗是否受到曹氏影响,我们不得而知,然可以明见的是,用鲸鱼来营造荒异怪奇的审美体验,在魏晋时期已经发轫,这或许是中唐险怪文风的渊源。回到元稹诗歌上,除《书异》以外,其另有十四首诗用到鲸鱼意象,其中,在《有酒十章·其四》“幽妖倏忽兮水怪族形,鼋鼍岸走兮海若斗鲸”[29]卷四百二十、《有酒十章·其八》“鲸归穴兮渤溢,鳌载山兮低昂……顾千珍与万怪兮,皆委润而深藏”[29]卷四百二十中,鲸鱼均是参与营造险怪意境的重要意象。
如果说元稹是“韩孟诗派”以外,中唐诗人中借鲸鱼意象“书异”的典型,那么陆龟蒙则是晚唐诗人的代表。陆氏有六首诗歌用到鲸鱼意象,其《奉和袭美古杉三十韵》一诗将炫彩夸博的工夫发挥到了极致。“虎搏应难动,雕蹲不敢迟。战锋新缺齾,烧岸黑黑兹黧。斗死龙骸杂,争奔鹿角差。肢(一作胈)销洪水脑,棱耸梵天眉。磔索珊瑚涌,森严獬豸窥。向空分荦指,冲浪出鲸鬐。”[29]卷六百二十三陆氏用“向空分荦指,冲浪出鲸鬐”来形容古杉直插青天的支脉,视角不可谓不奇特。从“虎搏”“雕蹲”“缺齾”“黑兹黧”“龙骸杂”及“鹿角差”等意象的运用上,我们亦不难看出陆氏求奇求异的创作倾向。关于陆氏对险怪文风的认可与追求,其在《记事》诗中说得很清楚:“虽然营卫困,亦觉精神王。把笔强题诗,粗言环怪状。吴兴郑太守,文律颇清壮。凤尾与鲸牙,纷披落杂唱。”[29]卷六百十九“粗言环怪状”“文律”“鲸牙”等字眼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韩愈的《调张籍》《城南联句》等诗,“粗言怪状”使得陆氏“精神王”,可见在对险怪文风的追求上,陆氏与韩孟等人并无二差。
除元稹和陆龟蒙,中晚唐诗歌中借鲸鱼意象来营造险怪审美意境的例子比比皆是,如陈陶《喜符郎诗有天纵》“海鲸始生尾,试摆蓬壶涡。幸当禁止之,勿使恣狂怀”[29]卷三百八十、章孝标《览杨校书文卷》“情高鹤立昆仑峭,思壮鲸跳渤澥宽”[29]卷五百六。杜牧在《李贺集·序》中评价李贺诗歌时亦云:“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42]中晚唐诗人如此热衷通过鲸鱼意象来表达对险怪审美趣味的追求,以致后人在谈到鲸鱼时多将其与“奇”“怪”相联系,如《增修诗话总龟》卷之二十八“诗病门”:“王靖学苏子美作壮语曰‘欲往海上吞鲸鲵’,又近有士人好为怪语。”[43]再如《四溟诗话》卷三在论述诗歌的几种风格时,亦专有“奇绝如鲸波蜃气”[44]类,来形容突兀怪奇的诗歌。
如果说初、盛唐是诗歌定型、辉煌的时代,那么中晚唐则是诗歌创新、变革的时代。我们认为整个中晚唐均有追险求怪的诗歌创作风尚,并不是指每位诗人都认同险怪的审美趣味,亦不是指中晚唐每个小时间段都有进行险怪文学创作的诗人,我们想强调的是:鲸鱼是塑造险怪文学的核心意象,它不光出现在“韩孟诗派”诗人的诗作中,也同时大量出现在此时期其他诗人的诗作中。中晚唐时期鲸鱼意象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实质上反映的正是对险怪审美趣味的追求,是此时期颇为风靡的诗歌创作现象。
三、 杜甫文学批评中的鲸鱼意象
盛唐是鲸鱼意象蓬勃发展时期,此阶段,鲸鱼复杂多元的象征意义不仅为塑造中晚唐险怪文风埋下了伏笔,同时,其亦开始染指文学批评。至宋代,鲸鱼已成为古典文论的一个重要理论范畴。
杜甫最早将鲸鱼引入文学批评,其《戏为六绝句·其四》云:“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钱谦益《草堂诗笺》云:“作诗以论文,而题曰《戏为六绝句》,盖寓言以自况也。”[46]406杜氏题虽为“戏”,用心却十分严肃认真。关于此诗批评的文学现象及鲸鱼所指称的具体内涵,历来注杜者皆有言明,宋人鲁訔编次,蔡梦弼笺校《杜工部草堂诗笺》补遗卷一云:
以翡翠喻,言今之为文者只得其小巧耳。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异物志》:赤而雄曰翡,青而?曰翠。‘未掣鲸鱼碧海中’,言为文之雄健未有能如鲸鱼之掣浪也。[47]
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卷二十二云:
言今之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赵云:此两句言数公者不过文采华丽而已,而公所自负其出群雄者,如掣鲸鱼于碧海,非钓手之善气力之雄,安能然哉。[48]
黄希《补注杜诗》卷二十二云:
赵曰:“郭景纯诗‘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言珍禽在芳草间交相辉映,而公借用言文章也。”“未掣鲸鱼碧海中”,洙曰:“言今之为文者止得小巧而已。”[49]9
“翡翠兰苕”是从辞章角度出发,言诗歌“文采华丽”,诸家均无异义。“鲸鱼碧海”,蔡氏认为当形容“文之雄健”,郭氏、赵氏则认为此乃指称作诗者“气力之雄”,鲸鱼的意义指向似乎并不明确。清代学者基本承袭宋人看法,但亦有所创见。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云:“兰苕翡翠,指当时研揣声病,寻章摘句之徒,鲸鱼碧海,则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人之所有之。亦退之之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46]1851。钱氏在宋人基础上,对“翡翠兰苕”与“鲸鱼碧海”的认识都有所突破,“翡翠兰苕”除指辞章华丽以外,亦指当时“研揣声病”的习气,“研揣声病”是诗歌声律上问题。“鲸鱼碧海”除指“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诗歌面貌,还多了一层险怪意义在其中。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浦起龙《读杜心解》对“鲸鱼碧海”的解释基本因袭郭氏和赵氏,“鲸鱼碧海”指“锯力惊人”,“锯力惊人”正与作诗者“气力之雄”同。宋人从文章风格与诗人才力两个角度去阐释“鲸鱼碧海”,表面上看似有分歧,其实二者相互融贯。刘勰《文心雕龙·风骨》篇即云:“夫翚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无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50]作诗者气力博大,文章自会呈现出雄健刚猛的风格面貌,所以“鲸鱼碧海”的意义指向是明确的。至于钱谦益所言“鲸鱼碧海”兼有险怪意义,当是“过度阐释”:此组诗是借古讽今,杜甫对“鲸鱼碧海”明显持赞扬态度,六朝时期安有以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为美的风尚呢?
除《戏为六绝句·其四》,鲸鱼作为文学批评术语还多次在杜甫的其他诗作中。如《八哀诗·其五·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进丽。是非张相国,相扼一危脆。争名古岂然,键捷歘不闭。例及吾家诗,旷怀埽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遰。[45]200
《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四释“鲲鲸喷迢遰”云:“喻邕诗之雄健也。”[47]764《九家集注杜诗》卷十四云:“鲲鲸,取其势之强壮。”[48]210《补注杜诗》引颜师古云:“鲲鲸,喻其雄健。”[49]11杜甫“近伏盈川雄,未甘特进丽”,盈川即杨炯,特进即李峤。爱杨炯之雄,不爱李峤之丽,正与“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所传达出的文学指趣异曲同工。又如《赠翰林张四学士》:“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溟。”[29]卷二百二十四张四学士即张说第四子张垍,“鲸力破沧溟”有言“此喻张翰林才力之健也”[47]338,亦有言“其势大”[32]45。“才健”“势大”亦与“鲸鱼碧海”“鲲鲸”的指称意义大同小异。再如《短歌行赠王郎司直》:“豫章翻风白日动,鲸鱼跋浪沧溟开。”[29]卷二百二十(此诗与《赠翰林张四学士》同,兹不赘言)杜甫笔下,鲸鱼用来象征雄劲刚健的诗歌风格(或才力博大的诗人),指称意义明确且集中。晚唐释齐己《风骚旨格》中有“诗有十势”,其一即云:“鲸吞巨海势,诗云:袖中藏日月,掌上握乾坤。”[51]又明人谢天瑞评唐人诗曰:“李杜韩三公诗如金鳷摩海、香象渡河,龙吼虎哮、涛翻鲸跃,长枪大刃、君王亲征,气象自别。”[52]“鲸吞巨海”与“涛翻鲸跃”代表的均是气力博大之诗,鲸鱼意象频繁用于文学批评中,俨然已成为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范畴。
齐梁文学绮丽艳靡,对文学独立自是一件好事,然时至盛唐,六朝骈丽习气仍然笼罩诗坛,这就严重了妨害文学的长远发展。杜甫以鲸鱼作喻,树立雄劲刚健的审美范式,鲸鱼意象对括廓清骈俪文风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杜甫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后人常将“登鲸海”“掣鲸”等所象征的雄健笔力与文学书写的真谛相联系,如陈陶《赠江南从事张侍郎》“几处谈天致云雨,早时文海得鲸鳌”[29]卷七百四十六、宋人王炎《用元韵答蒋簿》“诗来惊老眼,笔力掣鲸鱼”[53]、王洋《再赋前韵五首·其二》“子美才高不自期,却言苏李是吾师。若人欲逞兰苕句,试掣鲸鱼与对治”[54]、刘才邵《赠刘升卿》“方知掣鲸手,不足临渊羡”[55]、刘克庄《竹溪生日二首·其一》“两翁虽老殊精悍,笔力纵横可掣鲸”[56]、陆游《睡起》“白头漫倚诗豪在,手掣鲸鱼意未平”[57]等皆是此意。
杜甫将鲸鱼意象引入文学批评,是对中古文论的重要理论贡献。杜甫以后,经后人反复阐释,鲸鱼意象的内涵进一步扩大,其除用来象征雄劲刚健的诗歌风格外,还多了一层风雅意蕴。杜牧最早将鲸鱼意象与风雅传统相联系,其《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29]卷五百二十一“鲸海动”即找到了诗歌创作秘旨,杜氏认为,李杜上承“风骚”“风骚”正是杜甫诗歌价值所在。陆游《雨霰作雪不成大风散云月色皎然》亦云:“安得人间掣鲸手,共提笔阵法庄骚。”[57]卷四十九前文已述,“掣鲸”常被用来形容诗歌创作真谛,“掣鲸”与“庄骚”并提,鲸鱼意象实际被纳入文学正统中来。关于鲸鱼意象与风雅传统之关系,宋人诗话表述得很清楚,阮阅《诗话总龟·百家后集》卷之十二言:“李太白、杜子美诗皆掣鲸手也,余观太白《古风》,子美《偶题》之篇,然后知二子之源流远矣。李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则知李之得在雅。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则知杜之所得在骚。”[43]卷二十八太白诗的源头在《大雅》,少陵诗的源头在《离骚》,这正与杜牧等人的看法一致。
结 语
“鲸鱼在古代就分享着海洋的激进、神秘、歧义的他者性,象征着神圣的力量,无论其怀有善意还是充满威胁。”[58]古人海洋知识匮乏,对鲸鱼的认识模糊错乱,不仅是历史时期,即使同一时期,人们对其的看法也千差万别。可以说,中古时期,人们对鲸鱼的认识是真实与想象掺半,鲸鱼书写往往并不出于生活经验,而是来自前人记忆与时代思潮的杂糅。我们考察鲸鱼意象的历史演化,实际是在探索中古文学书写方式的历史演化。魏晋时期的鲸鱼书写零零散散,鲸鱼的象征意义单薄且单一,南北朝至隋唐初年,咏昆明池诗的大量出现,使得鲸鱼书写的数量陡增,相应的,此时期鲸鱼意象的象征意义亦开始变得多样化,这为盛、中唐鲸鱼意象的进一步发散打下了良好基础。盛唐时期,鲸鱼全面进入文人视域之中,不但此前有关鲸鱼书写的文学传统被毫无保留地挖掘出来,同时,鲸鱼意象的内涵也更加廓大,变得复杂多元。中唐时期,鲸鱼被文人有意识地引入诗歌创作中,成为塑造震荡光怪、瘁索枯槁文学风格的核心意象,这对中晚唐文学的定型、发展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鲸鱼对中古文学的渗入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书写形态上,更体现在以鲸鱼来言说其他:鲸鱼意象被纳入中古文论的理论范畴之中,这本身即标识着其得到了文人的认可,鲸鱼意象名正言顺地参与着中古文学的建构。总而言之,鲸鱼意象从文学塑造再到塑造文学,久远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古文学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