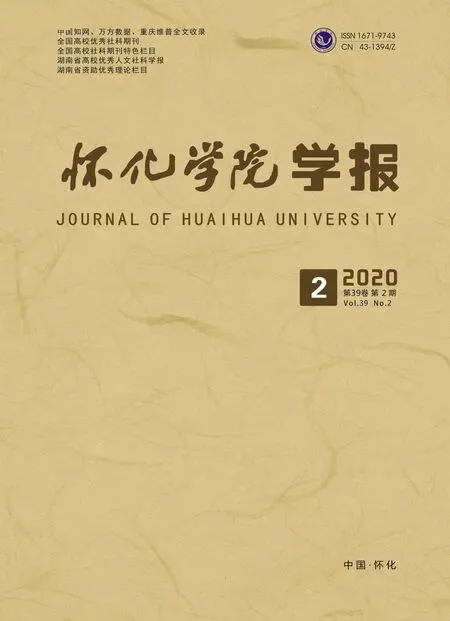清代浦市梓潼阁碑刻铭文的历史记忆
石慧琳, 陆 群
(1.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湖南吉首416000; 2.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114)
梓潼阁供奉的文昌帝君又称“梓潼帝君”,民间也称“文曲星”,最初由蜀中民间神“梓潼神”衍变而来。宋代道教广泛吸收民间神,梓潼神也由民间尊神升格为全国崇拜的文昌帝君,主功名利禄、文运科名。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方志及文史资料中多有关于道教宫观梓潼阁的记载,《浦市古镇》中记载浦市梓潼阁位于下湾后街,祭祀文昌帝君,为浦市“义学”创办地,抗日战争后为“志仁中学”。今虽阁碑不存,但三通清代重修梓潼阁的碑文都完整地收录在乾隆二十年《泸溪县志》中。碑刻作为一种记载历史的文化符号,具有非常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从梓潼阁碑文出发,可了解浦市道教的传播、多元信仰的互融、信众精神生活及清政府如何利用道教文昌信仰在浦市推行儒家价值观。
一、浦市梓潼阁及其碑刻铭文
浦市古镇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东南部,2019年底人口约6万,汉族居多。浦市古镇历史上曾为从沅江进入湘西苗疆的前哨,水运、驿道的节点,地理位置优越,商业繁荣,盛极一时。清康熙二十八年形成“泸沅交管”局面,至康熙五十二年裁撤泸溪、沅陵两地巡检司,设“通判”于浦市,俗称“三府衙门”。湘西的文昌信仰基本分布在苗族边墙之外的“熟苗区”,主要为辰州府的沅陵县、泸溪县、辰溪县、溆浦县,这些地方正是交通便利、较早纳入政府直接统治的地方[1]。清代浦市有12座铁板城门,西面就有“文昌门”,城门得名于浦市文昌阁。乾隆《泸溪县志》载:“梓潼阁,在浦市后街,康熙丙申年建,为浦市义学。”[2]《浦市古镇》载:“文昌庵:又名孔子庙,在下湾,今硫酸厂处……文昌阁:位于后街,祭祀文昌帝君。民国初年这里设浦市女子小学堂。抗日战争胜利后,姚少安兄弟捐谷五百石作经费创办‘志仁中学’于此。今为浦市医院。”[3]98县志所载梓潼阁位于后街,清康熙丙申年建,文昌阁在邑北延禧观后,明洪武初年建,且清代康熙、乾隆年间三次复修并撰有碑文。第一通碑文为康熙中叶(1692年前后)贡生李象珍撰《重修文昌阁碑记》;第二通碑文为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邑人张尔楚撰《复修梓潼阁记》;第三通碑文为乾隆二十年(1756年)沅陵进士魏绍撰《重修梓潼阁记》。按学界传统意见,湘西“改土归流”的时间应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开辟新苗疆为开端。三通碑文除《重修文昌阁碑记》为康熙中叶所撰无具体年份之外,其他两通均有具体年份且都在“改土归流”之后。据清康熙《复修梓潼阁记》载:“盖阁方颓圮时,楚履其地而忽焉”,说明浦市梓潼阁的建立应该早于康熙丙申五十五年。又清乾隆《重修梓潼阁记》载:“浦市祀文昌帝君久矣,康熙初年祀于卧云庵。”由此可知,浦市梓潼阁始建于康熙初年,丙申五十五年极有可能为移建,乾隆十二年在此基础上重修,但具体建阁时间还需要进一步考证。碑文内容如下。
碑文一:
重修文昌阁碑记
邑人 李象珍
城北旧有文昌阁,岁久圮。邑同人敛赀重修,工竣,属荒笔作记,以示不朽。余言安能不朽哉?
按,“文昌”之称,肇自玄宗,幸蜀封神为左丞相,后加封“辅元开化文昌司录帝君”神,注《大洞经》,详载《道藏》。而其聪明正直,能崇吾儒大伦,不逐异教,故海内士之敬礼者,自至圣先师外,莫不致敬于神,而不敢以他神俑人目之。盖神之昌文也,昌有德,不昌无德。士果学守兼优,为国家昌景运,为千古昌文教,则神必默昌之,可不尽其在己,以预为可昌地哉?
余言安能不朽?第愿凡我同人,益昌大其德,则人文昌盛,真不朽矣!是为记。
三通碑文中,贡生李象珍所记碑文时间最早,并且此碑文标题为“重修文昌阁碑记”,说明在清康熙中叶(约1692年)之前泸溪文昌阁已经存在。碑文作者李象珍,字尔玉,清康熙中叶贡生,选嘉鱼训导,辞不赴,卒后乡人私谥曰“文敏先生”[4]。此碑文中一记重修文昌阁的原因,即“岁久圮”;二记文昌神的来历、秉性、神职及功能,文昌神在蜀地封左丞相,后加封“帝君”,聪明,昌文教,受人尊崇;三记重修文昌阁的愿景,以尊崇文昌帝君许愿国家兴德、人文昌盛。
碑文二:
复修梓潼阁记
邑人 张尔楚
凡宫观寺庵之建,有捐赀者,人即重其所为,而载之石,至于预期其效果何为者,意其人始或有不乐于此,后姑勉强,以破一悭,故记之。欲其知所励也,抑其人心或有所私祷,故先欣言之,使俟券于他日云尔。
至若吾泸,地瘠俗厚,明而服官,幽而事神,罔有不虔,况梓潼帝君血食,载在祀典,不独主持文运,兼司人间禄命,其敬信之也素矣。则斯阁之建,乃其心之所乐为,无有觊觎者也,又何记焉?盖阁方颓圮时,楚履其地而忽焉,矢志若可以有成也,及谋之匠,科以二百余金,又爽然若失。忽而,亲友李、石诸君毅然为首,乡老高、杨等经之营之,庀材鸠工,俾事就绪,住持之劳力施财,众姓之劳心拮据,皆有可言。功遂告成,夫楚之愚懵,固易视天下事者,诸君则何以如此耶,其有神焉启之乎?
忆阁将成,资用告匮,众议敛于浦市。其夕,即有梦帝君马已备驾,将欲前征者,斯其验矣。则斯记也,虽记人之力也,实记神之灵也!是为记。
此通碑文撰写者张尔楚为泸溪县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贡生。碑文中一述撰文缘由;二记梓潼帝君的地位、神职,即梓潼帝君载在祭典,主文运,司禄命;三载梓潼阁的重修过程,即张尔楚倡议修阁,亲友、乡老、住持、众姓殚精竭虑,共同完成;四记梓潼帝君灵验,且人们信仰虔诚。
碑文三:
重修梓潼阁记
沅陵进士 魏绍
浦市祀文昌帝君久矣,康熙初年祀于卧云庵。举人李子皋、恩贡唐之命等迁于公所,其室褊小,不足以妥神灵也。
岁丙申,生员刘清、印天玙、谭峤、李文渊等欲式廓丕基,募化改造,同赴郡城,请序于郡守迟公煓,公欣然为引,捐俸以倡。有市民谭子芳发心助本,众等募化乡市,得百有余金,并付谭处,购木石砖瓦,鸠工命匠,除旧更新,殿宇成焉。前粮宪汪献扁(匾),府宪李挂对。继此,蒋、刘诸席,郝、邓诸公,月课赏贲,雅意作人。惟粮宪姚出罚锾百金有奇,买唐姓田为学田,契存泸库;买姚姓田为学地,契存沅库,延师以充膏火。公议除地租贰两为春秋祭费,余银为塾师学俸。其店地十间,除杨姓一间地租与管守者,为奉祀香火之资。
至丁卯春,新任粮宪王公敷贲,行香月课,见殿宇卑暗,文风难振,且右侧有余地,可作崇文书院,捐俸六十金,命绍偕首事生吴加锟、李文灏、张绍贤、罗万备等,商议重修正殿,以二殿作讲堂,造就人材。共醵金三百有奇,人心踊跃,阴有神助,不日成之。今当告竣之期,以助银姓名镌石,以垂不朽。
最后一通碑文的撰写者魏绍,字念远,虽为沅陵县人,但居泸溪浦市,家境贫寒,妻韩氏以女红佐之,虽饥寒交迫,仍苦读不辍,乾隆十年乙丑科得进士,任常德府教授,端品崇实,三载卒于官。碑文中提到的举人李子皋、恩贡唐之命、生员印天玙都在县志中有记载。李子皋为浦市人,清康熙(1684年)甲子科举,为人仗义疏财,凡地方公益事业均慷慨相助[3]254;唐之命,字尔咨,邑贡生,居浦市,童时遇土寇窃发,随父母窜匿乡村,市无义塾,与孝廉李子皋倡建文昌阁以居远近学者[5];印天玙,府学贡生。此碑文与前面两通一样,都记载有重修梓潼阁的原因和目的、集资过程、重修过程、神灵的灵验。
三通碑文呈现三个共同特征:第一,碑文撰写者及倡议者多为泸溪浦市当地家境贫寒的邑人,后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仕人、乡贤。李象珍、张尔楚、魏绍等都为当地科举文人。可见,文昌帝君的信众中也有乡绅文人及科举仕人,并且他们起到了倡议和带头的作用。第二,复修梓潼阁的物资基本为同乡、亲友所捐,也有地方官宦捐资送匾。《复修梓潼阁记》载:“亲友李、石诸君毅然为首,乡老高、杨等经之营之……住持之劳力施财,众姓之劳心拮据……”《重修梓潼阁记》载:“岁丙申,生员刘清、印天玙、谭峤、李文渊等欲式廓丕基,募化改造,同赴郡城,请序于郡守迟公煓,公欣然为引,捐俸以倡。有市民谭子芳发心助本,众等募化乡市……”可见,当时不同阶层的人都对文昌帝君十分尊崇,梓潼阁虽为道教宫观,却得到了官府的维护和支持。第三,信众对文昌帝君的信仰十分虔诚,都称帝君十分灵验。三通碑文都对文昌帝君的灵验做了重要记述。“则斯阁之建,乃其心之所乐为,无有觊觎者也,又何记焉?”“其夕,即有梦帝君马已备驾,将欲前征者,斯其验矣。”“人心踊跃,阴有神助,不日成之。”对文昌帝君的种种称赞,表现出文昌帝君在当时地位较高,得到民众的敬仰和信奉。
二、浦市梓潼阁碑刻铭文的历史记忆
浦市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当属清康乾至咸丰百余年间,在此期间,无论经济还是宗教文化都十分繁荣。仅乾隆年间《泸溪县志》中就记载有80余座祭坛、寺观,其中以浦市古镇居多。浦市民间有“72座古刹,99座坊”的说法,梓潼阁仅为众多庙坛中的一个。相比佛教寺庙,清代道教宫观的数量明显不及佛寺,在清代“崇佛抑道”的大环境下,梓潼阁得到推崇必有其特殊原因。县志记载的重修梓潼阁碑文很大程度上向我们透露了清代浦市道教的生存状态、道教文昌信仰的文治教化作用以及浦市民众的宗教生活与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
(一)浦市道教的传播
道教创始之初,湖南地区就有传教活动。《衡岳志》记载:“天师张道陵,尝自天目山游南岳,谒表玉、光天二坛,礼祝融君祠。”[6]22湘西地区传统道教具体传入时间史料上并未记载,但各地方志中多有描述道教的仪式、神灵及宫观。据1993年湖南省泸溪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泸溪县志》记载:“南宋时即在县城北建延禧观。明洪武时设道会司于县治东,后废。清雍正年间复设,以延禧观道士管道会司,民国时废。”[7]555泸溪地区早在南宋时期就有道士传教并建立道观。张泽洪先生把湘西归入广义的西南地区,因为湘西少数民族多为西南川、滇、黔、渝少数民族扩散而来,且道教与当地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互相渗透。地处沅水流域中游的浦市古镇,倚靠便利的水运交通,“上而滇黔,下而常岳”,在云南、贵州等地传道的道士于是顺流而下进入沅水中游。如元代道士陈致虚《上阳子注〈悟真篇〉序》云:“仆承师授,寝食若惊,首授田侯至阳子。遍游夜郎,邛水、沅芷、辰阳、荆南、二鄂、长沙、庐阜、江之东西,凡授百余人。”[8]972泸溪浦市的道教极有可能是从滇黔一带通过沅水传播而来,且以正一道为多。1993年湖南省泸溪县志编撰委员会编《泸溪县志》载:“县境道教分全真派(又叫清净班)和正一派(俗叫火居道士)。火居道士可娶妻生子如常人,但要诵道教经典,尊奉张天师,历年秋后主持祈神除灾的清醮、皇醮,各有施主,不许争夺。”[7]555浦市道教派别基本为正一派和全真派,每年都有道教祭仪。据碑文,浦市道教宫观类型包括梓潼阁(文昌阁),同时县志多有记载延禧观、三元宫、玉皇阁、玄天殿、九母殿、万寿宫等。其所祭祀的神灵都为道教神仙体系中的各位神灵。清代道教宫观除历朝遗存下来之外,还有各省商人来浦市经商所建立的会馆,也称宫观。最大的有万寿宫,福建客民所建,祭祀道教尊神许真君。但道教在浦市的发展没有佛教发展顺利,康熙朝以降,清廷对道教极力压制,导致道教生存困难。尤其是乾隆朝,清政府对民间道教宫观的修葺强加管控,修葺宫观必须上报当地督抚,请求同意。而湘西的流官,代表朝廷崇佛抑道理念,干涉道教活动。然道教文昌信仰在浦市的信众多,且民间和官府共同捐资修建,主要原因已在《重修文昌阁碑记》中有所体现:“而其聪明正直,能崇吾儒大伦,不逐异教,故海内士之敬礼者,自至圣先师外,莫不致敬于神,而不敢以他神俑人目之。”虽然在正统儒学家眼中,道教被称为“异端”,但碑文中记载的道教文昌神的神职与品性与儒家文化兴文教、昌道德匹配,故文昌神是“先师”孔子之外,海内外都崇敬的神灵。民国时期,浦市因战乱和匪患,当地的道士逐渐退出民间活动,走向衰落,直到改革开放后,道教才开始逐渐复苏。
(二)浦市多元信仰互融与信众生活
浦市“下湾遗址”足以表明新石器时代浦市地区就有人类生活。汉代以前就有“瓦乡人”与瑶族人共同生活于沅水中游。“瓦乡人”信仰盘瓠和辛女,二者都是农业社会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对象。除此之外,浦市还存在树神崇拜、岩石崇拜等其他自然崇拜,还有土家族“天王信仰”及苗族巫傩信仰等少数民族信仰。自唐朝开始,泸溪已建有佛教寺庙,至明清已有百余座,其中浦市最多。碑文《重修梓潼阁记》载,康熙初年浦市已经祭祀道教文昌帝君。且清乾隆《泸溪县志》中有更多道教宫观的记载:“延禧观在县治北,正间造,嘉靖中复修……三元宫,在浦市河街,浙江客民公建;天后宫,在浦市西街,福建客民公建;九母殿,在浦市后街;三元宫,在浦市蛾眉湾,明万历年间,浙客公建,兵燹后基地为人强据。”[2]这些宫观所祭祀的神灵都为道教吸纳进入其神仙体系的民间信仰,并且都是随着客民的流入而进入浦市的。相比其他朝代,清代佛教和道教之间的冲突少,相互促进和交融的良性互动更多。
道教与佛教的共存和互融最直观的体现便是浦市盂兰盆会。盂兰盆会又称“中元节”,是融道教、本土文化和民俗艺术为一体的大型佛教祭祀活动。在盂兰盆会仪式环节中,佛教文化体现在“开坛”“诵经”和“放焰口”,而“过街”“化财”过程中,人们会用纸扎道教的“四值功曹”游街,最后烧掉以将民间情况反映到天上。道教与本土信仰的融合则体现在丧葬仪式上。《泸溪县民族志》中记载,泸溪瓦乡人安葬死者前几日需请道士念经超度死者,并且进行繁琐的丧葬程序。泸溪古属楚地,兴巫教,祭祀的鬼神繁多,巫教与道教祭祀中都有“谢龙神”仪式,久而久之二者部分融合在一起。浦市道教与“儒家信仰”的互融表现在道教的民间俗神信仰方面。在三通重修文昌阁碑文中,文昌帝君其实已经成为儒家文化渗入地方社会的桥梁,虽然不及孔夫子的威望,但其“能崇吾儒大论”且能“为国家昌景运,为千古昌文教”正是封建王朝的核心价值观。文昌帝君的文运职能,应清代科举考试所需。除此之外,清代邑人李涌在《重修城隍庙碑记》中记:“余惟城隍之祀为固国安民计,城以卫民,隍以卫地。”邑令王光夔在《重修河街关夫子庙碑记》中记:“关圣帝君历代尊崇,可谓极矣!但侯始终不忘汉室,仍称汉寿亭侯……我朝典礼加隆,埒于至圣。”城隍神、关帝这些道教吸纳的民间俗神以其符合儒家义礼而被朝廷大加推崇,同时也更加强化了道教教理教义对汉儒文化的吸收。浦市关夫子庙、城隍庙与文昌阁的祭祀活动都被纳入国家春秋二祭。
海外的中国学研究中说过“乡绅模式”,即将封建文人视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9]。这个观点在解释清代民间信仰方面有一定的说服力。清朝是我国最后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和科举制度发展到顶峰。湘西土司统治时期,只有土家族贵族子弟享有读书的特权[10],清代改土归流后,一些家境贫寒的土家族、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子弟逐渐得以入学识字。浦市少数民族文人在通过科举成为地方士绅后,更加坚信读书识字的重要性。他们对朝廷推行的文化制度十分尊重和推崇,并且带动地方社会的文治和教化。倡导重修文昌阁和建立“义学”成为乡绅们十分热衷的事情。康熙五十五年,张尔楚《复修梓潼阁记》中记载“楚履其地而忽焉……亲友李、石诸君毅然为首,乡老高、杨等经之营之……”而乾隆年间,魏绍与当地文人募化改造文昌阁,普通市民、郡守、粮宪等都捐资购砖瓦和良田,并在文昌阁旁建崇文书院,以振文风。除此之外,县志所记乡绅为浦市宗教寺观所撰碑文多达18通,描写宗教寺观的诗文17篇。可见,清康乾时期,浦市地区比起湘西腹地,受儒家文化影响更深,当地的文人十分重视文治教化,也热心宗教文化事业,在官府支持下大力兴修学宫、会馆、祠堂。浦市文昌碑文的记述反映了儒家思想对当地士绅乃至普通市民信仰世界的重新塑造。
(三)浦市官民“对话”与信仰变迁
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讲究“恩威并用”,禁止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陋习”,对某些利于统治的宗教加以利用,继续“神道设教”,扩大教化。然而在湘西这片王朝的“化外之地”,朝廷对其管理体现出强制和压迫。文昌神从蜀地梓潼神演变而来,最初也为民间信仰,后被道教吸纳,成为文昌帝君。文昌信仰在民间影响十分广泛,各地几乎都建有文昌庙,尤其在明清时期,文昌祭祀之风盛行。正因如此,招致朝廷对文昌帝君的争论,清康熙、雍正朝时,文昌帝君祭祀被控告为“淫祭”并行文禁止[11]。同样,道教在清代基本上处于停滞和衰落状态,因为乾隆皇帝对道教事务的管理十分严格,禁止民间擅自兴修宫观,并把道教张天师、文昌帝君等神从神乐观撤除出去[12]。无论是文昌信仰还是整个道教,在清代上层社会都受到怀疑和抑制,但民间并不如此。
张践[13]先生提到,清政府对正统宗教管理严格而使佛教、道教失去了活力,思想和组织退化,而这正是民间信仰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从碑文可看出清代文昌信仰在浦市的信众阶层广泛,有官府、文人、乡绅和普通百姓。康熙五十五年《复修梓潼阁记》载:“况梓潼帝君血食,载在祀典,不独主持文运,兼司人间禄命,其敬信之也素矣。”乾隆二十年《重修梓潼阁记》也提到春秋祭费。由此可见,浦市文昌帝君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载在祀典,而朝廷正式将文昌帝君纳入国家祀典为清嘉庆六年之后。这说明浦市地方官府在朝廷之前已开始推崇文昌信仰,地方官府的推崇方式即为捐资修葺、载入祀典。况且康熙四十三年开始对湘西地区改土归流,浦市处于苗疆边界,历来交通便利,更容易改造。利用信仰阶层广泛且融“儒释道”三教的文昌信仰来“儒化”民众不失为一种适当的方式。文昌信仰赢得当地贫寒子弟中文人的推崇,而文人乡绅正是介于官府和民间的桥梁。可以说,文昌信仰在浦市是官府和民众和谐沟通的一个平台,也是清政府对湘西“王化”的一种方式。而白帝天王信仰则是官府为缓解流官汉民与少数民族冲突的另一个通道。在清代改土归流期间,苗族边墙的重修让汉族与湘西少数民族得不到沟通,矛盾更加尖锐,嘉庆年间爆发了著名的“乾嘉苗民起义”。苗民无所畏惧,唯独害怕鬼神,官府利用这一特点提倡“以神道设教,补政令之不及”,因湘西土家族、苗族和汉民同信天王神,一些冲突得以调适[14]。之后,统治者尤其重视白帝天王信仰,天王庙在众多寺庙中保存完整。浦市毛家坡的天王行宫就是最好的例证,其建筑规模宏大,有三进,共1 000余平方米,空坪两廊建有戏台。浦市人常把“白帝天王”视为民间“最高法官”,百姓有冤时就去天王行宫求神申冤。
文昌信仰和白帝天王信仰都在官方和民间的关系层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经过统治者的利用后发生了一些变迁。从浦市文昌阁碑文及县志记载的寺观来看,清代浦市多元宗教最大的变化即为信仰神灵的“儒家化”。无论是清代推崇的佛教还是抑制的道教,它们都以符合儒家思想为重要依据,虽然浦市信仰种类多元,但信仰思想却趋于儒家。并且清代改土归流后,流官政府在湘西各地多修学宫、会馆、牌坊和祠堂,十分注重忠孝伦理,各种信仰也直指忠孝伦理。虽然民众祭拜不同的神灵,但背后的宗教义理渐趋同一。这在统治阶级加强巩固国家政权方面可谓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在繁荣多元文化的层面上则不是一种很好的趋势。梓潼阁碑文记载的民间与官府的互动以及趋于儒家化的信仰体系,成为清代浦市宗教的一大特点。梓潼阁碑刻只是外在的记忆方式,民众重文情感才是内在的记忆,所以即使现今文昌帝君被浦市民众遗忘,但背后折射的重文教的思想始终都被人们所选择。碑刻唤醒记忆,同样唤醒遗忘,而人们在记忆中不断选择。
三、结语
清嘉庆六年后,文昌帝君祭祀升为中祀,地位几乎与孔子并尊,民间出现“北有孔子,南有文昌”的说法。清代浦市文昌信仰成为流官政府“王化”民众的一种方式,县志记载的文昌阁碑文不仅透露出文昌信仰本身的影响范围,还透露出浦市地方道教的传播历史和浦市民众宗教生活记忆及官府与民间的互动记忆。在现今浦市人们口中,文昌帝君已经近乎陌生,浦市当地的文昌阁也在历史的浪潮中毁坏消失,仅有部分年老的乡人记忆中残存着文昌阁的历史。在民众心里,他们求功名所祭拜的神灵大多为佛教的文殊菩萨或衍变而来的文官菩萨,但又将文才好的人称为“文曲星下凡”。正如前文所述,碑文一方面是“历史记忆”,一方面又是“历史失忆”,人们记忆的总是人们选择的,人们共同选择的便是社会最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