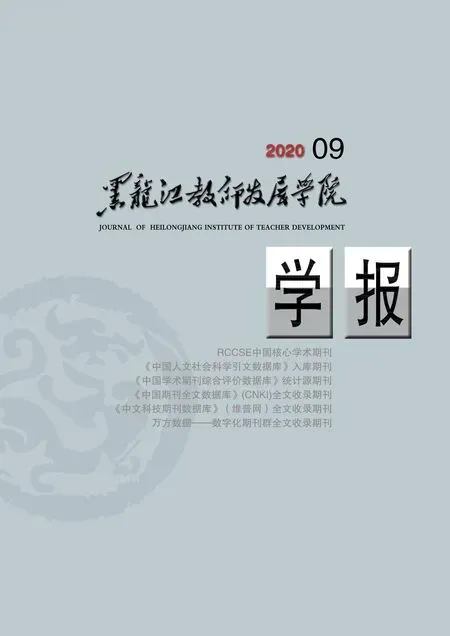大地之子的民族文化信仰
——以哥布《神圣的村庄》与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为例比较分析
杨 娇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6)
一、哥布与吉狄马加诗歌的共同特征
(一)民族文化信仰在诗歌里的体现
1.哥布诗歌里体现的民族文化信仰
哥布作为新时期哈尼族的代言人,用哈尼语惯常的神话思维表现庞大而复杂的现实生活,书写着本民族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面对如今多元共生的文化处境和相对边缘弱势的少数民族文化,哥布始终恪守着民族文化信仰,坚持用母语写作;自觉调整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碰撞和冲突,为民族文化信仰振兴奔波。以诗歌为例:
《诗人:“有一天祖先怆然出走”》(节选)
我们的吟唱就要转换新的曲调
我们的诗歌就要开启新的篇章
诺马阿美 传说中的故乡
哈尼人在那里发祥
有一天祖先怆然出走
……
不知未来何在 去向何方
我们的祖先 从此走走停停
回望故土 内心悲凉
哥布在此诗中向世界宣告着:“传说中哈尼人的发源地‘诺马阿美’。”诗人对本民族历史上艰难而漫长的迁徙过程,道出了“内心悲凉”的沉重心声。这次漫长的迁徙反映了哈尼族祖先的真实生活状况和基本精神风貌。他用母语写就的长诗《神圣的村庄》,这种原生态的书写最能体现祖先的节奏、语言和思想,传承哈尼族的文化信仰。正如哥布在《神圣的村庄 后记》中写道:“在我近30年的文学创作历程中,虽然谈不上著作等身,却也积累了一定作品,但从来没有像这部长诗一样给我带来成就感。有了它,我觉得上对得起祖先,中对得起父老乡亲,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它被刻录成光盘,进入哈尼人的日常生活。”《神圣的村庄》以吟唱形式行笔,诗的开篇就设定了人物表,通过莫匹、咪谷、女巫、诗人等逐一的念唱,蘑菇房、寨神树、苦扎扎等共同勾勒了一幅和谐的农耕文化场景。凡俗的尘埃又怎能表达诗人对母族的热爱,他的长诗深情无限地切入对民族文化信仰的歌唱,族群的生活被安静地雕刻在诗歌的纹理中。又如《咪谷:温暖的诺马阿美》中写道:“祖先的故土/诺马阿美/传说哈尼人在那里发祥/……/神话般的土地/充满秘密的温情/但祖先在那里住的并不久长/……/于是 祖先牵着半大孩子背井离乡/于是 背着最小孩子走向远方……” 哥布以宏观视角对哈尼族人的神话传说、民族文化信仰等做了书写。寨神居住的地方,哈尼人的丧葬习俗、吟诵祖先等都打上了祖先崇拜的烙印。诗人在这两首诗中都写到了祖先与故土“诺马阿美”,从中可以窥见哈尼族人对祖先的尊崇。诗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哈尼族祖先崇拜这一坚定的民族文化信仰。哥布诗歌中还体现了哈尼族的多神崇拜,其民族文化信仰味儿十足。如:
《诗人:“那永恒而神秘的帝王”》(节选)
多少年来 寨神一直是
我们精神上真正的教皇
……
多少年来 在寨神的佑护下
我们丰衣足食 人丁兴旺
寨神是一棵树 矗立在寨神林
寨神又不仅是一棵树
它是天 地 还可能是村脚的水塘
……
在《第二章:寨神的祝词》里,哥布对哈尼族人崇拜、尊敬的寨神进行了刻画。写出了一个有寨神居住的村庄是具有神性的、和谐的、安详的。寨神是哈尼族人民的守护之神,与寨神一起生活的地方才是灵魂安放之所,才是哈尼族人心灵和精神的故乡。正如诗歌里所说,寨神不仅是一棵树,它是天、是地,还可能是村脚的水塘。可见,在哈尼人心中寨神无处不在,寨神的灵和形已经幻化成每一个哈尼族人的精神力量,成为了他们坚不可摧的民族文化信仰。
诗人对一个拥有众神守护的村庄这样描写到:“我们的家在红河岸边/……/寨门撒上狗血/把所有的邪恶赶出村庄/寨门悬挂大刀/把所有的妖魔阻挡/六月苦扎扎节 盖起了/迎接天神的女儿我咀的秋房/……/我们生活在众神簇拥的村庄/不论别人怎么想/我们内心充满了宁静和安详”(《莫匹:“我们生活在众神簇拥的村庄”》)。哥布对村里的民族文化信仰进行了吟唱,即哈尼族人认为寨门撒上狗血、挂上木头的刀剑就可以辟邪、求安康。此诗的最后三句朴素而真切地写出了哈尼族人认为只有生活在众神簇拥的村庄里,心里才会无比的踏实、宁静和安详。又如:“我们的寨脚插满了电杆/我们的寨门迎来了电的缰绳/电神带着众电回我家/亮神带着光明回到故乡……”(《当家的女人:“我们的寨子是电的舅公”》)这一首诗是对众神之中的电神和亮神进行了生动的描写。哈尼族人对这两位极具现代化的“神”充满了无比的感激和崇敬之情。能够拥有如此的情怀,说明多神崇拜这一民族文化信仰已融进哈尼族人的血液,刺激着他们身上的每一根神经。形形色色的寨神、电神、亮神等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神崇拜。多神崇拜在哥布诗歌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展示了哈尼族坚定的民族文化信仰。
2.吉狄马加诗歌里体现的民族文化信仰
吉狄马加是彝族新时期的代言人,从80年代初开始创作。他对民族文化信仰的探求是其诗歌的主旋律之一。随着文化寻根运动的开展,人们需重新塑造精神文化信仰。于是出现了大批书写民风民情的作家,以及以刘绍棠、冯骥才、汪曾祺为主的具有民风民情的作品。继而崛起的“朦胧诗派”,如北岛、舒婷、食指等一批诗人对人性、历史、哲学的拷问……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深受他们的影响。
《星回节的祝愿》(节选)
我祝愿蜜蜂
……
长眠的祖先
到另一个世界平安
我祝愿这片土地
……
神灵啊,我祝愿
因为你不会不知道
这是神灵最真实的情感
吉狄马加通过把自己诚挚的情怀寄于脚下的土壤来歌颂自己的民族。他超越表层描述而进入对民族文化信仰、精神世界的深层思考,努力地揭示着彝族这个古老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信仰通过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等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通过火把节这一意象表达了对祖先和各神灵的可亲可敬之情。用上述诗中的话说就是“这是神灵最真实的情感”。他在诗《含义》中对民族图腾崇拜的真正意蕴进行了一次追根溯源的探求。“谁能解释图腾的含义?/其实它属于梦想/假如得到了它的保护/就是含着悲哀的泪水/我们也会欢乐地歌唱!” 他透过民族图腾,从中思考图腾的内涵:其实它属于梦想。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将一种美好的祈愿注入到自然景物中,以景抒自我之思,并希望得到图腾的庇佑。这就是图腾内涵属于梦想的一种体现。
哥布主要通过写祖先、寨神、天神、梯田、公路、红河等众多具有哈尼族特色的意象来歌唱他对本民族文化信仰的认同。诗歌或回忆、或赞颂了哈尼族祖先的智慧和民族文化信仰,而正是这种民族文化信仰的力量成为了哥布诗歌的细胞和血液,濡养着他的诗歌之思。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彝族是独特的,他们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对土地的基因、民族文化信仰有着奇异的理解和独特的信念。而这一切都根源于彝人心里虔诚的图腾文化信仰。在其诗作中,他将自己在大凉山生活中所见到的人、景都展现出来,进而来体现彝族的民族文化信仰。他的诗歌创作引领了倮伍拉且、阿库乌雾等后继彝族诗人,并成为新时期彝族汉语诗歌书写的开拓者、民族文化信仰的传承者。
(二)诗中民族文化信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沉忧隐痛
自然越美,自然的守望者似乎越显得悲哀,这源于少数民族特有的审美敏感。这种悲沉的特点不只是诗人的个人气质,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缩影。
1.哥布诗中民族文化信仰反映了哈尼族的沉忧隐痛
哈尼族文化信仰的载体很多,有神话传说、诗歌、故事等,从毛佑全、朗确到哥布,民间诗歌、文人诗歌一直交相辉映,共同促进了哈尼族文化信仰的发展。
哥布的诗集《神圣的村庄》都是对各种景、情、物的关切。他满怀热情地感受着“诺马阿美”、族谱、寨神的存在,体会着这些事物存在的久远、伟大。总之,一切景物都融入了诗人的字里行间,时时浮现在诗人的心里。如《当家的女人:“农事对着你挤眉弄眼”》:“年轻人喜爱的寨神节/无可争辩地光临 浩浩荡荡/……/往前走农事对着你挤眉弄眼/往后走农事对着你嬉皮笑脸/来到村头 农事/揪着女人的头发不放/去到寨脚 活计/拖着男人的大腿纠缠/所有的节日 都是/别人的玩场/……”这首诗写出了即便在隆重的寨神节里,哈尼族妇女仍要面对密如头发的活计。正如诗中所说“所有的节日 都是/别人的玩场”。哥布诗歌作品中感情基调以伤感为主,那为本民族担忧的沉忧隐痛是如此深沉。然而,哥布努力地张扬一种田园式的乐观主义精神,将人性纯真的一面展示给读者。哈尼族妇女善良忠实的民族性格得益于本民族的文化信仰。诗人的悲沉源于对身处社会底层的穷苦哈尼族妇女的同情。她们是伟大的,没有因眼前无尽的农事一蹶不振,心窝里满是那坚不可摧的民族文化信仰。
哥布越是想极力掩饰这种沉忧隐痛,其情感越是在描写青山绿水的静美、族群的未来走向、当下民族文化信仰所面临的困境中显露无疑。哈尼族人用勤苦和智慧创造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仰,却鲜为人知。就如哥布曾说的一样:“大多数哈尼人生活在哀牢山的崇山峻岭中,艰难的生存环境使这个民族多愁善感。”
2.吉狄马加诗中民族文化信仰反应了彝族的沉忧隐痛
吉狄马加的诗歌中蕴含着坚定的民族文化信仰,以悲沉为基调。如诗中写到:“我是口弦/永远挂在她的胸前/从美妙的少女时光/到寂寞的老年 ……/把忧伤和快乐/倾诉给黑暗/我是口弦/要是她真的溘然离开这个人世/我也要陪伴着她/最终把自己的一切/拌和在冰冷的泥土里面……”(《口弦的自白》)。 诗是民族文化信仰的代表,我们不能把吉狄马加的悲沉看成是纯个人的。他的诗浸透着对民族命运的焦忧,对英雄后裔和祖辈悲情的苦痛。事实上,他代表了整个彝族的辛酸史,透露出了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创伤。诗中的“口弦”已是民族文化信仰的化身,他把与人生死相依的口弦化作了一块悲哀的土地、一个悲哀的民族。
此外,吉狄马加在《鹰爪杯》《彝人之歌》中多次提及彝族的鹰图腾。“鹰”意象代表着坚定的彝族文化信仰,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它不仅表达了彝人对本民族文化信仰的虔敬,而且承载了一部彝族发展史。此外,“鹰”寄托着母族的情感,表达着彝人的愿望。它体现了诗人对民族文化信仰的独特感悟,并以此来探求彝族文化信仰的深层意蕴。吉狄马加用深思和痛苦的咏叹调写出了英雄的、光荣的凉山彝族。虽然这个民族是多灾多难的,但是彝人的灵魂是美丽而忧伤的。吉狄马加是伟大的,他通过诗的意象塑造,喊出了一个民族灵魂里最本质的声音。这一撕心裂肺的呐喊,通过一个小小的口弦充斥着多少的辛酸和悲痛,那是专属一个民族的沉忧隐痛。
在两位诗人的诗歌中,都包含着对民族文化信仰发展的担忧和隐痛,不以自己的出生、观点和身份凌驾于别人的生命之上。然而,诗歌中的人、景总能透过诗人的内心,展现一股挥之不去的忧愁。这些诗里的人、景越美,似乎以此孕育的民族越发显得悲哀,那都是源于以悲沉为基调的民族文化信仰。
二、哥布与吉狄马加诗歌的不同特征
(一)在传承民族文化信仰上面临的不同困境
我们要对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的生存前景进行理想性的意义剖析,就必定要触及“全球化”,以此来深入地探求当前少数民族文化信仰面临的困境。各民族文化信仰相互交融,强势文化的扩张和诱惑越来越威胁着少数民族文化信仰。
1.哥布诗歌在传承哈尼族文化信仰上面临的困境
哥布在文学刚起步时就选择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归依。他深刻地认识到坚持用母语创作能为民族文化信仰增添活力。于是,哥布做了一个惊人之举,回到母语写作上来,这意味着一切从零开始。
哥布面临的首要困境是从已经收获颇丰的汉语竞技场,进入到完全陌生且无竞争的领域。这不仅会面临着换笔之痛,还会给诗人带来换语言的不适。其次他面临的是发表的问题,只有发表,诗人才得以存在。作品写出来,主要是为了有相应的发表平台,能对人类社会产生相应的影响。哪怕写哈尼文诗歌不能走向全世界,为自己的民族而歌也是很好的选择。但目前好像连这条唯一的道路也行不通。面对这一系列的困境,哥布没有退缩和畏惧,而是在不停地思索着如何才能在这重重的困境中找到出路。
在回归母语写作的荆棘路上,倘若哥布用母语写成的诗歌无处发表,那么也就意味着找不到相应的读者。没有相应的读者,就没有哈尼族文化信仰的传承者,这是令哥布最忧心的问题。此外,即使有地方发表这些诗歌,这些用哈尼语写成的诗歌,也基本找不到读者,其受众仅局限于哈尼族这个狭小的领域。哈尼族人能在生产生活中熟练使用哈尼语,但多数人却根本不知道哈尼文。这是哥布面临的又一困境。于是,在哥布努力地摸索和思考后,他找到了一种更为变通的方法——听的艺术。换句话说,哥布的诗歌要以歌谣体的方式存在和传承,那是用来歌颂的。作为当下的母语写作者,他极力想要用母语去表达。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一个缺乏读者的诗人将会多么孤寂和压抑。还有一个问题是要不要将哈尼族母语诗歌翻译为汉语。如此一来,翻译的工作又该由谁来承担呢?为了可以照顾哈尼语和汉语的两个读者群体,哥布决定对其作品《母语》和《遗址》采用哈尼文和汉语的对照方式出版。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创作,便直接转换为用哈尼文、哈尼语思维进行诗歌创作。虽然,这些用哈尼语思维创作的诗歌被翻译为汉语后距离汉语诗歌的欣赏习惯更远了,但是它们有着来自祖先的节奏、语言和思想,能够传达哈尼族文化信仰深处的很多东西。
我们永远无法读懂哥布笔下那个用哈尼语构筑的“神圣的村庄”,那是来自一个民族底层的“秘密”。作为汉语读者的我们,怎样才能读懂其中意蕴呢?就如同于坚曾说过的一样:“语言中暗藏边界,我永远拿不到护照。”哥布在于坚等的鼓舞下,坚定了从事史诗性母语的创作。于是,他用哈尼文写成的一部名为《哟咪哟嘎,哟萨哟窝》的长诗,用汉语翻译为《神圣的村庄》。在对本民族文化信仰的传承上,哥布注重继承传统文化,并跟随时代对传统文化进行建构。他的地域性写作展现出对民族文化信仰的理性反思和重建,对民族文化信仰的追忆与重塑在如今多元文化的塑造中独领风骚。从哥布多年的母语诗歌创作史可以看出他对回归、重塑哈尼族文化信仰的坚韧品格和历史担当。哥布对民族文化信仰如何走出困境的探索结果是进行母语创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传承哈尼族文化信仰。
2.吉狄马加诗歌在传承彝族文化信仰上面临的困境
吉狄马加担心彝族文化信仰将在全球化浪潮的濡染下被同化甚至异化。因此,他常常用诗作表达对彝族文化信仰传承的隐忧。可见,要怎样才能在千变万化的全球化浪潮下使彝族的文化信仰免遭同化或异化是吉狄马加面临的首要困境。吉狄马加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担当,因而他对当前民族文化信仰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刻的思索。他清楚地认识到民族文化信仰的发展和进步急需外来文化的促进和融合。正是因为对母族的这种复杂的情感,才使得吉狄马加的诗既是传统的、本土的,又是世界的、现代的。因此,我们才能够读到《口弦的自白》《猎枪》《被出卖的猎狗》《头巾》等极富彝族文化色彩的诗歌,也才能够读到如《题辞——献给我的汉族保姆》《白色的世界》《黑色狂想曲》等具有多重文化语境的世界性诗歌。在传承民族文化信仰面临的困境中,吉狄马加认为诗人应当具有一种全人类的视角。他对大凉山、非主流文化的认同和坚守,也是从民族文化信仰的边缘地带开始的。作为一个民族作家及诗人,他不但受过现代教育的濡养、阅读了大量非洲和拉丁美洲诗人的作品,而且研究过西方的各种艺术思潮和流派。他的视野扩大了,目光也变得深邃和具有穿透力。我们能时刻感受到他那被认同和接纳的强烈愿望。当然,吉狄马加通过《一个彝人的梦想》表达了对彝族文化信仰的朴实、深沉、凝重。在归纳人生的经验和旅途上,吉狄马加对自己的民族有着深邃的感情,是彝族忠实的儿子。作为一个坚持传承本民族文化信仰、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精华的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世界的。在诗里,吉狄马加对诗歌有着独特的追求,融世界性、传统性、民族性于一体。
(二)哥布与吉狄马加诗歌在传承民族文化信仰上的态度不同
哥布与吉狄马加在传承民族文化信仰上,有着不同的态度。哥布进行的是母语文学的创作,其创作面临着艰难的困境。一方面是表达方式固化、表现手法和内容单一。在《神圣的村庄》里,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吟唱的方式,读来实有几分乏味。然而,吉狄马加却艰难且执着地寻找着能够沟通时代精神和彝族文化信仰的表达,追求着个性化的诗语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二是文化视野仅局限于哈尼族这片狭小的土地,现代性和世界性意识薄弱。如哥布所说:“对,是大山里的哈尼族群众,我是在为他们工作,只要他们能够听到我的诗,我已经十分欣慰。我并没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走向诺贝尔文学奖的远大理想……”虽然哥布的母语写作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仍非常有意义。吉狄马加则与之不同,他绝不会将自己封闭在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中,而是力求走向广阔的地带,从其他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他走出了大凉山的山谷,以一种世界和现代文化的眼光去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这样,他才能够把握本民族文化信仰的精髓。吉狄马加的诗歌较之哥布最大的不同是他在关注民族性的同时,更强调人类性、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视野宏大。
少数民族文化信仰的复兴需要更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人来共同完成,更需要多民族的共同努力来实现。
三、结论
由于两位诗人所处的民族文化信仰背景不同,他们所表现出的对本民族文化信仰的传承和发展的情感底蕴也是不同的:哥布是汉语诗坛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生活在哈尼族这个曾经历艰难迁徙的民族。吉狄马加处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寻根文化和文化反思的推动下,他的诗歌体现了民族诗人对本民族文化信仰的自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宣扬,对现实奋进的庄重宣告,其格调昂扬向上。他的诗歌饱含着彝族悠久的文化信仰,彰显着民族文化信仰复兴的豪放之气,流动着人类的灵性之光。作为民族文化信仰复兴的歌者,在民族发展的伟大时期,他们都以诗歌的形式来歌颂本民族的文化信仰,鼓舞自己民族昂扬奋发的精气神,并主张对民族复兴的生存状态和各种生命进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