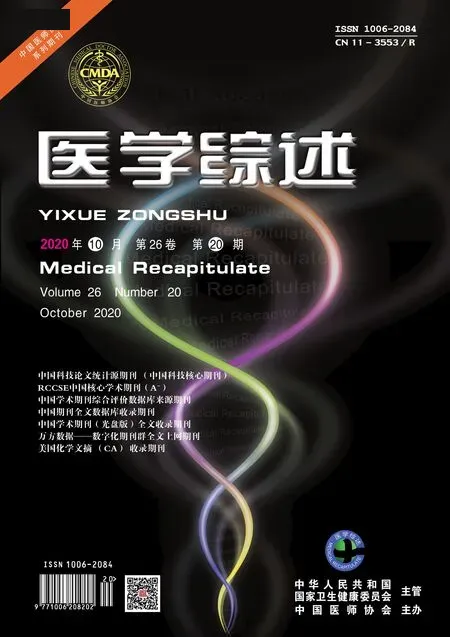癌性疼痛的中医治疗进展
陈雨,林青,刘传波,周天,胡凯文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肿瘤科,北京 100078)
目前,我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正逐年升高。据统计,2015年我国纳入统计的所有地区肿瘤平均发病率已达285.83/10万,且仍呈上升趋势[1]。随着癌症发病率的升高,肿瘤并发症的发生率也显著升高,如疼痛、出血、梗阻、转移以及消瘦等。其中,癌性疼痛作为恶性肿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据资料显示,我国癌性疼痛发生率约为60%,其中初诊癌症患者的疼痛发生率约为25%,而在晚期肿瘤患者中癌性疼痛的发生率可达80%[2]。当应用三阶梯止痛方案[3]或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提出的癌性疼痛指南[4]进行治疗时,大部分患者的癌性疼痛症状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治疗癌性疼痛常用的阿片类药物具有明显不良反应、耐药性和成瘾性。而且规范化治疗1~2周后疼痛仍控制不理想或不良反应无法耐受的难治性癌性疼痛患者,单纯西医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常需配合中医中药辅助治疗[5]。中医以辨证论治为理论指导,以中药内服、外敷、针刺、艾灸、拔罐、推拿以及穴位离子导入等为具体操作技术,不仅无明显不良反应、耐药性及成瘾性,还能有效降低爆发痛的发作频率,从心理层面缓解患者的精神压力。现就癌性疼痛的中医治疗进展予以综述。
1 西医认识及治疗
癌性疼痛的产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由癌细胞、外周组织、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免疫系统共同作用而产生[6]。癌性疼痛主要分为肿瘤相关性疼痛、治疗相关性疼痛以及合并疾病相关的疼痛。其中,肿瘤相关性疼痛包括肿瘤压迫、肿瘤浸润、肿瘤转移等,其在所有癌性疼痛中所占比例最高,为60%~75%;治疗相关性疼痛主要由手术和化疗引起,占10%~20%;合并疾病相关疼痛所占比例约为10%[7]。
目前,癌性疼痛的西医治疗主要以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指南为指导,通过对疼痛性质、疼痛原因、疼痛程度以及用药风险等方面进行评估,从而采取最为合适的治疗策略,包括选择合适的治疗药物、及时处理预期和治疗后镇痛药物产生的不良反应、提供心理支持以及关于防治癌性疼痛的教育等。
2 中医认识及病因病机
2.1中医认识 根据癌症的症状特点其可归为中医“积聚”范畴,又因“积属有形,聚属无形”,故癌症属于中医病名中的“积证”。《诸病源候论》在论“肺积”时曾提到“肺积脉浮而毛,按之辟易,胁下气逆,背相引痛,少气……”,与肺癌所致胸痛十分相似;论“肝积”时提到“肝积……因热气相搏,则郁蒸不散,故助下满痛”,可以理解为现代医学中的肝癌疼痛;《千金方》中所言“食噎者,食无多少,惟胸中苦塞,常病不得喘息”“其为病也,令人胸膈,妨碍饮食,胸痛彻背”均为食管癌疼痛的表现;《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腹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的论述与肠癌所致的腹痛、肠鸣泄泻较为类似;《肘后备急方》中葛洪的描述“治卒暴症,腹中有物如石,痛如刺,昼夜啼呼,不治之,百日死”说明了癌性疼痛患者的疼痛程度,而“不治之,百日死”则体现了病情凶险程度,是古代对癌性疼痛较为概括性的论述。
2.2病因病机 癌性疼痛的病因病机与所有疼痛一样,均可分为“不通则痛”与“不容则痛”两大类,即实痛和虚痛。程海波和吴勉华[8]认为,实痛的主要病机为癌毒内郁、痰瘀互结以及经络壅塞,其中癌毒内郁是病机之关键。而高萍和李芝秀[9]认为,正气亏虚是虚痛的重要病因,正气虚亏、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不足、经络失养导致不容则痛。
整体来讲,癌性疼痛的病因主要为邪实和正虚两大方面,结合历代医家对其理解,邪实多分为寒凝阻滞、热毒炽盛、痰湿凝结、瘀血阻滞、痰瘀互结、气机郁结以及气滞血瘀等;正虚则大致可分为阳气亏虚、阴血不足。其中,邪实所致的实痛多见于恶性肿瘤的早、中期,治疗以祛邪为主,而正虚所致的虚痛则在中晚期恶性肿瘤中更为常见,治疗时应注重补益正气。
3 癌性疼痛的中医治疗
3.1中药内治法 癌性疼痛的中医内治法主要根据患者疼痛性质,结合全身情况进行辨证论治,如寒凝阻滞者治法以温阳散寒为主,热毒炽盛者以清热解毒为法,痰湿凝结者以化痰祛湿为法,瘀血阻滞者则以活血化瘀为法。黄东彬和管静[10]认为,癌性疼痛多因寒凝导致,他们以自拟方附子汤(炮附子、茯苓、太子参、白术等)联合羟考酮缓释片对30例骨转移癌性疼痛患者进行治疗,2周后完全缓解16例,部分缓解12例,轻度缓解1例,无效1例,疗效明显优于单纯西药治疗。王赢健[11]将66例癌性躯体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以单纯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对症止痛,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自拟益肾骨康方(熟地15 g、骨碎补10 g、白花蛇舌草10 g、半枝莲10 g、白僵蚕10 g、山药15 g、山英肉12 g、丹皮10 g、泽泻10 g、茯苓10 g)口服治疗,2周后进行疗效评价。结果显示,试验组的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7.5%比60.8%),患者爆发痛次数明显少于对照组。叶慧青[12]对78例中医辨证为阳虚寒凝的癌性疼痛患者分别予以单纯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对症止痛治疗(对照组)及在西医止痛的基础上联合加味芍甘附子汤(芍药60 g、炙甘草20 g、制附子15 g、延胡索15 g、党参20 g、当归10 g、仙鹤草15 g、郁金10 g、菟丝子20 g、火麻仁15 g)加减治疗(治疗组),结果显示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92.5%比76.3%),平均镇痛维持时间明显长于对照组,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日均需用量明显少于对照组。曾志航[13]将63例中医辨证为脾肾亏虚型的中重度癌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按照三阶梯止痛原则予以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补肾健脾中药(黄芪20 g、党参20 g、补骨脂20 g、茯苓15 g、薏苡仁15 g、山茱萸15 g、枸杞15 g、山药12 g、白术10 g、炙甘草 5 g,并随症加减),结果表明联合中药治疗可明显减轻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带来的不良反应,并有助于延长止痛时间。
除自拟方剂治疗癌性疼痛外,亦有不少医家以辨证论治为基础,应用经方治疗癌性疼痛,且效果明显。阿依宝塔·努腊勒木[14]对50例辨证为肝郁气滞的原发性肝癌中度癌性疼痛患者分别予以三阶梯药物止痛及柴胡疏肝散加味联合三阶梯治疗,结果表明柴胡疏肝散加味联合三阶梯止痛对降低疼痛数字评分无明显作用,但可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缩短症状缓解时间。王德全等[15]将经方当归四逆汤与西药氨酚羟考酮片联合治疗癌性疼痛,结果发现止痛有效率高达96.6%(58/60),效果显著。倪红等[16]在治疗寒凝阻滞的中重度癌性疼痛时发现,与单纯西药治疗相比,吴茱萸汤合四逆汤加减联合硫酸吗啡缓释片在缓解疼痛、降低中医证候积分、改善生活质量、减少止痛药使用量以及减轻不良反应等方面均有显著疗效。张绍斌[17]认为,肝癌主要由气机阻滞、瘀血内停所致,对肝癌疼痛患者予以膈下逐瘀汤加减联合罗通定片治疗,效果显著。
3.2中药外治法 《理瀹骈文》中曾提到“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医学源流论》亦曰“使药性从皮肤入腠理,通经贯络,较之服药尤有力,此至妙之法也”,因为中药外用能提高局部血药浓度,精准作用于疼痛部位,并可以降低中药内服因胃肠道刺激导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故中药外用是目前中医药治疗癌性疼痛的最常用手段。王华伟等[18]将264例不同程度的癌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试验组予以中药止痛贴(延胡索、制马钱子、桃仁、红花、青风藤、冰片等)外用,重度疼痛配合吗啡;对照组予以安慰剂外敷,重度疼痛同样配合吗啡。结果显示,治疗后试验组患者的疼痛数字评分明显降低、疼痛持续时间缩短及爆发痛次数减少,睡眠时间明显延长。林燕等[19]将140例中医辨证为气滞血瘀型的癌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除均采用标准三阶梯止痛方案外,治疗组加敷止痛散(当归、川芎、桂枝、制乳香、制没药各30 g,血竭15 g,全虫、细辛各10 g,土鳖虫10 g;偏热性疼痛者,加酒大黄30 g、炒栀子15 g;偏寒性疼痛者,加桂枝30 g、细辛10 g)加减,30 d后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在疼痛治疗效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87.14%,对照组为59.99%)及便秘、恶心、呕吐、头晕、嗜睡、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方面,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陈施一骏等[20]通过复方癌性疼痛方(制川乌10 g、姜黄10 g、乳香10 g、白芷10 g、没药10 g、半枝莲20 g、白花蛇舌草20 g、龙葵10 g、大黄15 g、石菖蒲10 g、冰片3 g、醋延胡索10 g)中医定向透药法联合西药治疗40例瘀毒内结型癌性疼痛患者,结果发现其可明显减轻疼痛程度、减少西药用量和爆发痛次数及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罗先[21]将50例癌性腹部胀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予以基础治疗及丁香止痛方(丁香15 g、全蝎6 g、生蒲黄15 g、细辛15 g、薤白15 g、木香15 g、小茴香15 g、九香虫10 g、延胡索15 g、当归15 g、白芍15 g)或安慰剂于中脘、神阙穴位贴敷治疗,治疗7 d后发现治疗组的腹痛缓解率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疼痛数字评分显著低于安慰剂组。张双双[22]通过对80例癌症骨转移患者分别予以西医常规治疗及丁香骨痛方(丁香20 g、细辛20 g、肉桂20 g、炮姜20 g、全蝎6 g、穿山甲10 g、半夏20 g)或安慰剂穴位贴敷治疗发现,在治疗中重度骨转移癌性疼痛时,在阿片类药物的基础上应用丁香骨痛方穴位贴敷治疗可进一步减轻疼痛,疼痛缓解率可达89.5%,并可减少爆发痛发作次数、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减轻由阿片类药物导致的便秘;此外,丁香骨痛方穴位贴敷联合阿片类药物治疗可显著降低血浆内皮素-1水平。赵曼妤[23]将80例中重度癌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其中对照组予以常规西药止痛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的基础上加用消肿止痛散(细辛10 g、制川乌10 g、制草乌10 g、胆南星15 g、红花12 g、醋延胡索15 g、醋乳香15 g、肉桂10 g、炒没药15 g、徐长卿20 g、全蝎10 g、龙血竭10 g、生大黄12 g、降香12 g、干姜10 g、炮山甲5 g、冰片5 g、芒硝18 g)外敷,治疗2周后发现,治疗组的疼痛数字评分、24 h吗啡使用量显著低于对照组;爆发痛出现次数少于对照组。
3.3针灸治疗 在明代张三锡的《经络考》中曾有记载:“脏腑阴阳,各有其经,四肢筋骨,各有其主,明其部以定经”。针灸治疗局部疼痛自古有之,不同脏腑各自有其所主的经络,这为针灸治疗不同系统和部位的癌性疼痛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针灸治疗起效迅速、安全性高、成本低,现已广泛应用于癌性疼痛的临床治疗。张超等[24]分别对各34例骨转移癌性疼痛患者采用单纯针灸治疗(委中、肾俞、命门、华佗夹脊、大椎、悬钟、孔最、中都、太溪、筑宾、阴陵泉、地机、梁丘)和唑来膦酸对症止痛治疗,结果表明针灸组的疼痛缓解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唑来膦酸组(91.18%比55.88%),爆发痛次数显著少于唑来膦酸组,可获得的睡眠时间更长。黄颖[25]将62例癌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予以针灸(根据原发病灶和具体疼痛部位辨证取穴)联合三阶梯止痛药物治疗,对照组予以单纯三阶梯止痛药物治疗,治疗7 d后发现,试验组的总有效率为96.8%,对照组为87.1%。李扬帆等[26]将90例癌性疼痛患者随机给予循经特定穴电针配合雷火灸综合治疗(简称综合治疗)、局部取穴针灸治疗以及药物治疗,治疗7 d后发现,综合治疗组的视觉模拟评分改善程度最佳且镇痛起效时间最短,药物治疗组的视觉模拟评分改善情况优于局部取穴针灸治疗组,但在镇痛起效时间方面效果最差。Chiu等[27]对29项针灸治疗癌性疼痛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Meta分析得出,针灸对肿瘤直接导致的疼痛及术后疼痛效果明显,但对放化疗或内分泌治疗引起的疼痛疗效一般。
3.4中医联合治疗 大量研究证明,中药内服、外用及针灸治疗均对癌性疼痛有明显缓解作用,且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西药[28-30],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采用中医药联合治疗而避免使用西药,以期在获得良好疗效的同时保证患者生活质量。王林[31]将52例晚期肝癌癌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予以吗啡缓释片治疗,观察组予以莲莪止痛方(莪术、丹参、郁金、半枝莲各30 g,柴胡12 g,白术、白芍、枳壳、党参各15 g,威灵仙10 g)加减联合针灸及复方丹参注射液穴位注射(双侧心俞、肝俞、曲泉穴)治疗,4周后进行疗效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5-羟色胺及缓激肽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何爱国等[32]将120例癌痛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治疗组,其中对照组予以标准三阶梯止痛疗法,治疗组则根据患者疼痛程度分别予以消瘤止痛口服液、蟾乌巴布膏、针刺以及肌内注射氢溴酸高乌甲素针2~4项联合治疗,结果显示两组在镇痛方面疗效相当,但治疗后治疗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显著提高,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苏新平等[33]对111例气虚血瘀型骨转移癌性疼痛患者分别进行口服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治疗和补气活血中药口服、外敷联合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治疗,治疗2周后发现补气活血中药内外兼治联合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治疗可明显提高总有效率和患者生活质量,并可以减少盐酸羟考酮缓释片的用量。
3.5其他 随着对中医传统理论及现代医药科技的不断研究,癌性疼痛治疗方法层出不穷。部分医家认为,癌性疼痛是由于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通所致,故可应用耳穴的全息理论对脏腑进行调理,从而改善气血不通的状态[34-37]。疼痛与心情状态密切相关,疼痛会导致心情不佳,而心情不佳又会加重患者的疼痛感受。所以,有学者从中医五音治病入手,“对症下乐”;此外,随着中医药制剂发展水平的提高,有研究人员对中成药进行研究,亦取得满意疗效。张靖哲等[38]对112例消化道系统癌性疼痛患者进行穴位电生理治疗与联合耳穴压籽的疗效比较,结果发现联合耳穴压籽可明显缓解消化系统癌性疼痛患者的疼痛感,缩短疼痛持续时间,提高生存质量,效果优于单用穴位电生理治疗。陈晨等[37]将100例癌性疼痛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均予以西医常规基础治疗,其中治疗组在此基础上联合中医五行音乐疗法,对照组联合西方自然音乐疗法,1个月后对两组患者进行对比发现,治疗组疼痛症状的缓解情况及生存质量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彭志敏[39]、张春俏等[40]分别予以复方苦参注射液及康莱特胶囊单用或联合西药对症止痛,结果发现上述中成药对癌性疼痛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并可明显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4 小 结
癌性疼痛因其高发病率和难治性极大地影响患者的生存质量,打击患者与肿瘤积极抗争的治疗决心,从而影响肿瘤的整体治疗效果。因此,亟须寻找更为有效且不良反应少的癌性疼痛治疗模式。单独应用中医治疗时,在与西医标准止痛方案疗效相近的前提下,中医药治法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当中医治疗联合西医止痛方案时,联合治疗不仅有更好的疼痛治疗效果,而且在生存质量、止痛药剂量、爆发痛次数方面均明显优于单纯西医治疗,获益明显。综上可知,中医治疗可以根据患者不同情况进行辨证施治,为不同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并可以显著提高治疗过程中的生存质量,疗效确切。然而,中医治疗癌性疼痛的机制尚未阐明,未来需增加多中心、大样本、严方案、循规范的机制研究和高质量临床疗效研究,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方案在癌性疼痛治疗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