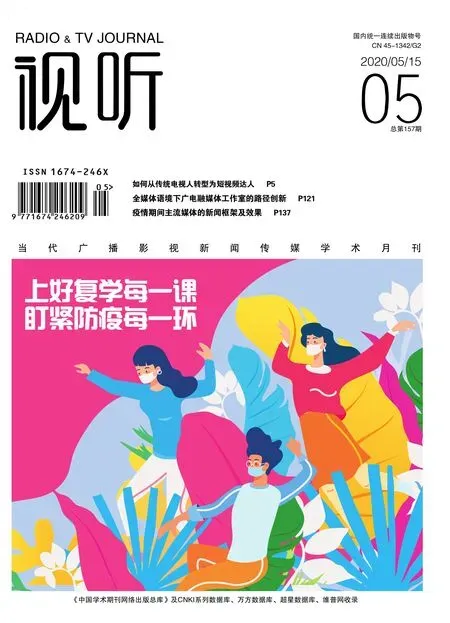浅谈新媒体环境下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 费璇 徐明明
1997年,美国学者迈克尔·戈德海伯提出“注意力经济”这一概念,“注意力”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媒体行业由此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革。在形式方面,媒介融合成为大势所趋,表现形式更加丰富生动的融媒体逐渐取代报纸、广播、电视等单一媒体的地位;从文本内容来看,更讲求故事性的“非虚构写作”势不可挡,电视文本话语也更强调叙事,以求抓住受众的眼球。这些变革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媒体人在互联网时代审时度势的结果。
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带来新一轮革命。互联网普及之初,美国网络研究专家埃瑟·戴森认为“网络会对人类机构带来深刻变化,而对人性则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成立值得推敲。
由技术更新引发的革命已不仅仅是一场媒介革命,更是一场社会变革,从社会结构到人性,都被新的技术逻辑支配驱动。这场风暴中,所有媒体都要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受众的意愿要求上去。
一、“动机沟”与受众的媒体选择
新媒体的低门槛赋予受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而事实是,在信息的滚滚洪流中,受众仿佛一叶扁舟,单薄弱小。一方面,受众被更加精密复杂的媒介机器控制,而忙碌的人群没有精力去筛选,面对海量信息无所适从,也只能被动接受,这也解释了为何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推送新闻如此火爆。另一方面,在视觉媒介中丧失思考能力的受众也在主动放弃自己的选择权,主动拥抱轻松娱乐的媒介内容。
这两方面共同描摹了当代受众“懒惰”的群体画像。从这类受众的需求入手,媒介应该提供“快餐型”内容产品,去满足受众“即时性”消费的需求。然而各类门户网站、新闻APP 界面繁冗,令人眼花缭乱,广告、页面弹窗、骇人听闻的标题党映入眼帘,用户不能一眼看到自己需要或者喜欢的内容。服务类平台也是一样,以淘宝为例,在成交金额掩盖下,“双十一”的参与热情逐渐下降,这与淘宝界面友好性降低有关,参与优惠的方式过于繁琐,许多用户因为“怕麻烦”选择退出。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甘愿接受“肥宅”的人设,动机沟的存在将受众的需求类型一分为二,前面所述的娱乐消遣型需求归为底层需求,而对自我提升的需求则更为高级。正是看到了部分受众自我提升的需要,以知乎、分答为代表的知识付费型应用日益崛起。但是这类平台的造假、雷同问题也逐渐显现,用户“认知盈余”的生产积极性衰退,许多回答也以调侃、戏谑为目的,平台甚至成为软文广告的宣传渠道,这对以专业性、知识性为招牌的平台来说是巨大的伤害。
喜马拉雅、樊登读书等语音类知识付费APP 成为传媒行业新风口。因为音频天然的伴随性特征,使得人们即使是在忙碌时也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充实自我,既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又解放了人体感官。
然而,这类平台也遇到了发展瓶颈。知识付费型的内容不适合做音频,首先因为音频的转瞬即逝性与知识的深度记忆要求相冲突,往往不能留下深刻印象。其次由于欠缺直观性,很难帮助受众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而这类平台的内容又多以成功励志学、职场生存策略等心灵鸡汤文为主,本身并不具备很强的科学性、知识性,久而久之,想获取知识的受众会发现事与愿违,并且受到会员付费机制的“驱逐”,往往选择退出。这样的平台在热度过后,用户沉淀少之又少。因此知识付费类媒体更应致力于垂直领域,深耕细作,打造以自身为核心、辐射各个地域的会员圈层,利用人脉、知识双轮驱动,吸引用户并形成较高的忠诚度。
二、受众焦虑与媒体的内容生产
相比于专业知识付费平台生存的窘态,不生产任何知识,只依靠贩卖焦虑为生的咪蒙火遍大江南北,商业变现能力令人惊叹。这反映了用户的媒介素养问题——对内容的辨识能力低,点击行为大多是依靠社交媒体平台的分享,进而形成病毒式的扩散传播。因此,专业性的平台也要重视抢占社交入口,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而“咪蒙之死”阐述了“渠道为王,内容为金”的道理,不注重内容生产的质量,利用受众的猎奇、求异、从众等心理捏造故事,制造爆点,玩弄受众心理情感,就是“玩火自焚”。可见,媒体仍旧是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机构,优质内容始终是生存发展的基石。
三、受众的表演欲与媒体的社交属性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定义了人们在社交过程中的前台和后台行为,这一理论揭示了作为社会动物的人与生俱来的“表演”欲望。随着技术成本的降低以及网红效应的激励,这种欲望更加强烈,形成了今天用户的社交属性。这一属性具体表现为某些火热的社会风潮,例如自拍、弹幕、短视频、Vlog 创作,用户期待对话,渴望展示自我,建构身份认同,希望借助这些形式在赛博空间建构理想完美的个人画像。
因此,新闻类媒体不能再坚守原来那种正统的评论观点和话语表达,文本内容和形式要能够满足用户的表演欲望,使用户通过分享具有个性、思想性、深度性的内容,在朋友圈中建构起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个人形象。形式上,传统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大多还是继承“沙发土豆人”的形式,而受众喜欢的是像弹幕视频、电影院观影般和众人一同“围观”的感觉。《成都商报》的“谈资”客户端就在进行内容和社交的融合。
对社交类媒体而言,微博微信固然是头部,但也有新势力的崛起。微信逐渐沦落成为一种办公工具,用户被越来越多的无效信息轰炸,信息处理变得低效。“距离产生美”,在强连接的熟人圈层中建构自我形象,可能会面临被长辈不理解、被领导批评的风险。而微博的势头逐渐反转,微博成长为公共事件爆发之后反应最为迅速的舆论场,有了社会公器的性质。其次,由学缘、业缘、趣缘形成的圈层,更少受到伦理道德的规训,能更自由地表达。在同一圈层中拥有相同的意义空间,更容易相互理解。受众更希望获得熟人社交场域以外的东西,这正是主打弱连接的社交平台抓住的情感痛点。但是微博平台也要警惕被粉丝的“圈地运动”绑架,成为粉丝话语“互殴”的场所,不应让热门榜单被“蔡徐坤染发”之类的话题霸占,让虚假的流量遮蔽社会公共事件。
社交必然衍生文化,对生来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自媒体而言,他们和受众的文化土壤较贴近,而对传统媒体来说,它们面临的是一场“跨文化传播”。传统媒体习惯了在垄断优势下掌握强势话语权,形成高高在上的庙堂式文化。在技术赋权下的拟态环境中,受众不再仰视媒体,而是通过社交互动衍生出圈层,进而形成某种亚文化潮流。不仅自身创造“宅、土、丧、佛”,还“盗猎”传统媒体的话语进行解构,在一次次精神走私中,不同种类的亚文化兴起,形成新的文化景观,并在虚拟空间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按部就班的传统媒体来不及反应,形成了横亘在受众和媒体之间的“文化鸿沟”。
传统媒体能做的,除了引导,就是主动拥抱。第一步就是搭建、转化媒介品牌文化形象。媒介品牌形象的建构仍然停留在明星代言、标识系统的建构、广告宣传等初级层面,缺乏媒体、产品文化的深耕细作。日本的NHK电视台以中立著称,BBC的纪录片闻名世界,具有历史的沉淀感。而我国的媒介,除了一贯坚持的党性以及泛滥成灾的娱乐性外,几乎没有为人称道的个性特点。而在这个亚文化对主流文化构成强烈冲击的今天,没有个性就意味着平庸,对媒体来说,就意味着凋敝和消亡。
四、受众的“消费”心理与媒体经济
鲍德里亚在提出“消费社会”时认为,人们在购买时越来越少地关注物品的实用性,而将目光转移到其符号意义上,如其对社会地位的彰显等。这样看来,媒介在内容中植入“小鲜肉”吸引粉丝固然有效,甚至能在短期内实现爆发式的传播。但是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巨大的。首先需要背负巨大的时间和金钱风险,如今明星“更新换代”太快,选择当红炸子鸡需要承担高昂的费用,而选择热度衰减的明星则会显示出媒介内容的“过气”。第二,明星一旦有负面消息缠身也会波及媒介形象。比如大型古装电视剧《巴清传》就因为问题艺人范冰冰、高云翔而延迟播出,北京台春晚也因为邀请吴秀波做主持人,不得不在后期剪辑上花费巨大精力弥补。第三,明星的个人身份要和媒介产品的气质相符。NBA 新春贺岁形象大使选择了蔡徐坤,这一事件引发热议,专业的篮球迷对NBA的专业性产生质疑,打击了核心目标群体的忠诚度和购买力,而这部分人才能为NBA 带来持久的流量和关注度,粉丝只是一时追逐。所以,媒体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不能盲目迷信明星符号,跟风“粉丝经济”。
吸引受众不仅仅意味着在内容、渠道方面进行创新。因为媒介产品是内容产品,但又不仅仅是内容产品,体验和服务成为建立在内容基石上的“上层建筑”。顺应这一趋势,背靠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内容媒体开始了平台化、矩阵化发展,通过“做加法”,让自身从单纯的内容媒体演变成为集内容、服务、社交于一体的平台媒体。如“浙报”集团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钱报有礼”,依托政策优势、媒体品牌和数据库资源,提供包括政务服务、生活服务在内的高品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