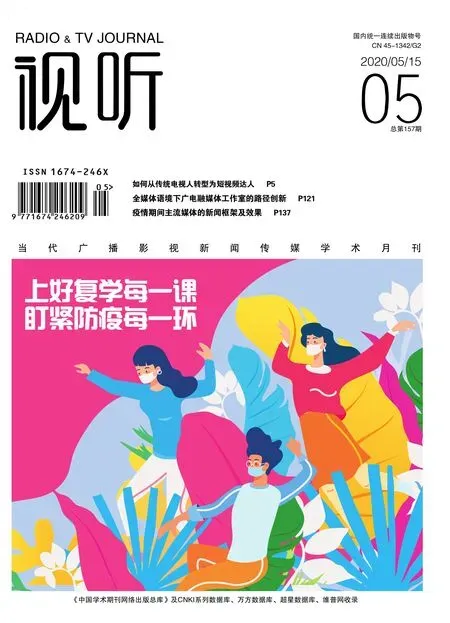《庆余年》:一场成长仪式的建构与狂欢
□张薇
一、成长仪式的建构
影视作品《庆余年》对原作的“穿越”元素略加更改,讲述了学生张庆想用现代观念剖析古代文学史,被专家叶教授拒绝,并因为观念不合无法接受其为自己的学生。面对老师的执拗和不解,张庆决定用写小说的方式解答看似相生却又相克的新旧难题。由于小说的立意与《红楼梦曲·留余庆》有异曲同工之妙,故起名为《庆余年》。然而,纵览全剧,在宏大的主题架构下,这部IP改编剧仍未突破网络原生属性的束缚。投射在主角范闲身上的,仍然是犹如儿戏的挫折和无可匹敌的外挂,对“因果循环”的理解逐步被淡化甚至一度简化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实际表现。由此,范闲带领观众经历了一场完美且难得的成长仪式。事实上,小人物的成长一直是影视作品乐于呈现和描摹的故事,这与观众的接受心理密切相关,契合其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和审美偏好,具有极强的代入感。
范闲的成长,从离家开始。剧中,其名义上是户部侍郎的私生子,实则是庆帝寄养在范家的儿子。因此,范闲虽从小不受重视,被寄养在澹州老家与祖母生活,但仍具有天之骄子的潜质和光环。无疑,范闲成长道路中的最大看点便是其现代化思想与古代制度的碰撞。而这种碰撞首先出现在其家庭之中,以此,该剧拥有了以往大男主剧或大女主剧不具备的或者叙述较少的家庭线索。拜别祖母之时,范闲孩子气地亲吻祖母的额头,这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他对于祖母的爱,转身又用传统的跪拜方式感谢祖母的养育之恩,这是符合古代礼制的他对于祖母的爱。这将范闲即将探索世界的喜悦之情以及少年离家的感伤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来到京都,范闲的成长故事步入正轨,而《庆余年》亦迎来第一个高潮——牛栏街刺杀。在此次事件中,滕梓荆为护他而死,周边人“只是死了一个侍卫”的说法激发了范闲与所谓礼法和制度抗衡的决心。原作中,滕梓荆更像是游戏世界中“NPC式”的人物,虽然游走于故事发展的始终,却没有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剧中,编剧虽然将他的生命线缩短,却加速了剧情的发展。如果说少年离家是范闲成长的第一步,那么痛失挚友则是加速其成长的决定因素。此时的范闲重回孤独,并且对于未来少了一分幻想,多了一分理智和不甘。
如果说在南庆的范闲是有各方势力庇护的温室里的花朵,那么出使北齐国的范闲则成为备受历练的职场新手,需要用个人智慧去协调、解决各类难题,因此,远走他乡这一情节的设置成为折射其成长之路孤独与艰辛的一面镜子。此时,沈重、上杉虎等异国敌对势力纷纷出现,而曾经无条件保护范闲的庆帝、陈萍萍又阴谋般地抽身事外,剧情不断反转。而此时,他无意却也必须卷入北齐国的政治斗争之中,在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对于权力、地位这些生存游戏中必须考量的元素有了新的认知。而剧情发展到此处,经历了少年离家——痛失挚友——远走他乡的范闲从初出茅庐的少年郎逐步变为了游走在各方的社交能手,成为所谓“上升型英雄”的实践模版。这种仪式化的成长既悲壮又现实,使观众在其中感受到所谓的热血和激情,但也埋下了诸多隐患,终沦为对于一种仪式景观的狂欢。
二、仪式景观的狂欢
齐泽克曾提到:“正是幻象这一角色,会为主体的欲望提供坐标,为主体的欲望指定客体,锁定主体在幻想中占据的位置。正是通过幻象,主体才被建构成了欲望的主体;正是通过幻象,我们才学会了如何去欲望。”①在《庆余年》中,范闲非凡的成长经历即是一副由光影编织的幻象,以此恰到好处地投射了当下人们的心理欲望,满足着大众的审美需求。范闲的成长仪式不仅属于其个人,更是无数观众所要窥探的盛大景观,其所经所历、所思所想成为牵动大众视觉神经的符码,以此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实现着其作为商业产品的利益转化。
剧中,范闲的现代思想与古代制度不断碰撞,即使在陌生的世界承受成长的烦恼和挫折,也仍旧过得如鱼得水且有能力转危为安。这不仅源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优越感,而且与强大的后援力量有关。这些生存游戏中的顶级配置,成为范闲成长进击过程中的必要元素。庆帝代表权力,陈萍萍代表地位,范建代表财富,范若若代表智慧,五竹代表武力,透过这些主要人物,还延伸出费介、王启年等一众帮手。同时,这种明确的分工模式,在一定层面上简化了该剧庞大的人物谱系,加速了剧情的走向,合理化了其间出现的反转或不确定因素,推动着范闲现代理念与古代制度的碰撞,也成就了《庆余年》中的大男主形象,满足了人们对于英雄成长的美好期待和集体狂欢。
但是,“范闲的奋斗并不能纳入从父母/体制的荫护中自觉挣脱出来的青年成长故事范畴,恰恰相反,在他甚至相当心安理得地利用这种荫护的时候,范闲的成功其实已经蜕化为在所谓的成长幌子下再次强化的阶层固化和复制的‘逆成长’滥调。”②更令人担忧的是,其间对于权力崇拜无所掩饰的表达,更偏离了开篇所陈设的因果轮回、积德行善的宏大立意,最终使其空具华丽的外壳。
这种权力崇拜深刻体现在范闲对于提司腰牌的认知和使用之中。初入京都,范闲便得到了足以凌驾监察院八大处之上的提司腰牌,对于这从天而降的好事,少年范闲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伴随剧情不断深入,“权力”一词的重量在范闲的心中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其对提司腰牌的使用心理之中,即从不知何用到游刃有余。而且,在此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范闲对权力的使用有增无减,而应具备的责任意识却未经提及。身处北齐国之时,范闲更产生了要当庆国第一权臣的想法。剧中,提司腰牌虽然出场不多,但却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或者说是有指代的“意象碎片”,暗示着范闲的心理变化。
同样备受关注却经不住推敲的还有祈年殿斗诗环节。夜宴中,不甘将内库财权拱手相让的长公主联合北齐文人庄墨韩向范闲发难,要求范闲自证颇具争议的《登高》一诗是出自其手而非挪用他人成果。范闲随即吟出百首诗词,句句经典。从李白、杜甫、王维到辛弃疾、范仲淹等,涉及爱国、思乡、爱情、生活、咏志等各方面,亦因此被庆国子民尊为诗中之神。这一自证的过程在笔墨挥洒和视听渲染间显得豪情万丈,确实激发了观众的欣赏热情,但是生物性爽感褪去,留给观众的就是被戏谑的历史、被玩笑的文化以及被简化的成长,而且用“借来”的诗作实现自身价值的确证,实在不是值得宣扬的事件。
三、《庆余年》热播现象之思
虽然《庆余年》的故事颇具特点,但是观众仍能从中窥见几分熟悉感。新思想与旧制度的冲突在《步步惊心》《宫·锁心玉》等剧中早已呈现。非凡的主人公经历重重磨难,凭借主角光环一路成长,最终收获事业与爱情的架构,与《楚乔传》《扶摇》等“大女主”剧所演绎的内容十分相似。该剧以男性角色为主要表现对象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女性IP泛滥所带来的剧作桎梏,但这早已在《莽荒记》《择天记》等男频IP剧中有所体现。但是,基于传统的剧作套路,该剧还注入了别样的故事内涵,即将现代意识所带来的爽点与小说试图体现的英雄情怀完美结合。
作为玄幻小说改编作品,《庆余年》虽然因为影视化创作局限弱化甚至割舍了原作品中的玄幻因子,但是在叙事过程中,仍通过讲述和演绎的方式呈现给观众。由此,该剧将武侠、玄幻、科幻等元素熔于一炉,在人类文明再次轮回的封建时代,已经经历过现代社会种种的叶轻眉宣扬民主、成立内库、创办监察院、发展工商业,这些流于其身的先见之明为观众带来了预言家般的爽感,而作为叶轻眉的后代,范闲的成长显然更具坐享其成的畅快。
巴赫金曾说:“个人的成长如果是囿于个人的私事,那就不是真正的成长,因为它不会触动历史和文化。”③在《庆余年》中,范闲的成长历程一直围绕自己或者与自己相关的人或事物展开,以此书写着个人英雄的绚烂人生,以供观众沉醉和痴迷。此外,这种个人化的成长意识,一度成为追逐权力的游戏,在原小说中更演化为一场“弑父”的悲剧。范闲在滕梓荆被杀后,决心要找出幕后主使并为好友报仇。妹妹范若若问范闲为何要如此做,范闲的回答是:“我想跟这世上的道理斗一斗,告诉那些大人物,他们不是草芥。”然而,在《庆余年》中,那些数不清的被杀死的、贬谪的、驱逐的人物大多都因与范闲一派相对立,而对于其他的“草芥”,范闲从未表现出不忍和仁慈。范闲厌恶身边位高权重之人仗势欺人,可是其生存进击之路之所以可以不断地出现惊人反转甚至逆风翻盘,便是因为无可挑剔的身份以及无处不在的金手指。事实上,范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依靠权位搅弄风云的人。
由于对于这个复杂的社会存在深深的恐惧,范闲一直在不断地挣扎和反抗,即小说中曾提到的“这个世道,看似太平,但如果你不够狠,终究还是自己吃亏”,也因此信奉“宁可害死他人也不要他人伤害自己”的利己主义信条。剧中,身处北齐国的范闲,因为陈萍萍的失信、肖恩等人的挑拨对于生存有了新的看法,由此不惜拉党结派,其掌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便是变为庆国第一权臣。对于《庆余年》而言,虽然其剧作之精心、形式之创新都值得业界称赞,但流转于剧情的价值内核却有待考量。目前,该剧所要实现的以现代思想烛照古代社会的目的明显存在牵强感和偏颇性。同时,可怕的不是其爽剧的内核,而是用贩卖情怀的方式宣扬着虚伪或虚假的正义。
四、结语
《庆余年》借助新鲜的视觉形象符号为观众建构了无暇思索且魅惑梦幻的成长仪式,使其在观剧过程中获得一种无需深刻思考便可获得的直觉式快感,即“爽感”,从而在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中短暂抽离,使身心得到片刻的疏通和愉悦。而当这场成长仪式的建构与狂欢退散,留给时间检验的便只剩其略显空虚和苍白的内核和意旨,更忽略了本应熔铸于影像之中的检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真理。同时,五年三季的播出方式虽然有利于剧情的深化和展开,但在正式运作的过程中或有夭折的危险,第一季与后两季怎样衔接,如何既保障剧作水准又可以使故事顺畅呈现,是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
注释:
①[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M].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9.
②董丽敏.角色分裂、代际经验与虚拟现实主义——从网络玄幻小说《庆余年》看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症候[J].文艺争鸣,2017(10):9.
③王一川.中国故事的文化软实力[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