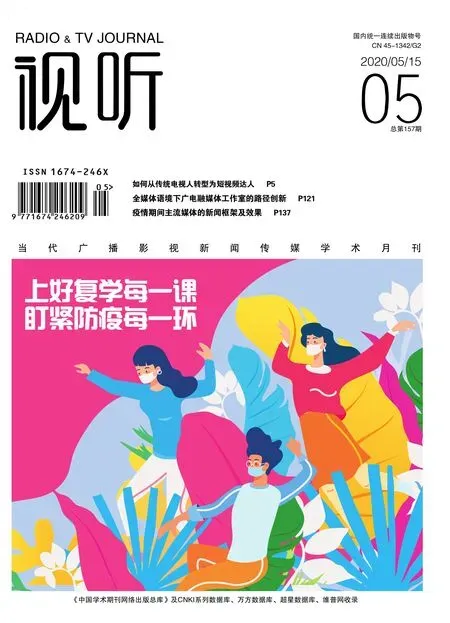浅析韩剧《爱的迫降》中的身份认同
□ 毕维娜
相关数据显示,《爱的迫降》大结局以约21.7%的收视率收官,创下了tvN 电视剧收视率历史第一的纪录。而在国内微博上,#爱的迫降#话题阅读量高达33.1 亿,讨论度达37.6 万。《爱的迫降》在传播中凸显了多种主题,其中,身份认同的主题尤其值得深思。
一、自我身份认同:“本我”与“超我”的斗争
大体而言,身份认同分为四类,即个人认同、集体认同、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的体验,以自我为核心①。自我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的存在状态的知觉,既包括对自己的认识,也包括别人对自己的感知。自我是个体对其扮演的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一种结果,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
而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与生俱来,受到先天本能和原始欲望的支配,追求欲望的即时满足。自我从本我分化,能同时意识到本能欲望和现实环境的要求,抑制欲望以适应客观环境。超我是理想化的自我,具有极高的道德感。
在《爱的迫降》中,李政赫和尹世莉就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不断挣扎。李政赫是一名朝鲜军官。从“本我”上,李政赫对尹世莉的帮助是出于保护弱者的本能;后来他喜欢上尹世莉,甘愿为她挡枪,则是出于爱的本能。但从“自我”角度看,李政赫是包庇并帮助尹世莉返回韩国的帮凶。他背弃军人职责,为隐瞒尹世莉韩国人的身份伪造护照,利用巡防值守之便私放尹世莉离境,之后为了阻止潜逃到韩国的赵哲刚伤害尹世莉。他秘密跨越“三八线”偷渡到韩国,进行枪战,是一个不被朝鲜和韩国两国认可的人。然而,“超我”却是李政赫所期待的。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守护者”,一个无罪者,能留在韩国与尹世莉在一起。
尹世莉是韩国财阀家族的一名继承人,因为童年被母亲遗弃的阴影一度想要自杀。她渴望获得亲情、爱的心理期望与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于是她常以高冷、严苛的形象示人,以避免自我遭受伤害。尹世莉的“本我”是一个孤独脆弱的人,渴望温暖,希望被爱。而她的“自我”是一个坚强者,同时也是一个迫降到“北边”(朝鲜)的“他者”。为了回到韩国,她融入了朝鲜三餐少肉、没有电、没有热水的贫困落后生活中。尹世莉的“超我”和李政赫相同,她也希望勇敢扮演“守护者”的角色,能跨越朝韩双方的界限和李政赫在一起。
“本我”和“超我”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本我”居中调节,以使满足欲望和恪守道德趋于一致。人格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决定了个体的身份,以及符合身份的行为,但是李政赫和尹世莉却对各自身份的恪守产生了混乱。“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的不协调使他们的行为与原本的身份相矛盾,难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从他们相爱的那一刻起,他们韩国人和朝鲜人之间的身份界限就开始变得模糊,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身份遗失。
二、社会身份认同:身份建构与理解
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是个体在群体中渴望被群体认同的一种心理。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同,个体须遵守在群体中的角色和群体的规则,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建构主义将“身份”分为四种类型,即个人或团体身份、类属身份、角色身份和集体身份②。集体身份(社会身份)就是在自我和社会群体的融合中产生的。
个人身份的建构与社会群体的影响密切相关。在群体中,个体扮演相应的角色,以被群体认同的言行方式表达自我,从而构建起与其他群体成员的关系,并获得他人的理解和评价。尹世莉初到朝鲜军官村时操着一口流利的韩语,着装奇异,披头散发,这些都显示着她的非本地人身份。为了尽快融入群体,获得离开的机会,她束起头发,与人以“同志”相称,加入村中的妇女团体,建构起了朝鲜人崔三淑的身份,很快就被他人接受和理解。而一旦回到韩国,尹世莉又重拾了事业成功的女强人身份。个体处于社会之中,永远需要在群体中通过与他人异同的比较来获得身份认同,尹世莉在朝鲜和韩国的身份切换即是如此。
霍尔认为身份是一种思想形态结构和权力的表现,反映政治上的不对等和来自阶级、性别和种族方面的压迫③。由于身份不同而遭受来自群体的压迫,在《爱的迫降》中郑万福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郑万福是一名躲在暗处的“窃听者”,这个身份在群体中不受欢迎,甚至遭到排挤,所以他常常低头行事。但这种排挤并不限于郑万福本人,还波及他的妻儿。他的儿子因为父亲窃听者的身份,被同龄人孤立、辱骂、殴打。他希望融入群体,但是常被人用有色眼镜看待,排除在群体之外。而当郑万福放弃了见不得光的窃听者身份时,他和他的家人才最终被主流人群所接纳。
三、他者的对照:逃离与回归的矛盾
他者是一个与“自我”相对的概念,被用来指称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④。正是因为“他者”的存在,“自我”和“他者”的差异才突显出来,“自我”的身份才得以界定。通过对“他者”形象的建构,一方面民族共同体的同一性被塑造,另一方面自我身份的优越性得以彰显。《爱的迫降》整部剧都在建构韩国和朝鲜的二元对立。通过住房、饮食、服饰、交通等多方面的对比,韩国被建构成富裕发达、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国家,而朝鲜被建构为贫穷落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国家。正是通过对朝鲜这个“他者”形象的建构,韩国人的身份得以被界定,在韩国人和韩国人之间就形成了一条紧密维系共同体关系的纽带。同时,在建构朝鲜形象的过程中,韩国的优越性被凸显无遗,而这时朝鲜就被贬斥到了“次等国家”的位置。
他者研究中的“他者”不仅仅含有消极的“他者”之意,它的外延显然更大,应该把被刻意抬高、夸大宣传的群体考虑在内⑤。所以,他者化同时包含了积极的“他者”之意和“消极”的他者之意。应该看到,《爱的迫降》对他者积极正面的构建也广泛存在。这种建构体现在家庭关系、邻里关系和朋友关系中。韩国人尹世莉所在的家庭缺少温情,父母子女之间冷漠疏离,兄弟姐妹之间为了争夺继承权尔虞我诈;而朝鲜军官村的几个家庭和睦温馨,邻里关系亲善友爱,常常是一家有难,多家帮衬,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这时朝鲜又被建构成了一个淳朴善良的国家。显然,《爱的迫降》对他者形象的建构充满了矛盾,而自我身份通过他者界定。换言之,这部剧对自我身份产生了怀疑,一方面对现代化的韩国进行了肯定,另一方面又对落后但淳朴的朝鲜充满了向往。
韩国在朝鲜战争和南北分裂中经历了一个身份丢失与重构的过程,原有的侵略、贫穷落后的身份被打破,新的现代化国家的身份逐渐被建构,但这种建构是在与美国的复杂关系中完成的。政治上,美国的介入使韩国丢失了纯粹的“朝鲜”民族身份。朝鲜是“朝鲜”民族主义纯洁性的代表,而韩国被全球化了⑥。所以韩国对此充满了向往,试图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这种重新认识自我的心理可能是导致韩国人身份遗失的一个原因。在韩剧《爱的迫降》中,可以看到韩国人对身份的追寻。
注释:
①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02):37-44.
②胡学雷.身份建构与利益转变——明治维新后日本身份变化的建构主义分析[J].东北亚论坛,2002(02):62-65.
③钱列英.浅析东野圭吾作品中的身份认同[J].新闻世界,2012(10):211-212.
④⑤童兵,潘荣海.“他者”的媒介镜像——试论新闻报道与“他者”制造[J].新闻大学,2012(02):72-79.
⑥[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M].刘成富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