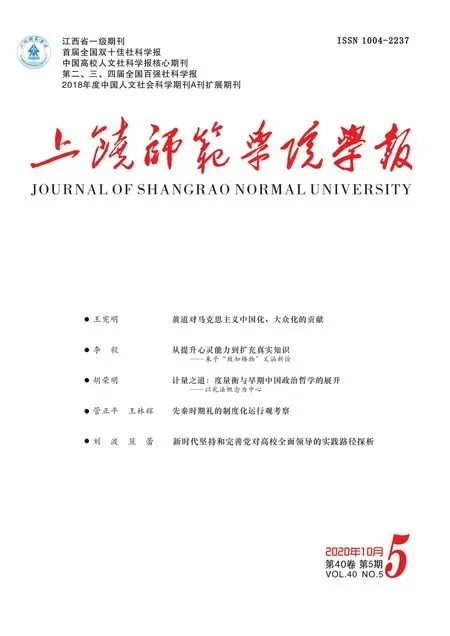论“非对象化”之观的涵义
——以老子与邵雍的“以物观物”为例
崔基勋
(上饶师范学院 朱子学研究所,江西 上饶334001)
道家之“观”,是修道的途径,修道者以“观”而知“道”之微妙、复归于道之境。冯友兰引用《老子》指出:“他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第十六章)又说:‘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第五十四章)这就是说,观,要照事物的本来面貌,不要受情感欲望的影响,所以说:‘致虚极,守静笃’。这就是说,必需保持内心的安静,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1]老子所说的“观”,与通常的观物过程颇有不同之处,不是主体对于客体的心知活动,此“观”具有特殊的形式,表现为“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2]147,即“以物观物”之观法。宋代理学家邵雍亦提出“以物观物”,在他看来,“以物观物”是相对于“以我观物”而言的,他以反观之义解释其观法。本文通过分析老子与邵雍的“以物观物”思想,以此显示其观法之能所、主客、彼此不分的非对象化之义。
一、老子的“以物观物”
关于“以物观物”的观法,《老子》五十四章曰: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2]147
对于此章的解释,历来注解者各有所得,却未能给出统一而通透的解读,其根本困难在于如何理解“以物观物”的观物之模式①关于此章的解释上的困惑,刘笑敢指出:“上文的讨论涉及到经典诠释中的一个困难的实例。”参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563页。。“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老子认为,守“无为之道”为修道之纲领②《文子·上仁》曰:“人君之道,无为而有就也,有立而无好也,有为即议,有好即谀,议即可夺,谀即可诱。夫以建而制于人者,不能持国,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胜。”参见: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第441页。。以无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其德”是就修道者之德而言的。关于“修之于物”,《文子·上德》曰:“大道坦坦,去身不远,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物,其德不绝。天覆万物,施其德而养之,与而不取,故精神归焉,与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与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3]294就修道者而言,家、乡、国、天下都是身外之物,“修之于物”的结果即是“其德不绝”。老子所认为的修道,是以达到上德为指向。修道不仅仅停留在个人身上,像天道对万物施与恩惠而“与而不取”的上德一样,修道也应“施其德”于外物,并在此过程中趋于完善。但此施与的行为不是有目的的、有心思的,而是其德的自然发挥,是“无为而无以为”的上德之作用①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参见: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第98页。。
“修之于身”具体落实在“以身观身”,“修之于物”具体落实在“以物观物”。以“以物观物”之观法能知“天下然”,其关键在于守“无为之道”。关于“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大体有四种解读。
其一,“推己及人”的解读方式。王弼说:“以身及人也……彼皆然也。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天下之道,逆顺吉凶,亦皆人之道也。”[2]147高明说:“修身则需推己及人,举一反三。视己之身推而及之,可知他身。视己之家推而及之,可知他家。视己之乡推而及之,可知他乡。视己之邦推而及之,可知他邦。以己所莅之天下,推而及之,可知他人所莅之天下。”[4]这样的解读方式,在解释“以天下观天下”的时候便会引发困惑。因为“天下”只是一物,没有自己的天下与他人的天下之分,“天下”包含着自己和他人在内,没有可比较的对象。说“以我的天下去观别人的天下”则迂曲而费解,所以王弼只能解释为“以天下百姓心观天下之道也”,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勉强的②参见:白欲晓:《论老子的“观”》,《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第136页。。为了避免同样的问题,高明将天下分为“以己所莅之天下”以及“他人所莅之天下”,使前天下与后天下两者具有不同的性质。
其二,“以道观物”的解读方式。河上公说:“以修道之身,观不修道之身,孰亡孰存也。以修道之家,观不修道之家也。以修道之乡,观不修道之乡也。以修道之国,观不修道之国也。以修道之主,观不修道之主也。”[5]严遵说:“我身者,彼身之尺寸也;我家者,彼家之权衡也;我乡者,彼乡之规矩也;我国者,彼国之准绳也;人主者,天下之服心也;天下者,人主之身形也。故天下者与人主俱病、俱邪俱正,主民俱全,天下俱然,家国相保,人主相连,苟能得己,天下自然。”[6]河上公与严遵以自身之“道”为行为准则、原则而观其他对象。在此,其观不是修道之方,不是知“天下然”的途径,而实际上是“以道正人”。
其三,“以物观道”的解读方式。王淮说:“此处章句历来无善解,旧注多无足取者……河上公所注似可解,而末句极不通,盖既言‘天下’,天下无二‘主’,如何‘以修道之主,观不修道之主’?……言由一人之言行,可以观(知)其人之德;以一家之家风,可以观(知)其家长之德;由一乡之乡俗,可以观(知)其乡正之德;由一国之国情,可以观(知)其国君之德;同理,由天下之民风物情即可以观(知)天下主之德。”[7]他认为,虽然各物之范围不同,但都从事物的实情、状态之中,洞察到万物中的道与德。这样的解释与“修之于身”“修之于物”毫不相干。就老子而言,“知天下”与“见天道”有关联,“见天道”是由于修道,其修道的原则仍然是“无为之道”③《老子》四十七章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参见: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第130页。,“知天下”是由于“以身观身”等观法,其观法就是“修之于身、物”的关键所在。
作为“知天下”的途径,“以物观物”之观法所带来的困惑在于,难以说明此观法中认识主体的意义。就能所(主客)的角度而言,此观法就是“以所观所”的形式,物作为“观”的对象,即以认识客体观认识客体,表示着主体意义的淡化、虚化,不明观者如何参与观之行为。为了解决此问题,上述的几种解释都附加了另外的含义:就“推己及人”而言,以身观身、以家观家等于以自身观他身、以自家观他家,即以自身的情况来推而知他身的情况,主体的立场明显,主客关系亦成立,成知的基本条件充足;就“以道观物”而言,以身观身、以家观家等于以自身之道观物、以自家之道观物,即以作为存在原则之道观物或正物,在认知问题上没什么不通之处,主客关系仍然成立;就“以物观道”而言,以身观身、以家观家等于以自身之情况知自身之道、以自家之情况知自家之道,虽然都是在于自身之内,但自身的情况为知其道的根据,以客体之物所观的不是客体本身,而是其物之道。如此解读的原因在于“以客体之物观客体之物”观法的模式,此句在字面的理解上,似乎没什么实在意义①例如,“由一人之言行,可以观一人之言行”实际没什么意义,因此所观的不是“一人之言行”,而是“其人之德”。在这里,自身之情况成为判断其道(德)之根据。。
在认识问题上,主客之间的距离加上主体能知的作用才可以成知,但在“以物观物”的模式里,主体能知的作用或位置比较模糊,故上述的解法一般附加了另外条件,使“观”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显得分明,以此来解决理解上的困难。也就是说,对于“以物观物”中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第一个“物”或者解释为判断基准,或者解释为原则,或者解释为事物的实情;把第二个“物”或者解释为他物,或者解释为不合道之物,或者解释为是万物中的道。如果不附加任何含义而对“以物观物”(即“以所观所”)进行直接解释的话,其解又该如何?其哲学含义又是什么?关于“以物观物”,以邵雍为代表所提出的“反观”(非对象化之观)的观法②关于此解读,北宋的吕惠卿、元代的吴澄等亦保持同样的观点。,提供了另一种解读,我们接下来对之进行考察。
二、邵雍的“以物观物”
关于“以物观物”的观法,邵雍在《击壤集序》提出:
性者道之形体也,性伤则道亦从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伤则性亦从之矣。身者心之区宇也,身伤则心亦从之矣。物者身之舟车也,物伤则身亦从之矣。是知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8]179-180
性由于道而生,性是道在万物之中的具体显现,故性者道之形体也;心由于性而发,心之深处具有性之本然状态,故心者性之郛廓也;身由于心而动,心是身之主宰而舍于其身,故身者心之区宇也;物由于身而用,物在人之身上实现其具体用处,故物者身之舟车也。道、性、心、身以及身外之物,都相互连贯在一起,所以物伤则伤身,身伤则伤心,心伤则伤性,性伤则伤道。在邵雍看来,以道观性乃至于以身观物,最终会伤害道之本然状态,引起连续反应的实际出发点乃是“以身观物”或说“以我观物”的观法。为了避免这种危害,邵雍提出以道观道乃至于以物观物。关于“以我观物”与“以物观物”,邵雍曰:
圣人之所以能一万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8]49
邵雍所说的“以物观物”是相对于“以我观物”而言的。对于“以物观物”,邵雍的解释有两个关键点:其一,“以物观物”意味着“反观”;其二,“以物观物”意味着“无我”之境。在邵雍看来,“反观”是就“以物观物”的观法而言的,此“观”即“无我而观”的状态,圣人由此能知万有之实情。关于此观法,邵雍又说:
天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8]49
邵雍认为,他所说的观,不是以目观,也不是以心观,而是以万物之中的理观,此乃是“以物观物”的实际内容,此说法与庄子的“心斋”很相似:“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9]80-81庄子说“听之以气”,但其气也不是物之气,而是符合于理、或道之气,故实际上他们的说法是相通的③庄子接着说:“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参见: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第81页。此“未始有回”之境,乃是庄子所说的“吾丧我”之境,或说邵雍所说的“不以我”即“无我”之境。。“以目观之”也好,“以心观之”也好(实际上两者表示“以我观物”的观法),都不足以达到“真知”,“真知”只能循由理、性、命而可至。
“以物观物”的依据是理,而万物莫不有理、莫不有性、莫不有命,修道之观法依据自身之理、内在之性,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以此得到真知,故邵雍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8]152就邵雍而言,“以物观物”是穷理尽性的具体落实:“观物”的过程无非是“穷理”的过程;“穷理”的过程无非是“尽性”的过程;“尽性”的过程无非是“至诚”的过程①《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第34页。,故邵雍曰:“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8]171换言之,“以物观物”的观法,乃是“自诚明”的过程,即内在之本性(诚)的自然显现。因此,邵雍说:“诚为能以物观物,而两不相伤者焉,盖其间情累都忘去尔。”[8]180本来,“以物观物”的说法,是为了避免“以我观物”的伤道之害而提出的,这种危害是由“情”而来的。“情”就是我和对象物(无论人、物,还是事)之间发生的事情,“以我观物”之观法必然使我与物之间产生距离,以此产生对于对象物的喜怒哀乐之情,而伤害其性。邵雍则提倡“以物观物”,其中“我”(主体、能知)之位子消失了,其观也不是我和物之对立而造成的,这样,“情”亦不发生②其状态实际上指的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之状态,即是“中”,也是“诚”的状态。,故说:“则虽欲相伤,其可得乎!”。由于“以物观物”而至诚,至诚而至理,至理而真知,即“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8]180其观,不是以我与物对立的心之对象化活动而成,而是以“无我”而观的“反观”,其观即是消解主客对立、彼此不分的“非对象化”之观。
三、“非对象化”之观
“以物观物”是“修之于物”的具体落实,是知“天下然”的前提,也是修道的途径。邵雍以“反观”解释其观法,此观具有超自我、超认识的特征。在他看来,作为宇宙整体统一状态的道,不能通过对象化的方式被认识。建立在主客关系基础上的日常认识模式无法把握它,反倒会伤害道之本然。一般的认识活动中,认识主体把握客体时必须有主观意识投射到对象物的过程,以此形成的“知”离不开人之诠释性的限制。“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2]60,道的把握不是获得关于道的知识,而是直接融入于道而与之为一,这是一种体验,也是一种直觉。在此过程当中,自我意识逐渐消失,进入主客未分的特殊精神状态,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吾丧我”的状态,无心、无我、无为而自然的状态。“以我观物”的无我之观,没有主观意识的参与③主客、能所、心物关系当中形成的主观意识,庄子称之它“成心”,是按自身的是非标准观物。庄子说:“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虽然,无为可以定是非。”参见: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第333页。是非的唯一标准就是道之“无为”,以“成心”做出的任何知不足以成为关于道的真知。,超于通常认识的主客二分式,使道之本然状态自然地显现出来④张世英说:“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总是与他人、他物相对而言的,这是因为在主客二分式中,‘自我’被实体化了、被对象化了……要超越主客二分,超越主客的对立,其本身就意味着超越‘自我’或自我意识,或者倒过来说,要超越‘自我’或自我意识,就意味着超越主客二分和对立,超越自我与他人、他物之间的外在性和对立性。”参见: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2007,第234页。。对于道家而言,其所求的“知”就是“自知”⑤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参见: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2011,第87页。,其知的对象不是外在之物,而是内在之道。作为修道之“观”,其观的对象不是观者之外的事物,在此意义上,其观乃是反观、内观。此观不把观的对象对立于观者之外而对之进行对象化,主客、能所之分因此消失,从而具有超自我(无我)、超认识(无知)的“非对象化”的属性。那么,如何做到“以物观物”之“观”呢?
首先,需要把向外的心知活动返回自身之本根⑥庄子曰:“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参见: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第83页。,就能所关系而言,此过程可概括为“以能为所”,即以认识主体为其观的对象。对于此过程,庄子描述为:
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若然者,其平也绳,其变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9]453-454
钟泰说:“‘以目视目’,目不外视也,‘以耳听耳’,耳不外听也,‘以心复心’心不外驰也。”[10]本来,耳、目等感官的作用是识别外在之物,但就真人而言,乃是以能知的认识能力观能知本身,他所关心的不是对象世界的外在之物,而是由道而存的内在之德、性、真。《文子》亦曰:
神明藏于无形,精气反于真,目明而不以视,耳聪而不以听,口当而不以言,心条通而不以思虑,委而不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3]413
“神明”作为得道之状态,不是由于外在之物,而是由于无形之道①《文子·道原》曰:“神明者,得其内,得其内者,五藏宁,思虑平,耳目聪明。”参见: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第37页。。修道者返于真的时候,耳目才聪明,其聪明不表示对于物的分别,而表示对于道的直觉,此时,外在之物无法伤害内在之性。庄子亦说:“吾所谓聪者,非谓其闻彼也,自闻而已矣;吾所谓明者,非谓其见彼也,自见而已矣。”[9]180不闻彼而自闻;不见彼而自见。“神明”的过程是返于真的过程,此由于目不外视而自见、耳不外听而自闻,即反观、内视的过程。“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即反观而内观,其结果为“神明”,此观不是彼此分别之观,而是无分别之观。“以能为所”,即以知之主体为知之对象,其知之方为“观”,使向外之心返回来照于内。反观而内视,内视而反听,此就是“以能为所”之反观的第一层含义。
彼此之分,作为一般认识成立的前提,同时也可表现为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分别,例如《管子·心术上》曰:“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修之此,莫能虚矣。”[11]141-142修之于此,意味着在主体、能知方面的修养工夫。彼此之分,也可以表现为彼我之分,例如《文子·守弱》曰:“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身,身得则万物备矣。”[3]162彼此之关系,就知之问题而言,也可以表现为所知与能知的关系。在彼此之关系上,管子提出能知方面的优先性、重要性,然而,庄子进一步提出两者之间的化解,庄子曰: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无穷,非亦一无穷,故曰,莫若以明。[9]35-37
彼之存在由于此之存在,此之存在由于彼之存在。就知的角度而言,主体(此)认识客体(彼)的时候,彼此、彼我之意义才显现。庄子又曰:“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9]29没有彼也没有我,没有我也无所可取,是因为“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此、彼我之分是相互依赖的。如果彼此“莫得其偶”②成玄英说:“偶,对也。枢,要也。体夫彼此俱空,是非两幻,凝神独见而无对于天下者,可谓会其玄极、得道枢也。”参见: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第36页。,两者都自然消失,彼此之分不再存在了,庄子把这样的状态谓之“道枢”。不分彼此的“彼是莫得其偶”之“道枢”的状态,实际上指的是“吾丧我”的无我之境。
那么,“以能为所”的反观之原则,在“道枢”之状态中,如何实际发挥?把自身(此)为观之对象,使观之方向从外在之物(彼)返回于能知之方,此即是第一层次的反观之义。以此,能知与所知之距离消失,达到主客未分的初步状态。问题在于,其以自身为观之对象的内观过程当中,又存在观者与被观者之分。也就是说,就“观”之行为而言,总有“观”之主体与“观”之对象。反观,并不是简单的自己反省(把自身的行为或观念作为反省、反思的对象),无论如何,有了彼此之分,还未做到“彼是莫得其偶”的“道枢”之状态。“以能为所”是不断“反”的过程,将向外往的分别心不断地找回来,使它返回于自身,即能知的“观”之行为本身成为所观的对象,以至于能所不分、彼此无生的状态。彼此无生意味着是非无始,由“成心”做出的各种是非观念因此结束。以其“反”的过程,得其“中”之虚静、虚空、虚无而无物。如此,使心达到“彼是莫得其偶”的“道枢”之状态,此就是“以能为所”之反观的第二层含义。
就反观的具体过程而言,“以能为所”的原则贯彻到底,也应当适用于内视中的观者之此与被观者之彼。那么,在内视中,“观”的主体是什么?“观”的对象是什么?庄子所说的“莫若以明”如何呈现?《管子》曰:“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11]110,庄子曰:“以其心得其常心”[9]106。修道者观自身的时候,并不是以心观其常心(常心,即本心、心之体),或说以常心观心,是因为如此观的行为之中,心与常心之间仍存在彼此之分离。“反观”行为之初,观的主体应当是平常之心(还没得道的分别心),其观的对象也是平常之心。也就是说,心作为观之行为的主体意识,此心观的对象不是别的,就是此观之行为中的主体意识本身,即主体的观者之心同时成为客体的对象。在此观的行为之中,主体与客体之分慢慢消失,主客二分的状态变成主客未分的浑然状态。按“以能为所”的原则,此观的模式成为“以能观能”,换言之,既不是“以性观心”,也不是“以心观性”,而是“以心观心”。邵雍认为,只有做到这一步的时候,物、身、心、性、道才不相伤,性命能够保全,这是“以能为所”之原则贯彻到底的表现。
然而,一旦进入“以能为所”的轨道,此心的状态就开始进行变化。在“以心观心”的观法之中,我们除了自己的心以外不再寻找或诉求他心、他物,如此,观者与被观者完全为一,进入“彼是莫得其偶”之道枢的状态。虚心是道家主张的在心上所做的功夫。在虚心的过程之中,试图解除杂念的主体之心本身是未脱于彼此之分的分别心。领悟到这一点时,主体之心就把所有企图和作为放下来,因为分别心做出的一切措施(有为)都会干扰道的显现(无为而无不为)。虚心停止彼此之分的对象性活动,达到无心状态,才可以进入“无为而无以为”的上德境界。邵雍指出,“心者性之郛廓也”,有了无心,内在之性显出来了,就可做到“以性观性”的阶段;“性者道之形体也”,有了性之明,道亦显现,就可达到“以道观道”的、心合于道的最终境界。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以其心得其常心”的含义。
对于以道观性以至于以身观物,邵雍说,“治则治矣,然犹未离乎害者也”,此观法还是观者与被观者之间有距离的对象化之观。对于以道观道以至于以物观物,他说,“虽欲相伤,其可得乎!”,此观法是观者与被观者之间没距离的“非对象化”之观。他又说,“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反观,以物观物之谓也,以心观心以至于以道观道,是守“无为之道”而观,能达到“心合于道”的修道之途径。此心之状态,即是无心,无心之心乃是老子所说的“玄览”,无偏见、无私见地照出而使物之本然自然如此地涌现出来。
邵雍承认老子以物观物之观法,他说:“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之矣。”关于《老子》五十四章,元代理学家吴澄接受邵雍的解释并指出:“德修于身,以及于天下,无一不修,然亦因彼之自然,吾无与焉。物各付物,不相系着,随其所生,观其所止,人人皆自得其分愿,此达到无为之治,心迹两忘,超然无累,如善建者无所建,善抱者无所抱也。邵子曰:‘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则欲相伤,其可得乎?’邵子所言,盖亦老子之意。”[12]“以物观物”的关键在于“因彼之自然”,即万物内在之德、性、真之自然如此的状态。作为能知的主观意识不得参与,从而达到彼此不分、心迹两忘的无分别状态,此乃是反观的实际内涵。关于如何反观、如何“以物观物”,宋代吕惠卿说:“然则何观而修之身哉?以身观身而已矣。何谓以身观身?今吾观吾身之所有何自也,则知吾身之所自而有,又知吾观之所自而观,则所以修之身者已足,而无待于外也。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古之所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用是道也。”[13]知吾身之所有乃由于道而有;知吾观乃不以我观物,而以内在之道(德、性、真)而观。此观即反观,无待于外的内观。
邵雍所说的“以物观物”是“反观”之谓,此是就不“以我观物”而言的。虚心而无心,无心而无为,无为而自然,此观表现为认识主体之虚化,即无心而观的另外表现。道家的观物,其所观者不在他物,反观、内观而已。观物而不以己,不依据主体的分别心,能知之心倒是虚化,虚心而无心,以此达到“无己而与物无际”①庄子曰:“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成玄英说:“圣人冥同万境,故与物无彼我之际畔。物情分别,取舍万端,故有物我之交际也。”参见: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第401页。“与物无际”,是无分别心的状态,也是庄子所说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的状态。;观物而不得已,依据内在之道,能所之分逐渐消解,无心而无为,以此达到“自然而物我两忘”②庄子曰:“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参见:郭象、成玄英:《庄子注疏》,中华书局,2011,第89页。托不得已,是“知其不可奈何,安之若命”,即托于内在之道的自然状态。。物我两忘,乃是主客未分的状态,超越通常的主客二分式的认识。通常的认识,有了主客之分才成立。也就是说,所谓“认识”必须包含能知之心以外物为“对象化”的过程,以此我们获得了对于对象物的某种知识以及与外物区分的自我同一性,但道家认为,以此产生的任何认识与把握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本质属性之“道”无关。道家主张,超认识的境界表现为无知、不知之知、真知等,超自我的境界表现为无己、无心、吾丧我等。做到超认识、超自我的时候,才能达到与道为一的“天人合一”之境界①张世英说:“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不分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而把二者看成浑然一体。”参见: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人民出版社,2007,第13—14页。。因为“道”的属性是彼此不分、主客未分的“一”之状态,此属性可以概括为“非对象化”之道②林光华说:“常道”有四个特点:动而无死、生而无名、妙而可观、虚而可法。这四个特点可用现代哲学词汇表述为‘非对象化’(non-objectification)。‘常道’是主客二分之前的非对象化存在,而言说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行为,所以‘常道’不可说。”参见:林光华:《非对象化之道:再读‘老子’第一章》,《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46页。道具有“非对象化”的性质,无己而与物两忘的境界具有同样的属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66,同于道的修道工夫就在于“效法”道的自然属性,换句话说,道的属性成为修道之工夫。道常无为,故修道者以无为而修;道常无欲,故修道者以无欲而修;道常无心,故修道者以无分别心而修。“反观”作为修道之观法,接近于“非对象化”之道,修道者亦以“非对象化”之观而修。为了呈现内在之道,停止向外对象性的心知活动,不待于外而观照内在之德,其观的要点在于“以能为所”的不断“反”的过程。此观亦是彼此不分、能所双绝的“非对象化”之观。道之属性乃是修道之路径,在“观物”身上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