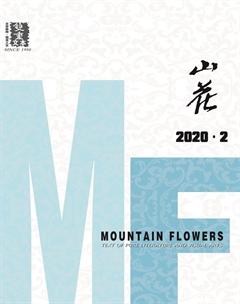障碍
唐月搬进冯赫那套房子,刚吃完冯赫请她吃的那份猪脚快餐,嘴上的油还没抹去,就迫不及待扭身、弯腰,手里捏着不知从哪儿寻来的一块抹布,把沙发上面的灰尘细细擦过一遍。
唐月的行李是两个编织袋,其中一个的拉链已经坏掉,裂开的大口露出朱红色塑料脸盆,活像吐出的半截舌头。另一个编织袋完好无损,窝藏着唐月的重要财物:几本书、所有衣物、一管口琴、一个化妆包、两袋方便面。
他和她,看起来都很单纯。他很洒脱,有怜悯心,反正有个房间正好空着。她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尚未找到工作,囊中羞涩,人也很羞涩。他们约定好,她可以拥有一个免费的房间,条件是她要负责整套房子的清洁卫生。
卫生间的镜子很大,灯光明亮,她终于能把自己看清楚了。来到这个城市后,她住过8人一间的廉价旅馆,住过蚊子能把人吃掉、墙角潮湿得长蘑菇的地下室,别说照个囫囵的镜子,连上洗手间都因为人多要排队而充满命运的紧迫感。
整个白天他占领整个沙发,但沙发本来就是他的。她小心翼翼把卫生间的陈年老垢洗掉,很卖力地擦完所有的地板,盘上去的发髻散下几缕细瘦黑发,在眼前晃啊晃,她也不去理。她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活儿太轻松啦,最好干得汗流浃背,汗珠儿大颗大颗掉在冯赫视野里,那样方能彰显出她跟这份免掉的房租有多么匹配。
冯赫早上十点起床,漫不经心踩着人字拖下楼吃油条豆浆,回来就把自己丢进沙发,眼睛眯眯地看碟片,看了一片又一片。肚子饿了,打电话叫外卖,吃完盒饭继续看碟。直到傍晚,开始淋浴、换衣、喷古龙香水,双手伸进裤子口袋,脚上仍旧是人字拖,慢悠悠地出了门。这个过程,唐月像保姆一样看着冯赫,从头到尾无话可说。这才是本地人做派啊。她跪在地上,翻了翻那些碟片,果然有三级片。她想自己是否要在晚上把房门反锁,免得打扰他的兴致。真是不错的一个男人,有本地户口,不太缺钱,而且肚子里只有一个肾。
既然主人不在,她就不必像白天那样畏畏缩缩。也去痛快洗个澡吧。卫生间灯光未免太亮,极不习惯,想起以前在又窄小又阴暗的地方洗澡,她闭上眼睛,任莲蓬细流从天而降,肆意泼洒。穿好衣服,立于那面大镜子前梳头,梳着梳着,有些恍惚。镜子大,显得镜中人瘦弱如飘忽之灯。镜子是别人的,显得镜中人有些鬼祟。
唐月第一次见到冯赫是在一家医院里。是陈洋带她去的医院。陈洋是前一天晚上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互留了电话,第二天陈洋就约唐月出来。唐月刚来到这个城市,她不想让别人看出自己的窘迫,说话时总是故作轻松,尤其不能暴露小县城人的扭捏。所以,陈洋约她,她就大方地说,好啊。
陈洋骑摩托,把头盔递给唐月,说,走,带你去见一个朋友。摩托车在一所医院门口停下。唐月问,你朋友得什么病?陈洋说,肾病。唐月没听清楚,问,什么?陈洋停下脚步,回过头说,他刚做完手术,你也别问那么多,反正告诉你,他很可怜就是了。
哦,是什么手术?唐月问。
割掉一个肾。陈洋的右手配合他的嘴,做了一个切东西的动作。
冯赫的病房是个单人间。陈洋和唐月进来时,冯赫正坐在病床上看一本书。虽然他穿着竖条纹的病号服,但头发显然刚吹過,可能还喷了发胶。唐月还发现他的手指白皙细长,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
出了医院,唐月跨上陈洋的摩托车。陈洋说了一句什么。由于风大,陈洋骑车速度又很快,唐月听不清他的发音。陈洋大声问,你觉得我朋友怎么样?
唐月很大声地回答,挺可怜的。
陈洋大声说,我是问你他帅不帅。
唐月说,还行。说完她笑了一下,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
陈洋说,可惜呀,可惜。如果不帅,就不会少掉一个肾了。
唐月问,为什么?
陈洋说,呵呵。
唐月说,他家应该挺有钱。
陈洋问,你怎么知道?
唐月像个见过世面的人那样慢条斯理地说,因为他长了一张有钱人的脸呗。
冯赫脸上有一个精致的鼻子,鼻翼很窄,有点不像亚洲人,令人担心他的呼吸能否通畅。即使躺在病床上,他也十分注重竖条纹病号服的整洁,衣领也比一般的病人干净。他嘴唇薄,人中深陷,据说这是长寿之相。脸型瘦削,皮肤细白,这似乎属于富贵之相。眉眼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忧郁,即使笑,也感觉不太高兴。总之他站在那儿,不说话,站姿有些吊儿郎当,像极了小说和影视里的翩翩公子或纨绔子弟。
唐月刚见着冯赫,心里就生出一点矜持。她的矜持里参杂许多卑微和谨慎。如果不是因为他肚子里只有一个肾,他怎么也不属于她可以对视的人。他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从长相到出身,都不是。但他少了一个肾脏,似乎就给了她一点底气,去靠近,去了解他那个世界。
住进冯赫家的第五天,他照例傍晚洗漱后出门。晚上唐月出门去了一个大排档,跟几个不太熟的朋友喝酒。说是朋友,其实连名字都叫不全。一个穿花衬衣的“朋友”把手搭在唐月肩膀上,吐出呛人的酒话:妹啊,你放心,你的工作就包在哥身上啦。一个穿绿色沙滩裤的“朋友”给唐月杯子倒啤酒的手摇摇晃晃,酒哗啦啦溢出来,一直流淌到她的白色连衣裙上,他道歉后信誓旦旦地弥补:有事打我电话,那家伙不给你介绍工作老子给你介绍!去他妈的!
唐月并不是很明白自己为何置身于此,不在此处,就该在彼处,而彼处又是哪儿?对她而言,命运是个神秘的大东西,而她只是这大东西的微不足道的可以随意抹去的小零头。这个晚上她喝了不少啤酒,虽然“朋友”们的热情强悍让她害怕,但她深知每一口酒都是自愿喝下的,没有人逼她,是她自己逼自己。间隙她去洗手间吐了一回,之后就一直把胳膊撑在餐桌上假装清醒。装清醒比装醉要难上百倍,她想她有家族遗传的定力,她希望自己能天衣无缝地假装活下去,携带着基因给她的所有或明或暗的物质沉淀。
回到冯赫的房子,已是凌晨1点半。黑灯瞎火,他应该睡了,她蹑手蹑脚洗漱关灯上床。第二天醒来,已是中午,她起床,从门缝里窥见冯赫正在客厅吃外卖盒饭,一条腿搭着另一条腿,斜靠沙发,边吃边看碟。不知为什么,她心里涌出很深的羞愧,不敢从房间里出来。
肚子很饿,印象中附近好像有一家沙县小吃,她想去吃一碗馄饨,让店家撒些芹菜和胡椒粉。他仍在慢吞吞嚼着饭菜,她只得重新躺下,辗转反侧,拿手抚弄凉席上掉线的竹条。明明是饿,心窝处感觉也空荡荡,想来也许是因为心腔与胃部离得太近。眯上眼睛,眼缝间瞧见天花板虚虚晃晃,继而整个房间都被云雾围绕。毕竟是寄人篱下,身心浇灌着铁打的飘渺。
终于,听到拖鞋摩擦地板的声音,接着是关上房门的响动,应是他进了房休息。唐月把门轻轻推开,做贼一般猫进洗手间,刷牙、洗脸、梳头,对镜中的自己发呆。嗯,在找到工作之前,应该好好珍惜这一切。“这一切”包括独立卧室、独立卫生间、大镜子、没有性攻击力的男性同居者、可以偷偷喘息的暂时栖居地。于是她临时起意,打开淋浴头,从头到脚冲洗自己。她从不在白天洗澡,今天是第一回。人生有时就是那么奇妙,第一次发生的事,往往能改变一生。
客厅有一台立式电扇,当冯赫占据整个沙发看碟时,电扇摇头晃脑发出的呼呼声总是配合着碟片里的男女剪刀一样的发音。唐月刚洗完的头发湿漉漉,她自然而然就弓身站在这台电扇前,想把头发快速吹干,自然而然也忘了自己刚刚洗完澡身上只裹了一条稀薄的浴巾。
电扇呼呼叫着,掩盖了房门被推开的咯吱声。弯腰低头的姿势使得唐月先看见冯赫的拖鞋。深棕色人字拖吸住了脚趾,继而就能吸住整具人体,甚至攥住围绕这具人体的整个主观世界。唐月一直就觉得“人字拖”这个名字很荒谬,一撇一捺这个造字原则原本就荒谬,把它强加在鞋子上更是荒谬至极。仿佛意味着:不管世界有多繁杂,“人”仅仅只是一撇一捺。
低头弯腰的姿势也使得唐月瞥见自己身上那仅存的财产——一条旧得发黄又因频繁清洗而边角脱线朽败的浴巾。这该死的浴巾还被电扇风鼓动着,使劲去勾勒唐月鲜明的身体轮廓。
冯赫的愤怒仿佛是从夹住拖鞋的脚趾往上升腾继而弥漫全身的,因为他的大脚趾和二脚趾来回搓夹,足以把唐月的时间夹住。风继续吹,糊糊的一大片。羞耻感从发烫的耳根开始,沿著脖颈、心窝、腰线、臀、膝盖、小腿、脚底,一直堕下无底的深渊……
后来,当唐月回忆那天的情形,对自己那久久不散的羞耻感,生出一种难言的惊愕。冯赫当时的愤怒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她的羞耻与他的愤怒,显然不是一对因果,更像一对同时诞生的容貌相悖的双胞胎。
冯赫要她搬走,并不是亲自跟她说,而是通过陈洋。他希望她立刻消失,急不可耐,还要通过另一个人告知。就像她是一个破烂,一只蛆,一张用完发臭的狗皮膏药。
陈洋问:到底你怎么他了?他很生气,态度很强硬。
唐月也不太明白自己是如何惹怒他的,就像不太懂得自己的羞耻心何以会自我繁殖、绵亘不绝,苍蝇遇见屎一般驱赶不走。搬走,这两个字对她来讲,就是一纸判决书。而她连辩护都不能,不可以,没门。
她没有可搬去的地方,她没钱的程度从她的外表是无法揣测的,因为她总是擅长隐藏自己的贫穷。如此,她在沙县小吃咽下一口馄饨(这是她为自己规定的高性价比晚餐)时,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几圈后倒流回去。鼻子酸涩,但必须调整出一个淡然的表情,然后给他打电话。她想如果自己的表情是淡的,语气就会跟着淡起来。她计划在电话里冷静而又严肃地向他表示抱歉,抱歉自己没能快速适应新环境,但自己会努力改变,之前的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有什么要求或建议请务必告知,自己一定会严格遵守,最后加一句:相识是一种缘分,你我坦诚相对,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如此大概。
但他并不接她的电话,连打了三次,硬是不接。
她来到这个城市已经两个月,没找到工作,该花的钱都花了,所剩无几。他要她搬走,她是无处可去的。当然,在大排档一起喝酒的几个男人,虽然不太熟,如果她跟他们联系,他们会给她安顿住处的,但她知道那将意味着什么,就像当初她知道搬到冯赫那里寄住,肚子里只有一个肾的他意味着什么。宽敞的房子加上他内脏的残缺,仿佛是她在这座城市里最后的救命稻草。
她听过很多跟她一样一无所有的女孩独闯大城市的堕落故事,多得像来自同一个寡淡无味的故事模板,无非就是,遇到各种困难、障碍,越发清楚自己在这个城市的位置,于是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堕落,要么滚回老家。是的,你除了还算年轻紧绷的身体,一无所有。
她讨厌这种腔调,讨厌别人指着鼻子告诉她你要怎么怎么活下去。
当然堕落的方法也很多种,即使要堕落,也要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
冯赫的大门钥匙还在自己包里,唐月把手伸进包内,细细摩挲那钥匙的轮廓。如果用这把钥匙打开房门,取走她可怜的一点行李,她就可以滚蛋了。这将是一个清爽的行为,符合她倔强的性格。但她性格里还有一样危险的东西,这东西是祖先遗传给她的,存放在她身体深处,她可以取出来用,也可以一直搁置不用,这要看生活给她的刺激够不够。
唐月有一个表姐,性子非常刚烈,十七岁就嫁作人妇,生了二女一男,表姐夫突然有一天宣布外面有人,要跟她离婚,表姐当晚就砸了家里那台21寸彩电,第二天就寻到了丈夫外面情妇的住处,泼了她一脸滚烫的开水。据说她本来想泼硫酸,但短时间内找不到硫酸,于是把刚烧开的的开水装进暖水瓶里,坐出租车直奔主题,在丈夫情妇家门口预备就绪,在对方开门的第三秒,拧开瓶盖,准确无误地泼满对方整个脸庞。据说暖水瓶内的开水水温虽然没有刚烧开的那么烫,却也有90多度,足以让一张脸毁得彻彻底底。唐月去监狱探望过表姐,表姐一脸刚毅,并无半点悔恨之意。表姐说,我当时心里一团火,打上出租车,恨不得车子能长出翅膀飞起来呢。
从小,唐月就被亲戚或邻居们拿去跟表姐作对比,都说她们姐妹俩如何相像,虽然当她们站在一起,可以明显看出迥异的脸型和五官排布。唐月在成长过程中,努力与表姐的生活轨迹背道而驰,表姐初中就辍学,早早嫁人,唐月则坚持读完了高中,若不是高考落榜,她会读大学,然后远远把表姐抛在自己的世界之外。随着时间流逝,亲戚和邻居们早已不再拿她俩作对比,她却隐隐发觉无论自己如何狠命抵抗家族基因的馈赠,都不得不承认,表姐那与生俱来的危险气息,同样也在自己体内潜伏与暗涌。冲动与缜密,暴烈与隐忍,那么对称地长在她们共同的祖传基因里,就像一对完好的肾脏那样美妙并蒂着。
以上故事是唐月告诉我的。我就是那个把唐月介绍给冯赫的陈洋。
我是在三年后听到唐月的死讯的,奇怪的是,我知道后并不吃惊,好像什么事发生在她身上都有一种喜剧效果。三年前她被冯赫赶出来,无家可归,我想她是个成年人,总会有办法的,而且我也没本事帮她,所以也没太在意。不知道这件事是否给她造成什么影响,总之在那件事之后的某一天我们见面时,在她身上看不出经历了什么。我开玩笑问,你后来没露宿街头吧?
她表情是云淡风轻式的,漫不经心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
我故意叹气道,是啊,人必有一死,生死之外,都不是什么事。
她反而安慰我说,你太消极了,如果用生死来消解一切过程,那活着和猪有什么差别?
我说,对啊,我本来就是猪。
她可能觉得这样没法聊下去,就转移了话题。但我记得她那天喝了不少酒,脸越喝越白,这种白,在当时月光下呈现出一种透明的灰色。除了挺直的腰杆慢慢萎曲下来,整个过程,她都保持一种不融于世的古怪和清醒。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三年后,唐月在×城的单身公寓,死于一把剪刀。我能够知道一些细节,一部分源于道听途说,一部分是因为有个朋友在警察系统内部,会有半真半假的信息泄漏出来。那是一把普通家用的剪刀,尺寸不大,也不算锋利,我相信它被制造出来并不是为了置人于死地。
警方最初怀疑是他杀,因为如果是自杀,从刀口看,剪刀刺向自己喉咙的角度有悖于常理,但是,在公寓内并没有发现可疑的足迹和指纹。排除他杀后,对自杀动机的探寻又陷入迷雾。总之这种死法太不合常理,但我觉得唐月是这种人,是这种要么活得很喜剧,要么死得很喜剧的人。我跟她第一次认识是在一个很无聊的聚会,当时男男女女各占一半,吵吵闹闹,话题分散,几乎都算陌生人。唐月被一个不太熟的男人邀请来聚餐,稀里糊涂跟一群陌生人见面、点头、微笑、说无关痛痒的客套话。那是一个椭圆形的大餐桌,围坐了二十多个未婚男女。我一眼就注意到了坐在我对角线的唐月,她在一群衣冠正统而混沌的人中间,极其醒目,就像一盘五花肉里的一根青葱。
我看到她除了跟旁边那个男人聊几句之外全程都在茫然地微笑。可以说她是在场唯一认真吃饭的人,其他人只是假借吃饭之名在社交。她穿着雪白的衬衫和深蓝色背心裙,被餐桌上的菜肴深深吸引,每上一道菜,她的灰黑色眼珠子就移过去。她的眼神中没有男女,只有食物,我长那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饿的人。旁人都在谈笑风生。她在吃饭。
不但吃饭认真,她的发型也很认真。相比其他男女的墨守常规的上班族发型,她有卷翘的板栗色长发。我想如果她再认真化一下妆,简直就是洋娃娃本人。所以那一刻我就决定约她出来,我遇到心仪的女孩,都会主动交换联系方式,主动约。但我很害羞,我用吊儿郎当无所谓的态度掩盖自己的目的。所以我把她介绍给冯赫,这个刚刚被切除掉一个肾脏的未婚男青年。
唐月的死,是否与冯赫有关,应该永远是一个谜。即使冯赫本人,也未必了然。三年后的冯赫不但活着,而且结了婚。娶的是一位小学教师,貌美而乖巧,婚礼极其盛大,在五星级酒店摆了八十桌,热闹非凡。这对金童玉女式的婚姻,在本城一度传为佳话。我掩饰不住自己的嫉妒,冯赫即使只有一个肾,也比我强一百倍,他父母的经济水平怎么形容呢,就是冯赫每十年换一个肾,换一百次都不成问题。但我的嫉妒表现得吊儿郎当,因为没有人在乎我的嫉妒,其实不管我嫉妒不嫉妒,都没有人在乎。
我站在冯赫的新居,望着墙上他和小学教师的婚纱照,发出啧啧啧的声音。当我把唐月的死讯告诉他时,他歪着帅帅的脑袋,眨了几下眼皮。
他对唐月的印象都装在脑袋里,密不透风,我发现跟他讲解案情很费劲。我絮絮叨叨讲了一通,他的反应只有眨眼。
我环顾屋内陈设,瞅见一把剪刀,抓过来,就站在冯赫面前比划。
我说,我排除了很多可能性,只剩下一种,你看过来……我猜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唐月在单身公寓里,她正穿着一件圆领的T恤……
等一下。冯赫终于开口了。为什么是圆领的T恤?
不但是圆领,而且领口太小,她觉得憋得慌,喘不过气来,于是突发奇想,决定拿剪刀把领口那儿剪大一点。我得意地一口气说出自己对案情的发现。
等一下,为什么不把衣服脱下来再剪?
因为麻烦啊。
麻烦?冯赫笑了笑。
对啊,你不觉得麻烦吗?
怕麻烦就不要活着了。
对啊,所以她不活了。
不是,我觉得这样不合常理。
对啊,要什么常理。
你在绕口令啊。
对啊,不然呢。
冯赫推了我一把,摇摇头,然后示意我坐下来喝茶。
我喝了一口茶,迫不及待地说:她拿剪刀的姿势和角度,完全吻合我的推理。而且她站在镜子面前,看着镜子里的剪刀,对着T恤的领口,就那么一下,没对准,刚好刺中自己的喉管,大出血而死。
冯赫看着我,没有表情。一分钟后,他说,我老婆怀孕了。
我说,对啊,恭喜你。
从冯赫家出来,在小区里我踢翻了一个花盆。冯赫的态度让我很不舒服,好像唐月只是一个屁,没了就没了。我从未告诉任何人,唐月在我眼里不但不是一个屁,而且是一个月亮。我决定去一趟×城。我从来没去过×城。事实上我除了出生地,哪儿也没去过。
我在网上搜索到×城的信息:
中国××省下辖县级市,由××地级市代管。位于××省西南沿海,××市西南部,×城下游南岸,三面临海。东连××湾,南与××岛隔海相望,西与××市交界,北和××区相邻。
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城在经济、军事、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城为××省综合实力最強的县市,也是经济最发达县市之一,经济指数连续×年位居全省之首,文明指数测评名列县级市第一。全市辖7个街道、14个镇,……等著名历史人物,为×城留下了丰富史迹和人文遗产……
看起来×城挺有料的,我又搜索了自己所在的本城,发现更有料,接着又随便搜索其他城市,发现个个都有料,个个都差不多。×城距离本城五百多公里,为了理解“五百多公里”我搜索了地图,手指大概比划一下,觉得纸上谈兵、寡淡无味。
我查了查从本城到×城的交通方式,交通倒是便利通畅,绿皮火车、动车、高铁、大巴、中巴,应有尽有,难怪经济发达,难怪唐月要去那个地方谋生。至于她是如何谋生,我只有找到她在×城的情人、朋友、同事,才能知晓。
在几种交通方式里,我比较倾向于绿皮火车,价格平实,不快不慢。动车和高铁速度太快,毕竟我是第一次出远门,应该好好体验坐火车的感受,之前都是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虽然拍摄的车厢挺高清,仍然不是亲临其境,再逼真,也不是真的,隔靴搔痒罢了。而大巴和中巴我在本城坐过,虽然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但偶尔坐一下公交车也是难免。最重要的是,我猜想三年前唐月从本城去×城使用的交通工具最大的可能就是绿皮火车,而两地之间的绿皮火车每天只有一班,发车时间是凌晨1点32分,所以我如果选择绿皮火车,说不定会坐上唐月当年的同一个车厢,这种缘分不是不可能的,那么说不定我能体验到她当时的心境。想想凌晨乘坐绿皮火车的滋味,夜色阑珊,从车玻璃望出去,是灰蒙蒙一片呢,还是黑漆漆一团?
接着我想到城东有一家沙县小吃就开在一截废弃的绿皮火车车厢里,生意特别好,离我上班的地方并不远,我有多久没去吃了?好像有三年了。怎么可以那么久没去吃呢?味道不错的,尤其是馄饨,老板很会做生意,不但馄饨汤是用大骨头熬出来的,且在馄饨上撒了一层碎碎的芹菜沫,即使价格比别家沙县小吃贵一块钱,但令人回味无穷,回头客很多。
是啊,为什么我有三年没去吃这家的馄饨?看来我对自己还是不够了解。
我想起来了,最后一次吃绿皮火车的沙县小吃,是跟唐月一起去的。那时我还没把冯赫介绍给她,她住在一个八人间的破房子里。我进去过一次,那么小的房间竟然能挤上下铺共八张床,唐月的床在最角落的上铺,因为没有窗户,空气不太好,我记得当时我还摸了摸鼻子。
当时房间里还有另外三四个女子,都很年轻。我突然到访,唐月似乎有些慌张,说,你怎么来了?我说刚好在附近,打你电话不接,门没关,我就进来了,没打扰你们吧?
那几个姑娘都不吭声,表情却不友好。我说,走吧,我带你去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沙县小吃。我说完这句话后非常后悔,因为我马上想到自己不高不帅又没钱,而且请客吃饭通常都是多么豪爽大气的事,我却当着几个陌生姑娘的面大言不惭地说要请唐月吃沙县小吃这种不上档次的东西。就算这个沙县小吃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也依然是沙县小吃,根本弥补不了它的寒酸气。
我不记得唐月当时的反应了,只记得她骑在我摩托车后座,身上飘来花露水的香味,真的太好闻了。三年来我无论走在街上,还是在办公室、餐厅、公交车、电梯,无论闻到廉价的或是高档的,香水还是花露水,或是脂粉、洗发水、沐浴露……总之,再也没闻过那么好闻的香味。此香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果然,此香,已在天上了。香消玉殒,这个成语,我之前总觉得矫情呢,人能有多香呢?还不是人工香精制造的幻觉。我一直觉得人是臭的,不管多美的女孩,总会出汗,总要排泄,臭才是人的本质,只有仙女才不会臭吧?果然,一切早有暗示,唐月是属于天上的。否则,凭什么只有唐月身上能散发那么好闻的花露水味?
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喜欢闭上眼睛,也许这样有助于打开记忆仓库。我努力嗅,想把记忆仓库里的香味掏出来,哦,全世界最好闻的花露水,你在哪里?嗅着嗅着,我嗅到了另一种香味,来自于全世界最好吃的沙县小吃。记得当时唐月吃得很认真很投入,一句话不说,右手拿筷子,左手使汤勺,沿着手臂上去——不记得左手还是右手——是淡绿色衣裙的袖口。当时,我盯着那袖口恍恍惚惚。那淡绿色的袖口像一个隧道,而唐月正把自己从隧道里伸出来……
在绿皮火车沙县小吃店,我们几乎没有交谈,店里客人挤得满满的,嘈杂如菜市场,斩断了交谈的可能性。但我现在的回忆里却有新的内容——唐月并不是一句话没说,她左右开弓把热情投入于一碗大骨汤馄饨时,还是露出了那晚的缝隙,或破绽:她告诉我有个男人想包养她,出价二十万,她问我是贵还是便宜。
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记得自己当时怎么回答她。按常理,我应会冷嘲热讽,所以我会说:差不多啦,你也就值这个价。作为一个极其自卑又极其自尊的人,冷嘲热讽是我的常态。事实上,面对女性,尤其是自己暗暗喜欢的女性,我从来说不出一句正经话。
记忆发生了一点差错,也就是我不确定唐月那天晚上是否真的问过那句话,也就是不确定是否真的有个男人提出要用二十万包养她。但我很明确知道一件事,就是唐月肯定不会同意被人包养。如果她同意了,她就不是唐月,而是其他随波逐流的外地女孩,那么我对她的朝思暮想就是一个笑话,那么她身上就不会有那种遗世独立的花露水之香。
但我能肯定的仅仅是三年前的唐月,在×城的唐月会不会变成另一个人呢?我想象在×城公寓里,一个女人顺流而下。是啊,也许在×城,唐月就接受了被包养的命运。随波逐流是一件多么舒服的事啊,即使我现在所使用的想象力,也是顺着比逆着要容易,逆着,意味着要克服阻力,而阻力,真他妈讨厌。
这样,“我要去×城”这件事渐渐变得复杂起来,好像是我给自己设置了障碍,好像障碍本来就存在。
我特地去新华书店,想买一张×城地图,没买到。我索性自己画一张,按照网上地图的概样,加上其他信息补充,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力,虽然比例失调,但这不重要。地图里包含本城与×城,包含我和唐月存在过的场所:我家,我办公室,她租过的房子,冯赫的家,绿皮火车沙县小吃店,我们认识时的餐馆,我摩托车行驶过的路线,她所乘坐的火车车厢……至于×城,我的地图里除了画了一个叫“公寓”的标志,其余空白。
慢慢地,我发现地图渐渐丰富起来。首先在本城的左下角的某个位置,我標上“美芳珍珠奶茶店”。记忆有时不讲道理,莫名其妙就裂个口子。于是当我把手指尖停顿在“美芳珍珠奶茶店”时,唐月说:“障碍那么多,我要先跨哪一个?”我说:“对啊,就像跨栏比赛”。
美芳珍珠奶茶店是我一个同学开的,楼上有个露台。那时认识唐月没几天,她像一颗鲜亮的柠檬,还没被切开口子,还没被挤出柠檬汁。她穿着雪白的娃娃衣,对这个世界还充满幻想。她很认真地质疑我不应拿跨栏做比喻,“跨栏比赛的障碍物是一个一个按顺序排列好的,生活里的障碍是没有秩序胡乱把你围在中间。”那时她对“障碍”的理解就像我画的地图,纸上谈兵,掷地有声,振振有词。三年后她站在×城公寓里,手握剪刀,有意或无意朝自己开刀,不知对“障碍”的理解加深了没有?而我发现“理解”这个词本身就很可笑。
我的手指沿著摩托车路线再一次停顿,这次我画了一个“新世纪夜市”。
我带她骑摩托环城一周。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约我。我不记得这次是否闻到花露水。记得自己多次有什么话想说,却欲言又止。记得她心情不好,表情黯淡。不记得这次见面的时间刻度停在冯赫之前还是之后。记得她说我是她唯一的朋友。记得我听到这话还冷笑了一下。记得她说了对未来的憧憬。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冷嘲热讽。
记得我把摩托车停在新世纪夜市门口。夜市就是夜里一排一排摆地摊,卖的都是廉价货,名字却叫“新世纪夜市”,我忍不住回神,手指尖抖了一下,笑出声来。唐月在前面走着,我在后面慢吞吞跟着。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心不在焉,因为她的背影就像一个梦,我在梦里呢,在梦里就该吊儿郎当。梦,是绝不能当真的。唐月东看西看,她好认真啊,她以为她不是一个梦。她停在一条裙子前,跟摊主讨价还价。摊主伸出粗糙的五个手指:最低五十块。唐月说太贵了。却不舍得走开。我在三米外站着,把手伸进裤子口袋,口袋里有一叠钞票,那是我刚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纸钞,每一张都崭新发亮。但我的手指却前所未有的游移不定、彷徨失措、踌躇不前。当唐月终于离开那个摊位,我才松了一口气,此时我的手指仍在细细摩挲那叠钞票,其实它不厚,甚至轻薄,但因为太新了,它的边缘摸起来有一种锋利的质感。
我长得不帅,个子不高,家里没钱,一无是处,所以我的自尊心特别大。自尊心仿佛是我唯一的财产,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爱护它。
离开新世纪夜市,我的手指尖沿着摩托车路线又一次停顿,这次我画了一个“城西大桥”。桥下是蓝黑色的河水,桥上有嗖嗖的风。我依稀记得我们站在桥上是为了吹风。对啊,我想起来了,当时她穿着一件白色圆领T恤,面对幽幽的河水,五指抓住领口说:“领口好紧,喘不过气来,真是要命。”
房间里开着空调,我也在冒汗。我看看日历,看看自己的手绘粗糙地图,思考要买几号的火车票。×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要呆几天?请几天假?怎么跟领导请假也是个问题,想到领导那张鼠标垫子一样的脸,我的心脏都想龟缩起来。活着真麻烦,好像每一步都隐藏障碍。我也没想到,原先那份想去×城的热情,如此经不起推敲和打磨。对啊,连我都在考虑值不值得,那么,我跟冯赫有什么区别?唐月的死,与我何关?
胡思乱想的结果是难受,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失眠,凸显这个夜晚的空洞。我的手在凉席上滑动,想到唐月的身躯也曾安放在×城公寓的某张床上,也许她的手也这么滑动。现在,她不再需要任何一个×城,任何一个房间,任何一张床,有一天,我也会跟她一样,什么也不需要,世界也不需要我,就好像我从来不存在,简直自由了,真是个笑话……
如果我给她买下那条裙子呢?最低五十块。五十块不就是一个屁吗?可是,买了又如何?买下那条裙子就能阻止唐月面对幽幽的河水撕抓自己的领口吗?我发现我的手正抓住汗衫领口,领口已湿成一大片,恍然大悟:唐月身上那件圆领T恤也是一个障碍,那么紧的领口,难道三年前命运就暗示了唐月的死法?“领口好紧,喘不过气来,真是要命。”
我反复暗示自己:唐月不是一个屁,她是一个月亮。所以我来到了火车站。我需要一张车票,去×城只需要一张车票。可是到了×城,我如何找到那个公寓?我没有唐月公寓的地址,我犹豫着要不要去问那个公安局的朋友,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对方未必会卖我这个人情,毕竟这是一个不该被关心的事件,一个安静的自杀事件。对方如果拒绝我,我的自尊心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因为我是一个一无所有却有一颗硕大自尊心的人。
在火车站,我看到一个背影很像唐月的女子,我的魂魄仿佛被这个背影勾走。我尾随其后,耐心等待她转过脸来。我没有等到,她消失在一个拐角。我将永远不能知道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是否像唐月一样有一张清亮又苦涩的脸。对啊,事情就是这样,各种琐碎的障碍克服了我,我终究没能去到×城。
作者简介:
张漫青,1984年出生,福建三明人,现居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