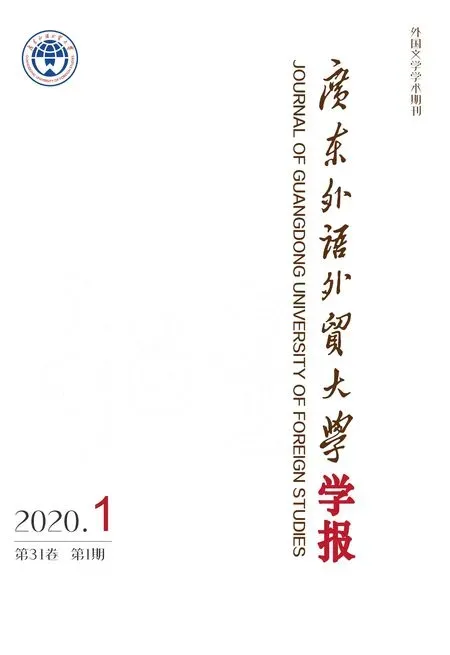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温顺的人”与圣像
俞 航
十九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品中刻画的“温顺的人”女性形象根植于俄罗斯传统,与东正教有着紧密的关系。“温顺的人”通常具有谦逊的、充满同情心的、乐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而这些特征又是虔诚的基督徒所具备的。她们有时象征了阴性的俄罗斯母亲,有时则以女圣愚的形象出现。西方派男性与她们的关系往往表现了精神或者肉体上“漂泊者”与俄罗斯母亲的关系。迄今,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类女性形象已经得到学界一定的关注与研究,同时,学者也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类女性形象上所寄托的宗教理想。但是,通过“温顺的人”与圣像之间的关系来阐释这一宗教理想的研究尚有深化的空间,海外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借鉴。“温顺的人”与圣像之间的关系展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的一个重要层面,即她们所具有的圣像之美能促使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分裂型知识分子以及周围罪恶的世界完成宗教意义上的变容(transfiguration)。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温顺的人”与圣母像的原型非常接近,并且她们以两种方式对周围世界施加着影响:首先,作为与上帝交流的工具,圣像邀请观者参与神圣的转变,而“温顺的人”通过圣像美来使周围的人触及神圣的原型,使他们发生转变。第二,具有圣像美的“温顺的人”进入了文学叙事中包含圣像系统的视觉结构,即文本对圣像的符象化(ekphrasis),成为叙述的圣像(a narrative icon)。这是视觉和文本结合对圣像进行的再现,即形象被语言所表达(Hutchings,1997:37)。
“温顺的人”与圣母像的互动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与“温顺的人”关系最紧密的圣像类型是圣母像。对“温顺的人”与圣母像互动的描绘最具代表性的是《女房东》和《温顺的人》。虽然就发表时间而言这两部作品几乎间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创作生涯,但是女性与圣像之间的联系是一脉相连的。《女房东》创作于一八四六年,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通过西欧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镜像来反思俄罗斯传统的东正教价值观。主人公奥尔登诺夫有着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是一个典型的浪漫派、梦想家,离群索居,建构自己的体系。但不同于俄国社会传统的梦想家,他热爱“科学”。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国语境下,这种“科学”暗示着乌托邦社会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个人物寄予同情的同时,也责备他脱离社会,忽略了宗教,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四十年代的西方派应该为当时弥漫俄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虚无主义负责。这种态度可以从奥尔登诺夫过度陷于自己的“体系”而丧失信仰及无意识中走到教堂后遇到祈祷的卡捷琳娜时产生的震撼之间的鲜明对比体现出来。
圣母像在《女房东》中出现了三次,均与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相关。第一次是奥尔登诺夫离群索居多日,在大街小巷游荡,恍惚间走入一间教堂偶遇卡捷琳娜。那时已近黄昏,余晖洒落在静谧无声的教堂中。太阳倾斜落下的光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一个重复出现的主题,它与欢乐、永恒的生命、基督相关。在这里,当教堂中的光线变得昏暗,而教堂逐渐被黑暗占据时,圣母像的光芒照亮了教堂。正是在这一光芒之下奥登诺夫与卡捷琳娜相遇。卡捷琳娜在圣母像前的祈祷让奥尔登诺夫有了第一次宗教体验:“祭坛边上的圣母像被照得光彩夺目……奥尔登诺夫对整个庄严肃穆的场面感到非常惊讶,他焦急地等待着看它如何收场。大概过了两分钟,这女人抬起头来,灯光再次照亮了她秀丽的面孔。……震惊之余,奥尔登诺夫在一种从未有过的甜蜜而又执拗的感情驱动下,紧跟他们后面,快步向前……”(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423)。奥尔登诺夫被这种力量所吸引并慢慢地发生了改变。随后他发现,卡捷琳娜因内心世界备受折磨而在圣母像前祈祷。她被一名叫穆林的老人控制着,穆林事实上是她的亲生父亲,他为了独占私生女卡捷琳娜,杀害了她的父母和未婚夫,并让卡捷琳娜深信这一切罪孽都是因她而起,以此将她控制在自己身边。
卡捷琳娜是传统的俄国女性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她命运的思考是通过她与圣母像的关系以及她所具有的宗教力量对两位男性的影响所展现出来的。在西方派奥尔登诺夫身上,卡捷琳娜在圣像前祈祷的画面启发了深陷西欧“科学”中的奥尔登诺夫的宗教天性。他通过卡捷琳娜的祈祷接触到神圣的原型,感受到俄罗斯传统东正教信仰的力量。奥尔登诺夫在离开卡捷琳娜之后开始祈祷,卡捷琳娜成为他心目中圣像般的形象。而在旧教徒穆林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展现出传统东正教在某些方面不是通过自由的信仰,而是通过“恐惧”来控制信众。他像宗教大法官那样通过奇迹、秘密和权威来控制“温顺的羊群”。穆林可以说是卡捷琳娜与圣像之间的中介,表面上看,是他使卡捷琳娜不断地在圣母像前祈祷,但事实上他却需要卡捷琳娜的祈祷来安抚自己的内心。穆林无法在圣像前祈祷,这显示了他缺少同情和怜悯。他或许感受到圣像面容上的神性,但他无法注视它,因此他必须将卡捷琳娜控制在自己身边。而卡捷琳娜更像是古老的俄罗斯的化身,她心中有着虔诚的信仰,但同时也有着对充满力量的恶的无意识渴望。例如,卡捷琳娜被穆林囚禁,虽然非常痛苦,但却享受这种被囚感的感觉。但她通过在圣像前沉思,克服了那种在堕落中寻找乐趣的诱惑。因此,穆林意图通过宗教来压制卡捷琳娜,结果反而动摇了他的原先假设。通过卡捷琳娜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了传统俄罗斯女性与东正教之间天然的紧密联系,同时强调了传统俄罗斯女性的矛盾性,一方面经历了邪恶的诱惑,另一方面则是对净化的渴望。圣像确证了救赎的可能,但是要实现这一可能,它必须变成沉思和祈祷的对象。在小说中,只有卡捷琳娜自始至终将圣像作为祈祷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温顺的人”卡捷琳娜与圣母像的互动展现了宗教思考。他认为东正教在俄罗斯民族文化观念中至关重要,但不同于美化前彼得时代的斯拉夫派,他否认俄罗斯精神是静止的。相反,在《女房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了一个处于持续变化过程中的俄罗斯:普通人还未发现真相,但他们力争去发现;至于知识分子,他们要达到真理必须接近俄国普通人,并且尝试去理解宗教信仰和俄罗斯本性的道德精髓。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的《作家日记》里探讨了当时俄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包括女性问题,如女性犯罪与女性自杀。《温顺的人》正是发表于这一时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注的妇女问题紧密相连。罗伯特·别尔克纳普(1990:47)把这个故事称作“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写过的最触及个人隐私、最富情感、最具宗教意识以及互文意义上最感人的篇章”。作品中的丈夫在妻子死后喃喃自语正是作者自己的真实经历。同时,《温顺的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性别差异刻画得最深刻的小说之一,它构筑了因为男性支配的文化而丧失了的却又必须在男性想象和忏悔中被找回的女性主体,这一过程同样与圣像和宗教信仰紧密相连。作品以男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展开,但男性独白却没有覆盖掉“温顺的人”作为主体的声音,她的声音是通过男性的意识发出的。圣母像在作品中出现多次,“温顺的人”将自己唯一的圣母像典当给当铺老板男主人公,在最后她怀揣圣母像自杀。
作品中的丈夫是希望通过控制他人而获得内心尊严的当铺老板,他的当铺生意并不能给他带来这种满足感,因此他娶了一位贫苦无依的姑娘,希望通过施舍和控制获得妻子的尊重。当他发现“温顺的人”有着自己的信仰和神圣的原则时,他便千方百计摧毁她的信念,最终导致她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男性独白揭示出丈夫的心理,他代表着宗教怀疑主义、对两性关系的不信任和对眼前利益的追求,同时他将这些因素上升到形而上学层面。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他的焦虑和缺乏安全感。因此,他病态地追求生活的稳定,希望妻子的屈服成为一种替代品,填补他理想的缺憾。不同于其他虚无主义的男性主人公,丈夫并非完全没有信仰,例如他自己也保存着圣像,他甚至在圣像前点灯。但他的信仰同《女房东》中的穆林一样,是“奇迹、神秘和权威”的信仰,而不是爱的信仰。他还要求妻子将她的自主权转交给他,正如宗教大法官要求人们“把他们的自由的负担扔在他脚下”。
“温顺的人”的原型是名为玛利亚·鲍里索娃的女裁缝,她因为生活的困苦怀抱圣像跳楼自杀。但她死前并没有激烈地控诉社会的不公,所有的一切都被她埋在心里,并被死亡带走。这种温顺的、平静的自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震撼不已。相较于他之前听闻的赫尔岑的女儿在国外自杀(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她出生和成长在国外,成长在一个弥漫着无神论和社会主义氛围的“偶合家庭”中,因而与故土的信念无关),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种手捧圣像、温顺的自杀更能反映俄罗斯传统女性的苦难,“圣像(圣母像)表明,该女子并非无神论者——在自杀行为本身中,受害者证实了自己的信心”(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226)。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的社会思考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温顺的人”与现实中女裁缝一样生活困苦。但不同的是,就物质生活而言,“温顺的人”并没有活不下去,她的自杀是为了确证自己的主体性,而这个过程是自始至终在信仰中进行。当丈夫像宗教大法官一样,将人类间的交往简单地归于弱者和强者之间的权力斗争。“温顺的人”却像基督一样,她的力量并非来自武力或辩论,而是来自她对生命的全新诠释,来自以身体语言和沉默传达出信息。她希望“成为主体”,渴望积极的自由。这种积极的自由,根据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是主体有自由去追求,而不是仅仅不受干涉(消极的自由)。不受干涉的“消极的”自由则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和斯塔夫罗金梦寐以求的,也是宗教大法官所实践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世俗的、以金钱为中心的社会问题,也是现代性语境下妇女问题的关键。积极的自由所实践的路径并非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主义,也不是宗教大法官的“奇迹、神秘和权威”,而是信仰。圣母像是“温顺的人”一生的目击者,也是陪伴者。不同于赫尔岑的女儿那样怀着对线性生命的愤懑而死去,“温顺的人”的死表现了对信仰的确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改变父权统治这一首要任务,可以被纳入现代思索的一部分。传统女性与那些尚未被“上帝已死”的怀疑主义所掌控的对信仰仍然持有信心的灵魂相通。同时,女性有权去揭露男性话语统治和“杀死上帝”的消极自由的罪恶。进一步,她们所展现的圣像之美对男性有着变容的力量,在《温顺的人》中,丈夫逐渐认识到自己对妻子的爱,最后,他在呼唤上帝的同时认识到妻子对自由的渴望。
“温顺的人”具有圣像美
罗文·威廉姆斯(2009:190)注意到新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艺术、美学和美的角色高涨的兴趣,尤其是与东正教圣像学传统相关,并认为,“在他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关于圣像的部分可以讨论更多。”理想化的美和救赎等圣像学的成份处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熟时期作品的中心。圣像理想不仅通过对真实圣像的涉及和刻画显示,也通过对具有圣像美的人物的再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圣像般的再现(iconic representation)来追寻对理想美的终极表达,部分原因是作者牢狱经历引起他的精神状态变化。他最初对审美理想的关注转变为对人类的宗教和道德存在的关注,并发展为认为是圣像美(iconic beauty)而不是审美(aesthetic beauty)是人类的最终救赎。在作家的后期长篇小说中,具有圣像美的角色在象征意义上将观看者从物质的状态转换为精神的,激发人类灵魂中隐藏的理想之美。具有圣像美的人物有着内在和外在的表现,内在的往往显示为谦逊、温和、智慧和无私。而外在则与人物的外形相关,包括面部表情和色彩的象征意义。罗伯特·杰克逊(1966:47)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男性主人公,特别是梅什金公爵阿廖沙,是作家受基督的形象激发灵感而创作的,而他的女性人物则唤起了相关的圣经女性形象,例如,《白痴》中娜斯塔霞·费利帕夫娜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群魔》中的玛丽亚·沙托娃则是怀孕的圣母玛利亚。“温顺的人”,如《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少年》中的索菲亚,《群魔》中的达莎等,都是表现了圣像美的女性形象,她们对周围世界施加转型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只有女性才在圣像前祈祷。通过在圣像前的沉思,她们变得与神圣的原型十分相似,代表着被偶像威胁的世界里救赎的圣像般的形象。虽然她们并不积极行动,保持沉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她们身上展现的圣像之美寄予了俄罗斯宗教精神重生的希望。
在《罪与罚》中,当拉斯科利尼科夫杀害了高利贷老太婆之后,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并不是法律的制裁,而是他杀死了上帝赋予神性的主体。杀人之后他陷入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将自己封闭起来,生活对他而言失去了意义。索尼娅的出现以及所展现的圣像般的美使拉斯科利尼科夫逐渐走上了救赎与复活的路途。索尼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中所塑造的第一个较为完整的代表基督徒美德的女性形象。她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谦卑等特质都体现了圣徒的特质。她的圣像美是道德中介,推动着周围世界的改变。
《少年》中具有圣像美的“温顺的人”形象是少年阿尔卡季的母亲索菲亚。东正教对于如何使普遍关怀成为可能的回答是神恩。但是阿尔卡季的生父韦尔西洛夫却在梦境中和他的思想体系中触及这样一个世界:人类某一天醒来,发现他们在宇宙中变成孤独的生物,没有上帝和永生,他们只拥有自己,这种孤独让人类不知所措。最终韦尔西洛夫认为,通过人类互相体贴和关照,世界成了另一个天堂。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上帝死去”后的人类社会给出的药方,这一部分来自卢梭的关于同情的命题,即人类本性的仁慈,但另一部分却来自东正教的“爱邻人”教义。“西方派”韦尔西洛夫可以理解这个药方的第一部分,因此对阿尔卡季说,“我始终需要你的母亲”,他在欧洲流浪的时候一直将索菲亚带在身边。特别能体现索菲亚圣像美的是韦尔西洛夫十分珍爱的一幅肖像,“在这张照片上,阳光正好抓住了索尼娅最具本色的瞬间——羞涩而温顺的爱,有点儿腼腆的、胆怯的纯洁。”随后,韦尔西洛夫坦诚,索菲亚就像很多俄罗斯女性一样,为了所爱之人,牺牲了美貌,即“俄罗斯女人很快就变得难看,她们的美貌只是昙花一现,其实这不光取决于民族的典型特点,还因为她们善于为了爱而舍己忘身。俄罗斯女人一旦爱上了谁,就会马上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昙花般的美貌、她的整个命运、包括她的现在和未来:她们不会计较得失,不会留有余地,于是她们的美貌很快就会在她们所爱的人身上耗尽。这干瘪的双颊就是她为了我、为了我短暂的欢乐而耗尽的美丽”(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616)。但是,“西方派”韦尔西洛夫直到小说最后都没能向超验的神恩开放,完成变容,甚至在马卡尔的葬礼上砸毁了索尼娅的圣像。他拒绝在灵魂上回归俄罗斯土地和人民,索菲亚的圣像美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因为韦尔西洛夫没有明白,索菲亚的爱不仅仅是他所理解的凡俗之爱,而且包含有超验维度的爱。
《群魔》中的达莎是另一位具有圣像美的“温顺的人”,她与斯塔夫罗金之间的关系隐于文本之后扑朔迷离。叙述者并未获得描述她内心世界的视角,因而读者只能通过她的行为、语言、外在描绘来了解她。从已知的描写中,读者看到的是一位温顺、沉静、富有同情心的女性。有研究者将达莎放入以普希金的《黑桃皇后》中的利扎薇塔·伊万诺夫娜开始的描绘俄罗斯侍女传统的文学画廊中,并认为在达莎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普希金的开放式情节的模棱两可转化为巴赫金所认为的角色作为人的“未完成性”(Grenier,1998:113)。达莎是被作为“新女性”丽莎的对立面和卖圣经的女子索菲娅的“化身”来进行描写的。在新女性丽莎看来,达莎显示了“奴仆般”的温顺。在外貌上,相较于丽莎的“黑眼睛”“燃烧般的目光”“响亮的声音”,达莎是“浅色眼睛的”“安静的”“单调而虚弱的声音”。不同于丽莎的索取,达莎更多的是给予,因而对于斯塔夫罗金来说,达莎是理想的救赎。但斯塔夫罗金害怕会像毁灭其他女性一样毁灭达莎,面对这一危险,达莎却非常坚决:“……您永远也毁不了我,您也没法把我给毁了,这点您知道得比任何都清楚。如果我不来找您,我就去当护士,当陪床的,我就去伺候病人,或者去当《圣经》推销员,卖福音书……”(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261)在“决斗”这一篇章中,斯塔夫罗金对自己“爱无能”的确信达到了顶峰,而相伴随的却是达莎发自内心的爱与善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然而斯塔夫罗金最终走向了自杀的结局,无论是达莎还是吉洪神父,都没能够拯救他的灵魂。“尽管达莎和玛利亚都体现了道德美,她们没能够在斯塔夫罗金身上形成长久的正面影响,他是圣像原型的对立面,因而在小说的结尾并没有提供内在美与非道德之间的和谐。除了他有教养的行为和不寻常的完美面容,斯塔夫罗金事实上是一副面具,是假的圣像,他的完美特征隐藏了反基督倾向和很多内在的和外在的关于撒旦的暗示。他那充满诱惑力的美,与他姓氏的象征含义所结合,即角(рог)的变形,唤起了撒旦的形象……斯塔夫罗金是反圣像,表现了基督之美的反面”(Gaal,2015:88)。因为与俄罗斯失去了一切联系,斯塔夫罗金无法找到一个生活的目标,他那自我流放的打算是切断这所有联系的最终象征。尽管达莎渴望首先从精神上,然后从道德上,使斯塔夫罗金回到俄罗斯,但最终依然无法拯救他。但是,达莎的圣像美成为复调话语的一部分,斯塔夫罗金选择自我毁灭的最终结局并不能减弱其道德上的力量。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哲学的至高点,描述了形成基督教家庭乃至基督教社会的重要道德责任。该书以父子关系贯穿全书:与阿廖沙相关的两位父亲般的人物——血缘父亲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和精神父亲佐西玛长老——以及阿廖沙与孩子们的关系。阿廖沙是圣像美的代表人物,但我们不能忽视具有圣像美的“温顺的人”在小说中的作用。这便是阿廖沙与其母亲之间的母子关系。虽然母职在他成长过程中是缺失的,但他受到母亲的虔诚以及关于圣母像的回忆的影响。阿廖沙在精神和气质上继承了母亲,老卡拉马佐夫指出,“你意识到吗,你很像她。”阿廖沙对母亲的记忆与圣像相关。“他母亲死的时候他才三岁多点儿,可是后来他却一辈子记住了她的模样、她的脸和她的爱抚。……他记得有一天傍晚,夏天,静悄悄的,洞开的窗户,落日的斜晖(他记得最清楚的便是这一束斜晖),室内的墙角供奉着圣像,圣像前点着一盏长明灯,他母亲跪在圣像前,在歇斯底里地失声痛哭,又是尖叫,又是哭闹,两手搂着他,紧紧地抱着,都把他抱疼了,她替他祈祷圣母,她伸直两手,把他举起来,举向圣母,似乎在祈求圣母的庇护……就是这幅画面!就在这一瞬间,阿廖沙记住了自己母亲的脸:他说,就他记忆所及,他感到这张脸是疯狂的,然而又是十分美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21)。女性那在圣像前祈祷美丽的面孔散发着神性的光晕,深深印刻到阿廖沙的心中。事实上,这张脸上的神性是与夕阳余晖中的圣像分不开的。因为“与圣像面对面的时候,人物展现了他们最深的自我,而且圣像对他们的影响将源于这一姿态(指的是与圣像面对面)”(Ollivier,2001:63)。母亲的面容和面容上圣像般的神性让阿廖沙铭记一生,而阿廖沙那与母亲十分相似的温顺的脸和其中透露出的温情与爱让亵渎圣像的老卡拉马佐夫归还了属于阿廖沙母亲的圣像。他人面容的敞开给老卡拉马佐夫提供了一个面对自我的主体间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暗示了救赎的可能性。同时,老卡拉马佐夫还允许阿廖沙回到修道院,使他可以继续跟随佐西玛长老学习。考虑到这件事发生在老卡拉马佐夫被长子德米特里袭击之后,我们可以认为“温顺的女性”与圣像重建了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父子关系。
“温顺的人”进入文本圣像系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可以被置于在话语中敞开的形象——东正教的圣像这一维度来思考,现实主义不光是对现实的刻画,还包括对形而上领域的描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话语诗学遵循了“道成肉身”的东正教教义,文学不但获得了展示词汇的能力,而且获得了展示形象的能力,“能够将被封闭的世界中的形象最相符地表现出来,并在词语中敞开的,是东正教的圣像”(Касаткина,2004:22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西伯利亚长篇小说都从不同程度上展示了文本中的圣像,而“温顺的人”则多次进入这些圣像视觉结构之中。
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犯罪前最后一次前往高利贷老太婆家察看情况时,他看到在角落里一幅小小的圣像。而他在杀死老太婆之后从后者的脖子里拽出了一幅圣像。拉斯科利尼科夫在索尼娅面前忏悔之后,索尼娅给了他一个十字架,并告诉他这是她用圣像同莉扎薇塔(高利贷老太婆的妹妹,同样被拉斯科利尼科夫杀害)换来的。“从象征层面理解,圣像出现在拉斯科利尼科夫道德发展三个重要时刻的前景中:谋杀前,谋杀本身,忏悔。这样的模式多次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亦即,圣像从最初的偶然事物及描述性的功能转化为更具活力的功能,并且越来越接近主要事件的象征核心”(Jefferson,2004:15)。拉斯科利尼科夫希望通过以利他主义为基础的理性推导来为自己的行为构建合理的论证,但是最终却发现他的行为导向了利己主义。而索尼娅则与他相反,虽然看似孱弱而沉默,但却象征了向他人开放灵魂力量。同时,索尼娅不但表现了救赎,还是“救赎”方式的原型,即亲自向拉斯科利尼科夫展示了可见的形象——圣像。
最初拉斯科利尼科夫没能够看到索尼娅所揭示的圣像般的救赎,要让一颗个人主义的心灵摒弃偏见、向神恩敞开是极不容易的。当他听说索尼娅和利扎薇塔曾一起读新约的时候,他将她们称为“圣愚”。此时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带着知识分子的蔑视,认为她们的宗教信仰是愚昧的。但是在长期的内心折磨以及情感的作用下,他祈求索尼娅给他读约翰福音中拉撒路的复活,这代表了他的内心逐渐向救赎开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伦勃朗蚀刻作品那种简洁色调描写了这个令人震撼的场景,“插在那个歪斜烛台上的残烛已快熄灭,黯淡地照着陋室里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卖淫女,他们奇怪地凑在一起读这本永恒之书”(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416)。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教会斯拉夫词语блудница代替更为口语的проститутка,因此将索尼娅与抹大拉的玛利亚,而拉斯科利尼科夫与拉撒路联系起来。②
在《罪与罚》结尾处索尼娅再次与圣经人物联系起来,而这次是圣母玛利亚。入狱之后,拉斯科利尼科夫不明白为何苦役营的犯人都那么喜欢索尼娅,“……但渐渐地,他们与索尼娅之间建立起某种亲密的关系:她替他们给亲人写信,并帮他们把信寄走……有时她去工地找拉斯科利尼科夫,或者同正去上工的一批囚犯相遇,所有囚犯都会脱下帽子,向她打招呼说:‘妈妈,索菲娅·谢苗诺夫娜,你是我们的母亲,温柔亲爱的母亲!’那些脸上烙印的粗野囚犯对这个瘦小的女人这样说话……”(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688)。苦役犯们将索尼娅看作圣母般(образ Богородицы)的女性,他们立刻就认出了她的形象并爱上了她。就像俄罗斯传统圣徒对某些社会阶层所起的保护作用,索尼娅成为苦役犯的保护者和帮助者。在东正教传统中圣像是将这些保护者——圣徒——刻画成圣像的。但是拉斯科利尼科夫却没能够像其他人那样真正“看到”索尼娅,“这是非常典型的,即苦役犯与索尼娅之间的关系对拉斯科利尼科夫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他作为一个非信徒并未看到周围的启示,我们说的正是这一点:信仰与不信仰界定了看见与不看见,当谈到犯人对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的原因时,二者彼此相通”(Касаткина,2004:229)。直到拉斯科利尼科夫在发烧中做了启示录般的噩梦以及随后索尼娅生病中断见面一段时间,他才突然明白索尼娅的重要性。他的心灵与春天(复活节第二周)的万物一起复苏。
此时,索尼娅出现了,“她悄悄走到跟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天色还早,严寒尚未散尽。她穿着破旧的斗篷大衣,扎着绿头巾,脸上还留着病容:消瘦、苍白、憔悴。她亲切而又高兴地对他微微一笑,仍然往常一样胆怯地向他伸出了自己的手”(陀思妥耶夫斯基,2002:691)。在这幅与拉斯科利尼科夫精神复活息息相关的画面中,索尼娅头巾的颜色是绿色的——大地生命的颜色,是与圣母相关的颜色。绿色在刻画圣母的圣像中十分普遍,例如费拉波托夫修道院里的圣母大教堂(собор Рождества Богородицы в Ферапонтовом монастыре) 的《指路者圣母像》(Богоматерь Одигитрия,现藏于圣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被描绘为身披着绿色的斗篷。而德米特洛夫(город Дмитрова)的乌斯宾斯基教堂(Успенский собор)来自狄奥尼修斯(Дионисий)工作坊的著名圣像《“为你道喜”圣母像》(О тебе радуется,现藏于莫斯科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美术馆),描绘了圣母怀抱圣子坐在绿色的宝座上。因此,从圣像学的角度而言,索尼娅温柔而充满生机的绿色围巾可以被看作如冠冕(венец)一般的宝座。
Касаткина认为还有一幅圣像与《罪与罚》尾声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最终“认出”索尼娅相关,那就是《罪人的保佑者》(Споручница грешных):“在我结束汇报的第二天,我们去了胡定修道院(Хутын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在那里维持着杰尔扎温的安魂弥撒,他们去考察那座教堂。那里有一些圣像。其中大多数(超过五幅)——其中就有自身就十分特别的‘罪人的保护者’——都不是最为普遍的类型。但是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几乎所有圣像都将圣母刻画为围着绿色的头巾。尽管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对事件比较随意的阐释,但我接受这成为对我的猜测的进一步确证”(Касаткина,2004:231)。同时,卡萨特金娜指出将对“绿色”的头巾象征含义的猜测放入整个小说系统来看更有说服力。这一绿色头巾可以对应于在拉斯科利尼科夫的梦里出现过的教堂的绿色拱顶,在“马被鞭打”的梦里,这座教堂是他童年时期所看到的,“在墓地中间是一个有着绿色拱顶的教堂,每年他和爸爸妈妈都会去两次,去做弥撒,那边他供奉着他祖母的安魂弥撒。”(Касаткина,2004)拱顶是教堂的冠冕,而在《罪人的保佑者》圣像中,圣母通常被刻画为戴着王冠。当拉斯科利尼科夫走向索尼娅,意味着他走向童年时期的教堂,也意味着信仰在他灵魂中复苏。
《群魔》是一部整体氛围十分阴郁的作品,结尾除了谢尔盖·涅恰耶夫的原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几乎所有的主要角色都死亡。但在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掀起的腥风血雨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留下了救赎的希望。其一是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踏上拯救之路。斯捷潘因内心不可名状的冲动,离家出走。他路遇农夫,问他是不是要去斯帕索夫,而斯帕索夫(Спасов)意味着救赎(спасти),指向最终的复活(воскресение)。在路上,斯捷潘奇遇到圣经兜售者索菲娅·马特菲耶夫娜(Софья Матвеевна),这个女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因为她,无神论者斯捷潘在三十年后再次接触了圣经。而索菲娅的名字也有宗教含义:索菲娅(Софья)为希腊语的智慧(премудрость),马特菲(Матфий)为希伯来语的天赐(богодарованный),即象征了天赐的智慧。最终斯捷潘死在了寻求救赎的道路上,并在死前皈依了上帝。与他相关的三位女性瓦尔瓦拉·彼得罗夫娜、达利娅·帕夫洛夫娜与索菲亚·马特菲耶夫娜在他去世时组成一幅象征意义上的圣像,即基督坟墓旁三个拿香膏的女人。
手持香膏的女子形象成为确证复活的形象。在种类型的圣像里,我们看到天使在宣告基督死后的复活以及永恒的生命。妇女们手持香膏谦卑而安静地站在棺木旁。但棺木中空空如也,在远方是耶路撒冷城粉红色的城墙。基督在为他们指明通往加利利之路。③在最后的场景中,斯捷潘·特拉菲莫维奇既是宣称永恒生命的天使,又是指出这条道路的基督。在十六世纪俄罗斯艺术中广泛存在着坟墓前的持油膏的妇女形象与复活的基督相联系的圣像。“在圣像中,在圣母的领导下,女子们安静地鞠躬,她们平静地手持罐子。戴着白色面纱的天使坐在棺木旁,向她们布道。远方是粉红色围墙的耶路撒冷城,上方是高耸的山脉。在那里,离开了棺木的耶稣基督向她们指明前往加利利的道路。在飘扬的长袍之上,基督向人们敞开一张明亮的面容,向人们指出一条道路,这条道路通向他的复活”(Барская,1993:116-117)。
在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死前,他不停地重复“上帝之爱”的话题,并回忆起生命中的很多人和事,他总说:“见到你们所有人”。但事实上此时包括丽莎、沙托夫在内的大多数人物已经死亡。“在古代,复活是用持油膏者的描述来指示的,后来根据尼哥底母的伪经福音,复活开始被指定为下降到地狱的故事。但基督越过了地狱,‘死亡的死亡,在那些坟墓里赐予生命。’即将那些在他到来之前堕入地狱的人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基督在这样的圣像描绘中重建了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Касаткина,2004:246)。《群魔》开端伊始,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在魔鬼的引诱下失去方向的群猪描绘了对上帝道路的背离,最终导向一场启示录般的大混乱;结尾处,他希望通过最终斯捷潘寻找上帝的努力来使所有人获得救赎。旧亚当打破了人与上帝的盟约,新亚当基督则重建了这种联系。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在小说中既是旧亚当们的老师,也是新亚当们的先在,在整部小说中他的旅途就是人向上帝重返的旅途。而“温顺的人”所组成的圣像“基督坟墓旁三个拿香膏的女子”正是这一旅途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对“温顺的人”这类女性形象的刻画与宗教思想的表达相结合。在创作生涯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了一系列与圣像进行互动的“温顺的人”,并在其中融入了对俄罗斯人信仰重生的思考。“温顺的人”是俄罗斯传统女性,她们谦逊、虔诚、富有牺牲精神。她们身上所具有的圣像般的美为孤独的西方派知识分子打开了通往神性的窗户,并促使他们回归俄罗斯母亲。同时,面对宗教信仰逐渐崩塌的俄国社会,对基督圣训保持忠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试图在创作中描绘俄罗斯人信仰重生的过程,因此他的文本中存在着圣像维度,语图关系在其中达到和谐。“温顺的人”则多次出现在文本中的圣像视觉结构中,她们所蕴含的宗教讯息承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救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