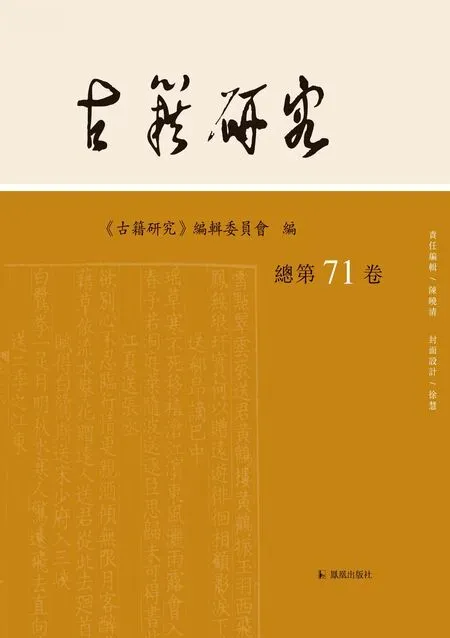《南山集》案與方貞觀*
代利萍
關鍵詞:《南山集》案;方貞觀;心態;詩學思想
嚴迪昌先生指出:“桐城文學自錢澄之、方以智父子等人而後,原自有所傳承,唯《南山》一案後,該地邑文風發生歧變。這種歧變簡言之,即批判理念失落,錢澄之以來詩文中的鋒鋭的批判性日漸消散。按批判性必悖背趨從、依附性,凡思想識見不能自持、人格獨立之個性不能自守,焉得言批判理念?”(1)嚴迪昌:《從〈南山集〉到〈虯峰集〉——文字獄案與清代文學生態舉證》,《文學遺産》,2001年第5期,第77頁。《南山集》案作爲康熙朝文字獄的一大高峰,使桐城士子思想委頓,批判精神失落,甚至使桐城文風歧變。其中方貞觀因《南山集》案被流放長達十年,其心態、詩風發生了明顯的轉變,詩學主張與詩學理想相抵牾。貞觀作爲桐城名士,以其轉變來觀照《南山集》案對戴氏、方氏家族士子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以此管窺文字獄對清代士子的影響,探知清代文學生態也有一定參照意義,而目前尚未有學者論及。
一、 《南山集》案與方貞觀
“方貞觀,字履安,號南堂。生而穎異,里稱神童,事嗣母王氏,以孝聞。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工詩善行楷,名噪淮揚,間爲盧雅兩運使所推重。既以事牽累,徙居京師,時與縣孫文定居館職,從之學詩。至雍正十三年,詔開宏詞科,文定首舉貞觀,貞觀以詩謝之,堅辭不就。終於家”(2)《康熙桐城縣志道光續修桐城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安徽府縣志輯》(第12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62頁。。方貞觀(1679—1747),少有詩名,然屢落秋試,後絶意進取,於康熙五十二年(1713)因《南山集》案遭流放,雍正元年(1723)得以赦歸,雍正十三年(1735)舉博學鴻詞不就。著有《方貞觀詩集》六卷,詩話《輟鍛録》一卷。
《南山集》案起始於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趙申喬據戴名世所撰《南山集》、《孑遺集》控告其“倒置是非”、“語多狂悖”,其實戴氏所言僅明末史實。“戴案發時適值所謂‘朱三太子’‘一念和尚’殘明遺胤懸疑之案未戢而康熙兩次廢太子事件峻急時”(3)嚴迪昌:《從〈南山集〉到〈虯峰集〉——文字獄案與清代文學生態舉證》,《文學遺産》,2001年第5期,第74頁。。因而康熙帝對此事格外警惕。方氏之所以被牽連進《南山集》案,係族人方孝標所致。方孝標被捲入此案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刑部尚書哈山爲審明戴名世〈南山集〉案並將涉案犯人擬罪事題本》中明確記載,戴氏承認在撰寫《南山集》時受方孝標《滇黔紀聞》的影響。“我與餘生書内有方學士名,即方孝標。他作的《滇黔紀聞》内載永曆年號,我見此書即混寫悖亂之語,罪該萬死”(4)張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歷史檔案》,2001年第2期,第21頁。;其二康熙帝認定方孝標身仕僞朝,他在《清聖祖實録》中批復刑部衙門所奏《南山集》案時道:“此事著問九卿具奏。案内方姓人,俱係惡亂之輩,方光琛投順吴三桂,曾爲僞相,方孝標亦曾爲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處也。”(5)《清实录》(第六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5頁。(關於方氏仕僞朝一事,多數學者持否定意見。)且他所著《滇黔紀聞》中多用南明年號,又尊稱弘光帝,因而觸怒了聖祖。“方孝標身受國恩,已爲翰林,因犯罪發遣,蒙寬宥釋歸。順吴逆已爲僞官,迨其投誠,又蒙洪恩免罪,仍不改悖逆之心,《滇黔紀聞》内以弘光、隆武、永曆为帝,尊崇年號,書記刊刻遺留,大逆已極。之後,刑部對戴氏和方氏擬定處罰,然擬定懲處過重,牽連甚廣。康熙帝斟酌一年多後,决定:“戴名世從寬免凌遲,著即處斬。方登嶧、方雲旅、方世樵俱從寬免罪,並伊妻子發往黑龍江。這案干連應斬絞及爲奴安插流徙人犯俱從寬免罪入旗。”(6)張玉:《戴名世〈南山集〉案史料》,《歷史檔案》,2001年第2期,第24頁。《南山集》案最終的處理結果是戴名世被處斬,方孝標遭挫尸,其餘戴氏及方氏族人多被流放,入旗籍爲奴。方貞觀因與方孝標同屬方拱乾一脉而被牽連。康熙五十二年(1713)貞觀被發遣至寧古塔,時貞觀正值壯年。
雍正帝即位後,大赦天下,頒佈恩詔,他對《南山集》案的意見是,“除本身犯罪外,因族人有罪牽連入旗者,著查奏赦免”(7)張玉:《從新發現的檔案談戴名世〈南山集〉案》,《歷史檔案》,2001年第2期,第93頁。。最終的審議結果是,“除戴名世和方孝標的嫡派子孫、媳婦外,戴、方兩姓族人以及受牽連的人共計82人均被免罪釋放,返回原籍”(8)張玉:《從新發現的檔案談戴名世〈南山集〉案》,《歷史檔案》,2001年第2期,第93頁。。雍正元年(1723)三月貞觀從寧古塔回到故鄉桐城,途中作有《卜居二首·其一》“版籍重爲故土民,一椽從遣卜居新。飄摇已慣經風雨,僻陋終須遠市塵。樹老種從誰氏手,井甘汲共舊時鄰”(9)《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0頁。。貞觀感慨想要獲得平静的生活一定要遠離塵囂,回鄉後他只願在家安穩度日。方貞觀深知《南山集》案是政治鬥争的産物,是統治者禁錮士人思想的利器,在《登舟感懷》中他憤恨直言:“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影多含沙。未聞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蟲奚足矜攛爬。豈知道旁自得罪,城門殃火來無涯。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豈辨根與芽?舉族驅作北飛鳥,……殺身只在南山豆,伏機頃刻鉶阬瓜。古今禍福匪意料,文網何須説永嘉!君不見烏衣巷里屠沽宅,原是當時王謝家。”(10)《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9—180頁。方氏一向秉承正道,卻因《南山案》,下受小人構陷,上遭文網波及,致使闔族流亡。貞觀因《南山集》案認清了清廷統治的嚴酷,返鄉不久後他再次離開,後來長期客居揚州、通州等地,晚年重返桐城。
二、 《南山集》案陰影下詩人心態的轉變
《南山集》案使方氏家族遭遇重創,方貞觀自身正值壯年卻遭牽累流放長達十年,這雙重的打擊使原本困頓於仕途的貞觀,更添悲憤,心態幾經轉變。被流放後悲痛衰頽,赦歸時余怨難平,餘年仍懷憂懼之心。
(一) 流羈悲痛常衰頽
《南山集》案後,方貞觀被流放至寧古塔一帶,别親老,居苦寒,内心悲痛且衰頽。《癸巳之歲建亥之月奉》:“詔隸歸旗籍,官牒夕至行。人朝發倉卒,北向吏役驅。逐轉徙流離,别入版籍瞻。望鄉國莫知,所處先隴棄。遺親知永隔,行動羈縶,存没異鄉。嗚呼哀哉!豈複有言,而景物關會,時序往復,每不能自已。始乎去國,迄于京華。其嗚咽不成聲者……庾信所謂其心實傷者也。後之君子尚其讀而悲之。”(11)《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79頁。此詩作於康熙五十八年(1779),距被遣發已過六年,但詩人對當時情形仍歷歷在目,悲痛不已,久久不能釋懷。《抵都僦居義興坊題壁》:“此生豈複惜餘辰,積習猶教愛絶塵。噉杵已成無想夢,立錐翻羡去年貧。卻嫌席敝勞多轍,幸少兒嬌惱比鄰。莫漫相逢嗟旅食,自今我屬版圖民。”(12)《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2頁。自被流放後,詩人對於餘生已經没有任何期待,而今羡慕以前貧困潦倒的時候,當年卻嫌生活困頓。詩中悲傷之濃,失望之極,令人心生歎息。
(二) 赦歸餘怨也難平
雍正元年(1723),雍正帝下恩詔,貞觀得以赦歸,此時詩人已45歲,最應該有所作爲的年華已經在流放生涯中逝去,雖被放歸,但仍心懷餘怨,只願做避世老翁。其詩《雍正首元三月二十八日詔還故里紀恩書懷》:“網開一面感重華,聖澤滂流詎有涯。直似秋霖遷土偶,豈同黨錮怨匏瓜?由來造命憑君相,不料餘年有室家。得遂首邱何以報,惟應努力事桑麻。”(13)《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0頁。詩人性情耿介,直指《南山集》案背後方氏遭闔族之禍的真正原因是黨争,且並不避諱於詩中點破。詩人在感恩赦歸的同時内心悽愴,怨氣難平,表示餘生要做不問世事的田間人。《東阿道中》“高嶺豁屏風,孤邨翠靄中。幾行山木瘦,一半夕陽紅。歸鳥各競暮,秋烟不礙空。溪流最深處,應有避秦翁”(14)《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0頁。。返鄉途中,只見高高的山嶺猶如屏障隔絶了秋風,零星幾户人家掩映於翠緑的霧靄之中。在夕陽的餘暉中山與木都一樣清瘦。歸來的鳥兒在暮色中疾馳,幾縷炊烟很快湮滅於空中。在溪流的最深處,應有避世隱居的老翁。詩人内心並無太多喜悦之情,反而如老僧一般淡漠地看着山林村落,希望與避世的秦翁一樣隱居山林。
(三) 餘生憂懼半心酸
貞觀後來長期客居揚州、通州等地,然《南山集》案爲詩人留下了巨大的陰影,導致其晚年仍心懷憂懼。《丁巳冬日病中》:“餘生偏自戀微生,一病兼旬轉未平。夢醒乍驚年在巳,鳥來猶幸日非庚。肝家業火方炎上,耳畔客塵時作聲。安得孝光婁傴僂,爲餘傾鉢洗心情。”(15)《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3頁。距被赦歸已經過了十四年,詩人已到花甲之年,仍因《南山集》案夢中常常突然驚醒,對家族之禍仍懷驚懼之心,由此可見此案對詩人的挫傷之深。《悔游》“丁年重意氣,然諾可殺身。老懷兒女情,慷慨化酸辛。厭爲淮海遊,喜與鄰里親。伏臘宴同社,迭相爲主賓。……朝昏幸粗給,寤寐豈憂貧。前非悔方悟,後事計誰真?崦嵫分寸暉,一息良可珍。孰謂故山土,不如歧路塵”(16)《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7頁。。此詩作于詩人晚年客居揚州等地時期,詩人後悔餘生遠行,應留故鄉與親里遊。然而回想前事,又覺故鄉不如客居地。詩人雖未明説遊蕩在外的原因,但大抵是因爲一方面他曾在家鄉因《南山集》案的牽累被流放,另一方面則是由於至今許多族人仍飄流在外,怕自己睹物思人。其中的寥落心酸之意溢於言表。
三、 《南山集》案前後詩人詩風的曲折變化
《南山集》案不僅使貞觀心態幾番波折,也致其詩風幾經變化。友人李可淳在《方貞觀詩集序》中曾言:
“予與貞觀先生遊近三十年,見其詩幾數變。最初學張籍、王建,既又學孟東野,三十以後盡棄其所素習,沉淫於貞元大曆之間,熔煉淘汰獨標孤詣,務極雅正。而貞觀固欿然自以爲未足。未幾患難歸京師,隸入旗籍,棄先壟,别親故,行動羈摯,出入恐懼,人事都廢,何有於詩?顧其屈鬱抑塞之氣,羈孤離别之感,轉喉即露。隨露隨掩,愈掩愈出,宛轉沉痛,言短意長。貞觀之詩至此始造其極。夫難生慮表,流離顛躓,窮愁無聊,托之謳吟。貞觀之詩之工,亦大可哀矣!如是者十年得複歸江南。今又經十年矣,所爲詩益造平淡益近自然。惜多散逸。所存僅若干首。顧讀之,輒令人流連往復,如其悲喜而不能自已,何其入人之深也。嘗見粤人陳恭尹之論詩,云感人以理者淺,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盡,感人以聲者靡涯。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貞觀其庶幾乎。”(17)《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1頁。
李可淳與貞觀交遊近三十年,見其詩風幾經轉變,初學張籍、王建之平易流暢、委婉深摯;繼學孟郊之幽僻冷澀;三十以後沉淫於貞觀大曆詩風,苦心孤詣,力求雅正;流放後,其詩孤詣沉痛;至老而平淡自然。其論貞觀詩較爲符合實際,貞觀詩風的確幾經轉變,流放前,其詩孤詣清寒;居流放地,詩風抑鬱頓挫;晚年客居揚州等地時,詩作平淡自然。
(一) 發遣前詩孤詣清寒
貞觀束髮習誦經史,以詩與書法聞名揚淮,少負才名,身懷抱負,然天不從人願,屢困場屋。“束髮誦典墳,垂髫事孔孟。了了開大義,搜鑿殫厥藴。十五爲文章,摛毫快風迅。二十學經濟,霸王别邪正。所志在遠途,親朋亦深信,得失匪意測。值彼凶悔吝,伏櫪懷九衢。哀傷致疾疢,飲啜日漸减。壯氣一秋盡。”(18)《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8頁。詩人自述年少時投身於科舉,然而結果屢不如意,並因此致病,人近中年豪情壯志已然散盡。“我年二十七,衰替若半百。少不問生産,老大計轉拙。文章止費才,年年泣秋血。辭君西入山,匿不與物接。襟袖披烟霞,饔飧淡薇蕨”(19)《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頁。。少年時將精力放在文章、經濟上,不事生産,然應考多年並未成功,年紀漸漸大了,開始爲生計發愁,如今只能採摘野菜果腹。一介才子淪落至食不果腹,令人扼腕歎息。科舉的失意、生活的困頓使其詩飽含清寒凄凉之意。其《秋夜與偉珍上人吟集月溪》:“邗江古禪客,石室共搜吟。閉目燃孤燭,千峰在一心。悲風撼遥夜,衆響入横林。會此苦空意,開門寒月沉。”(20)《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7頁。“孤燭”“悲風”“苦”“空”“寒月”等意象皆飽含孤獨清寒之意,詩人將内心之凄苦透過清冷之秋夜言説,更添一層寒意。
(二) 流寓詩抑鬱頓挫
沈德潛稱貞觀:“十年中别母妻,棄丘隴,行動羈縶,極人世之困窮,然境窮而詩乃工矣。卷中所採,多流離抑鬱時作。”(21)(清)沈德潛等編:《清詩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170頁。貞觀被流放後,内心凄苦,詩作抑鬱頓挫,飽含沉痛之意。《送大兄隨册使徐諒直之琉球》:“故國飄零遠向燕,星槎更泛斗南天。生涯何至須航海?筋力况當非壯年。萬里回瞻中夏月,八蠻遥辨島夷烟。難餘兄弟相爲命,此際能毋一泫然。”(22)《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9頁。詩人感慨自己飄零在外,距故鄉遥遠,轉而感歎其兄方世弘晚年不得已隨徐諒直遠赴琉球,繼而想象以後只能借助月亮遥望兄長,思及此處,忍不住潸然淚下。詩人將抑鬱哀傷之情輾轉道來,更顯示出哀情之濃厚,使人淚目。《寄十兄沃園塞上》:“大漠悲風隴上烟,零丁誰與慰窮邊。魂招雪窖來無路,書寄龍荒去隔年。鼠穴乘牛真幻夢,馬頭生角枉呼天。並州縱比桑乾近,説着咸陽總泫然。”(23)《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2頁。詩人從眼前的瘡痍之景,飄零之身,想到此地的荒無人烟和家人音信的稀少。再想到翻案回鄉之事難於上青天。最後提起咸陽總是淚如雨下。凄哀之意在胸中反復流轉,最終未能爆發,而是化作淚再次返回詩人胸中,哀轉回蕩,更添哀傷之意。
(三) 客居詩平淡自然
貞觀被赦歸後不久即從家鄉離開,長期客居揚州、通州等地。此時,詩人雖客居在外,但生活有了好轉,再加上步入老年,其心歸至淡然,因而詩作趨嚮平淡自然。《雲際寺》:“初地何年寺,鐘聲隔嶺聞。樓明穿落日,山白擁秋雲。行過石樑險,坐看麋鹿群。客程方未已,楓葉又紛紛。”(24)《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7頁。詩人在行至雲際寺的途中,聽見清越的鐘聲越過山嶺陣陣傳來。遠處落日的餘暉將亭樓浸亮,青山與秋雲依偎。穿過石樑險處,坐在亭内看在林中穿越的麋鹿。旅途還未結束,楓葉紛紛下落。詩人將行至雲際寺的見聞細細道來,平淡自然,並無太多情緒流露。《真州旅夢》:“堠短堠長長短程,離家節後又清明。春風野店真州夢,猶在鳳儀坊下行。”(25)《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3頁。詩人不舍離家遠行,羈旅在外,夢中感覺自己還在故鄉,思鄉之意濃烈。《令聞集拙詩至數百首繕寫成卷出以相示戲題解嘲》:“古人情性多奇癖,或愛驅鳴或斗牛。君好我詩應有説,前身我是孟靈休。”(26)《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4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5頁。詩人聽聞友人汪廷璋將自己的詩集結成書,便借劉邕嗜痂一事自嘲己詩,調侃中卻藴含着無法言説的落寞與失意。
四、 “詩人之詩”説與推重中晚唐詩
在《南山集》案的影響下,詩人心態與詩風轉變的同時,其詩學思想也發生了衝突——“詩人之詩”的詩學理想與推重中晚唐詩的詩歌宗法相抵牾。關於“詩人之詩”説可見於《輟耕録》的卷首:
“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才人之詩,崇論閎議,馳騁縱横,富贍標鮮,得之頃刻。然角勝於當場,則驚奇仰異;咀含於閑瑕,則時過境非。譬之佛家,吞針咒水,怪變萬端,終屬小乘,不證如來大道。學人之詩,博聞强識,好學深思,功力雖深,天分有限,未嘗不聲應律而舞合節,究之其勝人處,即其遜人處。譬之佛家,律門戒子,守死威儀,終是飩根長老,安能一性圓明!詩人之詩,心地空明,有絶人之智慧;意度高遠,無物類之牽纏。詩書名物,别有領會;山川花鳥,關我性情。信手拈來,言近旨遠,筆短意長,聆之聲希,咀之味永。此禪宗之心印,風雅之正傳也。”(27)郭紹虞輯、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34頁。
貞觀將“詩人之詩”“學人之詩”“才人之詩”對舉,認爲 “詩人之詩”,心地空明,意度高遠,抒發性情,含蓄雋永,藴含禪意,爲風雅之正傳。貞觀所論“詩人之詩”之内涵與王維之詩風貌頗爲一致。王維爲盛唐詩壇大家,其詩歷來爲人所稱道。趙鐵岩稱:“右丞通於禪理,故語無背觸,甜澈中邊。空外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於沈實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于建康也,使人索之於離即之間,驟欲去之而不可得,蓋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28)(清)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頁。姚鼐曰:“盛唐人詩固無體不妙,而尤以五言律爲最。此體中又當以王、孟爲最,以禪家妙悟論詩者正在此耳。”(29)(清)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21頁。姚又言:“右丞七律能備三十二相,而意興超遠,有雖對榮觀燕處超然之意,宜獨冠盛唐。”(30)(清)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36頁。綜觀王維詩作及歷來詩論家對其詩的評價可知:其詩境界空明、寧静致遠、悠然禪意。而這正與貞觀“詩人之詩”説契合。
然觀《輟鍛録》,舉例論詩之時,貞觀絶口不提王維,反大讚杜甫與大曆詩人,尤盛讚杜甫《赴奉先縣五百字》:“當時時歌誦,不獨起伏關鍵,意度波瀾,煌煌大篇,可以爲法,即其中琢句之工,用字之妙,無一不是規矩,而音韻尤古淡雅正,自然天籟也。”(31)郭紹虞輯、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38頁。稱讚杜詩古淡雅正、自然天籟。貞觀還力推大曆詩人之詩,並以此來教育後學。貞觀自言:“晚唐自應首推李、杜,義山之沉鬱奇譎,樊川之縱横傲岸,求之全唐中,亦不多見,而氣體不如大曆諸公者,時代限之也。次則温飛卿、許丁卯,次則馬虞臣、鄭都官,五律猶有可觀,外此則邾、莒之下矣。”(32)郭紹虞輯、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39頁。他按詩作高下對詩人進行排序,將大曆諸公置於李商隱、杜牧之前。至此,我們可以發現詩人在詩學理想上應是推崇王維之詩的風貌——“詩人之詩”,然而在詩歌宗法上卻推重杜甫、大曆詩人等中晚唐詩人之詩,由此可見方貞觀詩學理想與詩學宗法之間矛盾。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矛盾,應與貞觀所處時代及個人遭遇有關。他雖然欣賞摩詰詩之清新淡雅、境界空明、禪意悠然,然而面對當時詩壇及清廷的現狀,推舉摩詰詩並不合乎時宜;自身的不幸遭遇又使其難以達到摩詰詩的空明境界。因而,在時代與個人的雙重選擇下,詩人將目光轉至中晚唐詩。
正如蔣寅先生所言:“在後王漁洋時代步入中年的方貞觀,實在無法擺脱對親身經歷的那段詩歌史的失望及連帶産生的對當代詩歌寫作的悲觀意識。在他的回憶中,近幾十年的詩歌史完全是失敗的記録……而眼下的詩壇也看不到什麽希望,甚且正在向邪道上滑去。”(33)蔣寅:《方氏詩論與桐城詩學的發展》,《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693頁。貞觀認爲當前詩壇存在鄙棄經史,蔑視唐名家,而專拾宋元小説典故以入詩的邪風。貞觀自小接受儒家教育,自覺有匡世濟民的責任,面對詩壇的“風雅道喪”,自覺有匡正詩風之責。爲糾正不良風氣,他大力倡導唐詩,欲引導今人重拾古人精神,重振詩風,並將此理念落實在選詩上。正如程晋芳所言:“先生嘗欲選唐人自劉長卿以下至中唐之末爲一集。去昌黎、長吉、盧仝、劉叉四家,而以義山、牧之、飛卿至堯續焉,以教世之學詩者。”(34)《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96頁。貞觀選詩時非常謹慎,選用李商隱、杜牧、温庭筠詩,而拋去韓愈、李賀、盧仝、劉叉四家詩。因這四家詩喜用冷僻、怪奇意象,不利於引導詩風歸於雅正。他宣導協律工整的雅正之詩,“詩必言律。律也者,非語句承接,義意貫串之謂也。凡體裁之輕重,章法之短長,波瀾之廣狹,句法之曲直,音節之高下,詞藻之濃淡,於此一篇略不相稱,便是不諧於律。故有時寧割文雅,收取俚直,欲其相稱也”(35)郭紹虞輯、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34—1835頁。。他提出詩作必須協律,做到體裁、章法、波瀾、句法、音節、詞藻等協調統一,並極爲讚揚杜詩之雅正古淡。
再者,與其不幸遭遇有關。在詩學理想上詩人雖崇尚聲律風骨兼備的“詩人之詩”,然而崎嶇的人生經歷已經使他難以心無旁騖、平静淡然地去創作詩歌,由此也影響到其詩歌審美取向。詩人對氣象闊大、樂意進取的盛唐詩閉口不談,而對沉鬱頓挫、孤寂清冷的中晚唐詩更爲偏愛。杜甫及大曆衆人不僅與詩人經歷相似,詩風也都頗有孤寂清寒之意,因而得到詩人的格外青睞。杜甫懷有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早年過着漫遊南北、裘馬輕狂的生活。中年後求仕無門,十餘年在長安顛沛流離,一度落入安史之亂的叛軍之手。晚年貧困潦倒。杜詩或沉鬱頓挫,《春望》:“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36)鄧魁英、聶石樵選注:《杜甫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1頁。或蕭散自然,如《月夜》:“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遥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虚幌,雙照淚痕乾。”(37)鄧魁英、聶石樵選注:《杜甫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6頁。杜詩或沉鬱或蕭散的詩風、工整的韻律、渾融的境界都使貞觀爲之折服。劉長卿家境貧寒、應舉十年不第,一載登科又因剛直而兩遭謫貶,失意落拓,内心凄凉。《重送裴郎中貶吉州》:“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38)儲仲君撰:《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85頁。劉詩的孤寂凄冷之感與貞觀詩如出一轍。或正因這兩方面的原因,貞觀特重杜甫及大曆詩人。
餘 論
胡光奇説:“(清代文字獄)持續時間之長,文網之密,案件之多,打擊面之廣,羅織罪名之陰毒,手段之狠,都是超越前代的。”(39)胡奇光:《中國文禍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頁。清代文字獄之盛對士子的打擊是巨大的。嚴迪昌先生指斥道:“(文字獄)其最明顯而又對民族文化最具破壞性災難效應的,是文士的失語。於是,層累有千百年人文積澱,又歷經翻覆更變之人生體審,本屬才識之士輩出的時代,卻由此陷入令人浩歎之心靈荒漠,呈現一種集體怔忡症:或熱衷拱樞、或冷漠遁野,或餖飣雕蟲……總之,靈光耗散,卓識幽閉,順者昌,逆得亡。”(40)嚴迪昌:《從〈南山集〉到〈虯峰集〉——文字獄案與清代文學生態舉證》,《文學遺産》,2001年第5期,第74頁。在文字獄高壓環境下,士子思想受到禁錮,批判精神衰落,或噤若寒蟬,或謳功頌德。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清代思想界、學術界萬馬齊喑,阻礙了本應百花齊放、生機勃勃的清代文學的發展,使清代文學生態發生畸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