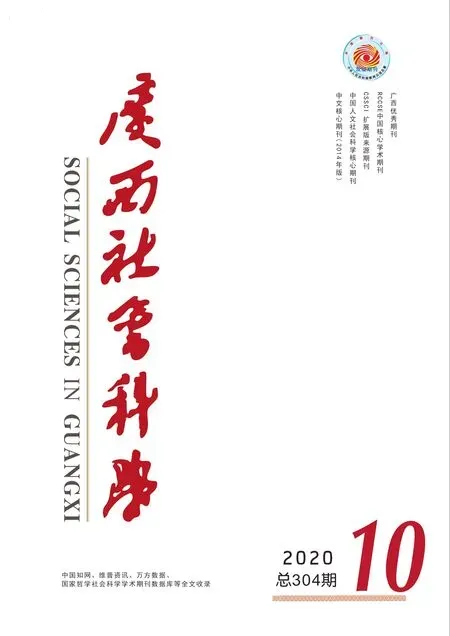从“悄吟”到“萧红”:由笔名管窥萧红上海时期创作思维的转变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萧红以《跋涉》在哈尔滨文坛初露头角,到上海后,因《生死场》而备受关注,后在上海出版《商市街》《桥》《牛车上》,跻身知名作家之列。对于萧红在上海的经历,萧红产生与前期有别的创作思想转变的动因,以往在讨论萧红前后期迥异的文学创作风格时,这个较为复杂的内部思想转变的过程或被忽略,或将其简单化约为“被自己的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1]。事实上,萧红曾借两则仿写鲁迅《野草》的日记,颇为含蓄地使用“曲笔”陈述过内心的曲折郁积,本文即以这些问题为中心,以“悄吟”和“萧红”的使用和置换情况为切入点,透过“名”的抉择管窥萧红研究中长期被遮蔽、被悬置的个体内部的重重思想动因,探寻萧红在上海时期创作思维发生转变的缘由。
一、上海作为场域:从“悄吟”至“萧红”
萧红最早的创作起始于中学时期,1930年5月她写的小诗《吉林之游》发表在校刊上,署名“悄吟”,寓意“悄悄地吟咏”,此后该笔名代替其原名“张迺莹”,成为萧红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指称。尽管萧红用过“玲玲”“田娣”的笔名,但在萧红离开哈尔滨和青岛之后再也未使用过,而“悄吟”“萧红”之间却有多次抉择和往返,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入探究。
1935年12月《生死场》经过鲁迅和胡风的推荐,作为“奴隶丛书之三”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署名“萧红”,“悄吟”第一次成为“萧红”。《生死场》中“悄吟”成为“萧红”,跟鲁迅在信中建议“二萧”(萧红和萧军)用新笔名有关。1935年4月4日,鲁迅写给“二萧”的信中说:“此后的笔名,需用两个,一个用于《八月》之类的,一个用于卖稿换钱的,否则,《八月》印出后,倘为叭儿狗所知,则别的稿子即使并没有什么,也会被他们抽去,不能发表。”[2]萧军使用“萧”字来源于萧军喜爱的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军”则是为了纪念他的军人出身,《生死场》出版时萧军和萧红的笔名联系起来,成为“红军”的谐音[3],这也是“萧红”之名的来源。当时难以合法出版的《生死场》以“萧红”为笔名,一定也与鲁迅的建议紧密相关。问题在于,此后萧红选择笔名时又经历多次“悄吟”与“萧红”之间的往返,且不同的笔名之下有着明显两异的创作内容指向。
1935年,萧红完成散文集《商市街》,于1936年将其交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署名“悄吟”。同年她签下《桥》的出版授权与契约,该契约中有一处醒目的涂抹痕迹。在著作人签名中,先是签署“萧红”,随即该名用方框和斜杠划掉,改为“悄吟”,似乎她在自我指涉上蕴含称谓上的不确定。此时萧红对自我指涉的不确定还不止于此,在现实生活中,萧红放弃“张迺莹”的原名,将自刻印章上的名字改为“张莹”,该印章用作领取稿费。巴金时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后收到萧红赠予他的一本精装本《桥》,封面上作者署名“悄吟”,扉页上有萧红的手写字“巴金先生”,隔行写“萧红赠”,“悄吟”与“萧红”再次陈于同一页。如果说出版契约中划掉“萧红”而改为“悄吟”是由于“出版社强调合同签名与图书出版的署名一致”[4],那么在送给巴金《桥》时签名“萧红”,则代表萧红在自我指涉上发生某种内在的“名”的自我认知上的转换。
1937年5月,萧红的《牛车上》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收入她在日本所写的散文和小说,出版时署名“萧红”。其中的小说先后在《作家》《中流》《文学季刊》上发表,发表时均署名“萧红”。而在发表记叙个人生活印记明显的散文《孤独的生活》时,署名却又回归到“悄吟”,同时期再次启用“悄吟”为笔名的作品还有组诗《沙粒》与短篇小说《两朋友》。萧红旅日时期,萧军与许粤华产生感情,二人的纠葛并未因萧红回到上海而终结,1937年3月,组诗《沙粒》发表于上海《文丛》月刊第1卷第1号,署名“悄吟”,萧红将二人的情感危机公之于众。最后一次署名“悄吟”的作品是《两朋友》,讲述的是少年“荣子”与“金珠”悲伤的友情故事,与此同时萧红因情感问题独自生活于北京,从北京写给萧军的7封信中,所有的信署名均为“荣子”,文学创作中的“荣子”和情感困境中的“荣子”构成称谓上的同构。
不仅创作与发表时的署名蕴含萧红对“名”的构建,她的书信和私人往来中的署名也能提供一些新的证据。1936年7月至1937年1月,萧红独自生活在日本期间给萧军写了35封信,共用6个称谓,使用频率不尽相同,其中使用“莹”8次、“吟”15次、“荣子”8次、“小鹅”3次、“萧”1次、“红”1次。1936年7月,在萧红去往日本的前一天,黄源设宴为萧红送行,宴后黄源与“二萧”合影,后有萧红题字:“悄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七日赴日,此像摄于十六日宴罢归家时。”[5]使用“萧”字为名的一封信写于1936年8月,信中关心萧军伤风、买枕头的事,也诉说自己的寂寞,期待萧军寄书给自己。使用“红”为名的一封信写于萧红得知鲁迅逝世的消息之后,该信于1936年10月从东京发往上海编入1936年11月推出的《中流》第1卷第5期,该期是“哀悼鲁迅先生专号”,萧军将其拿给《中流》编辑,最终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发表。如此可见,萧红从日本写这封信给萧军时,她表达的是私人情感,而在私人生活中以“红”自称,在此处是第一次。与他人的通信和交往中也可以窥见“悄吟”和“萧红”的置换。在1936年10月萧红从日本东京写给黄源的信中,署名为“吟”。至萧红北上北京时,给萧军写了7封信,全部署名“荣子”。
萧红在上海的第三段生活经历是她从北京归来以后,即1937年5月至1937年9月。从这一段上海生活开始,“萧红”的笔名固定下来,所有的作品发表时均署名“萧红”,私人往来、社会活动签名、图书出版中都无一例外使用“萧红”为名,从表面上看,大约以1937年《沙粒》和《两朋友》为界,“悄吟”被“萧红”全面置换,自此以后再也没有用过“悄吟”,这自然与其以“萧红”成名有一定关联,但联系“悄吟”和“萧红”的使用情况,“名”的转变显然不止笔名的随意使用,其中涵盖萧红对自我指涉的犹疑和主体构建的思考,也向深延展出萧红在上海时创作内容的思考和创作思维的转变,对这些问题要深入萧红在上海的具体生活中进行探究。
二、焦虑与探索:从《商市街》到《牛车上》
萧红、萧军于1934年11月1日当晚抵达上海,次日租下法租界拉都路北段路东“永生泰”文具店后面二楼的亭子间[6],仅仅住了一个月以后就搬往另外的“亭子间”。在萧红完成《商市街》以前,二人共换了4个“亭子间”的“家”。李欧梵将上海的“亭子间”视为特殊的空间场域考察对象,生活于此的中国现代作家众多,他们“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7]。频繁的“亭子间”的变迁使萧红产生“家”的焦虑,这投射在萧红的创作中,萧红抵达上海后第一篇文章即是讲述搬家故事的《小六》(后选入《萧红散文》时改名《搬家》),《商市街》中也有《搬家》一文,《小六》写的是青岛时期的邻居“小六”一家的搬家经历和无以为家的跳海悲剧,《搬家》则讲述二人从欧罗巴旅馆搬迁至商市街的经历。两篇《搬家》创作时间间隔两个月,萧红在其中写下对家的体验:“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8]“家”的现实境况与萧红对家的构想形成鲜明对比:“家是可以回去的,而且家也是好的,土地是宽阔的,米粮是富足的。”[9]加斯东·巴什拉认为家是认同感产生的地方,同时“人的无意识是美满而幸福地安居着的。它安居在自己的幸福空间里”[10]。亦即,人在对家宅的理想构建中,家宅是温暖的、幸福的、美满的。反观萧红的生活,逃离了旧家庭的萧红始终处在“无家”的境遇中,如何平衡“家”的理想预设和“无家”的现实裂隙,是萧红初到上海即被“家”的焦虑所扼时不得不直面的问题。哈尔滨时期萧红写过《弃儿》《广告副手》等,她以“芹”“蓓力”为第三人称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无家、生育、失业经历,而在上海,萧红以频繁搬家和上海都市现代性的挤压为肇始,从自身“无以为家”的处境入手,以“我”为书写对象,直面自己生存层面的困境,“她认识到,要成为‘我们’,首先要承认‘我’的存在”[11]。萧红置身上海,自身焦虑使其转变了第三人称叙事策略,不再以“他者”视野观望生活困境,转而以第一人称书写策略直面自我,直面由“家”的焦虑延伸出的饥饿、病痛、寒冷、职业困境。
萧红在上海还陷入小说创作的困境中,鲁迅最早发现她的创作困境。1934年12月6日他写给“二萧”的信说:“一个作者,离开本国后,即永不会写文章了,是常有的事。我到上海后,即做不出小说来。”[12]一个月后鲁迅在信中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13]。萧红初到上海后的两个月内都没有创作出新的作品,借《小六》与《商市街》完成对自己往昔的剖析与审视之后,萧红又一次陷入困境。1935年9月19日鲁迅在信中说:“久未得悄吟太太消息,她久不写什么了吧?”[14]此时鲁迅所说的写文章,应指《商市街》以外的小说创作,直至萧红去往日本,小说创作只有《手》《桥》《马房之夜》,萧红并不满意这几篇带着旧有印记的小说:“自己的文章写得不好,看看外国作家高尔基或者是什么人……觉得存在在自己文章上的完全是缺点了。并且写了一篇,再写一篇也不感到进步……”[15]萧红意识到了自己处在创作困境和瓶颈之中,而如何在写作中“进步”或者说如何改变原有的创作方式成为她思考的问题。小说集《牛车上》的出版是萧红创作焦虑困境的突破,要寻找其新旧言说的跨越,则需比照《牛车上》和此前出版的《桥》。《桥》选入13篇散文和小说,其中散文与《商市街》中区别并不太大,但两篇小说《桥》和《手》却蕴含着超出文本的指涉。《桥》讲述家在桥东、身在桥西富人家做保姆的黄良子的失子悲剧;《手》中的染坊女儿王亚明因贫苦出身在学校受尽师生侮辱欺凌。若将其与萧红此期的“创作困境”相关联,这两篇有寓意的故事似乎是此期萧红对自己创作困境的“赋形”,《桥》《手》以及去日本前发表的《马房之夜》,基本还沿用早期小说中对人物关系的构建方式,将主要矛盾放置进财产贫富、阶级对立、以及身份高下的重重二元组建关系之中。与其说此时的萧红陷入创作的困境,不如说萧红产生一种如何超越往昔二元关系构建人物的思考,以此为喻,萧红似乎借着王亚明的无法洗去旧日印记的“手”,诉说自己苦于无法找到突破旧日印记,无法找到匹配当时困惑和思考的突破之“桥”,即无法找到“进步”的创作方法。
日本时期的创作是萧红找到突破的转折点。1936年8月27日萧红写给萧军的信中说:“现在要开始一个三万字的短篇了,给《作家》十月号。”[16]8月31日信中萧红说:“不得了了!已经打破了记录,今已超出了十页稿纸。我感到了大欢喜。”[17]这篇作品在5天后得以完成,萧红对该作也非常满意:“自己觉得写得不错,所以很高兴。”[18]这篇小说即是以“有二伯”为主人公的《家族以外的人》。新的书写范式疏解创作焦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萧红就完成了《家族以外的人》《牛车上》《王四的故事》《红的果园》等作品。通观这些作品,有二伯、五云嫂、牛车车夫、王四无一不是有着对“家”的渴慕,有对圆满之“家”的预设,而所有人物或因战争、或因死亡被置于“无家”的境地中,对“家”的期待不断面临撕扯,“这种撕扯见证了偏僻的人生的存在;同时裂口在撕扯中产生的痛苦又使得逃离裂口成为可能”[19]。《牛车上》提到五云嫂坐着牛车去看望城里的儿子,路上她与车夫闲聊,坦言自己的丈夫因为当逃兵被杀,“家”被战争撕裂,而车夫则隐匿了曾经当逃兵的经历,只说自己赶车为生。之后,五云嫂乘坐的牛车在路上巧遇其他车子,两个车夫彼此招呼,在雾中“两个车子又过去了”,虽则未知的“兵灾”和“荒年”可能又将撕裂他们短暂的安宁,但车夫和五云嫂在“无家”的命运中对“家”依旧有所期待,人物命运未卜却又饱含憧憬,萧红也自述“所以我就向着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20]。将这个自我表述投进萧红的创作中可见:从《家族以外的人》至战争时期创作的《汾河的圆月》《朦胧的期待》《黄河》及至香港时期的作品《北中国》《呼兰河传》《马伯乐》,每个主人公都有着“家”的焦虑和“无家”的命运,然而萧红又以悲悯之心为人物投注“温暖和爱”,给笔下人物“憧憬和期待”。如《朦胧的期待》中李妈被上战场的金立之掐灭组建“家”的希望,却在梦中与金立之安了足以使人慰藉的“家”,未完成的《马伯乐》也原想给他一个“光明的结局”[21]。为人物设置“家”与“无家”的生存境地代替以往阶级、贫富式的二元式构建,是萧红创作思想发生较大转变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牛车上》入选的作品在单篇发表时,署名上出现“萧红”和“悄吟”之间的往返。其中的小说在发表时,全部使用“萧红”作笔名,唯有散文《孤独的生活》署名“悄吟”,此后这种情况在组诗《沙粒》与《两朋友》都出现过。《沙粒》抒写她与萧军情感中的迷茫和焦虑,最后一次使用“悄吟”作笔名的《两朋友》,如前所述讲述少年时代的友情与分离痛楚。由其中的情感倾向可见,萧红在两个笔名之下蕴含着不同的表述策略:“悄吟”指向情感郁结,而“萧红”则代表着直面自己感情困境的独立个体,使用“悄吟”时抒写个人情感的失落,而“萧红”又在是否挣脱这种情感的徘徊状态,两个笔名在情感的纠葛中发生嵌套叠合。萧红以感情受挫为主因而远走日本、独上北平,以“悄吟”表露了自己的情感痛楚之后,成长为独立的个体“萧红”,此后在延安与萧军诀别,恐怕都与这个历尽情感失落又不得不独立的“萧红”有关。
从“悄吟”置换至“萧红”过程伴随着萧红“家”的焦虑、创作焦虑和情感焦虑,这些个体焦虑使萧红不得不直面生存、情感、创作困境,也思考着如何在创作中跳出旧有思维模式转向新的言说方式,萧红置身上海,上海尤为复杂的场域空气又进一步促发萧红创作思维的转变。
三、仿写与突破:从《野草》到《日记》
1937年8月1日与8月2日,萧红写下两篇日记①1937年8月1日日记分为两部分发表,其中《八月之日记一(上)》发表于1937年10月28日汉口《大公报》副刊《战线》第36号,《八月之日记一(下)》发表于1937年10月29日汉口《大公报》副刊《战线》第37号。《八月之日记二》作于1937年8月2日,发表于1937年11月3日《大公报》副刊《战线》第41号。三篇日记发表时均署名萧红。,在《野草》中能找到萧红日记模仿的“模板”,试举几例,见表1。

表1 萧红《日记》仿照鲁迅《野草》的句子示例
萧红显然对《野草》有极深入的了解,中学时萧红就与喜欢同学读鲁迅的书,“《野草》中的一些妙句和篇章,她们都能背下来”[22],鲁迅1934年10月9日写给萧军和萧红的第一封信中就谈到《野草》,“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23]。木山英雄认为《野草》中蕴含鲁迅此时期的孤独、怀疑、颓唐、消沉等情感,鲁迅以“曲笔”书写内心,涉及“作家自我认识”和主体构建的问题[24],那么萧红何以用日记来仿写《野草》?萧红对《野草》的仿写与萧红的心理沉郁和创作思维转变有无关联?这些应该是隐匿在形式的仿写之后的问题。两则日记从表面内容上看似在记录“闲情逸致”中的闲聊和琐事,但其中不乏对友人、乡土和战争等进行的重新思考,还透露出萧红的孤独和无人应和,反观此前萧红的境遇,则能看到萧红模仿鲁迅的多重“曲笔”之下涵盖的潜文本。
“朋友们,坐监牢的……留在满洲的,为了‘剿匪’而死了的……”[25]二萧说起的这些朋友应是在哈尔滨时期结交的左翼青年作家,初到上海时二人也颇为关心“左翼”文学运动和成员命运[26],然而鲁迅在写给二萧的信中却一再打破二者对“左翼”阵营的想象:“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27]鲁迅也提醒二者上海文化界的复杂性:“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28]鲁迅在信中呈现于“二萧”的是一个与想象两异的复杂上海,而他们在生活中除了感受到寂寞、孤独之外,还置身于阵营内部的重重不信任、冷漠、隔膜感之中,“那时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29]热情好客的萧军也因要担心是否被徒出卖而搬家,这些因素可能使身处上海的萧红对往日想象产生了怀疑,或者更夸张一点地说,上海使得萧红产生一种与往昔截然不同的认知危机,从“左翼”队伍内部的犹疑开始,往昔写作中“工人与农民”的集体群像式阶级书写也并不能在左翼“大本营”的上海寻得现实中的对应,这恐怕也是沿着旧有的二元对立创作思维写下的《手》《桥》被萧红视为全是“缺点”“没有进步”的部分原因所在[30]。
革命者的悲剧命运亦使萧红产生对革命者书写的思考与转向。以友人金剑啸的命运为例,萧红在哈尔滨时期的许多社会活动都与金剑啸密切相关,金剑啸、萧红、萧军、舒群、罗烽、白朗等人曾一起创办反满抗日的《夜哨》周刊、创建“星星剧团”,等等。后“二萧”离开伪满洲国,金剑啸留在东北继续抗日,1936年8月15日被日军处决。萧军在《未完成的构图》中写到金剑啸之死:“听说在他入狱后的七天,他的女人还生了一个儿子,爸爸如今是死了,但愿他的儿子会康强起来,好完成爸爸的那‘未完成的构图’。”[31]曾经同行者在革命中的悲剧命运使萧红对革命产生了关注重心的转移,从革命本身转而关切革命背后“人”之命运,这种关注重心的转移不仅萧红独有,在由萧军、力群等人创办的《报告》创刊号上,刊物首页即是力群作的木刻画,画面中是一家三口分离的送别场面,男主人背着枪,跨开大步离开,其身后是双手掩面哭泣的妻子和抹泪的孩子。这个画面与萧红的诸多小说有颇为明显的相似性,在《牛车上》《汾河的圆月》《朦胧的期待》《北中国》中都有相似的情节片段,由此可见,对革命者作为“人”在“革命”中延展的个体悲剧、家庭悲剧的关切是萧红创作思想中重要的转变部分,也是她打破早期二元论人物构建方法的重要突破。
萧红在日记中还多次提到上海的战争,此时“八一三”事变还未发生,如果萧红所说的“战争”有“七七事变”的指涉,那么她所指上海的“战争”应与上海文坛的“战争”不无关联,萧红也数次被夹缠其中。环顾萧红所置身的1934年至1937年的上海文坛,先是发生“海派”“京派”争论,接着是“两个口号”论争,至1936年萧红也被裹挟进文坛“战争”中。1936年4月下旬,徐懋庸、何家槐等人发起成立作家协会,鲁迅拒绝参加,也未在内定人发起人名单上签名,但鲁迅、巴金、黎烈文、黄源、靳以等人对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拥护的,于是决定在6月份也发表一个宣言,即《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32],萧红也在上面签名。无论战火还是文坛论争,两种战争都使萧红躁动不安,她继续使用“曲笔”:“那么吵着的只有我自己,和那右边草场上的虫子。”[33]除此之外,萧红还要面对无以应和的孤独。两篇日记都在与萧军的对谈中展开,“每谈过之后,就总有些空寞之感”[34],这种与鲁迅“寂寞”极相似的“空寞”何来?从日记中可见,无论二人说起友人、喝酒、念诗、南北的雨,两人都有不同步的隔膜,萧红无法得到萧军的呼应,只能自语,最终置身无人能懂的寂寞中。投射进文学创作中,这种“空寞”感并非茅盾所理解的由情感生活所困而无法投身到农工劳苦大众中去的“寂寞”,而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所思考的以“曲笔”诉说内外郁积的寂寞,也即艾晓明所说,萧红进入“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对人类精神上的愚昧、卑劣作战。这就是个人写作的意义和价值”[35]。此后在抗战文艺的大潮中写下的“不合时宜”的《呼兰河传》《马伯乐》,未尝不是这个“寂寞”的萧红的“寂寞”书写。
鲁迅借《野草》的曲折表达绝望与幻灭,萧红此时以《日记》反写《野草》不光是为了纪念鲁迅,她以对《野草》的模仿与挪移串联起自己难以言说的内外积郁。也正是在此时开始,在“名”的构建中,萧红结束了“悄吟”和“萧红”两个笔名之间的往返,在创作中,萧红全面放弃早期创作中贫富/阶级/等级二元式人物构建的范式,转向对新的创作范式的探索中。
四、结语
萧红有着多次对“名”的关注,她显然清楚“名”不仅是外在表征,还具有丰富的内在指涉。从“悄吟”到“萧红”两个笔名的往返与置换,与萧红对自我的建构有密切的关联,而这个动态的、内在的、重重焦虑中建构起来的“萧红”的主体生成质素以及由此延展而出的创作思想转变动因,多年来被学界忽略。
本文为方便分析将引起萧红思考的不同焦虑做了分割处理,事实上这些焦虑是融溶嵌合的,若将这个动态过程做一整体性的爬梳,大致如此:抵达上海后的“悄吟”以“家”的焦虑为始,借《商市街》对往昔回望来直面自我的困境,思考“我”的生存层面的困境。而鲁迅对左翼内部的剖析和她对左翼文人阵营的体验促成了她对往昔阶级二元论创作方式的犹疑思索,也由此产生创作困境,加之情感困境、文坛纷争使“悄吟”远走日本,在日本寻找到新言说方式的“悄吟”在创作中寻到突破,而两度远离萧军独自远行经历也使其有了情感上和生活上的独立性。除此之外,战争、时代也衍生新的焦虑,每一重焦虑都促使萧红在重重裂隙中寻找到个体得以成长的契机,从思想内部产生构建自我、思考自我的可能,促发其创作思维上的转变,“悄吟”也自此成为“萧红”。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