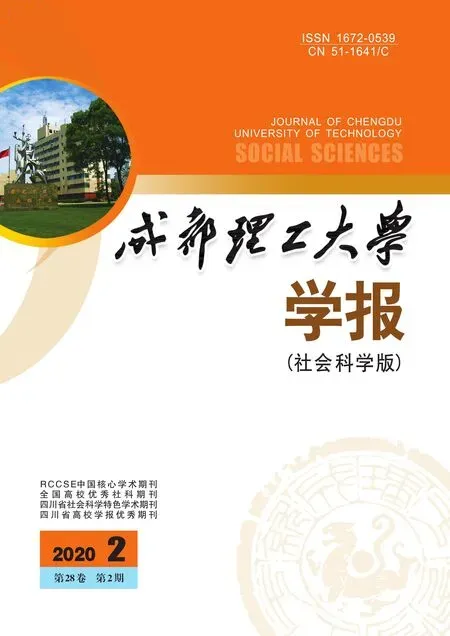《洛神赋图》中的“神兽”寻踪
张 起,张心仪
(1.成都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 610106; 2.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成都 610065)
一、《洛神赋》《洛神赋图》及其历史关系与意涵
传为东晋顾恺之作的《洛神赋图》,是一幅长达六米的绢本绘画长卷,有非常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它是根据曹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创作而成的。《洛神赋图》以连环画的构图形式展现了曹植与美丽的洛水之神宓妃的邂逅、相恋以及依依不舍的惜别,画卷缓缓展开,故事随之演绎,让人动容。在人们不禁感慨画作中充斥着南方绘画的屈原式的骚楚浪漫主义,为人神相恋却不得善终而哀婉。同时,我们在画作中还能看到在天上虚无缥缈的飞兽,在洛水中浮沉泳跃的水兽。这些神兽显然不只是出自洛水,而是融入了南方神兽的特征,这符合东晋文化在江左的特征,也符合画家的生活环境。画轴中的神兽灵动优雅,极富想象力,然而它们的名字却仍然不得而知,这是本文所要探寻的。《洛神赋图》如今原作已失,只留下了四册宋代模本。我们将以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第一种北宋模本为研究对象,翻阅中国古代记述山川地理、神鬼怪谈的奇书《山海经》,寻找这些洛水神兽的答案。
《洛神赋图》是对《洛神赋》的再现,其将文学语言转化为图像语言,画作的展开也是按照《洛神赋》中曹植与宓妃的相识、相恋、相别的时间顺序展开的,用洛神的形象代替了甄夫人,以真实的爱恋为基础,虚构了与神明的思慕爱恋,可以说是“寄心君王,托之宓妃”[1]。再观《洛神赋图》,第一段中描绘的就是衣衫飘飘的洛神漫步于水面之上与曹植相遇,曹植不敢惊扰的场景,对应原文中“俯则未察,仰以殊观。睹一丽人,于岩之畔”[2]189,“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2]190。第二段描绘的就是曹植和洛神相爱,但奈何人神不一,只能若即若离的矛盾,对应原文“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2]190。“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2]190画卷第三段描绘了洛神与曹植的别离,依依不舍的曹植回头张望的场景,对应,《洛神赋》中的“于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2]191。可见,顾恺之是非常忠实于文学原作而创作的《洛神赋图》,按照原文分段绘画了此作。《洛神赋》原文中也描写了一些神兽,我们可以根据原文的描写,对应画作的形象和后人对《山海经》的解释,来确定原文中提到的神兽。
顾恺之为何选择这一题材,我们可以从两人的生活年代去观察。曹植生活在192年至232年,而顾恺之生活在348年至409年,两个时期相距一百多年,这说明在当时《洛神赋》的影响很大,至东晋时期仍然历久弥新,受到东晋时人的喜爱;从文化层面来看,东晋衣冠南渡后,汉民族事实上的南北分离,使当时社会上出现一种结束分裂、恢复统一的愿望,而这一愿望在东晋时期又难以实现,当时士大夫文士的心境正合《洛神赋》的题旨,所以可以推见《洛神赋》在东晋士大夫中的流传情况,这才有了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这也是当时人们的普通愿望和心理感受,所以亦可窥见顾恺之画作的时代意义。
而这幅巨画又风神潇洒,可照见魏晋风度于画中的影响及其体现。应该说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才成就了这一幅举世名画,其山水虽拙,但也融入魏晋文人寄情山水的理想,画中神兽无不寄托了南方神话传统元素,体现深厚的南方楚骚文化,所以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选北方题材与南方文化融合的巨作,充分体现了反对分裂,民族融合的时代主题。
二、《洛神赋图》“神兽”考释
(一)飞天六龙
《洛神赋图》中一共有神兽17只,它们大多集中于洛水之上,在空中的有5只。这些神兽集中于画作的高潮部分,成为故事的衬托。仅洛神乘云车而去的场景,就有神兽12只。而《洛神赋》原文中提到的神兽,也出现在这个场景。文中写到:“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六龙俨其齐首,载云车之容裔。鲸鲵踊而夹毂,水禽翔而为卫。”[2]191其中点出给洛神拉车的是六条龙,《洛神赋图》高潮部分中也有六只神兽在为洛神拉车,那这六只神兽应当就是龙了。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便有“六龙驾日”的典故。《淮南子·天文训》中“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车”,《初学记》将“其女”引为“羲和”,“其马”引为“六螭”[3],指的是有六条龙在为驾驭太阳的羲和拉车。汉代刘向在《九叹·远游》中写到:“贯澒濛以东朅兮,维六龙於扶桑。”扶桑是太阳栖息的神树,刘向所说的六龙与扶桑的故事来源于“六龙驾日”的典故。另外,六龙的组合在《易经》中也有出现。《易·乾》里记载:“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由此可见,六龙的组合作为一个神圣的典故,可以出现在文学、绘画中,所以,无论是曹植的“六龙俨其齐首”,还是顾恺之在此画中描绘的驾车之龙,都可能受此个典故的影响。但顾恺之的六龙看上去却不像我们心中“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4]的龙。这六只神兽以赤色和白色相交排列,在洛水之上拉车奔跑。它们有鹿一样白色的角,角没有分叉,大而长的耳朵,鱼一样的眼睛,脸部较长。身体看上去像走兽,身上有鱼鳞,背部无毛,尾部也无毛,肚子有蛇纹,爪子看上去更类似于虎豹的足。这样的龙的形态与后世对龙的观念与想象不同,让人疑惑到底是不是龙。但这种龙形在汉代画像砖中数量较多,可见东汉绘画艺术与东晋是一脉相承的。汉代留下了许多表现“四象”的画像砖,作为四个方位的守护神之一,青龙时常作为表现对象和白虎成对出现[5]。汉代画像砖中的龙并没有长长的身体,其表现对比蛇而言更像是走兽,和白虎相得益彰。比如巴蜀汉代石棺画像石画像砖上的龙虎衔璧图,其中的龙也是角无分叉,身材较短,爪似虎豹,尾部无毛且卷曲的形象。此外还有藏于四川博物院东汉时期、于四川省彭州市征集的《骖龙雷车》,表现的就是龙拉车的主题,可以看到画像砖中有三条龙在拉雷神的车辗疾驰。这三条龙的表现为身体像虎,颈长而似蛇,头顶两角小而无分叉,背部披鱼鳞,腹如蟒,四肢如跑兽,尾部长而无明显毛发。这些汉代龙像和顾恺之的“六龙拉车”极为相似。东晋距汉不过百年,有很多文化艺术都上承汉魏,因此顾恺之画的龙类似汉代画像砖中的龙是完全可能的。还要特别注意一点,东晋以江南、湖湘文化为主,就是我们说的属于“泛南方文化”。巴蜀地区虽不属于东晋政权范围,但也属于“泛南方文化”,与荆楚文化相互影响,荆楚文化又与吴越文化相交。有了这样的逻辑,可知顾恺之“六龙驾车”存在巴蜀文化的影子。此外,《洛神赋图》不止一个版本,我们所熟知的是北宋的模本,南宋也有其他模本。其中有一版南宋模本,画的题材内容与顾恺之作完全一致,只是人物、神兽形象有所不同[6]11。在南宋模本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是六条青龙在拉云车,六龙的形象与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龙一致,身体似蛇,爪似鹰,毛发如狮子,张牙舞爪。这张南宋图本明显是后人对顾恺之图意的模仿又有发展,随历史与时俱进,融入了南宋人的“青龙”观念,不过这一模本反而证明了原图。《洛神赋图》中拉车的水兽可能就是承袭南方,主要是巴蜀地区汉代画像砖形象的龙(参见图1、2)。
(二)鲸鲵夹毂
《洛神赋》中提到的另一种神兽——鲸鲵,也容易辨别出来。原文中提到:“鲸鲵踊而夹毂”[2]191,也就是说鲸鲵从水中跃出,夹车欢迎洛神。在《洛神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洛神云车两边有两种鱼形神兽。原文“夹毂”,就是说将车辗夹在中间,那么鲸鲵这种神兽应当有两只,并夹车而行。《洛神赋图》中的神兽除了拉车的六条龙,其他的神兽都是单独出现,成双出现在云车两端的就是这种鱼形神兽。鲸鲵,也就是鲸鱼,雄性叫鲸,雌性叫鲵。但鲸鲵在中国古代,无论是绘画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不一定是实际生活中的鲸鱼,而是一种神兽,有特定的意象[7]。从《洛神赋图》中可以看出,顾恺之是按照想象来绘制这些神兽的,因此他的鲸鲵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鲸鱼,但也有一定的典籍记载,不是凭空的冥想。顾恺之描绘的鲸鲵长着狮子般的头颅,鼻子像龟,呈赤色,张开大口伸出舌头,头上有一角。其身体肥大,呈青色,上有鱼鳞,四鳍、尾巴、刺一样的背鳍呈赤色,夹在云车两边保驾护航。
鲸鲵有很多种别名,我们比较熟悉的名称叫“鲲鹏”。鲲鹏最早出现在庄子的《逍遥游》中,其开篇中就提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8]。其中写到鲲是可以转化为鹏的,也就是说,鲲鹏这种神兽有两种形态,一为鲸,二为鸟。此外,这种神兽既然生活在“北冥”,那么可以从《山海经》的《海外北经》和《海内北经》中寻找鲸鲵的原型。而在《海内北经》中,只有两种鱼类:陵鱼和大鯾。书中写到:“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9]35“大鯾居海中。”[9]35清代有很多描绘《山海经》异兽的册本,其中汪本和吴本都画有陵鱼。汪本的陵鱼呈站立状,有人一般的四肢,但却有鱼的身体。面孔看上去像是丑陋的人,头上还有两个角。吴本的陵鱼和汪本大致相似,只是画得更简单,头上的双角更加明显。此外,书中也没有提到这两种神兽的巨大,以及可以幻化成鸟。与《洛神赋图》的描绘和《逍遥游》的描写不太符合。再看《海外北经》,其中提到了禺疆,是北海之神,“北方禺疆,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9]449。此外,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记载,“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9]585。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有神,人面鸟身……黄帝生禺彪,禺彪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彪处东海,是为海神”[9]529。禺京指的就是禺彊,既是风神,又是海神。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关于禺疆的描绘。在曾侯乙墓的石棺内,便有禺疆的石刻画。禺疆呈现出鸟的身体,人的面部,咧嘴而笑,头上长有两角,手里还拿着戟一般的兵器。禺疆身上的羽毛根根分明,刻画得非常细腻。它的双耳呈S形,似传说中耳朵上挂着蛇。在与顾恺之同属东晋的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中,禺疆有两种外形,当它作为海神统治北海的时候,就变成大鱼的模样,当它作为风神的时候,则会变为鸟身,也就是《山海经》中提到的“人面鸟身”。这至少说明东晋时期社会大量流传古代神奇怪异的奇闻异事,不仅影响了干宝的创作,还影响了顾恺之的绘画思想。清代汪本绘制的禺疆就是风神的形态,它有着孩童的面孔,鸟的身体和翅膀,耳朵里伸出两条小蛇,脚上缠绕着两条蛇。禺疆具有同庄子的《逍遥游》中所记载的可以在鲲和鹏之间转化的一样特征。庄子心中的鲲和鹏的原型,可能就是《山海经》中的禺疆。而《洛神赋图》中的鲸鲵,也应该是禺疆的一种化身。由此可以看出,上古传说到战国记载到汉初成型的《山海经》再到晋代郭璞的《山海经传》,各种神话传说相互杂陈,相互影响,在中国文化洪流中不亚于正统文化而存在,这中间的神兽“鲸鲵”,无不激发着顾恺之的灵感与创作。试想如果没有这一盛行于世的文化洪流,也许就很难描绘这种神兽了(参见图2、3)。
(三)神鸟玉鸾
《洛神赋》中又写到,“腾文鱼以警乘,鸣玉鸾以偕逝。”[2]191也就是说,文鱼腾飞起来为云车警示,玉鸾作响来宣告洛神的离去。玉鸾,在古汉语中有三种解释,这也导致了本图中的神兽有两种解释。玉鸾可以指一种神兽——鸾鸟,又可以指鸾鸟形状的车铃,常常作为车铃的美称。玉鸾还可以比喻雪,但在《洛神赋》的语境中不可能用来指代雪。于是,解释的不同导致了原文翻译的不同,也导致了对图像中神兽解读的不同。如果解释为车铃,则应该翻译为“鸾鸟形的车铃叮当作响宣告着洛神的离去”,那么玉鸾就是指洛神云车上鸾鸟形的铃铛,并不是指的神兽。如果玉鸾就是神兽鸾鸟的意思,就应该翻译为“鸾鸟发出鸣叫宣告着洛神的离去”。针对上下文的修辞“互文”照应,前文既然是“文鱼”,后面当是指的神兽“玉鸾”,我们较为偏向这种解释。如果是这种解释,那顾恺之在画中就一定画了鸾鸟。这就很好辨别了,因为在《洛神赋图》中除了飞翔的水禽,只有一种鸟形神兽,它应当就是鸾鸟。鸾鸟在《山海经》中的记载出现在《西山经·西次二经》中:“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9]86其中“翟”的意思是有很长尾巴的野鸡,也就是说鸾鸟看上去像野鸡,羽毛五彩斑斓,它的出现预示着天下安宁。另外,在《艺文类聚》卷九《决疑注》里有“象凤者有五……多青色者鸾”。可以看出《洛神赋图》中的鸟形神兽,颜色非常缤纷,由于时代久远可能会有褪色的现象,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也依然可以窥到它的美丽。它大致由三种颜色组成:红、黄、绿,颜色之间又有不同的变化,它的头像鸡,头上有绿色羽冠,张开双翅正在飞翔,翅膀为绿色,其中有红色羽毛和黄色花纹,身体为橙黄色,胸前有绿毛,身后有双足。它最大的特征是有一根月牙型的、长长的尾巴,上翘卷曲着,尾巴上有纤细的绒毛,非常细致。这样看来,基本上可以确定它就是鸾鸟了,它的模样和《山海经》中提到的鸾鸟高度相似,特别是“其状如翟而五彩文”[9]86,野鸡般长长的尾巴和斑斓的色彩都非常符合书中所写。这种山鸡巴蜀楚荆山区较多,出现在《山海经·西山经》中不奇怪,而东晋政权中心在南方,顾恺之也可能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这样他在绘画处理上就不是想象,而是写实了。明代胡本的鸾鸟就有野鸡般的尾巴,抬起一足向后观看,头部似鸡,有小冠。清代汪本的鸾鸟则更加细致地刻画了羽毛,尾部像孔雀,头部像鸡,头顶有高高竖起的头冠。这些特征大体上也与《洛神赋图》中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如果顾恺之将玉鸾表现为神兽的话,则这只载着仙人的飞兽就应该是鸾鸟了。
但如果玉鸾被解释为车铃时,那它应该就是另一种神兽了,并很有可能是“骑凤仙人”身下的凤凰。在看到这只鸟形神兽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坐在它背上的那位仙人。那位仙人梳着高高的发髻,露出半个身子,手里持物,穿白衣,表情静美,充分显现了东晋的时代风貌,即洒脱的魏晋风度。当仙人和这种神兽组合在一起时,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骑凤仙人。骑凤仙人,或又称为骑鸡仙人,常常作为中国古建筑屋脊上的吻兽出现,骑凤仙人是吻兽中排在最前面的,也是为吻兽开道的。紫禁城太和殿上一共有十只吻兽,排在最前面的就是一尊黄色琉璃的骑凤仙人。此外,它出现在几乎所有带吻兽的传统建筑中,由于排在第一位的重要位置,它不会因为建筑等级不够而被去除,就不像行什、狻猊、天马、海马等神兽只能在高等级的建筑中看到。骑凤仙人和《洛神赋图》中的形象非常相似。凤凰出现在《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中:“佐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海,有凤皇、鹓鶵。”[9]45“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徳,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9]44书中详细地描写了凤凰的五彩、羽毛上不同的纹样以及习性。清代的汪本和《禽虫典》都有对凤凰的描绘,有着细脖长尾,头顶有冠,羽毛丰满,色彩瑰丽。这些特征与《洛神赋图》的鸟形神兽比较接近。因此,对原文中“玉鸾”的解释不同,其所指也不同,可以猜测这只神兽也有可能是凤凰,和它背上的神仙组成骑凤仙人。
(四)水生文鱼
文鱼也是《洛神赋》中提到的一种神兽。文鱼腾出水面为洛神鸣警,警示着云车的到来。《山海经》里有很多鱼类,很难确定哪个是文鱼。我们知道,一种神兽可以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文鱼是否也只是其中一种名字呢?按照字面解释,文也就是纹,就是身上有纹路的金鱼。在《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八经》中提到了文鱼:“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其多丹粟,多文鱼。”[9]336郭璞的注释为“有斑彩也”。清代的汪本就描绘了文鱼,但他的文鱼看上去更像石斑鱼。在《山海经》中,文鱼指的应该就是石斑鱼,它色彩斑斓。但在这里,文鱼指的应当是更神奇的神兽,而不仅仅是石斑鱼。“腾”字,体现了文鱼能飞的特点,唐代著名学者李善给文鱼的注解是“文鱼有翅,能飞”。而在明代刘基的《兰陵王》中“文鱼翼短沉书扎,泪滴在衣袂,尽成清血”提到了“文鱼翼短”,表明文鱼是有翅膀的。我们看《洛神赋图》中,却没有看到带翅膀的鱼,因此不能按照原文和注解中描写的神兽来寻找。在洛神乘云车的画面中,在云车下端有一只长相怪异的神兽。它有着猴子般的面孔,身体较长,尾部隐在水中,可以看出身体下端像蛇,上半身像鲶鱼,但有明显的两肢,双手张开,仿佛在推开波浪。颜色为青色,背部为黑色,且有斑点。由于《山海经》中的鱼类形象太多了,如文鳐鱼、薄鱼、人鱼、赤鱬、冉遗鱼、鳋鱼、氐人等,有的鱼类特征相差不大,因此只能根据画面中的形象找出书中与它最为相似的。从图中可见,这种神兽最大的特征是蛇一样的身体。在《山海经·西山经·西次三经》中,有一种叫鱼骨鱼的神兽,这种鱼长着四只脚,有长长的尾巴,像蛇一样。书中写道:“桃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是多白玉,其中多鱼骨鱼,其状如蛇而四足。”[9]101清代汪本和郝本都有描绘,汪本的鱼骨鱼有鱼的身体和蛇的尾巴,有人一般的四肢。郝本的鱼骨鱼更像蛇,身体很长,有四只脚。汪本的鱼骨鱼与《洛神赋图》中的神兽非常相似,它们都有人一样的双手和长长的蛇的尾巴,因此,鱼骨鱼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较为相似的神兽是虎蛟。在《山海经·南山经·南次三经》中有:“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9]44虎蛟有着鱼的身体和蛇的尾巴,和《洛神赋图》中的神兽比较相似。清代汪本的虎蛟为鱼身蛇尾,但没有四肢,这一点和图中的不太一样。但汪本也只是在《山海经》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原文中也并没有提到虎蛟到底有没有四肢。因此,虎蛟也是一种可能性。也许顾恺之想画文鱼,但却将文鱼画成了虎蛟或者鱼骨鱼的样子(参见图4)。
(五)白色巨龙
在“六龙拉车”的上方,有一条白色的巨龙。这条龙处于非常醒目的位置,通体是美丽的白色。这种纯净的白色保留到现在仍然没有褪色,与黄色背景形成鲜明对比,也使这条龙成为《洛神赋图》中最为醒目的神兽。这条白龙只有上半身露出了水面,以正面示人。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头上的角比其他神兽更长,非常引人注目。龙角呈优雅的流线型,分别长出两只向下弯曲的分叉。这条龙通体被白色的鳞片所包围,肚腹是黄色的蛇腹,一只臂膀上缠绕着缎带般的赤色火焰,其中一只龙爪伸出水面,另一只没入汹涌的波涛之中。它的爪子也呈白色,可见三指于其上。白龙的背部、头部、肘部均有绿色的毛发覆盖。它的双眼呈鱼目,正盯着洛神的船只,从嘴中仿佛衔着绣球,又仿佛是伸出的舌头。它的形象与下方的“六龙拉车”中的龙完全不同,但动作都异常优美。六龙在向前奔腾,白龙在向后回望,构图极具动感。从外貌上来看,它是一条为洛神护驾的龙。不过,它的形象和其他龙都不一样,我们猜想它们应当是不同种类的龙。但是,要确定它具体是什么种类非常困难,在原文也没有写到有一条回望洛神的龙。对比另一个版本的《洛神赋图》,我们可以发现在六龙拉车的上方,云端里有一条飞龙驾云回望洛神,与此北宋模本如出一辙。虽然神情、构图相似,但龙的形态却完全不同。一只是跃出水面的白龙,一只是飞腾在天的青龙。所以,只看北宋模本的白龙可能会联想到蛟龙,但没有太多证据证明它就是蛟龙,古代文献中对蛟龙的相貌特征解释也各不相同,更何况看北宋模本中的飞龙更不符合蛟龙的特点。因此,只能猜测顾恺之画的这些龙是不同种类的龙,但不能确定具体是什么种类,也许顾恺之只是希望画面不要这么单调,根据想象绘制了不同形态的龙。有趣的是,清代萧云从绘制了一副《羿救宓妃图》[6]71,此图讲的是后羿和宓妃相爱,但宓妃却被河伯夺去,于是后羿从河伯手中将宓妃救下的故事。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宓妃与后羿站在激浪当中,在他们上方有一条飞龙。那条飞龙有可能是河伯的化身,可能是河伯派去的神兽,也可能仅仅只是为了增加神话感而绘制的神兽。可以看出,在绘制宓妃的同时画家有时会在她身边画一条龙,无论是宋代不同版本的《洛神赋图》,还是清代的神话插图,洛神身边都有龙的出现。不过,由于时代相隔太远,我们不能将顾恺之的绘画和清代的《羿救宓妃图》中的龙联系起来,只能说明有时宓妃会与龙一起出现。当然也不排除《洛神赋图》中的白色巨龙是宋人摹画时添加上去的可能,毕竟这条白龙与六龙形状不同,也与东晋时人对龙的认识想象不同。这条龙可能符合宋代社会流传的白龙的形象,所以此图是否顾恺之原作临摹尚须存疑不能邃下结论(参见图5、6)。
(六)婉约游龙
我们将视线转移到画面的前端。很明显,可以看到在群臣聚集的左边,虚无缥缈的洛神的右上方,有一条腾飞的龙。这是非常明显的龙的形象,因此比较好确认。这条龙与前文“白色巨龙”又不同,它能对应曹植《洛神赋》原文,应该不会是后人添加上去的。这条龙比较短小,脖颈很细,如蛇颈,身体稍粗。四肢较长,张牙舞爪。爪上有三四指,如鹰爪般张开。它的四肢肘部有墨色长毛,尾部毛较少,背部无毛。龙身上长着鱼鳞一般的鳞片。令人惊讶的是它的精美程度,每一片龙鳞都被刻画地清清楚楚,就算过了千年,也能看得出线描的鳞片。这些鳞片方向随着龙的身体扭转而变化,仿佛是真的长在龙的身上,非常生动形象。它的神情闲怡,自由地腾飞。这条龙特殊之处在于它仿佛只有一只角,爪指也非五根。它的角呈鹿角状,稍稍往上弯曲。这条龙的出现不禁令人好奇,为什么顾恺之要在这里画一条龙。是象征曹植还是象征洛神呢?我们知道,龙在古代一直是非常神圣的动物,甚至是皇权的象征。这条龙不是双脚五爪的金龙,但也象征了高贵。曹植不是皇帝,但地位也很显赫,这条龙的出现也许是曹植的影子,可能象征着图中曹植的地位不凡。不过,如果联系原文,我们就能发现也许这条龙代表了洛神宓妃。原文写道当群臣询问曹植洛神的模样,曹植答道:“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2]190其中描写了洛神的模样,提到洛神就像游龙一般婉约。这条龙恰巧出现在洛神出现之地,是不是就预示着诗词里的“婉若游龙”呢?仔细观察龙的形象、神态,我们可以发现它看上去不像象征权力的那样凶猛、锐利,而是更多了一份女性的柔美。它的嘴巴是闭着的,没有像龙袍上的龙那般露出獠牙,仿佛还有笑意,看上去娴静又超然。另外,在龙的上方有两只飞翔的鸿雁,顾恺之在这里画鸿雁显然不是随意的,可能描绘的就是“翩若惊鸿”。如果这样解释,那么这条龙应该表现的就是洛神的“婉若游龙”了,象征着她在画面中的登场(参见图7)。
(七)日中金乌
美丽的洛神立于岩畔,在她左上方有一轮明日。顾恺之将其画为橘红色,里面隐隐约约有一只黄色的鸟形神兽,仿佛还长了三只脚。在太阳里面的三足鸟形神兽,自然让人想到了金乌。金乌是一种居住在太阳里的神鸟,本来世界上有十只金乌,传说中的后羿射日其实就是后羿射死了其余的九只金乌,剩下的那只就是我们现在的太阳。《山海经》中有关于金乌的记载。金乌传说为帝俊和羲和的儿子。他们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踆乌,会飞翔的太阳神鸟。另外,神话传说中也有“望舒驭月,羲和驭日”的说法。《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9]549这十日指的就是金乌。《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9]467也就是说,汤谷边上有一颗扶桑树,十个太阳(金乌)在这里居住。这十个太阳有九只住在树下端的枝条,有一只住在上端的枝条,它们的存在使汤谷的水都沸腾了。另外,《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有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9]530也就是说,汤谷中长了扶桑树,一个太阳刚刚回到扶桑,另一个又飞了出去,这些太阳都承载在金乌的背上。在《淮南子·精神篇》中有“日中有踆乌”[10],踆乌指的就是金乌。在太阳中描绘金乌的并非顾恺之一人,他的金乌有对前人的借鉴模仿。金乌的形象在西汉前为居住在太阳里的乌鸦,有两只脚。西汉后期,神兽演变为有三只脚的乌鸦。最著名的金乌形象是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绘的鸟形神兽。它是一只黑色的双足鸟站在一轮红日中。除了此帛画外,金乌的身影在汉代石刻中也常常出现。在江苏省铜山县小李村发掘的苗山汉墓中就有画像石描绘金乌。它站在圆形的太阳中,有三只脚。另外,现藏于金沙博物馆的出土于四川成都的太阳神鸟金箔。围绕着太阳的四只富有古蜀国艺术特征的神鸟与金乌非常类似,但也可能是古蜀国自身所崇拜的鸟形图腾。无论是何种情况,都显示出这种神鸟与太阳之间的强烈联系。不过,我们还是要佩服顾恺之的想象力,在这一幅奇妙长卷里精心加入各种神奇的元素,连在画面中不起眼的太阳里都要画上金乌,使画面更具神话感(参见图8、9)。
(八)北方屏翳
在画面中段,可以看到一个嘴巴大张的怪兽。它穿着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裤子,腰间系着褐色的腰带。它身上长着黄褐色的毛,它的头看上去像是野猪一般的猛兽,脸上也长着毛。它有大大的赤色鼻子,张开血盆大口,嘴里有五颗獠牙,还长着人的眼睛。头上仿佛有角,但由于画面模糊不能辨认清楚。它的四肢像是虎豹般猛兽的爪子,身后还有一条尾巴。它像是几种动物的集合,很难说明它的具体形象。它的四周围绕着云,张开的嘴仿佛在将这些云吸进去。联系《洛神赋》,我们可以看到描写洛神出现时众神迎接的场景:“于是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2]191其中提到了风神屏翳将风收起来,对应顾恺之画的这只猛兽,它也有将风往嘴里吸的动作。顾恺之用线条表现了云朵变成风被吸入嘴中的样子。通过它嘴上的纹理,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风在被吸入时产生的力量,几乎可以确定这只神兽就是屏翳了。在《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有对屏翳的描写:“雨师妾在其北。”[9]467雨师妾本来是国名,意思是雨师妾国在北边。郭璞注“雨师,谓屏翳也”,那么,《山海经》里的雨师应该就是屏翳了。屏翳代表北方。顾恺之是东晋人,当时正是衣冠南渡,北方沦陷于外族的时代,汉民族积弱的心态下,使得画家对来自北方的屏翳心怀恐惧。在这种心理下,它自然带有北方胡人的色彩:赤色鼻子,装束似外族,有黄色体毛,脸上有浓厚胡须,青面獠牙,这些人物指向了人们想象中“五胡乱华”的胡人形象,展示了创作《洛神赋图》的时代背景。在另一版的《洛神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屏翳是另一种形象。它看上去更加凶猛,像是长着翼膀的恶鬼,穿着豹皮纹的服饰,有着青绿色的皮肤,瞪大双眼,张开蝙蝠似的翅膀,站在云端收风。这幅摹于南宋的画,北方的神兽屏翳更为凶猛可怖,这也许也与时代相关。南宋江山分裂,北方沦陷,所以任何画作不是无缘无故创作的,而是时代社会心理的照见。
对于屏翳的形象,民间解读认为它是长着翅膀的鸟的形象,可能与最早的祈雨巫术有关。不过,《山海经》里没明确描写屏翳的形象,因此,屏翳的具体模样还不能确定,也许顾恺之是根据想象画的屏翳,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心理是必然的。(参见图10、11)
三、结语
神兽与洛神的呈现,并非只是曹植或顾恺之的一时兴起,而是寄托了他们的复杂情感及时代感。曹植的《洛神赋》来源于他对哥哥曹丕之妻甄夫人的特别感情,前有《感甄赋》,后有《洛神赋》。除了对甄夫人的情感思念外,处在政权斗争漩涡中心的曹植,压抑而失意,心中的理想与抱负无法实现,作为争夺皇位的失败者又失去了宝贵的自由。在这样的郁闷心境下,曹植通过幻想存在一位美丽的仙女,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神仙世界,来慰藉自己苦闷的精神世界。笔者还认为“甄妃”可能隐喻的就是他可望而不可得的“皇权”,只不过曹植借鉴了屈原以来“香草美人”的技法,委婉抒发心曲,那么《洛神赋》就是反映宫廷斗争的有所寄托的政治之作。因此曹植这本来充满悲剧色彩的作品,就不能简单理解为抒发纯真情感,以及对神仙生活的向往,在神仙氛围的背后是曹植对“皇位”的美好隐喻。但《洛神赋》中的神仙意境却被顾恺之借鉴,转换到画作中愈发飘渺,披上浓浓的神话和仙道色彩。东晋年间,战乱频发,衣冠南渡后汉民族的南北分裂,八王之乱后政权内部的斗争与更迭,北方五胡乱华的威胁,内部九品中正制对普通士人仕途的排斥,都使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现实感到失望,但他们心中仍充满情怀,不免会产生宗教想象,期望获得一个仙境般的太平盛世。这就孕育了晋人的仙道意识,与此相关的仙道文学作品出现在了顾恺之的时代,可见《洛神赋图》与《洛神赋》创作的内外条件非常相似,他们跨越时空的洪流共同描绘了洛神和神兽们,可谓是创造出了既有时代理想又有现实意义的不朽之作。
《洛神赋图》中的神兽,从神龙到鸾凤,从鲸鲵到金乌,这些神兽刻画精美、栩栩如生,就连时光也无法撼动它们的美,即使穿越千年仍然熠熠生辉。它们展示着顾恺之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揭示着东晋人对神妙仙境的无限向往。如今,对这些神兽的研究学术界还做得不多,上述研究也只是根据各种神兽的特征与《洛神赋图》比较,再联系原文所得出的猜想与解读,因此可能会有疏漏,本文权作抛转引玉。在将来的研究中,还有必要对这些神兽的象征、民间信仰等进行系统的考察、研究,并联系历史背景研究顾恺之创作这些神兽的时代意义,以及《洛神赋图》所体现出的东晋时期的宗教与世俗、政治与现实、文学与绘画多元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