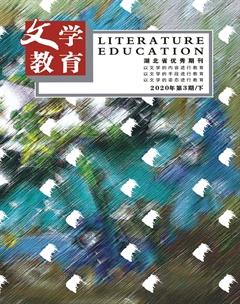小说家如何制礼作乐

一
晓苏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晓苏先生还是一位礼俗复兴的实践者,这一点恐怕许多人就不知道了。实际上,作家晓苏也是他的家乡油菜坡“苏系家族清明会”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甚至可以说是灵魂人物。这个家族议事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已经过去七年了,会中的活动尤其是一年一度的清明大会开展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受晓苏先生的邀请,笔者和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的师生一道,有幸参加了2018年度的油菜坡苏系家族的清明大会,亲身体验了祭祖、宴会、家族报告及文艺表演等礼俗活动。亲历之下,笔者不仅在情感上被苏系家族和谐和睦的温馨景象打动,更在思想上为组织者别出心裁的礼俗设计所激动,所以很快在心中有了这样一个引人兴味或让人疑惑的题目:小说家如何制礼作乐?
说引人兴味,是说苏系家族的礼仪设计,隆重、实在,又平易、活泼,处处透露出小说家式的细节感和人情味,完全没有某些“儒士”、“乡贤”拷贝的“古礼”给人的繁文缛节和不伦不类之感。说让人疑惑,是说小说家制礼作乐,这在传统(古板)的脑筋听来,一定是极为冒犯的举动。因为,几千年来小说一直是被视为“小道”,学问家们是不屑一顾的,而制礼作乐,从来都是“圣人”们的事业,至少也是“大人先生”们的专营。但到现代以来,时势为之一变,小说成了“文学之最上乘”,俨然文苑独步。但在礼俗方面,随着近年来传统复兴,被些近水楼台的古代史、古代哲学专家抢占了先机,当起了代言。小说家参与礼俗设计,不仅很少听闻,即使有,怎么也得穿件“传统文化”的国服才显得名正言顺些吧。但我们的这位礼俗设计者,偏偏是个主张“后现代”风格的小说家。
二
礼俗这东西,被有些人弄得正襟危坐高不可攀,实际上却是人类文化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根本就不稀奇。什么是礼俗呢,用美国的一位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的说法,就是“小群体中的艺术性交际”,或者也可以叫作“交际性艺术”。道理很简单。正如荀子所说过,“人之生也,不可无群”,人类的日常总是处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群体中的,这就免不了有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而人的交流,往往不是直接的、直白的,和动物式的“父子聚麀”有很大的不同。人的交流,是委婉的、间接的,是用了隐喻化、艺术化的手段来表达的。简易如点头握手、肃穆如礼乐祀典,“野蛮”如纹身画面,文明如对歌传情,这些都是小群体或日常情境中的“艺术性交际”,都是礼俗。
所以不单单儒家有礼俗,道家也有礼俗,文明人有礼俗,野蛮人也有礼俗,社会主义有礼俗,国家社会主义也有礼俗,甚至黑社会想要维系起来都得有礼俗——比如天地会的仪式戒条、斗茶对诗,其繁复程度,是丝毫不亚于儒家的。当然,形式上的相似不等于内涵上的相同。使得人类文化中的种种礼俗体系相互差异的,在根本上是其对待人本身的态度——是以上下尊卑为要务,还是以人人平等为宗旨,是以小团体利益为本位,还是以天下大同为己任。
这就是说,作为人类生存中最常见的文化手段,其实无论谁人都是可以创制的,关键是其根本宗旨是什么。所以不是只有“圣人”才有资格制礼作乐,而且圣人也不过是个名号,是个形容词。圣(聖)的本义,《说文解字》解释为“通”,差不多就是今天俗话说的“懂行”;《风俗通义》解释为“聲”,闻声知情,就是圣,差不多相当于现在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制礼作乐的圣人,不是天地间的怪物,而是能协调礼仪之现象与本质、内在与外在的行家罢了——即不仅懂得礼的原则,还懂得什么样的礼仪最适合表达这个原则。如果用《礼记》里的话说就是“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当然,儒家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对人性的基本尊重,在于它对天下为公的不懈追求,这使得儒家的礼乐堪称文明,虽然不乏历史的局限性。儒家制礼作乐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它的宗旨始终在于维护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还表现在由于对礼仪的过分执着而衍生的教条化倾向,即礼仪可能脱离人性而成桎梏。而礼教要想不成教条,就得时刻谨记制礼的要点,是“因人之情”。这一点“先圣”是有自觉的,不过具体执行起来很不易。因为要因人之情,就先要懂得人情,那么问题来了:儒家的圣人和后学懂人情吗?今时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懂人情吗?不见得。话又说回来,如果谁懂得人情谁就更有资格制礼作乐,这下恐怕就要轮到小说家们窃笑了。因为,就像古代那位最伟大的小说家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到即文章”,小说家其实正是人情的专家。
三
实际上,无论是儒家圣人后学,还是原始部落首领,抑或芸芸凡夫俗子,一旦涉及如何设计礼俗,他们都会面临一些根本性的难题。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小说家或者小说式思维,正能为此一难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启发、补充以及矫正。
古人说,诗言志,实际上礼仪也是心志的表达,无论是礼容(神情)、礼仪(动作)还是礼器(礼物),都是表达内在之心意的外在载体。既是载体,就免不了会有“异化”的时候,即外在与内在不能相符,或者东西不能代表“心意”,或者礼虽到而情未到,也可能是有心而无力表示。礼崩乐坏,自然是“人心不古”的征兆,但礼仪隆盛,也不见得一定有多少真情流露;甚至过份的繁文缛节,恰恰是对礼义匮乏的掩饰。所以孔子会无可奈何地悲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甚至有时候也不得不舍弃对形式的要求——“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概括一下,礼之内在与外在的脱节,或古话所说的心與迹之间的张力,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相互缠绕的维度。
其一,公共的仪式如何表达个人的情感?礼仪的本质和语言很相似,都涉及一个公共符号如何表达个人情感的难题,由于礼仪所用载体的局限,这一难题甚至更为棘手。比如,父慈子孝应该是亲子之间的伦理要求,但如何以礼俗表达这一要求,却很难一概而论。比如,《礼记》里讲,“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丑夷不争”,这能否看作屡试不爽的通则?
实际上并不见得。如何做父母,如何做子女,不一定只有一套通行的规则,更让人刻骨铭心的往往是极为个人化的个例和细节。晓苏先生非常赞赏的小说《上边》(作者:王祥夫)里有个细节,令人过目难忘。住在乡下的母亲,好不容易盼来了城里上班的儿子回家小住,但不久儿子又要走了,临走前儿子在院子里像小时候一样撒了泡尿。儿子走后心情失落的母亲,用个盆子扣住这滩尿迹。也许只有最敏感的心灵才能想像出这等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而这恐怕是古板的礼俗专家们轻易看不见的。
如何做子女,也是一样的道理。晓苏先生写自己的父亲、母亲,显得很真实,不虚伪。在散文《读父》中也有一个细节令人难忘。文章写自己在一个雪天跑去父亲工作的地方玩,没想到父亲忙于打牌,根本没有问自己是否吃饭,还立刻打发他回了家。但也许这种爱恨交织才是亲情的真相。正如作家自己说的,“父亲也是个凡人,他也有自己的兴趣,也有自己的个性,也有自己的脾气,偶尔的疏忽、偶尔的暴躁,偶尔的失误,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原谅的”。小说《父亲的相好》则更是一个更能让礼学专家惊掉大牙的话题。小说以一个人到中年的女儿的口吻,讲述了她对父亲出轨行为的谅解:父亲年轻时那么帅,他的相好那么漂亮,又那么善良,这段故事又那么美好,怎么让人忍心去破坏和否认呢?毫无疑问,故事里有受害者,但这就是真实的人生,没有完美的生活。人既不纯粹是天使,也不纯粹是魔鬼,善恶交织、即圣即俗才是生活的真相,以非黑即白、“人人皆可为尧舜”思维搞人性大清洗才是最可怕的罪恶。
这个故事也道出了制礼难题的第二个维度:抽象的原则如何表达丰富的生活?儒家制礼的热情,很大一部分是放在了“别男女”方面。但他们的目标和办法都简单、粗暴,用一个字就是“坊”,就是修筑防御工事,最好别让男女相见,因为见了就是洪水滔天。但男女之事就一定是洪水吗?小说《花被窝》讲了一个婆媳出轨与和好的故事,或者说因出轨而和好的故事。本来秀水只是因为怕婆婆秦晚香发现自己偷情才大献殷勤的,但在偶尔听说了婆婆年轻时也有相好时,才真正地理解和接纳了她,“秀水愣愣看了秦晚香好久,像看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而且晚饭时,婆媳俩“就你一杯我一杯地喝开了。后来,两个人都有点醉了”。这篇小说构思得极为狡黠,仿佛是在故意挑衅古板的思维。但小说也至为美好,因为小说中潜藏了一条伏线,秦晚香在相好去世后,每年都会去看一次他的老婆。这背后的情感之复杂与深沉令人惊讶、令人遐想,令人动容,这份复杂的深情,恐怕是任何抽象的心灵都体味不到的。
晓苏先生确实善于写性,善于写出性的具体、丰富,善于用性的丰富戏弄抽象的大脑。当然,小说可能是虚构的,是允许异想天开的,但小说式的思维对礼俗专家提出了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如何避免礼仪的抽象化与教条化遮蔽或戕害丰富的、具体的、个体的、微妙的、复杂的生活。当然,现实生活往往容不得精妙的构思,但当晓苏先生以小说家的敏感和细腻参与礼俗设计时,仍然透露出了小说式的细节生动与平易近人。
四
在油菜坡的参观能让人直接地感受到,苏系家族的组织活动有许多平易与细心的设计。尤其触动笔者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贴近人性。从平凡的人性出发去设计活动,不刻意拔高,也不刻意贬低,这是活动让人心情舒畅的根本缘由。每年的清明大会上,除了正式的祭祖、家族年度报告、表彰先进人物等活动,还有文艺节目表演和同吃清明宴。后面这两种活动的意义,其实是朴素而深刻的,容不得轻蔑。反观《礼记》中的儒家礼俗,是肃穆有余,活泼不足,有时候甚至给人的印象是儒家与欢快有仇。儒家对燕饮、诗乐倒是重视的,不过仍然庄重过头,看看诗经中保留的风雅颂就知道了,都是板起面孔教训人的,即使有几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民歌,也是被做了了无趣味的曲解。而苏系家族活动上的节目,贴近家族,贴近生活,带来的是笑声不断,掌声如潮,也是真情难抑,泪流满面。
二是贴近百姓。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尊重他们的文化,推动他们的生活,这是家族活动能长久维系的关键。家族作为一种人类团体,一定有主导者和从属者。传统的家族是家长制的、精英制的,是蔑视民众及其文化的,文人、乡贤是教化者,普通族人则是被教化者。表现在仪式用语方面,它是崇尚书面语言、贬低口头语言的,从家谱到祭文,仿佛只有用上之乎者也伏惟尚飨才显得文雅。所以当我们看到苏系族歌时,不仅莞尔,又深为赞服。这首歌唱到:“苏氏族人个个要牢记,八个必须和八个不许,第一必须孝顺老辈子,千万不能忘恩负了义。”显然,这是借用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重新填的词。这样广为流传又郎朗上口的曲调,不知道比那些不文不白的语言高明了多少倍。同样地,族人上台表演节目,一开口就是喜闻乐见的花鼓词、三句半和顺口溜,也不是装神弄鬼式的汉唐古风。
三是贴近女性。家族维系的是男性的谱系,也是男权和父权的集中体现,所以女人历来在家族中没有什么地位。外来的女性,只承担着一个延续男性香火的功能。前几年某电视台的公益广告就拍了一个新媳妇在族长和族人面前拜祖先的情景,可见这传统是多么根深蒂固。可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毕竟已经喊过一甲子了,社会上能干的女人多的是。面对这种现实,今天的家族还能将女人扫除在外吗?我们欣喜地看到,苏系家族中的女性,包括外来的媳妇和出嫁的女儿,都不是被动和沉默的,而是突出的甚至卓越的。尤其几位被评为年度先进人物的女性,或者致富不忘族人,或者持家不忘叔伯,或者出嫁不忘祖父,在女儿、媳妇、母亲的身份转换之间,表现出新时代女性的动人风姿。
但女性进入家族的意义,恐怕还不止于此。它甚至撼动和改变了家族这种人类共同体的情感品质,为父系共同体的生硬带来了母系的温暖。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人类最亲密的共同体形態有三个,依次是母子、伴侣、同胞,而把父子关系放到了核心圈之外。母亲是家庭的核心,其实也是家族的核心,这是人类由情感天性决定的。正如人类的语言显示的,德国人把祖国称为Muterland,也就是“母国”,民间俗语说“回娘家”而不是“回爹家”,就说明了这种情感的深厚。滕尼斯还说,兄弟姐妹之间的亲情也源于同处母亲怀抱这一情境和记忆。所以,在家族中容纳女性,其实是正视她们的情感地位,是恢复她们对于维系家族共同体的关键价值。这样的家,才会成为游子永远的牵念。
五
古人说话其实和乡下人差不多,好打比方。比如,他们把最伟大的事物称为天或天地。因为天地养育万物,一视同仁,绝不偏私,这就是《礼记·中庸》里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万物各有其生长之规律和条件。三月桃花开,八月桂花香,腊月梅花放,每一种都需要有不一样的水土气温,才能开出不一样的姹紫嫣红。如果给它们施同样肥,并要它们开同样的花,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人作为万物之灵,也是一样的,但更为复杂、微妙。那么,如何可以用同样的礼仪来约束他们呢?
所以制礼作乐者,一定要有天地的胸怀和视野,尊重每一物、每一人的天性,而成其天命,他们必须要有洞察人类情感复杂性的能力。而小说家提醒我们的,正是这种复杂性。和语言一样,礼仪、礼俗是人类交流的必需品,但也有遮蔽丰富、微妙的个体生活的可能性。小说家的职业伦理,正是去发现和保护生活的复杂与“例外”。这样的功夫就是通常被误解了的“想象力”。想象力的意思,不是凭空臆想,而恰恰是要回到具体;它不超越生活,而只是超越生活的“常规”,以便更深地进入生活的具体、细节。制礼作乐者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容纳例外的视野,关注细节的视力。
毫无疑问,近年来的礼俗复兴是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但是叫卖药方的不一定都是国医圣手,还有江湖郎中。在今天的倡言礼俗者中,有开闭门会议要让女性回归家庭的,也有要恢复文言文以便行文化霸权的,还有表演给父母洗脚这类孝道或“笑道”的。他们都应该听听小说家之言,悟悟小道可观的道理。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