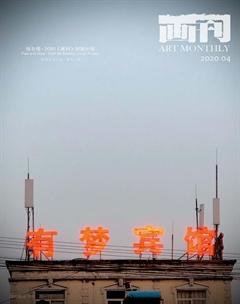荷花女
张嗣

荷花女是一个十七八岁的苏州农村姑娘。她眉目清秀,勤劳、伶俐,也很健谈。
当荷花女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便跟我说起她大婶20世纪90年代时,在北京给一家从他们村子出去的大户人家做保姆。大婶厨艺很好,主要负责烧菜做饭。据说那家老先生吃惯了南方菜,北方的师傅做不来。老头最爱吃家乡的梅干菜烧肉,大婶家里每年都会晒好了梅干菜预备着带去北京。“后来老先生走了,再后来大婶也回来了,每年清明节她还会端一碗梅干菜烧肉到老先生的祖宅家堂上去。”
如果不是后来听村委会老姚说,荷花女的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村里给上海运送军粮的民兵组长,后来还当过村长的话,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厨师世家——荷花女小小年纪却很有烹饪天赋。我之所以称她为“荷花女”,是因为初加微信时见她的名字是“A:)荷花湾农家院133xxxx”。
荷花湾农家院是荷花女的父母经营的一家农家乐。父亲主管客房,母亲主管厨房,荷花女中专毕业后就帮母亲打下手,家里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弟弟。农家院建在村口一个半圆形的荷花塘旁。后来几天我才发现,村里随处可见的水塘都是鱼塘,准确地说是蟹、虾和鳜鱼的天下。这个全村唯一的荷塘不算太大,约有半亩地,但修整得很好,四周是用青石板层层垒起来的。三进的农家院,前院是餐厅、厨房和一个小停车场,中间是七八间客房,后院是老板一家和伙计的生活区域。
我到村里的时候是11月初,荷塘里的荷叶差不多都已经凋敝了。荷花女告诉我每年盛夏的早上6点到8点是赏荷的最佳时刻,因为这个时间段的荷花最有生机。我来复述一下从她那儿学到的自然知识:一般荷花为了繁衍后代的需要,保证授粉成功,都会开放两天。第一天早上开花,到接近中午时花瓣会全部收拢,仍然变成花蕾。第二天早上收拢的花蕊会继续开放,这些花在接近中午时花瓣会脱落,已授粉的莲蓬就留在枝头继续慢慢成熟。所以清晨的荷塘是一天中最美的。每天这个时候,荷花女已经帮母亲喂完牲口、洗切完毕一大篮子时令蔬菜从厨房出来了。
“荷花湾”不是村里唯一的农家乐,但一定是全村位置最好的一家。除了荷塘外,院门口有一条来往车辆的必经之路。这条路上每天跑着鲜水活产运输车来村里上货,司机和工人们常在荷花湾吃饭住店。自从20年前这里的老百姓发现种水稻远不如养蟹养鱼挣钱,甚至还赔钱时,村庄几乎所有的耕地很快都改成了鱼塘,很多村民靠鱼塘致了富。那会儿荷花女的爷爷——老村长虽然也为乡亲们感到高兴,但心里开始有了芥蒂:一是因为上面有压力,使得各村每年上报所有的鱼塘登记在册仍为耕地,至今如此。二是他常挂在嘴边却很难引起大家注意的粮食安全:苏南、浙北城市和乡镇的粮食供给完全依赖东北、苏北,万一遭了自然灾害或战事,目前像苏州地区的粮食储备量只有30多天,而在1987年时能维持3年。
同样被改造成鱼塘的是桑园,大部分村民也就渐渐不再养蚕了。当年家家戶户孩子们跟着长辈采桑叶喂蚕,父母半夜还要起来添叶的情景再也见不到了。这里著名的丝绸业的原料来源转向了千里之外的广西,那儿有大片的桑蚕基地、缫丝厂与相对廉价的劳动力。
荷花女回忆起童年里那些大眠了的蚕宝宝,肥胖的身子发白透亮……弟弟比她小10岁,就没赶上这样的美时光。说起她这个随母姓的亲弟弟,还需介绍一种此地由来已久的叫做“两头挂花幡”的婚姻形式。当地人十分看重家族香火的延续,过去就有不少本村本乡甚至本镇通婚的青年男女采取“两头挂”:在婚前祭祀仪式上,男家将一面用红布或红纸做的花幡挂在自家家堂的祖宗牌位上,女家也做一面花幡挂于女家祖宗牌位。花幡是传嗣的象征,以此表示男家是娶新娘,女家是招女婿。两家共同决定结婚事宜,不设彩礼,各置办一处婚房,婚后可根据需要轮流住。并且,这种婚姻中不成文的规定是一般应生两胎或以上,尤其放开二胎后,不论男女,头胎随父姓,二胎随母姓。孩子们无外公外婆娘舅舅母之说,都以爷奶叔婶称。荷花女的弟弟就是“两头挂”的二宝。
荷花女小时候的村办学校早已被撤销,弟弟今年到离家15公里外的镇上读小学,家里为此在镇区买了套商品房。撤乡并镇政策在苏南基层落实得很彻底,教育系统内大量撤销乡、村初中小学并入城镇,集中资源搞优质教育。但是,非常多的农村孩子因此上学就很不方便了。
“说不定哪天我们全家都搬去了镇上,不在荷花湾哩……”她说道。
现在,因为母亲在镇上陪读,把荷花湾的厨房交给了荷花女。我在朋友圈常常看到她掌勺的刚出锅的新菜品,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