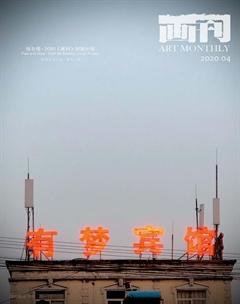七种不可行的治疗方法(上)
[美]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
你将要阅读的这篇文章最初是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的。在18世纪的英格兰,有一种传统的小册子:它们是以非正式文体写的小书,引起了激烈的辩论而出版的。人们过去常常随身携带它们,并在公开辩论中使用它们。我写的《艺术批评发生了什么?》就是用这种传统小册子书写的。书中提出艺术批评家变得对赞美艺术比对分析和判断艺术更感兴趣。我认为艺术批评已经变成中立的了。
当我写这本书时,我引用了当时刚完成的一项调查,证明北美的艺术评论家不喜欢批评艺术。那已是15年前的事了,但很幸运的是,第二项调查也刚刚完成,也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很可惜的是,这两项调查都仅针对北美的艺术批评家。如果能有来自其他国家的類似调查就好了,尤其是因为目前还没有关于全球性艺术批评的研究。
人们对于艺术批评本身知之甚少。当今有一个国际艺术批评家协会(AICA),但他们不分析批评本身,他们的出版物也不是艺术批评的典型例子。艺术批评仍然是艺术界研究最少的领域之一。相较之下,国际双年展或展览通常会有多种语言的图录,许多艺术史书籍已经被翻译成欧洲语言。但是,艺术批评却很少被翻译成母语之外的语言:如果一个评论家用爱沙尼亚语写了篇文章,然后在当地报纸上发表,那它可能永远不会在爱沙尼亚以外的地区被翻译或阅读,其结果就是艺术批评就如同一个未知的大陆。如果将更多的艺术批评文章从中文翻译成英语或其他语言,也有从许多其他语言翻译成中文和英语,那将是极好的。翻译将是唯一的方法,以决定是否有一个全球性的艺术批评实践,或是否在不同国家其实践并不相同。
《艺术批评发生了什么?》也是我正在撰写的一本有关全球艺术批评的书的第一章。2019年,我对欧洲和美洲的艺术批评现状进行了调查,包括视频记录和线上杂志的最新发展情况。这项调查可在网站academia.edu(tinyurl.com/y6xg86ju)上查询。
我非常欢迎每一位读者给我写信,提出问题、发表评论和告知最新信息,我的邮箱是jelkins@saic.edu。(詹姆斯·埃尔金斯)
试图逃避当前艺术批评的迷雾,跑出去呼吸清新的、确认的空气,是充满诱惑的事情。当然,每个人关于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气氛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参与《十月》(October)杂志圆桌会议的人想要更多地关注严谨而又有理论性的成熟批评,以及“批评话语的复杂层次”。另一些人则希望艺术批评家们有规则、规范、理论,或者至少有一些共同的关注点。有人哀叹说,21世纪没有引导性的声音——哪怕是一个可以引导我们走出日趋衰落的多元主义迷宫的声音。呼吁对艺术批评进行改革的那些报纸通常是抨击术语,提倡用简明的观念。保守派批评家想要提升艺术的道德目的。克雷默(Kramer)希望引入一些老派的学科和严格的标准从而进行“区分”。报纸批评家们有时也想通过取消批评与市场的联系来改革艺术批评。
我认为事情要复杂得多。在当前的批评状态中发现问题的想法是由历史本身决定的。为什么《十月》杂志要在2001年秋举办一个批评的圆桌会议?这些会议文章大部分没有发表。为什么以“艺术批评发生了什么?”为标题的文章在2003年春天出现?理解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浮出水面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在驾驭历史思维的潮流,而我们只是断断续续地意识到这些潮流。对各种呼吁进行批评改革的原因的思考,有助于揭示那些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往往是来自于对过去特定时刻的怀念。让我试着用七个增加长度和难度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这些并不是对应艺术批评的七个头部,而是一旦你开始思考这七点,你就很难停下来。)
1.批评应该通过改革回归到那种非政治性的形式主义活力的黄金时代。在《罗杰·弗莱读本》(A Roger Fry Reader)一书中,美术史家克里斯多夫·里德(Christopher Reed)指出,因为弗莱(Roger Fry)具有复杂性,“与权威的反传统关系”,以及“社会使命感”,弗莱可以被解读为是一位“后现代”的批评家。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写了一篇像往常一样不耐烦的批评文章,声称里德的观点是不可行和错误的;克莱默认为这是后现代“无视历史”的典型产物。替代里德(Christopher Reed)的版本,克莱默想要一个深思熟虑但又保守的弗莱,而不是一个像“前卫燃烧弹”的弗莱。克莱默不喜欢受到政治影响的艺术批评,这促使他强调弗莱有兴趣在“生活之外的领域”中找到艺术法则(里德用这一短语来提醒读者,弗莱所做的并非全部)。没有什么能阻止弗莱从每一代新人中重生:那是历史接受的本质。然而克莱默的弗莱是克莱默的“前卫”语言:一位杰出的形式主义者,他了解并尊重过去的艺术史,并且不害怕提出“生活之外的领域”。显然,克莱默的争论是出于怀旧。他想要的是他想象的事物曾经的样子,而这并不是当代艺术批评的合理模式。
2.批评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声音。1973年,既是艺术家又是美术史家的昆汀·贝尔(Quentin Bell)用与我一开始说的同样的话,哀叹权威艺术批评家的衰落:“尽管用出版商的话来说,艺术文学正在蓬勃发展,但在某一方面遭受了损失。”贝尔思念的是那种批评家,他可以是一个“审查员”和为当代而辩护的批评家,就像狄德罗(Diderot)、波德莱尔(Baudelaire)、拉斯金(Ruskin)或者罗杰·弗莱那样的人。为什么现在的艺术界没有这样的“大学者”?贝尔认为这就是“现代艺术的特征”,它很难被讨论,或许是高质量的插图的传播消除了描述的必要性。不幸的是,对于贝尔的论点而言,批评的历史表明,在瓦萨里之后的几十年里,甚至可能是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缺乏强有力的批评声音。在温克尔曼(Winckelman)之前,批评的声音很弱,而且很分散。正如托马斯·达科斯塔·考夫曼(Thomas DaCosta Kaufmann)所说的那样。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争论说,在狄德罗之后,批评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在波德莱尔之后,出现了许多有趣的批评家,其中包括泰奥菲尔·托雷(Theophile Thoré)、欧内斯特·切斯瑙(Ernest Chesneau)、朱尔斯·卡斯塔纳里(Jules Castagnary)、爱德蒙·杜兰蒂(Edmond Duranty)、费利克斯·费内翁(Felix Feneon)或者阿尔伯特·奥里尔(Albert Aurier),但没有一个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那样对现代主义如此重要。在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和格林伯格(Greenberg)之前,批评的声音可以说是微弱的。我们目前没有先知,但这并没有对我们产生不良的影响。贝尔的抱怨是怀旧的另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主要是指布鲁姆斯伯里派的过去。
3.批评需要系统的概念和规则。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批评简直就是一团糟。在20世纪40年代,美学家赫尔穆特·亨格福德(Helmut Hungerford)想要把绘画按“类别”进行分类,并制定出和每个类别相关的标准,如组织、整合和技巧。在他固执的理性主义背后,我读到了他对形式分析命运的焦虑感。亨格福德的标准崩溃了,尽管他试图通过在类别和标准中提出“一致性”的附加标准来支撑这些标准。在我看来,亨格福德现在已经完全被遗忘了。也许艺术批评不能在逻辑上进行改革,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没有符合规则的结构。艺术批评长期以来在学术上都是一个混血儿,它从其他领域(崇高與美丽、判断与模仿、凝视与景观)借用所需的东西。它从未一以贯之地运用哲学的概念,而且,希望它将来会做到这一点也是毫无意义的。
4.批评必须变得更加理论化。也许,可以稍微降低一下标准,艺术批评应当运用共享的理论兴趣,不管它们来自哪个领域。影评家安妮特·迈克尔逊(Annette Michelson)在一篇关于保琳·凯尔(Pauline Kael)的精彩文章中提出了这一观点。她把凯尔和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他写了一篇关于《卡萨布兰卡》的文章)进行了比较,认为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她说,艾柯确信“激励和支持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将有利于交流”。迈克尔逊认为,凯尔“对她毕生作品主题理论化的顽固抵抗,抑制了她用品位和厌恶之外的其他术语来解释电影的影响的能力。”随着岁月的流逝,凯尔“不再更新她的知识资本,而是承认并从庞大的集体努力取得的成就中受益”。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表达观点的方式:与这一代的其他人一样,成为概念和理论工具宝库的一部分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他们只在未使用的资本形式中进入工作。我发现很难反驳这一点:它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由对早期完美激情和雄辩状态的怀旧支撑起来的。我会在最后有更多的说明。
5.批评应当是严肃的、多层面的和严谨的。这一呼吁或多或少是2011年《十月》圆桌会议上的共识,它有一个特殊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与《艺术论坛》有关的批评家,主要是从1962年《艺术论坛》成立至1967年左右(这一时期)。这些批评家包括卡特·雷特克里夫(Carter Ratcliff)、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约翰·卡普兰斯(John Coplans)、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芭芭拉·罗斯(Barbara Rose)、彼得·普拉根斯(Peter Plagens)、沃尔特·达比·班那德(Walter Darby Bannard)、菲尔·莱德(Phil Leider)、安妮特·米歇尔松(Annette Michelson)等。还有一些人属于一个松散的并且基本上分裂的群体,尽管如此,他们共享了一种艺术批评新的严肃目标。艾米·纽曼(Amy Newman)的访谈集《挑战艺术:艺术论坛(1962-1974)》(Challenging Art: Artforum 1962-1974)是理解该群体难以捉摸的批评意识的一个很好的来源。在《挑战艺术》一书中,约翰·科普兰斯(John Coplans)认为,这股致力于分析批评的浪潮间接地来自侨居在外的德国学者,尤其是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尽管事实上,有几位艺术批评家的职业生涯始于对像悉尼·弗里德伯格(Sydney Freedberg)等美术史家作品的批判。科普兰斯指出,美国早期唯一的严肃的艺术批评典范就是《艺术杂志》(The Magazine of Art),特别是当罗伯特·戈德沃特(Robert Goldwater)在1947年担任杂志主编时。他说,《艺术杂志》“完全反对法国的模式”,那种被认为诗人的传统模式。纽曼(Amy Newman)采访的一些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诗人和评论家卡特·拉特克利夫(Carter Ratcliff)回忆说,一些诗人-评论家仍然对“私人历史、个人历史”感兴趣,而另一些人,尤其是《艺术论坛》群体的批评家,他们“试图建立一些合理的方案,一份历史示意图”,从而将新艺术放入其中。“就这样,”他总结道,“他们就能在历史发生的时候正确地追踪历史。”在同一本书中,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区分了《艺术论坛》式的批评和典型的法国“美女语言”式的写作,“诗人会为艺术家撰写充满感情的目录序言”。她说,发表在《艺术论坛》上的批评文章要归功于英美新批评,这种批评“涉及到一种文本分析,在这种分析中,你要对你面前的文本作出陈述,这些陈述必须是可证实的。你无需介绍关于艺术家的传记或者历史,它实际上仅限于页面上的内容,因此任何读者完全有能力查看你对该作品的评价”。克劳斯说,除了格林伯格,她对西德尼·詹尼斯(Sidney Janis)、托马斯·赫斯(Thomas Hess)、多尔·阿什顿(Dore Ashton)和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等用英语写作的艺术批评家的“观点的模糊性和不可实证性感到非常沮丧”,他们所写的任何内容都没有让她感到是“确凿的、可以证实的”。同样,弗里德也提到赫斯和其他人“所有那些夸张的写作”(Fustian,一个非常尖锐的词,通常用来形容羊毛织物,不仅意味着夸张和膨胀,而且因此也毫无价值)。科普兰斯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伦敦唯一有趣的批评家是“劳伦斯·阿莱塞(Lawrence Alloway)与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他们就超现实主义的重要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罗伯特·罗森布鲁姆(Robert Rosenblum)在《艺术论坛》上总结了这一情况,他回顾了马克斯·科兹洛夫(Max Kozloff)撰写的一篇题为“威尼斯艺术与佛罗伦萨批评”(1967年12月)的文章。“我喜欢这个标题,”罗森布鲁姆回忆说,因为“它指出了《艺术论坛》经典写作的一个问题,即它是佛罗伦萨风格的,它是知识分子那种干巴巴的,从来没有真正符合观看艺术的那种感官愉悦感”。撇开罗森布鲁姆的特殊观点不谈(他的写作在这些术语中是出了名的纯粹),他用佛罗伦萨风格和威尼斯风格的比喻是准确的:《艺术论坛》以及晚些时候的《十月》杂志,代表了艺术批评是严谨精确的写作,是对各种各样浮夸写作的反对。
所有这些都是“严肃的批评”将意味着所有的基础。自1976年以来,它还体现在《十月》杂志,以及托马斯·克劳(Thomas Crow)、托马斯·麦克维利(Thomas McEvilley)以及许多其他作者在不同场合撰写的论文作为例证。要求回归到严肃的、多层面的和严谨的批评,要归功于《艺术论坛》及其后继者所提供的批评模式。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我们有必要问一下:重新唤起那些特定的承诺感、可验证性和知性主义是否有意义?在我看来,唯一站得住脚的答案是,这样的价值观不再适合21世纪初的艺术。在《艺术论坛》的讨论中,智力劳动、困难和挑战的隐喻反复出现,从格林伯格开始:当作品是枯燥的、坚硬的、顽固的、不可分割的……时候,作品就是好的。很难想象这些价值观是如何被转换到当下的,即使它们是,也很难想象它们在现在还能如何使用。
6.批评应该成为对判断的反思,而不是对判断的炫耀。这就是罗莎琳·克劳斯在1971年提出的观点,并且在1985年又再次提出。主要是在学术写作中,批评在接受史和制度批判中付诸实践。如果你把艺术世界想象成一个由制度和权力关系构成的矩阵,那么像“质量”或“价值”这样的词就没有直接的意义:它们是由艺术界的分工所决定的,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制作,这目的包括学术权力和市场价值。如果你对接受史感兴趣,那么艺术界的硬仗就成了历史趣味的对象。你会想知道产生对“质量”或“价值”这样的词感兴趣的历史上下文,而你的兴趣将是纯粹的历史,甚至是语言学的——你对结果的投入不会比昆虫学家观察一个蟻族与另一个蚁族之间的斗争更多。即使是制度批评所提供的解释也会受到接受史的影响:制度批评的理念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有自己的历史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它对“质量”或“价值”等词的解释将有分量,但在它之前、之后或之外,它们就没有分量了。
制度批评和接受史所面临的问题是当下。我们生活在其中并作出判断。当我们评判当代艺术时,我们会采用我们相信的概念,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评判。对于一个实践接受史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这样的批评家会敏锐地意识到,当下还没有概念诞生。用来判断艺术的概念必须有它们自己的历史,一旦这些历史变得显而易见,就不可能像它们曾经所要求的那些批评家们全心全意地去相信这些概念。如果像格林伯格这样的人物已经远远退居过去,以至于他的论述成为历史分析的对象,那就意味着当代艺术中发挥作用的概念与他已经完全无关。如果它们不是——如果格林伯格对“扁平”“抽象”“庸俗”和“前卫”等词的感觉仍在当下回响——那么对当代艺术的评价就会变得非常成问题。毕竟,怎么可能用那些不再可信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标准来评判一件当下的作品呢?当所有的概念都属于过去的批评家时,批评就变成了编年史,而判断变成了对过去判断的沉思。当下沉浸于历史之中,并最终被历史所淹没。
这些都是艺术批评的难点,我已经尽量阐明了它们。据我所知,像布洛赫(Buhloh)这样的批评家,他们进行制度批评和接受史的实践,并不认为对日常判断的交汇和中立的立场是有问题的:像每个人一样,布洛赫在遇到新作品时就作出评判,他把老作品理解为他们那个时代对话的产物。作为给艺术批评开的处方,转向对判断的反思一直是这个“病的解决(方案)”(illresolved),尤其是当它的目标是取代艺术批评的时候。(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