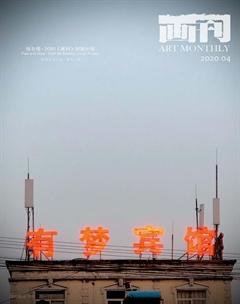谁是持摄影机的人(中)
按:自新千年以降,“影像”作为媒体艺术的基本样式,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最主流的表现形态之一。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其自身亦形成了一部模糊的非线性历史,而这部历史因为其羸弱的发展轨迹和驳杂的血缘谱系,使得许多词源概念、语言逻辑、资料史实、陈述文体等都缺乏翔实性与可考性。
“映验场”(EX-CINEMA)作为一个意象性的专栏名词,穿越了从电影(Film)到录像(Video)、从新媒体(New Media)到动态影像(Moving Images)一系列历史语汇,以穷究于理、正本清源为栏目的既定目标,以达成一次媒体考古学的文本预演。(曹恺)
打开维尔托夫的“电影眼”
在刘呐鸥的电影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对理论的迷恋——阅读、研究、翻译、写作。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他甚至创办了一份名为《现代电影》(Modern Screen)的月刊,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一系列电影理论文章——《论取材:我们需要纯粹电影作者》《电影节奏简论》《现代表情美造型》《开麦拉机构——位置角度机能论》等等。日本学者三泽真美惠是近年来重要的刘呐鸥研究专家,根据她的考证,刘呐鸥早在20年代中期留学日本之际,就已经开始了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关注,这些关注主要来自日本学术期刊的日文转译资讯,而这个时期,正好是“蒙太奇”(Montage)理论诞生之初,被日本学术界引入后风行一时,得此契机,使刘呐鸥几乎同步知晓了当时那些具有先锋色彩的西方电影理论。
从蒙昧、开化到成型,电影语言在20世纪早期突变式急剧发育,主要得益于苏联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S e r g e i M. Eisenstein)的“蒙太奇”理论。“蒙太奇”揭秘了人类运动视觉的内在逻辑,使得画面元素得以通过电影语法过滤,归置整合成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电影。在此基础上,另一位苏联电影大师维尔托夫(Dziga Vertov)提出了“电影眼”(Kino-Eye)理论,强调主观意识对摄影机的控制,竭力推崇纪录电影,而排除所有被他称为新“大众鸦片”的虚构电影。
从理论到实践,维尔托夫都在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证明“电影眼”的价值,并由此拍摄了一系列堪称样板的电影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29年推出的实验性纪录片《持摄影机的人》。该纪录片使用了当时所能涉及到的所有复杂的画面剪辑技术——多重曝光、升降格、冻结帧、跳接、多画面分切、倾斜荷兰角、超大特写、轨道推移、倒转连续镜头、定格动画以及一种独特的自我反射图式(a Self-reflexive Style)——把推轨镜头呈现的荷兰角画面分切为左右镜像。在这部作品中,维尔托夫把“蒙太奇”的语言实验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并独创了许多新的剪辑技术。
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早期电影的黄金时代,电影处在一个自由而肆意的勃发阶段。在好莱坞商业电影的影响之余,苏联的左翼艺术电影以及蒙太奇电影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比如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就曾在上海一些重要影剧院上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理论和相关电影如《电影眼》《持摄影机的人》《热情:顿巴斯交响曲》等也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维尔托夫的理论与作品,引起了刘呐鸥的极大兴趣,他为此撰写了《俄法的影戏理论》(1930年)和《影片艺术论》(1932年)这两篇研究维尔托夫的文章,其中他把“Kino-Eye”译作为“影戏眼”,并以他自己的理解阐述了维尔托夫的理论:“影戏眼是具有快速度性、显微镜性和其他一切科学的特性和能力的一个比人们的肉眼更完全的眼。它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能,能够钻入壳里透视一切微隐。一切现象均得被它解体、分析、解释,而重新组成一个与主题有关系的作品……”
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理论完全是建立在打开摄影机取景器的观看角度上的理论,对此,刘呐鸥深刻地认识到,“影戏眼只靠着个摄影机用着总括的组织法,由森罗万象中,提出最有个性合目的东西,而把他们归入最视觉的节律和形式中去。”在這样的情况下,直接通过摄影机来观看并通过“开麦拉”的方式验证自己的这种观看,对刘呐鸥而言,是一种更为真切地反向实证式地研究理论的方法。
作为一位电影人,尤其是作为一位电影编剧与导演,刘呐鸥与摄影机的距离似乎应该很近。但是,如果切实了解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工业“片场”的状况,就可以知道,作为一项分工极其精细的行业,编剧、导演与摄影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工作差异——编剧几乎是连拍摄现场都无须抵达的;而导演除却在预演阶段可以间或观看取景器,基本上是通过分镜头脚本来控制摄影画面;而摄影部门也仅仅只有摄影师本人才能控制唯一的取景器——在实时的电子监视器诞生之前,摄影师本身就是掌机员,他才是影像画面的实际掌控者。所以,刘呐鸥虽然作为一个电影编剧和导演,但距离直接观察“电影眼”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对刘呐鸥而言,只有身体力行地去亲自掌握摄影机,才能取得最终的影像话语权。而且,以肉身之眼透过机械之眼来观察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既是一种新奇而充满冒险乐趣的事情,也是借此参照既往的银幕观看经验和文字理论,来验证“电影眼”存在感的最好办法。
拉片与读片
媒体艺术考古从方法论上而言,大致有两个方向可供切入:其一是信息研究,是媒体所提供的虚拟信息,包括图像(静态的与动态的)与声音,以及内嵌的文字信息;其二是物态研究,指媒体本身的物理性存在,比如胶片(含胶片盒、卷轴等)、录像带(含外盒、封套、标贴)、光碟、硬盘等。
但是,基于现有条件,目前一般研究者仅仅可以接触到《持摄影机的男人》的数字化影像,而无法触及到原版胶片本身。而对胶片的影像数字化过程,并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百分之一百的还原。目前可以知道的信息是,林建享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恢复了影片原貌”,所以《持摄影机的男人》的数字影像文件,并非百分之百的复原,这其中含有一定百分比的原型损耗,虽然这仅仅是来自一种推断。
因为缺乏对影像附着媒介的第一手原始样态的物理认知,所以,图像细读成为了发掘研究的一种必要方法。从粗略地拉片,一直到逐段逐格地读片与细究,通过推演、假想、代入、关联、比对等多种方式,寻找其中内在的逻辑关系。
黑白无声默片《持摄影机的男人》全片由“人间卷”“东京卷”“风景卷”“广州卷”“游行卷”5个章节组成,共计片长约46分钟。
“人间卷”时长13分钟,拍摄地点是在台南新营,内容主要是刘呐鸥的家庭生活,以儿童与妇女为主,休闲、饮食、游戏、漫步、闲聊,所摄场景基本都是在“耀舍娘宅”周边;有一场是刘呐鸥坐上人力车到新营火车站上火车出行,包括一个完整的火车进站的镜头,一直到火车徐徐开走。本卷有一特别的章节,记录了台湾新竹湖口书画家叶汉卿在画案前作画的过程。
“东京卷”时长不到12分钟,描绘的是东京景观。开卷即展示了一组假日休闲的画面:公园湖泊里的荡桨游船,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随后是一段作者参与小型双翼飞机“高崎”号飞行的历程,拍摄了飞机的滑行与起飞,以及在飞机上鸟瞰的航拍;接着,镜头回到城市景观主体,包括市内繁华的街景,以及郊外的山涧、溪流和瀑布;最后以一个夜景画面为结尾。
“风景卷”时长5分钟,拍摄了东北——当时的伪满洲国的奉天(今辽宁沈阳)与新京(今吉林长春)的名胜古迹。有一对青年男女反复出现在片中,使得本卷旅游花絮的特色得到加强。后半部分拍摄了一艘轮船离开热闹港口的情形,通过海面与天空的空镜头过渡,出现椰树林剪影,回到台湾的农田与果园风光。最后是一组台南“耀舍娘宅”建筑的局部近景与全景。
“广州卷”时长11分钟,全片具有浓郁的南粤色彩。本卷可以分为三个段落,先是一组轮船甲板上的镜头,几位时髦男女(有作者本人在内)的各种摆拍;接着是作者家人在广州各处名胜漫步行走游览,以及古建筑的空镜头;第三段是非常特别的一段,拍摄了粤军操练的场景,包括了军车、装甲车、步兵、炮兵、检阅台、行走的士兵队列,以及前来观看的市民人潮。
“游行卷”时长4分钟,拍的是作者家乡台南庙会的巡游盛况,有旌幡、花船、舞狮、踩高跷、和式舞蹈等,呈现了当地特色的民俗文化。其文化主体是汉文化与台湾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的结合,部分涉及到日本的殖民文化。
《持摄影机的男人》全片的拍摄地点,包括了当时的几个城市,分别是台南、东京、奉天与新京、广州。因为这几个城市的纬度差异较大,所以无法根据片中人物的衣着来判定拍摄的时间顺序,只能大致依照片中四季风景变化,判断这部作品的素材拍摄周期至少在半年以上。
字幕考:作为一种推断方法
从最初的拉片开始,随意性的影像镜头和碎片化的影像结构就充斥了我的全部感知,非常让人怀疑,《持摄影机的男人》究竟是否算是一部已经完成的电影作品,或者它仅仅是一堆未及清理的素材。值得庆幸的是,字幕的存在形态,证明了《持摄影机的男人》是一部已经剪辑完成的作品,其中透漏的制作信息,亦是对该片系统考证的一个重要依据。
全片仅“人间卷”和“风景卷”保留了完整的字幕,由片首字幕、卷首字幕、段落字幕切分,结构相对清晰。字幕基本语言为日文——日文汉字与假名。片首字幕为日文“‘カメラを持ッ男作品”与英文“Film By‘The Man Who Has Camera”,标明了全片名称。
之后是卷首字幕。“人间卷”之名来自该卷首字幕“人间の卷,一人一场”,“风景卷”之名被写作“风景の卷”。其余三卷皆为纯影像,其卷名应当是后来的修复者依据其内容所命名的。
在“人间卷”中,有一版特别插入的字幕——“叶汉卿先生挥毫”,这个稍显突兀的段落拍摄了一位书画家叶汉卿的作画场景。
“风景卷”标明地点的整屏字幕:“奉天”“北陵”“新京公園”“ヤマトホテルにて”。“奉天”,即沈阳;“北陵”,即清昭陵,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墓,位于沈阳北部;“新京”即长春,当时伪满洲国的“首都”,依据我的初步考证,“新京公园”极可能是在1933年刚修造完成的新京大同公园;“ヤマトホテルにて”可以翻译为“在大和酒店”,那么,“大和酒店”是什么呢?影片中显示了俯拍的一处人群密集的岸边码头,可以推断拍摄机位大致是在一艘邮轮甲板上;紧随此后的一组海景和天空的空镜头画面,可以加持这一推断——这可能是一艘名为“大和”号的邮轮。
全部字幕皆为毛笔手写,深底反白字,独幅满画。按照当时的历史状况,电影胶片字幕最简单的制作方式有两种:其一,是把文字书写在纸面上,用定焦直接拍摄之后,再洗印剪接;其二,是用物理方式(锐器擦划)或化学方式(溶剂药水)直接书写在胶片上,再做显影拷贝。考虑到9.5毫米胶片的尺寸不便于第二种方式的实施,再依据影像观测,可以大致断定刘呐鸥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但他在做拷贝时直接使用了负片,呈现了反白字的效果。
至于刘呐鸥是如何洗印、剪接该片的整个后期制作过程,已经无法考证;该片是否还有其他拷贝存在,也无从知晓。但根据一般逻辑分析,因为百代系统独特的9.5毫米格式,刘呐鸥很难利用上海电影工业的洗印后制工程为自己服务,更多的可能是直接交由百代公司在东亚的后制工坊委托冲洗,或由其他个体专业人士手工冲洗影印——也不能完全排除刘本人亲自动手,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
虽然现存的胶片经历了霉变损坏到修复还原的过程,但是从目前所能呈现的影像质量上来看,即便是胶片本身完好无损,其冲印工艺手段也是相当有限的,各种黑白默片时代流行的后制技术在片中使用十分有限——譬如,所有的镜头之间的转场,没有一个画面是叠印过渡和划像过渡,也没有一个淡入淡出的起始和终场,都是最简单的切断和硬接。据此,基本可以判断出刘呐鸥在后制上或许只有一台最基本的胶片剪接机。
假想的“开麦拉”行程
依据目前我所能触及到的资料,尤其是通过对影像文本的细读与深究,我以假想的方式大致還原了刘呐鸥摄制全片的行程。这一假想过程所依据的历史逻辑完全是一种现在时态的推断,或许并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犹如对未知案件的主体描摹,有相当多向壁虚造的成分,许多缺失的空白也被临时填充而一一纳入。
大约在1933年前后,刘呐鸥开始了他的“开麦拉”行程。先是他在上海通过日常阅读的日文报纸广告,知晓了“百代宝贝”9.5毫米摄影机的销售信息,再通过查阅相关的法文书刊上刊载的资讯,并咨询上海电影界的专业摄影师后,认定这是符合他“开麦拉”理想的一部机器。虽然价格不菲,但他还是亲赴日本东京,一次性购得了全套“百代宝贝”摄影与放映设备。
拿到摄影机后,刘呐鸥迫不及待地拧上发条、打开取景器,拍摄了东京繁华的街景。因为是第一次拍摄,所以还无法做到平稳持机,意外地拍摄出了“荷兰角”的倾斜画面。之后数日,他满怀新奇地拍摄了他与妻儿家人的日常出行:郊游、划船、荡秋千、逛动物园等。还特别记录了一次乘坐“高崎”号小型双翼飞机的旅游经历,并冒险完成了航拍。
离开东京,刘呐鸥乘船抵达中国东北——当时为伪满洲国所统治。他先后去了当时东北最大的城市奉天,以及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在奉天,他游览了北陵等许多当地名胜古迹;在新京,他去了刚落成的大同公园。之后,刘呐鸥乘坐了一艘可能叫“大和”号的邮轮回到了台湾,沿途拍摄了壮丽的海上日落。
在台南新营的“耀舍娘宅”家中,刘呐鸥拍摄了许多家人的日常生活的画面:饮食、午睡、玩耍,尤其是他喜欢的那一群年幼的孩子。期间,刘呐鸥短途出行一次台北,他拍摄了这个出行过程:乘坐人力车抵达新营火车站,火车进站后,他把摄影机交给其他人,拍摄了他自己上车后在车窗内挥手道别。另外某次,刘呐鸥去拜访了新竹湖口书画家叶汉卿,记录了他两次作画过程。又恰逢台南庙会,刘呐鸥站在路边,拍摄了一次盛装游行的全景画面。
之后,刘呐鸥携同他几乎整个大家族去广州旅行。在出海的邮轮甲板上,刘呐鸥拍摄了许多家人和朋友的合影,抓拍了女眷们瞬间的音容笑貌。这时,刘呐鸥已经使用了一个阶段“百代宝贝”摄影机,对拍摄技巧有了切身感受,摄影技巧也愈加纯熟,他已经能够熟练地使用抓拍技巧,拍摄人物的大特写表情。在广州,刘呐鸥还意外地邂逅了一次粤军检阅,他把这个大场面拍摄记录了下来。
最后,或许就如前文所猜想的那样,刘呐鸥在东京完成了洗印,拍摄并制作了日文字幕——按照历史逻辑推演,刘呐鸥也有可能是在上海完成洗印,但我更倾向于他是在东京委托洗印的,主要是考虑到9.5毫米胶片的特殊规格,并非一般电影洗印厂可以批量完成。除了手工冲洗,更为便捷的方式还是直接交由销售商所属的洗印服务代劳,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京更符合这样的条件。
在片中,刘呐鸥本人不止一次地被摄入画面,说明拍摄者并非完全是刘呐鸥一人,至少还有另一人也担当了少部分摄影工作,而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刘呐鸥的某位家人。除了“游行卷”之外,刘呐鸥的家人反复出现在其他各卷当中,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刘呐鸥之妻黄素贞(1904-1984年)——也是他的嫡亲姨表姐,其余大致可以辨析的还有刘呐鸥的母亲陈恨——一位裹着小脚的妇人、其妹刘琼瑛与妹婿叶廷珪、其弟刘樱津与弟媳杨蓝菊。在全片出现了许多刘氏家族的幼儿,依据史料分析,其中有刘呐鸥和黄素贞的四个儿女:5岁的长女刘频姎、3岁的长子刘江怀(后以刘呐明为笔名)、2岁的次子刘航诗、刚出生不久的次女刘玉都,另外还有刘樱津与杨蓝菊的四个女儿。根据其他研究者的辨识,唯一比较明确认定的是“人间卷”中回望镜头的那个小女孩,是刘呐鸥的侄女刘光玲。
由此可见,该片最有可能的第二掌机者,应该是其弟刘樱津,在1933年他刚24岁。如果刘呐鸥需要一位摄影助理,那么刘樱津从学识到能力来看,都是不二人选。可以说,刘呐鸥的家人伴随了他这次“开麦拉”旅程的始终,而且,他们不但是片中的人物主体,也是影片拍摄的重要参与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