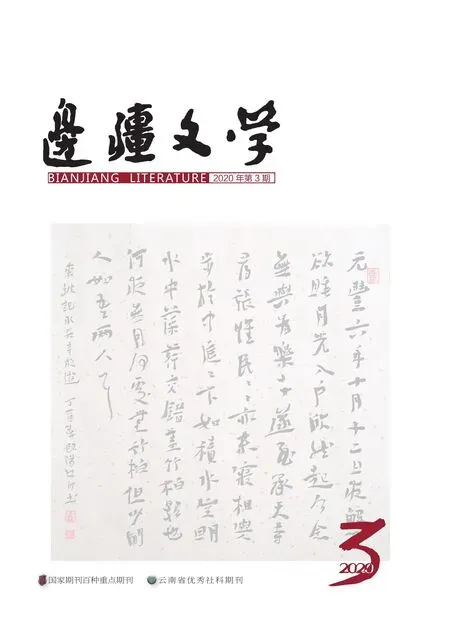大风吹过辽阔北方[散文]
安宁
一
昨晚纷纷扬扬的雪,一早起来,就淡若无痕。似乎阳光在深沉的夜里,张开巨大的斗篷,将所有遗落在人间的雪花,都收入囊中。除了楼下荒芜的小花园里,零星点缀的白,或者芜杂的枝杈间,残留的冰冻的雪,大地上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世界静寂无声,有人轻咳着从窗前经过,随即便消失在清冷的虚空中。
这是一年中的第一天,四季的起始。天空蓝得耀眼,没有风。一切都是静悄悄的。偶有鞭炮声响,但并不长久,似乎怕惊动了什么。
在窗台上,看到一只西瓜虫。它早已死掉,身体干枯,轻轻一碰,就会碎掉。或许,是它的灵魂先行厌倦了躯壳,于是便在某个秋天的黄昏,神秘地消失掉了。我能想象它生命最后的时刻,从某个潮湿阴暗的角落,沿着一束梦幻般射入房间的光,慢慢爬到窗边。它在那里,被巨大冰冷的玻璃挡住。它在绝望中,看过北疆深蓝的天空,壮阔的落日,皎洁的月亮,和自由飞翔的鸟儿。它隔着窗户,深情凝视了整个的夏天,最终,在某个寒潮袭来的孤独的夜晚,放逐了自己,只留下微微皱缩的躯壳,向世人呈示着临别前它曾有过的痛苦的挣扎。
春天即将苏醒,不知去年离去的小虫的灵魂,会不会探头进来,看一眼自己曾经的躯壳?
二
过去常常抱怨天寒地冻,雨雪交加,而今却深深眷恋这些自然中的事物。犹记去年四月,已是春暖花开的北京,忽然降下一场大雪,于是跟朋友欣然去了郊外。虽是一个经营比较粗糙的农家山庄,但因了这一场雪,园子里陡然有了生气。孩子们撒欢似地踏雪奔跑,大人们抱着江米棍,老鼠一样咯吱咯吱嚼着。喜鹊在古老的杨树间跳来跳去。两只大鹅高扬着细长的脖颈,在潮湿的草地上,优雅地来回踱着。一只驴子站在门边,发出一声声寂寞苍凉的鸣叫。空气清冷干净,新鲜的氧气洗涤着人们被雾霾裹挟了一个月的胸肺。我的双手冻得有些发僵,但在泥泞的路上小心翼翼行走的时候,却有童年时一群人缩着脖子,拢着袖口,在零星炸响的鞭炮声中,走街串巷的快乐。于是忍不住起了童心,跳上秋千,抓住冰冷的锁链,闭上眼睛,任由朋友推着,朝半空中飞去。
常常想,如果一觉醒来,能够回到童年,该有多好。那时日月洁净,繁星满天,自然中的一切,都散发着让人迷醉的气息。我站在庭院里,并不知道二三十年后,能够清晰地在夜晚辨出北斗七星,酣畅地饮用大地上流淌的河水,仰头看到大片的云朵从天空上飘过,并在没有雾霾只有雾霭缭绕的天地间悠然散步,原来是自然赐予我们人类的幸福。
以前见了人聊天气,是打哈哈,是没话找话说,是尬聊。现在聊天气,是真枪实弹地聊,是愤愤不平地聊,是感慨万千地聊。
今天在市区拍到的照片,蓝得让人觉得好像活在一个孤独的星球上。因为这份动人的蓝,我内心无比柔软。但不知为什么,车越接近郊区,天空越发浑浊。滴滴司机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听了我的疑惑,一声叹息,说:“你难道不知道吗?有两个污染企业,就在呼和浩特郊区,一个是制药厂,一个是味精厂,还都是你们山东人投资的,十多年了,每次刮风,都能闻到一股浓郁的臭味。有一次出城,途经武川,我在高处俯视整个城市,觉得像裹了一层密不透风的塑料薄膜,让人喘不过气来,也不知道人们都守着城市干什么?要不是农村医疗不方便,我早就搬走了。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两年呼和浩特还是有许多变化的,关停了不少小厂子,植树造林和沙漠绿化的效果也不错,否则,哪有你刚刚看到的市区的蓝天?”
忽然想起课上训练学生的观察能力,不止一个学生提及,秋天时潮涌一样大片大片的云朵,好像从人间消失了,许久都不曾再见。学生们知识欠缺,不知那是因冬季天气干燥,缺乏湿气,不能形成云所致。但他们在这一学期,表情由明亮渐趋忧郁,却让我意识到,天空、气候、环境这些原本与我们遥远的词汇,却因人类不知收敛的破坏,正像一日三餐一样,进入我们的日常聊天。就连我没有文化的父母,在提及村里某个人得了癌症去世的时候,都会惶恐不安地胡思乱想,并一再向我追问:你说,跟空气和地下水变坏,有没有关系?
滴滴司机初中毕业,临下车前,却说了一句让我内心震动的话:人啊,怎么就想不通这个理儿呢?你怎么样糟蹋老天爷,老天爷就怎么样加倍地报复你……
三
早晨一拉开窗帘,见窗外一片耀眼的白,地上竟然已经覆了厚厚的雪!而半空中,雪正以大如席的气势,万马奔腾般飞向大地。
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二场雪,恰好在情人节。年前的那一场,好像有些仓促的开场白,只在地上薄薄洒了一层,就消失不见。这期间南方接连下了好几场雪,北疆大地却迟迟不见雪来,不免让人着急。尤其,春天马上来临,只有一场雪的冬天,怎么能算是冬天呢?
女儿阿尔姗娜比我还要渴望这一场雪。上次我们怀着满腔的浪漫,盛了一杯雪,放进冰箱冷冻层,想着夏天的时候,拿出来尝一口冬天的雪。结果,却被不知情的爱人当成垃圾丢掉了。于是我许诺阿尔姗娜,等再下雪的时候,我一定为她盛满满一大杯新的,藏进冰箱。
果然,阿尔姗娜一醒来,就兴奋地朝我喊叫:妈妈,快带我去盛雪!
一出门,见小区里的孩子们早已堆出一个笑嘻嘻的雪人,一个小女孩还将自己的手套戴在雪人细长瘦削的树枝手臂上,又写下“请勿触摸”四个大字,挂在雪人胸前。就连门口宠物店的中年女人,也童心忽起,聚拢了门口台阶上的雪,一边快乐地哼着歌,一边兴致勃勃地堆着小巧的雪人。
阿尔姗娜更是兴奋到恨不能在雪地里打几个滚。她吃了一口又一口的雪,还不停地让我也舔一口。
雪好甜呀,妈妈!她伸出粉红的舌尖,一边舔着车上的积雪,一边朝我欢快地喊叫。
我仰头拍下雪花浩荡下落的视频,而后忍不住朝着天空大喊:我——爱——你——
阿尔姗娜也学了我的样子,抬头发出稚嫩的呼唤:我——爱——你——
而雪,则以愈发雄浑的气势,不停地下落,下落……
四
在飞机上,我倚窗看了许久的云。
看云的时候,我真想变成其中的一朵,飘荡在浩瀚的太空,不与任何的一朵发生碰撞,更不与热闹的人间烟火发生关联。我只是我自己,包裹在万千耀眼的霞光中。风来了也不动,雨落了也不走,没有什么,能够让我心生波澜。
天空中一定还有一个人类永远不能抵达的神秘城堡,飞机之下是苍茫雪原般的无边大地,那绵延八千里的雪原,让人很想种下亿万朵火红的玫瑰。即便那里是荒芜的,也可以做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在上面自由地打滚,跳跃,奔跑,呼喊,发出丛林野兽般的吼叫。
再远一些,还有黛青色的群山,连绵起伏,永无休止。一条金色的游龙,贯穿南北,在远山上纵横驰骋。山脚下金碧辉煌的宫殿,肃穆威严,熠熠闪光。童话里的怪兽,则在巨大的廊柱间,忽隐忽现,自由奔走。宫殿的左侧,是蓊郁繁茂的森林,成千上万的鸟儿呼啦啦飞过上空,洒下无数粒饱满的种子。
这个红尘之上寂静阔大的世界,没有喧哗的人类,却又如此有序地运转。上帝之光,照亮了一切。而人类,只能透过飞机封闭的舷窗,看一眼这永远无法征服的世界。
我把一颗心丢在云朵里,将沉重的肉身,安放在尘世。我知道未来的某一天,其实并不会太过久远,不过是短短的四五十年过后,我将丢弃腐朽的肉身,重新回到这浩荡的天空之城。
五
二月末的成都,已是春天,但出门走走,湿冷的天气,并不比北方暖和多少。
找了一辆小黄车骑行一段时间,手便有些冰凉。但白玉兰却早已在街头巷尾,热烈地绽放开了。簇新的叶子犹如一盏一盏空灵的灯,点亮了沿街的树。人家的屋顶上,明亮的迎春花瀑布般倾泻而下,又在半空里带着惊讶,忽然间止了步。银杏树尚未发芽,但空荡荡的枝头,却已有了一抹隐约的绿意,在悄然流淌。山茶花在人家店铺的门口,安静吐露着芬芳,如果俯身去嗅,那香气会让人一时间失了魂般,呆立半天。沿着护城河生长的菖蒲,最是旺盛,遍地铺排开来,它们冷硬的叶子,犹如剑戟,高高地刺向半空。
南方的美,在这时节,不可言说。氧气被充沛的绿意一遍遍洗涤,吸入肺腑,让人心醉。北方的大道上,此刻依然荒凉开阔,南方却行人如织,慢慢热闹起来。但这种热闹,不是夏天挥汗如雨的稠密,是恰到好处的暖和轻。走在路上的人们,闲庭散步般地,安静踱着步。巷子里的猫猫狗狗,顽皮地一路小跑着,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茂密的毛发里,散发着春天热烈的气息。
难得今天见到阳光,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喝茶或者去晒太阳。因为没有暖气,南方人对于阳光的热爱,北方人大约不能理解。但凡一出点太阳,大家就开心得好像中了百万彩票,呼朋引伴,赏花看水,轰轰烈烈,好不热闹。
南方似乎永远都是树木繁茂、生命旺盛的样子。阳光一出,每片叶子都近乎透明,每个角落,也瞬间闪烁光芒。就在一片浓密的树丛中,我还看到几只小松鼠,衔着捡来的松果,欢快地在大树间跳跃奔走,那光亮的毛发,在风中熠熠闪光,犹如柔软的绸缎。行人纷纷驻足,仰头注视着它们,眼睛里含着笑,好像这几只可爱的精灵,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使者。
再走几步,又见一百年古树,竟被几株清秀挺拔的松柏,密不透风地团团围住,犹如相亲相爱的家人。道家讲,道法自然,大道无为,或许,像草木一样吸纳天地精华,自由自在地活着,也是人类至高的生命境界。
六
三月,在北疆大地上,柳树枝头已是一片鹅黄。河流破冰而出,发出古老深沉的声响。大风撞击着泥土,唤醒沉睡中的昆虫。就连大地深处蛰伏的树根,也在春天湿润的气息中,轻轻抖动了一下。于是,整个北方便苏醒了。
随后一场大雪,犹如最后的哀愁,浩浩荡荡降落人间。它短暂到犹如惊鸿一瞥,当我洗漱完毕,走出家门,阳光已经从深蓝的高空上洒落下来。好像片刻之前经历的,只是一场虚无缥缈的幻觉。这遍洒蒙古高原的强烈的光,让天地瞬间光芒闪烁,璀璨斑斓。风席卷着大片大片的云朵,将它们吹成嘶吼的烈马,腾跃的猛兽,繁茂的森林,壮美的山川,或者舒缓的河流。于是北疆的天空上,便有气象万千、荡气回肠之美。
校园里飘荡着沁人心脾的花香。一路走过去,看到香气袭人的丁香,白的粉的,正用热烈浓郁的香气,吸引着年轻视线的关注。一个男孩嗅着花香,情不自禁地念起戴望舒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他前面沿丁香花路行走着的,是两个温柔小巧的女孩。她们大约听见了男孩的朗诵,扭头看他一眼,而后轻声笑了起来。
相比起来,榆叶梅的香气就淡远羞涩得多,需低头用力去嗅,香气才会丝丝缕缕地从花蕊中徐徐飘入鼻腔。一阵风吹过,榆叶梅粉色的花瓣纷纷扬扬洒落人的脚下,那样娇嫩柔美的粉色,总让人不忍心踩下去,于是便满怀着怜惜,绕路而行,却又忍不住回头张望,希望它们不要被人踩入泥土里去。
上课前的十分钟,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风景。窗外的桃李湖静寂幽深,一树桃花犹如含羞少女,粉红娇嫩,俏皮地探出湖心小岛,在水中映下婀娜倒影。柳树已生出鹅黄新叶,微风吹过,在水面划出细细涟漪。一对情侣牵手在湖边散步,女孩时不时仰头,看天上悠然的云朵。阳光洒落下来,晒得人心暖融融的,好像有一只猫,正温柔地靠在人的手边,不停蹭着乖巧的脑袋。
远处的草坪上,绿色的绸缎尚未完全蔓延开来,只在阳光充沛的地方,这里一汪,那里一团,犹如不疾不徐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以北疆的缓慢速度,从南方开来。草坪上的迎春,开得无比灿烂,一丛一丛,是校园里最耀眼的明黄。麻雀们从蓄满生机的树梢上呼啦啦落下,啄食一阵草籽,又呼啦啦飞过半空,停在遒劲高大的法桐上。
操场上传来打球的欢快声响,还有进球时热烈的喊叫。那声音如此的年轻,又那样的蓬勃,满溢着青春的激情。
我在这样的叫喊声里,开始上课。
课上,在学生中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查:假如给你一片森林,你会用来做什么?
有的说要建一个房子,住在那里,直到终老。
有的说要卖掉,而且只要给钱,对方买了做什么,他一概不管。
有的说要在树上建一个小木屋,像动物一样栖息其中。
有的说要建旅游度假村,大挣一笔。
有的说要将森林砍掉,建高楼大厦出售。
有的说不知道要做什么。
只有两个学生,说,什么也不做,就让森林保持原貌。
我有些哀伤,为已经成人的学生,却依然无法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类想要抵达最为理想的生活,也即诗意地栖息在这片大地上,没有森林,草原,河流,山川,我们也将失去所有诗意的源泉;犹如大树没有了泥土,飞鸟失去了天空,鱼儿离开了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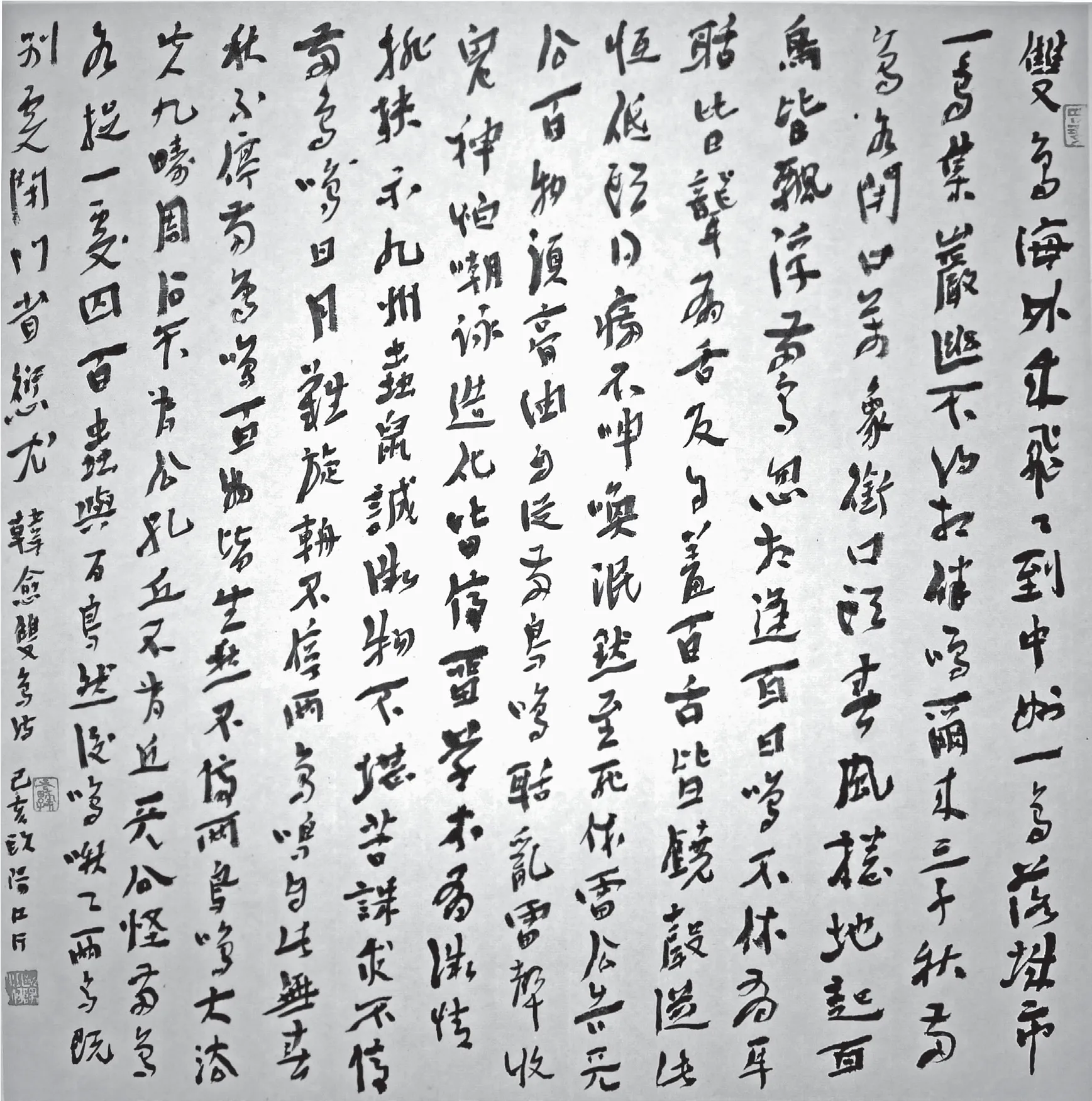
欧阳江河 书法
七
天忽然就热了起来。
可是在房间里坐着,却凉飕飕的。靠窗读书,我常常穿了毛衣,还要外加厚的外套,才能坐得住。阳光遍洒北国大地,就连云朵,都似乎怕热,消失得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边缘。杨絮漫天飞舞,并借人喘气的间隙,争先恐后地朝鼻腔里跑。空气一时间变得拥堵稠密起来。
花朵开得有些不太耐烦,懒洋洋地在阳光里站着;若是有点荫凉,它们大约全都会跑过去躲上片刻。还好有风,但这会北疆的风也是暖的,粘稠的。人走在路上,总希望下一场雨,将杨絮从空气里全部过滤掉,只留湿润的气息,供人呼吸。
虽然无雨,但天空还是一览无余的蓝。只是远远的天边上氤氲着热气,那热气在阳光的照射下,不停地晃动着,好像炉中跳跃的火焰,在不息地燃烧。
一夜之间,北疆的春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夏天,正马不停蹄地赶来。
给阿尔姗娜卧室的墙上,安了一面穿衣镜,安装师傅走后,房间里便立刻安静下来。
阿妈在厨房里擦擦洗洗,偶尔传来一两声咳嗽。一只鸟站在窗外洒满阳光的榆树上,朝着天空发出一阵空寂的鸣叫。那叫声大约震动了簇拥的云朵,于是我一转身的功夫,窗前便换了另外的一簇。它们看上去比之前的更飘逸了一些,犹如并蒂的金银花,在那无尽的洁净的空里,无限地延伸下去。似乎,它们已经失去了形体,只留下空灵的魂魄,以圣洁的白,漂浮在苍茫宇宙之中。
我沉浸在无人打扰的寂静之中,并忽然间意识到,这样美好的片刻,才是我一直寻求的永恒之美。它无关房子的大小,无关外人的评判,无关虚荣和攀比,无关嫉妒和算计。它只与我内心的宁静有关。犹如一条河,不管多少人曾经为它驻足,它都只向着远方永不停息地流去。没有哀愁,也无喜乐。是无尽的永恒的空。
我因这片刻的寂静,心中涌起幸福。
去近郊,在一大片花期已过、刚刚结出小巧果实的桃树林里,忽然看到一只野猫,昂首挺胸地走在两排桃树中间的空地上。它的毛发在树隙间漏下的阳光里,闪烁着光华。这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桃林,犹如它的王国,一排排桃树则是庄严肃穆的士兵方阵。风吹过桃林,树叶哗啦作响,犹如一首舒缓的奏鸣曲。而野猫就那样孤傲地走着,不关心尘世的喧哗,不关心马路上呼啸而过的车辆,不关心猎物,也不关心明天。那一刻,它高贵的灵魂里,流淌着一条自由奔放又野性不羁的河流。
午后,一场大雨清洁了整个的天地。大青山在雨雾中氤氲着,犹如浮在飘渺半空中的虚幻城堡。远远近近的树木,在湿漉漉的空气中,满含着诗意与哀愁,静默无声。
我问开车的司机,大青山的青色,到底是怎样的色泽?答曰:青色是介于蓝色和黑色之间的颜色。我注视着窗外,忽然很想化成一抹深沉的青色,融入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
傍晚,雨依然纷纷扬扬地落着,伴随着轰隆轰隆的雷声,似乎在为夏天敲响战鼓。夜幕中的城市,在雨中变得愈发的清寂。空气中飘荡着花朵的香气。有人打伞在道旁慢慢走着,并不着急。雨水打湿了女孩的裙脚,路灯投下昏黄的光线,女孩的影子,便落在青灰色的砖地上,有惹人怜爱的瘦。
忽然想起午后站在窗边,跟朋友一起看雨。雨水敲打着窗户,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整个城市都安静地沐浴在雨中。车马的喧嚣被雨水过滤后,也淡远下去,似乎声音来自遥远的天边,那里正涌动着厚重的乌云,这是北疆辽阔的天空,每一片云朵,都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我跟朋友边注视着变幻不定的云朵,边细细碎碎地说着闲话。这北疆壮阔辽远的天空,让我内心忽然充满了哀愁。人的一生中,要修多少年,才能遇到一个跟你说一会闲话的人,或者一起看云的人,一起听雨的人,一起乘船的人,一起打伞的人呢?
这样美好的一起看云听雨的片刻,稍纵即逝。而一旦逝去,便成为我们心中的永恒。
我爱这让我心生哀愁的飘雨的初夏。
八
早起一拉开窗帘,就见窗外世界末日般漫天沙尘飞舞。而伴随着沙尘暴的严重雾霾,则让世界呈现出一种绝望的毒气室般的黄褐色。一出门,风便吹来满嘴的沙尘。行人皆带着口罩,急匆匆地在风里走着。虽是白昼,却如黄昏。仿佛某个地方,会有一股剧烈的黑风,裹挟着妖魔忽然降临。
这是今年的第二次沙尘暴。好在内蒙古几乎每日都有猎猎大风,于是临近正午的时候,沙尘暴和雾霾便被刮得无影无踪,天空重现大片大片飞翔的云朵。站在窗前看了一会,感觉整个人都深深地陷在柔软的包裹之中。从手指到脚趾,都是空的,仿佛这沉重的肉身并不存在,我只是一个空的灵魂,躯壳被遗忘在人间。但我并不关心,犹如一只从未关心过自己外壳的蝉。
下课后,我坐在校园的小树林里,抬头看天。
天上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阳光洒在一株年轻的白桦树上,将每片新生的叶子瞬间照亮,于是整棵树便在圣洁的光里,随风发出亲密的私语。
芍药尚在含苞,红色粉色白色的花朵,羞涩地隐匿在叶片中,只等某一天,被鸟叫声惊醒。洋槐树有着惊人的生命力,它们的根基伸展到哪儿,哪儿就很快长出一株茂盛的槐树。它们隐居地下的根系,也一定遒劲发达,即便有人斩断了其中的一段,也会从断裂处,迅速长出新的生命。
一株过了花期的桃树,在白桦树的对面,静默无声地站着。几只喜鹊飞来,蹲踞在枝干上,许久都没有离去,仿佛在耐心等待一只瓢虫爬过枝头。蜜蜂有些孤单,绕着四周嗡嗡盘旋一阵,便掉头飞往附近一棵正在枯萎的丁香。火炬树高高擎起红色的果穗,以入侵者的姿态,向其他树木昭示着自己的所向披靡。在九月来临之前,它们的叶片是温和的绿色,一旦嗅到秋天的气息,狂热的火焰立刻照亮脚下每一寸土地。
我坐在石凳上,将视线从火炬树上慢慢收回,转向半空中两株枝干温柔触碰在一起的梨树。它们是从一个根系上生出的分支,在此后漫长的时光中,它们也一定这样依偎在大地上,根缠绕着根,枝干环拥着枝干,树叶亲吻着树叶。风穿越茂密的树林,发出美妙犹如天籁般细微的声响。
一棵梨树与另一棵梨树在舞蹈,我注视着风中雀跃的枝叶,忽然这样想。这是爱情的舞蹈,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在拥挤的丛林之中,它们忘记了尘世间的一切喧哗,指尖触碰着指尖,身体缠绕着身体,唇舌啮咬着唇舌。风从肌肤上滑过,一只鸟儿惊起,尖叫着冲上云霄。这是性爱的舞蹈,树木,花朵,昆虫,鸟兽,皆在这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中,静寂无声。
九
今天呼啸的大风,吹出大片大片抒情的云朵,天空宛若仙境,无数金色的光线穿越云朵的缝隙,洒在辽阔的大地上。风掠过树梢,穿过高楼,奔出街巷,又一路越过沙漠和戈壁,森林与草原,最后,从气象万千的云朵中席卷而过。
我坐在窗前,看着对面高大的柳树在风中狂舞,忽然想起昨天在校园里,看到的一株占据了大半个草坪的奇特的柳树。确切地说,那是三株柳树,只不过它们的根基是从一个母体中生出。每一株柳树,都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住。它们几乎成了这一片草坪上唯一的主人。其中的一株,在一场风暴中被吹倒在地,粗壮的枝干便紧贴着地面向前顽强地生长。它就这样匍匐在地上,枝繁叶茂地度过了很多很多年。没有人能够说出这株大树是哪一年植下的,反正学校还没有建成的时候,它就已经根深蒂固地盘踞在这里,成为一方霸主。以至于人们敬畏于自然的威严,小心翼翼地在其中一个倒地的粗壮枝干下,撑起一根木头,让它靠近地面的身体,能够时时有风自由地穿过。
前往大巴山的朋友,微信上发来照片。那里的天空,也像此刻的北疆,浪漫舒展的云朵,铺满了广袤的天空。大巴山上层峦叠嶂,茂密蓊郁,绿色犹如河流,在山间肆意流淌,无休无止。有好奇的云朵下到凡间,在半山腰缭绕盘旋,于是那里便似有了仙人,让人神往。我对朋友说:等你老了,就定居山中吧,将你一生风云和爱情传奇,都交给后人言说,你只“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朋友哈哈大笑,回说:当然如此!
而另一个朋友,则发来小花园里空荡荡的鸟巢。两只斑鸠曾经在那里生活,并抚育了它们的孩子。当那只小小的斑鸠学会飞翔之后,它们一家三口便永远地消失了。我看着风中闪烁的葡萄藤蔓,和藤蔓中安静栖息的鸟巢,耳畔似乎又回旋起斑鸠的叫声。那叫声与布谷鸟如此地相似,“布谷,布谷”,一声一声,响彻无边的大地。
虽然大风,但午后还是带阿尔姗娜去了附近的“森林”。这是我偶然间发现的一片居于市区的清静之地,属于林业局的树木繁育中心,但对外免费开放。林区面积很大,慢慢逛完每一片树林,至少需要两三个小时。树木茂盛粗壮,一看即知,此片林区已有很多年的历史。遍地都是漂亮的松球,野草四处蔓延,不知名的鸟儿在枝头雀跃啁啾。因林区已形成良好的自然生态,树木可以独立生长,无需人工浇灌,于是过去修好的水泥沟渠,就废弃掉了,成为老旧但却别致的风景,人行走其中,恍若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下。
阿尔姗娜像一只重返山林的鸟儿,在人烟稀少的树林里快乐地奔跑。她时而因发现了三株环拥的大树,兴奋地指给我看。时而捡起隐藏在层层松针下的鸟雀的羽毛,欣喜地玩耍。时而四处捡拾杨絮,并细心地摘去上面的杂草,将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入兜里。时而又采下一朵蒲公英,噗地一声,将它们全部吹走。时而又叫喊着,让我看草丛里蹁跹飞舞的蝴蝶,风中疯狂起舞的大树,天空上自由舒展的云朵。甚至一只蚂蚁,一片蜘蛛网,一朵米粒大小的花,一根枯死的树干,被风刮断的树枝,都让阿尔姗娜发出惊呼,和由衷的赞叹!
这片林场,不知是没有太多宣传的缘故,还是城市里的人们早已忘记了自然的美好,以至于一路只看到六七个人在林中散步。不过这反而让我欣喜,仿佛这片森林独属于我和阿尔姗娜。我真想仔细地看清每一株树木,记住它们深沉的双眸,记住枯死的树干上秘密一样隐匿的木耳,它们是大树的双耳,代替死去的树木,重新倾听世间的风声雨声。没有一株树木是相同的,每一棵大树,都是一片汪洋。它们世代栖息于此,自成一个无人打扰的静寂王国。而我和阿尔姗娜,不过是恰好从这里路过。
我们只带走了遗落在地上的松球、杨絮、羽毛和松针。阿尔姗娜试图采走一片树叶,我阻止了她:这样我们下次再来,你就能看到它依然生长在这里。我这样告诉阿尔姗娜。
十
八月一到,呼伦贝尔草原便进入了秋天。男人们一边在院子里忙着检修打草机,一边四处打听今年谁家的草场更好。黄昏还没有来,草尖上就浮起了露水。庭院里站上片刻,湿漉漉的凉意便化作清幽的小蛇,沿着脚踝冷飕飕地向上爬去。暮色中沿伊敏河走上一会,会偶遇一两只孤独的飞鸟,在河岸上空久久地盘旋。风沿着枯黄的草原吹来,吹得人心起了苍凉的褶皱。奶牛们拖着膨胀的乳房,蹚过冰凉的河水,列队朝家中走去。小镇上人烟稀少,偶尔有男孩驾驶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街而过。
蜂拥而来的游客犹如溃散的军队,迅速地撤离,被无数双眼睛和照相机遍览过后的草原,重新归属于牧民。于是打草的机器,便代替了人的双脚和车轮,在大地上日夜劳作。一捆捆草仰躺在大地上,注视着深蓝的天空,那里依然有夏日残留的云朵,在无拘无束地游荡。再过一个多月,大雪就会来临,夏日所有的喧哗,都将被封存进茫茫无边的雪原。
相比起热烈的夏天,我更喜欢蒙古高原上的秋天。劲烈的大风吹去枝头的绿色,大地重现寂静孤独的面容。收割完毕的土地上,泥土裸露,秸秆零落,放眼望去,一片荒凉。接下来的半年,塞外将被大雪层层裹挟,一一冰冻。生命隐匿,大地荒芜。也只有此时,蒙古高原才向真正懂得它的世代栖息于此的人们,展现最为凌厉也最为诗意哀愁的一面。
想起去年的秋天,我前往鄂尔多斯高原,徒步在沙漠中行走。大风席卷着云朵,吹过浩瀚无垠的沙漠,并在这条汹涌澎湃的大河上,画出春天般的绚烂花朵。秋天的沙漠腹地,犹如浩荡的海洋,是另外一种壮阔的美。细腻的沙子恍若遍洒人间的金子,在高原的阳光下熠熠闪光。天地间满目耀眼的金黄,除此之外,便是与沙漠遥遥接壤的宝蓝。风呼啸着吹过来,卷起漫天黄沙,人裹挟其中,渺小犹如尘埃。只有低头在沙漠中行走的骆驼,会用温暖的驼峰,向人传递着可以慰藉漫长旅途的温度。它们长长的影子,在黄沙中缓缓地向前移动,不疾不徐,枯燥却又有无限沉稳的力。没有起伏的平静喘息,伴随着声声驼铃,在永无尽头的单调色泽中,一下一下撞击着人心。
没有什么生命,能够比这存在了亿万年的洪荒大地,更加的永恒。即便在二连浩特的恐龙家园,那些长达40 米重达上百吨的庞然大物,它们曾经在蒙古高原上栖息繁衍,奔跑飞翔,可是最终,也在这里彻底地绝灭。只有永无休止的大风,带着亘古的威严,从凛冽的寒冬出发,向着万物复苏的春天,浩浩荡荡,长驱直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