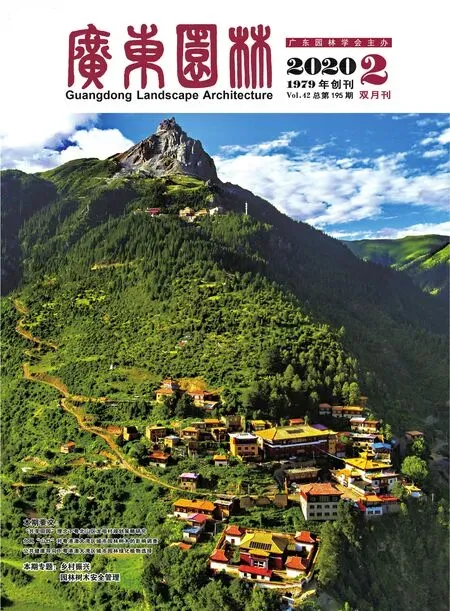风景园林学视野下的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研究*
高凯 陈虹羽 张榕珊
GAO Kai,CHEN Hong-yu,ZHANG Rong-shan
乡土景观(Vernacular Landscape)是在土著居民为满足生存、生产、生活的需要,与自然协同演进、动态适应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地表形态,是其宗教信仰、文化内涵、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投影和折射。作为当地居民适应独特自然环境的有形证据和智慧积累,乡土景观不仅是解读其文化的档案库,更启迪着未来。在美丽中国、生态文明、乡村振兴、国土空间规划等时代背景下,乡土景观在风景园林学等人居环境学科中的研究价值愈发凸显。
1 风景园林学科体系下的乡土景观研究
1.1 乡土景观研究的现状及多学科属性
乡土景观的研究始自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西方国家[1]。美国文化地理学家J. B. Jackson 于1984年出版的《Discovering Vernacular Landscape》[2]是西方国家关于乡土景观的重要论著。20 世纪90 年代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将“历史乡土景观(Historic Bernacular Landscape)”定义为文化景观类型之一,架构了乡土景观和文化景观之间的联系。此后,西方国家对乡土景观的类型和范畴的研究更加广泛,研究视角更加丰富,涉及文化、自然、人类学、历史、农业、美学等[3~4]。
我国学者对乡土景观的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涉及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人居环境学科等多种学科[5]。“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的人居环境学科群是研究乡土景观的中坚力量,少数民族乡土景观是相关研究的重要领域。尽管各学科的研究视角、侧重点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对乡土景观具有共识性认知:乡土景观与“政治景 观(Political Landscape)”相对立,是自下而上的、没有设计师的,反映贴近生活的日常性和贴近乡土社会的草根性,具有无名的、自发的、土著的、动态的、乡野的等特征属性[6]。
1.2 风景园林学视角下的乡土景观研究现状
新时代背景下风景园林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研究范畴由城市延伸至乡村,乡土景观逐渐成为风景园林学科研究的前沿领域。钱云[1]将乡土景观划分为乡村景观、本土/地域景观、寻常/非正式景观3 大类,从风景园林学科角度提出了乡土景观研究的初步框架。刘通等[7]以风景园林学视角提出乡土景观的研究内容应包括自然景观、农业景观和聚落景观,乡土景观在区域、国土景观尺度下的研究应以农业景观为核心。侯晓蕾、郭巍[8~10]从风景园林学的角度,以圩田为研究对象,将乡土景观理解为自然系统、农田系统(含水利系统)、聚落系统的层状叠加体系,带动了一系列相关研究[11~12]。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风景园林学视角下的乡土景观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乡土景观的类型划分和辨识角度;二是以自然系统、农田系统、聚落系统等子系统层状叠加的方式研究乡土景观。
1.3 风景园林学科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新框架
2011 年3 月,“风 景 园 林 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被新增为一级学科。《增设风景园林学为一级学科论证报告》[13]前瞻性地指出:“风景园林学是规划、设计、保护、建设和管理户外自然和人工境域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户外空间营造,根本使命是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云南省元阳县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为例,将乡土景观的研究归位于风景园林学科体系,提出以风景园林学科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使命为基础的乡土景观研究新框架,突破上述两类研究视角的桎梏,提供乡土景观研究的新思路:首先,根据核心内容研究乡土景观的空间组成结构;其次,根据根本使命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方式,并实现对乡土景观空间组成结构的形成机制的深入解读;最后,基于上述乡土景观研究成果,探讨利用风景园林学相关理论展开规划与应用、保护与管理等方面后续研究内容的可行性及实现途径(图1)。
2 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的空间组成结构
阿者科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红河南岸的哀牢山山区,海拔高度约1 880 m,共64户479 人,是保存完整、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哈尼族村寨,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的空间组成结构是当地居民户外空间营造的直接结果,紧扣风景园林学的核心内容。乡土景观的空间组成结构是人与自然关系及互动方式的作用结果和外在呈现,对其进行研究是对乡土景观的系统性解读,是乡土景观研究的基础和核心。
联系风景园林学科人与自然之间的作用关系及作用结果的核心内涵[14],依据人与自然关系紧密程度的圈层特点,将乡土景观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3 个层面进行深入研究。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在宏观层面满足的是当地居民“安生立业”的生存需要,表现为自然山水环境、森林景观、农业景观和聚落空间等;在中观层面营造的是当地居民“安身立命”的空间场所,以村寨聚落空间为核心;而在微观层面体现的是一种“心安理得”的归属感,以建筑及庭院空间为主要内容。
2.1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的乡土景观是土著居民以生存为第一要义,寻求一种能够“安生立业”的理想景观模式的结果,空间组成结构主要表现为在以生存为目的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及其在局部国土空间的排列组合。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在宏观层面上的生产空间主要由水梯田组成,生活空间集中于阿者科村寨,而生态空间主要由高山森林构成(图2)。
在邻接关系及空间布局方面,基于山地自然环境的约束条件,在宏观层面上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的生态空间居上,生活空间居中,生产空间居下,沿山势邻接排列(图3)。水系作为重要而特殊的要素,源自高山森林,流经村寨,汇入梯田,串联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形成“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整体空间结构特征。
2.2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的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以村寨为核心,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交通空间和广场等公共空间的集合。村寨是阿者科哈尼族人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最为集中的场所,是人化自然程度最高的核心,其面积虽然不大,但控制整个乡土景观的形成、演进和格局。阿者科的“寨头”寨神林联系村寨之上的高山森林,“寨尾”磨秋场关联村寨之下的梯田,两者控制村寨的空间结构逻辑秩序,是极具哈尼族文化意义的重要空间节点,也是村寨生活空间与生态、生产空间之间的过渡。
阿者科村寨依山而建,顺势而为,沿山势自上而下整体呈现不规则的倒三角形(图4)。村寨内的道路连同水系构成村寨的骨架,统制村寨的整体格局,控制村寨的演变。村寨内的1 组主要街道垂直于等高线,沿山势自上至下贯穿整个村寨;次要道路连接主要道路和民居等建筑,沿等高线分布,形成网状、不规则的道路系统。阿者科的街道主要由石材等铺装,蜿蜒曲折、步移景异,空间开合变化丰富。街道在地势平坦处拓展为带状或块状的广场,是举办长街宴等集体活动的场所。这类广场连同村寨空旷处,结合周边功能建筑,形成了村寨内的主要公共开放空间,具有文化、娱乐、交往等多重作用。村寨内的6 个水井是重要功能设施和聚集场所,紧密关联村民的日常生活,制约周边建筑的分布,影响村寨布局,是村寨的重要空间节点。阿者科村寨的传统民居形式为蘑菇房,受地形条件、道路、水系、水井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呈不规则式分布,构成村寨的肌理和景观风貌。
2.3 微观层面
蘑菇房因其四坡草顶、脊短坡陡,状如蘑菇而得名,其墙体由生土砖砌成,屋顶由茅草覆盖,极具哈尼族传统风格,并且冬暖夏凉、低碳环保。阿者科的蘑菇房多为3 层,底层喂养牲畜及放置杂物,顶层储粮,中间楼层居住,具备哈尼族人居家生活的全部功能需求(图5)。由于生活习惯、地形限制、经济条件等因素,村民仅在蘑菇房周边放置少量杂物,多数无院落空间,更无私家园林。以晾晒稻谷为主要功能的晒台及各类屋顶平台,可供居民聊天、抽水烟、纺织、清洗等,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庭院的功能。阿者科村内的2 个水碾房是重要水力基础设施,具备一定公共空间属性,其主要依据水系特征和使用需求设置,建筑形式同样为蘑菇房。
3 阿者科哈尼族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互动方式
阿者科哈尼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互动方式是其乡土景观空间组成结构的成因机制和内在基石,紧密联系风景园林学科的根本使命。
3.1 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
哈尼族信奉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的原始宗教信仰,认为自然界的万物皆有神灵司管,如天神、地神、山神、水神、寨神等[15]。基于此,哈尼族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决定了其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此外,哈尼族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还举行众多祭祀活动,如祭山、祭田、祭树、祭庄稼、祭寨神等。这些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祈求神灵的护佑,另一方面也从精神层面巩固、传承哈尼族村民崇拜、尊重自然的信仰,坚定其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
3.2 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
哈尼族是古羌人南迁的分支。阿者科等哈尼族先人因战乱、瘟疫、资源枯竭等原因,被迫迁徙至红河南岸的哀牢山地区。该地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偏远闭塞、山高林密、沟谷纵横,耕地资源极为匮乏。在自然资源极端约束的条件下,阿者科哈尼族人根据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依照水源丰沛的自然资源特点和迁徙过程中掌握的水稻Oryza sativa 种植耕作技术,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以梯田稻作为主的与自然的互动方式:顺应当地的立体气候特征,在气候适宜的山腰建寨,将其下适应稻谷生长的低海拔山坡开垦为水稻梯田,并将水源由高山森林引至村寨、流入梯田,形成了以生存、生产、生活为目的的宏观层面的阿者科哈尼族乡土景观格局。同时,阿者科村还根据其民族文化体系和社会组织结构,制定了严格的森林保护、水资源管理利用等乡规民约,发展了精密复杂的山地农耕技术体系,利用而非穷竭自然。这些保障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和良性互动,也保证了阿者科村在大山深处依靠自然的馈赠而生存发展。
阿者科村寨的选址位于山腰地带的“凹塘”之处,是对特定自然环境的理性选择,既蕴含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又是生态智慧的折射。根据既定选址,阿者科村民圈定寨神林,建造蘑菇房,修建磨秋场,聚居生活,发展村寨:根据复杂的地形条件,建设、发展村寨的道路系统,以满足出行及运输稻谷等生产活动的需要;依据地势条件,结合零星空间,设置空地及广场等文娱活动场所和交往空间,以增强村寨凝聚力;规划、管理进入村寨的水系,并依据水系、地势等设置水井,建造水碾房,以持久有序地利用水资源,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最终,经过哈尼族人长期不断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阿者科村寨逐渐形成、完善,中观层面乡土景观的组成结构和景观格局确立。
为适应当地雨水较多的自然环境特点,阿者科哈尼族人将传统的邛笼系土掌房增加四面坡茅草屋顶,创设了匠心独具、风貌独特的蘑菇房建筑类型,构建了微观层面乡土景观的核心。
4 新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对后续内容的基础作用
4.1 规划与应用
风景园林学科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新框架,以全面、深入研究乡土景观空间组成结构为基础,这为风景园林学科发挥学科优势,科学合理划定生态红线,划分主体功能区,参与“三区三线”等国土空间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基础。
异彩纷呈的乡土景观是“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载体,是风景园林审美和规划设计的灵感来源。新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聚焦空间组成结构及其形成机制,冲破物质与文化、有形与无形的对立藩篱。基于此,在风景园林和城市设计等方面提炼并应用乡土景观的“物”“事”“意”[16],是避免“千城一面”“千园一面”的有效途径。
4.2 管理与保护
乡土景观是人与自然长期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结果,多属于有机演进类的文化景观(Organically Evolved Landscape)。风景园林学科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是对研究区内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及相互作用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这与文化景观的核心内容高度重叠。文化景观是风景园林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理论体系相对成熟。因此,新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对后续应用文化景观的相关理论研究,及实践红河哈尼族乡土景观的管理、保护、传承、发展等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实现国土景观的“绿水青山”、建设“美丽中国”等也具有支持作用。
5 结语
乡土景观镌刻着历史的痕迹、民族的感情和文化的渊源,从精神上保障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具有文化、社会、历史和科学等丰富价值。风景园林学科是研究乡土景观最为合理的学科背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土景观领域亟待风景园林师进行的更多学术研究和工作实践。
相比于现有研究,风景园林学科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具有以下特点:1)紧扣风景园林学科的核心内容与根本使命,符合学科的领域和任务等,与学科的紧密度更高。2)不仅分析乡土景观的空间组成结构,更以人与自然关系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风景园林学视野,深层次研究其形成机制,即不仅解读“户外空间是什么样”,而且解答“户外空间是如何营造的”,与风景园林学科息息相关。3)突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架构自然与文化的桥梁。4)承认乡土景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紧密程度、干涉程度的异质性,以及以村寨等聚居空间为核心的“人化的自然”的圈层特点。5)注重乡土景观的整体性和复杂性,不禁锢于当前应用较多的垂直分层研究视角。6)在此研究框架下,宏观层面可以引入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中观和微观层面可以借鉴建筑学、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研究手段,系统性研究乡土景观,丰富风景园林学科的研究体系。综上所述,风景园林学科视野下的乡土景观研究不仅拓展乡土景观的研究视野,也有助于风景园林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