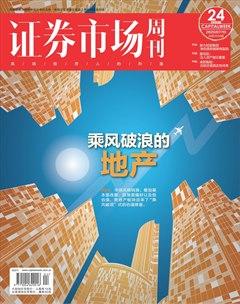宏观交易笔记:你有时光机吗?
相纪宏
很多情况下,价格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不研究资产价格形成机制,只是在一些资产价格数据表面跳跃,很可能陷入数据挖掘甚至神秘主义的误区而不自知。例如,近期的一个热门话题,如果疫情逐渐消退,或者特效疫苗研制成功,那么各类资产价格,尤其是跟宏观密切相关的债券、外汇和商品价格会如何变化?应该回归疫情之前的位置吗?
研究這个问题,我们仍然希望遵循我们习惯的宏观金融视角。在这个视角里,资金和信贷在金融体系之间流动,资金流动量而不是价格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应该把价格理解为资金流动的结果,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价格成为了资金流动的催化剂,也需要有市场结构、政策和参与者行为的共同作用。跳过市场结构、简单比较不同历史情景下的资产价格,毫无可取的逻辑。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把宏观情景的变化,简单直接地映射到相应资产价格的变化上。即便出现了特效疫苗、疫情风险已经完全可以排除、经济潜力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衡量利率、汇率等资产价格是否合理的标准,应是能否支持金融体系以比较健康、可持续的速度扩张。在国内市场,这个标准可以更加明确一些,亦即是否能满足信贷增长规模和社会融资规模并完成既定增长目标。事实上这也是政策部门的目标。观察央行的表述,我们发现央行对于信贷规模的增长和结构的变化一直是最关心的,对利率、汇率的绝对水平的关注,反而表述不多。无独有偶,将货币金融体系结构过分简化的所谓政策利率的泰勒规则,即使在完全市场化调控的欧美货币政策体系,也一直面临较大的争议。
所以,谈及6月份流动性退潮和债市调整时,我们并不认同当下比较流行的观点,亦即从疫情前的情景中划出几个关键点位并比较债市和宏观流动性的状态。在我们的分析情景里,即便疫情完全退去,政策层面仍需要维持较长时间的宽松和引导。首先,经济下行期进行的宏观调控刺激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退出。尤其是货币和流动性方面的刺激措施,一般来说,在社会需求的回升已经形成明显的结构性通胀压力之后才有退出的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也见过通胀回升之后货币政策收紧,但是很快又发现需求回升缺乏持续性而不得不二次宽松的例子,例如2001年的日本央行和2008年的欧洲央行。这往往会对政策部门尤其是中央银行的信誉形成严重的损害。当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企业大规模增加CAPEX、增加雇佣或者累积库存等典型的周期性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认为存在货币政策转向的必要性,即使是相对前期转向。更何况,当前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仍然面临扩张动力不足的问题,例如中小型银行仍然面临补充资本的压力。
那么,如何理解5月份以来的债市下跌和流动性收紧?应该来说,既有市场的因素又有政策导向的因素,但是都不应该认为是宏观环境恢复到疫情之前了。市场方面,在债市陷入流动性狂欢的时刻,几乎所有信息都被解读为政策部门大力促进流动性宽松,例如超额准备金利率的下调本来是央行降低运营成本的举措,却被解读为新型宽松政策。投机心理的堆积促使参与者们无视估值和基本面,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近期,投机心理已经消退了很多。例如,新的调控措施如再贷款利率调整等被市场以极其平淡的心理解读。政策方面,近期央行对金融风险的关注度较高,这多少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结合《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2018年以来的一贯思维,应该认识到遏制金融杠杆、控制金融风险和打通对实体经济融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对于更加重视金融服务实体的中国央行、而不是一味强调金融体系市场化运作规则的欧美央行而言,尽早关注流动性措施的副作用,本来应该是我们可以提早预料到的。
但这样可能也意味着金融系统能享受到的超额流动性有限,尤其是对习惯了固定收益或者信贷类商业模式的金融机构。这对我们最习惯的宏观金融研究模式也是一个挑战,因为由流动性促成的宏观金融策略,尤其是二级市场策略,往往构建在超额流动性在某些行业或者某些商业模式的堆积与释放上。直观上,如果社融继续因为政策刺激而保持比较高的增长,但是金融系统堆积的超额流动性有限,那么大类资产切换和市场主题切换,都可能更加频繁。
政策层面市场目前最为纠结的是政策的持续性。中美两大经济体的政策其实从2019年四季度或者更早已经开始有所调整,疫情导致政策彻底逆转。中美两国政策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着力点都在需求端,而中国的政策传统的着力点在投资端,本次虽然有不少声音希望中国能够在需求端做更多,但是从实际的经济运行体系看,中国经济支持政策最为有效率的依然是在投资端。从国内情况看,随着疫情控制手段的调整,投资端的反弹比较明显,不论是从高频的工业品的生产库存价格情况、发电量等,还是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看,投资的恢复比较明显,特别是进入5、6月份以来。此外,比较意外的是海外政策对于需求端的支持也导致我们的外需情况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如果我们客观地看目前的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价格等情况,某种意义上处于一个Goldilocks(刚刚好)状态:友好的政策环境,持续改善的增长数据、温和的价格表现,当然目前的绝对增长水平处于一个低水平位置上。从这个角度静态看,资本市场依然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之中,至少没有明显的系统风险的政策和经济基础。
这种经济状态是二季度市场趋势形成的一个基础。一个趋势的形成在一个大的运动的基础上裹挟各类物质同向涌动从而进一步加强趋势的运动方向。趋势的运动本身一方面会逐步耗散趋势的动能,同时也会逐步出现一些反方向的阻滞和干扰因子,从而结束乃至逆转趋势。本轮趋势的最大基础是流动性,最为确定的方向是增长的确定性。疫情导致的经济变化和传统经济及金融危机完全不同,传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导致的是整个经济体系统性的萎缩,从而伤及的几乎是所有经济单元,而疫情导致的经济关闭则带有强烈的结构性,流动性和结构性的经济结果的结合形成了最大的趋势。虽然我们现阶段并不认为这个趋势已经到高潮或者即将结束,但是从风险角度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什么可能会成为趋势结束的标志。
毫无疑问,本轮趋势最为重要的基础之一是政策的支持和流动性的充盈。那么什么条件下流动性充盈的条件会得到改变呢?从美国来看,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就业和增长,主要约束是通胀,而这两个边界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很少能够给政策退出提供一个充足的条件,仅有的一点窗口是2018-2019年减税之后形成一个短暂的退出希望。从中国来看,我们政策的主要目标也是增长和就业,但是多了一个结构的调整,约束的主要条件是杠杆,通胀更多时候是个阶段性的条件,这是由中国的经济和治理体系决定的。如果我们考察中国的杠杆情况,一个是中国杠杆从基础上和其他主流经济体并不具有完全可比性,中国政府拥有的资源能力是其他经济体政府不可比拟的,那么如果用传统的负债和经济总量的横向比较就有点刻舟求剑的意思了,中国杠杆最主要的负面后果是经济资源分配的失衡。因此,我们对于杠杆调整的目标更多的切入点应该在调整资源失衡上,而不是简单地压低杠杆率,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去杠杆取得了总量层面的一些成果,但是结构性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从窄义的金融体系杠杆来看,随着影子银行的治理,金融体系的复杂杠杆链条得到极大的梳理,故而,我们认为近期货币政策的一些调整更多是预防式修正而非转向。对于结构调整的目标,从增长角度看,货币政策从总量层面能够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往往也会有很多副作用,那么随着2019年以来新的税收体系的建立,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将会更加活跃。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一些传统的长期因素开始削弱或者消退,人口结构、科技进步、全球化等,短期看疫情导致的经济运行成本的上升也将持续比较长时间。但是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过去多年科技进步带来的变革继续发挥作用,比如互联网的渗透在疫情的影响下得以加速,大规模的网络效应从而降低成本是互联网的魅力之一,虽然中美之间的波折不断,但是如果我们看两国的经济和民众的沟通和多年以前已经是个本质的变化,中国领导的“一带一路”下更多欠发达经济体的进一步融入也会带来非常多的积极基础,例如东盟现在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中国的长期增长会在一个低水平平衡,并且经济结构将会进一步从投资驱动向需求带动转换。在这个大的宏观环境下,利率中枢是下移的,我们当下对于债券并不悲观,虽然也不认为空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