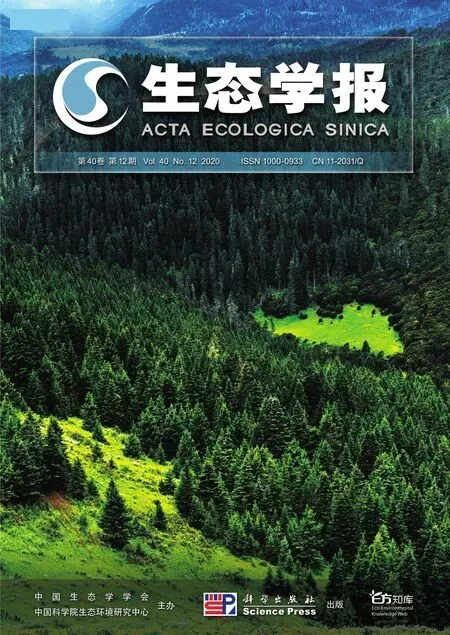三峡库区典型流域聚落变迁的土地利用效应
冉彩虹,李阳兵,2,*,梁鑫源,3
1 重庆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 重庆 401331 2 三峡库区地表过程与环境遥感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 401331 3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南京 210023
聚落变迁是人类活动的直接反应,其扩张、衰退或消失对周边用地类型有较大干扰,尤其对环境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1]。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聚落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型明显[2- 3],但山区由于受到地形、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制约,先天条件和后天经济发展与平原地区都存在较大的差异[4],因此山区聚落和周边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较为模糊[5]。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聚落扩张,使得农户生计需求产生变化[6],乡镇企业逐渐发展起来[7],从而推动了农村家庭的差异化发展[8],这种差异化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影响了土地利用变化的过程[9- 10],但聚落扩张势必会对土地利用类型造成较大的扰动,对山区农村环境和乡村振兴都有较大的影响[6]。另一方面,山区乡村劳动力的转移加速乡村聚落的衰退过程,而逐渐弱化的聚落体系反馈于乡村社区造成乡村人口的进一步析出,加剧了山区“空心村”问题,从而推动了山区土地利用的转型[11- 13];此外退耕还林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户生计安全和粮食安全都有重要影响[4]。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寻求农村生产力、土地资源等的可持续发展[14]。故探索山区聚落变迁所带来的周边用地类型变化对于山区农村土地整治、土地和生态系统等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
三峡库区由于其地理环境和三峡工程的建设,形成了一个集生态敏感区、典型移民区和农村贫困区一体的山区[15],但因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库区内聚落和土地利用发生了较大变化[16],且森林和耕地利用发生转型[17]。在这种变化趋势下,聚落的扩张或收缩是否对土地利用转型有推动作用,在土地利用转型进程中其驱动机制是否产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否会对区域内经营主体产生影响等值得深度挖掘。因此,探索库区内聚落变迁的土地利用效应及其机理,对库区社会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山区农户生计方式均有积极意义。因此,本文以库区腹地草堂溪流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三峡水库建设过程,从微观尺度着手揭示山区聚落演变特征,进而挖掘由聚落扩张或消失过程所引起的土地利用转型以及其他现象(如农户生计来源转变等),从而为库区社会经济发展,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草堂溪流域(109°35′03″—109°45′20″E,31°03′40″—31°11′06″N)位于重庆市奉节县的东北部(图1),属于长江的一级支流,河流全长33.3 km,流域面积191.5km2,共流经奉节和巫山县的22个乡镇。流域内地形起伏较大,受蓄水工程和移民工程的影响,聚落区位变化显著;且现有研究表明流域内耕地转型明显,多向以果园为主的经果林转型为主[18- 19]。基于此,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草堂溪流域为研究对象。

图1 草堂溪流域及调查点位置示意图Fig.1 Location of Caotang River Basin and survey sites
2 数据来源
2000—2018年土地利用图源自GOOGLE EARTH(分辨率为0.26m)高分影像,以及重庆市1∶5万地形图,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采用人机交互解译,划分出坡耕地、聚落、草地、有林地、灌木林地、河流、道路、撂荒地、果园、建设用地(主要是流域沿岸移民产业园区和机场)和未利用地等12种土地利用类型。并利用ENVI 5.0将划分出的土地利用类型进行精度校正,并结合实地踏勘进行抽样验证,确保精度均在90%以上。经营主体数据主要来自实体调查和政府统计资料提取。
3 研究方法
3.1 聚落类型划分指标
(1)基于ArcGIS 10.2软件生成500 m×500 m的格网,共计841个,并提取出有聚落的格网。首先,提取出2000—2018年聚落格网内消失的聚落,将其定义为消没型。其次利用扩张强度指数将其余聚落进行类型划分,扩张强度指数可体现聚落用地空间变化[20]。扩张强度指数越高则聚落空间变化越剧烈;指数越低,变化就越缓慢;当指数为负值时,表示聚落用地由扩张变为减少。公式如下:


图2 聚落类型划分Fig.2 Classification of settlement types

图3 草堂溪流域不同聚落类型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ettlement types in Caotangxi watershed
3.2 缓冲区分析
为清晰反映出聚落扩张、衰退或消失所引起的周边土地利用转型,本研究以聚落为中心,通过对不同类型聚落建立线性模型,得出聚落与土地利用类型之的间函数模型。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主体(聚落“y”)与邻近实体(土地利用类型“x”)之间相应的比值距离,同时根据二分法确定每种聚落类型的作用范围,从而确立出不同类型聚落的缓冲半径,如(表1)所示。
3.3 实地调查
奉节县草堂镇占整个草堂溪流域面积的78%以上,因此此次野外调研主要选取了流域内草堂镇产业的主要集中区域的6个乡村。主要以走访和问卷调查为主并结合奉节县和当地政府的统计资料,对农户经营主体变化进行确认(表2)。

表2 研究区经营主体变化
4 结果分析
4.1 单元格网内聚落与土地利用演变
聚落扩张或消失,对周边用地类型有较大干扰。故将研究区聚落分为4种类型,探讨由于聚落变迁所带来的聚落格网内土地利用变化(图4,5)。消没型聚落根据其消没原因可分为由于城乡经济发展带来的居民向经济状况较好区域搬迁的边缘-消没型和水库蓄水所导致的淹没-消没型。本文主要分析边缘-消没型聚落所带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变化幅度最大的为2000—2010年,随着聚落的逐渐消失,人类活动对该地带的影响逐渐减弱,耕地撂荒,聚落废弃使得森林生态空间持续扩张[21- 22]。

图4 2000—2018年不同聚落类型格网内斑块面积及数量变化Fig.4 Changes in plaque area and quantity in different settlements type grids from 2000 to 2018上图中柱状图为斑块数量占比,折线图为面积变化
衰退型聚落是流域主要聚落类型。聚落虽没有消失但面积逐年减少,耕地面积降幅明显,逐渐转化为具有一定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林草地、果园等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化,一些自发性的经营主体和政府或企业经营组织相继出现,使得大量耕地转变为具有生态和经济效益的果园,故虽聚落逐年衰退,但果园面积增幅较大。
扩张型聚落分布较为集聚,沿河流和道路呈斜“Y”字型分布,以西南部的扩张最为明显。流域西南部为草堂镇乡镇中心所在地,经济和城镇化率增幅迅速,聚落逐渐呈条带状或团块状向该区域聚拢,使得耕地逐渐收缩,转变为果园或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逐年增高。
自然增长型聚落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布于东北部地区。聚落扩张幅度较小,多沿道路两旁呈条带状分布。耕地和灌木林地都有所减少,有林地、果园等用地类型面积逐年增加。自然增长型聚落周边,以干支流交汇处为界,2000—2010年东北部地区土地利用类型以灌木林地、耕地为主;到2018年,该区域耕地收缩明显,土地生产功能下降,而大量耕地撂荒或转变为果园或林草地等土地利用类型。而在西南区域,2000—2010年主要以耕地为主要用地类型,但流域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且该区域经营主体多以政府或外来企业为主,到2018年,该区域大量耕地转为果园,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均有所提升。

图5 2000—2018年草堂溪流域空间单元内土地利用演变Fig.5 Evolution of land use in the spatial unit of Caotangxi watershed from 2000 to 2018
4.2 聚落变迁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
聚落格网内主要体现不同聚落类型周边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为深入挖掘不同聚落类型周边由于聚落动态变化所引起的土地利用转型,本研究基于ArcGIS 10.2软件进行叠置分析和3.3的缓冲区分析统计出研究区四种聚落类型变迁所引起的土地利用面积变化(图6)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图7)。
从图7可看出, 四种类型聚落周边随着聚落的扩张或衰退,土地利用类型均以耕地收缩转型,果园和林地扩张为主。扩张型聚落扩张迅速,影响距离较远,土地利用类型转移主要发生在其周边1000m范围内,2000—2010年随着聚落扩张在与聚落中心距离300m内以耕地转为果园和撂荒地为主;300—500m之间主要以耕地向林草地等类型转变,但该阶段有林地面积增幅较小,灌木林地逐渐由2000年距聚落中心500m向2010年与聚落中心距离300m处收缩,面积有所减少。2010—2018年有林地和果园面积大幅度上升,与聚落中心距离200m内以果园为主,200—400m间以有林地和果园两种地类为主;且随着聚落的扩张和耕地转型,撂荒地面积逐年上升,2018年逐渐在与聚落中心距离400m处达到最大值。

图7 草堂溪流域不同聚落类型周边土地利用转移图Fig.7 Land use transfer map of different settlement types in Caotangxi watershed
自然增长型聚落由于聚落本身面积基数较小,且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因此聚落扩张较慢,主要距聚落中心500m内,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活跃。2000—2010年随着聚落的缓慢扩张,对聚落外围土地利用类型干扰较小,故与聚落中心距离200m外有林地和灌木林地面积大幅上升,100—200m之间果园面积有所上升,但涨幅较小;2010—2018年,由于受到退耕还林政策和生态建设的影响,耕地大幅度减少,与聚落中心150m内耕地主要转变为果园,150m后转为林草地等类型,且与聚落中型距离越远,林地、撂荒地等生态完整性较高的地类面积越大。
衰退型聚落中在与聚落中心750m范围内用地类型变化明显。2000年,距聚落中心150m范围内,以耕地为主,林草地等地类主要分布在300—750 m 之间,且以灌木林地为主,有林地和果园面积较小;2000—2010年,聚落面积逐渐收缩,但聚落周边75m内仍以耕地为主,但75—150m之间逐渐转型为果园、灌木林地、有林地等地类;2010—2018年,与聚落中心150m范围内耕地逐渐被果园所取代,且与聚落中心距离越远,土地利用类型逐渐转为林草地、撂荒地等地类。
消没型聚落由于其自然区位条件较差,聚落分布较为分散,且聚落面积较小,故土地类型变化主要发生在距聚落中心250m范围内。2000年,与聚落中心距离越近,耕地面积占比越小,但聚落周边仍以耕地为主;2000—2010年随着聚落逐渐消失,周边土地利用类型逐渐转变为有林地和灌木林地等地类,且与聚落中心距离越远,生态完整性越高。
从图6可看出,聚落扩张主要源自占用周边耕地、林地等用地类型。2000—2010年,由于三峡大坝的建设,人类活动强度大,使得生态环境较为脆弱。2010—2018年,政府实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林地和灌木林地面积有所增加,同时注重经济效益的提升,流域内果园经济快速发展,到2018年果园取代耕地成为聚落周边面积占比最高的用地类型。

图6 2000—2018年草堂溪流域不同聚落类型周边用地面积变化Fig.6 Changes in land use area of different settlement types in Caotangxi watershed from 2000 to 2018
5 讨论
5.1 山区聚落变迁引起的土地利用转型效应
5.1.1 生态效应
山区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对山区生态恢复及保护有较大影响[4]。三峡库区地形条件复杂,作为典型的移民区和生态敏感区,土地利用转型无疑对库区生态恢复具有一定作用。2000—2018年草堂溪流域所表现出来的土地利用转型以耕地和森林转型为主[17],且流域整体生态状况从恶化向明显好转改善的趋势[23]。研究区不同聚落类型周边土地利用转型所带来的生态效应具有差异性(图8)。2000—2018年消没型聚落由于聚落逐渐消失,耕地和果园逐渐退化撂荒,逐渐演替为有林地、灌木林地等生态完整性高的土地利用类型。而扩张型、自然增长型和衰退型均以耕地转型为主:2000—2018年耕地逐渐减少一方面是由于三峡工程建设进程中蓄水工程和移民工程;另一方面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和长江防护林工程和研究区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森林快速扩张[24- 25],到2018年消没型聚落类型周边土地利用功能逐渐转变为生态功能,而另外三种聚落周边土地耕地生产功能虽然下降,但果园这种生产生态功能兼顾的土地利用类型发展较快,因此这三种聚落类型周边均以生产生态功能为主。这种转变趋势对于区域生态安全亦具有积极作用,草堂溪流域地形条件复杂,尤其2000—2010年之间人地活动剧烈,造成流域内生态系统脆弱,且农户为满足生计需求,陡坡开垦十分严重,土壤侵蚀严重。而这种土地利用转型的发生,使得区域生态完整性提高,保障了区域生态安全。

图8 聚落变迁的生态效应Fig.8 Ecological effects of settlements change
5.1.2 社会经济效应
宋小青在对法国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机制中发现,耕地发生转型时,农户的收入大幅度上升,且这种上升趋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反作用于土地生产功能,使得土地集约化程度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加快,从而推动了城镇化发展速度[26]。而草堂溪流域耕地的收缩和撂荒大大缩减了粮食等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这势必会对农户生计安全产生影响,故耕地利用转型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通过2010年和2018年走访农户调查发现农户生计来源不再是单一的从土地中索取。2000—2010年果园经济有所发展,除了流域内经济较为发达的西南部区域外,其余区域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2010年后奉节县开始实行“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方式,在兼顾扶持农户的同时,致力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农业企业、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故2010—2018年研究区西南部和干支流交汇处出现一系列移民生态产业园区,政府、企业产业有所发展,经营主体逐渐向政府、企业为主的经营主体转变(表2)。
5.2 聚落变迁引起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因素及启示
5.2.1 驱动因素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经济因素会成为聚落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聚落区位的变化必然导致土地利用的变化(图9)。2000—2010年4种类型聚落中造成土地利用转型的根本驱动力是劳动力的转移。消没型和衰退型聚落周边因大量劳动力往外迁移且在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质量低,耕作不方便的土地资源就会被撂荒,逐渐演替为林草地等用地类型;而扩张型和自然增长型聚落周边由于劳动力的迁入使得聚落扩张,但该时期政府颁布退耕还林政策,是造成耕地收缩,林地扩张的直接因素[25]。2010—2018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使得聚落向经济条件优越区域迁移,进而促使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故该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促使用地类型变化的直接驱动力;而该时期土地利用转型的根本原因是农户需求增加,随着农户需求增加单一的耕地种植不能满足农户日益增加的农户需求,使得果园经济逐渐发展起来。衰退型聚落周边耕地逐渐转变为果园、林地等类型;扩张型和自然增长型聚落周边土地利用类型转变较快,主要表现为耕地到果园的转变;而消没型聚落周边到2018年逐渐形成一个以林草地为主完全生态型的区域。

图9 草堂溪流域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因素及启示Fig.9 Driving factors of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in caotangxi watershed and its enlightenment
5.2.2 启示意义
研究区聚落存在多种演变类型。4种聚落类型虽然演变方向不同,但随着土地利用驱动机制的转变,果园经济逐渐成为聚落周边的支柱型产业,聚落变迁不再是驱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唯一驱动机制,山区土地利用变化进入了多样化阶段。
土地利用驱动机制的变化使得经营主体也发生相应变化。2000—2010年果园主要以农户个体经营为主,果园主要分布于聚落周边,与耕地相间分布。2010年后果园呈规模化发展,其经营主体逐渐由农户个体经营转变为政府、企业经营为主。经营主体的转变一方面促使农户生计来源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另一方面对农业集约化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提供了驱动力[27]。
随着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聚落不再是驱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唯一机制。新型经营主体代替了小农经济,山区土地利用变化进入了多样化阶段。但由于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更易于发展旅游和农业相结合的生态观光农业。如梯田景观、生态采摘等。这既可以拓宽农户就业渠道,保证农户生计安全,也对区域生态建设有积极意义。此外,还应重视农村教育投入,培养技术性人才或适宜性人才(符合当地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保障农户后顾生计来源。
6 结论
本文选择库区典型的代表性的草堂溪流域,用聚落强度扩张指数、缓冲区分析等方法,进行山区聚落变迁引起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聚落的动态变化对周边土地利用类型有着直接的影响。随着聚落的扩张,聚落周边耕地转为果园,与聚落中心较远的地区则以耕地收缩,林地扩张为主;聚落消失,周边耕地和果园面积相应减少,撂荒地、林草地等地类面积扩张,区域生态环境逐渐恢复;聚落衰退,周边耕地逐渐转变为果园,而聚落外围土地利用类型则以耕地收缩,林草地、撂荒地扩张为主。除消没型聚落周边土地利用功能由生产生态功能转为生态功能外,其余三种类型聚落周边随着聚落的扩张或衰退,周边土地利用功能由生产功能逐渐向生产生态功能转变。
2)2000—2010年劳动力转移是驱动4种类型聚落周边土地利用转型的根本原因,政府政策是土地利用转型的直接关键因素;2010—2018年社会经济因素成为土地利用转型的直接因素,该时期农户生计需求成为用地类型变化的根本驱动力。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驱动因素的转移,带动了流域内经营主体的转移主要由农户个体经营向政府、企业等他组织经营主体转变为主。对流域内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积级的推动作用。
3)山区聚落变迁使得劳动力转移驱动土地利用转型和经营主体转型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山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转型驱动机制发生转变,推动农业集约化发展进程;而农业集约化发展又作用于农户生计来源和经营主体的转变,进而影响山区聚落的扩张或衰退。二者之间相互作用,互为辅助。聚落变迁是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山区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土地利用转型是农业集约化发展、实现乡村人口回流和乡村振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