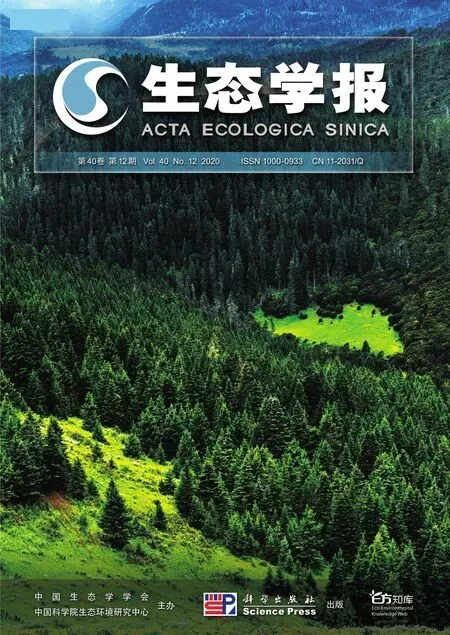全球跨界保护研究及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朱里莹,徐 姗,兰思仁,王光玉
1 福建农林大学园林学院, 福州 350002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林学院, 温哥华 V6T1Z4
跨界保护(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是跨越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国家内不同行政区划边界来实现保护目标的过程,致力于保护和维持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和文化资源的永续利用,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手段促进不同管理机构的合作管理,减少人为划定的政治边界对动植物种群分布、生态学过程和区域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1-4]。跨界保护不但是增强生态完整性,保障物种生境的有效措施,还有助于社会、文化和经济的融合与发展,提高区域管理效率,受到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的推崇,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1]。跨界保护包含了IUCN所定义的广泛的保护地类型,例如马来西亚的Lanjak Entimau Reserve(IUCN第IV类,生境和物种管理保护区)和印度尼西亚的Gunung Bentuang Dan Karimum(IUCN第II类,国家公园)共建,从自然、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开展跨界合作,成为两国开展国际林业合作的里程碑[3,5];意大利Alpi Marittime Nature Park(IUCN第V类,陆地/海洋景观保护区)与法国的Mercantour National Park(IUCN第II类,国家公园)共建,合作内容从野生动物管理、视觉认同,到在欧洲领土合作(European Grouping of Territorial Cooperation)背景下建立共同司法结构[3,6]。可见,跨界保护已经成为各类型保护地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国家公园也不例外。1932年,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Waterton Lake National Park)与美国冰川国家公园(Glacier National Park)合作成立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Waterton-Glacier International Peace Park),在二者之间建立了自然和文化连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跨界保护区[3-4,7]。
随着跨界保护理念的引入,我国也不断参与到跨界保护事业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与蒙古、俄罗斯、越南、老挝等周边国家取得共识,积极促进跨境保护区的成立,签署了《关于建立中/蒙/俄共同自然保护区的协定》、《中国西双版纳尚勇-老挝南塔南木哈联合保护区合作协议》、《中俄关于兴凯湖自然保护区协定》等双边或多边协议,推动跨界生态保护事业的发展[7]。我国仍在建设中的10个国家公园试点之一,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中俄朝3国交界地,其东部、东南部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豹地国家公园接壤,西南部隔图们江与朝鲜相邻,且跨越吉林和黑龙江2省5个县市,是跨界保护的典型示例之一[8-9]。可以预见,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与我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建设,在与境外交流中,中国将与更多周边国家开展跨界保护合作。在境内国家公园建设中,则会更多地跨越行政区划边界,形成跨界保护。然而,目前我国在跨界保护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发展均处于起步阶段[2,7]。因此,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在较短时间内从大量国外研究资料中掌握跨界保护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趋势成为这一阶段的当务之急。鉴于此,本研究基于CiteSpace文献研究量化和可视化分析工具,梳理国外跨界保护相关研究,直观呈现文献聚类情况,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全球跨界保护研究都有哪些主要方向?(2)这些研究方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3)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有哪些启示?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SCI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检索源,以“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为主题,时间跨度为1900—2019年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19年9月1日,共得到427篇英文文献及其相关信息,包含作者、摘要、关键词、来源、赞助机构及21549篇参考文献信息等内容,形成相对完整的跨界保护领域文献覆盖网络。
1.2 研究方法
作为常用的文献量化及可视化工具之一,CiteSpace可以通过数据挖掘、信息分析和科学计量,形成多元、分时、动态的文献共引分析,将某个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知识引文节点、共引聚类等进行可视化呈现,标定学科前沿和热点动向[10-12]。相对于传统的文献计量分析,CiteSpace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机器学习对庞大的数据量进行分析、分类并自动标定内容信息。除了可以分析检索到的主题相关论文,将其列入施引文献外, CiteSpace还可以分析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并将其列入被引文献。CiteSpacec认为施引文献可以代表某领域的知识前沿,被引文献则代表该领域的知识基础,并以此构建相对完整的知识网络。
本研究首先将跨界保护领域的427篇英文施引文献、21549篇被引文献,及其相关信息以TXT格式导入CiteSpace,以1年为段落对1900—2019年的时间区间进行切片,用每个时间切片内排名前20位的数据,例如排名前20位的作者、排名前20位的关键词、排名前20位的被引文献等信息,以此来生成知识网络图谱,并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呈现。其次对主要聚类的大小、同质性、主要内容等因子进行聚类整合,同时找出主要代表性施引文献与主要代表性被引文献。为了更深入地剖析各聚类所反映的具体信息,还需要结合聚类内部原文献中近似议题出现频次与主题进行相关性梳理,通过文献阅读与分析,将研究网络中的聚类进行类群划分,以此识别全球跨界保护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核心内容,对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提出建议。
2 跨界保护热点聚类与类群识别
借助CiteSpace共被引文献分析识别出12个聚类,包含446个节点,1543条连线,其聚类指标Modularity Q值为0.8064,意味着文献网络被合理地划分为松散耦合的多个聚类,Mean Sihouette值为0.8618,意味着各个聚类内部同质性较高,聚类结果较优。总体来看,跨界保护研究各引文文献节点集结为同一知识网络,网络整体较集中,共同知识基础明确,聚类之间重叠度较高,虽然涉及多学科交叉内容,但是尚处于研究核心力量凝聚阶段,未形成强势分支,呈现出典型的研究初期状态。
采用机器学习LLR(Log-likelihood ratio)文献分析常见算法对主题进行自动提取与标识,共计识别出12个聚类。在此基础上,通过原文献分析,归纳整理出12个聚类的主要内容,其中“#0北部针尾鸭(northern pintail)”的核心内容为“迁徙物种”、“#1相连海域(contiguous sea)”为“海洋空间规划”、“#2领土三会合(state-territory triad)”为“解决军事化争端”、“#3地缘政治不稳定(geopolitical instability)”为“海洋跨界倡议”、“#4金枪鱼管理(tuna management)”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5西南边界(southwestern boundary)” 为“大型食肉物种”、“#6跨界生物圈保护区(transboundary biosphere reserve)”为“社会-生态系统”、“#7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为“国际协定”、“#8干城章嘉景观(Kangchenjunga landscape)”为“保护范式转变”、“#9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delivery)” 为“保护优先次序”、“#10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 analysis)”为“制度分析”、“#11国家边界(country border)”为“食腐鸟类”(见图1)。

图1 跨界保护知识聚类Fig.1 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 knowledge clusters
根据文献分析结果,本研究将12个聚类划分为4大类群,分别代表跨界保护研究的4个主要研究方向。具体详见表1。

表1 跨界保护聚类与类群
2.1 类群G1:跨界物种
类群G1“跨界物种”的核心内容包括“迁徙物种”,“大型食肉物种”和“食腐鸟类”,分别对应聚类#0北部针尾鸭、#5西南边界和#11国家边界。从现有研究来看,跨界物种保护的挑战在于,某个保护地的保护效力,不仅取决于该保护地本身,还取决于地理距离或行政距离外的其他地块(可能位于几千公里以外,甚至另一个行政管辖区域)[13]。为了识别跨界物种移动过程中对各个保护地块的依赖程度,现有研究使用GPS定位系统全球追踪物种时空分布[14],相机摄影识别动物个体来构建物种丰度模型[15],微卫星标记计算种群模型[16]等,发现物种迁徙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大范围消失[17];大型食肉物种的日常活动范围往往超过现有单一保护地的保护规模[18];而日常在觅食区和繁育区进行长距离跨界飞行的食腐鸟类则每天都可能面临人类干扰及环境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14]。
由于活动范围广,跨界物种很难满足于现有静态的岛屿式保护地形式。而跨界物种在空间上的移动并不只是两点之间简单的直线运动,还会通过不同的路线,经停若干停留点,形成相互关联的网络。任意一个环节上的变化,包括移动廊道或者中间停留点的生境质量变化都会对跨界物种产生影响。Runge等[13]指出即使是小型连接场地的生境质量下降或者连通性丧失都将导致跨界物种数量的大幅度降低。这一观点与“木桶短板理论”相似,从最弱的保护环节推算保护网络的整体效应。相应的,在此空间网络中对某一环节进行人工增强,例如人工设立停留点,也会对跨界物种产生显著影响。欧洲卫生立法处理动物残骸的政策导致秃鹫等日常长距离活动的食腐鸟类食物量减少,造成繁殖成功率降低、死亡率增加、种群停止生长等问题,于是人工设立喂食站[19]。但是这一结果也可预见地改变了栖息地的质量,不仅对食腐鸟类个体和种群规模造成影响,也增加了喂食站附近中小型脊椎动物的捕食风险[19-20]。这是因为跨界物种除了在地理位移上形成的空间网络外,在移动的过程中还通过捕食与被捕食,能量运输和营养传递等方式动态地改变着移动路线上的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是嵌入周边生态社区的复杂的网络化生态过程。因此,Bauer和Hoye等提出从“网络化的网络”、“动态网络”和“多元网络”3层网络结构来理解物种移动的影响,认识到物种移动不仅连接两个地点,还在不同的阶段影响着位移路线中的整个生态社区,在营养关系、寄生物传播、互惠互动等方面相互作用,动态地改变着移动路线上的群落结构和生态系统功能,并以此发展跨界物种保护策略,评估各种干预措施在不同网络结构中的扩散效率[21]。综合现有研究发现,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护地并不是越大越好,或者说即使再大的保护地也很难完全匹配跨界物种的活动需求。跨界物种保护需要看到物种在移动过程中形成的地理上的网络、时间上的网络,以及不同层面作用力上的网络。因此,从静态的岛屿式保护向动态多元的网络化发展是符合跨界物种保护需求的重要趋势。
2.2 类群G2: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类群G2“社会-经济-生态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生态系统”、“制度分析”和“保护范式转变”,分别对应聚类 #4金枪鱼管理、 #6跨界生物圈保护区、 #8干城章嘉景观、 #10制度分析。跨界保护除了跨越地理边界外,还跨越行政边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态相结合的讨论,包括构建跨界保护在生态、政策、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依据[22],结合国际社会、政策的生物圈保护区合作框架[23],结合地方社区的可持续跨界景观管理等[24]。其中,跨界保护是否能与社会经济同步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从现有人口、社会和经济指标来看,边境区域的贫困问题往往更加严重[25]。跨界保护地对边境土地的占用是否会剥夺土地发展的社会经济机会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代表保护地与贫困直接相关。事实上,施行保护也可以起到降低贫困的作用,保护生态服务系统,例如提高森林集水区的产水量即有益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26-27]。不同于一般保护地,跨界保护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重点更在于对跨界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其利益相关者除了个体、群体、区域,甚至还包括不同国家,涵盖了不同层级和不同规模。由于跨界自然资源属于同一生态系统,又使得跨界双方或多方在资源共享上既具有竞争性又具有非排他性,例如根据金枪鱼的跨界和洄游性质,在某一国家管辖范围内或在公海上不加限制地开发就可能对其他区域的获取数量产生重大影响[28]。
考虑到跨界资源的复杂性、跨界区域发展机会和生态安全等问题,跨界双方或多方在广泛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合作成为跨界资源管理的重点。而跨界资源合作需要建立在理解人类社会多个层级的基础上,包括国际-国家-区域-地方-社区。从跨界保护经验来看,针对某一层级的资源共享如若出现矛盾,需要在其上一层级达成合作协议。例如针对多国在跨界渔业管理和保护上的矛盾,40多个沿海国家成立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共同协调跨界区域渔业责任和权利[28]。这种至上而下的机制优势在于对总体的把握,其不足则是容易在推行过程的基础操作层面,即社区层面受阻。与荒野保护最初的圈地式保护不同,如今世界上大多数保护地都拥有社区,尤其是人口密集区的保护地,例如印度、缅甸、南非等[29]。从保护地和社会经济的关系来看,将原有社区居民从保护地驱逐只会导致贫困加剧[30]。因此,跨界保护顺应全球保护范式的变化,从保护旗舰物种到生境和生态系统保护,向结合当地社区发展的综合性可持续保护方式转变[31]。在Sandwith等提出的9项跨界保护合作指导意见中,为了鼓励社区参与,提出要在识别和推进跨界双方或多方共同价值的基础上,争取惠利社区[3]。事实上,社区经济保障早已成为跨界保护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等在在Virunga跨界野生动物保护的研究中发现,尽管该地区在过去25年经历了内战,但是由于旅游收入的增长,以及刚果、卢旺达和乌干达3国之间跨界合作的加强,该地山地大猩猩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32]。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跨界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能否同步的问题。但是仍然需要在不同规模不同层级的跨界保护中进行验证。因此,在国际-国家-区域-地方-社区多个层级上理解实现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保护相结合的综合可持续性保护,是跨界保护研究未来不断发展的方向。
2.3 类群G3: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
类群G3“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解决军事化争端”、 “海洋跨界倡议”和“国际协定”,对应聚类#2领土三会合、#3地缘政治不稳定和#7国际法。根据环境和平假说,跨界保护一直被视为加强国家合作,减少军事化冲突的重要工具[33]。然而,受到跨界区域权力失衡、空间关系重建、法律制度不协调等问题的困扰,跨界保护是否能够如期待的那样协调多国利益[34],实现国家甚至多国区域的连接与复兴仍然受到质疑[35]。Barquet等分析了1949年到2001年包括328个共享边界的国家,发现曾经经历过军事争端且没有卷入重大致命性战争的国家更倾向于建立跨界保护地,但是和平效应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会显现[33]。这一观点为跨界保护的环境和平假说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功利性地说,虽然陆地上35%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都跨越国界[36],但是生态保护本身可能并不足以促成两个国家进行跨界保护。而解决军事化争端,维持边境稳定则为跨界保护地的存在提供了强烈的政治意愿,例如韩国多次呼吁在韩国和朝鲜的非军事区建立和平公园[37]。在双方合作意愿强烈,却存在一定分歧的情况下,引入第三方协调机构将有助于进一步预防冲突和建立合作信心,例如1997年墨西哥、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之间的中美洲大堡礁系统协议(Mesoameircan Barrier Reef System)[38]和2009年由印尼、菲律宾、东帝汶、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所罗门群岛,6国组成的珊瑚大三角协定(Coral triangle)[39]等都离不开非政府组织的协助。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教科文组织等自然保护组织对跨界区域的认定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例如1933年《关于保护自然环境中动植物的伦敦公约》要求其缔约方就相邻的受保护自然区域进行合作; 1971年《湿地公约》要求缔约国就任何跨界湿地进行协商;1979年《伯尔尼欧洲野生动物和自然生境保护公约》责成缔约国协调保护边境地区的自然生境;1982年《关于地中海特别保护区的日内瓦议定书》责成缔约国就边境保护区问题进行协商,并审查建立相应地区的可能性;1992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缔约国酌情建立一套保护区制度并相互合作等[40]。由此,跨界保护在受到生态需求、政治意愿和国际协定约束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了全球解决军事争端,寻求区域和平的重要力量。
2.4 类群G4:跨界保护决策
类群G4“跨界保护决策”主要探讨了 “海洋空间规划”和“保护优先次序”,分别对应聚类#1 相连海域和#10生态系统服务。与单一地点保护类似,跨界保护决策的本质上也是通过对未来的预测来达到相应的保护目标。为了科学判读未来趋势,例如来自全球变化的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生境丧失等,现有研究发展出了一系列预测模型,包括多尺度生态变化驱动空间数据集[41]、人类-自然耦合集成动态建模方式[42]、生态威胁地图[43]等。Pouzols等预测了2040年的全球土地使用变化将如何影响保护地的空间分布模式,并推演出了全球空间保护优先次序,发现各国优先保护区域和全球优先保护区域之间存在重大效率差距,呼吁更多国际行动的参与[44]。而国际行动则意味着更多跨界的可能。与单一地点保护不同,跨界保护的难点在于,它的保护目标因为利益相关者的增加而成倍增多。而不同保护目标所指向的保护规划,例如空间优先次序等,都可能完全不同,这大大提高了决策的难度[45]。
如何在多目标背景下,通过确定优先保护次序来引导规划布局和资金投入,实现效益最大化,是跨界保护决策关注的重点。目前主要的对策是“多目标热点”,即将多个保护目的优先区域中重叠度最高的区域作为热点,集中力量投入资源,这样可以减少投入成本,实现效益最大化[46-47]。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公平性原则,例如某个单目标突出区域不在多目标热点范围内就失去了获取各项保护资源的可能[48]。同时,也不利于在遭受局部灾难的时候分散风险[45]。而加入跨界保护的每一个国家或区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愿望、资源和机会,不能获得资源支撑,可能减少非多目标热点国家的跨界参与热情。因此,Beger等提出利用“单目标互补”补齐“多目标热点”的短板,在多个目标不能全部有效达成的非热点区域,针对单个目标采取补充措施[45]。目前来看,“多目标热点”和“单目标互补”相结合的方式既可以提高跨界双方或多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资源整合的效率,又可以根据国家偏好和具体资源特征进行利益保护,对推动跨界保护进行科学决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该设想仍然需要在多个跨界区域进行验证后才能评估其有效性。
3 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启示
随着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工作推进,行政边界与生态边界不重合所带来的困扰逐渐显现。尽管行政边界不具备生态功能,却可以通过不同的政策结构、优先次序和社会态度等来管理其管辖权内的生态系统及其所含物种。而无论是实体意义上的边境安全围栏[49],还是由政策法规形成的看不见的屏障[50],都造成了生态系统被行政边界割裂[18]。为此,跨界保护将逐渐成为我国国家公园的重要内容,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而我国跨界保护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国外跨界保护研究对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东南亚、中亚地区、 南亚地区的合作发展更为紧密,如何实现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跨界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完善、边界社区发展与居民福祉的改善等,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3.1 匹配物种保护规模,完善跨界生态系统
跨界物种保护规模与物种实际活动范围不匹配是造成跨界生态系统完整性断裂的关键。就保护规模而言,独立的国家公园即使面积再大也很难满足某些特定物种的日常活动范围。有针对性的保护行为应当根据生态完整性考虑物种的动态活动范围,确保保护规模与物种规模相一致,并寻求不同行政界限之间的优化合作方式,将保护形式由孤岛式向群落式、网络化转化。
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不应当受限于既定的人工界限,而应当跨越行政界限,包括国界、省界、市界等;跨越类型界限,包括国家公园与不同保护地类型之间;跨越层级界限,包括国家级与省、市级保护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跨界群落组合,例如加拿大落基山公园群(Canadian Rocky Mountain Parks)即包含了班夫(Banff National Park)、贾斯珀(Jasper National Park)、库特奈(Kootenay National Park)和幽鹤(Yoho National Park)4个国家公园,以及罗布森山(Mount Robson Provincial Park)、阿西尼博因山(Mount Assiniboine Provincial Park)和汉伯(Hamber Provincial Park)3个省级公园,共计7个保护地[51],跨越艾伯塔和不列颠哥伦比亚2省,保护了包括灰狼、灰熊、北美狼獾等在内的区域性跨界物种[52]。除此之外,为了维持和恢复落基山脉3200公里的生境完整性和连通性,加拿大还和美国联合提出了从南部的黄石生态系统延伸到北部的育空麦肯齐山脉的“黄石到育空地区保护倡议(Y2Y, Yellowstone to Yukon)”[53]。与之类似,我国云南与老挝、越南接壤的热带山地森林大三角洲区域,藏南与印度交界的峡谷区域,东北绵延至朝鲜、俄罗斯的长白山区域等,都具有集合不同保护地类型,寻求跨国界合作,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建立跨界国家公园的潜质。
3.2 联合双边意愿,寻求跨界社区发展
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国家公园最初设立于荒野地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优越区域往往融合了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复杂的人地关系。从国际跨界保护经验来看,国际-国家-区域-地方-社区多个层级的系统中,社区是执行力最强,也是最有可能使至上而下机制受阻的层面。因此,我国国家公园在面临跨界保护时,需要联合双边或多边社区的意愿,以达成共识。
对于跨界社区而言,界限双方或多方的传统文化、经济需求和个人福利是否得到满足,是跨界保护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传统文化涉及认知层面,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相对而言,经济需求和个人福利的变化则更为直接。因此,在国家公园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在尊重社区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共同的生态保护目标,确认不同社区对该目标的支付意愿,并且量化社区从保护中获得的利益和可能的经济机会。
除此之外,公平性也是跨界社区关注的重点。虽然跨界资源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在人类利用特性上仍然具有相似性。跨界社区双边或多边共同享用并共同承担由人类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结果,不论好坏。因此,寻求跨界社区发展就需要避免社区同质化竞争,以及可能的资源拦截。这就要求尽可能减少跨界双方在共同资源使用上的不平衡,包括收入、税收、生活成本、资源使用限制等,公平分配社区利益,保证信息渠道透明度,鼓励社区参与保护程序、决策过程和结果,建立公平正义感,保障跨界社区可持续发展。
3.3 搁置领土争议,建立跨界合作协定
在“一带一路”加强国家间全方位合作,发展区域利益和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我国与邻国建立跨国界保护关系的可能性不断攀升。仅在2007年,IUCN即识别出中国与14个邻国中的10个具有建立跨界保护地的可能与潜力[2]。然而,我国与邻国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无论是数十年前的中越战争、朝鲜战争,还是近年来的中印对峙、南海争端等,都横亘于中国与邻国之间。跨界保护国家公园的建立,可以促使双边或多边搁置争议,实现共商共建共享。
事实证明,生态保护并不足以说服跨界双方放弃土地可能的经济机会来建立保护地,但是保障边境稳定的和平愿望却可以激发建立跨界保护地的政治意愿。因此,我国在建设跨界国家公园时,需要评估对方进行跨界保护合作的意愿是否强烈,例如最高级别的政府是否介入等。利用跨界保护解决军事冲突的潜在能力,吸引更多的政治力量参与到跨界保护工作中。在广泛的框架下,创造性地建立与完善多边磋商机制,明确跨界保护中的权利和责任,将约束管理与自愿管理相结合,达成跨界保护地国际公约。
为了保障跨界双边或多边协议的有效性,除了寻求高级别的政治支持外,引入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例如非政府组织等,也是协议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1997年墨西哥、伯利兹、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中美洲大堡礁系统协议就是在缔约国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世界资源组织等大型国际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推动下签署的,并于2001年获得了世界银行的资助[39]。该项目还设立了两个跨界保护委员会来协调和管理保护地事务,包括加强体制建设、人员培训、公众意识教育和项目管理透明化等,取得了良好成效[39,54]。可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广泛的利益相关者、长期的资金投入和固定的管理机构等都是跨界国家约束自我,履行和平公约的重要保障。
3.4 科学规划,合理安排优先保护次序
确定空间保护优先次序,是国家公园规划与决策的重点。跨界保护国家公园的难点在于,不论是跨国境,还是在国境内跨越行政边界,由于不同利益驱动,不同区域的保护目标往往不同,从而导致空间规划热点的不同。事实上,即使是保护目标一致,不同学科视角形成的规划热点也往往不同,例如我国国家公园系统规划中,有学者根据生态系统完整性、生态重要性等指数识别出55个国家公园潜在区域[55],有学者根据生态地理识别出84个国家公园备选区[56]。为了平衡各方观点,全息国家公园系统规划的出台迫在眉睫。这就要求国家公园保护规划,尤其是可能涉及大量跨界保护的规划,应当首先站在更高层级的视野上对整体进行把握,例如从全球视域来理解我国国家公园保护工作,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工作与全球生态保护接轨,根据更宏观的目标来协调现有争论。根据“多目标热点”和“单目标互补”相结合的方法,在全球、国家、区域、省级、地方等不同层面通过系统性科学规划,逐级选择空间保护优先次序,设立规划方案,以获取多个尺度的支持。在全球视域下设计顶层规划,协调多目标热点,根据具体需求进行单目标补充,根据不同规模和尺度,分阶段制定国家公园保护动态适应性规划。
4 结语
目前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可以预见,跨界保护将成为国家公园发展的重要趋势。国家公园跨界保护可以通过国际或区域间的合作,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语境下最大限度地保护跨界物种与生态完整性。在国家层面上,释放友好信息,以绿色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军事争端。在地方层面上,通过打破行政边界,有效沟通各省各部门管理层级,提高资源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在社区层面上,通过理解跨界社区在资源利用上的连通性,串联并共享资源以减少社区同质化竞争,避免因资源拦截而造成的贫困。研究国外跨界保护经验,将有利于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前布局,预先制定应对策略。
从国外跨界保护研究经验来看,跨界保护经历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单一保护到融合社会、经济、生态等多维视角,从排除受益人到体现人文关怀,从军事争端不断到逐渐达成国际公约,从模糊性协议到科学定量规划的过程。我国国家公园跨界保护在跨界物种保护方面,应当积极促进与物种保护规模相匹配的跨层级跨尺度合作,完善跨界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生态系统方面,联合跨界社区意愿,采取量化并公平分配社区经济利益的方式,维护居民福祉,促进跨界社区可持续发展;在军事争端与解决途径方面,完善多边磋商机制,达成跨境国际保护公约,从生态需求、政治意愿和国际协议约束等多个方面,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在跨界保护决策方面,将多目标和单目标热点互补,科学评估保护优先次序。推动我国跨界保护研究,将有效解决国家公园发展过程中境内和境外行政边界与生态系统不匹配而产生的各项矛盾,在促进交流与合作的同时,为全球自然保护地事业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