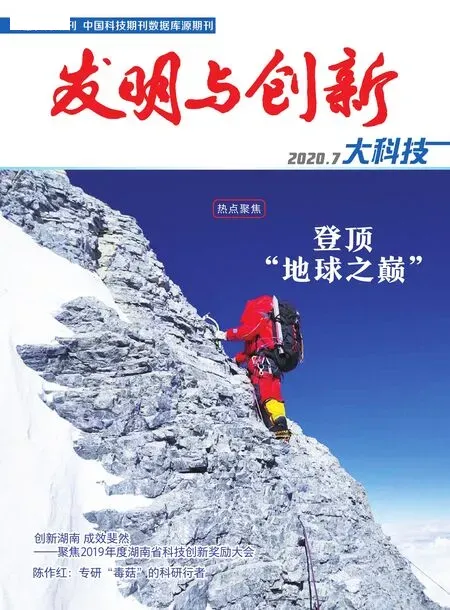陈作红:专研“毒菇”的科研行者
文/本刊记者 雷蕾 李瑚 图/受访者供图

陈作红(左)协助医院救治病人
“这些都是剧毒的蘑菇,得把它们脱水烘干,以便制作标本。”6 月17 日下午,记者来到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真菌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陈作红教授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整理从宁乡采集回来的几大袋蘑菇样本。烘干后的蘑菇样本装在一个个透明网纱袋里,袋子里附有记载了蘑菇详细采集信息的小纸片。“这些还只是一小部分,”陈作红打开一个冰柜,里面已经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毒蘑菇样本,“这是我们十几年来收集的样本,这些可都是宝贝。”陈作红的话语里充满自豪。
实际上,这26 年来,陈作红一直在从事毒蘑菇及其毒素研究,而他刚刚凭借在毒蘑菇研究方面的科普作品《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荣获2019 年度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十余年磨一剑——强强联合凝成科普著作
食源性疾病是当前影响中国食品安全、危害公众健康的最主要因素,而误食毒蘑菇中毒是我国食物中毒事件中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每年的6 到9 月,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野生蘑菇进入生长旺季,误采误食野生蘑菇中毒进入高发季节。
“在2000 年以前,我国对毒蘑菇中毒事件缺少有效的调查和研究,这种情况给有效弄清我国毒蘑菇种类资源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也对我国蘑菇中毒分型和治疗带来了巨大困难。有文献报道,某地区1985 年至2000 年间的378 起蘑菇中毒事件中有八成以上未能鉴定出有毒蘑菇的种类,且毒蘑菇中毒的死亡率超过20%。”一起起中毒事件的发生,一个个生命的逝去,让陈作红惋惜不已。而1994 年发生在湖南省长沙县的一起9 人误食毒蘑菇后全部死亡的事件,则是让当时在一线调研的陈作红意识到,对毒蘑菇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刻不容缓。“从那之后,我的研究方向从食用菌转向了有毒蘑菇及其毒素研究。”
这一干,就是26 年。
这20 多年来,哪里有毒蘑菇中毒事件,哪里就有陈作红的身影。湖南、湖北、广东、江西、贵州、云南……通过对十余个省市350 余起毒蘑菇中毒事件的调查分析,陈作红基本弄清了我国南方的主要毒蘑菇种类及其中毒症状。
不过,要弄清楚全国毒蘑菇的种类及其中毒症状,仅靠陈作红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够。“科学研究一定要形成合力。这些年来,已经有不少真菌分类学家和疾控专家积极参与野生蘑菇中毒事件的调查和标本鉴定。”陈作红欣喜于我国毒蘑菇研究力量的不断壮大,“编写《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一书,我们就联合了中科院昆明植物所杨祝良研究员团队、吉林农业大学图力古尔教授团队、广东省微生物研究所李泰辉教授团队。书中记载的200 种我国主要的毒蘑菇种类及描述特征,全部来自野外采集和研究标本,大部分采集于中毒现场。”强强联合让这部科普作品不仅方便老百姓正确识别毒蘑菇,也成为我国疾控、医院、食品安全等各领域工作者的“毒蘑菇知识宝典”,更对我国毒蘑菇鉴别、中毒预防、诊断和防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具有指导意义。
积跬步至千里——上下求索修成跨界专家
“陈教授,今日一男子误食一种白色菌菇,出现呕吐、腹泻、腹痛等症状,现附上患者吃剩的蘑菇图片以及医院检验单,请您鉴定毒菇种类。”采访中,陈作红向记者展示了武冈疾控中心负责人早几天发来的求助微信。
“这是欧氏鹅膏,中毒症状与其他剧毒鹅膏菌不一样。根据检验数据,病人主要表现出急性肾衰竭,需要立刻询问及观察病人是否有少尿或无尿现象。”陈作红迅速给出毒菇种类鉴定结果,并在证实了病人的确出现少尿状况后,立即将《毒蘑菇识别与中毒防治》中记载的对症治疗方案发给了武冈疾控中心负责人。
这样的求助事件,陈作红有时一天要接到五六起,多的时候甚至有十几起。“我们有一个500 人的微信群,里面是全省各地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我的微信好友有1000 多人,其中一半是医生。”陈作红笑言,自己不是学医出身,但现在每天几乎都要和医生打交道,帮助他们确定毒源,和他们交流诊疗方案。
陈作红从医学外行“跨界”成为现在能帮助疾控和医疗部门进行诊断的“行家里手”,离不开20 余年的点滴积累。
这些积累是陈作红一家一家医院跑出来的。
目前,世界上尚无治疗毒蘑菇中毒的特效药,唯一的办法就是早治疗。因此,一旦疾控和医疗机构有需要,陈作红总是会在第一时间赶往医疗机构配合治疗工作。详细询问症状,详细了解发病过程,详细记录生化检测数据……在调查过程中,陈作红发现:一些患者误食剧毒蘑菇后,中毒症状和生化指标出现滞后,往往会导致误诊,错过最佳治疗时期,造成严重后果;还有一些患者食用了某些非剧毒种类蘑菇后,一开始产生严重昏迷、抽搐现象,一些医院采取过度治疗,增加了不必要的医疗开支。
“蘑菇种类不一样,所含有的毒素肯定也不一样,那么产生的中毒症状不同,治疗所采取的方案和方法也肯定不同。”通过多年实地走访调研,陈作红根据中毒症状将毒蘑菇分型归类为急性肝损害型毒蘑菇、急性肾衰竭型毒蘑菇、神经精神型毒蘑菇、胃肠炎型毒蘑菇、溶血型毒蘑菇、横纹肌溶解型毒蘑菇、光过敏性皮炎型毒蘑菇和其他中毒类型毒蘑菇,并逐步总结出每类毒蘑菇中毒诊断要点和治疗原则方法,为医疗机构实施及时精准救治提供了宝贵依据。
“从来没有祈求过上天,这次真的求你了,爸爸还年轻……”在陈作红的微信中,记者看到一名男子的绝望与不舍。“他父亲误食了亚稀褶红菇这种剧毒蘑菇,可导致横纹肌溶解,病死率非常高。”陈作红在得知此事后,立刻前往病人所在医院,指导医生对病人进行血液净化治疗,让病人转危为安。“非常感谢陈作红教授,您的孜孜不倦,才会有我父亲的第二次生命,愿好人一生平安……”
病人家属的感谢也让陈作红激动不已,这是他不断钻研、上下求索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做科研为社会服务才是最重要的事,只有让研究成果真正有利于人民,才是真正发挥了最大效力!”
为此,陈作红团队也在不断开辟新的研究方向。“蘑菇毒素不是只会‘害人’,也可以是治疗肿瘤的良药!”近年来,陈作红团队对我国主要鹅膏菌有毒种类、欧美剧毒鹅膏的肽类毒素以及鹅膏毒素进行了系统的检测分析,在鹅膏毒素检测、制备与分离纯化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为多家单位提供了毒素产品用于开展研究及进行药物的制备。“这是未来治疗肿瘤很有前景的选择药物,也是我们期许的发展方向。”于他而言,研究之路任重而道远,唯有上下求索,奋斗不息。

陈作红(右)在“案发现场”采集毒蘑菇样本
踏遍辽阔山河——行者无疆永葆赤子之心
陈作红的微信昵称为“行者”。行者无疆,一往无前,这便是陈作红人生的写照。
自从选择了研究毒蘑菇,陈作红便风雨兼程,从不懈怠。
每次进行毒蘑菇中毒事件调查,陈作红总是跑完医院跑“案发现场”,实地寻找致人中毒的蘑菇,收集样本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研究;进行菌种资源调查,绘制菌类家族“图谱”,是陈作红的日常工作之一,这决定了他需要常年在野外作业,一年要去十几次,一去可能就是十多天,多年来,他与同事已经带领研究生走遍了湖南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医院、野外、实验室,三点一线的工作,使得陈作红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寒暑假和周末都被划归成了工作日。
除了忙碌,条件艰苦的野外科考还面临重重危险。“摔跤都是司空见惯的小事,蚊虫叮咬更是数不胜数,最麻烦的是遇到毒蛇,我有好几次都差点被咬,好在最后有惊无险。”陈作红说起自己惊险的经历时有些轻描淡写,甚至是有些乐在其中的。当被问及为什么如此执着于毒蘑菇研究时,陈作红脱口而出两个字:“热爱!”
是啊,只要走进过陈作红办公室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这份热爱。蘑菇标本、蘑菇绘画作品、蘑菇玩偶、蘑菇摄影照片、蘑菇工艺品……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都印证了陈作红对蘑菇的深切的感情。而每一个和陈作红交谈过的人,更是能从他谈及毒蘑菇时那种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讲述中感受到他对于蘑菇那份永远炙热的深情。
这份深情还延伸到了生活中。陈作红还有两大业余爱好——徒步和摄影。这是他在研究毒蘑菇时衍生出来的兴趣。科考往往需要走很远的山路,徒步的爱好就这样培养起来,“科考还得拍摄菌种的照片,于是我的包里时刻背着摄影机,为了拍摄蘑菇的美和神奇,为了找到最好的拍摄角度,我可以对着一个蘑菇拍上一两个小时,拍摄出来的作品绝对专业,我曾经还专门去给别人讲过摄影课呢!”陈作红的“诗和远方”,与蘑菇有关,但显然更加丰富多彩。
2017 年国庆长假,时年53 岁的陈作红和朋友一起登上了海拔5588 米的那玛峰。“我们从凌晨2 点开始冲顶,花了两个小时走过了150 米长、近70°的雪壁,最终在8 点40 分成功登顶,那一刻真是心潮澎湃!”在当时拍摄的视频中,陈作红兴奋地振臂高呼“登顶啦”,随后激动得声音哽咽,“那时候真的会哭的。”陈作红看到那时的视频,虽说不再激动,但眼中闪过的光华,脸上浮现的微笑依然让人感受到“热爱”二字带来的力量。
陈作红,一位科研中的行者,亦是生活中的行者,“行者”二字,如今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方式。他热爱这样的生活方式,并将沿着这条路继续不停歇地“行走”下去。■

普通人很难分辨食用菌和毒蘑菇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