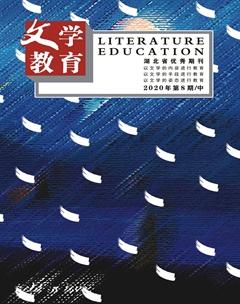文学史写作的思想性原则和审美性原则
顾耸皓
内容摘要: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和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是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本文通过比较《史稿》和《三十年》对赵树理的述评,讨论思想性原则和审美性原则在文学史写作中的对立和统一。
关键词:史稿 三十年 思想性原则 审美性原则
赵树理的小说兼具思想性和审美性,《史稿》和《三十年》都给予了赵树理很高的评价。王瑶受到新民主主义的影响,在写作《史稿》时强调思想性原则,此举不但忽视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而且也忽视了左翼作家身上的艺术性。经过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思想性原则和审美性原则从二元对立逐渐走向统一,到了90年代《三十年》对赵树理的叙述兼具了艺术性和思想性。
一.赵树理的评述差异
(一)作品的选择和解读
《史稿》把赵树理归入了“解放区农村面貌小说”,称他的小说足以代表解放区小说的一般特点,并引用了周扬的评价“一位具有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王瑶在介绍赵树理作品时,《小二黑结婚》被一笔带过,而给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大量的篇幅和高度的评价。《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的主题都是写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是赵树理根据当时的政策创作的小说,所以在主题上是符合新民主主义论的要求的,《史稿》具體介绍了两部小说的内容,并称“《李家庄的变迁》不但是表现解放区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说,并且也是延安文艺整风以后文艺作品多大道德高度水准之例证。”但是在《三十年》中,这对这两部小说中农民地主斗争的情节大写特写,反而把《史稿》中一笔带过的《小二黑结婚》称为赵树理最具魅力的作品。
另外,《史稿》和《三十年》对赵树理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也会对作品主题有不同的阐释。《史稿》习惯使用“改造”、“劳动”等词汇,而在《三十年》中多使用“苦难”、“觉醒”等字眼。《史稿》中把《富贵》描述成一部写二流子改造过程的小说,而在《三十年》中形容《福贵》是写高利贷盘剥下农民悲惨命运的短篇。《史稿》中形容《传家宝》是写妇女也应该参加劳动的,而《三十年》写称《传家宝》是写农村妇女民主意识觉醒的短篇。
(二)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性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他的人物塑造和对小说叙事结构和语言的探索,而这种艺术性恰恰是在《史稿》中被忽略的。《三十年》对待赵树理小说中塑造的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如二诸葛、老秦、金桂婆婆等,不再像《史稿》那样把他们摆在阶级斗争的对立面,《三十年》评论“赵树理笔下的这些落后的老一辈农民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作者只是写出了他们具有的根深蒂固的旧意识、旧习惯阻碍着他们对新事物的理解。他们身上也常常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善良、朴实等优点,这正是他们转变的根据和起点。”
《史稿》对赵树理的小说叙事和语言只有一句话的叙述,并且与人民斗争挂钩,“在形式上,他运用了简练丰富的群众语言,创造了故事性和行动性很强的民族新形势,适宜于反映群众的斗争和生活。”而《三十年》中对赵树理开创的“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有着很高的评价:“首先,赵树理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的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结构特点:其次,在描写与叙事的关系上,吸取传统评书式小说的手法。”与《史稿》中把赵树理的成功归因于实践了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不同,《三十年》更强调了赵树理小说艺术性与大众性的完美的结合。
二.述评差异背后的文学史评价标准
(一)《史稿》写作的思想性原则
王瑶的《史稿》写作深受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自觉地运用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尺,过分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王瑶在《史稿》的初版自序中介绍了《史稿》的成书因为是“工作分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把“中国新文学史”定位各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而国内还没有一部正式的“中国新文学史”的教材,出于教学和政治的双重需要,王瑶创作了《史稿》。[1]王瑶在《史稿》的自序分为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四节,在自序中深度解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并自觉地把新文学和新民主主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文学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新文学是反映了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要求和政治斗争的,它的基本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学的领导思想也是马列主义思想,“从理论上讲,新文学即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领导思想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思想。”因此,《史稿》在述评赵树理时,重视赵树理小说中反映农村中斗争和改造的主题,以及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
(二)“重写文学史”的思想性原则和审美性原则之争
80年代知识范型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采用“二元对立”的方式去思考、分析问题。在“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发刊词中,陈思和和王晓明开篇声明的就是“审美原则”:“重写文学史……它决非仅仅是单纯编年式的史的材料罗列,也包含了审美层次上的对文学作品的阐发批评。”[2]后来又不断强调“本专栏反思的对象,是长期以来支配我们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流行观点,即那种仅仅以庸俗社会学和狭隘的而非广义的政治标准来衡量一切文学现象,并以此来代替或排斥艺术审美评论的史论观”。[3]
“重写文学史”最终以“审美原则”作为它的标准和方法论,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而是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它是“当代文学”全部历史生成的结果,如李杨所言,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80年代文学?[4]正是因为受到《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影响的“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对小说语言形式及其他艺术性方面的过度排斥,才会在社会意识形态开始放松的80年代,开始对“纯文学”和“审美性”的极端追捧,这是一种话语被长期禁锢后强烈反弹的表现;另一方面,它是80年代话语方式生成的产物,之前的文学史写作都受到政治话语的训诫,如王瑶的《史稿》就是以“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的编写,把文学创作纳入政治书写的范围。作为现代化话语的内在要求,“审美性”原则对于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专业化起到了的积极作用,现当代文学史才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革命史”、“思想史”、“社会史”的模式,重塑了一个新的现当代文学。[5]
三.《三十年》-思想性和审美性的完美结合
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主持《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该专栏从当年第四期开始,到1989年第六期结束,总计发表四十余篇关于探讨20世纪中国重要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论文,掀起“重写文学史”的课题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里,赵树理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如1988年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就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反响,戴光中在文章中指出赵树理“民间文学正统论”反映了中国整个文学界的精神萎缩,并且赵树理在对待西方文学持保守和抗拒态度。[6]戴光中在“重写文学史”中关于赵树理的讨论已经淡化了其小说的思想性和历史性,转而指出赵树理小说艺術性的不足,这是对以往文学史重思想而轻艺术的反叛。在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作为“重写文学史”内涵之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方面,最能彰显这一“重写”课题业绩的,是1998年7月由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版。
陈思和曾提出“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他在文学上所构成的成就,不在于他写什么,更要紧的是他怎么写的,也就是他怎么运用他特殊的艺术感觉和语言能力来表述。”[7]《三十年》在前言里对现代文学内容与形式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它要求文学的通俗性,使文化程度很低的普通人民可接受;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文学的现代性,既表现现代意识,现代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以便于把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思维方式、艺术欣赏能力都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的读者提高到现代化水平。”[8]《三十年》对赵树理的述评既肯定了其宣扬党的政策方针和鼓励农村阶级斗争等思想价值,又赞扬了其人物形象创造和现代评书体形式创造的艺术价值,突破了以往文学史讨论中“审美性/历史性”、“艺术性/思想性”、“形式语言/思想内容”二元对立的思维范式。
王瑶的《史稿》虽受政治形态影响痕迹太重,但是作为新中国后的第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起了奠基性的作用。《三十年》的成功,是站在了《史稿》的肩膀上,既借鉴了《史稿》的思想性原则,又吸收了“重写文学史”对于审美性原则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J].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3]陈思和,王晓明.主持人的话[J].上海文论,1988年第5期.
[4]李杨.没有“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J].《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5]杨庆祥.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再谈“重写文学史”[J].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6]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J].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7]陈思和.《关于“重写文学史”》,《笔走龙蛇》,第117页.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