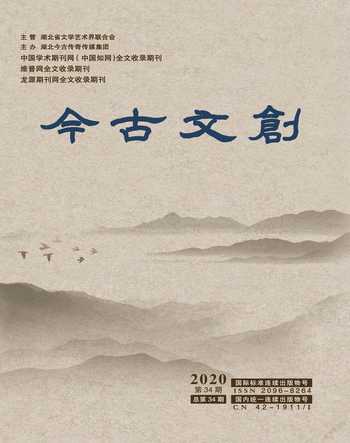《毛诗序》中的风象与风教
陈雪雁
【摘要】 《毛诗序》中“风”多用而意义多变,从而造成理解的歧义丛生。但究其根源,《诗序》“风”的用法正是基于风象的种种特质,由风象入手,可以发现传统风教和诗教的种种端倪。
【关键词】 《毛诗序》;风象;风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14-02
《毛诗序》关涉古典诗学的诸多方面,其中的种种问题至今聚讼纷纭。从《诗序》开端,《诗》与风的关联便跃然纸上。“从风字推出风教二意为全序主脑”。它以“风之始”“风天下”开启其诗论,且以风教说论诗。由此,对风义的考察便成了把握毛诗意旨的关键。
同时,《诗序》表面上表述含混处又多与“风”的使用相关,后人《诗大序》分歧点究其根源亦多基于此。故而,对毛诗“风”义的切近又是一个难点。风义多歧解。故李樗有言“既曰‘风之始也’,又曰‘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又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则知其说一‘风’字,其多如此。故学《关雎》者,当随文而观之,欲以前后相属而通之,则必胶泥而不通矣”①。正是提醒学者毛诗风义多变且难以厘清,要依据文本反复揣摩。由此,厘清《毛诗序》“风”义成为把握《毛诗》意义脉络的关键之一。此外,虽风义多变,然古人讲求文气贯通,在《诗序》整体论述中,这些风的不同用法定当织就一个“风”意义流转又贯通一气的意义脉络。同时,古人尤重开端,《毛诗序》首句“《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中的“风始”与“风天下”为《毛诗序》风义奠定了基本情调,从而成为理解毛诗“风”义的起点。姑且从此出发,从字里行间中体贴《毛诗序》的“风”义并进而体味《诗序》所塑造的那个影响深远的解诗传统。
在解读风义之前,要先理解风象,因为所有的“风”之意涵,當从作为自然现象风象的种种表现引申而出。这不能不说到先民理解世界和自身生命的一个原则——法象天地、类物之情而象其物宜。风的物象奠基了人们对风的一切理解。风是什么?其一,风必在。风作为气的流动,有气必有风,则风无所不被。其二,风自然。风不知其所起,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生发。其三,风由微小而之广大,飓风的缘起也许是蝴蝶翅膀的一次轻轻地扇动。其四,风动物。风不定形且本无象,只能通过处于风之中的事物之动而感知它。简言之,风必动物,物动而知风至。其五,风有声,动物必有声,由声可审风。其六,风有变,风随时节、地域、所被之物的各种情况而变化。先民可能不知道风是什么,却知道风怎么样。《释名》言“风,泛也,其气博泛而动物也”,取遍及与动物二义言风。另一解释风的传统来自服虔“牝牡相诱谓之风”之言,以牝牡之相交相感兴起《国风》男女、人们之交通感动。然推本言之,牝牡之诱当是风物感动义的延伸。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风之始”,陆德明言“风之始,此风谓十五国风,风是诸侯政教也”,孔颖达言“文王风化之始” ②,朱熹《诗序辨说》言“所谓‘《关雎》之乱以为风始’是也,盖谓国风篇章之始,亦风化之所由始也”,黄櫄言“其风化之始” ③,陆、朱先以“风”为《国风》,可见此或为世所常见惯用之义。然《毛序》言约而精,岂会审言此显见而无须多言之事?且《国风》义为短而风化之义长,李樗由此直言以《国风》解“风”“其说肤浅”。“风之始”与“风天下”当为《关雎》教之起点与终点,正是有鉴于此,无论是否以《国风》为表义,注家皆以“风”指向政教之风化义明矣。“风天下”便成“天下之匹夫匹妇皆被其风化”④之象与事。结合上一段,惟风有动物之义,风化天下、上化万民才成为可能。由此,这里的“风始”“风天下”的风教正是基于风有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特性和风能吹而动之,从而人能感而动之的风象及其特性。
英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 Lorenz)说:“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英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恰恰是可以以风化的方式开始教化(“风始”)的依据,因为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扩散正类似教化的推扩。与“齐、鲁、韩皆以为周衰所作”不同,《关雎》以后妃之德支撑起风化的开端。从后妃之德开始,无疑是风化从夫妻向父子、君臣的推扩,也是修齐治平路径的展开。这其中体现的从家政向国政的自然推扩,从亲亲向尊尊的无障碍过渡等等古典政教理解中不言自明的东西。党建初期经历了历次整风运动,正是基于对风教的意识。风教的基础是感而通之,感而遂动。今天人仍然是可感的,但所谓同感和通感也越来越少,因感而动这样的可能也越来越少,从而使得风化政治的运行越来越不可能。
陆德明言“‘所以风天下’,《论语》云‘君子之德风’,并是此义”⑤。风化在风草之喻中达成。“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风吹而物动,此当是风所有意义的最初来源,从这一点看,风化当是一个施动者与被动者之间交互感动的过程。风化既是对能动与承担者的上位者的能力模式与行为范式的描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对作为被动与承受者的民人被动而化、效法君师习性的理解。孟子说“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也正因此,使得风化而教民成为先贤的政教选择。以风与草的关系来描述君民与官民关系,即以风化言政治的运行方式。风化的立足点在于德,君子之德参与小人之德的建构与化成,君子以自身的躬行自然而然地感化民人。“风”正揭示了这种垂范活动的感而遂动、无所不被的品格。正因为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毛序》对《诗经》风化天下意义的坚守,意在申明或建构一种以风化为本质的《诗经》政教观。它以男女、夫妻之义作为风化的开端,解释了风化外扩和推行的方式。二南从王者之风到诸侯之风的降格,与具体诗篇中风化主体从后妃到夫人到媵妾的下逮,提示了风化不断及下,下亦成其自身之德而能化的风化格局。二南首篇《关雎》、《鹊巢》之化与末篇《麟之趾》《騶虞》之应的呼应,展现了风化中德性的感应关系。
《毛诗》风教一端所系是上位者的德性,其美刺盖由“德与不德”而来;另一端强调的却是德性的“逮下”“所致”“化行”“应”等等。古典之教多由行示,上古圣王有巢氏“教之巢居,冬则营窟,夏则居巢”,燧人氏“教人炮食,钻木取火,有传教之台,有结绳之政”,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水为耒,耜耒之利以教天下”等等传说都展现了中国政教思想从开端起的以身立教传统。后世以“立德”为太上之选择,亦因为此。
陆德明、朱熹以象、事关系解风教之说。陆德明言:“沈云:‘上风是《国风》,即《诗》之六义也。下风即是风伯鼓动之风。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今从沈说。”朱熹言“承上文解风字之义,以象言,则曰风;以事言,则曰教。”上教民之行与风动物之象类同,象虚而事实,这样风便成为事实之形容。此说以“风也”为诗教之象,有得于《诗经》参物取象以明道义的风教路径。
先儒解此一段皆未尽其意。或云:风犹天之风,而敎则君之敎。此诸家之说皆然也。然本文但云“风也,敎也”,何尝有天与君之别哉?一以为譬辞,一以为实辞,古人之意本混然,而固离之何也?⑥
物象、人事的判然二分恰恰动摇了参物取象以制人纪的诗教之本,割裂了物象与人事之间沛然兴起、感而遂通的态势。脱离象事之浑然,则毛公独标兴体,传文对兴之重视便无所据。黄櫄紧接着提出了从诗教的过程理解“风也,教也”的看法。
窃尝谓古人之意,以为《国风》之诗,其本系于一人,而其化被于一国。自其本于一人言之,则谓之风;自其及于一国言之,则谓之敎,岂不简且直哉?如闻伯夷、柳下恵之风者,莫不兴起,此“风以动之”之意。孟子所谓“君子所以敎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此“敎以化之”之意也。先儒谓“动之则开悟其善心而已;化之则明其敎令而为之劝率其事加详夫。所谓化者,感之于心术之·而变之,于形迹之外与之俱化而不自知也。若曰其事加详则不足以为化矣,予请为之例曰:闻二南之风者,感动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变易其气质。动则变,变则化,天下之理然也。⑦
以德性垂范者,自身之言行举止,成风而教人。此正“德风”之义的展开,且“王者之风”“诸侯之风”、贤者之风、君子之风等,皆就教化的施为者以自身德性构成的教化场域言之。德风成教,“待文王而后兴”的教化接受者因教而化之。《毛序》以“风以动之”“教之化之”描述“风也,教也”,其中的“动”与“化”正好是施为及其所及的动态过程。当然,化之不断逮下,被化者也不断成为化人者,风教由此不断的伸展与流通。
这里,所有的注疏皆以此句句首之“风”与上句“风之始”之风同为《国风》之风为出发点。《诗序》开端以“风天下”论诗之政教,其中,动词性的风正是对诗之政教过程的开示。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毛诗序》言“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以风言诗,风不离象。同时诗也是一个教的事业,风即是教,诗如风动物般以风教化民。若从风教的开端看,它自然、自发而起,情动其中而生发。以情志之生发言诗,人心之感物而成诗,亦象风之发生。从风教的过程来看,这是一个如风之扩散一样从切近到广远、从细微到宏大、从个体的性情际遇到邦国天下的礼仪法度的推进。从风教的形式看,如风以声响和物动而彰显,教以诗、乐之事为中介,使得个人与他者、邦国和天下结成一个政教共同体。从诗教的结果看,诗中之教动(化育)人心从而化行于天下。教政合一,风教行而风政成。
注释:
①③④⑥⑦李樗、黄櫄:《毛诗李黄集解》,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6页,第26页,第26页,第28页,第28页。
②⑤毛亨、郑玄、孔颖达:《毛詩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