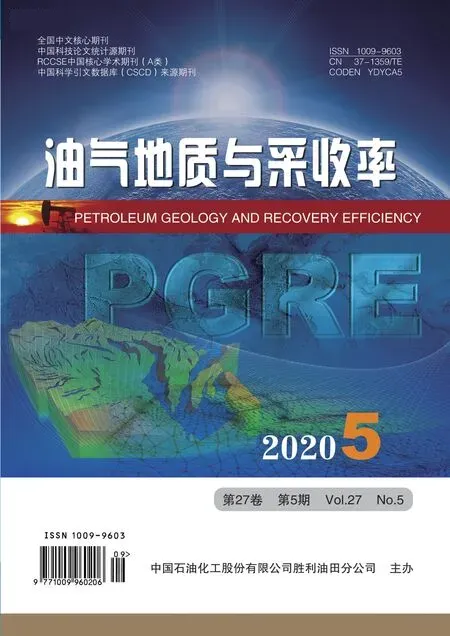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降黏及微观驱油机理
熊 钰,冷傲燃,孙业恒,闵令元,吴光焕
(1.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2.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山东东营 257015)
稠油化学降黏作为一种效益与效率均较高的降黏方式[1],目前在各大稠油油田都开展了广泛性的先导试验。特别是针对高黏稠油采用化学降黏冷采,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化学降黏剂的研发趋势是在分子骨架上引入具有极性或表面活性的侧链,利用极性基团和表面活性基团的空间效应和降低固液界面张力的能力,提高对蜡晶、胶质和沥青质的分散作用以降低黏度[2]。但由于表面活性剂降黏主要是形成水包油乳液,仅仅降低稠油表观黏度,并且在岩石中油水乳状液的包封有时会堵塞孔隙空间[3],因此表面活性剂降黏也具有一定局限性。而引入极性基团的分散型降黏剂在分子中含有极性基团侧链和高碳烷基主链,主碳链主要使降黏剂分子能溶于油中,而侧链中的极性基团则与胶质和沥青质中的极性基团形成更强的氢键,从而使降黏剂分子渗透进入胶质和沥青质片状分子之间,拆散平面重叠堆砌而成的聚集体,形成片状分子无规则堆砌而变得结构松散,并减少聚集体中包含的胶质和沥青质分子数目,降低原油的内聚力,改变稠油分子结构,从而起到降黏作用[4];由于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在现场应用过程中注入到地层后,不会吸附停留在地层表面,也就不需要泵入氧化剂来清洗沉积的聚合物,从而节省了处理环节与时间[5],因此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由于其独特的优越性而备受重视。为此,通过降黏机理研究及微观驱替实验发现,该降黏剂既能改变稠油分子结构,又能降低稠油分子间作用力,驱替过程中还能对吸附在颗粒上的稠油起到剥离携带作用,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1 乐安油田原油性质
乐安油田位于济阳坳陷东营凹陷南斜坡的纯化-草桥鼻状断裂带上,构造背景复杂。由于处于盆地边缘,地层经常发生剥蚀和超覆,形成多个不整合面[6-8]。油藏埋深为2 000~4 000 m,油藏压力系数为1.0 左右,地层温度为50~60 ℃。地面原油平均密度为0.985 7 g/cm3,含蜡量平均为3.68%,凝固点平均为14.44 ℃,总体含蜡和含硫量偏低,胶质和沥青质含量大于50%[9]。由于油藏埋藏较深,蒸汽热损失量也较大,发展特殊的降黏剂冷采技术尤其必要。
2 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的分子结构及基团性质
本次研究所用的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是具有较大刺激性气味的、乳白色的水溶性液体。该液体与水结合后会出现分层,上层是由大量浅黄色油溶性细小颗粒组成的、呈分散状态的极薄层,下层则与水充分混合呈现灰白色液体。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该降黏剂是以水溶性为主、具有部分油溶性颗粒的分散型降黏剂。由于波数大于4 000 cm-1为近红外光谱区,通过傅里叶红外光谱分析法无法准确分析,因此,主要分析波数小于4 000 cm-1的光谱,再通过专门的处理软件分析降黏剂的分子结构,以便于从分子结构层面研究其作用机理。
由图1 可以看出:1 565 cm-1为羧酸根COO 反对称伸缩振动峰,说明降黏剂中可能含有乙酸钾。在波数为2 200 cm-1附近出现的是脂肪族异硫氰酸酯N═C═S反对称振动峰,该化学键的出现表明降黏剂结构稳定。波数为2 458 cm-1附近的弥散宽峰为P─OH 伸缩振动峰,说明降黏剂含有磷原子且依然存在大量氢键。波数为2 626 cm-1处升高幅度增大,显示有少量H2S存在于降黏剂中,存在含硫基团,这也解释了降黏剂有较大难闻气味的原因。CH2和CH3反对称伸缩振动峰出现在约2 908 cm-1处,体现了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存在长链烷基与饱和烷基。波数为3 050~3 600 cm-1处出现多个O—H,形成宽的吸收带,振动模式为糖类O—H 伸缩,由于糖分子之间存在大量氢键,这说明该降黏剂分子间作用力也主要以氢键为主。波数为3 650~3 700 cm-1处的峰强且尖锐,为金属氢氧化物的O—H 基团伸缩。对图1 所示的红外光谱,使用ChemSketch 软件对降黏剂分子结构基团进行整理,得到的结果如图2 所示,将其命名为硼烷基乙酸钾羧基二甲基磺酰己基异硫氰酸酯基膦酸。

图1 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红外光谱Fig.1 Infrared spectrum of water-soluble dispersed viscosity reducer

图2 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分子结构式Fig.2 Molecular structure of water-soluble dispersed viscosity reducer
由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分子结构式可以看出,该降黏剂分子以极性基团为主,属于亲水分子,当该降黏剂与水结合后,形成的溶液又有部分非极性基团,因此该降黏剂同时具有部分溶于稠油的特性。对稠油的降黏在分子结构和缔合作用机理方面主要体现在:分子主链为由5个碳组成的碳链,相连的有乙酸钾基团,当降黏剂与水结合形成降黏剂溶液后,钾以离子形式存在,并且作为“活跃体”会分散稠油堆砌复杂的分子体,而羧酸的氢键非常强,该强极性基团与稠油分子结合后通过氢键作用吸附胶质与沥青质[7],从而导致稠油内部分子间的氢键减弱;硼烷基与亚甲基形成支链,当降黏剂与稠油结合后,硼烷基中的硼会以杂环原子的形式存在于稠油分子中。第2 个碳与P—OH 和N═C═S 组成的支链相连,P—OH 基团与稠油分子结合后会拆散稠油分子中冗杂的碳链,插层进入片状分子间,起到分散结构的作用,脂肪族异硫氰酸酯N═C═S则体现了降黏剂分子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第5个碳相连的巯基在水溶液中得到氢离子后易形成H2S气体而逸出,该基团本身就具有臭味,易被氧化,在与稠油分子结合后以游离态存在于混合体系中。
3 降黏剂的分散作用及降黏机理
3.1 分散插层作用
为明确稠油加降黏剂后的分散效果,利用真空条件下的电子束,经高压加速后穿透样品,形成散射电子和透射电子,并在电磁透镜的作用下于荧光屏上成像对比。实验步骤包括:①将加降黏剂前后稠油样品分别放入150 ℃恒温箱中烘干。②用小勺取出少量未加降黏剂的稠油和加入质量分数为1%降黏剂溶液的稠油,分别加入到体积相同的无水乙醇中,经超声波分散震荡后形成无色透明溶液,取出一滴滴在载玻片上,待液滴水分蒸发后剩下的稠油颗粒肉眼不可见,则认为样品制备成功,然后进行透射电镜测试。
测试结果(图3)表明,稠油在加降黏剂后与加降黏剂前相比分散程度明显增大,加降黏剂前的稠油在50 nm 级才能看到清晰的颗粒图像,而加降黏剂后稠油在100 nm 级便能看到稠油颗粒,显示稠油加降黏剂后具有明显分散现象。

图3 乐安油田稠油加降黏剂前后透射电镜测试结果Fig.3 Comparison of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st results of heavy oil from Le’an Oilfield before and after adding viscosity reducer
加降黏剂前稠油颗粒结构稳定且形状规则,在电镜下呈现深黑色点状;加降黏剂后颗粒边缘明显开始向四周扩散,形状发生改变,颜色由深黑逐渐变为浅灰色,颗粒中心出现一些细小气泡,说明降黏剂溶液进入了稠油颗粒内部并与其发生了作用;分子排列有序度降低,出现明显分裂现象,这是胶质与沥青质中部分胺醇醚类化合物被降黏剂分散携带出的结果。测试结果说明该降黏剂降黏效果较好,能够拆散堆砌重叠的复杂片状分子结构,破坏了稳定的胶质分散体系;结合降黏剂分子结构和基团分析,认为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分子凭借形成氢键的能力和渗透扩散作用进入胶质和沥青质分子间,使胶质与沥青质之间作用力减弱,片状分子无规则排列,且以芳杂稠环的形式包覆在沥青质粒子表面,从而使未加降黏剂稠油颗粒间的紧密包覆层被有效分散和破坏[10],稠油中的轻烃会从内部流出,起到降黏作用。
3.2 黏附力改善效果
原子力显微镜主要是根据针尖与样品表面的相互作用对样品表面和黏附力进行研究[11],加降黏剂前后的图像变化和表面黏附力的变化可反映降黏剂对稠油分子间引力的降低作用。具体实验步骤主要包括:①用2 根消毒棉签分别蘸取少量加降黏剂前后稠油均匀涂抹在直径1 cm 的圆形载玻片上,并用干净的刀片将涂抹在载玻片上的油膜削得尽可能薄。②处理完成后,将2 个圆形载玻片放入温度为150 ℃恒温箱中烘干,保证样品中不含挥发性物质。③静置24 h 后,将载玻片取出,装入防止样品受到污染的自吸盒内;然后借助原子力显微镜观察针尖靠近样品和远离样品时的黏附力变化,进而评价降黏剂是否对稠油有分散降黏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在相同放大倍数(1 μm)下,覆盖在载玻片表面的稠油颗粒间相互黏连区域的延伸范围广,颗粒之间存在强相互作用力使其相互黏连,形成宽且长的桥状通道;从微观层面来说,这是大量杂环原子与胶质和沥青质分子间结合形成络合物导致的结果。这种络合物数量增多,会形成稳定的胶体。这些胶体又会聚集成大分子聚集体,造成稠油黏度大幅升高[12]。加降黏剂后,稠油颗粒间联结通道变细,颗粒图像虚化说明颗粒受降黏剂影响流动性变好并向周围扩散,黑色区域与黄色区域?混合后变得模糊,颗粒间相互作用力大大降低,桥状通道被破坏。这些现象显示微观层面下降黏剂溶液分散进入了胶质和沥青质片状分子之间,部分拆散平面层叠堆砌而成的聚集体,使片状分子无规则排列,分子结构变得松散,减少了聚集体中包含的胶质与沥青质分子数目,降低原油的内聚力,增加了流动性,降黏效果显著[13]。
对样品在5 μm×5 μm 的扫描范围内均匀选取256 个点绘制黏附力曲线。其横坐标为微悬臂与样品间相对移动的距离或者说是针尖与样品间的距离,横坐标的变化反映针尖与样品靠近与远离的过程,靠近曲线与远离曲线构成完整闭合的黏附力曲线图;纵坐标为悬臂偏移量(针尖形变量),与弹性系数有关,悬臂偏移量与弹性系数之积为样品与针尖之间作用力。悬臂偏移量大于0,则针尖与样品间为斥力;悬臂偏移量小于0,则针尖与样品间为引力。
对比加降黏剂前后稠油黏附力曲线(图5)可知,两样品最大引力对应的横坐标明显不同:未加降黏剂稠油在针尖与样品远离过程中的0.3 μm 处出现最大引力(悬臂偏移量为90 nm),加降黏剂后稠油在针尖与样品远离过程中的0.17 μm 处便出现最大引力(悬臂偏移量为45 nm),说明稠油加降黏剂后结构更分散。即通过加降黏剂前后横坐标对比可以发现:稠油在加降黏剂后,针尖与样品间远离的过程中到出现最大引力的距离比未加时小,黏附在针尖上的稠油颗粒产生的拉丝断裂点提前,即黏性降低,且最大引力也变小。

图5 加降黏剂前后乐安油田稠油黏附力曲线Fig.5 Adhesion curves of heavy oil from Le’an Oilfield before and after adding viscosity reducer
为了对比加降黏剂前后的引力差,用实际计算值进行比较。在实验中,所使用的针尖为AC20-0型针尖,弹性系数为2 N/m,当用胡克定律计算时,弹性系数与针尖形变量之积为针尖与样品间力的大小。通过加降黏剂前后黏附力曲线计算,加降黏剂后稠油与针尖之间的最大引力(曲线图中引力曲线最低点对应的距离与弹性系数之积)(8×10-8N)与加降黏剂前最大引力(1.6×10-7N)相比显著降低,即加降黏剂后稠油与针尖之间的最大引力降低了一个数量级,显著降低了稠油颗粒表面的黏附力,也降低了黏附力的离散程度。如果把这种黏附力降低看成是微观结构的改变,说明降黏剂对稠油表面有修饰作用,它显著地改变了稠油表面的微观结构,从而达到降低黏附力的效果,与图4的加降黏剂前后变化所反映的情况一致。
3.3 分子基团变化
加降黏剂前后红外光谱对比分析是研究降黏剂分子与稠油分子之间相互作用的方法之一。其实验原理为:红外光是一种具有连续波数的光,这种光源照射样品后,某些波数的光会被样品中特定的分子基团所吸收,通过加入某种标准样品(本底)作为对比进行红外光谱图分析[14],即可获得分子缔合和结构改变方面的信息,从而研究降黏机理。利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以纯溴化钾作为仪器本底,分别对加降黏剂前后稠油进行红外光谱分析。具体实验分为4 步:①从干燥箱中取出少量溴化钾分别放入2个研磨皿中。②用小勺分别取出少量未加降黏剂稠油和加入了质量分数为1%降黏剂溶液的稠油倒入2 个研磨皿中,油与溴化钾的体积比约为1∶100。③使用研磨棒对2 个器皿上的混合物进行充分研磨,研磨后将样品使用压片机进行压片。④制作完成后送入红外光谱仪进行检测,再对得到的谱图进行分析。
对比加降黏剂前后稠油的红外光谱(图6)可知:波数小于1 000 cm-1时光谱图较为平坦,加降黏剂前721 cm-1处出现的波动为亚硫酸酯S—O 伸缩,在加降黏剂后峰消失,说明降黏剂分子与稠油分子结合后拆散了此处的分子链。1 373 cm-1处的波动是稠油分子中存在的CH3基团,加降黏剂后波数对应峰变化幅度小,吸收峰向上发生了相对位移且波数变化范围变窄,说明CH3基团数量减少,推测长链分子发生了断裂。1 498 cm-1出现的峰为芳香族亚硝基N═O,加降黏剂前稠油与加降黏剂后相比吸收峰向下偏移且波数变化范围变窄,这反映了芳香族亚硝基N═O基团数量少,由于有机亚硝基化合物在稀溶液中以单分子形式存在,这说明加降黏剂后稠油中N═O基团之间联结变得松散,出现了以单分子形式存在的物质。2 358 cm-1处为CO2反对称伸缩,此处加降黏剂前稠油透过率比加降黏剂后透过率高的原因应该是空气中存在大量CO2对检测结果产生干扰所致。2 904 cm-1处为铵盐NH2+伸缩,在此处出现弥散谱带,即说明稠油中存在铵盐,并且加降黏剂后吸收峰向上发生相对位移,说明NH2+基团数量减少。3 050~3 600 cm-1处加降黏剂后稠油的伸缩振动频率与未加时相比向高波数侧位移(波数为3 033 cm-1),吸收强度增加会使谱带变窄,反映在分子基团变化上表现为糖类O—H 伸缩变弱,O—H 单键力常数增大,稠油分子间缔合作用减弱。波数为3 500~4 000 cm-1时出现一系列尖锐吸收峰为气态水的振转光谱,加降黏剂后稠油在此区域吸收峰向下发生了相对位移,波数向低频发生了相对位移,即降黏剂溶液吸收了稠油中大量的气态水分子,侧面反映了该降黏剂对稠油有一定脱水作用,也说明它具有降低分子间强缔合作用的能力。总之,稠油分子基团在加降黏剂后发生了显著变化,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溶液在改善稠油分子结构的基础上,降低了稠油分子间的作用力,起到了降黏效果。

图6 稠油加降黏剂前后红外光谱对比Fig.6 Comparison of infrared spectrum before and after adding heavy oil viscosity reducer
3.4 微观降黏机理

图7 乐安油田稠油加降黏剂前后分子结构式Fig.7 Molecular structure before and after adding viscosity reducer to heavy oil from Le’an Oilfield
通过红外光谱分析得到的所有分子基团对稠油分子和加降黏剂后的稠油分子结构进行合理推测,并用Chemsketch 软件对这2 种分子结构式进行绘图。图7a显示,稠油的主体结构以片状强缔合堆积结构为主,故黏度高。分析降黏剂分子与稠油充分结合后得到的分子结构式(图7b)可知,降黏剂溶液可部分溶于稠油,这是降黏剂分子中的长链烷基、氢键和杂环原子等与稠油分子结合的结果;但是由于N═C═S 这类稳定的不饱和键以及游离S 原子的存在,使得降黏剂溶液也不会完全溶于稠油中。与未加降黏剂时稠油分子结构相比,加入降黏剂后,降黏剂分子的主碳链保持完整,与主碳链相连的部分侧链,以及支链中的极性基团与稠油片状分子相结合,分子延伸度变大,并使片状分子无规则分布,同时稠油本体的杂环原子如S 和N 在稠油与降黏剂溶液结合后大部分被拆散,有效地减少了络合物的形成。
降黏剂分子通过P—OH 和羧酸根COO 基团插层进入稠油分子间以及羟基基团进入分子中,形成了更强有力的氢键,使得油溶性部分与稠油分子充分结合形成更加稳定的结构,而稠油本体沥青质粒子与胶质粒子通过氢键和缔合作用聚集而形成的胶束数量则显著减少。
结合红外光谱、原子力显微镜和透射电镜等微观实验,同样显示降黏剂分子间能形成很强的氢键,与稠油分子结合后渗透并扩散到稠油胶质与沥青质片状分子之间,使得稠油本体分子间氢键等作用力降低,从而导致了由片状胶质与沥青质分子形成的平面层状稳定结构聚集体产生分离,原来规则的聚集体转变成片状分子无规则分布,分子结构变得疏松,有序度降低,熵增大;而且加入降黏剂后稠油分子黏附力有效减少,大大改善了稠油的流动性,从而起到降黏的作用。
4 微观驱油机理
4.1 剩余油分布与降黏剂溶液驱替速度的关系
CT 扫描通过X 射线,将岩心内部的微观孔隙与喉道结构特性真实地反映出来。通过实验分析不同驱替速度下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对稠油在微观孔隙条件下的分散作用,具体实验步骤包括:①将渗透率为240 mD的干岩样放入微型岩心夹持器中,用CT 扫描干岩样孔隙与喉道分布。②在地层条件下(温度为60 ℃,围压为10 MPa),使用质量分数为2%的降黏剂溶液对饱和油的岩样进行1 mL/min 恒速驱替,驱替结束后进行CT扫描。③在同样地层条件下,用质量分数为2%的降黏剂溶液分别进行3和5 mL/min 恒速驱替,驱替结束后对岩样分别进行CT扫描。
从图8 可以看出:剩余油大多分布在细小的孔隙与喉道中,降黏剂溶液在这部分孔隙与喉道中难以动用,但在较大孔隙与喉道中动用程度大,效果明显;在孔隙与喉道中剩余油分为2种,一种是游离态剩余油,此类剩余油并未吸附黏连于矿物内部结构,而是在矿物表面游离;另一种是吸附态剩余油,存在于孔壁表面或细小的孔隙与喉道中[15],不同驱替速度下微观剩余油的形态差异较大。
相对于驱替速度为1 mL/min 驱替结束后岩心孔隙与喉道中微观剩余油分布,驱替速度为3 mL/min 时的吸附态剩余油比例更低,说明降黏剂在岩心中对稠油的剥离作用更大,从岩心中驱出了更多体积的油;而驱替速度为5 mL/min 时游离态与吸附态剩余油占比均较前两者大,驱油效果最差,说明一味增加驱替速度与驱替压力并不是提高驱油效率的有效方法。
分析岩心横截面驱替结束后的剩余油分布(图9)可以看到:驱替速度为1 mL/min 时驱替图像中剩余油呈现分散分布,整体驱替效果较好,说明分散型降黏剂在此驱替速度下能够对岩心中稠油有较好的分散作用,使得稠油从岩心中分离出来,未被驱替出的剩余油则零星地分布在岩心中。驱替速度为5 mL/min 驱替结束后的图像中剩余油分布较为集中,与驱替速度为1 mL/min 时相比,其驱替效果已明显变差,说明提高驱替速度对驱替过程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分散降黏作用由于高速驱替而减弱,岩心内部窜流通道形成后弥散作用和降黏协同作用降低。驱替速度为3 mL/min 时驱替效果介于低、高速驱替两者之间。

图8 不同驱替速度驱替结束后岩心孔喉中微观剩余油分布Fig.8 Distribution of microscopic residual oil in pores and throats after displacement at different displacement rates

图9 不同驱替速度驱替结束后岩心中剩余油与降黏剂溶液分布Fig.9 Distribution of remaining oil and viscosity reducer solution in core after displacement at different displacement rates
4.2 剩余油分布与降黏剂溶液驱替质量分数的关系
利用微观刻蚀模型模拟真实岩心铸体薄片,通过加入质量分数为1%,2%和3%的降黏剂溶液分析刻蚀模型驱替结束后的剩余油分布。该模型是将2 个厚度为1 cm、直径为1cm 的圆形载玻片盖在一起,其中一个载玻片表面有激光刻蚀的模拟孔隙裂缝通道,经胶皮套胶封固定而成。实验步骤如下:①将刻蚀模型抽真空,在地层条件下(温度为60 ℃,围压为10 MPa)饱和水。②饱和水后用油驱水,使刻蚀模型饱和油,建立束缚水饱和度后模型老化24 h。③使用质量分数为1%的降黏剂溶液对模型进行驱替,整个过程用高清摄像头进行摄像,至出口端稳定见水20 min,认为驱替结束。④将驱替结束后的模型清洗干净,重复步骤①—③,使用质量分数为2%与3%的降黏剂溶液分别对模型进行驱替,至出口端稳定见水20 min,认为驱替结束。
对比驱替结束后的图像(图10)可见,不同质量分数降黏剂溶液驱替后裂缝中微观孔隙与喉道剩余油形式多样。质量分数为1%的降黏剂溶液驱替结束后,孔隙与喉道中存在包围式簇状、并联式喉道状、死角式点状和绕流式粒间孔隙状4 种形式的剩余油[16-19];质量分数为2%的降黏剂溶液驱替结束后存在包围式簇状和绕流式粒间孔隙状剩余油分布,小喉道内部的稠油以及孔隙与喉道中角隅或者盲端中的剩余油基本被驱出,与质量分数为1%时相比,适当提高降黏剂质量分数可使降黏剂能够进入孔隙与喉道内部,具有一定的调驱作用,使降黏剂溶液进入低渗透通道驱替出其中的残余油;经质量分数为3%的降黏剂溶液驱替后只存在包围式簇状剩余油,调驱作用更加明显,高渗透条带两侧较小孔隙与喉道中的剩余油也被驱出,但包围式簇状剩余油仍未被驱出,可能是驱替压差不足所致。

图10 不同质量分数降黏剂溶液对微观刻蚀模型驱替后图像Fig.10 Images of micro-etching model after displacement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viscosity reducer solution
综合岩心与微观刻蚀模型驱油机理发现,该降黏剂虽然可以有效降低稠油黏度,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增加溶液浓度可以改善降黏剂溶液的调驱能力,增大稠油驱油效率,但是降黏剂溶液在高驱替速度下的驱替及波及效果并不理想,可能是因为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与稠油作用需要一定的时间。
5 结论
乐安油田稠油主要结构是胶质与沥青质片状分子间的层叠堆砌,分子中的杂环原子、氨醇醚类分子基团以及它们之间形成的氢键,导致地层温度下稠油黏度大。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分子具有疏散稠油分子结构、降低稠油分子间氢键的作用,从而达到降低乐安油田稠油黏度的效果。
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的降黏机理主要为:降黏剂能够部分溶于稠油中,凭借P—OH 和羧酸根COO等分子基团插层进入稠油片状分子间形成更强的氢键,减弱稠油内部分子间的缔合作用,同时拆散稠油内部分子中的杂环原子来减少络合物的形成,疏散了稠油分子结构,减弱了稠油内部分子间作用力,使稠油结构分散达到降低黏度的效果。
水溶性分散型降黏剂微观驱油机理表明:由于其分散插层作用使得该降黏剂对颗粒表面吸附油具有剥离作用;但在较高驱替速度、较低浓度下,剥离作用相对减弱,且存在较大量的包围式簇状剩余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