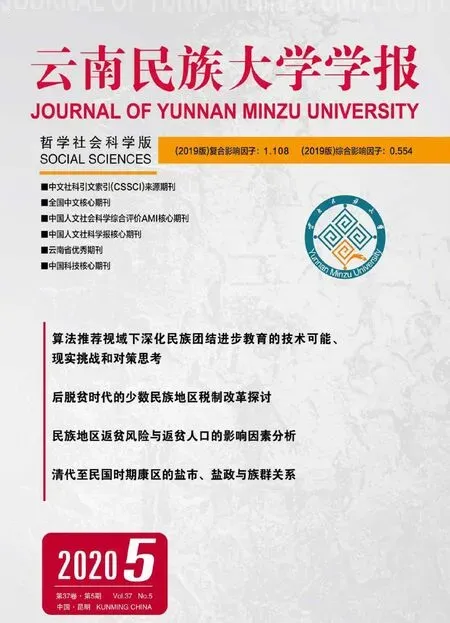民族地区返贫风险与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耿 新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引言
通过多年的大力扶持,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得到较大缓解。2012-2018年底,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从3121万人减少到60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0.8%降至4%,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就。同时,脱贫成果不实、脱贫质量不高、少数民族返贫等问题相伴而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数据显示,2016—2018年,我国返贫人口数分别为68.4万、20.8万、5.8万人,返贫比例虽呈下降趋势,但防止返贫压力依然巨大。(1)肖泽平,王志章:《脱贫攻坚返贫家户的基本特征及其政策应对研究——基于12省(区)22县的数据分析》,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防止已脱贫人口返贫是当前打赢扶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既是紧迫的现实问题,也是长远的战略问题。民族地区贫困更具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返贫问题接踵而至蚕食了精准扶贫的成效,打击了扶贫干部和贫困户的信心,严重影响了精准扶贫的工作成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必须有效防止返贫现象发生,自觉树立及时有效化解返贫风险的意识,对已返贫人口实施针对性帮扶。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一)文献综述
1.返贫的概念。张俊飚认为返贫是某些贫困人口在解决温饱、脱贫后,因诸多因素交互制约作用,经济上又陷入贫困的状态,即“饱而复饥”“暖而复寒”现象。丁军、陈标平指出扶贫开发后已摆脱贫困的部分人口再返回到贫困人口行列的现象即为返贫。(2)丁军,陈标平:《构建可持续扶贫模式 治理农村返贫顽疾》,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姚学刚认为脱贫后返贫是由于贫困人口自身存在一定的脆弱性或返贫风险未完全消除。(3)姚学刚:《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思考和建议》,载《重庆行政》2020年第2期。
2.返贫的类型。返贫类型分为生存艰难型返贫、温饱不稳定型返贫、素质低下型返贫、环境恶劣型返贫、天灾人祸型返贫。(4)刘玲琪:《陕西省返贫人口特征分析与对策思考》,载《人口学刊》2003年第4期。按返贫因素,返贫可分为政策性返贫、贫困人口能力缺失返贫、环境导致的因灾返贫和约束性因素导致的发展型返贫。(5)邓瑞强,曹国庆:《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载《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年第6期。返贫的理论模式为断血式返贫、狩猎式返贫、失敏性返贫、转移性返贫、传递性返贫。
3.返贫风险。返贫现象的社会学特征为多因性与一定时期内的不可抗拒性互为前提,贫困空间分布的广泛性与不平衡性交织,返贫的突发性在潜伏性和持久性中间歇发生,冲突性与相关性共存。(6)郭志杰等:《对返贫现象的社会学考察》,载《中国农村经济》1990年第4期。返贫诱发因素是综合的、多样的、复杂的,既有自然因素和历史因素,也有制度、贫困户自身因素。脱贫户自我发展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弱,因灾返贫、因病返贫的概率将升高,政府缺乏对脱贫人口的动态跟踪与精准管理(7)杨园园等:《基于典型调查的精准扶贫政策创新及建议》,载《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第3期。。返贫因素主要是政策性返贫、贫困人口自身能力缺失返贫、环境导致的因灾返贫、约束性因素导致的发展型返贫。(8)邓瑞强,曹国庆:《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载《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年第6期。包国宪等认为返贫现象的诱导因素来自返贫主体(贫困家庭或个人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客体(国家内部发展的差异性)、载体(自然、生态环境的供养力)。(9)包国宪,杨瑚:《我国返贫问题及其预警机制研究》,载《兰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李长亮认为影响脱贫人口返贫的因索众多,既有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因索,也有贫困人口自身因素,还有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实证检验发现文化水平、劳动能力、健康状况、外出务工、贫困户属性、贫困户自身条件等因素对返贫有显著影响。(10)李长亮:《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返贫因素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
4.返贫的阻断机制。贫困存在“致贫—扶贫—脱贫—返贫”的循环机理,对已脱贫人口进行动态精准识别或跟踪精准识别尤为必要。应构建遏制返贫的保障机制、自我发展的动力机制、创新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机制、创新参与机制等。(11)韩广富:《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机制的创新》,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建立返贫管理机制、产业扶贫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群众内生动力机制。(12)张鹏飞:《关于返贫防控机制建设的几点思考》,载《法制与社会》2017年第33期。返贫的阻断机制为财富内生阻断断血性返贫、心理改善阻断狩猎式返贫、制度供应阻断失敏性返贫、价值挖掘阻断转移性返贫、教育阻断传递性返贫。(13)何华征,盛德荣:《论农村返贫模式及其阻断机制》,载《现代经济探讨》2017年第7期。
(二)基于贫困脆弱性的返贫风险
脆弱性的概念最早由世界银行于2000年提出,指个人或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脆弱性概念较好地解释了贫困的动态性和返贫问题,是衡量福利水平的良好指标。脆弱性与贫困紧密相连,脆弱性不能事前直接观测到,只能事前预估;脆弱性群体当前处于贫困线之上,未来可能因风险冲击而陷入贫困。(14)Clewwe P,Hall C.Are some groups more vulnerable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than others? Hypothesis test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Peru.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98 (1).受风险冲击未来几年有一次陷入贫困的家庭是脆弱性家庭。(15)Pritchett L,Suryahadi A,Sumarto S. Quantifying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A proposed measure,with application to Indonesia.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2000 (3).基于不同视角,学者对贫困脆弱性赋予了不同内涵,代表性的量化定义有预期的贫困脆弱性、风险暴露脆弱性和低期望效用脆弱性。可见,现有成果较多研究贫困户返贫风险,直接分析民族地区返贫人口脆弱性的并不多。2020年后,我国反贫困的重点转向相对贫困,成功解决相对贫困户的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将具有重要意义。返贫人口的最大特点是脆弱性强,表现为经济脆弱性、社会关系脆弱性和自然环境资源脆弱性,因脆弱性而重新返贫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比较普遍。
三、民族地区返贫风险作用机理
走出“贫困——脱贫——返贫”怪圈,需要准确把握返贫风险与作用机理,将返贫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为实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打下坚实基础。根据贫困脆弱性的冲击来源,民族地区的返贫风险主要体现在:
(一)能力缺失型返贫风险
依据能力贫困理论,贫困户能力缺失指健康状况下降、应对市场风险能力不高、技能水平偏弱。一旦人力资本缺乏或者不足,就会影响已脱贫人口的能力提升和后续发展,进而影响到家庭,使得已脱贫的贫困户成为返贫的边缘群体,产生返贫风险。
1.因病返贫风险。民族地区是我国地方病分布重点区域,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地方性克汀病、氟中毒、克山病等地方病流行县占全国比重较高,威胁人口多、作用时间久、危害程度深。民族地区也是我国传染病高发区,是艾滋病、结核病、肝炎等疾病流行区域。民族地区生存环境恶劣,疾病风险相当高,居民健康风险大是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高的主要原因,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突出。2015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户的占比升至44.1%,脱贫人口中因病返贫比例大的主因是高昂医疗费用。(16)刘小珉:《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载王廷中,方勇,尹虎彬,陈建樾:《中国民族发展报告(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页。2018年,新疆、青海、西藏每10万人口中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分别为659.75、433.29和358.09,新疆、四川、云南每10万人口中甲乙类传染病法定报告死亡率分别为6.31、4.98、4.9,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市场能力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有的产业项目同质化严重,有的就业不够稳定,有的政策性收入占比高。”当前最主要的返贫风险是产业经营失败以及就业困难等导致的收入锐减,收入问题是返贫的主要成因。市场机制下,经济成果的分配本质上并不偏向贫困人口,而贫困人口自身不具备市场风险预知力和应对规避风险的能力,同等市场条件下因缺乏竞争多以失败告终,容易跌入贫困线以下,出现脆弱性返贫。如,一些贫困民族地区生产的农产品的品种和品质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有的冷链物流技术因不达标导致农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损失惨重。
3.就业技能风险。随着农业现代水平提升,技能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不高、致富能力弱成为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17)邓瑞强,曹国庆:《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载《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年第6期。近年来,民族地区以贫困人口作为培训重点,开展贫困劳动力全员培训,但一些针对贫困户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培率不高、学习动力和能力严重不足,技能培训供需严重脱节。加之现代农业技术推广难,贫困户技能实用性不强,因就业技能不高导致返贫风险。
(二)政策性返贫风险
1.社会性政策返贫。脱贫后现有扶贫政策仍可继续享受,目的就是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由于贫困人口脱贫摘帽后会退出建档立卡之列,按照“脱贫不脱政策”要求,脱贫人口对扶贫政策形成一定的惯性,政策持续性的效果弱化,脱贫人口的发展有一定困难与乏力,(18)李月玲,何增平:《多维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返贫风险——以定西市深度贫困地区为例》,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9期。存在返贫风险。脱贫后,水利扶贫、交通扶贫、电力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基建上的帮扶项目可能不再继续;民族地区未形成“行政——市场”结合式的发展秩序,脱贫人口因技能、知识等而被新发展方式所排斥。
2.环境性政策返贫。脱贫人口赖以发展的贫瘠资源如果受限于退耕还林还草、水源区保护、减少碳排放等生态保护政策约束,补贴标准降低容易导致脱贫人口返贫。有的易地扶贫搬迁可能导致生计遭受损失带来生计风险。
3.虚假脱贫后的返贫。按中央部署,各地制定了脱贫攻坚时间表,有的地区十分积极、层层加码,扶贫领域出现了本位主义、形式主义的苗头。在扶贫时限高压下,一些地方存在追求短期效应倾向。为尽早脱贫,一些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将扶贫项目或资源更多地投向凸显政绩的示范点、合作社等,而不是偏远的贫困村或贫困户。有的干部捐款捐物的扶贫方式,不利于可持续脱贫和稳定脱贫。虚假式脱贫、算账式脱贫、指标式脱贫、数字式脱贫在个别地区经常出现,脱贫质量不高不稳。有的靠低保、退耕还林补贴等政策性脱贫,脱贫基础不扎实。
(三)环境性返贫风险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很多是限制开发区域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使脱贫人口陷入“贫困—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返贫”陷阱。国家对生态环境的政策性保护与约束,对当地经济发展有一定制约作用。因“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实施的生态移民带来的生计损失也会造成返贫。(19)邓瑞强,曹国庆:《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载《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6年第6期。
1.灾害性返贫风险。灾害性返贫风险主要指因旱、因涝、因气候失调等原因导致的返贫风险。民族地区气候复杂多变、地质构造特殊、自然灾害繁多,是致贫返贫的重要原因。西藏和四省藏区暴雨、泥石流、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较多,南疆地区暴雨洪涝、冰雹和大风沙尘的灾害影响最重,凉山州、怒江州、临夏州等地泥石流、暴洪灾害较重。而贫困人口面对灾害带来的风险往往十分脆弱,难以应对。贫困人口大多靠天吃饭,缺乏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丰年温饱,灾年返贫,循环反复。(20)王延中,丁赛:《中国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7页。2016-2018年,“三区三州”3级以上有灾地震共发生13次,损失258.37亿元,约占全国的46.40%;共发生严重水旱灾害20多次,损失65.65亿元,约占全国1%。灾害频发对民族地区脱贫影响较大,2016年,西藏因暴雨洪涝灾害造成28.8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3万公顷,绝收面积6000多公顷,直接经济损失14.2亿元。临夏州2018年“7·18”特大暴洪灾害造成农业直接经济损失5644.52万元,11.94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达0.49万公顷。
2.疫情性返贫风险。2019年12月以来,突发的新型冠状肺炎无疑是对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次严峻考验,“战疫阻击战”和“脱贫攻坚战”在贫困民族地区相互叠加,疫情防控对返贫风险有较大影响:一是外出打工受影响。贫困家庭的收入来源很多依靠外出打工,居家隔离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地方封闭管理、延期复工复产等,使得贫困人口缺少收入来源,可能出现因疫返贫。二是扶贫产品的销售和旅游市场受影响。由于人流出行、物流运输受到一定限制,一些时鲜、时令农产品销售受影响很大。刚脱贫人口“摘帽”又“带帽”的潜在风险增大。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上不断蔓延,国际订单不断锐减,外向型经济、大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受出口锐减的冲击而收缩,大量贫困农民工务工机会减少,收入无法得以保障,面临新的返贫风险。
(四)发展型返贫风险
发展型返贫主要指脱贫人口追求生计发展,提升贫困脆弱性中的返贫。
1.因教返贫风险。一是贫困民族地区平均教育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低,能力供给不足。2017年少数民族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7.01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05年)。有的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巩固率仅86%,初中辍学率高达30%;有的边境地区高中升学率仅31%,甚至有些边远山区的孩子要到离家一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上学。(21)罗黎明:《民族地区脱贫攻坚至关重要 须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人民网,http://industry.people.com.cn/n1/2019/0310/c413883-30967366.html,上网时间2019年3月10日。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临夏州(1%)、凉山州(1.1%)、怒江州(1.9%)高等教育比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二是知识水平技能缺乏使缺乏技能的贫困户“就业难、发展难”。农业科技信息时代来临促使生产方式转变,农民工回家务农获得收益少、效率低,造成可持续生计差的发展窘境。少数民族群众运用科技水平的意识和能力不足,难以形成长效脱贫的门路,存在较大程度的因教返贫风险。
2.精神返贫风险。自我发展意识低、主体素质差、抵御风险能力脆弱的返贫者,极易再次落入贫困。实践证明,不解决内生动力问题,就无法彻底解决返贫问题。有的脱贫人口参与扶贫政策和项目的意愿不高、动力不足;有的虽参加产业扶贫、资产扶贫等项目,但却没有主动了解这些项目的利益联结机制。
四、民族地区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
“全国脱贫看甘肃,甘肃脱贫看临夏,临夏脱贫看东乡。”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位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堪称“贫中之贫,困中之困”。2019年,课题组深入国家级深度贫困县东乡县进行访谈并收集资料,调查了解东乡县返贫人口的脆弱性风险,以期对民族地区返贫人口的总体特征有细则入微的了解。
(一)东乡县脱贫攻坚现状
东乡县是全国唯一以东乡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同时也是东乡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区。东乡县位于甘肃省中部地区的西南部,临夏州的东北部,地貌呈方圆形,四面环水,中间高突。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中间高四面低,六大山梁、六条深沟呈伞状分布,自然资源匮乏。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财政自给率仅为3.2%,是全国地方平均水平的5.5%。东乡县现辖8镇16乡、5个镇、229个行政村、1893个合作社,总人口31.47万人,其中东乡族27.76万人,占比88.2%;全县总面积151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6.78万亩(人均耕地仅为1.17亩),其中山旱地占87.3%。东乡县贫困人口从2013年底的10.91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1.28万人、累计减贫9.63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8.69%下降到4.25%;纵向来看,东乡县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但与全国的倍数却逐年增加(见表1),属于典型的深度贫困地区。

表1 东乡县与全国分年度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22)来源: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数据提取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
从“一二三”的脱贫标准来看:
第一,东乡县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9年,国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收入高于6000元,(23)《国新办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扶贫办网站,http://www.cpad.gov.cn/art/2020/3/12/art_61_114841.html,上网时间2020年3月12日。东乡县贫困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均值为2926.58元,中位数为2886元,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差距较大。从贫困类型来看,1511名返贫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为3329.45元,中位数为3115.4元,均低于当地扶贫标准线3800元。
第二,“两不愁”指标。东乡县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交汇处,全县海拔1735~2664米,往往十年九旱,人畜饮水难度大。取水下沟上山要走3~5公里,人挑畜驮来回需1~2小时。根据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东乡县作出的“把水引来,把路修通,把新农村建设好”的重要指示,解决“饮水难、饮水贵”刻不容缓。目前,黄河、洮河河水已提上高高的山梁,输水管线铺到偏远山区,形成了水源工程和供水管网骨架,自来水入户率达93.7%,每户每年实行126元的统一水价,不限用水量,(24)《贫中之贫 决战决胜——来自深度贫困县甘肃东乡的最新报告》,人民网,http://hn.people.com.cn/n2/2019/0430/c357128-32896387.html,上网时间2019年4月30日。全县安全饮用水的指标达100%。供水改善提振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信心。2018年,东乡县农村骨干调蓄水池(北部片区)工程已投入使用,中部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一期)主管道通水成功,彻底解决了全县供水末端吃水难问题。
第三,“三保障”指标。一是控辍保学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义务教育巩固率从2013年的47.9%提高到2019年的95.3%。(25)《东乡县2018年度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要点》。东乡县采取异地劝返等超常规措施治理控辍保学,有4833名辍学学生被劝返。108所幼儿园和28所薄弱学校改造项目在加速推进,教育硬件水平不断提升。二是基本医疗有保障。协调甘肃省人民医院在县医院设立分院,完成了7.4万名贫困人口签约服务,通过科室建设、人员培训、诊疗指导、资源共享等全面提升了县乡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县外转院人数比往年降低近30%;县外转诊率由2017年的39.75%下降至2019年的25.01%。东乡县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报服务,新农合参合率达96.78%,一二类低保户和建档立卡户实现全覆盖;贫困人口医疗报销率达95%,有效缓解了看病贵、看病难问题。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项制度,东乡县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网。三是住房安全有保障。2018年,东乡县核定确认存量危房3498户,省州年下达危房改造任务2924户,现已竣工2939户,危房竣工率100.5%;实施61个贫困村风貌改造、9389户预脱贫户庭院硬化和改厕项目,结合危房改造、风貌改造和城乡环境整治,共投入补助资金480多万元,拆除危旧房屋4753户,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二)东乡县返贫人口的特征
本文以2019年8月东乡县“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1511名返贫人口(占贫困人口的比例为3.06%)为样本数据,分析东乡县返贫人口的特征与影响因素。1511名返贫人口中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返贫的人口数量分别为962人、394人、151人、4人,占比分别为63.7%、26.1%、10%、0.2%,说明脱贫时间越早越容易返贫。
如表2,在1511名返贫人口中,东乡族占比最高(87.3%),略低于东乡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重(88.2%)。从文化程度来看,占比最大的分别是小学(55.5%)、文盲或半文盲(32%),说明文化程度在返贫影响因素中至关重要;在1511名返贫人口中,在校生人数为416人,占比为27.5%。从健康水平来看,返贫人口中患长期大病或慢性病的占比为11.4%,因残返贫占比为6.2%。东乡县群众在饮用水和生活习惯方面具有典型的地域特色,容易产生大骨节病、克汀病等地方性疾病。由于医疗设施和社会保障还不完善,当普通家庭出现因病因残时,周围亲缘的社会网络支持度较低,使得脱贫人口在面临家庭疾病风险时呈现出明显的贫困脆弱性特征,产生返贫风险。从返贫人口的劳动技能来看,无劳动力或弱劳动力的贫困人口占比为49.6%,而普通劳动力占比为50.2%,可见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普遍较差,无一技之长的较为普遍。从务工状况来看,83.4%的返贫人口没有务工,而到县外省内务工比例仅为12%,到省外务工的比例仅2.2%,这与东乡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贫困人口普遍缺乏劳动技能有一定的关系,这说明是否务工以及务工的距离远近对返贫有一定影响。从参加大病医疗来看,98.7%的返贫人口已参加大病医疗,这说明国家的大病医疗政策在返贫户中得到了有效实施。从贫困户属性来看,低保贫困户占返贫人口的比例高达63%,是一般贫困户返贫比例的1.75倍,可见低保贫困户更容易返贫。从返贫原因来看,缺资金(占42.7%)已成为返贫的主要因素,其他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缺技术(18.7%)、因病因残(11.5%)、自身发展动力不足(11%)、缺劳力(7.7%)、交通条件落后(4.7%),其他原因(因学、因灾、因婚、因丧、缺水等)合计为2.5%、缺土地(1.1%)。12.1%的返贫人口中属于危房户,这主要与贫困户居住条件生态脆弱、容易受灾有一定关系。返贫人口中100%已实现安全饮用水,是“两不愁三保障”指标中完成最好的。

表2 东乡县返贫人口的基本特征与变量赋值(26)数据来源:《东乡县2018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和2019年工作要点》。表中“健康状况”缺失1人,“劳动技能”缺失2人。
(三)东乡县返贫人口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个典型的深度贫困县,近年来东乡县贫困发生率逐年降低,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返贫问题依然存在,蚕食了精准扶贫的成果,进而影响如期脱贫目标的实现。因此急需分析返贫人口的返贫风险与影响因素,进而分类指导,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本研究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将返贫人口的人均纯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将民族、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劳动技能、务工状况、参加大病医疗、贫困户属性、致贫原因、危房户作为自变量,详见表2。对各自变量间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VIF值均小于10,自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回归结果稳健准确。表3是影响返贫人口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模型的P值远小于临界值0.01,模型总体上显著。

表3 东乡县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民族对脱贫人口返贫有显著影响,东乡族群众返贫人口的占比是汉族的7.86倍。而在东乡县贫困人口中,东乡族贫困人口占比高达97.8%,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其他民族,需格外引起注意。
文化程度对脱贫人口返贫有显著影响。返贫人口的小学、文盲或半文盲的占比很高,证明实现脱贫并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贫困户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后返贫风险将会大幅降低。
健康状况对返贫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身患残疾、长期大病或慢性病的人群通常是长期的特困户,国家已将因残致贫、大病或慢性病致贫纳入了农村低保救助政策范围,属于兜底扶贫对象,这部分群体的兜底保障程度较高。另外,也说明国家要针对健康的贫困人口出台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有效措施,提高其内生发展动力,巩固脱贫成效。
劳动技能对返贫无显著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能劳动力、普通劳动力、无劳动力或弱劳动力对返贫的影响不显著。
务工状况对返贫无显著影响。说明贫困劳动力非农就业渠道比较窄,应加强对贫困人口的职业技术培训。
参加大病医疗对返贫无显著影响。这与李文亮(2019)研究结论不同,这可能与东乡县98.7%的返贫人口参加大病医疗有关。东乡县脱贫攻坚到人到户惠民政策规定:贫困人口个人负担合规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报销后,合规医疗费用年累计超过3000元以上部分,通过医疗救助政策全部兜底解决。
贫困户属性对返贫有显著影响。低保贫困户、特困供养贫困户缺乏发展基础和条件,发展能力较差,脱贫的脆弱性和稳定性相应较低,但受到返贫风险冲击时返贫概率会增大。
致贫原因对返贫有显著影响。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应着力在发展产业扶贫的资金、技术、劳动力上给予重点保障,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也是需引起关注的地方,应注重扶贫扶志相结合。
危房户对返贫无显著影响,因为危房经过一次性改造合格验收后就不会再返贫。
五、结论与启示
根据影响民族地区返贫人口的影响因素,应将防止返贫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第一,建立返贫监测机制。要把存在返贫风险的贫困人口找出来,重点监测有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和脱贫困难的贫困人口。通过村民申请、乡村报警和部门大数据分析预警,动态监测易返贫和易致贫人口,严格把好退出关。将监测预警和帮扶情况纳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实现全过程动态监测与管理。(27)耿新:《差别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1页。
第二,建立返贫预警机制。在制定返贫预警机制时,实施源头预警,评估贫困户不同的返贫风险和脆弱性来源,分类扶持,增强其抵抗贫困脆弱性的能力。从政策环境、自然环境、主体自身、项目资金等方面针对性地构建返贫预警机制。
第三,建立返贫人口帮扶机制。从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社保兜底保障、健康帮扶等方面建立对返贫人口的系统帮扶机制。着力提升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推动贫困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脱贫。
第四,建立内生动力机制。实证表明,文化程度低、资金缺乏等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是造成返贫的重要原因,应加强教育救助制度化建设、优化宣传引导机制、建立经济与精神的协同机制。
总之,影响贫困人口返贫的因素既有贫困人口自身原因,还有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等其他因素。本研究仅是依据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分析了返贫人口的自身影响因素,对其他因素尚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因此,要科学分析这些影响返贫的因素,增强抵抗脆弱性的能力和水平,防止返贫。
——东乡县韩则岭学校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