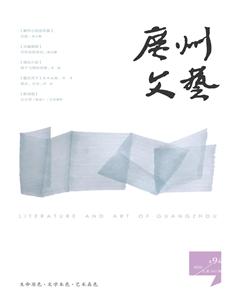冗余代码
张彤
1
科技馆要来大人物了,人物大到什么程度,馆长老林说,组织上有纪律,还不能公布。大人物来的时间初定明年四月,满打满算还有半年,上面会有系统的方案,展陈、安保,甚至改建。老林说到最后这两个字的时候,嘴唇、舌尖、牙齿的距离相当近,送气很长,老林年轻时在汽轮机厂当工人,汽轮机厂的管乐团很有名,老林在那儿吹过双簧管,现在还坚持每天一早到山上吹长音,故而“改建”二字,音量不大,却送到了每一位员工的耳朵里。
这悠远的“改建”二字,令本周一的例会意味深长起来,例会结束,各个部门就行动起来。由于上面还没有具体的指令,这动作就带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特点,那就是打扫卫生,用展陈部部长李跃进的话来说,就是清理多余物资。
展陈部的副部长杨树林在二楼的小仓库里发现了一架废弃的单筒望远镜。这望远镜他很熟悉,刚到科技馆那会儿,它就放在临海的草坪上,投币一元钱可以看五分钟,五分钟后,会有一个黑色的钢板咔嗒一声弹起来,镜头里就是乌黑一片了。从前望远镜前总是围着人,每个周一,杨树林就打开望远镜下面的铁盒子,取出一堆硬币,有时候还有压扁的啤酒瓶盖、游戏币以及不锈钢垫片等。多的时候一周能有两百块。
科技馆刚刚落成时,顶楼是一个球幕影城,球幕放映设备只有日本的两家企业生产,中标的公司挺上道,在安装影城设备前,就先赠送了这台望远镜。
球幕影院的设备组装后只放过两部电影,一部是《浩瀚的星空》,一部是《快乐动物园》,此后胶片电影就过时了,球幕影院就一直那么放着,杨树林都好几年没去过了。
科技馆是圆形的建筑,所以在某些角落就有几间不规则形状的小仓库,不规则的结果是每个小仓库都里大外小,处处是死角,东西一旦放进去,就再也找不着。身世不凡的望远镜与断腿的椅子、有裂纹的镜子为伍,看起来也没什么突兀,它表面的白漆有些驳落,机身上还刻着王一凡到此一游、哈尼永远爱张洁,还有用油性的马克笔写的少妇寻一夜情156XXXX、办证177XXXX等字样,刀刻笔写,十分风尘。杨树林沾了一手灰,要不是戴着手套,这望远镜他肯定不会动,但是他动了心思,把它搬回办公室。用酒精擦拭了一番,放开三脚架,投进了一枚硬币,没有反应,下面有一个电池盒,他换上两节五号电池,镜头咔嗒一声打开了。调好焦距,杨树林在里面看到了老李油汪汪的额头,黑白相间的头发,有几根的末端带着毛囊,头发不多,却也有皮屑,高倍望远镜中,这个额头就像清晨看到的野馄饨收摊后的路面,内容相当复杂。杨树林听到自己的喉头咕咚一声,赶紧把望远镜调了个方向。
2
自从搬到站山小区的这套两居室的房子,杨树林就上班非常早了,以前天天都要乘半小时地铁,再倒两站公交,经常到单位都快十点了。科技馆周末开放,周一开例会,周二到周五排班轮休,每个人的上班时间都不一样,所以也不好管理。展品十年没更新,其实到了周六周日来参观的人也不多。杨树林是展陈部的副主任,副科级,工程师职称,展陈部主任李跃进退休还得七年,馆里年龄最大的高工张文革退休也还得九年,至少这七年,空转干耗,一切没指望,就像程序里的循环冗余指令——杨树林曾做过好几年的程序员,30岁那年考进了科技馆,从此告别了“码农”的生活,过起了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去年夏天,女儿杨翘楚转入实验小学四年级,妻子李云娜决定,全家南迁到实验小学附近。经过了一番艰苦的看房,他们租下了站山六小区的这套陪读房。这套两居室的房子——说是两居室,其实没有客厅,大约等于原来住单身时那种筒子楼的两间——只有52平方米,一个月的租金却是杨树林半月的工资,他们原来那套房子装修得挺好,不舍得出租,这样每月又添了一笔开支。房贷刚还完,现在又添了房租,杨树林签租房合同时,也是感觉到心里一阵发紧。
可是在家里,杨树林的意见并不重要,女儿坚决地站在云娜一边,云娜呢,在公司里拿惯了主意,所以对于家里的任何决策,都只是通知杨树林,不留协商的通道。
站山小区的这套房子,云娜收拾得干干净净,女儿住小间,有一个两层的床,一层是桌子,床在上层,云娜说,将来女儿读高中就得住校了,得提前适应。另一间是云娜与杨树林的房间,一张双人床,一张方桌,既做餐桌,又是偶尔在家工作用的电脑台。杨树林无班可加,这张桌子就成了云娜的专享,云娜每天吃完晚饭,把餐桌收拾干净,就从包里拿出薄得像剃刀一样的苹果笔记本,在这里做EXCEL表格,做PPT。一会儿绩效考核、一会儿KPI评测,看名字云山雾罩,而内容,也就那么回事。她们公司有几家子公司,经营范围互相交叉,内耗不断,第一任领导要各子公司充分发挥积极性,鼓励内部竞争;第二任领导提倡集团效应,要求形成合力;最近又换了新领导,偶尔瞥一眼云娜的PPT,满屏都是“统分结合”“统分协同”“统分有序”这样的词。
云娜十分敬业,每晚工作完一般都九点多了,她会迅速地把笔记本收起来,桌子上没有一点杂物,面巾纸都放在下面的小抽屉里,擦脸的时候迅捷地用两根手指抽出一张。杨树林也被训练得相当熟练,开抽屉、抽纸、关抽屉,一气呵成,手快得跟公交车上的扒手似的。哪止桌子,整个的两居室都没有半点杂物,小厨房里只有一口炒锅,一个蒸箱,一家三口只有一个双门的衣柜,每个周末,云娜会回海口路原来的房子里,取每人五套换洗的衣服,连袜子都是配好的,就像电梯里天天更换的地毯,杨树林想,也许应该在每件衬衫上写上星期一、星期二的编号。墙是灰色的,地板是浅褐色的,仅有的几件家具均有棱有角。没有电视机,两人各有各的iPad,为了防止互相干扰,各配耳机一副,苹果耳机的造型像是两台微小的吹风机,戴的时间久了,耳朵不舒服。
没有一丝杂物的房间相当趁妻子的意,她每天收拾完房间后,都会露出节制的笑容。在这个方方正正的新房子里,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既定程序走,女儿吃完晚饭先练一小时琴,然后写一小时作业,再看半小时闲书。书都是按照书单来的,这学期是《窗边的小豆豆》和《斑羚飞度》。杨树林的程序就比较简单,每天早下班做饭——他从一个叫“下厨房”的APP里下載了一周的菜谱,每晚按图索骥,然后就是看美剧。云娜,收拾厨房、餐桌,看女儿练琴,然后做表格和PPT。狭小而又一尘不染的空间里,目光无处可落,一家三口长时间处于死盯状态——杨树林盯着iPad,云娜盯着笔记本电脑,女儿盯着作业或者琴谱。
从搬进“新居”起,三个人都有点小心翼翼,拖鞋底软,走路没声,LED的顶灯,光线是漫射的,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他们果真连影子都没有。空间小,又安静,女儿写完作业开始弹琴时,常把杨树林吓一跳。
双人床比原来家里的要小一尺,睡觉时几乎肉贴着肉,肉帛相见,女儿听见不好,所以要自备消音器。床虽小,却相当结实,怎么晃也没声音,杨树林默默地进入,云娜默默地应合,杨树林无声地抖了一下,云娜轻轻出了一口气,像完成了一次默契的肌肉注射。杨树林想起上学时有一阵子宿管抓打麻将抓得严,于是他们弄了一套纸麻将牌,输赢都无声无息,辅导员来敲门,打扫战场也很容易,这种隐秘的游戏只打了几回,就没人再玩了。
云娜收拾早餐时,发现杨树林的iPad纠缠的耳机线,她说,要不,我送你一副蓝牙耳机吧?云娜从网上订购了两副BEAT SOLO的戴头式蓝牙耳机,可以折叠,浅褐色的。蓝牙耳机与iPad再没了关联,声音不知从何而来,音效倒是超过以往。
每天下午5:40进门,每天早晨6:00起床。云娜会把被子平铺到床上,枕头位置的被子倒翻出来,床罩也是浅褐色。房间满眼望去,毫无人烟的迹象,杨树林就觉得自己没棱没角的,与房间风格十分不配。
他就赶紧送女儿去上学了。
3
老林最近脾气很大,常在各个部门逡巡,眼睛里闪烁着光。老林的气息是悠长的,眼睛和嗓门都是亮的。他与科技馆仿佛浑然一体,每天几乎一进馆里,杨树林就可以判断出老林在不在。除了老林之外,每个人都与自己的工作若即若离。老林若在,所有人都遛边走,一派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假象,老林若不在,科技馆就像一位垂暮的武林高手,招数散乱,真气难行。
在散乱的气氛里,杨树林已经把小仓库收拾得干干净净,除了这台望远镜,其他物品都处理掉了。他花了整整三天,拆开了投币的装置,杨树林看见自己在凸透镜面上笑开了花。这个装置投进规格适宜的硬币后,电路闭合启动五分钟计时,五分钟一到,电路断开,内置的镜头盖就盖上了。这个装置的学名叫作“单片机”,有运算、控制、存储和输入输出功能,如果有烧录器,修改一下代码,再加上传感器,可以实现微信扫码识别。他甚至都想到了几行指令的写法。杨树林曾经很擅长删除冗余代码,用汇编语言写的程序,简直像拉丁文的十四行诗。不过这些知识对今天的杨树林来说,完全没有用了,删除冗余代码这件事,成了“冗余”知识。即便科技馆有要求想把望远镜的投币改成扫码,也只要在网上花几百块钱买个零件就行了,在他们的采购系统里,这种单片机大概算是办公耗材。杨树林看到电路板上焊点十分规整,他仿佛看到流水线上有一个穿着雪白工装的人,正用锃亮的电烙铁烧制这个电路板,他在扔掉的一瞬间又改了主意,右手腕一转,把它放到兜里。不过他想,那位雪白工装的流水线工人,现在也该失业了。
望远镜的焦距原本是可以调的,但当初焦距环被锁住了,经过他这一番拆装,望远镜变得十分自如,他把它放回到小仓库里,这个喇叭形的小仓库,如今只有这台望远镜,透过一扇圆窗户,望远镜大约在120度的观测视角,完全像一个瞭望哨。科技馆位于东海路上,西侧的爱丁堡花园在二十年前是绿岛市最贵的公寓,东侧是一个公共绿地,北侧是两三栋高耸入云的写字楼,南边是一个两车道的小路,再过去,就是红色礁石与蓝色海水的混合体,从前,只要一起风,这里就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自从修了防波堤,风浪就小了,礁石在平静的海水里无所事事,上面长满了海蛎子,又缠绕了许多不明身份的海草。爱丁堡花园、防波堤都在望远镜的覆盖范围,每天早晨,送女儿到学校后,杨树林就步行到单位了,直奔这间小仓库。
爱丁堡花园有公寓也有别墅,别墅是仿欧式的,红顶黄墙,刚建好时貌似老城的老洋房,但是老洋房越老越好看,新洋房一褪色,就旧得不行,远远看去,好像一座座公厕。几栋六层高的公寓外墙涂料都驳落了许多,从望远镜里看,原来的窗子是铝合金涂着深褐色漆,有好多住户更换了窗户,新换的窗子大都是白色塑钢材料,塑钢窗的外沿有许多白水泥的痕迹,有几家还抹得特别恣肆,窗口像放了许多溶化了的奶油冰激凌,淌得到处都是。
科技馆南侧的小路上,有许多人在跑步,有一个背着双肩包的姑娘,手持自拍杆四处找风景。自拍杆真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的形状很像猪悟能的九齿钉耙,又可以伸缩,兼具金箍棒的优势。女孩旁若无人地抽出如意九齿耙,高调地宣誓她与这世界尚有一耙的干系。杨树林觉得这想法挺逗,忍不住自己哈哈大笑起来。
这条小路所邻的大海,礁石林立,但是大约五十米处有一道防波堤,防波堤挺宽,像是一个半岛,在半岛的尽头,有钓鱼的老人,夏天时,还有人在这里跳水——那里没有礁石,是一个天然的野浴场。一个背着氧气罐的蛙人从防波堤上下来,在浅浅的海中艰难地走,冷不丁就扎了一个猛子,两条腿在水面上甩啊甩,脚蹼像是壁虎脱落的尾巴,过一会儿就看不见了,只留下一些泡沫。大约十五分钟后,蛙人步履艰难地上了岸,腰间沉甸甸的。他摘下面罩和氧气瓶,脱下潜水服的上衣,爬上防波堤,从一辆小面包车里拿出一个大水盆,然后从裤裆方向一样样地往外掏。杨树林调了一下焦距,发现他掏的东西挺多,有一个像大老鼠那么肥硕的黑乎乎的东西,不像是鱼,再调焦距,居然是一只大海参。海边的人管这种粗大的海参,叫大老参,一只野生的能卖一两百。此外,还有大小不一,最大像月饼那么大的鲍鱼。防波堤上一下就围了好几个人,杨树林想,这家伙今天可得赚不少钱。
爱丁堡花园里已经有许多人开车出门了,有个西装革履的老男人,站在一辆黑色的特斯拉旁边,一会儿,那车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升起了翅膀,老男人坐进去,刚开出一点,就把车停下,他从车里出来,在楼道里推出一辆小摩托车,摆在车位上,然后蹲在地上,杨树林看见他从摩托车上解下一把链条锁,将摩托车锁在地上——那地上,有一个小铁环。西装男人把摩托车锁好,站在那儿又端详了几秒钟,才放心地走了。如此高科技的车,得有高科技的车位保障,不像旁边的车位,放的是破沙发、旧轮胎。占車位的东西是最卑微的财产,虽然价值趋近于零,但是需要有一定的体积,看起来难以移动。这些卑微的财产,却又是忠诚的,可信赖的。杨树林站在望远镜前,思维就变得空前活跃。他想,摩托车和沙发,原来都是重要财产,现在却只能用来占车位了。
望远镜里能看到三幢公寓楼,别墅区就被树挡住了。公寓最东面的住户都有一个大阳台,有一个飘窗。前些年,飘窗算是阳台,卖房时只算一半的建筑面积,所以能买到东头的,都会赚几平方米的面积。多数住户在飘窗外都装了防盗网,里面还有窗帘,啥也看不到,但是四楼的一家是透明的大玻璃。里面有个女人正在做瑜伽。去海边做瑜伽多好,杨树林一边想,一边调整焦距。那女人上身穿半截的运动装,下身是七分紧身裤,背对着阳台,正在做一个提臀的动作。在望远镜里,这女人用右手食指隔着裤子把内裤下沿的松紧带勾了一下,又放手。夏天时,好多女人会当众做隔着外衣拉胸罩带子,杨树林猜想,是因为出了汗,带子黏到身上不舒服,他也经常把手伸进裤袋里,若无其事地拉一下内裤边,但是这都是高度隐秘的,没有声音。女人就不同了,女人的内衣内裤都很有弹性,拉起之后一松手,就會弹回去。他在望远镜里仿佛也听到“嘭”地一声,又闷又脆。
4
关于要建新科技馆的呼声早在几年前就有了,每年的两会上,都有科技界的政协委员联合起来提提案,《绿岛日报》还曾派出几路记者到南方的几座城市探访新建的科技馆,有个城市由民资兴建了一个超大的馆,“已经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编者按里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绿岛,也应该有一流的科技馆了。
关于建新馆的事,大家的态度比较暧昧,盼望事业做大做强,是人之常情,但是摊子一旦搞大,难免不受控制,“if……else if……”杨树林认为,这个程序在科技馆每个人心里都运行了无数次了。未来毕竟还没有来,这也只是个冗余程序。
老林说,假如来视察的大人物发了指示,新馆可能就会变成现实。“虽然设备老化,但是我们的精神面貌是历久弥新。”老林慷慨激昂地说,他站在多功能厅的小舞台上,阳光从圆形的小窗户里射进来,光柱中,有黄亮的尘埃在做布朗运动,间或会有白色粉末喷涌进来,那是老林的唾沫星子。现在,每周一的例会,都成了大人物专场。
老林像打了鸡血一样,瞪着血红的眼珠子继续喷,他当“红小兵”的时候就给西哈努克亲王献过红领巾,后来有国际政要来访时,他也常作为各界群众的一员夹道欢迎,科技馆刚建成时,中央领导三天两头来视察,老林——那时还叫林工——每次都前后左右地忙活。虽然他自从当上馆长,就再没见过大官儿,但这回听说有个大人物要来,老林马上又被附体了。老林的嘴角和嘴唇一起抖动,他的眼睛里放着奇异的光,有一种“自以为把握了真理的确信”,让人身不由己地服从。每当老林以为大事将临、重任在肩的时候,这眼神就准时到来。行政部已经做出了一张A3纸那么大的行动任务表,并对总任务进行了分解,行政部主任牛小菁今天穿了紫毛衣配皮裙子,活像一只山茄子,她扭来扭去地将各个部门的分解任务书派发下来。“时间表,路线图已经明晰”,老林说,“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展陈部的主任李跃进有一抽屉的核桃,有的很方,像铁轨上露出的枕木,有的很圆,像久经沙场全是疤痕的玻璃弹珠,还有一对,各有五个瓣,像剥开后风干了的橘子。老李每天戴着白手套摩挲它们,它们也各有名字,这个叫狮子头,那个叫鸭子嘴,一天幸御一对,这个要文玩,那个要武玩,老李每天中午文武双全地去暴走,两个疙疙瘩瘩的核桃与他的激浊扬清运动相得益彰。对桌的小蒯,刚开了微店,天天在网上卖“战国红”——一种介于石头与玉中间的东西,微信朋友圈里每天都更新图片,但是杨树林从未见过她拿来任何实物。小蒯一度跟老李讨教过核桃,老李滔滔不绝地白话半天,把小蒯绕晕了,连称水太深,水太深。
他们沉湎于各自的世界不能自拔,办公室里仅闻核桃声。其实上次例会后他们只是打扫了一天卫生,就不知该如何“层层落实”老林的意图了。老李小蒯虽都研究文玩,但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如今他们也很少交流,与杨树林就更加地互相视而不见,他们从来不问杨树林鬼鬼祟祟地出去,又心满意足地回来,中间发生了啥。科技馆在非周末日基本无人问津,他没有什么事需要出去那么长时间啊?老李小蒯为何从来都不问呢?杨树林想,他们一定趁他不在研究过,甚至也去过小仓库看望远镜。管他呢!杨树林不管他们,自己又去研究望远镜去了。
他在里面有了好多发现。
在防波堤上卖海货的蛙人,隔两天就会抓上一只“大老参”,杨树林怀疑,他每次下海前,都会把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海参、鲍鱼装在腰间的橡胶袋子里,然后假模假式地在海里捕捞一番,再上岸兜售。所以挨冻受冷地下海,只是表演一番。有一个固定在堤坝尽头甩鱼竿的老头,蛙人一上岸,他就会走过来,蹲下挑三拣四,但是从来没买过啥。也许他是“托儿”吧,没准两人还分成。
潮汐是变化的,这一天是满潮,然后一天天地落下来,蛙人与甩竿老头出动的时间也随之推移,这几天,满潮的时间已经变化为上午10:00。
还有一个奇怪的人。高个头的小伙子,头发长,只穿了一条泳裤,他开了一辆小破车,不是比亚迪就是吉利,最早的那种款式。连续几天早晨,都是7点半左右从大海里上来,既不戴泳帽,也没有眼镜,游泳的姿式挺难看。上岸后,便用钥匙捅开后备厢,拿出一个大塑料水桶和一个水盆,然后就不见了。回来时,身上罩了一件巨大的白T恤。然后钻进车里,出来时,白色衬衣下摆都束到裤子里了,他对着车玻璃梳头,系领带,然后穿上黑色的西装外套,过一会儿,又用钥匙捅开车,轰地一下就走了。杨树林从来没见过这小伙子下海时是一个什么情景,每天7:30他来到望远镜前的时候,这小伙子就该回来了。有时天气好,大海中一片金光,小伙子的长头发都贴着脸,从海中一步步走上来,长相很像老电视剧里的霍元甲。有一集霍元甲被陈真推到河里,本来以为他活不成了,结果霍师傅抱着石头屏住气,硬是从河底走出来。那形象实在是太像了。杨树林用望远镜跟踪过这辆小白车,按它的方向,“霍元甲”是在华银大厦工作,那里有一家银行和一个大型房产公司,两个单位都曾与科技馆搞过合作,签合同时,都有严格的程序,接头的人都会说“我们的法务说,这里不规范”,然后再要他改合同,十分烦躁。写字楼里的人工装穿得整整齐齐,个个低眉顺眼,逢人就笑,胸前各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铜牌,部门经理则如入无人之境,眼皮基本不抬,两家公司的大BOSS都在顶楼,大BOSS什么扮相,杨树林无缘得知,总不会像僵尸博士一样,长一百多个头吧。霍元甲应该就是那忍气吞声的制服男之一,他从大海里爬上来,在那辆小白车里换好制服时,有一束光从他胸牌上反射过来,透过数百米和两组望远镜镜头后,依然灼目。霍元甲或许每天就是接合同、改合同、按法务要求跟各类客户走程序,他自己的程序也相当精确,每天早晨7:15都要到10度左右的海水里游一会儿,几乎是风雨无阻,也不管潮汐。那么高档的写字楼里难道没有浴室吗?杨树林有疑问。但是他随后就想明白了,霍元甲一进公司就得人模狗样,哪能每天早晨去了就洗澡呢?所以他的浴室就是后备厢里那桶凉水。他的车钥匙上会有一根橡皮筋,能套在手腕上,这暴露了他的爱好。杨树林想着,有点好笑,每个人都活得这么惨吗?不过,寒潮将至的11月,长发男人开一个小破车,后备厢里一桶淡水,是不是很可笑呢?
爱丁堡花园里的特斯拉男人,每天都雄赳赳气昂昂地出门,然后搬出他的摩托车占车位,杨树林发现,他与四楼那位靠窗练瑜伽的女人是一家人,男的也曾很偶尔地出现在飘窗前,看样貌体态,大概五十左右,女的看起来也就是三十出头,应该不是原配,不过谁知道呢?这年头,人们的年龄和婚姻状态都不太好猜。男人每天都在同一时间出门,锁车位,女人都在同一个时间做瑜伽。最近,女人开始使用器械,所谓器械,是一个挺大的橡胶球,女人坐在上面,一会儿伸伸胳膊,一会儿伸直一条腿,上身绷得笔直,却是摇来晃去,像小孩儿玩的不倒翁。孵卵的鸵鸟,杨树林想到一个奇怪的比喻,可是鸵鸟自己并不孵卵啊?
5
蛙人、甩竿的老头、像霍元甲的小白領、开特斯拉的老男人、做瑜伽的黑衣女子,这五个人现在成了杨树林最熟悉的人。杨树林每天一早就去望远镜里问候他们,然后一整天的时间,这五个人都陪着他。他们每天所做的事具有高度的规律性,场景、动作都十分雷同,假如拍成视频短片进行数据传输的话,时间和空间的冗余度很高,几乎没有什么“关键帧”。人生在世,关键帧并不经常出现,容颜易老,壮志常失,大部分时间都是多余的,杨树林想,就像眼前的这座科技馆,其实完全是一个垃圾时间收容场嘛。
杨树林每天在望远镜前思绪万千,这些魂飞天外的想法大概活跃了大脑皮层,促增了多巴胺的分泌,现在人人都夸他气色好。连馆长老林都罕见地夸过他两次,老林有老林的逻辑,他认为,大事即将降临,人人都有所准备,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是必然的。相比之下,李跃进则脚踏实地得多,他认为,杨树林神采飞扬,完全是因为搬家的原因,他说,天天坐公交地铁,呼入的都是浊气,所以他每天中饭后都要到海边暴走,为的是机体的呼吸。在朋友圈里,老李的步数一向是遥遥领先,他头发虽然少,但从头到脚都被太阳晒得黑黝黝,老李吸收了很多紫外线,每天下午都在办公室里激浊扬清,杨树林以前见了他就觉得矮了三分。现在不了,现在杨树林走到哪儿都觉得自己前呼后拥,老李再黑也黑不过蛙人和甩竿老头吧。杨树林每次想到这儿,都觉得底气足了很多。
大人物的信息迟迟没有更新,馆长老林的例会也进入了指令循环期,说来说去,就是要治慵治散,展品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以良好的精神面貌迎接每一位观众。科技馆里的观众百分之九十都是周末陪孩子来上机器人课的家长,他们东倒西歪地坐在大厅里的椅子上,来得晚了只能找个墙靠着,人手一个手机,屏幕的光照在脸上,蓝瓦瓦的,个个都像僵尸,下课音乐一响,僵尸们就集体蹦了起来,拥到楼梯口抢孩子,把自己的孩子一把拉进怀里,嘘寒问暖,一副对未来十分负责的样子。杨树林想,跟僵尸们有什么精神面貌可讲呢,他们不过是在这里打发冗余的时间罢了。家长对孩子的时间抓得很紧,一到周末就跑好几个课外班,而自己的时间就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他们在科技馆等,在少年宫等,在新东方等,在学而思等,时间被切碎后就不再是时间了,像一些破破烂烂的布条在风中摇来摆去。他几次想辩解,但是这时候霍元甲就会跳出来劝劝他:“杨哥,知足吧,看哥们,每天都得先物理降温才敢去上班,要不然,冒火啊。”说着,他从海水里面无表情地走出来,上小破车里换上西装,轰的一声开走了。杨树林的眼中泛起了光亮,老林收到了这束光,笑着对他点了点头。
与云娜的无声麻将好久没打了,但这天女儿房间的灯刚灭,杨树林就来了情绪,他发现自己满脑子都是做瑜伽的女人。虽然他看不清楚那女子的面貌,不过她的身材十分曼妙,尤其是翘臀。想到这里,杨树林感觉十分羞耻,不过他也在此小振奋了一下。云娜赶紧捂住嘴,从腹腔深处传来暧昧的一声,她满脸通红,指甲在杨树林背后用力抓了一下。
6
大人物如科技馆上空的五彩祥云,忽远忽近,杨树林想了一下,自己活到四十多,见过的唯一一位大人物是二十多年前在读大学时。
他曾做过一段校报记者,有一次,团委书记兼总编吩咐他去做一个陈姓老校友的采访。陈校友是工程院院士,光学仪器专家,据说,他在读书时就发明了一种叫“皮老虎”的照相机。杨树林在实验室里曾经看到过“皮老虎”,镜头像手风琴一样,可以伸缩。陈院士虽然是光学专家,但是他却是个弱视。他说,读书时,他总是早去,坐第一排,因为远了就看不清楚黑板,“像数学分析、线性代数这种公共课,在阶梯教室里上,我就自己备一架望远镜。”陈院士说得杨树林目瞪口呆,他记得院士当年六十岁多了,他的妻子看上去也就三十来岁,颇有些姿色。院士校友十分疲弱,问三句才能答一句,他十分歉意地对杨树林说,如今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连望远镜都帮不上忙,余生一片黑暗,作为一位光学科学家,想必是痛苦的。院士家住的是老房子,客厅里有七八个又窄又高的窗户,他的美貌妻子,那天正在一个小窗前收拾自己的化妆品。
杨树林为校报写了一个整版的人物通讯,叫《望远镜里的世界》,团委书记大加赞赏,象征性地改了几个字,还把自己的名字也添了上去。这篇通讯后来被《科技日报》转载了,那个栏目叫“科海甘辛”,《科技日报》的编辑还配发了短评。这个人物通讯评上了全国优秀科技新闻奖,杨树林得了两百元的奖金。团委书记刘卫东凭它评上了副教授,又调到系里当总支书记。刘卫东每回见了杨树林就会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跟他称兄道弟。那都是快二十年以前的事了。
杨树林就读的是东北的一个光学精密机械学院,当年,他学的光学仪器专业,还是十分高精尖的。毕业那年,VCD机卖得正火,刘卫东刚从广东考察回来,在毕业分配的动员大会上兴高采烈地跟同学们描述广东一家VCD企业的盛况,“卫西蒂机,就跟一本书一样薄,漂亮!一天就生产一集装箱,哗哗地运到咱们北方,全是钱。”杨树林就去了广东的这家企业,再跳槽到深圳的IT公司,虽然那里遍地都是财富传奇,但是他始终都没能进到这些传奇里。与大时代擦肩而过,云娜曾经这样形容他。
不过,擦肩而过的岂止他一个呢?后来听说刘卫东力主在光学系办了一个工厂,生产他崇拜的“卫西蒂”光头。现在VCD已经不见了,就连DVD也没有了,听说刘卫东办企业犯了点事,在学校里待不下去了,去了一家专门生产数字监控设备的公司。后来,他们的学校汇入了高校合并的汪洋大海中,杨树林已经不知母校现在叫啥名了。刘卫东消失了,他与学校的联系也就断了。那位院士校友,在七十岁左右时,突然“坠楼”。这个消息曾让同学们唏嘘了一番,不知为啥,杨树林倒是不觉得奇怪。
想起这些尘封往事,是因为科技馆突然要进行一次“专业技术人员摸底”,杨树林填了一份巨大的表格。表格上他的籍贯——那个海边的县城也并入了附近的一个区,中学、小学全都改了名,父母已经过世,大学校名如今已经查不到,他曾经供职的VCD厂、IT公司均已不知去向,所有的履历都像是伪造的,社会关系也显得极其虚弱。每个人都与这世界有着看似牢固的联系,其实呢?杨树林想,这牢固的联系其实说没就没了。
杨树林现在与世界的联系方式又重建了。每天早起送女儿上学,然后就到单位看望远镜里的老朋友。到了9:00,就去办公室里泥菩萨一样地坐着,午休时再去看望一下望远镜里的朋友——这时,大老参、特斯拉、霍元甲、老甩都已经不见了,鸵鸟也只是很偶尔地在飘窗前闪一下,她几乎不出门,除了做瑜伽,就是在客厅里的桌子上摆弄一台笔记本电脑,也许是在炒股吧。鸵鸟虽然很少出门,但是也很少拉窗帘,她与世界隔着一层玻璃。杨树林与她隔了三层玻璃,也许是五层,杨树林想,望远镜的镜头是成组的,说不清有几个镜片。
7
12月的第一周,绿岛就罕见地下了一场大雪。
周一,又要开例会,8:50,杨树林赶到多功能厅时,所有的同事已经罕见地全部到齐。等他在大家的眼光中找到座位坐下时,杨树林才知道,科技馆的新规划已经在《绿岛日报》上公示。在开发区,将有一个新的科技馆问世,投资50亿,占地300亩。新馆是由城投公司投资,进行完全的企业化运作,科技馆的老员工可以选择到新馆工作,不过要放弃事业单位编制,岗位要双向选择,在规划旁边有一个招聘启事,对专业人员的要求,是35岁以下,985或211大学工学硕士以上。他们也可以选择保留事业单位身份,等待分配。据说市里的事业单位要进一步缩编,可选择的职位不多,还有两个是在殡仪馆。
科技馆的原址,将改建成一个高端养老中心。
大人物不来了,据说在此前市里的踩点中,这一站就被砍掉了,踩点采取暗访式,这是小蒯在微信群里说的。单位有两个微信群,一个由老林作群主,满屏都是点赞的表情,另一个由小蒯做群主,小道消息满天飞,充满了抱怨与不满,这两个群杨树林都不怎么看,今天因为开会时间长,他阅读了所有的未读信息。
老林要回科协,任正处级调研员,老李正在通过玩核桃的朋友联系某个区的政协。小蒯小声地跟牛小菁嘀咕。
你呢?牛小菁問。杨树林想,牛小菁这是明知故问,小蒯的公公曾经当过组织部副部长,虽然已经退休,但总不至于办不了这点事。
杨树林开完会直接去了小仓库。望远镜四仰八叉地放在那儿。防波堤上有两行车辙,车辙的尽头,是一些水渍——霍元甲在雪天也没有中断游泳。大老参已经冬歇,老甩却依然独钓寒江雪。
爱丁堡花园里特斯拉的车位上,停了一辆执法车,警灯把雪地上映照出一片晶莹闪烁的蓝,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冒雪拆除车位锁,旧摩托车和破沙发都被清理了。
驼鸟家的窗帘紧闭。
杨树林扛着望远镜走出科技馆。
雪下得更大了。
责任编辑:卢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