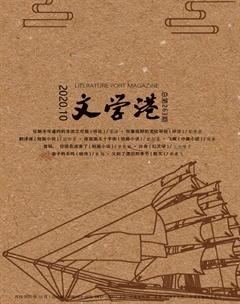化解不可通约的生活之可能
张涛
一
“翁教授虽然每年讲的都是新课,但每换一次新生,他就改变一次教课方式。每讲一次课,他都用一个关键字,这样便于记忆,因为他已经老了,还因为那些同学都还小,几乎接近90后。年纪小的和年纪老的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记事。课堂内容多了,不仅备课花时间,讲起来也费神费事,接受起来也有问题,内容太多,吸收不了,最后还是个还。不如每课或每天的课,集中在一个内容上,以一个字来概括。”同为老师,对翁教授的“良苦用心”感同身受;对翁教授面对的学生们的状态,同样是“历历在目”。因为职业的缘故,《翻译课》的内容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吸引我的主要不是“翻译”,而是“课”。翁教授还算是个用些心思上课的老师,但他在“课”上的尴尬遭遇,还是很让人唏嘘——
听到这里,学生都不做声,也不知道是赞许,还是反对,反正一声不响,也许是在等着教授叫他们,把第三句的译文念出来。
翁教授讲课,喜欢海阔天空地闲扯,把各种知识,融入讲课内容中,因为他认为,翻译就是一个杂学,但这些交了高昂学费的学生却有些不耐烦了,课上了半天,却连翻译的皮毛都没有触及,他们恨不得一夜之间学到全部技能,第二天一过,就能通过翻译考试,顺利取得移民资格,获得澳洲永久居留身份。看看他讲的这个阿罪的故事,没有引来一个笑声,估计没有兴趣,他就开始点名了:兵器!
思想的相互认同,不同见解的彼此争论,这都是课堂上的理想状态。但“一声不响”的沉默,也是如今课堂的真实场景。我们常说理想是对现实的反驳,但现实何尝又不是常常反驳理想。这种课堂上的沉默也正如翁教授“本次课”讲的“反”字一样,现实的课堂是对理想教学状态的“反”面。
翁教授课堂的尴尬状态,也与他的这门课有关系,他教的是“翻译课”,学习的学生也都是希望获得翻译的秘笈,一夜之间顺利通过翻译考试,获得移民资格。他们以为翻译就是一个“语言”问题,翻译也一定有标准的“公式”和“套路”,但“翻译”里简简单单的就是“语言”问题?翁教授自然明白个中道理,除了“语言”之外,翻译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现代语言学看来,文化就在语言之中,只能说明此理。如果不懂得一种语言的文化、历史,仅仅从“单词”和“语法”的角度进行翻译,难免会闹出类似于“常凯申”之类的笑谈,但是那些心心念念尽快获得移民的学生哪里关心这些,所以他们才会对翁教授的“东拉西扯”十分不满。除此之外,翁教授与学生们的隔膜或者代沟,也是造成他们彼此对“翻译课”错位理解的一个原因。阿城说过,“年龄”不是划分“代际”的标准,“文化构成”才是划分“代际”的重要标准。有相似的“文化构成”就是同代人,要不怎么会有“忘年交”?翁教授的“文化构成”就与他的学生们差异巨大。翁教授为了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讲了他在文革中经历的“趣事”——
他知道,这个故事只要一讲,定会活跃课堂气氛,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讲了起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中学读书,经常停
课闹革命,不是到工厂学工,就是到农村学农,在农村学农时,带队老师管得特别严,就连学生上厕所,也要叮嘱一句:去去就回,不要耽搁时间!班上有个不服管的学生,长得大头大脸,自己编造了一句话,就是上面要你们翻译的那段话,带着几个不怕事的学生,从老师面前走过时,像念经一样,反复诵读这句话,想故意惹恼老师。
这段“趣事”讲完之后,在座的学生依然没有反应,还是鸦雀无声。翁教授对此倒也应对自如,便迅速进入了正题。年轻一代对于翁教授们的“历史感”毫无体认。这或许也不能把问题全都算在年轻人身上。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就是教育,如何在教育中呈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也是一个大问题。同时,每一代人切入历史的“方式”是不同的,年轻人不大可能再像翁教授那样“亲历历史”,同时也不大可能以一种“正统”的方式切入历史。他们切入历史的方式,主要還是由当下的文化形态所决定的。这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翁教授对此显然是无能为力的。我想,不仅是翁教授如此,我们亦然。
二
翻译既然涉及文化问题,在两种文化转移的过程中,难免会触碰到各自文化中的一些禁忌以及文化的“变形”。
翁教授在翻译课上为了说明“中文之粗”与“英文之细”,就举了一个关涉强奸的案例——
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两种语言互为倒反,一个没有复数概念,另外一个却很在乎单数和复数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却不料暗中伤了那些文化不同,样子一样的人的感情,这使得翁老师很气馁,很郁闷。
因为班上的女生多,翁教授举的这个例子,让一些学生感到“惊恐”和“厌恶”。课后,就被学生“举报”了。好在学校的经理人不错,估计也了解翁教授,只是提醒下翁教授以后要多注意。
在《夜宿国王十字街》中,也有“翻译”的问题——
另一次我译约翰·厄普代克的一首小诗,也是关于做爱的,标题为“Fellatio”。这个字翻遍大大小小的中国人编的英文字典就是查不出来,让我气馁。找他问时,他显得有些窘,我这才发现自己时间地点都选得有些不对,因为马上就要上课,班上的人已陆陆续续到齐,就我一个人立在讲台前问他fellatio的意思,等我弄清这是“口交”的意思时,就轮到我发窘了,好在除我而外,那些读研究生的没一个知道fellatio的意思,最后我把那首诗的标题译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飞拉吮》。什么意思让人家捉摸去好了,反正国人有的是想象力。
上段引文中女学生对翁教授的“误解”,此段引文中我对乔的“理解”,其实都是牵涉“性别”与“文化”的大问题。无论是误解,还是理解都源于此。
欧阳昱的两篇小说,表面上都谈及了“翻译”问题,其实质是呈现两种文化或异质文化之间的隔膜或者是矛盾,以及国人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生存状况与文化境遇。
这两篇小说都涉及“性”的问题,我料想可能是欧阳昱觉得,这个问题更能直接地表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异质性”与“冲突”。正如在《夜宿国王十字街》中,“我”最后坦言:“我知道我又失败了。在性的问题上,你就没法和乔深谈,推而广之,你没法和任何澳洲人深谈。简言之,他们是不跟你谈这个问题的,对于他们,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好谈。”
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尚且是个不太容易的问题,更何况是不同文化与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翻译”与“适应”,肯定是难上加难。化解这些“不可译”或不可通约的难题,恐怕通过一种斯特劳斯所言的“自由教育”是一个可能的形式。这种教育是“在文化里或朝向文化的教育”,只有在最大限度上让不同文化相互融合,才有可能化解不同文化之间的隔膜与误解。只有这样,在跨文化语境中生活的人,才会安顿好自己的肉身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