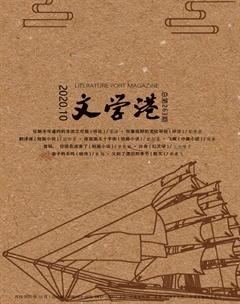翻译课
欧阳昱
翁教授虽然每年讲的都是新课,但每换一次新生,他就改变一次教课方式。每讲一次课,他都用一个关键字,這样便于记忆,因为他已经老了,还因为那些同学都还小,几乎接近90后。年纪轻的和年纪老的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记事。课堂内容多了,不仅备课花时间,讲起来也费神费事,接受起来也有问题,内容太多,吸收不了,最后还是个还。不如每课或每天的课,集中在一个内容上,以一个字来概括。比如他有一节课,关键字就叫“一”。还有一节课,关键字就叫“加”。再还有一节课,关键字就叫“切”。复习的时候很简单,只说“一加切”就成,虽然可能与“一刀切”容易弄混,但听了他围绕这些关键字讲的课,就明白是啥意思了。
今天这课的关键字是“反”。翁教授准备了三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句子,让同学们译成英文。一句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一句是:“他到柜台前买了一瓶可乐,就走回桌边。”第三句是:“管天管地,管不住我拉屎放屁。”除了最后一句,前面两句都应该是毫无问题的。至于说为什么把最后这一句拿到课堂去讲,翁教授自有他的道理。
他趁学生做作业的当儿,上网查了一下电子邮件,有倒是有几个,但都是垃圾邮件,一个说有几千万美元,要打到他账上,只要他在回邮中,把所有相关细节,包括个人信息都发过去就行。他立刻删了。这种好事曾经让他上过一次当,还往伦敦发过一个传真,上面不仅签字,而且盖章,搞得像真的一样,直到对方找他要500英镑的手续费,他才恍然大悟:果不其然,世上的确没有免费的午餐,而免费的500万英镑,那就更甭想了!还有一个邮件向他推荐阴茎扩张术。一看见“阴茎”二字,他就立即删了,同时警觉地抬眼往下面看了一下。还好,学生都在埋头做作业。第四个邮件更邪门,标题叫“揭露伊斯兰”,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默罕默德是个喜欢酗酒,猥亵儿童,怯懦卑劣的皮条客吗?”这个邮件这两天来,他是第二次看到,来者他不认识,名叫“Eloise”,而且还是群发。这很讨厌,不符合他的世界观。他想:如果把该句中的默罕默德换成耶稣基督,群发出去,接收者会同意吗?想到这儿,他手一动,又把它删了。
他看看电脑右下方的表,已经过了5分钟,就决定乱点鸳鸯谱,随便在点名表上按顺序找几个人来,口头念念上次布置他们做的作业。第一个点到的是一个名叫Linfung Ng的人。一看到这个人的姓,他就想笑,好容易才忍住没笑,因为他想起了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也姓Ng。那是英国华人作家毛翔青的长篇小说《余勇》中的一个人物。Ng这个姓,西方人不知道怎么发音,往往会把它拆解成两个字母,发成NG(恩基)。其实那是不对的。这个姓如果还原成中文,至少有两种解释,一是姓黄,一是姓吴或伍,在闽南语中是黄,在粤语中则是吴或伍。毛用英文写的那部小说中,为了让英语读者便于发这个音,而不是发成什么“恩基”,就借主人公“我”之口说:我这个姓的发音其实很容易。设想你便秘,使劲拉也拉不出来,你拼命“震”的时候,喉咙和鼻子里哼出的那个声音,就是我的姓。翁教授想到这儿,面露微笑,把Ng这个字用便秘的方式发了出来,立刻就有人应声,看来发音很正确。应声者是一个看上去像广东人的男子:宽脸,高颧骨,眼睛有点小凹,回答虽是普通话,但里面夹着粤语的尾巴。翁教授问他:“怎么样,第一句话译出来了吗?译出来了,那就请念一下。”
“Dear Dad and Mum: You are good!”
学生都笑起来了,其中有个笑得前仰后合的,是个瘦高女子,脸上显然化过妆,但仍然显得疲倦不堪。
翁教授说:你笑什么?你怎么译的?
“Dear Dad and Mum: How are you?”那女生说。
此话一出,笑声就熄灭了,再也没人吱声。
“是这样吗?”翁教授问。“还有没有异议?”见大家都不做声,翁教授看了看名单,就又抓了一个,念出声来:“Qi Bing!请问Qi Bing来了吗?”一念出声,他就自觉好笑,听上去好像“骑兵”,而且也不知是男是女,估计是个男的。在吉朗这个地方,为大陆学生办的这所学校,一切采取澳洲的方式,只用英文,不用中文,电脑打印出来的名单,都是汉语拼音,而且有倒置之嫌。
“Bing Qi,”一个怯生生的女声,从不知什么地方发出来,“是Bing Qi,不是Qi Bing。”
循声望去,翁教授看见一个极为瘦小的女生,缩在教室一个角落,似乎很为自己不该起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而感到抱歉,默默地看着教授。
“对不起,”翁教授先行道歉了,说,“第一句你没异议,那你第二句是怎么翻译的呢?”
“He bought a bottle of Cola and went back to his table。”
“好像很准确嘛,”翁教授说,脸上现出一种淡淡的嘲讽意味。尽管大家从他的评语中,也约略能听得出一丝讽刺的味道,但仍然觉得该句翻译似乎无可挑剔。前面那个姓Ng的广东学生说:“我觉得挺不错的。”
“是吗?”翁教授明知故问,但又不置可否地说:“那好,那好。”说着低头又瞧了一下桌上电脑边的点名表,看到旁边写了一个“P”,表示“present”(已到),就说:“Hua Jia。”全班又哄堂大笑起来。原来还有个不画画,却叫“画家”的人。
“老师,不是‘画家,是贾骅!”一个脖子瘦长,支楞着一个摇摇晃晃的脑袋,脑袋上竖着一堆乱哄哄的头发的小青年纠正教授道。
翁教授已经道歉过一次,这次发现自己又不得不为叫错名字而道歉,心底里有点儿不服气,就顺嘴溜了出来,当然那股小气,是冲着办公人员发的:“以后造表时,至少也应该把中文姓名放在汉语拼音后面吧?”他其实说过几次,但都未奏效,没人理会。想到这儿,他想起一个可说是笑话的历史故事,大意是说,当年华人淘金工甫抵澳洲时,要在移民官那儿登记才能上岸。一边是一句中文(都是粤语)也听不懂的白人移民官,一边是一句英文也听不懂的广东农民,大家只能比比划划。移民官为了把自己的英语提高到最能懂的程度,就把文字降低到最小限度,仅两个字:You(你)和name(名字)。一手按住下面的花名册,一手捏笔,指着面前那个戴着草帽,挑着担子的广东农民说:You。然后指着花名册上已经写好的名字一栏,说:Name?农民低头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咧开大嘴,一口粤腔地说:“阿华!”或“阿新!”无论姓啥叫啥,都是阿这个阿那个的,澳洲移民官一听,也不管那么多,就写下来:Ah Ket,Ah Sin,Ah Yeh,等等。你们有所不知,后来这个Ah Sin(阿罪),还成了澳洲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过是个反面角色。
听到这里,学生都不做声,也不知道是赞许,还是反对,反正一声不响,也许是在等着教授叫他们,把第三句的译文念出来。
翁教授讲课,喜欢海阔天空地闲扯,把各种知识融入讲课内容中,因为他认为,翻译就是一个杂学。但这些交了高昂学费的学生却有些不耐烦了,课上了半天,却连翻译的皮毛都没有触及。他们恨不得一夜之间学到全部技能,第二天一过,就能通过翻译考试,顺利取得移民资格,获得澳洲永久居留身份。看看他讲的这个阿罪的故事,没有引来一个笑声,估计没有兴趣,他就开始点名了:“兵器!”
“是冰齐!”瘦小女瘪了瘪嘴,说。翁教授从她那一瘪的嘴巴上,看出了不悦,但他不管。他要的是译文:“请念译文。”
“You can control the earth and the sky but you cant control the way I want to pull shit and release a fart。”(管天管地,管不住我拉屎放屁。)
“怎么样?”翁教授停下来,目光炯炯地环视四周,想让大家评述一番。但没人做声,甚至都没人笑,他就对大家说:“这位同学翻译得很不错呢,知道为什么吗?在我说为什么之前,我能不能再给大家讲个故事?”
男生那儿传来肚子痛的呻吟声,其实那是不想听的表示,但翁教授不管。他知道,这个故事只要一讲,定会活跃课堂气氛,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讲了起来。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中学读书,经常停课闹革命,不是到工厂学工,就是到农村学农。在农村学农时,带队老师管得特别严,就连学生上厕所,也要叮嘱一句:去去就回,不要耽搁时间!班上有个不服管的学生,长得大头大脸,自己编造了一句话,就是上面要你们翻译的那句话。当他带着几个不怕事的学生,从老师面前走过时,像念经一样,反复诵读这句话,想故意惹恼老师。
出乎意料,课堂上依然没有反应。翁教授当机立断,直接进入主题,说:这个译文译得之所以好,就在于这位——呃,这位,哦,这位名叫冰齐的同学,对英文的把握相当不错,尤其表现在英文的细微处,“the”字和“a”字上。知道怎么观察一个人的英文水平吗?不是看他是否长篇大论,也不是看他说得头头是道,而是看他“the”和“a”这两个最小的字母单位是否用得到位。英语学到最高处,就是看这两个字的运用,而且,最难的是知道啥时这俩字都不需要。
这时,班上一个穿花衣服的男学生愁眉苦脸地说:老师,你不是要讲“反”的话题吗,可你跟我们讲的这个,跟那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说着,乜斜着眼睛,看着旁边一个大胖男孩子:你说呢?大胖子身子往后一靠,椅子在他屁股下尖锐地“吱吱”叫了一声,说:是啊,是啊。
“看来,”翁教授说,“如果我不反,你们也要反了,是不是?”他顿了顿,接着说,“哎,你别说,中文的这个反了的‘反,还真是很不好译呢!”
接下来,他逐个指出了三个译例中所存在的问题,即在进入英文时,全都需要反其道而行之。“爸爸妈妈”译成英文,应该是“Mum and Dad”(妈妈爸爸),“买瓶可乐”应该是“bought a bottle of coke”(买瓶可口),而最后那个拉屎的“拉”,进入英文应该是“推”(push)。
“想一想吧,”翁教授趁着这个令学生措“口”不及,笑声此起彼伏的当口说,“这两种语言比较起来,究竟谁更符合逻辑,汉语还是英文?汉语几千年来都是拉,可你在拉时,有谁在那儿替你拉?你又何曾自己拉过?据我所知,人只有在便秘得很厉害时,才会自己动手去拉。你再想想,拉不出来的时候,你就会‘震,一个汉语里所没有,只有方言中才有的词,这个‘震的动作,就是英文里所说的‘推。这时,当然‘推比‘拉更符合逻辑,也更适合人类的大肠运动,对不对?”
本来还觉得翁老师挺乏味的学生,此时因这突如其来的“反”向思维而笑得团团转四面倒,反而觉得他很逗了。花衣服男生好不容易笑定,就来了一句评语:“老师,我覺得照你这么一说,来自贾岛的‘推敲一词,将来可以改为‘推拉了。”他立刻得到翁教授的赞许,说以后如果编词典,一定会考虑把这个新词也编进去,同时开玩笑说:“是啊,是啊,这事的确值得‘推拉一下。”
课讲到这儿,需要方便一下了。翁教授请大家继续做昨天发下去的其他作业,便走出仓库一般巨大的教室,一转身,钻入窄窄的甬道,来到走廊尽头的厕所,却失望地发现,两个紧挨的厕所间,女的那边是空的,男的这边却被占着。他即使再急,也不敢贸然走进女厕所,就只好干等着,同时在手机上查电邮。一个朋友从中国发来电邮,用的是英文,基本还行,但结尾在本来应该用“祝好”的地方,用了一个地道的澳洲式祝词,即“Cheers”,却用错了,写成“Cheer”。这就好像把“祝好”写成“祝”或“好”一样,总觉得缺胳膊少腿了。正这么想着,男厕所门开了,出来一个女的,是班上一个学生。翁老师装着没看见,仍低头查看手机,让那人挨着身子从旁边过去,回头望了一眼,是那个身子瘦小,却特爱穿高跟鞋的女孩,鞋跟高到走路左摇右摆,晃来晃去的程度。
翁教授走进去,把门在身后一关,就拉拉链解溲,抬头一看是没有天花板的屋顶,低头一看,咦,这是什么!马桶的水里似有红血,慢慢漾了开来。这一看不打紧,小便出不来了。这种事不用专业侦探也可弄清楚,八成是女厕有人,另一个女生如厕时,看见男厕没人,就钻进去了。这跟大学情况很相似。四楼的女生无论春夏秋冬,随时都可在男生宿舍来来去去,但一到夏天,四楼台阶就摆了一个告示:男生止步,不得上楼。即使到了澳洲,即使到了80、90后这一代,情况依然一成不变。那红的东西,翁教授打了一个寒颤,心说:怎么这么不注意!
如厕回来,翁教授开始了小组讨论,请大家就“反”的话题,举出几个当代实例。
一同学说:澳洲人对孩子的态度,跟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带孩子逛商店,孩子要啥就买啥,从没有个不字。澳洲人就不一样了,不仅不买,还要说服孩子,现在买这东西不合适,而且你又没钱,等你钱攒足了以后再买不迟。
翁教授听到这儿,就说:“我能加入一点我的内容吗?”同学们齐声说:“好!”
翁教授就说,有三个例子,能够比较充分地说明,中西文化呈倒反现象,这也是发达文化和不发达文化之间的常有现象。说着,他就讲了三个故事。
故事一。诗人S与智利女郎结为伉俪,育有一个美丽的女儿,今年三岁。一天,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和爷爷奶奶一起,在花园里闲坐闲聊闲玩乐。大人坐在帆布椅里晒太阳的晒太阳,看书的看书,聊天的聊天,就让孩子在草地上跑呀跳的,很开心地独自个儿玩着。忽然,孩子跌了一跤,哭了起来。说到这儿,翁教授卖了一个关子,问:“假如这是你的女儿,你们会怎么做?”男女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了起来,一下子竟分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尽管猜得出讲的都是一个意思:肯定会跑上前去,把她扶起来。翁教授得意了,说:你猜怎么着?孩子的爷爷和奶奶坐在那儿,脸上笑呵呵的,一点也没有急着上前去扶孩子的意思,甚至都没有想从椅子里起身的感觉,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孩子从跌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吧。咱们小时候不都是这么长大的么?可诗人的智利太太就不同了,赶快跑上前去,把孩子扶起来,给她拍本来就没有的灰,还不断哄呀劝的,叫她别哭。“你们看看,这是不是一个文化倒反?”翁教授说着,又讲了第二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诗人告诉他的。当“诗人”两个字从翁教授嘴里冒出来时,班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声音里似乎听得出几丝嘲弄的意味,但当翁教授问他们为什么笑时,他们的笑声又立刻消失,真像来得快也去得快的墨尔本的阵头雨。这个故事更跨国,讲的是一个智利男友找了一个瑞典女友,在阿根廷被盗,身无分文,于是瑞典女友就打电话回家,找她父亲借钱,注意,不是要钱,毕竟父亲是个家有豪宅豪车和豪华游轮的富商,就算找他不是要钱,借点钱总可以吧,何况女儿在国外遭难,应该不成问题。翁教授这回没让大家猜,因为不用猜也知道,女儿的富豪父亲一分钱都没借给她,反而振振有词地说,你已独立成人,应该独立地处理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包括你目前所处的困境。谢谢你能想到我并来找我,但是很对不起,我帮不了你的忙。女友告诉男友后,气得男友破口大骂,差点把两人关系和两家关系都弄僵了。不过男友很快偃旗息鼓,毕竟爸爸再“坏”,没有他,女儿也生不出来。
讲到这儿,低头一看手机,时间已到中午1点,是吃中饭的时候了,翁老师挥挥手,说:吃饭吧。下午再来。希望能听到你们的“反”动或逆“反”故事。
中饭回来,在电梯里,他遇到了上午那个跟子高得人走路都两边打晃的学生,但此时,他们同处一台吱嘎作响,大约有百年历史的老电梯,他发现她矮了许多,眼睛便不由自主地往下看去:哦,穿的是拖鞋!学生见他疑神疑鬼的怪样,脸上憋不住地露出一个笑,问:“老师,你吃饭了?”翁教授说:“是啊,你呢?”“也吃了。”这个他想不起名字的学生说。他想问她叫啥,又怕她笑他记性这么不好,就干脆闭嘴不言。
一开始上课,翁教授就直接进入主题:正如英文汉语的造字,常有男权主义作祟,比如,英文把历史(history)当成“男人的故事”(his story),汉语把“嫉妒”加上“女”旁,算作女人特有,虚空中似乎还有另一只手,在操纵这两种语言,把它们隔得如此之开,就像处于地球的南北极地。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因为它只是一种现象,只要加以注意并谨慎对付就行。我们呢,还是接着上午,继续讨论一下两种文化中出现的倒反现象好吗?“梅里美,”他往下看看点名表,脱口而出,念出这个名字,因为它的写法就是如此:Mei Li Mei。
“哎!”一声尖脆的小叫,从中间靠墙的地方发出。他一看,哎,这不就是那个先高跟,后拖鞋的女孩子吗。原来她叫这个名字!
“老师,”大眼睛——他这时才发现,她的眼睛有多大——的女学生看着老师说。“我叫李媚媚,不是梅里美。”
翁教授再瞧一眼,不觉“哎呦”了一声,说:“真对不起,的确是Mei Mei Li,而不是Mei Li Mei。看来,我老花眼了。”
学生中早有眼尖的人,看见翁教授双鬓已经发白,虽不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星光,但至少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夕照了。
翁教授清了清嗓子,說:“这样吧,既然我错了,那就该罚我一次,但我想先问一下,各位有知道梅里美是谁吗?”大家都说不知道。翁教授想,这些小家伙呀,读的不是会计,就是工程学,再不就是媒体,对文学一窍不通,也不屑于了解,再往下走,文学就要失传喽。于是,他讲起了法国文学家梅里美的一篇小说,说这篇小说中的父亲,因为自己的儿子经不住金钱诱惑,而出卖了一个革命者,就把儿子当场枪毙了。
“这也太过分了点吧。”一个学生说。
“儿子怎么不反抗,把枪夺过来,当场把他打死呢?真是!”说这话的是翁教授从来不正眼瞧的一个重如泰山的肥女。因为她口出此言,他倒是认真地正眼瞧了她一下:很轻蔑的笑容,很不屑的面相,很不耐烦的姿态。
“好了,好了。”翁教授说,“你们看看,这不正是一个倒反现象吗?十九世纪用以说教的生动事例,到了二十一世纪,竟然为你们所不齿。这就像我当年一个大学同学,看了《欧也妮·葛朗台》后,竟对吝啬的葛朗台大为欣赏,觉得是一种值得学习的精神。”
一学生举手说:“老师,你看这算不算。我觉得西方人都很讲集体精神,而我们却很个性化。比如,外国人举行澳式足球赛期间,大家一窝蜂地都去看。对我们这些不感兴趣的人,他们还很瞧不起,觉得好像有意跟他们隔绝,而我们在这儿,都是各就各位,互不来往,自由自在地来来去去。”
“好,很好。”翁教授赞许道,“你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倒反现象,那就是,本来在中国很讲集体精神的人,离开本土,来到外国,哎,其实这儿不是外国,而是澳大利亚,而他们也不是‘外国人,而是澳大利亚人,你自己才是‘外国人,对不对?”等到笑声平息,翁教授继续道,“一到澳大利亚你就发现,原来你在此地已经没有了家乡那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一个个都成了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这也难怪,本土以外的国土上,失却了文化凝聚的胶泥,成为散沙也是很自然的,而散沙本身就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可你看看澳大利亚人,也就是你们常挂在口上的‘外国人,他们走到哪儿都是集体的、家庭的、社会的,很少有单独的,因为这儿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扎的根好像隐而不见,但却深广扎实。”
“老师,”那个被错叫成“梅里美”的女生说,“你不是要问我什么问题的吗?”
“哦,”翁教授说,“很对不起,我已经忘记要说什么了。这样吧,我就讲讲我知道的一个倒反故事,好吗?”
他知道学生已无太大兴趣听,他们有的在看手机,有的趴在桌上睡着了,还有的支起个袖珍电脑,戴着耳机在上网看录像,邻座的头也凑过来,时不时地笑出声音。翁不是个拉得下脸,凶猛批评的人。对这些孩子——他在内心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只要他们开心,自己也开心,大家都能学到一点平常学不到的东西就行。
这个故事,又是一个跨国的,又跟诗人有关,内核依然是倒反。他是那年去伦敦,在一个诗人家里吃饭,听诗人谈起来的。这位诗人长期侨居伦敦,与一位英国白人小姐喜结良缘,生了一个中英合璧的千金。孩子小的时候,夫妻常为一些家常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其中最为经典的一例是,有一天孩子发高烧,诗人提出要打电话叫救护车,英国老婆硬是不肯,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只要把澡池里放满冷水,把浑身发烫的孩子泡在里面,再到加油站去买几袋冰块,放一袋冰块压在孩子额头,就能物理性地把高温去掉。试想,在一个中国家庭,无论男方还是女方,如果有谁提出这种方案来解决孩子发高烧的问题,两人一定要打得水不落石也不出,绝对没完没了。
讲到这儿,翁清楚地听到了一声鼾声,它此起彼伏地从那个肥人女生鼻子和桌子之间的缝隙间发出,同时伴以阵阵笑声,那是两个同桌正在看录像——希望他们不是在看黄色录像——翁教授这么一想,都好像觉得被自己的这种想法而玷污,就立刻提高嗓门说:“大家注意听了,我现在要你们把这句话译成英文。”说着,他把遥控器拿在手里,按了一下键,在等电脑屏幕在墙上出现之时,在文档里打了这几个字:
反了,反了,你们要造反了是不是!
肥人女生被点醒后,不知所云,头重得直不起来,就又扑通一声掉下去,“叭”地砸痛了,忙不迭地揉脑袋,还狠狠地盯了翁教授一眼。
翁教授视而不见,眼睛转到Ng的身上,对他说:黄姓同学,请你译一下好吗?他估计,这个学生要译出来,至少也要十分钟。没想到,Ng同学立刻脱口而出,说:“Anti, anti, you going to rebel is not.”
这一下,全班笑惨了。睡觉的笑醒了,看录像的笑停了,不笑的都笑了,笑的都笑大了。只有翁教授没笑。他问:“你的译文来自何处?”
见他如此严肃,Ng同学只好从实招来:“是谷歌翻译的。”临了还补充一句说:“怎么,难道不行吗?”
翁教授来了精神。只要提起谷歌翻译,他就恨恨有声。这个东西貌似强大,什么都能翻译,但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把黄金翻译成垃圾。比如上面这句,完全没有“反”的感觉,把“是不是”这种反问句,译成了一个完全说不通的“is not”。更有甚者,它把“反了,反了”,标签一样机械地译成“anti,anti”,看似正确,其实相差十万八千里。说到这儿,一件近事浮上心头。
最近有个客户找他,请他翻译一份合同文件,他赶天赶地,起早摸黑地完成任务交稿,这个客户却几十天如一日地不付钱给他,被他催急了,就来了一句:“其实你译的东西,还不如谷歌好。我把原文放进去,一分钱不要,眨眼译文就出来了。”这件事把他恨得牙痒痒,就立刻通过律师,向那个胡搅蛮缠的客户下了一纸催款单,虽然最后解决了问题,但关于谷歌的那段奇谈怪论,令他不提谷歌则已,一提便要大张挞伐。最后他下了一道禁令:在我这儿学翻译,一律不得偷懒,不得滥用谷歌翻译。发现者分数为零。
这天下课之前,也是这篇文字结束之前,翁教授讲了一个业界衡量翻译的标准,大家闻所未闻。澳大利亚的翻译公司,一般都由白人主持,所译语种世上有的它都译,不单单限于中文,但它通行一种校对校验方法,俗称反译,也就是当公司的白人头头想知道一篇英文译成中文后,是否有漏译或误译情况发生,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反译”一下,让译者B在未看英文原文的情况下,把译者A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这一来,头头只消两相比较,立刻就会发现问题所在。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翁教授说,“有天公司请我来做这个译者B,让我把一篇中文译文译成英文。我在一个地方看到‘马杀鸡这三个字,颇感犹豫。我当然知道它指按摩,但译文并没有注明,而是直接用了一个众所周知、带有谐谑性、打了引号的音译。无论如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反过去的时候,我就把它译成了‘horse killing chicken。”
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笑例,一般讲到这儿,都会哄堂大笑,但这次笑的音量和面积远不如以前大。估计时候到了,该就此打住,干点正事了。可翁老师这个人,一旦讲得兴起,有时就会忘形。此时就是他忘形的时候,竟然讲了一件法庭的典型案例。他完全没有料到,学生中起了一阵颤栗的微澜,其中的恐惧和厌恶情绪,被他完全错漏过了,且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第二天中饭时分,白人经理请他到办公室去一趟。翁老师端着微波炉转过的饭盒进去时,特德正在打电话。瞥见他进来,就用手指了指门前那个位置,要他坐下。他坐下来,不知是什么事,心里有点忐忑不安,只听见对方说:All right then. Can I have your number please?
听到这句话,翁老师习惯性地试着译了一下:我能有你的电话号码吗?不行,他想。这句话不能这么译。看来,只能反其道而译之:你能把电话号码给我吗?
正想到这儿,特德挂了电话,走过来把门关上,对他连寒暄都没有,就单刀直入:“翁老师,有学生反映,说你昨天讲课有些不好的内容。”
“我说什么了?”翁老师说。
“哦,”特德说,“你是不是跟他们讲了法庭的案件?”
“是啊,”翁老师说,“但我在讲案件之前,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并告诉他们说,想听的举手。大家都举手了。”
特德,没跟他计较,只是说,今后遇到此类敏感的话题,要尽可能小心处理,毕竟女学生比较多。
哈,翁老师头一下子大了。女学生?谁是罪魁祸首?他把教过的脸一张张想过去,也想不起谁是可能打小报告的人。这件事情,也没法去跟学生核实,那多难为情呀。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自己的嘴巴管紧一点。
其实,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为了说明中文之粗和英文之細这样一个倒反问题,而用了一个颇为生动给力的法庭事例,是他从一个译员朋友那儿听来的。大意无非是说,在一次涉及指奸的强奸案中,当女证人被问及,男犯把几根指头伸进她的性器官中时,她说的是“指头”伸进,译员却把它译成“fingers”,即复数的指头,导致该案急剧戏剧化,男犯罪加一等,直到朋友译员把中文的无复数向法官解释了一番,又较为准确地把“指头”二字译成“finger or fingers”(一根或多根指头),然后让法官追问究竟几根指头,才从女证人那儿得到了比较准确的回答。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能够说明两种语言互为倒反,一个没有复数概念,另外一个却很在乎单数和复数之间的细微差别,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却不料暗中伤了那些文化不同,样子一样的人的感情,这使得翁老师很气馁,很郁闷。这个早已加入澳洲国籍的华人老头子,第一次感到了不开心,从此决定,不再以“反”字为题,讲“反”的内容了。谁知道今后还会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面情况呢?
回到家里,翁老师把下周“反”的内容提前取消,那是一首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其中的“前不见”和“后不见”,如果译成英文,就要变成“后不见”和“前不见”了。正所谓汉语之“前”,即英文之“后”,反之亦然。但是,他对此兴味索然,不想再钻“反”角尖了。就这样吧,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