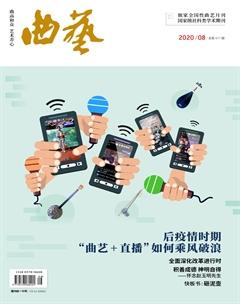浅谈相声直播的新局面
胡克非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许多计划,工作、生活、学习及文化娱乐等多方面的停滞让人们始料未及,而对舞台艺术来说则更是影响巨大,剧场的关闭、文艺演出的推迟和取消,让许多本就生存艰难的艺术团体举步维艰。
无论是茶楼、书场还是小剧场,缺乏舞台对曲艺人来说,失去的恐怕不仅仅是短期的收入。当传统艺术舞台不能满足或是不能全部满足人们的需要时,尤其当疫情袭来,人们被迫在家,几个月的时间足以让人们远离曾经的生活娱乐方式,或是说因为替代产品的足够优秀,让人们的注意力发生了转移,多年来培养的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也在悄然被打破,至此,传统舞台艺术尝试转型恐怕已是迫在眉睫,这其中就包括相声。
“相声+直播”兴起的必然性
即便不发生疫情,相声本身也需要转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活成本和压力成倍增加,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逐渐呈现碎片化和快速迭代的特点。人们对文化艺术有全新的需求,曾经我们认为艺术与观众理所应当的某些共存方式逐渐被消融、分解后,催生出新型的业态和产品。回到相声演出市场来看,近年来,随着大型活动、晚会等活动的减少,曲艺的舞台逐渐减少,除了中国文联及各地文联举办的专场演出外,就是各地市场化的相声社团为广大曲艺爱好者提供的文艺产品。随着大浪淘沙,各地的相声小剧场在经历了一次淘汰和整合后,绝大部分在经营模式、生存理念、发展方向上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相声作为舞台艺术,和戏曲相似,它是一门人的艺术,无论是角儿、名家还是艺术家,总是一个群体中掐尖的人,作为爱好者和观众,欣赏这类演员的演出无疑是既过瘾又舒心的。但事实证明,由于相声班社的相对分散,每个团体中真正拥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数量并不充足,再加之创作达不到人们对曲艺的需求,在核算成本后,许多观众不再接受去小剧场试错,当然,拥有成熟粉丝群体的偶像艺人除外。于是,足不出户地看到相声行业内所有的佼佼者成为了人们希望达到的目标,视频平台就给了这样的机会。
这些年来,视频平台通过版权交易的方式,和许多包括相声在内的曲艺团体合作进行整合打包后的分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播技术日渐成熟,人们不断开掘新鲜的内容,直播技术从最初的游戏直播发展到后来的秀场、文艺展示再到如今的相声,人们可以通过终端以付费或免费的形式收看自己喜欢看到的相声演员和节目,这对喜欢相声的观众来说更精准,成本更低,而由于拍摄录制的技术手段的先进,人们观看相声的体验反而更好。人们对直播形式的追捧说明,这样的产品满足了人们在其他形式中得不到满足的需求:
首先是人们更加垂直化的兴趣爱好。由于人们审美和喜好的分众化,想要一个产品拥有所有人的好评已经不可能了。但在直播平台,用户可以自由地选择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主播,以成本极低的方式达到满足的目的,选择主播变得无比自由与个性化,也许是因为才华,或许是因为颜值,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选择是用户自己决定的,而且他们放弃的成本也很低,一旦不爱看了,不想看了,随时可以结束。
其次是陪伴。这一点尤为重要,直播帶来的陪伴感可以对冲背井离乡、生活压力等负面情绪所带来的孤独感。主播的声音、面孔和日常直播的时间,都成为了一种陪伴方式,类似于婴儿傍晚的“睡前故事”。而直播技术的支持,让每一名用户都可以随时与主播进行沟通和互动,这样的互动更加深了陪伴的黏性,拉近了主播与用户的距离,人们逐渐习得新的习惯,而这种习惯背后最大的动因是满足了人们的心理诉求。
人们的时间,尤其是碎片时间是有限的,选定了一些文化娱乐的方式就势必会放弃另外一些,而直播带来的娱乐新方式,带来的全新舆论氛围和话语场,造成了大量的新用户涌入,这里既包括传统相声的受众,也包括传统相声的目标受众群体,当然更多的是非相声的广大受众。在这样的信息模式和分享圈子的体系中,人们的欣赏口味、欣赏风格、欣赏模式在发生变化。随着资本的进入,商业模式一旦建立,那么它就具备了一条完整的链条,“存在即合理”便发生了。而疫情的暴发,使人们减少了外出活动,社交频率的降低倒逼多行业进行转型突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今年上半年,相声直播的兴起变为了一种必然。
直播对相声发展的意义
疫情期间,尝试直播平台的相声演员并不在少数,但更多的表演形式只能称之为才艺展示,而不能叫作相声,或者说是带有相声元素的直播形式,当然由于相声演员自身的积淀带来的观众群体,会通过刷礼物或者是购买产品等方式进行消费,也有一些演员在尝试直播平台的过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但是这样的收益能否变为常态,目前看来依然是未知的。
更多的演员采用了和观众聊天的形式,来保持自己的曝光度和增加自己的亲和力,比如讲述学艺的故事、台前幕后的见闻,与观众分享自己对相声的理解,以及通过和老艺人的连线来呈现不同代际曲艺人的坚持,这些从内容上来说都不错,但是并不是相声本来的样子,而观众有没有兴趣在直播中坚持听完整的相声作品,这同样是未知数。
通过直播平台获得持续的经济收入也绝非易事,随着直播带货的逐渐冷却,在线下没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到了线上除非脱胎换骨,不然依然没有太多的吸金价值。演员明星的带货能力直线下降,头部主播的价值凸显的情况下,曲艺人去尝试直播带货绝非是能长期解决生存的方式,那么单纯通过打赏和刷礼物,对于大部分曲艺人来说则是杯水车薪。
那直播对于曲艺是否就完全没有价值呢?并非如此。拥抱互联网、直面受众的最大利好便是信息和口味的收集,通过直播平台,面对自己的受众,相声爱好者可以最快地获取人们对这门艺术的期待或是想法,这样的方式是在以往的所有时代都不具备的。相声演员应该在接触移动互联网的过程中,分析用户的心理需求,勾勒他们的画像,真正地去感受观众所需要的艺术形式的内容,这和前辈艺术家们口中所说的深入生活其实是一件事,只不过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了线上罢了。
直播行业中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奥,在没有这个名词之前,对于艺术而言,大数据就是所谓的采风、深扎和体验生活,只不过分析的不是机器而是演员本身。一名优秀的曲艺演员必须具备这样的能力:收集信息、整理信息后进行分析和思考,最终反哺自己的创作和表演,这就是直播平台能带给相声演员最大的价值。通过直播相声节目,对这种表演方式的感受和尝试,可以给下一阶段复工复产后的舞台表演提供更多的素材和内容支撑,而通过拉进与观众的距离,也能让更多的观众和演员产生陪伴感和共鸣感,这对接下来的艺术生产生活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目前看来,直播在未来给相声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可以达到某种补充的作用,例如当人们在相声小剧场中欣赏完一场节目,散场后意犹未尽,演员们可以利用回家通勤的时间进行直播,和观众进行即时的互动,吸收演出本身的评价和反馈,观众也可以通过直播平台拉长自己对文化生活的满足感,这样的直播互动可以增强观众的黏性。
某些相声演员也可能将当下的传播方式和直播平台优势发挥到极致,在直播中找到自己更好的生存价值。不过到那时,这样的表演形式是否还叫作相声,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争论。
相聲直播的内容生产
很多相声从业者都对相声下过不同程度的定义,“语言的艺术”“使人发笑的艺术”“带有讽刺的语言艺术”等,但这样的定义对行业内的从业者可能重要,但对受众来说并不重要,人们无心去探讨相声的定义究竟为何,而更多的是索取,也就是“我要从这门艺术中获取什么”。
绝大部分相声爱好者对相声的美好回忆来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声作品,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甚至更早的相声的一些录音作品,这些作品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可能已经不符合当下普通受众的审美需求了。不过,梳理这一时段的相声作品不难看出,无论是相声从业者还是相声段子的内容质量,都可谓是优秀,再结合当时的社会风貌、文化追求和相对匮乏的物质生活,于是很多人喜欢上了相声,通过相声排解生活的压力,进而欣赏相声艺术中的精妙之处,但每一名观众爱上相声,都不是因为一下子被精妙的艺术所打动,而是被艺术的表象感染,这是一个因果的问题。在被表现感染之前去探讨艺术的精髓,是没有价值的。在那段时间中,相声演员脱离传统的剧场演出,去拥抱广播电视,这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的尝试,这样的尝试也让相声借助当时先进的平台找到了更多的受众,也培养了更多的消费者。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生活的现代化发展,娱乐方式有了多样的改变,多种载体的涌现,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人们的眼界和口味发生了变化,电视这一媒介的弊端也逐渐显现,相声无论是从时长容量、表演内容、表演方式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乏力感。有人说人们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喜欢相声这种表演形式的,实则不然,近些年相声小剧场的火热和每年人们对春晚的语言艺术的期待可以看出,人们从来没有厌倦相声这种表演形式,厌倦的其实是表演内容。
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是大众喜欢的?所有艺术形式都一样,首先是真实感和亲近感,让人欣赏后感觉不到不适的作品,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我们听到了太多让人不适的作品,作品本身并没有艺术表演或是技术上的太多问题,而更多的是内容上的问题。有一些相声段子的内容不是日常生活中交谈的内容,它们高高在上,内容空虚,口号生硬,让人们失去了从相声中获得的愉悦感,这本身与载体无关,这样的内容无论是在广播、电视上,还是在现在的小剧场或者是互联网中播放,都不会有任何市场,因为人们不想在下班后还要接受任何文化活动中出现的空话、套话。随着时代的变化,载体的改变是一种必然,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应该拘泥于载体而故步自封,无论是何种载体都相当于只是提供给演员们一个舞台,而在不同的舞台上如何“舞蹈”才是艺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一段时期的内容变味,才是导致相声观众流失,最终走向分化的根本。
当然,这样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性,绝非某一两名相声演员个人为之,而是一个群体选择的结果,这样的选择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样也是一种必然,这也正是当年小剧场出现,又一次让人们眼前一亮的原因。
小剧场的出现,拉近了观众与舞台的距离,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参与感和仪式感的同时,在内容上,一反之前时期的生硬作品,而采用更鲜活更适应人们审美趣味的内容,一下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了相声的美,而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到了曲艺的乐趣。《买猴》《夜行记》《纠纷》《打电话》《虎口遐想》《小偷公司》这些作品无一例外在当年都是新作品,人们不可能100年不变去听《黄鹤楼》《八扇屏》《洪洋洞》《怯拉车》《学大鼓》这样的作品,即便这些作品是老先生们口中的经典。
但随着小剧场的发展,同样出现了内容的问题。由于演员们周而复始的演出,不再有老先生那么多充足的时间去观察体验生活,甚至许多年轻人短短几年就完成了学习相声到登台演出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生存,部分相声小剧场开始通过相对低俗的语言和不那么高明的笑料来拉拢观众,这样的结果是满足了生存但同时却在消耗观众,因为低俗没有底线,当某一天人们看着舞台上的低俗作品却满足不了时,他们依然会放弃这门艺术。
归根结底,疫情带来的大众生活娱乐方式的改变只是加速了行业的转型,将行业本身的问题暴露出来。从长远上看,这并非坏事,对于艺术来说,更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相声,它从来都是在改变、学习、融合中进步发展的,重要的是寻找到人们的需求,然后去满足它。
目前看,线上娱乐并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但会对人们的审美风格产生影响,对于相声来说,内容、节奏方面都需要相应的调整,一门艺术要往前发展,总是要不断调整和进步的,站在今天看昨天,直播是更先进的平台和媒介,而站在明天看今天,直播也许只是一个节点,相声从业者应该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借力的问题,更多的还是相声艺术究竟要向何处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