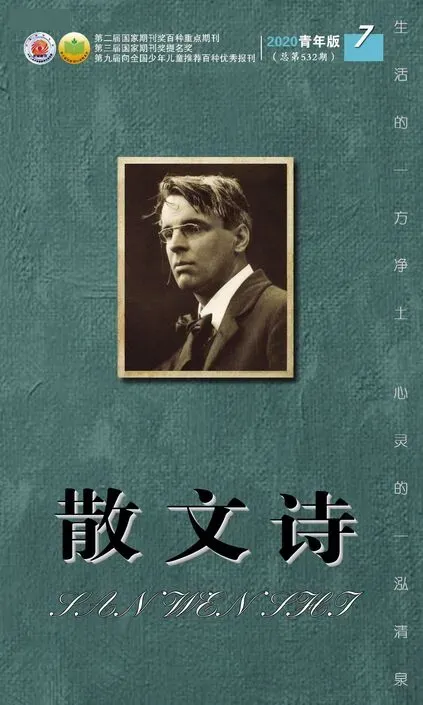“为我们剪下词语”
——“思”之信札
庄 庄

图/曾丽霞
一 初冬的夜, 已有了丝丝寒凉。 这是我喜欢的季候, 伴随着大气的下沉, 我的身体终于听见某种落定的暗示, 而本能地放缓了自身的节奏, 开始向着一汪宁静的湖泊张开, 并在细微的预感中获取秘密的辽阔和远方。 是的, 我安静了下来, 而不是像夏天那样, 在无休止的热浪和蝉鸣中总是在经历着内在的昏暗和紧张。你称我为敏感体质, 因为这种季节变化激起的明显带有个人性的波澜。 在停笔半年之后, 身体的局限得以克服, 随之而来的, 是一种表达愿望地被唤起。 而我的每一次表达, 都希望你在场, 仿佛那是更为安全和恣意的, 是一种更深地守护和鼓舞。 如同我相信, 当我从 “思” 之暗夜中一次一次地归来, 你必会在黎明和朝霞中迎候。 如同我相信, 循着心灵的地址, 这些不曾寄至案头的信札, 必会经你连心的十指一一打开。
一直以来, 我都在告诫自己, 要对那些因袭的、 固有的认知心怀警惕。 时间, 更像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仪式, 日升日落之间,汹涌而至的日常总在向着每一个我们所能触及之物流泻、 覆盖,那么盲目和强大, 滚雪球似的, 越裹越紧, 于是, 我们目力所及,往往只是表象。 而我相信每一个事物都会发光, 相信有一个内核的东西在黑暗的岩层里闪烁、 呼唤、 渴求。
尽管更多的时候, 我茫然于并不知道用什么来去除这无所不在的遮蔽, 但总是, 会有那些闪现的瞬间。 当我凝神于某个突然来到的事物, 它可能是某个事件、 某段记忆、 某个词语、 某种幻象、 某个人, 或者更多的, 是并无对象的指向一种形而上的空茫,此刻, 因出离纷乱而抵达的宁静的愉悦, 使时间显得如此完整,并从未如此清晰地被标识为 “我的时间”。 这样的时刻, 我视为一种隐秘的创造, 因为它越过庸常而抚触到一颗温暖清澈的 “思”之心。 你知道, 那些夜晚, 常常, 于清寂中, 我泪流满面, 因为这种 “思” 之喜悦还有某种难以言传的类似对时间和未知的乡愁。
在我看来, 这才是值得珍视的, 在那些人所共见的表象时间之外, 当我们短暂地抛开生活的纷繁和肉身的重负, 专注于来到和发现中的事物, 我感到视觉被关闭了, 带来污染的眼睛不存在了, 只有黑暗让你开始重新体认和找寻, 慢慢地, 就会发现那些来自自身的光, 那些原本孩子般安睡的事物, 就会呢喃、 说梦话, 或者站在黑暗尽头的微光里向我们招手。
你看啊, 他们是如此鲜活多汁, 如此灵性盎然, 正是借助他们, 我得以保持自己的温度、 湿度, 以及孩子般的天真和柔软,来对抗僵硬的生活和日益枯竭的生命。 “为我们剪下词语”, 并非要将 “思” 局限于语词, 而是, “思” 和语词本来就是同时展开的。 又或者, “思”, 有时会先于语词, 但最终, 它要依附于词, 依附于和它有着同样的音调和振动频率的词 (在最高限度上默契的词), 才能承载 “思” 之曲折、 迂回、 盘旋。
我只是要保留这样的时刻: 当那些被庸常紧锁的事物偶尔挣脱约束而在心灵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 一种全然自我的气息——萦绕、 震颤, 在突然而至的光中如蝴蝶翩飞。 “为我们剪下词语”, 即是通过语言的选择在貌似平静的整体中剥离出一个创造的自我、 生长的自我——为我, 为我们。
二 我从未相信消失。
在我的生命里, 任何经历和体验过的东西, 即使形体和轮廓被时间溶解, 即使发生的时空流逝或转换, 它们仍然以碎片或信息的形式得以在我的体内居住。 自然, 因为强大的遗忘, 它们可能丢失或损伤了那些显而易见的部分, 但作为一粒种子般的元素, 它们只是暂时或长久地安静下来, 蛰伏在大脑和身体的最底层。 一旦有哪怕是最细微的触发, 它们将恢复沉睡的知觉和弹性,并如此默契地呼应着现时的生活, 进而它们在新的时间中得到重塑, 并完成又一次的在心理上的铭刻。
如此反复, 一个貌似消失或远去的事物总是在记忆、 想象乃至虚构中获得更加蓬勃的活力。 这绝非简单的重复, 而是一种丰富和赠予, 相比于遗忘, 更是秘密的幸福和慰藉。
这首先在一种童年经验上得到印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龄的增长, 我们所经历的世事尘埃一般, 总在一层一层地叠加, 总在淹没那个田埂上、 溪水边的童年影像。 然而, 不管时间过去多久, 即便我早已来到生命的中年, 那个懵懂羞涩、 桃花般绯红的孩子总是在穿过晨雾、 穿过暮色、 穿过乡间窄窄的小路……是的, 总是。
我仿佛依然站在正午的阳光下, 春天的时候, 满眼的油菜花一路铺陈, 蜂群在带着甜味的空气里来回穿梭。 它们有着多么干净的金黄和耳语, 我听见了, 那纯金色的回响。 而现在, 我依然听见, 并感知满腔的蜂蝶在我的内部飞舞。 我相信, 这样的听见和飞舞同样在你之中持续, 因为我们拥有一个相同质地的童年:70 年代的农村, 物质的匮乏、 人情的淳朴、 自然的生态, 农耕的散漫和自由。
而日后当我深究我的内在与我所经历之物的关联, 我是如此感激那个 “散漫和自由”。 它一开始就为我拆除了那些横条竖条的栅栏, 让我像一匹小野马, 在田野和野花的辽阔里疯跑、 嬉戏;让我在无人管束的窃喜里伴星月, 听虫鸣; 让我无限地滑入不着边际的遐想并依此编织自己的内心。
是的, 那个依世俗时间的逻辑早已终结的童年, 已经化入气血, 并在记忆和怀想中一次又一次地凝固成形, 一次比一次清晰,一次比一次鲜活: 那扇动着透明的翅膀、 时刻准备飞起来的孩子。
正如现在, 当我写到它的时候, 它在我的话语中再次到来。
三 这是一个被死亡标记的上午。
人们在谈论他。 一个陌生者, 在夜晚的黑暗中, 自26 楼向下, 把自己交给了血色漾开的大地。
人们在反复谈论他。 他因此在我的意识里反复地坠落、 坠落……那样决绝和急迫, 犹如电影中不断重现的镜头。 就这样, 一个与我毫无关联的人, 通过死亡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我。
这是否意味着, 他以更隐秘无形的方式在延续着他的生, 甚至在一个毫无交集的人的脑海和意识里。 这看似有点荒诞, 但它真实地发生了, 在两个全无瓜葛和亲缘的人身上, 生和死, 完成了一次对接。 自死亡那锯齿形的粗糙的边缘, 我把自己嵌入了进去。
其实, 从一开始我就预感到, 这样的表达会有一些艰难。 但这样的主题值得我们一再伸展语言的触角, 从不同的点面和维度去试探, 去接近, 直到它得到至少是我们自己认为的较为精准的表达。 或许, 我想说的是, 死亡并不代表终止和结束, 而是从未停止它的衍生和繁殖,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 不但从未关闭什么, 还反而如此生生不息。
在我大约六岁的时候, 死亡第一次向我展露了它苍白、 幽蓝的面孔。 多年以后, 当我回想起, 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不甚明了的冬日阳光、 被槐树遮蔽的隐约的天空。 那一天的晚饭时分, 场院里的邻居开始穿梭, 夹杂着急促的说话声和脚步声, 说是二爹爹没了。 我挤在人堆里, 看见二爹爹躺在自家堂屋的地上, 青衣青鞋, 身上盖着红绸被子。 那双鞋, 白底上缀着黑色的圆点, 冷硬而恐怖。 离我那么近的一个人, 活生生的, 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 这自然是一个六岁的孩子无法懂得的, 而那双充满鬼气的鞋, 成为无法摆脱的死亡意象, 一直悬浮在我的脑海里。
在对死亡的恐惧中, 我小心地甚至神经质地活着。 我小时候一直怕黑, 怕影子, 怕乡下的夜里各种无名的声响。 晚上躺在床上, 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有无数的黑云朵在飘, 夹带着一些闪着金光的火星。 等我在惊恐中打开眼睛, 一切又无影无踪。 如此反复。 要是雨夜, 我总会听见一双雨靴由远及近、 由远及近, 但永远走不到我的门前。 而檐下的雨似乎永远也不会滴完, 不紧不慢地敲打着我的神经。 这是一段梦魇般的时光, 我感到某种灵异的气息总在我身边围绕。
多年以后, 我亲历了父亲的死亡。 悲伤的五月, 用短暂到窒息的几分钟, 阻断了一切。 那一天的父亲躺在一张粉红色的床单上, 像是沉入永久的睡眠。 父亲照例被换上一身青衣, 趁着他的手还有些许温热, 有人在他的手中放了桃枝, 让他握着。 另一只手握着半把桃木梳, 梳子是我平时用的, 另一半留在我身上。 我看着父亲, 没有了儿时的恐惧, 我竟觉得他那么整齐地像是去赴一个约会。 死亡, 在这一日, 竟然有着温和平静的面容。
在对死亡的体验中, 一个转换生成了: 从最初的恐惧, 到后来平静的悲伤, 再到现在的死即重生、 生死同一。 这并非我找到了解脱之道, 只是生和死的对峙在认知里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而另一层面, 当生死的边界变得模糊, 其实质是我们每天都在生,也每天都在死。 是的, 无人可以取消这种宿命: 越接近越荒凉,越接近越虚无。 因而, 我一直试图通过写作来尽量保留一些气息, 以证明生命的曾经在场。 如果你读到了太多的疼痛、 太多的沉重, 请原谅我还没有找到更为轻逸的方式。 但请去除那样的忧心, 请与我一道, 照看悲伤但永不熄灭的内心。
四 语言, 在我看来, 远非书写的工具, 而是存在本身。
因此, 语言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存在, 无疑是对一个书写者功力的考验。 事实上, 在个人的书写中, 当我试图用自己的语调说出存在, 我感到了面临的无数漩涡和困境: 浪涛会吞噬我, 高墙会阻挡我。 渴望中有如春天的话语——新鲜的生长的话语, 还在冰封的途中, 等待我前去认领。
这种困境首先来自语言与物的距离。 是的, 曾经, 我如此信任语言的烛照和洞见。 而有意思的, 却是越写越清晰地看到了那个“距离”, 不可穷尽, 越走近越遥远, 越凝视越两眼皆空。 就像是在暗夜里行走, 凭借星辰赐予的微光, 紧追一个缥缈游移的背影, 却从未赶上他的步伐, 更无缘目睹宛如源头的真容。 是自我的眼睛蒙上了太多的灰尘以致视物无以清明, 还是物的本身被太多的纷乱和神秘包裹而被捆缚? 或许, 幽暗是双重的, 人和物都需要一个双方心领神会的密码, 才能完成对接和向彼此打开。 这让我想起阿拉伯故事里的 “芝麻开门”, 多么童稚和美好的发声,皆因无障无碍的天真呼唤而宝藏洞开。 那么这个密码的寻得, 定然会排斥语言和思维的添加和繁复, 而是返归一个自然的仪式:让事物在语言中找到它们质朴但谜一样的本名。
其次, 还有语言与自我的距离。 从表面上看, “语言” 由“自我” 来说出, “自我” 是 “语言” 的场所, 仿佛有着最近的距离, 而事实上, 我始终感到这种距离是难以缩短和消弭的。 这源于自我的多重性和多变性所带来的复杂和神秘。 一个人内心任何微小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打断语言的节奏, 犹如黑暗的海上航行, 注定要承受偏离带来的波涛、 起伏, 甚至搁浅。 生成中的语言将会成为碎片的浪花飞溅, 当它再次汇入汹涌的语言之海, 已瞬间变得踪迹全无。 这时, 将要重新寻找一种语言的方向。 如此反复。 因而, 用语言说出自我是如此艰难和难以确定。
我还想说的是语言与他者。 语言与自我相距尚且如此遥远,更遑论他者。 更多的时候, 不同的人因内心构造的不同而在心智、 思维方式、 语言习惯、 感知力、 想象、 直觉等方面会存在极大的差异, 这差异像尖利的冰山, 难以消融。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从不期待大众的眼睛和耳朵。 我要找寻的是与我同质的人, 这个 “同质” 表现为在对外部事物和隐秘内心的观察中,“思” 的起点和落点拥有一片共通的水域, 任凭他们各自波涛汹涌, 他们总能听到对方自幽深的水底传来的呼唤, 并作出应答。只有这样的耳朵才会把另一个人的言说听成充满意义的悦耳之音,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穿过语言的迷雾, 而真正到达另一个生命的栖息之地。 而当我在语言与物、 语言与自我的距离中无端损耗的时候, 我惊喜地发现了你, 一个同质的人, 一双灵敏的耳朵, 在守护, 在倾听, 包括我的笨拙之处。 为此, 我想说出感恩, 说出朝霞, 说出那迎接我们的语言的曙光。
五 当时间来到新的一年, 它仍如镜子般平静。 我知道, 它的下面, 深不见底。 没有什么能激起持久的波澜, 一次次短暂的飞溅之后, 重又归于黑暗。 我们来不及找到痕迹、 缺口, 更无路径。这让我们深以为苦的水平面, 是令人绝望的玻璃之镜。
是的, 我们总是受缚于时间, 犹如困兽之于牢笼, 既回不到过去, 也看不见未来。 这时, 我想, 我们应该容许自己从一个小心翼翼擦拭镜面的人, 变身为一个鲁莽者、 冒险者: 当我们松开手中之镜, 至少将得到无数的碎片。
也许你同样意识到了, 在这样的困境里, “碎片” 是多么美好的礼物。 正是在这一打碎中, 暗喻着重拾、 拼接、 修补和重置的无数可能, 也就是说, 时间开始从一个无望的客体转换成我们可以参与的可感之物。 这让我对时间的绝望得到缓解, 我的心胸因此一度充满了某种喜悦, 这也让我确信, 时间是可分的, 可挽留的。
当我开始凝视过往, 我意识到, 如果我们把时间设定为通常比喻的流水, 那么, 只有那些淹没过你的头顶、 打湿过你的衣衫、濯洗过你的双足的波涛和浪涌是属于你的。 只有这个在我们的记忆和意识中铭刻下来的时间, 才会因为获得个人的印记而不朽。这样的时间, 尽可不断地添加自我的各种信息而使其变得日益丰富而最终形成自我循环的时间之流, 或者, 自己将会变成一个时间的容器。 这远非对时间的征服和占有 (对此我们永无可能), 而是一种有效的联结和重置。 依此, 我们似可找到一个个为我们的生命所曾经经验的清晰可触的时间截面, 它的纹理, 它的路径,或能带给我们对未知的某种方向性的探寻。 而那正是朝霞升起的地方, 是我们的生命从陈旧走向永新的地方。
而那些无法与我们的生活和经验互证的时间, 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 一种氛围, 一种类似中国写意的晨雾, 它来过, 却不能被表达, 亦不能被抓住。 它漂浮, 它是 “梦的时间”。 它需要被安放在我们心灵的上界, 与我们的尘世生活遥相呼应、 互为联结。
(注: “为我们剪下词语” 出自策兰 《低处的水》 中 “无人从心墙上为我们剪下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