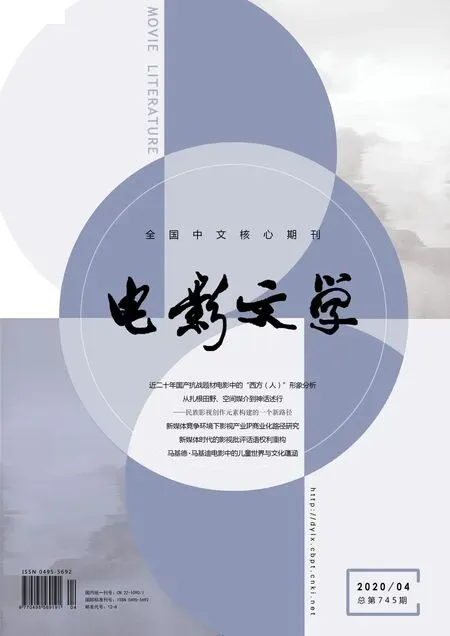新世纪蒙古族题材电影的民族主体性表达
黄肖嘉
(内蒙古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我国边疆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建构是在网格式的线索交叉中进行的,既纠葛于个人与历史、性别与政治、身份认同与非同一性的矛盾,还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张力。人作为“人自身”的主体性是现代文艺的意义焦点,体现在人的有限存在与历史先验条件的矛盾关系,“人是一个奇怪的经验——先验对子”。“民族”是人的集合,其主体性也充满个体偶然性与先验必然性的互相作用,“我们生存的时代,我们种种生理上的能力,我们的母语等,虽是偶然的,却也是难以改变的”。而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主流文化核心,不易产生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故须强化其与内地汉族共享的历史记忆。“就中国而言,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并不仅是一个民族自决的过程,而且也是创造文化同一性的过程。”如此,少数民族主体性的文艺表达成了复杂的话语场域。
具体到电影对此问题的思考,蒙古族题材影片是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便是《内蒙春光》,《东归英雄传》等“马上动作片”重启了类型电影探索,《天上草原》又是我国第一部数字电影……因此,它们对民族主体性的表达也有标本意义。
总体而言,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民族主体性表达走过了“潜抑—高扬—犹疑”的轨迹。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草原上的人们》等为了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对民族文化元素做了汉化处理,谈不上主体性表达。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成吉思汗》等通过钩沉本民族历史传说与文化仪式,试图重建民族主体性。由于意识形态环境较宽松且现代化副作用尚未暴露,主体性表达姿态是高调坚定的。蒙古族题材电影也扣合了这一脉络。
21世纪以来,民族主体性表达逐渐呈现出网格式姿态。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价值取向都在转型,民族主体性表达也充溢了意义的犹疑,不仅面临边缘民族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更遭遇了令双方都深陷其中的现代性焦虑。所以,新世纪影片以个体对历史的游离、私人性别对公共政治的隐喻、身份认同欲求与同一的不可能为横向线索,以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为纵向线索,伴以电影语言探索,使民族主体性表达成为网格式的互文场域。当然,这种表达是未完成的,对某些时代征候的解决也是想象性的,关于真正的民族主体性“是什么”及“如何建构”的探索仍处于“在路上”的状态。
一、历史表述:游离在历史轨道之外的草原民族个体
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甚至“人在其本质上是历史的”,因此文学艺术首先要对历史进行表述。而阐述历史离不开个体的人,没有脱离个人而抽象存在的历史,也没有与历史完全割裂的个人。“如果个体的命运中没有表现出普遍适用的、有代表性的规律,那么我们就没有解决具体人的描写问题。”所以电影中的个体人物是观照影片历史性的切入点,也是本民族主体意识的表达出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蒙古族题材影片都在民族个体的历史境遇中书写民族主体追求。但新世纪情况的不同在于,影片弱化了民族个体对历史的积极干预,强化历史对个人命运的操控性。并且,“去边缘化”的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加微妙,因为少数民族在试图摆脱边缘位置时又遭遇了由现代性话语入侵带来的文化疼痛,而主流意识形态也遭遇了这种疼痛。这令蒙古族主体性建构不得不面对多重价值的挤压和定义困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许多影片都盛赞了蒙古族群个体对历史的积极作用。如《成吉思汗》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歌颂铁木真母子的勇武博爱对民族发展的影响;《骑士风云》《悲情布鲁克》中的草原英雄则力挽狂澜,或保护革命者,或消灭日寇。这样,个体有能力掌控自身命运与历史走向,令负载在个人努力上的民族主体性书写也是明确而自信的。
然而在新世纪的影片中,草原民族个体面对战争风云变幻、文化价值裂变、城市工业文明扩张等历史图景变迁,没有了那种掌控局面的自信,被抛到历史轨道之外,对历史的主动行动力也渐趋弱小,在传统与现代话语系统中都遭遇了人格分裂,无所凭依而又焦虑地追寻着本民族主体精神的安放地。
这种“被抛离”的境遇主要表现在影片叙事打破了空间与时间的封闭性。《嘎达梅林》中牧人的草场被卖掉,《季风中的马》中的乌日根在牧区与县城之间来回奔走,《红色满洲里》中的刘平安走出家门往来于车站草原等地,《长调》中的其其格从草原来到城市又回到草原,《雕花的马鞍》中的阿拉坦离开草原去参加世界马术比赛,《蓝色骑士》中的巴勒尔要到离草原“很远很远”的地方生活……空间的开放也带来了时间的变动,多种异质话语在流转的空间中展示了时代变迁的拼贴画面。如嘎达梅林离开草场是因为代表农耕文明的军阀要在此放垦,乌日根的奔走是因为乡里要退牧还草,刘平安穿梭于家里、车站与草地是因为要掩护中共代表穿越国境,其其格往返于城市和草原是因为歌唱事业的变动……
异质话语的侵入带来了空间与时间的开放性,使蒙古族的主体情怀无法稳固定位,民族个体无法再如从前那般创造历史,其命运轨迹游移不定,在传统与异质话语中都遭遇了撕裂般的错愕。比如嘎达梅林固然拒斥农垦,可他在王爷府里也只是低等的“梅林”;刘平安固然因革命任务而牺牲,但那位喻示古老草原意象的牧马人也没找到“成吉思汗的八匹骏马”;阿拉坦固然因赛马输给了公司董事长而沮丧,可他依靠传统牧业换来的家当也价值无几;其其格固然在城里伤透了心,可她在草原上重新唱出的长调仍然嘶哑走调……这些微观叙事昭示着蒙古族个体在环境的逼迫下无法融入任何一种历史语汇,被放逐在真正的历史之外。
个体命运的游离和对历史干预能力的减弱源于“稳定”被打破。影片中最先出现的草原、家庭等生活场景无疑是传统的符号,而传统话语的核心是稳定,民族主体性正是附着于此。“文化本来就是传统……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而异质的现代话语追求变动不居,“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21世纪以来,稳定的游牧文明价值观已不适用,新的城市工业文明价值观又尚未固定,历史异化为外在于个体的力量,个体无法准确地表述自我身份。乌日根、其其格们的窘境指涉了本民族以历史主体身份进行自我表达的困境。
这种由现代异质话语入侵而导致的“稳定”崩毁不仅是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所经历的,同样也降临在主流意识形态头上。这共同的现代性焦虑迫使原先处于“边缘/主流”关系两端的少数民族主体性诉求与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张力态势更加复杂,并使草原民族个体与大历史轨道之间的疏离感愈发明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蒙古族题材电影欲以自内而外的“表达”、而非自外而内的“窥视”角度来取回曾被弱化的“表征权力”。影片只须用成吉思汗、草原母亲等历史典故以及蒙古包、马头琴、长调、马群等器物作为叙事起点,便可重现这些文化元素的独立存在价值。因此,影片的历史态度乐观,对民族主体性的定位是肯定的。但是,21世纪以来的创作语境是多重话语的角力场,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紧张关系既表现在“各民族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日益的全球化”焦虑,也表现在“民族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妇女、同性恋群体等边缘群体对他们的社会权利的要求”。我国也经历着“全球化/反全球化”忧虑,以及内部文化的多元化挑战。在此语境中,不仅少数民族个体无法顺畅地参与历史,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也同样需要不断重标自身在现代性大历史中的定位。由此,基于历史思考的蒙古族民族主体性表达便在历史周围进行着“力图参与/易被抛离”的徘徊。
为了在视听层面完成此类历史表述,许多影片对电影语言也进行了探索。如《红色满洲里》中的牧马人既与革命事业无关,又找不到成吉思汗的骏马,带有历史游离者的意味。为了传递这种神秘的修辞效果,影片让这一形象反复出现,却不用清晰的近景镜头来拍摄,而有时让它在景框边缘若隐若现,有时从弱逆光角度为其面部打上阴影。再如《季风中的马》在结尾处用空镜头来表现草原中央出现公路的视觉不协调,并结合景深长镜头,让一匹瘦骨嶙峋的马从远处慢慢走来,让马作为象征物在前景上的形象更加突兀,弱化现实感,强化个体与大历史的疏离,也对蒙古族民族主体性的存续做出满怀不信任的猜测。
然则,个体与历史的不快有时又是在历史横断面上浮现出来的,表现为意识形态的意义扭结点,且常常隐匿在男女感情纠纷一类的琐细之事的背后,这便需要对影片的性别表述进行剖析了。
二、性别表述:作为意识形态隐喻的性别伦理
在中国的文艺传统中,男女情爱从来不仅属于私人空间,更是一种公共空间中的意识形态隐喻,如《诗大序》在阐释《关雎》时曾云:“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固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
中国电影史上关于性别伦理背后意识形态隐喻的探索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女性》《丽人行》《太太万岁》等便已肇始,多以女性解放来暗指社会进步。蒙古族题材电影受到主流惯例的影响,为个体性别赋予公共政治品格,在80年代后也开始了性别书写。但因蒙古族文化曾属于被展览、被欲望观看的客体,所以性别表述也携带了民族主体性思考,如《黑骏马》便“用汉族知识分子和蒙古族少女的爱情故事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两个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新世纪的蒙古族题材影片多以女性的性别悖难来映照本民族在社会转型夹缝中的主体性困境。女主人公难堪的情感经历背后是社会机制的运转难题,无法回答民族主体意识与同样面临转型的主流体制如何相处的问题,这是性别伦理对意识形态的建构。只是,这种建构藏在小格局的男女婚恋背后,是隐性的表述。
《珠拉的故事》与《图雅的婚事》均讲述了一名女性与两名男性的感情纠葛,看似为非政治化的生活碎片,但个体性别难题折射了社会公共话语层面的问题。嘎拉对珠拉的爱之所以欲说还休,是因为他在草原火灾中受到牵连蒙冤入狱,养成了内向倔强的性格,而他从未想过为自己的错案申诉。这表明,珠拉与嘎拉、拉西之间感情矛盾的深层原因是国家机器的运转失误剥夺了个体的人性权利。同时,珠拉等女性的性别符号还有另一层所指。导致嘎拉入狱的火灾是拉西带着城里的女友来草原烧烤野味时引发的,这意味着造成情感不畅的深层原因是文明的龃龉。拉西女友代表城市生活,这对草原这个前现代空间来讲是一种尖锐的异化力量。珠拉与城里女友标示了二元对立的文化争衡。于是,珠拉在私人感情中的胜出便不能不引申以对蒙古族群主体精神的召唤。
图雅的境况与珠拉相似,在情感尴尬主线的近旁闪现着诸多意识形态碎片。她之所以不顾谰言而“带夫出嫁”、扑向早有预示的悲剧结局,是因为她在独自劳动养家时累得腰椎病变,被迫以此来为家人争取经济来源。她的悲剧在于其性别宿命很难确立在与社会元素的关系中,而只能归入家庭内部逻辑。她也曾走出家门去劳作,但这是对传统女性性别功能的僭越,“男人与家庭之外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天地相联系,而女人则与私人的、居家的心思相联系”。她很快便被挤到社会经济秩序之外,而当她试图回到家庭、归还本不属于她的性别权利时,才发现僭越的代价是惨痛的,她的哭泣宣告了“归还”的不可能。
在图雅的悲剧里,意识形态与公共话语是一种“在场”的“缺席课题”。与嘎拉一样,她不可能获取自己从未听说过的社会资源来改变潦倒的状态,如大病保险等,而只懂得依靠男性。因此,图雅的悲剧既是性别伦理的悲剧,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难堪。无论女性的情感多么丰富,她们也无法直接获得大历史的命名,却又充当着大历史的牺牲品。不过在特定语境中,公共领域或大历史的某些深层矛盾属于话语禁忌,对它们的言讲只能采取“去公共化”的策略,将个体在社会角色层面的绝望隐遁在小女人的性别痛感之后。为了在感官上传递这种难堪,影片刻意强调人物“呼哧呼哧”喘息声的同期声写实与写意效果,以此渲染带夫出嫁这种令人不安的人物关系,并且用颜色艳丽的浓粉色嫁衣与暗色调的环境形成对比,使嫁衣颜色显得格外刺眼,也使焦虑的氛围无处不在。
此外,图雅再婚前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插曲。靠石油生意发了财的宝力尔先向图雅示爱,但她却选择了无能的离婚男子森格,只因森格愿与她留在干旱的牧场。宝力尔的石油生意与蒙古族文化格格不入,是典型的现代工业符号。图雅留守牧场并接纳森格,说明她执意固守本民族原态文明,但这是徒劳的。最终,性别伦理、意识形态、文化冲突形成了三维张力,民族主体自由面临着从多重夹缝中突围的考验,影片由此成为“身体的意识形态/第三世界文化中的民族寓言”。
不过,女性的性别尴尬固然源于民族主体精神诉求与“主流—公共”话语间的不快,更暗示了后者自身的困境。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加大,带来了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剧变,不断调整的政策法规代表了剧变完成之前的社会躁动和迷惘。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一元性被打破了,也在重寻价值定位。如此,性别尴尬的意识形态隐喻并非单义的“边缘/主流”“私人/公共”话语之争,而是在民族传统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咬合不平与各自本身的发展考验纠结于一处之后,为民族主体性表达带来了艺术语境的错综变化与内涵空间的延展余地,让研究者在以性别为断面来思考民族主体性时看到更多的意义细节。
只是,在历史表述与性别修辞的基底上,蒙古族作为少数民族族群的代表,其主体性表达最终要着落在民族身份想象上。而构建民族身份想象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便是让本民族所特有的、具备象征含义的地域空间——草原——反复出现,来强化民族身份的符号标志。
三、身份表述:边缘空间的精神救赎价值
21世纪的蒙古族影片对本民族身份的塑立表现为以草原为鹄的引入“还乡”母题,以及对巴赫金所谓“时空体”的构建上。许多影片让漂泊在外身心俱疲的蒙古族个体回到“草原”这个在地域与文化层面均属边缘的独特时空体,为草原建立一种“精神救赎者”的身份想象,用特有的民族文化情结来表达主体性诉求。
草原情结源自蒙古族的精神祖先——出身草原部族的成吉思汗和他的勇士,“真正的蒙古人……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后代蒙古人多以此为精神归宿。前现代中国的还乡母题是对生命来源进行诗性想象后的安全感诉求,如《广雅·释诂》云“生,出也”,将生命的产生视作一种离开,并试图回到熟悉的生命之源,“熟悉的处所、人、物体以及事件肯定了基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到了现代,还乡母题在现代/原始的争衡中建构文化身份。“身份”与“认同”都有“同一”之意,二者的英文拼写均是“identity”,词根iden即“相同”。还乡母题将文化个体安置在与之具有同一性的文化群体中来赋予它独立的身份。在蒙古族题材里,草原在整个民族主体性层面上为个体身份命名。
自从《重归锡尼河》《黑骏马》等开启了蒙古族题材电影的还乡叙事,草原这个边缘所在便成了承载公共记忆中的“安全感”、为蒙古族群提供精神救赎的独特空间,围绕它所展开的人物悲欢也造就了一种乌托邦文学式的“时空体”。
在巴赫金看来,“时空体”是指文学艺术话语中时间/空间维度的不可分割性。“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所以,文艺作品中的空间不仅是地理概念,也带有特定的象征意味,搭载了所有的时间记忆以及存活在记忆中的民族文化存在感。许多在城市生活的蒙古族人已不熟悉真正的草原,但经过一代代的文学记忆强化,草原仍是蒙古族群的情感认同点和文化身份符号,救赎着失落了的民族主体精神。
新世纪以来的很多影片都选用了“返归草原”的情节框架。《天上草原》中的城市男孩虎子因家庭剧变而变得阴郁,被送到草原后才恢复心理健康。《寻找那达慕》中的赵星是城里的网瘾少年,被送到草原牧民家后,不仅戒掉了网瘾,还懂得了人间温情。《长调》中的其其格在音乐会上失声,回到草原后却重新唱出声来。《雕花的马鞍》中的高娃是回到草原才选出真正的蒙古族骑手去参加世界马术比赛的。《锡林郭勒·汶川》中的牧民布仁将地震孤儿带回锡林郭勒草原。
这些在草原上达成的创伤治愈均是想象性的,在影片文本内外留下了叙事裂隙与现实经验残余,对蒙古族群文化在现代化社会中位置的指认似有强行命名的嫌疑。事实上,接受过城市文明的蒙古族人很少再能适应草原游牧的生活方式。围绕草原重建蒙古族群的地缘联系,让“草原民族”作为民族主体性实现的阐释,这只是乌托邦化的解读,反而造成了关于现实的乡愁。相比之下,《蓝色骑士》对现实的逼视更加犀利。萨蒂毕斯坚决反对女儿嫁给卡车司机,而逼她嫁了一个“真正的牧人”,可女儿婚后并不幸福。当儿子长大后也向城里私奔时,萨蒂毕斯再次盛装骑上心爱的坐骑追上去,但这次他发现自己与坐骑都已苍老,终于放儿子远行。萨蒂毕斯身穿被蒙古族视为最圣洁的蓝色长袍、高踞马上睥睨着孩子们的形象是一种雕像式造型。当影片用中景平视镜头把他的蒙古袍与儿子的牛仔裤、他的马与儿子的摩托车放在同一个景框时,只能传递出两种文化之间的不和谐,承认弘扬民族主体性这一愿望达成的艰难,对草原的诗性想象也面临着被解构的危险,这也是电影这一艺术门类对民族主体性表达所尽到的艺术责任。
然而,在这些影片中,草原这一特殊时空体尽管只在想象层面做出了救赎的姿态,但这种想象仍是必要的,因为建构同质化社群只能通过想象,无法将每一个个体的特殊性都作为划定民族意义边界的考量因素,“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想象不是捏造,而是要通过强化成员的共同生活意象来增强族群内部的认同感。探索民族身份,就是要探索某种政治与文化想象的建构情况。
如此,在新世纪的蒙古族题材电影中,草原的叙事价值便在于试用还乡母题的结构,以特殊时空体的面貌在社会心理层面为蒙古族群提供情感支点。尽管现实层面的“返归草原”很难实现,但不妨通过电影中反复出现的草原意象,为拥有草原情结的人建立同一性想象,强化彼此同源的民族身份意识。观众也可以悬置用返归草原来疗治文化冲突夹缝中的个体心灵创伤的可行性,而应从电影这一文化产品在社会意义网络中的位置出发,看看它如何推动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以及如何证明一种民族文化在精神层面实施自我救赎。这种民族主体性的表达方式不仅参与了影片情节,也回应了新世纪以来文化多元化的现实语境。
显然,进入21世纪后,许多蒙古族题材电影显露了更为鲜明的民族主体性诉求,并在历史、性别、身份三条横向线索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间张力的纵向线索铺排下做了网格式的表达。影片对蒙古族个体在大历史面前的无力与疏离、个体性别尴尬背后的意识形态难题以及草原意象对民族文化身份的想象性救赎进行了电影艺术所能触及的思考,以期框定本民族的主体性存在。但因当今社会的新媒体层出不穷,消费需求此消彼长,诸多外部因素影响着电影创作的内部动力,影响着一个民族对自身文化的审视角度和书写方式,所以,所谓的民族主体性表达其实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也是所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今后的意义增长点。鉴于此,对之前十余年电影情况的研究也应当是开放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