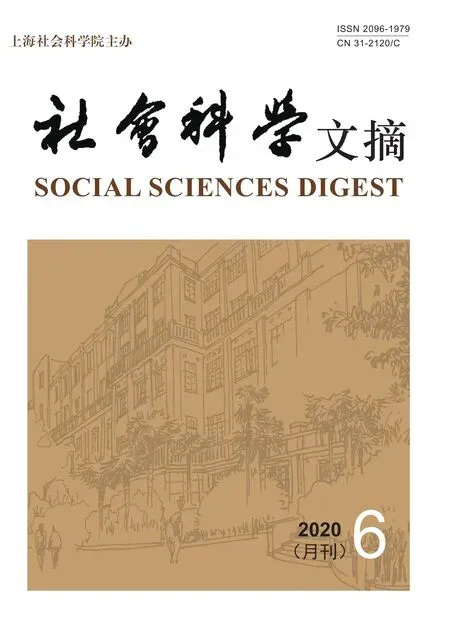新媒体创作自由的艺术规约
文/欧阳友权
通过电脑、手机等新媒体终端进行文艺创作,其改变的不只是作品存在方式和传播形态,也带给了作者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那么,新媒体语境中的创作自由有没有必要的限度、有什么样的艺术规约,不只关乎媒介变迁的技术认知,更蕴含着人文审美的艺术哲学问题。
赛博空间的艺术自由及其限度
从艺术生产方式看,互联网之于创作的一个历史性贡献是为其提供了技术和观念层面的双重自由。在技术的层面上,数字化赛博空间的平行架构和平权机理,绕开了传统媒体单向传播的“把关人”前置模式,最大限度地开启了媒介民主和出入自由的新体制。尽管这个自由的网络世界只是一个虚拟空间,但网络化的虚拟现实系统可以用技术手段复制现实,足以提供一种关于现实的置换。在观念的层面上,网络媒介创造了话语权下移的主体哲学和媒体社会学,把由社会分工和权力宰制划分得层级分明的媒介控制权和自由表达权交到每一个普通网民的手中。对于文艺创作而言,话语权的下移,让文艺表达权从少数文化精英和社会权力者手中挣脱出来,重新回到“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人人均可自由表达的本来状态,从而拆卸了创作资质认证的门槛,消除了作品的“出场”焦虑,给了每一个文艺爱好者以自我圆梦的机会,使来自民间的文艺弱势人群有了“人人皆可创作”的平等权力。他们可以在没有外在障碍和强制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自主的艺术活动。因而,新媒体解放了以往艺术自由中的某些不自由,以便文艺更充分地享受自由,更自由地打造精神家园,新媒体文艺的活力与魅力正在于此。
文学艺术从赛博空间赢得的自由度,除了主体话语权的创作自由外,在经验的层面上还有媒介转换带来的另外三种形态:
一是无远弗届的艺术传播自由。数字化“比特”作为“信息DNA”,消除了“关山迢远”和“物理时延”的壁垒,用“软载体”消弭作品的重量和体积,以比特代替原子,用网页替代书页,规避了昔日作品传播的所有障碍,虽然少了“望尽天际盼鱼雁,一朝终至喜欲狂”的期待快感,但其蛛网覆盖和触角延伸的传播方式,却能“笼天地于尺幅之屏,挫万物于眉睫之前”,只要联通世界,就能坐拥书斋,充分满足万千欣赏者对文艺“在场”的期待,使昔日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变为“得来全不费工夫”,有效降低了传播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实现了文学传播方式的根本革命。
二是“拉欣赏”的艺术选择自由。网络是信息的海洋,欣赏者的“网海觅珍”不再是传统的 “施动(推)—受动”关系,而是“能动(拉)—施动”关系,网民只需拖动鼠标便可实现“所想即所见”,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网民据此不只实现了从“推”到“拉”转换,还实现了“推拉并举”的权力升级——网络使他们不仅可以在作品欣赏环节获得自主的选择权,还能在接受的同时获得发表的主动权,变信息接受者为信息发布者,让人的自由意志得到更充分的展开。
三是“间性主体”的艺术交往自由。由于网络世界便捷的实时互动与自由交往,创造者与欣赏者之间的身份常常可以互换:如网络文学的读者可以参与创作、影响创作或实施同人写作,作者也可以成为一个被人指手画脚的受控者、聆听者或粉丝群的读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认识论的“我—他”关系,而是本体论的“我—你”关系,是自我与另一个“我”之间的“交往—对话”关系,即自我主体与其他主体间的平等共在与和谐共存。间性主体的交往自由,丰富了文艺主体性的内涵,拓宽了创作主体的边界,为文艺生产赢得了更大的自由度。
尽管新媒体文艺在数字化传媒时代获得了比过去更多的自由或更大的自由度,但赛博空间的自由也是有限度的,自由与自由的限度恰是新媒体文艺自由性的两翼。赛博空间的文艺自由,需要从理性觉醒、人性自律与实践过程中,去认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让技术的合规律性与艺术的合目的性在新媒体文艺实践中得到统一。
首先是创作主体文艺创造力的限度。不同创作主体的艺术创造力不仅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而且无不存在自身的局限性。文学是人学,艺术是人之镜鉴,人(作者)的禀赋才华、襟抱性情连同他的局限一道,都将体现在他的创作中。新媒体创作只能在主体创造力的范围之内施展自己的创作自由,而任何一个网络创作者的自由都将受制于他的创造力,一个作家悟性与天赋的限度也就是他文学自由所能抵达的边界。
其次是新型媒介之于文艺表达的限度。数字化转型让文艺创作跳的是一场“镣铐舞”——既是对文艺生产的全媒介敞开,又给创作带来某些方面的阈限。譬如,仅就网络文学而言,新媒体对语言(文字)单一媒介的消解,文学创作可以走出“语言的囚牢”,摆脱文字的桎梏,充分利用视频、音频与文字的融合,实现多媒介文学表意,然而无论你怎么论证文字书写与多媒介表意各有其长,或者阐述线性文本与超文本互有其短,都无以回避一个基本的事实: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媒介自由与文学限度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是同时并存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享受媒介自由的同时,把握好新媒介使用的限度,因为其自由与限度都根源于新媒介的社会语境。
再次是文化资本之于艺术适恰性的商业限度。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影视,包括网络综艺,本身就是商业文化携带资本的“行囊”借助技术传媒催生出来的文艺新品。文化资本是新媒体文艺安身立命的硬核与动力。中国的网络文学堪与好莱坞大片、日本动漫、韩剧并称为“世界四大文化现象”,能够以类型小说为产品主打,以网文IP为源头,形成市场化的“供给—满足”机制,并跨界分发构成泛娱乐产业链,无不是拜文化资本所赐。然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在刺激网络文学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艺术”与“商业”的悖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脱节,甚至导致唯利是图、忽视社会责任等现象,进而导致资本的助力变形为艺术的掣肘。赛博空间的文学艺术被纳入“商业槽模”后,其触底的创作自由便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由驱动艺术的适恰性要素异化为艺术创新的商业限度。
新媒体创作的跨界与规制
新媒体文艺创作跨界有三种常见形态。
首先是从文学跨界到艺术。与书写印刷文学的文字媒介相比,网络文学创作可以便捷地使用多媒介和超文本技术制作视频、音频与文字相融合的作品。这种作品既具备文学的特点(可以阅读),又拥有艺术的功能(可以有音乐、音响,也可以配图片、图像、影视剪辑等),实际上是一种数字化的综合艺术。我国早期的文学网站上就曾出现过诸如《晃动的生活》《阴阳发》《哈哈,大学》等,类似这样的多媒体作品,是文学,也是艺术,是网络文学向艺术跨界的初步实践。
其次是从艺术跨界到文化。新媒体艺术能直接生产网络文化产品,如网络游戏、网络音乐、网络动漫、网络设计、网络二次元制作,等等。网络文学的大众文化特征也十分明显,“人人都能当作家”的网络平权机制,让那些“准文学”甚至“非文学”的产品常常与文学作品并陈于网络空间,生活与艺术、纪实与虚构、文学与非文学界限模糊,常常是混搭在一起的,因此,用“网络文化”的“大箩筐”倒是正适合容纳它们。今日网络文学平台上在作品也不是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的“四分法”可以囊括得了的,那些二次元创作分明就是“Z世代”文化、青年亚文化的数字化表征,那些为网游、网络大电影、动漫而创作的故事桥段,以及粉丝互动中的长短评表白、自媒体中的精彩段子,也是文学与文化交织、文学向文化跨界的产物。
再次是艺术类型、文本文体的跨界。可以说,新媒体文艺的所有形态都是艺术与技术“杂交”的产物,是“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跨界融合。比如,网络音乐、网络绘画、网络设计(艺术设计、产品设计),虽然吸纳了传统艺术的规律与技法,但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的音乐、绘画以及美术(平面)和雕塑(立体)设计,艺术化的技术方式让它们成为独立的艺术新品类。网络大电影、网剧与传统的院线电影、台播电视剧的区别,显然不限于制作成本、播放平台和分账方式的不同,更有创作理念、技术手段、作品容量和消费对象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它们正“自立门户”,试图从传统的影视模式中剥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网络艺术形式。网络文学的文体跨界更是为新媒体创作的文体变迁吹响了“集结号”。我们看到,基于网络创作的“文学”打破了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文体类型,为新文类的产生创造了新的可能。微信APP诞生后,在朋友圈、微信公众号中涌现的微信文学,它们在文体上已不限于诗歌、小说、散文。这使得各种文体之间的界限不再是那么了然分明,数字化新媒介创作让新的文学文体不断展露在网络的虚拟空间。
新媒体创作无论多么自由、怎样跨界,都是艺术规制下的自由、媒介限度下的跨界,是“戴着镣铐跳舞”、循着目标远航。作为一种人文性精神文化生产,新媒体创作的规制仍将以其逻辑的必然性彰显出艺术的合理性。
首先是艺术审美规制。艺术审美是文艺的底色和创作的“靶的”,新媒体创作也不例外。网文圈中的多数写手并非是冲着“文学”而走进新媒体、走进网络写作的,怀着功利化商业动机和娱乐性消遣目的者、上网“试水”者甚多。加之网络写作的“后置型”生产模式,重“出口”不重“入口”,准入门槛不高,缺少严格的把关人,导致网络文学中平庸或格调不高之作较多。这也正是网络文学饱受诟病,乃至需要以“净网行动”“剑网行动”不断治理的一个重要原因。网络并非文外飞地,网络文学既然是“文学”,就仍然需要有文学的要求,不能没有艺术审美的规制。网络文学作品无论是谁在写,不管是写什么,都需要按照艺术审美的要求,遵循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创造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网络”不是理由,“业余”也不是借口,“文学性”的艺术魅力才是网络创作绕不过去的“铁门坎”。如果“创作自由”是它的理想,“审美规制”就是它的宿命。
其次是道德伦理的规制。网络创作应当倡导高雅的审美取向,追求积极、健康、乐观、高雅、清新的审美趣味,反对消极、颓靡、悲观、低俗、污浊的审美趣味。互联网并不是冷冰冰的网络,作家面对它实即面对生命、面对人生、面对鲜活的生活,因而应该对文学心怀敬畏,对网络志存高远,并把这样的观念体现在自己的题材选择、情节设置、人物塑造、语言使用、文本格调等创作过程的始终。
再次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制。如果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价值赋予、一种观念构建,或一种精神的表达,就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营造和体现。传统文艺创作是这样,新媒体创作也不例外。无论新媒体文艺多么另类甚或叛逆,不管其媒介载体、创作技能、传播途径和欣赏方式与传统文艺有多么不同,只要它还是文学艺术,只要它还属于精神产品,它就应该具有作为精神产品所必具的基本特点,就需要蕴含特定的意义指向和文化价值观,并应该让它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力与感染力,使其成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特别是青少年成长的精神“钙质”。新媒体创作也应讴歌真善美,形成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
作者主体的自律与他律
在自律方面,基于新媒体艺术实践,创作主体的自律大抵包括:
其一,“角色面具”消解后的身份自律。匿名上网是有“角色面具”的,网民可以化身为任何一个他想要的角色与他人交流,暂时摆脱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扮演”和“身份焦虑”。当现实角色被匿名上网暂时(只是暂时,不是永远)消解后,一个有责任感的理性网民,需要的是“不忘初心”,用自律坚守道德、信念和法规,在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交往自由与社会责任、平等与互惠之间,把握好必要的平衡和一定的度,而不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网络空间滋生的谣言、诈骗、窥探隐私、黑客犯罪,某些网络作品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恶俗、低俗、庸俗或情色、暴力、迷信等有害内容,身份自律丧失的表现。
其二,虚拟沉浸中的理性自律。被称作“赛博空间”的互联网是一个足以让人沉浸其中、乐而忘忧的世界,一个既非物质亦非精神,却又关涉物质与精神的“数字化世界”。网络作品所描写的是网络化了的生活世界,甚至是独立于现实又迥异于现实的虚拟真实世界,因此,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衍生为写作与超现实的虚拟关系,不仅艺术与现实间的“真实”关联失去本体的可体认性,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联也被赛博空间所隔断。于是,人与现实之间的审美关系就变成了人与网络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创作成了一种‘临界书写’,作品显露的是一种客观本体论与价值本体论双重悬置的“镜映效果”。此时,理性的干预、意志的自律不仅是必要和重要的,也是必然和应然的。
其三,话语自由情境下的艺术自律。新媒体催生文艺话语权的下移,让“零门槛”的创作自由和表达自主情境下的艺术自律问题浮出水面。并且,新媒体创作“大跃进”式的爆发式增长,使创作规范和艺术约束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而成为一个需要仔细考量和重新设定的艺术规制。否则,有“网络”而无“艺术”,或有“文学”而无“文学性”将成为新媒体文艺良性发展的一大“软肋”。这种艺术自律的必要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的艺术素养提升,二是新媒体生态语境中的艺术坚守与自觉。
创作主体的他律,以文学传统、政策法规、消费市场这三种因素影响最大。其中,文艺传统的他律是对新媒体创作的内因规约,政策法规是对行为主体的外在规制,而消费市场则构成新媒体文艺创作的商业驱动。比如,传统的规约力量是潜在的、柔性的,也是巨大的、深远的、无所不在的。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艺术传统能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浸透在新媒体创作、传播、欣赏、交易的各环节中,对文艺的评判、价值、影响力形成影响。而政策法规的制约力量是直接的、刚性的,并且是强制性的,其效果也将立竿见影,法律法规对网络文艺的“他律”举措,对于约束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版权,打击网络空间的违法行为,促进整个行业健康长远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消费市场的他律性约束更加直接,也更为强大。新媒体作品的市场化竞争十分残酷却也非常公平,它不会埋没任何一个勤勉的文艺天才,也不会给任何一个庸才以鱼目混珠的机会。这正是新媒体创作自由与艺术规约之间存在逻辑统一性与艺术必然性的又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