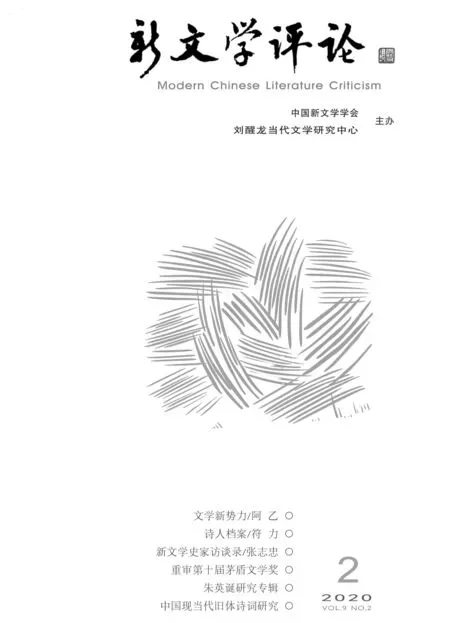此心安处是吾乡
——朱英诞诗歌的“江南情结”及其精神向度
□ 周书阳
纵观整个现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作家作品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缔结关系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关注。杰出的小说家往往能够发掘、创设一个投射自我生命体验的空间:鲁迅的鲁镇、未庄,沈从文的茶峒、湘西,师陀的果园城,张爱玲的上海公寓,都是经典例证。即使是在叙事因素薄弱的诗歌体式中,空间也与环境、背景、意象、结构等要素一同发挥着提升艺术表现魅力的作用。像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现代派诗群,其笔下经常出现的“辽远的国土”“古城”“荒原”“异乡”,即具有心灵与艺术的双重母题功能①。
基于这一角度考察同属现代派诗人的朱英诞,不难发现,“江南”担当了他的“空间诗学”主角——构成其诗歌世界的一个地标、一抹底色,一个重要的书写对象,一份珍贵的写作资源。无论短制,抑或长篇,江南既是诗人凝聚灵感、发挥情思的福地,又是诗人写作的中心关怀和精神旨归,为我们统揽其作品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聚焦。
从地理学的角度界定,由于不同时期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的空间范畴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推进和压缩的历史。但在“地理的江南”之外,大众还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划出了一块民意的疆域。所谓“人人尽说江南好”,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在年深日久的积淀中,江南逐渐聚敛为一个指称美好、富庶、安逸、精致生活的专有名词,一枚浓缩了感性、温润、婉约、恬淡、超脱等诗性精神的优美内核——雨打芭蕉,风叩门环,梅窗望月,曲水流觞,“文学的江南”应时而生。
朱英诞的诗歌正是“文学的江南”孕育的一个美的收获。诗人将江南创造发明为“乌有之乡”,反映出一种“不在而属于”的生存处境;又在回返古典途中,以“梦”的形式复活“桃花源”这一民族文化原型,委婉地传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返乡的诉求。在诸多以江南为背景或直接书写对象的篇章中,古典的江南诗意被浸渍、汲取、置换,最终培植出了具有多重精神向度的“江南情结”。那些浮动、弥散于诗行间挥之不去的浓情淡意,让一代代读者欣然阅之、心向往之。
一、“不在而属于”的“乌有之乡”
朱英诞1913年生于天津,后举家迁往北平,祖籍江西婺源,寄籍江苏如皋,家在武昌有藏书楼。几个地理空间的罗列,大致说明了朱英诞一生的行迹。正如他晚年在自传《梅花依旧》中写道:“我常自嬉,谓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我个人却生长在津沽与北京——我家寄籍是宛平。”②有待推敲的一点在于,虽然朱英诞的诗歌寄予江南无限的热忱,但他实际上从未到过江南,其涉笔江南之处,皆是“缺席的在场”。如果说“在故乡里还思故乡”③(《华灯词》)是朱英诞的基本立场,那么“北国里怀念着江南”(《断续的风》)则确立了他的写作姿态。
朱英诞经常在诗作中建立一个北平与江南互为参照的坐标系:他用江南的时长计量北国的光阴,“因为有着江南的故乡/北国的夏天特别长”(《枯思》);他用江南的景致品鉴北方的风光,“这时候北平黄昏,像江南/翠尾扫开三月雨”(《晚雨旋晴》);他用江南与北平的同频共振解说心灵的悸动,“我爱这里和到处的民间,/我爱我遗失或背离而永远保持着的江南/和民族心灵的永远新鲜的运动和摇撼,/我爱大街上北平的黄昏之无边”(《春雨》)。诗人绝无扬此抑彼的用意,于他而言,北平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江南却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意涵:一边是“遗失或背离”的家园,一边是“永远保持着”的记忆中的乐土。如何理解江南在他的生命中所居的位置,并且通过书写江南完成自我身份的注解,是朱氏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诗学命题。
“在故乡”与“去异地”这组矛盾几乎伴随了朱英诞的诗路,其创作也不时隐秘地流露出面对江南的微妙心态。一方面,江南是理想的生命归宿地:那儿春意盎然、生机勃发,“桃林依旧留下红意/江南的水边已生新绿/女儿们正在发育”(《冬天》);那儿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江南的丰草有着大迁徙,/经过一片虚无的海上吗?/未到花时而已经浮动着/暗香”(《江南》);那儿草长莺飞,触发了诗情:“草是盈城盈野的绿遍了,/长大的影子伸入花间;/黄鹤,鹰,苍蝇飞起来,/诗人们,暮春的江南”(《黎明》);那儿微风和煦,盛满了希望:“仿佛吹来江南的风媒花,/花的种子粒粒是梦想”(《寒潮》)。另一方面,它却如此玄远,无法企及,远至“永远隔在雾里以致雾会变成了雪”(《试茶》),远至无形中竟揭示了某种悖谬式的生存处境:“暖暖的绿草在梦中生长,/江南的家于我是陌生的异乡,/异域的客人却来遨游了,/来了又走了”(《夜春词》)。它甚至永存于现时态之外:“黄昏每多是美丽的天空,/又怅望于江南了”(《新晴》),“江南花草的蜃楼?自海上泊来”(《晴》),“啊流汗的石头,我遗忘了的/江南成为天外的悠然的存在了”(《暮雨》)。“怅望”“蜃楼”“遗忘”“天外”这些轻盈、纤弱的语词,暗示着江南虚无缥缈的幻象性质,仿佛预兆了令诗人魂牵梦萦的“江南情结”必将无端失落。
联系朱英诞初登文坛时诗界的文化氛围,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人大都是在“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的政治低谷期步入诗坛的,从时代的峰巅跌落,感受到难以排遣的生命苦闷,堪称一代“边缘人”。同时,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广袤的乡土来到都市,因受到传统和现代双重文明的挤压,找不到自己的稳定位置,心灵久久处于悬置状态,又是一群漂泊异地的“零余者”。当他们以游离时代主潮的姿态从事写作之时,诗作中往往映射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意向,文本中充斥的是对远方的憧憬与他处的怀想,并最终指向一个“乌托邦”意义上的幻境。朱英诞的江南书写分享了相同的心理逻辑和写作策略,他笔下的江南与其说是一个实在的归处,不如说是一个怨怀无托的他乡,是一个倦行的旅人需要抚慰时,创造发明的远方。因而,不必要亲临该地,任由其可望而不可即也无妨,只需把一颗诗心托付给这“乌有之乡”,“一切龌龊的人事都远了/江南三月的和风吹着嫩绿的稻苗”(《读韦应物诗》)。这种苦心经营的归属感消泯了“在”与“不在”的界限,使江南集故乡与异地于一身,暂时调和了诗人身心分离的冲突。
身向乡关何处?诗心皈依何方?在《乐园放逐——梦回天北望江南》这首诗的开篇,诗人饱蘸着深情的笔墨娓娓道来:“我将愿意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而死于怀乡病”。那个陌生的地方,会是诗人渴念的江南吗?可是这个江南不也成了“失乐园”,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的范型吗?诗人接着解释:“因为这里有我的乡土的气味/当我已经没有了乡愁的时候。”借用斯维特兰娜·博伊姆在《怀旧的未来》中的说法:“现代的乡愁是对神话中的返乡无法实现的哀叹,对于有明确边界和价值观的魅惑世界消逝的哀叹;这也可能就是对于一种精神渴望的世俗表达,对于某种绝对物的怀旧,怀恋一个既是躯体的又是精神的家园,怀恋在进入历史之前的时间和空间的伊甸园式统一。”④或许“乌托邦”的视景不能逼真地复现江南的形象,甚而愈发映衬出现实的匮缺和“乐园”的先天脆弱;但是,当诗人的笔触有意无意地徘徊于现实与理想的边缘地带之时,拖曳着真实的江南同虚构的“乌有之乡”叠印在一起的重影,传达的是每一个罹患“怀乡病”的诗人“不在而属于”的普遍体验。
二、“桃花源梦”里的文化乡愁
诗歌原本就属于个人内心的彻悟,诗人面对的是一个无比丰富的表象世界,但如果要入诗,这个世界就得经过个性化的消化和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朱英诞的独特性,在于他以江南作为观察世界的视点,通过书写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抵达远方,抒怀乡愁。乡愁是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备受中外诗人青睐,在众多文本中得以微观化、形式化和具体化的一个艺术范畴。江南的花草讯息、鸟虫微语,经诗人虚实相生的妙笔点化,皆晕染上一层乡愁的底色,余韵悠长。江南风景与诗人内心契合蓦然唤起的乡愁,固然有现实世界无力自足而回溯生命本源的心理动因,但也不容忽视古典文化传统的询唤。
对古典文学的态度和选择,对传统的吸纳和借镜,是贯穿现代中国文学的一条线索。新诗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有意识地将古典诗美结合现代因素,挖掘传统的文化养分和诗学潜能,是一批诗人在创作理念和实践上的共识。已有论者对朱英诞“与古为新”的艺术特色加以阐发,找到了朱诗与宋诗理趣、掌故使用、意象思维等方面的勾连⑤。而从民族文化原型的角度透视,我们则发现朱英诞与“桃花源”的不解之缘。朱英诞自述酷爱陶渊明诗文,而《桃花源记》因为“是父亲教的窗课之一,必须会背诵”⑥,更是对他一生影响深远。在《读桃源记后》的后记中,朱英诞说:“全篇为短句,其旋律之明快,足征心灵之妙悟,所谓欣慨交心是也。以内涵言,或曰寓意,或曰纪实,前者谓是复古,小国寡民……近年来引西儒乌托邦说,亦不知此近代之发现,桃源虽不姓陶,张冠亦岂能李戴乎?此一心灵世界,实陶公之创造,遂为吾人喜闻乐见者,正复是‘灿然有心理’耳。”⑦《桃花源记》中所表达的丰衣足食、自由安适的理想社会图景,一直以来都镌刻在怀抱着古典情怀的朱英诞精神记忆深处,并且以江南这个变体形式呈现,成为他写诗回应社会变化、表达思想情怀的一个重要出发点。这个遗世独立的审美世界在他的渴慕、遥想、手追心摹下,渐渐显出原貌——一块亦真亦幻、若即若离的梦中飞地。他在暗香浮动中敏锐体察到“温暖的风里江南又如梦了”(《如梦》),他犹疑地发出“唉,怎能不多梦呢,/我的故乡在江南?”(《多梦的春天》)的一声喟叹,他还因“我所爱的渔人在哪里?/桃花依旧,田舍空了/捕鱼的人儿呢,不见”(《怀古》)觉今是而昨非。常伴江南的幻想痴念,与“桃花源”的良辰美景汇合一处,最终通向一个记忆和梦境的世界——这里的记忆混融着个人的情感经验和对传统文化的深情眷恋,频频回首;这里的梦境也并非指向未来的憧憬,而是怀乡式的哀愁。
弗洛伊德有言:“即使严肃的思想也不能阻止我们对作家想要利用的梦的有用之处产生兴趣……它可能会使我们从一个侧面获得某些关于创造性的写作本质的细微理解。”⑧朱英诞的“桃花源”虽然以“梦”的曲折形式泄露,且在诗歌的现代征途上发生了变异转换,但涤除不尽的是数千年来古典诗歌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建立完备的审美理想,以及世代相传的文化心理。“桃花源”与“梦”的联结促成了传统文人经验中最富于无意识内涵和美学敏感性的隐喻,它所唤起的是一种“文化乡愁”的集体共情。“文化乡愁”经由阅读、想象、记忆,以审美的方式展开,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通过调动早已沉淀于读者阅读经验中的传统文化积累,通过激活深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民族文化基因,召唤一份因文化共通而心领神会的默契。
RVOT组患者右胸导联(V3R、V4R、V5R)R波振幅均明显小于LVOT组,而LVOT组患者V3R、V4R、V5R的S波振幅均明显小于RVOT组。见表2。
于是,我们看到“互文性”语法在朱英诞诗歌中大量被运用。比如重复征用关于江南的耳熟能详的典故:《渔火》中,“渔火红红的如一粒江南的红豆”化用了王维的“红豆生南国”,并巧妙地对接了原诗传达的相思之情;同样是渔火,《夜乡》结尾“江南的渔火伴我愁眠”则是致敬张继名篇《枫桥夜泊》的“江枫渔火对愁眠”。又或者对前人书写江南的形式特征及本质特征的重复与改造:《北平曲(二)》中“那江南的贵客低低的口笛”让人不禁联想到李白《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的意境,而《春寒》起笔两句“梦来到江南见一枝花,/我以为它就在你的手中”则与陆凯《赠范晔》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异曲同工。自古洎今,江南文化中那种超物质、超功利的审美自由精神筑造了无数文人墨客念兹在兹的理想家园,甚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文化品格。也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驱役下,一切被赋予江南特质的抽象情境或具象物体都不可避免地唤起诗人言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的冲动。事实上,通过这些文本对共同积累的语言、文学惯例与手法的参与,我们欣喜地看到古典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新诗中的再生。
三、“以诗还乡”的寻回之路
“乌有之乡”的创造发明,和“桃花源梦”的几度回眸,凝聚了现代人寻回精神家园的渴望,提醒我们关注那些还乡的归人。朱英诞的诗中也有一个徘徊不去的“游子”身影,大概是他本人心象的化身。他打远方而来,逡巡在暮春的江南,却又不知归向何处。他淡漠的忧愁,随连天碧草蔓延铺开,随氤氲着雾气的雨丝渗出诗句,意境静穆辽远:“远方的游子又徘徊了/江南的水边草香了吗?”(《细雨》),“江南的春天是江南的梦,/浮云满载着游子光阴;/日落了而天是更暖了,/春天的梦啊海一样深”(《江南》),“你羡慕谁的行止呢/游子:你总是说/江南是春天的梦”(《游子界说》)……
还乡即是回家,朱英诞的诗歌通过“巢—家宅—故乡”的审美同构奠定了游子还乡体验的诗意根基。在《初夏》中,诗人形容“江南仿佛是巢,/在美好的大地上”,“巢”是一个暗含着庇护、温暖、安定等意义的居所,它孵化着游子还乡的祈愿,直接关联“家”的想象。在另一首诗《老屋》中,诗人摄取了屋宇一个角落,低低吟哦:“旗帜随了晓角升高,/风停落在我家。/杨柳是月光的巢。/青苔满院了。//但我心已经长满了草。/同那老屋一样。/用彩笔描摹吧,/当梦着江南的时候。”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的名著《空间的诗学》,从现象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角度分析了诗歌中家宅的象征意义,他将其称为我们“最初的宇宙”,“在人的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家宅在自然的风暴和人生的风暴中保卫着人。它既是身体又是灵魂。它是人类最早的世界”⑨。老屋保留着逝去岁月的宝藏,是安顿回忆、值得依赖的生命港湾。即使外表被改造,它依然表达着内心空间。家宅的颓圮衰败、形迹消隐往往是游子痛感的起点,它连接起“无根”的恐惧和认同匮乏的焦虑。从巢的形象到家宅的形象,其间的过渡是建立在“重返”这个主题上进行,倦鸟还巢、游子归家都是为梦回江南所做的注脚,所以,还乡不仅是人生的遭际,也是一种诗歌心理。
如果把朱英诞的“江南情结”作为一种确切存在的生命和写作经验,有限地推扩到其他同处于受传统与现代文明撕扯的诗人的创作中,我们应该能够发现其中内嵌有一个“以诗还乡”的精神结构。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说过一句话:“当某一个事物真正终结之时,我们才有资格去追溯它的起源。也许是我真正认识到了故乡的死亡(不管是在实指意义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才有一种描述它的迫切感和使命感。”⑩面对不可逆转的乡土的解体和沦陷,面对辗转曲折也不再轻易抵达的故乡,从传统的农耕文明社会走来的知识分子遭遇的是前所未有的“失乡”体验和精神危机。在这个层面上,以回望的姿态建构起一方独属的思想阵地,通过文学这种艺术形式感受、见证、记录、思考精神的原乡,竭力守护与延续它最核心的灵魂,这是永远潜藏于每一个现代人内心深处的冲动。在《我的诗的故乡——〈春知集〉后序》中,朱英诞在满怀深情地回望写诗道路时,已经隐露了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童年消逝的担忧:“绿野间散发着浓郁清新与腐朽混合的香味,笼罩着的实是童年的王国。然而不知是什么时候,有什么势力,竟不费吹灰之力地把它永远地灭亡,实际上却像是失去了乐园!是不是标帜现代文明的城市的威力呢?”因此,有理由相信,朱英诞的诗歌创作正是借助文学的重返、重现功能,通过对江南的怀旧和再造,修复和慰藉遍布创痕的故乡。诗就是乡愁,就是指引失乡之人迷离返本的路。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唯通过返乡,故乡才作为达乎本源的切近国度而得到准备。守护那达乎极乐的有所隐匿的切近之神秘,并且在守护之际把这个神秘展开出来,这乃是返乡的忧心。”
“以诗还乡”不但清晰可辨地勾勒出朱英诞的精神轨迹,同时也触及诗的内在品质和表达方式,暗示着诗人更为宏大的抱负,或者说另一种艺术发展的可能——以回返古典的方式抵达现代。自中国的新诗诞生以来,因其与传统诗歌美学规范的切割与断裂,人们普遍对古典怀有一份眷恋的失落,“它似乎已经由无意识向意识渗透,回忆、呼唤、把玩古典诗歌理想,是人们现实需要的一部分,维护、认同古典诗歌的表现模式是他们自觉的追求”。深受古典文学浸润滋养的朱英诞,更是深解其中况味,追踪古典诗歌的艺术旨趣,寻回传统故而也带有形而上的“还乡”意味。如前文所述,从古人处引来的江南山水,让故乡向现代诗人唤游,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把握现实、防止迷失的精神力量,发出诗美的邀约。然而,当“能不忆江南”的情调汹涌地占据诗行,我们似乎也能察觉古典美学施加的威压,以及因传统诗意过剩而掩盖的内在的贫乏。
有诗为证:“江南的茶花香了,/我应该回到故乡去了,/否则将被那枝头小鸟/呼作‘客人’和‘你是谁呀?’//我的故国是我的故乡呵,/我们的时代和唐代是/两座高峰,遥相对望,/遥远,显得渺小,/我们的,/在望的峰顶呵,/让我们攀登上去!再回顾那另一座/染着夕阳的黄金的峰顶,/它才真的小于我们的了。”(《白日》)在这则古典美学与时代艺术正面对峙的寓言演绎中,诗人为自己找寻到的“还乡”途径是去努力攀登比肩唐诗的艺术巅峰;但是,一旦面对“染着夕阳的黄金的峰顶”——这个东方审美创造的极品,这个难以企及的辉煌成就之时,所有的后来人只感到“遥远”“渺小”:那种在大师的阴影笼罩下迟到的晚生感,那种用白话展现诗意时力不从心的沮丧感,那种逃离不开的“影响的焦虑”。“古人的江南”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与魅力的传统,但它也有可能是一种对现代诗创作失效的传统。“作为一个现代诗人,只有摆脱‘文化的幻觉’和传统的因袭,摆脱传统诗意的诱惑——它真的如同那神话中的塞壬的歌声,才能重新抵达‘现实的荒野’,使诗的写作和现实经验发生一种切实的摩擦。”必须警惕,“以诗还乡”在揭示的同时可能造成另一种遮蔽,虽然它已然构成反思现代性的一种批判角度,但批判力量的限度和效果尚需仔细厘定。
总的来看,朱英诞的“江南情结”,既承载了时代加诸个体的心理负担,又回应了古典情怀的遥远声响,还抚慰、修复和守护了“返乡的忧心”。就像文化乡愁永远代表着一个民族记忆的密语,离乡怀念也在代代相传中变成宿命的轮回。无论是“乌有之乡”的构筑,还是“桃花源梦”的访觅,无数游子仍在寻回的路上辛苦跋涉,哪怕注定望断天涯归无路,也要用凝视的目光代替肢体的返乡——“我将永眺着江南,远望天空”(《江南》)。
注释:
①现代诗歌中的空间和地标,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既是诗人发现和寻找的特定内容,也是自我外化的符号,是情感心理的“客观对应物”。通过分析这些共同分享的意象、原型,我们能够考察一个诗歌流派共通的艺术形态、文学思维和美学理想。相关论述参见吴晓东:《临水的纳蕤思:中国现代派诗歌的艺术母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②朱英诞:《梅花依旧》,《朱英诞集(第九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42页。
③如无另外标注,本文所引的朱英诞诗歌,均出自王泽龙主编的《朱英诞集》第一至五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④斯维特兰娜·博伊姆著,杨德友译:《怀旧的未来》,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⑤如王泽龙、任旭岚:《朱英诞新诗与宋诗理趣传统》,《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2期;周丹:《朱英诞新诗用典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罗燕玲:《论朱英诞新诗的意象艺术》,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⑥朱英诞:《新诗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99页。
⑦转引自程继龙:《朱英诞新诗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4页。
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常弘等译:《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幻觉与梦》,《论文学与艺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页。
⑨加斯东·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6页。
⑩转引自格非、陈龙:《像〈奥德赛〉那样重返故乡》,《南方日报》2016年7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