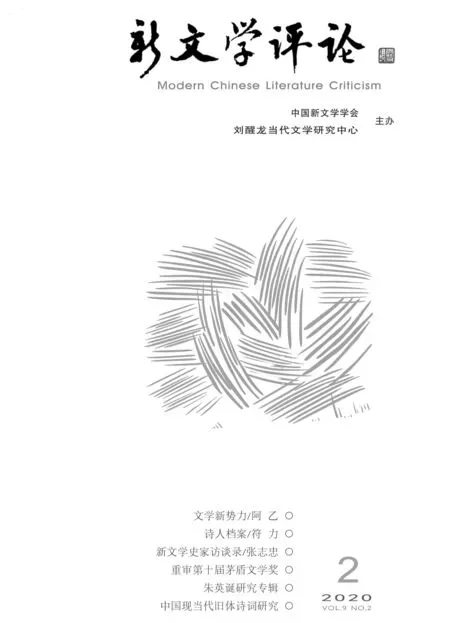北平下的彷徨
——论朱英诞的漂泊诗思
□ 陆之超
“我常自嬉,谓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我个人却生长于津沽与北京——我家寄籍是宛平”①,在朱英诞笔下,“北平”一直作为“江南”的“他者”而存在着,作为地理坐标的“北平”与“江南”这一心灵坐标在身为漂泊者的朱英诞诗歌中互渗交错,彰显出诗人与其所处境遇的微妙隔阂的精神悬浮状态,如何突破这种困境,成了诗人创作生涯中的重要命题。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概念认为:景观社会及其空间是彻底异化的与主体精神分裂的社会与空间,空间迁移与心理地理坐标的背离,将会导致个体对所处境遇产生微妙的疏离感与悬浮感。身处“北平”,心在“江南”的空间错置感对朱英诞诗心的生成乃至主体生命的构建产生了多维度的影响;在这种错置状态下,对现实坐标的“漂泊”感就此生成。本文以居伊·德波的景观空间理论为基础,以该视角来探讨朱英诞诗歌世界中漂泊主体的身份转换、漂泊诗思下北平形象的演变以及诗学家园的构建问题,以期进一步理解这位“隐没的诗神”的内心世界与文本内核。
一、 漂泊下的身份转换:从“思乡游子”到“无根的流浪人”
“若然,你要问我出身,我该怎样回答?”②朱英诞在《神秘的逃难》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在漫长的诗人生涯中,朱英诞始终以“江南人”自居,其祖上在江南为官数代,在武昌城内有一藏书楼,其族谱又在如皋刻印成书。“家在江南也在江北”是诗人对自我身份的注解,然而地理位置与心灵坐标的背离却导致了诗人对自我身份构建的疑惑——诗人自始至终从未离开过中国北方,“北平”作为一个地理符号在激发诗人浓重的乡愁的同时,也让朱英诞陷入了“身心两地”的漂泊困境。这种困境的发生关涉着空间领域和心理地理学两个维度,伊凡·齐特齐哥拉夫在进行心理地理学研究时这样写道:“先生,我们来自另一个故乡,我们讨厌城市。”“另一个故乡”所衍生出的情感困境随着时间的变化与漂泊状态的转换,最终导致了诗人在漂泊处境下由“江南游子”向“无根的流浪人”身份的转变:
在北京这儿,深刻体验到“寂寞人前”的况味……可怕的狂风……摇撼着纸窗木屋,以及江南游子的魂魄的……③
——1936年《〈小园集〉自序》
1932年朱英诞考入北平民国学院,在写下这篇自序时 ,在北平已然居住了4年,然而“江南游子”的身份认同始终没有改变,北方的大风摇撼着他的内心,“可怕”是其在异乡的情感注脚,郁结的乡愁啃噬着诗人年轻的灵魂,“归而不得”的心理境遇由此产生:
描摹着北平的天蓝
描摹着北平的天蓝/描摹着北平的天蓝/最高的时候/最高的山/在你的头上/月正圆/最快的帆的船
听见了林中的大风/感到更大的宁静/而你投下一个黯淡的花影/给我的心的岭头
如何描摹北平的天蓝?诗人将笔触投向天空的最高处,在最高山的头顶,只有一轮圆月孤悬。“月是故乡明”,“我”看着这轮明月,心中渴望着以“最快的帆的船”回到心中的故乡。然而这终究是不可能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北平林中的大风呼啸,摇撼着游子的魂魄,月光照在山岭上,投下了黯淡的花影,也照在了游子的心上。“我”望着北平的天蓝,却只看见了代表故乡的明月,风帆不动,心却如月下孤山一般,黯淡如花。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岁的增长,这种情感上的困境产生了微妙的变异,诗人对“北平”的看法有了奇妙的变化:
我在北京居住了二十五年了,但是对于古城的好处仍是觉得不太容易说清楚……因为习惯了,也不甚怀念江南江北的故乡了……“小劫如风吹已过”,我的心情正是如此……北京有一点容易看到的美妙……④
——1956年《记青榆》
二十多年后,诗人对于江南江北的故乡却已然是“不甚怀念”了,对待“故乡”的心情不再如多年以前那般摇撼震动,而是“小劫如风吹已过”。“小劫”出自梵语,指的是提婆达多受地狱苦报之期间,或指释尊一劫之寿限,在佛家中代表着漫长的岁月,“故乡”这一符号在诗人心中流转千遍,却最终也如风吹过,让人“不甚怀念起来”,而先前“可怕”的北平,却在诗人心中有着容易看到的美妙,虽只是一点,却也折射出“江南游子”这一身份符号在诗人心中开始逐步消解,诗人似乎开始以北平为家了。
有趣的是,虽然心理坐标与地理位置的长久背离在某种程度上疗愈淡化了朱英诞的“江南怀乡病”,但北平却终究无法成为诗人缱绻灵魂的真正归宿,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诗人对于自我归属的困惑:
民廿一年夏,我初回北京……看起来或许近似梦游病,我自己却知道:不过是“游子澹忘归”罢了……现实与幻美如此深妙的交错……至此,在“诗的天空”下,我避免了超诗的理想主义的危机。⑤
——1973年《〈春草集〉后序》
不同于从前那个渴望以“最快的帆的船”归乡的游子,也不同于那个在北平度过二十五年岁月,感怀北平“美妙”的诗人,朱英诞此时重新拾起了“游子”的身份,虽然清晖娱人,北平的风光仍然对诗人有着深刻的影响,江南故乡的秀美却也挥之不去,现实与幻美相互交错,北平终究不是家,身为游子的“我”却也忘记了归乡的路,在“诗的天空下”,诗人不再执着于返乡的归途,而是默默承认了自己身为“无法归乡者”的现实,避免了理想主义的危机,却又在无形之中带来了迷惘的诗思。
不难看出,心理坐标江南与地理位置北平的长久割裂与背离,激起了诗人对于自我游子身份的消解与重构——精神还乡的不断重临在北方的朔风与时间的浸染下逐渐远去:从“江南游子摇撼的魂魄”到“忘归游子”,“还乡”这一心理症候逐渐衍生成“无根者”的自我言说:
枕上作
我愿意我的生命如一张白纸/如圣女有她的天堂/日出如昨晚的落霞/我苦于我不知道啊/哪儿是我的家……⑥
“我苦于我不知道啊/哪儿是我的家”,这是诗人对自我身份归宿的终极质问,圣女有她的天堂,落霞伴生着日出,所有事物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终极归宿,可“我”呢?“我”空有着属于“家”的记忆,然而这“家”却并不真实存在着,岁月在“我”的生命上留下了属于她的色彩,却让“我”始终无法触及,“我”陷入了深沉的迷惘之中。正因为如此,“我”渴望着自己的生命如白纸一般,了无牵挂,这样超诗歌的理想主义是注定不可能实现的。当无根的迷惘取代了怀乡的梦呓,“无根的流浪人”便取代了“江南游子”,成了朱英诞的诗歌注脚。
从“思乡游子”到“无根的流浪人”,身份的变化并非单纯由于时间向度的延长而产生,心理坐标与地理位置的二元对立的单一结果。回望朱英诞的一生,其人历经革命失败,抗日军兴,随着北平的沦陷,当地的文人们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根”的集体共情之中。作为身陷沦陷区的“留守者”,朱英诞自始至终都游离于时代的主潮之外,然而他对自我身份的不断发现与重构,恰恰是时代在诗人内心留下的深层次刻印,也是大环境下朱英诞对个体精神与人类共性的敏锐感知所带来的结果。对自我主体意识的深入发掘,给予了朱英诞诗歌独一无二的现代性品格。
二、 漂泊诗思下的故乡投影与再造
波德莱尔认为:“诗不是再造自然,而是创造与自然具有‘契合’关系的超自然的理想世界。”⑦一个从未离开过北方的人,又如何在自己的诗歌中怀乡呢?在朱英诞的诗歌世界中,作为“江南游子”的诗人努力探求北平这一“异乡”与内心“故乡”的契合成分,试图以此“投影”来疗救内心的“怀乡病”:
晚雨旋晴
……/这时候北平黄昏,像江南/翠尾扫开三月雨……
今年的春天·北平
惟有我的寒碧的小园/像心脏,是最后的一点弥留/实现的梦;江南如在眼前了/当梅子黄熟的时候……
北平曲(二)
长长的街道上平静的步履/长长的小溪水岸柳飘远的/长长的北国天深深的边际/那江南的贵客低低的口笛
这些诗歌在“北平”“江南”之间反复闪回交错,诗人构造出了北平——江南的意象迁移与交错,“北平的黄昏、北平的小园、街道、小溪”是诗人面对自然时作为“洞察者”“猜测者”以一种心灵非凡感知所探寻到的语言意象,如同马拉美所说的“客观事物”与“意象”、艾略特说的“客观对应物”一样,从朱英诞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某种奇妙特质,给予其诗歌以非凡的表现魔力与审美体验,现实与超现实在诗人的笔下相互重叠,暗含了其生活与精神层面的嵌合维度,“我爱北京,是爱这里特有的秋高气爽;但是也爱北京的深巷,还有幽居:‘绿荫生画寂’,宜于我追怀我的诗的故乡”⑧。这里的“爱北京”是为了更好地“追怀故乡”,怀乡之思至此生根发芽。
事实上,这种怀乡方式自古有之:“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然而“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北平”在朱英诞的诗歌世界中成为“客观对应物”的同时,也是他的“楚歌”“鲁酒”,虽得一时清欢沉醉,却终究“曲高和寡”“酒难消愁”,仅仅作为故乡投影的北平终究无法疗救诗人的怀乡症候,随之而来的便是在北平黑暗长街与墙头上的惘然游荡:
孤独者之歌
各个星座都在我视野里啊!/肉体大可哀——/这是什么样的墙垣/既推不倒,也不能飞越?/北京的红墙?/天上的银汉?/孤独是一个丽日吗?/我沉沦于那深林之夜里/谁梦着我是一片月?/任凭日全蚀/月全蚀
原本与诗人思乡情感相契合的北平在此发生了突变,高耸的“红墙”矗立在诗人的内心世界,北平上空的“银汉”隔绝了江南的“日”“月”,谁来拯救诗人?谁又梦着他这个孤独的江南游子的魂魄?红墙高耸,银河广阔,却把诗人拘束在一方狭小的“深林之夜”中,诗人想推倒、想飞越这些障碍,却只能唱出那属于孤独者的歌声,“归而不得”的冲突在此出现了,“北平”不再是“江南”这个乌有之乡的投影符号,它在诗人无限的追索中获得了新的独立意义:
秋花落
只留下一片影/但岁月无穷/夏天是这样长长的/像北平的大街一样长/如此静默/等待着一场大雪吗/谈谈厌倦的故事吧/像冬夜的梦一样长长的
如同前文所说的那样,原本作为诗人故乡的北平,在与“江南”的纠缠互渗中上升成了一个生命、精神震荡状态的载体。北平的“影”笼罩在诗人心头,它的街道漫无边际且静默无言,如同冬夜寒冷的梦一般没有尽头。漂泊的尽头依旧是漂泊,“语言的产生/并不能增加或减轻/人类沉默的痛苦”⑨,诗歌对还乡病的疗救终究还是失败了,“还乡”的意象契合逐渐变为“无根”者身份错置的心理冲突。在这样的冲突中,诗人对“北平”表现出了彷徨无措的心理状态,进而陷入了时而缅怀时而清醒的双重困境。
随着诗人漂泊状态的空间性持续,这样的文本性冲突终究还是发生了某种显著的变化,“北平”的心理指涉第三次有了根本性质的蜕变,如同“游子澹忘归”一般,诗人与“北平”迎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心理上的和解:
古城
让窗饰静观你走过/让商标的孩子引逗母爱/在城市中稍稍停留/快乐的阳光仍高视阔步吧/黄昏的右手卷为风/我也收拢我的黑绸的伞/啊/古城的大街上逡巡/我平静地走着如在家中
“北平”上空无际的“银汉”消失了,“快乐的阳光”照耀了下来,诗人走出了《孤独者之歌》中的那片“深林之夜”,看见了孩子、母亲以及古城的大街。北平所象征的“红墙”轰然倒塌,“平淡冲和”之气氤氲而起,诗人在诗歌的生成过程中获得了在“北平”这一古城的宁静。
百宝箱
……在大街上/正如在平安的家里一样/走着……
北平大街(二)
步履平静如在家室/流水伴着垂柳远去/长长的蓝天随了红墙/也如流水的流向天边
“北平的大街”不再如“夏天”一般悠长无尽,诗人的步履不再是孤独者的彷徨踉跄,他步履平静得如在家中,“红墙”再次出现,却已没了先前的高耸,蓝天取代了辽阔的银汉,诗人对江南的思念不再横亘在心头,而是如同流水般流向了天边。
黄昏
疏林的后面无人/寂寞的落日的远村/我喜欢北平的黄昏/街谈巷议里/则有人们来往着/我喜欢北平的黄昏/隐隐的青山啊/夜夜是这时候
先前“长长的”“如冬夜的梦一般”的北平大街消失了,诗人反复运用“家”一词来表现自己的生存状态,不同于先前诗歌中“江南—北平”的意象交错与感官互渗,诗人直白地表达了对“北平”的喜爱之情,北平不再是江南的一面镜子,也不再是困囿自身的地理牢笼,它成了“江南游子”的“家”,先前文本所表现出的诗人与北平的冲突状态似乎在此彻底消失了。然而,即使诗人意图通过“喜欢”“如在家中”这样的表达来获取与北平在某种程度上的缓和,赋予其新的诗思路径与想象空间,但诗人的“无根基状态”依旧没有改变:
夕阳
……/胸襟上无须簪野花/这儿是你的家,但无所谓家/荒村野店里没有悲愁/这儿也无须系着红旗的酒招牌
“无所谓家”,“没有悲愁”,即使“小劫如风吹已过”,诗人“无根者”的身份构成依旧没有任何改变,巨大的空虚感困囿着诗人的内心,代表江南的“野花”“红旗的旧招牌”在北平“夕阳”的映照下呈现出寂寥的姿态,作为“家”的北平、作为“家”的江南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颇有杜甫“近侍即今难浪迹,此身那得更无家”(《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的诗情。
从投影到再造,朱英诞对北平的描摹,突破了单纯情感的线性维度。折射出在岁月的砥砺下,作为“无根者”的诗人虽开始拒绝先前的彷徨心理状态,然而“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⑩。朱英诞在表现出释然态度的同时,分泌出淡淡的愁绪,这种愁绪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先前的乡愁,而是诗人在反思自我生存状态,明白始终无法突破心灵世界的桎梏时所产生的巨大的空虚感,“北平—诗人—江南”三者互相纠缠,带来的是情感上的复杂转变:悲愁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境遇的深沉思考。
三、 漂泊中的突围:从“以诗还乡”到“以诗为家”
尼采认为,摆脱人生的根本烦恼和痛苦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逃往认识之乡,另一条是逃往艺术之乡。乐天有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重题》) 事实上,“以诗还乡”早已有之,陶潜写《桃花源诗并记》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这里人民安居乐业,民风淳朴,家家富足,“怡然自得”之象令人神往,然而“桃花源”只是诗人的精神之乡,他在自我描绘的精神乐土中获得了心理上的快慰,无论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闲适,还是“狗吠声巷中,鸡鸣桑树颠”的悠然,都展现了诗人以诗还乡的精神追求。朱英诞受陶渊明影响颇深,无论是“这时候北平黄昏/像江南/翠尾扫开三月雨”(《晚雨旋晴》)这般对“北平”这个借居故土的江南化描绘,还是“我所爱的渔人在哪里/桃花依旧/田舍空了/捕鱼的人儿呢/不见”(《怀古》)这般对梦中“江南”的创造性想象,都是对自我漂泊困境突围的有力尝试。
然而,相较于古人,朱英诞对“故乡”“家”的追寻显得更为深入。心灵与地理坐标的错位造成了朱英诞“无根者”的主体生成与精神家园的缺失,无论是江南还是北平都无法填补其“无根”的精神困境。当“以诗还乡”无法满足朱英诞对“家”这一文化符号的追求时,诗人便不再一味模仿古人将“诗”单纯地作为满足“还乡”欲求的工具,而是作为“家”本身而存在着,完成了从“以诗还乡”到“以诗为家”的创造性转变:“唯有诗是昙花/它还诸一点温暖给我/……但江南永远隔在雾里以致雾会变成了雪……”(《试茶》),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针对知识分子的流亡话题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在体验那个命运时,能不把它当成一种损失或要哀叹的事物而是当作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事物、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吸引,那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乐趣。”虽然流亡与漂泊并不相同,但二者都让知识分子们进入了“无所依靠”的精神状态,面对与自我精神世界彻底分裂的社会空间,陷入“无依靠”困境的诗人又该如何突围?居伊·德波认为突破的方式之一便是“构建情境”,所谓“构建情境”便是“为了弥合人们的内在精神分离与分裂,为了摧毁平庸化的日常生活所建构的虚假迷人景观,必须重新建构人们真实的生存情境,必须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的生存瞬间”。当诗人意识到自己“无根者”的身份事实时,他便不再追寻灵魂的地理归宿——“这儿是你的家/但无所谓家”(《夕阳》),转而探索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灵魂归宿——使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的瞬间,即诗歌本身作为家园的存在价值:
我在北京度过的三十年间,移居过四次,而五个居处是都够不上称作一个小园的,于是我就渴望地幻想我的诗的局面是一座小园了。
——1966年《小序》
对于北平的“小园”,朱英诞是这样解释的:“北京,——改称北平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这儿,除了园林深密,几乎小门深巷家家宅边有古树,家家各自形成一个小园……古老的理想‘不取高深,但取旷敞’与当我的绕屋的篱园,更无根本的不同了。”在朱英诞看来,“北平”的“小园”与“绕屋的篱园”没有“根本的不同”,然而三十年后,在北平移居四次的他,为何称“五个居所是都够不上称作一个小园的”?对此,朱英诞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小者,自己也,小园也就是那古老的‘自己的园地’吧?”归根究底,虽在北平居住了近乎一生,朱英诞却始终未能寻得“自己的园地”,于是诗人开始幻想“诗歌”本身便是属于自己的园地了:
水边商籁
我仿佛悲哀我是没有家的人/(事实上证明也是如此)/于是我爱自己有自己的镜子/一个不认识的人和我亲密/对语,——但,不许握手!/一个洁净空旷的世界隔离着/我们,你和我;于是我爱我的/船儿经过,我也爱我的/风经过/也爱我的/树林经过: 却不愿想到那死/正如一个受着自杀的诱惑的女儿/而对花睡去/我也爱着/花是我的一面镜,啊遨游的孩子,/青青天如果是苍苔/小园里寂静是繁华的爱! 唉!
这首小诗,是朱英诞以诗歌为家园的最佳注脚,它描绘了一个无家之人,历经爱、孤独、死亡,却依旧坚定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属于自己的爱的个体形象。在诗歌中,“我”的内心活动恰恰对应着诗人对“北平”或者说“心理家园”的寻找历程:
诗歌开篇就表明了“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家”指代的自然是内心的遥远的江南园地,然而事实上诗人永远不可能回到那里,于是便流露出了“悲哀”的诗情。“我”试图从“北平”这一面镜子中汲取属于江南的乡味,“不认识的人”便是诗人想象中属于江南的自我——可以与之亲密、对语,却永远无法触碰彼此。“洁净空旷的世界”指代着巨大而又无法弥合的时空间距。“一个洁净空旷的世界隔离着/我们/你和我……”这里诗人凸显了“你和我”被这个巨大“世界”隔离的事实,这种隔离是如此的遥远与绝望,以至于诗人不再追索镜子中的美好,转而探求“船、风、树林、睡花”的美妙之处,“于是我爱我的/船儿经过/我也爱我的/风经过/也爱我的/树林经过……”。这里的诗句有着两种理解方式:一是诗人爱船、风、树林的同时,它们也深爱着他,二是诗人爱着这些事物,得到的却只是沉默的回音。诗人显然自身也陷入了迷惘与空虚,“却不愿想到那死,正如一个受着自杀诱惑的女儿/而对花睡去”,诗人最终仍是爱而不得,他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与迷惘。此时,另一面镜子出现了,“花”带着诗人沉沉睡去,如孩子一般遨游天空,之后梦醒了,诗人的小园中充满着他爱的事物:船、风、树林、睡花……却始终以沉默回应着诗人,“唉”代表着诗人从梦中回到现实,巨大的空虚感挤压着其脆弱的心理时所发出的哀叹。
诗人在这首诗中,通过对自我意识的超验表达完成了对诗歌园地的寻找——漂移中的无家者与镜中的自己进行着超时空对话,“船、风、树林、睡花”等在此时由单纯的意象上升为其诗歌小园中的构建符号,诗人试图通过构建这样的一个诗歌小园,来刺透漂泊境遇所带来的空虚,抵达诗性内部借以抚慰自身。虽然对于这样的尝试,诗人始终报以消极的态度,“爱与不爱”成为诗人热衷探讨的话题,对诗歌园地的热爱能否反哺自身,让自己最终取得精神上的补足语慰藉?或许只能以“唉”这样的叹息作结,但其在漂泊命运中对于诗歌内部世界的不断构建和调整,对自我主体的重构与对话,仍在一定程度上舒缓内心难以释放的无力感与空虚感,同时为其诗歌增添了超越现实与时空的巨大美感。
在《小园集》的跋中,诗人对其创作这样评价道:“私意以为即此可见少年时之纯净,对人间琐屑如之和抵抗而复不自觉。”在诗人看来,其诗歌创作本身便是“无根者”自身以“少年”这一饱含情绪的精神载体对人间琐屑的“抵抗”,“以诗为家”便是对自我困境反抗的一种姿态,这样的抵抗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历经岁月磨砺,人世数载之后不自觉之结果。作为时代大潮之外的“无根流浪者”,朱英诞清楚地认识到内心的困境,并将自我的诗学理想、情感流动注入诗歌当中,以期到达诗歌家园的彼岸,或许这条道路永无尽头,如同《蓝天》中所描绘的那样,“人间的琐屑的道路/美好而又艰难的道路/永日伸长——”,但朱英诞的抵抗姿态也促成了其较高的诗学成就与现代性品格,其作为“无根者”的漂泊诗思为我们理解他的诗歌提供了一条幽暗的小道。
注释:
①朱英诞:《神秘的逃难》,《我的诗的故乡》,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页。
②朱英诞:《神秘的逃难》,《我的诗的故乡》,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③朱英诞:《〈小园集〉自序》,《我的诗的故乡》,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④朱英诞:《神秘的逃难》,《我的诗的故乡》,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
⑤朱英诞:《〈春草集〉后序——纪念写诗四十年》,《我的诗的故乡》,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8~69页。
⑥朱英诞著,王泽龙主编:《朱英诞集(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2页。本文朱英诞诗歌均出自王泽龙主编的《朱英诞集》第一至五卷,不再另注。
⑦陈太胜:《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⑧朱英诞:《〈小园集〉自序》,《我的诗的故乡》,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⑨北岛:《语言》,《北岛作品精华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⑩胡适:《追忆志摩》,《云游:徐志摩怀念集》,兰亭书店198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