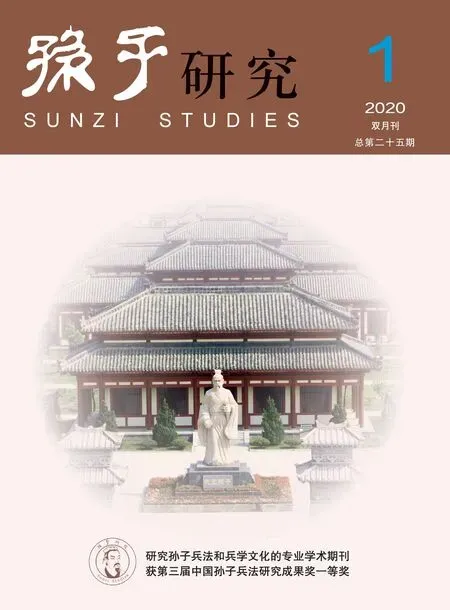《春秋》“围齐”载明了齐长城的建成
《春秋》是六经唯一有确切作者的个人著作。孔子说:“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春秋》是史书,其中有大约五分之一的文字是有关军事方面的。孔子对战争有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他对 “侵”“伐”“战”“围”等关键词的使用就可见一斑。齐长城是为阻挡和抵御西南方向的敌国入侵而建的,孔子在《春秋》中记述齐国与晋、鲁等国的战争时反映了齐长城的存在。《春秋·襄公十八年》:
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
“围齐”表明了齐长城在抵御晋、鲁等国入侵时的作用,载明了公元前555年,齐长城已修筑完成的历史事实。
《春秋》记事严谨而简约,蕴含的信息量很大,结合《左传》《国语》等研究《春秋》,更容易发现其丰富的内容,考证出《春秋》所记述的客观事实。齐长城的建筑年代就隐含于《春秋》“围齐”和其他相关内容的记述中。《骉羌钟铭》“韩宗彻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则以实物印证了《春秋》“围齐” 的准确记载。
一、《春秋》“围齐”表明齐长城公元前555年已经建成
《春秋》对战争的记述十分简练,与《左传》相比,在现代人看来,《春秋》的记述不过是个题目而已,连提纲都算不上。所记鲁襄公十八年之“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是一场有十三个诸侯国君亲自参加的历时半年的大战,第二年春天,鲁襄公才“至自伐齐”(《春秋·襄公十九年》)。
(一)从孔子对关键词的使用看:“围齐”是确实的
“围”是孔子记述战争常用的关键词之一。《春秋》记“围”有44 次,起于鲁隐公五年“宋人伐郑围长葛”,终于哀公七年“宋人围曹”。“环其城邑曰围”。《春秋》所记“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围某国的首都,这都记其国名,如僖公十九年:“秋,宋人围曹。”二十七年:“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宣公十一年,“楚子围郑”。定公四年,“楚人围蔡”等,围困国都有32 次。二是围城邑,即国都以外的城。围城邑又分两种情况,一是围别国之城邑,如“宋人伐郑围长葛”就表明“长葛”是郑国的城邑,再如僖公二十三年:“春,齐侯伐宋,围缗。”襄公元年的仲孙蔑等“围宋彭城”共8 次。二是围本国反叛的城邑,仅见于鲁国,如昭公十三年“围费”,定公十年两次“围郈”等4 次。
《公羊传》《谷梁传》都说“邑不言围”,但孔子12 次书“围”城邑“围”的对象,都是城。如僖公六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两传都说“邑不言围”,是《公羊》《谷梁》把都城之外的城都理解为“邑” 了。此“新城”明显是“城”。因为有了城墙,军队不能进入敌国城中,所以“围”。如果没有城墙阻挡,兵车可以进入其内,则没有“围”的必要。所以,《春秋》所记“围”的都是“城”,无城则无“围”。
“围”是攻的第一步。春秋时期攻城,一般先长期围困,楚国曾围困宋都达9 个月。《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愤而蚁附之,杀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齐国曾用了一年的时间“围莱”而“齐侯灭莱”(《春秋·襄公六年》)。晋、鲁等国这次伐齐,因不能像34年前鞌之战那样无碍地侵入,被齐国挡在境外,所以才“围齐”。
(二)从孔子对关键词的选炼看,“围齐”是经过反复斟酌的
晋、鲁等12 国诸侯从今济南长清孝里镇“围齐”,本也可以记作“伐齐”或“战于平阴”,但孔子把它记为“围齐”。这里的“围齐”之“齐”显然不是齐国都城临淄。以前孔子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到底该怎样记述,孔子一定反复考虑过,经过认真斟酌之后才确定记为“围齐”的。“环其城邑曰围”,“围”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城”,没有“城”就无所谓“围”,《春秋》中的另外43 例,“围”的都是城。那么,这次“围齐”有“城”吗?回答是:有——齐长城。正因为有齐长城,晋、鲁等兵才无法进入齐国而不得不拼死攻打防门,因有齐长城,晋将荀偃、士匄才会“以中军克京兹”,因有齐长城,孔子才记为“围齐”。当时的诸侯大军就是环于齐长城外围困齐国的。
虽然“围齐”是客观事实,但“围”不能表明这次战争的性质。如果用“伐”,则无法说明事实上的“围齐”,而“围齐”是这次伐齐的一大特点。但“围齐”不能表明孔子对这次战争的定性,这次12 国诸侯“围齐”是齐国多次侵鲁引起的,作为一个鲁国人,对这场战争不能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性。经过再三思考,孔子采取了“围”“伐”相搭配的办法,在写出“围齐”之后,又在第二年春天补出“公至自伐齐”,这样就把这场战争记述得完整了。
《左传》在记述这场战争时,用得是“伐”,如:“晋侯伐齐,将济河……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溴梁之言,同伐齐。”以此也可以想见孔子在当年著《春秋》时反复推敲的认真精神。
(三)《谷梁传》和《公羊传》对“围”解说相矛盾
因为忽略了齐长城的存在,对《春秋》的“围齐”,《谷梁传》和《公羊传》都不解。《谷梁传》说:“非围而曰围,齐有大焉。”(《春秋三传·襄公十八年》)“大”是张大的意思,意思是说“围齐”是为了张大齐国。但这有什么根据呢?一个“怙恃其险,负其众庶,弃好背盟”(《左传·襄公十八年》),多次侵略鲁国,挑起战争的齐国有什么值得孔子“大焉”的呢?刘敞批驳说:“《谷梁》曰:‘非围而曰围’,非也。《春秋》信史也,若未围而言围,岂得为信史哉?”(《春秋三传·襄公十八年》)孔子是不会“非围而曰围”的,从《左传》的记载看,诸侯大军确实“围”了齐国,只不过不是一周而已。
《公羊传》在解说“公至自伐齐”时说:“此同围齐也。何以致伐?未围齐也。未围齐,则其言围齐何?抑齐也。”(《春秋三传·襄公十九年》)《公羊传》举出“未围齐”的理由是“公至自伐齐”,意思是既然同围齐的鲁襄公“至自伐齐”,那说明就不是“围齐”,好像不能既围又伐。其说:“言围齐者何?抑齐也。”“抑”是贬抑,压低的意思。《公羊传》对“围齐”的理解与《谷梁传》恰好相反,《公羊》说“抑齐”,《谷梁》说“大焉”。这两种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认为是孔子的主观意志的表达,而不是对客观事实的如实记录。《春秋》虽有字面上与事实不符的个别案例的记述,但绝大部分是忠于事实的。两传之所以认为“非围而曰围”主要是他们对事实的了解不够,只有把孔子的记述与客观事实相对照,才能证明“围齐”是否真实。事实上是又围又伐,其实围就是伐的开始,攻入齐国以后就不能说是“围”了,所以孔子说“公至自伐齐”,这与前面的“围齐”并不矛盾。
(四)从《左传》的记载看,齐灵公二十七年已经建成了齐长城
《左传》对这次“同围齐”有较详细的记载,从晋、鲁、卫联军所进攻的据点,我们可以看出齐长城的存在和方向。
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溴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及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弗克。
“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偌大的齐国,面对12 国诸侯的入侵,齐灵公在平阴只是“堑防门而守之”,就把侵略军挡在了国境之外,令“诸侯之士门焉”。诸侯国的勇士只有攻打防门才有可能进入齐国,“齐人多死”,晋、鲁应该死得更多。这说明,只要死守防门,当时的晋鲁大军就无法攻入齐国。如果其他地方能进入齐国,晋、鲁还会在防门拼命吗?这说明,其他地方,至少是在相当的距离内,晋鲁之军是无法进入齐国的。鲁国与齐是邻国,对边境一定很熟悉,鲁国是这次伐齐的主要发起国,一定会向晋军提供一个好的进攻方案,晋、鲁联军死攻防门,说明其他地方根本无法攻入齐国。这说明,齐国的长城挡住了晋鲁等国的兵车。晋将荀偃说“齐环怙恃其险”,齐国懂军事的宦官夙沙卫说,“不能战,莫如守险”“鲁卫请攻险”。这三处“险”字所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那就是在齐鲁边境上齐国有据以阻挡外敌侵入的据点。仅有这些险要之点还不行,在这些点与点之间,敌人也不能进入,“守险”才有实际意义。在这些险要之处,齐国已经做了人工工事,且有士兵防守,这就是齐人要“守险”、鲁卫要“攻险”的客观实际。这也表明这时有齐长城。
究竟有多少险要之处,这些“险”与“险”之间有多远距离?我们分析一下《左传》的记述。“防门”是险要之一,其北面是平阴城,齐侯御诸平阴,齐军大营就驻在平阴,所以当齐灵公撤退时,叔向才说:“城上有巫,齐师其遁。”巫山也是一处险要,而且是这一带的制高点,所以灵公才“登巫山以望晋师”,这里离平阴城,有一段距离,起码是平阴城不在山上。齐军是在“十一月丁卯朔”(初一)撤退的,晋人想要乘胜追击逃归的齐军,“鲁卫请攻险”,鲁、卫为什么提出与盟主晋国不同的进攻目标?鲁、卫都与齐国为邻,齐国势力扩张,受害的是鲁、卫。如果不把齐国“怙恃”的险要之点拔除,晋国退兵之后,齐国就有可能据此再侵伐鲁卫,攻克这些据点,就会使齐国规矩一些。晋平公认为鲁、卫的意见有道理,听取了他们的意见,首先向这些险要之处发起攻击。“己卯,荀偃、士匄以中军克京兹”,这是晋军的主力,“己卯”是11月13日,晋军用了12 天才攻下京兹。“乙酉,魏绛、栾盈以下军克邿”,“乙酉”是19日,晋将栾黶战死,其子栾盈接替父职,攻克了“邿”。“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弗克。”晋国的三军都参加了“攻险”,用了近20 天时间,有两处攻下了,“卢”没能攻下。尽管齐军主力撤退,但并没有全线崩溃,晋、鲁联军遭遇了顽强的抵抗。晋军又用了13 天时间攻到了齐都临淄。
从《左传》所记叙的这些地点看,大体上是东西向的,杜预的注解说,京“在平阴城东南”;“平阴西有邿山”(《春秋三传·襄公十八年》)。这是符合齐长城的走向的。
(五)以齐长城与《春秋》对照,诸侯之兵确实是“围齐”长城
《春秋》之“围齐”,《左传》有比较详细的记述。在叙述“围齐”和攻打防门等“险”时,记叙了多处地名,记录了这次“围齐”的大体范围。因此笔者认定:“围齐”围得就是齐长城。那么,公元前555年“围齐”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齐长城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济水》说:
济水又北迳平阴城西,《春秋》襄公十八年,晋侯沉玉济河,会于鲁济,寻溴梁之盟,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者也。……平阴城南有长城,东至海,西至济,河道所由,名防门,去平阴三里。齐侯堑防门即此也。其水引济,故渎尚存。今防门北有光里,齐人言广,音与光同。即《春秋》所谓守之广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阴东北,昔齐侯登望晋军,畏众而归。师旷、刑伯闻鸟乌之声,知齐师潜遁。……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谓之孝子堂。
晋、鲁等十八国诸侯“围齐”,攻打防门,齐灵公登巫山以望晋军,为我们留下了查找当年地址不可移动的证据巫山。河流虽有变,但与山联系在一起,也就定位了。郦道元从认定巫山和广里而认定“平阴”是正确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齐长城的起点是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广里村。广里村因齐灵公“堑防门而守之,广里”而得名。广里,春秋时属“平阴”,就在齐长城的西端。
司马迁也认为这次发生在平阴的战争是“围齐”。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晋平公三年”写道:“率鲁、宋、郑、卫围齐,大破之。”在同年的“郑僖公十二年”亦写道:“晋率我围齐。”
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但巫山仍在,广里村仍在,齐长城仍在,济水虽被黄河占道,但黄河在济水故道仍奔流不息。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的“冬十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围齐”和司马迁在《史记》中写的“围齐”,是实实在在的。
二、从“围齐”与“战于鞌”比较中,能证实齐长城的修筑年代
《春秋》“围齐”的记载表明了鲁襄公十八年、齐灵公二十六年、晋平公三年,公元前555年,齐长城已经建成且起到了阻止晋、鲁等国侵犯的作用。那么,齐长城是什么时候开始建设的,其起因是什么呢?
风俗画的出现,表明艺术走入了大众生活。风俗画家的创作素材一般都取自现实,主题以反映社会的日常生活与民俗为主,受到社会各阶层市民的喜爱,这些风俗画作品大多通过人们津津乐道的绘画形式展现生活的每个角落,尽管在大众的意识中,它没有通过主流的艺术形式呈现,但却从没有停止过发展之步伐,风俗画的魅力对大众的审美趣味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各个阶层的市民都能愉悦地去欣赏这一艺术形式。从风俗画的出现到发展,可以看出绘画是如何从贵族阶级走向平民,从神坛走向生活的。
齐长城作为一项空前大的创新军事工程,其创造肯定与军事有关,与大战有关,与来自西南方向的敌国入侵有关。循着这个思路,我们继续在《春秋》《左传》中寻找答案。《春秋·成公二年》: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帅师会晋郤克、卫孙良夫、曹公子首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
这年是齐顷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比“围齐”早34年。这次战争,史称“鞌之战”,又称“靡笄之战”。“靡笄”就是历山,鞌之战就发生在今济南市区,晋军曾追击齐军“三周华不注”,华不注就是黄河南岸的华山。
(一)从晋鲁两次伐齐的路线看,走的是一条路
春秋时期是车战,马拉着战车,行进很不容易,所以进军路线的选择很重要,不是随便怎么走都能到达目的地的。这次四国侵齐之前,“夏四月丙戌,卫孙良夫帅师及齐师战于新筑,卫师败绩”(《春秋·成公二年》)。新筑是卫地,故址在今河北魏县西南,与今山东莘县相隔大名县,在济南的西南方向。新筑战后,齐军撤兵,而晋、鲁、卫等伐齐的四国联军则“师从齐师于莘,六月壬申,师至于靡笄之下”(《左传·成公二年》)。晋、鲁等军是跟着齐军的车辙侵入齐国的。
可以肯定,鲁襄公十八年的晋、鲁、卫联军伐齐走得大体还是34年前的路线,但与34年前不同了,鞌之战,齐顷公在济南与晋军相战,这次,齐军向西南方向推进了数十里,“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把晋鲁联军当在了防门之外。
把《春秋》《左传》对这两次战争的记述进行对比,齐国的西南边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鞌之战时,敌军可以直入济南,这一次则被挡在了广里、巫山一线而无法进入齐国。这也让我们可以断定:公元前589年鞌之战时,齐国还没有长城,也就是说齐长城的修筑年代不会早于齐顷公十年。那么,在这30 多年里,齐国究竟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促使齐国筑成了长城呢?
(二)“尽东其亩”的惨痛教训
鞌之战,齐国失败了。晋、鲁联军攻到了离临淄城不远的袁娄,齐国的使者宾媚人在向晋军献上“纪甗、玉磬与地后”与晋、鲁展开谈判。晋国开出的停战条件之一是:“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宾媚人驳斥说:“《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左传·襄公十八年》)晋国之所以提出这样无理、不义的谈判条件,目的就是唯其兵车是利。同时,以此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齐国的田埂沟壑妨碍了晋军的前行,所以晋国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齐使坚决地拒绝了晋国的无理要求,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鲁、卫看齐国甚怒,恐怕真死拼起来对其不利,劝晋国撤销了这一无理要求,与齐国达成停战协议。“秋七月,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春秋·成公二年》)
晋国“尽东其亩”的无理要求,启发了齐国修筑长城的创意。
(三)灭莱的成功,坚定了齐国修长城的决心
顷公死后,其子灵公环立。灵公亦不在西南方向招惹诸侯,而是专谋向东发展。自鲁襄公二年春天“齐侯伐莱”到鲁襄公六年“十有二月齐侯灭莱”(《春秋·襄公六年》),他用了5年时间灭掉了莱子国,使齐国的土地几乎扩大了一倍,整个胶东地区全部归入齐国的版图。齐国灭莱,“堙之环城傅于堞”,用了一年时间修筑工事,围绕莱子国都城又套了一圈城墙,而且在新城墙上建了垛口等。齐国围绕莱都建城虽然费了很大的劲,但与取得灭莱的胜利相比,那还是很值得的。齐国人看到了军事工程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想想20年前晋军要其“尽东其亩”的无理要求,想想城墙对兵车的有效阻挡,使他们产生了修长城的想法。围莱修城锻炼了齐国一支有经验的工兵队伍,再加上当时齐国的富庶,这让齐灵公坚定了修长城的信心。大概在灭莱之后不久,齐长城的修筑就开始了。
(四)从齐对晋鲁的不同姿态看齐长城修筑的具体时间
开始伐莱是在齐灵公十一年,这之前要有几年的准备工作,齐灵公刚即位的几年,不会有修长城这样的大动作,当时不具备修长城的条件。齐长城的开建应该是在灭莱之后。
大约用了8年时间,完成了齐长城的修筑。这虽然史无明文记载,但我们同样可以在《春秋》的记述中获得信息。自鞌之战败后,齐国便不再向盟主晋国挑衅,不再侵犯鲁、卫等国,而是归顺了盟主晋国,直到鲁襄公十四年,齐国还参加了晋国组织的诸侯伐秦。但到了鲁襄公十五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齐侯伐我北鄙,围成,公救成,至遇。(《春秋·襄公十五年》)
齐侯伐我北鄙。(《春秋·襄公十六年》)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成。(《春秋·襄公十六年》)
秋,齐侯伐我北鄙,围桃。齐高厚帅师伐我北鄙,围防。(《春秋·襄公十七年》)
冬,邾人伐我南鄙。(《春秋·襄公十七年》)
秋,齐师伐我北鄙。(《春秋·襄公十八年》)
这么密集地伐鲁,与自成公三年到襄公十四年30年无一次伐鲁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齐国之所以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是因为以前没有长城,现在有长城了。这就是晋卿荀偃说的“齐环怙恃其险”,也就是齐长城。以此可以断定,这次侵鲁之始,即鲁襄公十五年,就是齐长城建成之年。自灭莱到伐鲁,中间有8年,就是建筑齐长城的时间。
三、《骉羌钟铭》铭文与《春秋》“围齐”相一致
晋平公率领十二国诸侯同“围齐”,在春秋时期是极为重大且唯一的事件,不仅《春秋》《左传》有记述,在一些出土文物上也有铭文记载。
(一)葛陵竹简“晋师战于长城之岁”
1994年在河南新蔡葛陵发掘一座楚墓,出土1571 枚竹简,研究报告指出简中有九条大事纪年,其中有一条是:
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①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33页。
这事的叙述顺序,也可以是:“晋师战于长城之岁,大莫敖阳为。”可以译为:晋军战于长城之年,“大”莫熬阳为。“莫熬”是楚国的官职,阳为是楚国的一个人名,《左传·昭公十七年》有“吴伐楚。阳匄为令尹”的记载。究竟楚国怎么“大”莫熬,我们不得而知。“晋师战于长城之岁”与“大莫熬阳为”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前者只是一个“纪年”而已,就像说“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样。
中国的纪年是以干支纪年,起于“甲子”,终于“癸亥”,60年循环一次,再配以天子或国君的在位时间,这样某一年就可查了。但是这很抽象,难于记住。于是就有一种“以事纪年,以大纪小”的纪年方法。就是以某一件众所皆知的大事或新奇的事来记住这一年,其他一些事只要记住与这件大事的时间关系就行了。
《左传》中就常用这种方法,如记齐国灭莱这件事之开始时就说:“于郑子国之来聘也,四月,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左传·襄公六年》)这是说围莱的开始时间是郑国的子国访问鲁国的那一年。子国访鲁在齐灭莱的前一年,即鲁襄公五年,《春秋》有记载。从上年的四月围困莱子国,到了第二年十一月灭莱,齐国围困莱子国都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于郑子国之来聘也”就是表述齐国围莱开始的时间的。
“大莫敖阳为,晋师战于长城之岁”,楚国以晋军战于长城这事作为纪年,正说明了这事在当时的重大影响。
李学勤先生把“晋师战于长城”与《骉羌钟铭》联系在一起,认为是一回事是很正确的。
(二)《骉羌钟铭》:“入长城,先会于平阴”
骉羌钟于1928年出土于河南洛阳金村,一组14 件,其中两件藏于加拿大皇家大略博物馆。其中有长铭文如下:
唯廿又再祀,骉羌作戎厥辟,韩宗彻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楚京,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成烈,永世毋忘。①李学勤:《文物中的古文明》,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434、435页。
文中的两个空白处的两字,杨树达先生说:“字从嚞声,当读慴。……《说文》训强取,经传通作夺字。……慴惧震动而夺气也。”③
铭文今译如下:
二十日,又再一次祭祀牺牲的武。骉羌作表彰军功的铭文:韩宗彻率领武等先征秦后伐齐,进入齐长城,先集合于平阴,然后分兵进攻。武随韩彻到达寺力,武的奋不顾身震慑了楚京的齐军,为韩宗部立下战功。武的奋勇杀敌受到了韩宗的赏赐,得到了晋公的命名,记载于王室的档案。根据国家的礼法将其事迹刻铸于铭,武文成烈,使其事迹永世不忘。
青铜器的断代是件极为艰难而复杂之事,根据铭文内容断代是最基本的方法。《骉羌钟铭》所记“入长城,先会平阴”是场大的战争,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样的大事往往有历史文献记载,可以采取铭文与史籍相对照以确定年代的办法。
从铭文“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以及葛陵简“晋师战于长城之岁”看,这场战争的主导者是“晋公”。晋公上有“天子”,下有群臣,“韩宗”是他的臣下。所以,当韩宗的部下“武”立下大的战功之后,才“赏于韩宗,命于晋公,昭于天子”。“命”是“命名”的简语,晋公有“命名”的权利,他还要上报天子,“昭”是昭明的意思,大概是在周天子那里备案。这可见晋公是这场战争的领导者,不然,命名之事不会是晋公。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盟主、霸主,后来六卿专权,晋侯的权利逐渐削弱,到了晋“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魏之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史记·晋世家》)。这时候的晋公是绝对没有领导包括韩在内的诸侯的力量了,更不要说韩、赵、魏为侯之后的事了。韩等“初为侯”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晋公领导韩宗“入长城”只能是在韩宗为晋卿之时,绝不可能在韩氏为侯之后。可以断定,韩宗“入长城,先会平阴”或“晋师战于长城之岁”是在春秋时期,而不会是战国时期。那么,这事在春秋时期的那一年呢?
铭文有“韩宗彻率征秦迮齐”,这话的意思是:韩彻率领征秦之军伐齐。韩彻是韩氏正宗,所以称其为“韩宗”。这里是下属对长上的称呼,“彻”应是字。“迮”是“逼迫”之意,可以理解为“伐”。韩彻是在征秦之后又伐齐的,这样的事不多,可能有唯一性。从“赏于韩宗,名于晋公”我们知道韩宗是晋卿,这事是晋国征伐之事。
《春秋·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叔孙豹、晋荀偃、齐人、宋人、卫北宫括、郑公孙虿、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这次伐秦,“晋侯待于境,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左传·襄公十四年》)。韩起是当时的六卿之一,他是参加了这次“征秦”的。韩起是韩献子韩厥的次子,本无承袭其父爵位的资格,因为他的哥哥韩无忌有“废疾”,无法继承父位,韩起才得以立为“韩宗”和晋卿的。《左传·襄公七年》载:“冬十月,晋韩献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废疾,将立之。辞曰:‘《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无忌不才,让,其可乎?请立也!’……庚午,使宣子朝,遂老。晋侯谓韩无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宣子就是韩起,他自此为晋卿至到鲁定十三年,《史记·韩世家》载:“晋定公十五年,宣子与赵简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因此我们知道《骉羌钟铭》之“韩宗彻率征秦迮齐”的韩宗就是韩起。春秋时期晋卿只有韩起一人“征秦迮齐”,没有第二人。
从“征秦”到“迮齐”,中间仅隔3年,晋国姓韩的卿一人连续率军参加这两次战争的只有韩起。以此可以确凿地断定:“迮齐”的韩彻就是跟随晋平公“围齐”的韩起。在鲁襄公十八年“围齐”后,“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韩起是上军佐,晋六卿之一。因此,我们根据铭文“韩宗彻率征秦迮齐”和《左传》断定:《骉羌钟铭》所铭之事就是《春秋·襄公十八年》晋、鲁等12 诸侯“围齐”、伐齐之事。
从《左传》到《骉羌钟铭》到《葛陵简》都载明了晋平公三年晋、鲁等联军入齐长城伐齐这件事,这也证明了孔子《春秋》“围齐”记载的准确性和可信性。从上述考辨中,不难看出,《春秋》是考定齐长城建筑年代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