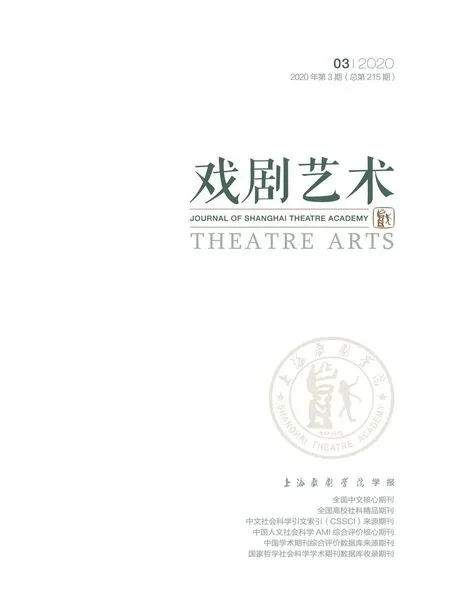论昆曲《桃花扇》舞台美学的中西交融与本体转向
刘 津
关于《桃花扇》的创作,孔尚任自云旨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1)(清)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 :《桃花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2页。而《桃花扇》的纸本传播与舞台演出效果,在《桃花扇本末》中有一段记载:“《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灺酒阑,唏嘘而散。”(2)(清)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 :《桃花扇》,第1-2页。此“洛阳纸贵”的旷世之作,勾起故臣遗老们的亡国之痛。“灯灺酒阑,唏嘘而散”则记录了观众的观剧反应。王国维说:“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3)王国维 :《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1页。后来,竞演《桃花扇》的热潮逐步冷却,后来竟至销声匿迹。从现有资料看,四大名剧中,《桃花扇》连一个演出的折子戏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4)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由钱德苍编选,汪协如点校完成的《缀白裘》堪称当时最受欢迎的昆腔戏摘锦大全,收录了四百余个折子戏,但没有收录一出《桃花扇》的折子戏。陆萼庭先生根据《申报》等上海旧报戏目广告整理出的《清末上海昆剧演出剧目志》中,《桃花扇》依旧没有任何踪迹。孙崇涛编著的《风月锦囊考释》亦未收录《桃花扇》。对以表演为本位的戏曲来说,失传的是演员的身段、鼓板锣鼓、宾白念法等 “场上”的演法记载。造成《桃花扇》绝响的原因,大约与剧情触犯清王朝之忌讳有关。,实在令人惋惜。在当代昆曲舞台上,仅有江苏省昆剧院(简称“江苏昆”)排演过串本《桃花扇》。1987年,张弘在整理《桃花扇》时,为《题画》一折的“二度桃开,物是人非”的情境所触动,与王海清、石小梅共同捏了这一出折子戏,首次让《桃花扇》中的《题画》一折复归舞台。(5)张弘,江苏省昆剧院国家一级编剧,1991年版《桃花扇》《一戏两看桃花扇》的编剧。参见张弘老师谈《30年磨一戏——〈桃花扇〉创作》的资料,采访人:刘津,时间:2018年8月10日,采访地点: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之后,江苏昆在此基础上编排了1991年版《桃花扇》。2001年,昆曲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江苏昆邀请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执导《1699·桃花扇》,由中、日、韩知名艺术家共同助阵,并于2006年3月17日在北京首演。2017年4月14日,《一戏两看桃花扇》全国巡演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拉开序幕。从1987年到2017年,江苏省昆剧院三十年悉心打磨《桃花扇》精萃,是昆曲当代演绎不断提纯、走向精致化的一个缩影。20世纪以来,自西方话剧传入中国,使古典意义上的传统戏曲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长时间以来,中国戏曲面临着多方位的“创新焦虑”,而舞美的改革成为首要阵地。江苏昆的三个不同版本的《桃花扇》,最大的差异也外显在舞美上。江苏昆30年磨一戏,走出了一条从“以西鉴中”到“本体转向”之路,此转向并非局限在对传统艺术单纯的恢复和持守,而是在承续中国戏曲美学精神基础之上的新探。
一、昆曲《桃花扇》三个版本中剧本剪裁之下的舞美呈现
传奇文字浩繁、精美,而现代的演剧习惯,又不允许演出整本。于是,增删取舍便成为剧本改编、剪裁的第一要义。如何改写,其拿捏的分寸也值得斟酌,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舞台形式的呈现成为剧本改编的先决条件。从昆曲《桃花扇》的三个不同版本来看,其剧本剪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改写《余韵》、还原求真和寄“情”赏“趣”。
(一)舞美思维的先导——改写“余韵”
1991年版《桃花扇》在演出上有一定的开创之功,演出剧本由《访翠》《却奁》《圈套》《辞院》《阻奸》《寄扇》《骂筵》《题画》《惊悟》和《余韵》十折戏组成,铺陈了全剧的故事线与情感线。张弘在这一版《桃花扇》中,有心延展《桃花扇》所传递的悲剧意识,改编了《余韵》一折,在舞台上设置了一道虚拟的“推不开的门”,这是隔开侯方域和李香君,使之最终未能相见的一扇观门,这与原著二人双双入道的结局不同。在孔尚任原著“入道”一节,侯方域与李香君邂逅白云庵,惊极喜极,心心念念“夫妻还乡、人之大伦”(6)(清)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 :《桃花扇》,第170页。,却被张瑶星道士当头喝破:“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7)(清)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 :《桃花扇》,第170页。两人闻之冷汗淋漓,大彻大悟,双双入道。从受众心理来看,总是期望有情人终成眷属,成不了,便是悲剧。
在舞台呈现上,这道虚拟的“推不开的门”阻隔了原本要相见的侯方域和李香君。门外,香君还在苦苦找寻被她虚构出来的那个理想的“侯郎”。她说:“想他此时,不在岭南,定在闽北,不在粤东定在赣西,那里义旗云集,烽烟犹烈,正是男儿一展抱负之地,正是壮士戳力报国之时。哪怕千山万水、天涯海角,寻不着侯郎,香君死不瞑目。”(8)张弘 :《张弘话戏——寻不到的寻找》,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9页。不见,在她心里还有一个理想的“侯方域”存在,政治理想的一致是她倾慕的基础;见了,“爱”未必随着理想的不复存而存在。门内,侯方域入道,空余感叹“一介书生,挽狂澜无力,投新主无颜,空怀壮志,报国无门”(9)张弘 :《张弘话戏——寻不到的寻找》,第46页。,他万念俱灰,并未去给李香君开门,与自己心爱之人见面,只能吞声而泣;而李香君也并不知道门内之人正是朝思暮想的侯方域。一个苦苦寻觅,另一个却因时过境迁,惭愧天地,不敢相见。就侯李而言,推开这扇门是很轻便的,然而,见亦悲,不见亦悲。比躯壳不团圆更令人悲哀的,是精神的不团圆。正如张弘所言,戏曲舞台的方寸之地,有界亦无界,倘若用实景,大抵会受到无尽桎梏,无法接近“真实”,这道“推不开的门”,饱含悲剧的美学张力,将门内外两人截然不同的情绪投射到观者心中,一面叹惋于侯李永恒的分离,另一面令人感慨这茫茫孤另、千古寂寞的惆怅。《余韵》中这扇“推不开的门”,使“离合之情、兴亡之感”由此而生,感染了观者的情绪,产生了情感的共鸣。
(二) 舞美空间的重构——“还‘原’求‘真’”
《桃花扇》成稿于1699年(10)《桃花扇本末》云:“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己卯,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因此,这成为田沁鑫命名《1699·桃花扇》 的缘由。她说:“这次我对昆曲进行了‘空间改造’。”(11)田沁鑫 :《田沁鑫的戏剧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1699·桃花扇》的舞台视觉迥异于传统的“空的空间”式样的昆曲舞台表演场域。制作人李东称:“我们要做的是还原明末清初昆曲鼎盛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12)田沁鑫 :《田沁鑫的戏剧场》,第150页。作为昆曲经典剧目现代展演的一次探索性尝试,是在“还原求真”的创作思路上对剧本进行剪裁。“还原求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剧本,在梁启超点评《桃花扇》版本的基础之上,《1699·桃花扇》删减了人物和情节,由原戏的四十出改为六出,强调“在剧本上并没有新编和擅改”,将原作中散在各折的戏词抽取出来重新编排。二是表演,在《1699·桃花扇》的排演中强调对昆曲历史上的“文武并重”的还原。田沁鑫强调:“昆曲在过去的历史中,是文武并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文’与‘雅’部分逐渐成为主流,我们既然要恢复昆曲当年的繁盛场面,武戏部分是不可或缺的。要让观众看到,昆曲不仅仅是才子佳人,还是有力量、有场面的艺术。”(13)环球在线 :《中日韩三国演绎昆剧——〈1699·桃花扇〉》,2006年3月15日。《1699·桃花扇》为扩容武戏比重增演了原著第九出《抚兵》,将其安排在《沉江》之前,交代时局和战况,左良玉出场,带领武生展现了铿锵的唱腔、威武的工架和大将风范的造型,与孔尚任《桃花扇》原作正相吻合,故称为“还原”。三是舞台设计,试图还原《桃花扇》的故事场景。通过现代的舞美灯光、材质创作出具有立体感、多层次的摹真空间。“当他们在舞台上走动时,我很恍惚,像回到了属于我们的600年前的生活方式。”(14)田沁鑫 :《田沁鑫的戏剧场》,第151页。《1699·桃花扇》采用“戏中戏”“台中台”的写实布景方式,这种还原求真的理念与西方戏剧的“摹仿说”紧密关联。舞台上的“摹仿”既是创造性的再现,又是理想化的再现。田将“还原求真”的思路与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融合,力图复原《桃花扇》的故事场景。
(三)舞美观念的回归——寄“情”赏“趣”
2017年版《一戏两看桃花扇》分为全本演出版和选场演出版。江苏省昆剧院李鸿良说:“《一戏两看桃花扇》体现了江苏省昆剧院思考之后的态度,当下戏曲舞台,邀请话剧导演跨界执导、大制作、声光电是流行趋势,《一戏两看桃花扇》坚守传统,秉持原汁原味,让昆曲规律做主,用纯粹的南昆风格的表演艺术,对观众负责。”(15)中国江苏网 :《精心打磨三十年,一戏两看〈桃花扇〉》,2017年2月10日。在此,坚守传统、凸显昆曲规律主要体现在舞美观念的回归。《一戏两看桃花扇》的舞台上只有一桌二椅、纯色幕布;同时,也删减了舞台上的龙套演员,让观众的注意力完全聚焦于主要角色的表演。
在此基础上,《一戏两看桃花扇》的剧本剪裁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增加【哀江南】。在孔尚任原著的《余韵》中,苏昆生的【哀江南】将“兴亡之感”渲染到极致。全本演出版将它放置在第一出《访翠》之前,在选场演出版中,则将【哀江南】放在演出之后,演员们身着水衣,致敬先贤,发一声浩叹。一头一尾,首尾呼应。《桃花扇·全本》以侯方域为第一主人公,重点表现他的人生际遇和心理变化;剧本方面,全本分为九折:选取《访翠》《却奁》《圈套》《辞院》《寄扇》《骂筵》《后访》《惊悟》和《余韵》,与1991年版《桃花扇》脉络基本一致。
二是增加折子戏选场。《桃花扇·选场》分为《侦戏》《寄扇》《逢舟》《题画》《沉江》这五个折子戏。以李香君、侯方域、史可法以及在全本中难以铺陈的反面人物阮大铖,甚至是李贞丽、苏昆生、老兵这样三个大戏中的小角色为主角。每一折都既依附于大戏,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选场演出版的每一折侧重于让观众欣赏昆曲的唱、念、表演和情趣,凸显表演而非故事呈现。如《侦戏》主要表现阮大铖,让反面人物唱主角,此折将阮大铖前后截然不同的表情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颇具谐趣与讥刺的意味。《寄扇》一出重点体现李香君的坚贞不屈,但又有所改编,将原剧中点染鲜血为桃花的杨龙友改为李香君,以血寄情,以扇寄意,正如唱词《碧玉箫》所云:“便面小,血心肠一万条。手帕儿包,头绳儿绕,抵过锦字书多少。”(16)(清)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 :《桃花扇》,第95页。以溅血之扇代替书信,别有深重情义,亦有评论所言之“最伤心、最惨目”(17)(清)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 :《桃花扇》,第96页。的内涵所在。《题画》则着重刻画侯方域的形象。媚香楼二度桃花盛开,却已物是人非,李香君被选入宫,空留侯方域一人惆怅寂寞,正所谓“情无尽,境亦无尽”。(18)(清)孔尚任著,云亭山人评点,李保民点校 :《桃花扇》,第96页。
折子戏和全本之间互为侧重、彼此同源。折子戏虽短小,却浓缩了戏曲舞台表演艺术之精华,折子戏演出也让昆曲的生命得以更好地传承与延续,且对戏目定型有推进之用。因此,这也成为2017年版《一戏两看桃花扇》在剧本改编上增设折子戏的因由。可以说,《一戏两看桃花扇》是在1991年版《桃花扇》演出基础之上的优化和完善。
二、昆曲《桃花扇》三个版本的舞美之路——以西鉴中、偏离传统、本体转向
比较三个不同版本的《桃花扇》,它们最大的差异突出地体现在舞美设计上。中国传统戏曲较少物质性的布景,舞台道具设计也极为精简。厅堂、舟船、街道、广场、院落等均可作为戏曲“撂地为场”的表演场地,舞台上最主要的道具是“一桌二椅”。而现代舞台美术的布置主要由“形”“色”“光”三要素组成。“形”从物理空间上包括舞台背景、幕布设计、舞台道具等。“色”则从主要用色、辅助用色、色彩的冷暖、材质的搭配等对形象进行表现;光是现代舞台上最活泼、最灵动的舞美要素之一,从用光冷暖、用光区域、用光层次等方面对舞台形象展开辅助性的调度。20世纪以来,瑞士舞台美术家阿庇亚、英国导演兼舞台美术家戈登·克雷等极力反对传统的舞台平面布景,主张借助抽象的中性布景形象(如立方体、条屏、平台、台阶等)作为戏剧布景,对东、西方舞美设计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1991年版《桃花扇》 —— 条屏布景与多层平台
1991年版《桃花扇》的舞美造景试图突破传统,借鉴了戈登·克雷的 “条屏布景”,再配以多层平台,运用了“线”与“面”相结合,将传统戏曲舞台的净幔处理成类似条屏布景的线型结构,大大小小的“桃花扇”则以“面”的形式出现,交代剧情的故事空间。吴光耀对戈登·克雷的“条屏布景”理论有一段阐述和评价:
他使用了许多块长方形的条屏(屏风)作为基本构件, 在舞台上可以组成许多种的形状,千变万化的场景。在他的条屏布景中,他摒弃了一切生活细节,土地不长花草树木,建筑不设门窗屋檐。街道、广场、室内、室外,都由条屏通过多样的配合而显示出来,最终还要靠观众以自己的想象来加以补充才能完成。他的条屏像是音乐的音符,文字的字母,数学的数字,……它是构成布景的符号,由它所组成的布景是异常抽象和单纯化的。(19)吴光耀 :《戈登·克雷的舞台设计理论和实践》,《戏剧艺术》,1979年第1期。
1991年版《桃花扇》以条屏幕布为演出背景,条屏则选用纱幔制作而成,主色调选用冷光源,烘托剧情气氛。同时,在舞台上设置了三层平台,每一层平台以三步台阶、斜坡进行衔接,在每一平台的侧面亦设计了一些体量稍小的“桃花扇”造型,便于演员在不同角度进行表演时以“桃花扇”为背景。胡妙胜强调此类平台构成装置受到了阿庇亚的设计和理论的影响:“由一系列平台、台阶、斜坡组成的抽象的平台装置,又称形式舞台,……强调舞台上演员的存在,强调只有立体的东西才能和演员立体的身体相调和。”(20)胡妙胜 :《舞台美术的样式(续一) 》,《戏剧艺术》,1980年第1期。
在舞美设计上增设台阶式样的平台,其初衷是为了增加表演的层次感,通过台阶结构与动作、语言、服装、道具、灯光相结合,进而优化观者的观演体验,对于强调“台词”表演的话剧而言,这种设置有其合理性;而对于注重身段表演的昆曲来说,这种设计却给演员的表演带来困扰。石小梅提到在1991年版《桃花扇》“平台”上演出的经历时说:“第二稿时舞台上有很多龙套演员,满台全是景,要站在很窄的平台上表演。……为了这个平台,我一直很焦虑,做梦都梦到摔跤。现在是回归戏曲的本体,回归写意的传统了,我非常喜欢现在这样的一马平川。”(21)环球昆曲在线 :《一戏两看〈桃花扇〉是怎么磨出来的》,2018年3月15日。可见,为了凸显表演空间层次感的平台反而给昆曲演员的身段表演带来束缚,这也成为后期舞台设计“删繁就简”的缘由。
(二)《1699·桃花扇》—— 摹真的追求与对昆曲精神的偏离
在《1699·桃花扇》的舞台呈现上,主创团队的思路是以西鉴中、力求摹真。强调以“外观”感受为主体的对“外物”的模仿。这种“还原求真”,其实质是观众被视觉异置的时间、多维的空间所包裹,在现代的技术中体验舞台演出的场景。田沁鑫导演说:“让那些昆曲演员走入戏台时是传统的戏曲状态,当观众时是一种话剧的状态。”(22)田沁鑫 :《田沁鑫的戏剧场》,第172页。这里的话剧状态就是摹仿故事情境的“真实”,通过舞台布景,向观众提供可视化文本,摹拟特定场域空间,营造真实的“现场感”,引领观众进入历史场景的幻觉之中。关于《1699·桃花扇》的舞台空间设计,在《田沁鑫的戏剧场》中有一段阐述:
田沁鑫研究了明代后期昆曲鼎盛时期的演出盛景。在《南都繁绘图》中发现, 戏台“亭台楼阁”的设置便于三面观看,且乐队是置于后台而不是两侧。此次《桃花扇》的场景布置,便以《南都繁绘图》为布景,让乐队坐在演出台的后面,两侧又添置了座椅,以形成三面围观的效果。同时也增添了亭阁式的主要舞台区,地面则用“镜面体”来表现秦淮河上的波光粼粼。(23)田沁鑫 :《田沁鑫的戏剧场》,第152页。
《1699·桃花扇》的舞台将有“明代《清明上河图》”之称的《南都繁会图》作为演出幕布背景。该图描绘了中国明朝晚期的陪都南京城商业兴盛的场面。舞台设计以一个“台中台”为中心,其外围是二百多平方米的空间,此外,还将明式家具等老古董放置到了舞台上。台中台的设计试图把舞台还原成当年既有演出又有观众在场的情景。对这种 “摹真”的写实主义,现代戏剧理论家作出了简明的理论表述:
写实主义对于探讨人的深层心理不起作用。它的传统是运用“第四堵墙”的技巧,而摒弃了富有诗意的对话和独白,这就只能从平面来表现人们的经验和感情,它让观众看到的只是表层的东西,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表面的存在。虽然写实的戏剧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人的内在自我却恰恰是不合逻辑的。(24)John Gassner, The Theatre in Our Time(New York:Growon,1966),p.16.
以表面上看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求真”思维来表现实际上不合逻辑的人的内在世界,当然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与西方戏剧强调情节的逻辑不同,昆曲的表演更注重情感的逻辑,强调对“情”之“境”的深入发掘;因此,舞台视觉常常不指向“对象化”的故事空间,而是“非对象化”的 “审美意象”的营造,中国戏曲的时空自由性和表现性使之不能在舞台上纤毫毕现地反映“真实”。
演出带给人的印象是混乱的。首先是对原著中心驾驭不稳,内容的选择与开掘过于随意或者说是不准确。其次是过于注重舞台外部形式,而外部形式的构设却与昆曲的内在质感形成错位。水色反光的地面,稍微有一点秦淮河行船的投影感,却不能为人物表演带来灵感。这一切或许都是导演的有意追求,但戏曲却以和谐美而非错讹感示人。于是这场演出就成为现代派探索对于传统戏曲的一次阉割。(25)参见廖奔 :《品剧日记(2004-2010)》,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第105-106页。
不可否认,《1699·桃花扇》在昆曲的现代传承和舞美技术革新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在编排上力图重现昆曲行当齐全、文武场兼具、场面宏大的规模,在舞台的外部形式上做足了功夫,例如为了还原《桃花扇》原作的故事空间,剧组专门从英国购进仿水面石材以营造秦淮河波光粼粼的场景。配合丝竹管乐,剧组试图还原600年前的属于中国人的优雅。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还原明末清初昆曲鼎盛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 《1699·桃花扇》的创作理想是锻造“精品昆曲”,“原汁原味地再现原剧的传奇色彩”,但其类似话剧的舞台设计、简略的剧情处理,则影响了观看体验。
(三)《一戏两看桃花扇》—— 文化认同与本体转向
相比较之前的两个版本,2017年版《一戏两看桃花扇》的舞台表演和舞美设计呈现出“本体转向”的面貌,这与主创团队的美学观念重新定位紧密关联。回顾三十年磨一戏,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1991年版《桃花扇》和《1699·桃花扇》从改良舞台空间设计方面着手,力图“创新”,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削足适履的教训。《一戏两看桃花扇》的舞美设计则是基于中国戏曲“极简”美学风格的再创作,在剧场空间上做“减法”,舞台背景采用净幔的处理方式,在配色上,则选择了更为突出演员的黑色幕布,既古典又现代。在全本中全程选用大红色一桌二椅的桌围椅披;在选场中根据折子戏的内容对桌围椅披的用色做出调整,以淡雅的日常配色为主,通过桌围椅披的配色变化寓示空间的转换。简练的舞台空间和灯光设计让观者把所有注意力都聚焦于演员的表演。这一版本从观演效果到观众评价,都收获了广泛的赞誉。
不难发现,从1991年版《桃花扇》到《1699·桃花扇》,其背后的美学特质,是试图走东方艺术向“西”看的革新展演之路,向话剧“学习”空间设计,究其实质,是注重“外观”“外物”和形式之美,注重视觉感受。2017年版《一戏两看桃花扇》则体现出从“外观”到“心观”、从“外物”到“心物”的转变,它注重内在的神韵,注重昆曲自身的精神品质,重视观演体验,从而既回归传统,又融入现代。
三、昆曲《桃花扇》三个版本的舞美设计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流动性的空间意识,对绘画、文学、戏曲等艺术形式的空间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宗白华说:“中国舞台表演方式是有独创性的,我们愈来愈见到其优越性。而这种艺术表演方式和布景问题又是和中国独特的绘画艺术相通的,甚至也和中国诗中的意境相通。中国舞台上一般不设置逼真的布景(仅用少量的道具桌椅等)。”(26)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88页。正是空间之“空”为观众的想象敞开了时间与空间之门,为艺术的升华与驰骋提供了哲学的意义。
在昆曲表演中,舞台时空不局限于“视觉空间”,而是与“时间”相联的“视知觉时空”。这种空间的建构实际上是包括视觉形象、审美感知、情感联想等叠加而成的“复合空间”。空间的生成包含三个层面:一是作为表演场地的“空的空间”,具有流动性的时空特质,舞台布景不拘于一时一地;二是演员的“身段画景”,即“景在演员身上”;三是从观者视角出发,由演员的表演推动观者的视知觉想象进而生成的“心象”空间,这也是昆曲艺术最耐人寻味之处。三者互相作用,缺一不可。进而,昆曲的舞台空间美学对应表现为三个主要特质:流动的时空、身段画景和对物象的超越。
(一)流动的时空
从演出空间视角来看,在昆曲表演中,演出的时间与空间、表演场地与舞台布景都相对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如何以无限突破有限,实现有限和无限的有机统一,昆曲的表演自有其高妙之处。在昆曲演出中,并不需要一个对象化的表演空间来模仿真实的故事场景,而是体现在走圆场、指手划脚,剧中的“时间和地点在演员的嘴上、手上,唱之即来,挥之即去”。(27)邹元江 :《空的空间与虚的实体——从中国绘画看戏曲艺术的审美特征》,《戏剧艺术》,2002年第4期。风光迤逦的秦淮河不需要用镜面的玻璃砖地面写实地呈现,其表演空间只需要一方简洁的舞台。在《一戏两看桃花扇》的《访翠》一折,苏昆生的手往前方一指,就出现了跃然眼前的秦淮河;老生与小生在舞台上团团转几圈,就穿过了条条深巷;苏昆生停住脚步,道一声“这里是了”,媚香楼就应声而成;鸨儿作出开门的姿势,便界分出门内门外的空间;进入内院,侯方域抛扇坠、接樱桃,只用了小小的舞台砌末,便跃然出现在楼上楼下的空间——这就是昆曲艺术的简便与高妙之处。“空”方能“纳万境”,在假定性的表演时空之中,根据剧情需要而产生空间的变化,具有流动性和时空的不断生成性。正如著名舞台美术家阿庇亚所说:“舞台美术的基本任务不在于表现(例如)森林,而在于表现森林中活动的人。”(28)尤宝诚 :《美术辞林·舞台美术卷》,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19页。中国传统艺术重写意、重传神,如绘画,春风难以直接画出,则画柳枝飘动、树叶飞扬,这是以“实”表现“虚”;如戏曲,仅仅做一个开门的动作,即显示门的存在,这是以“虚”表现“实”。因此,这种时空必须张弛有度,使物象与演员、与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之不沾不滞,物象得以独立自足,自成境界:这都是在距离感、间隔感中构建的流动的时空。
(二)身段画景
从演员视角来看,表演空间的生成依托演员独到的“身段画景”。“身段画景”出自清代《审音鉴古录》中的《荆钗记上路》 ,“身段虽繁,俱系画景”。(29)(清)琴隐翁 :《审音鉴古录(下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在此,身段画景有两层含义:首先,身段画景所画的不是外在景物,而是建构(“画”)姿态化的心象之“景”。“在感觉间的世界中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完形。”(30)梅洛-庞蒂著 :《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8页。在这种完形的状态之中,身段表演是有着特定价值倾向的有机塑形。其次,“身段画景”是一种活态的空间生成方式,意味着身体空间性的确立。虚拟化的身段(虚的实体)使虚灵化的(身体的空间性)不断生成。在此,既有戏曲演员的身段表演呈现,也有观众对身段表演的感受,这是身段画景确立的前提条件。因此,演员的身段表演都是“画景”的媒介。
尽管中国戏曲在剧本形态上与西方话剧有很大的差异,但其本质规定却不在剧本上,而在演员的舞台“程式”上。以“行当”“程式”为中介,是一种符号化、象征化、装饰化的表意手段。身段就是程式化了的审美形式,不仅塑造了完形的身体姿态,还生成了戏曲的表演空间。拿折子戏《沉江》一出来说,舞台上的场景设计十分简练,仅用一张插着“史”字旗帜的椅子寓示一座山头。故事空间里的茫茫江水、激烈惨败的战争场面、国破家亡的悲恸场景全凭演员的身段表演而生。在此折戏中,急促的锣鼓声寓示战况告急,扬州生灵涂炭,惨遭屠戮。史可法和老马夫扬鞭作舞,紧张的战争场面跃然眼前。白龙驹的一声长啸仿佛是史可法内心的哀鸣。柯军说:“眼睛就是戏的所有的节奏和力量,必须一睁眼就在那个环境里,不是在剧场,是在战场,看到梅花岭尸骨成堆,瘦西湖碧血染红,看到、感受到,只有自己进入场景,才能带观众入戏。”(31)环球昆曲在线 :《〈一戏两看桃花扇〉是怎么磨出来的》,2018年3月15日。这种由“身段画景”比出来、画出来、舞出来、唱出来、器乐演奏出来的空间是具有时间性的、瞬时性的、心象性的空间,比摹真的空间更有意味儿,更耐人寻味。因此,这就决定了昆曲的“戏景”在演员身上,而非具象化、场景化的布景。
(三)物象的超越
从观者视角看,戏曲舞台的空间设计不局限于“物”之“观”,更体现在对舞台布景的“物象的超越”。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舞台上很少设置实体性的布景,有的也只是少量必要的道具。若以大量实景作为物理的陈设,就会与动作呈现的虚拟情境相冲突。更进一步说,如何借助观者视角实现从“物象”到“心象”的转化,追求视觉和知觉共同构成的“审美意象”,这一点戏曲与戏剧没有不同,真正的差异是体现在艺术如何表现方面:
西方戏剧的形象创造,是把象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意放在矛盾的次要方面,最后在艺术形象中达到两者的统一。而中国戏曲的形象创造,则是把意放在矛盾的主要方面,把象放在矛盾的次要方面,是以意为主导,以象为基础,在象中有意、意中有象的意象交融中,完成艺术形象创造的。(32)贾志刚 :《戏剧理论与批评》,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因此,西方话剧注重“象”的实存与对应,追求空间的“摹真”,强调在一个摹真的场景之中展开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而中国戏曲更看重“意”的主导性地位,更着力于情感空间的深入。戏曲的舞台空间一方面是“身临其景”, 另一方面是“心临其境” ,因此,戏曲表演中的“意象”则更多地指向“心观”意义上的“虚的实体”,是一种想象空间,具有超越具体、超越有限的物象的“非对象化”的特质。
类比这三个版本,不难发现,1991年版《桃花扇》从模拟西方的条屏布景出发,为丰富舞台视觉而设置多层平台;《1699·桃花扇》追求摹真的故事场景,在舞美上设置秦淮河景与媚香楼空间,追求剧本的还原;《一戏两看桃花扇》对中国戏曲美学的“极简”(高度抽象化)进行了舞美设计的再思考,删减了最初全本的群场、龙套,舞台精简到只有纯黑的丝绒幕布与经典的一桌二椅。做减法的目的是要让观众感受到昆曲的“戏情”与“戏境”是绝对“集中在演员的身上”的。在昆曲的舞台上,通过极简的舞台物象,给演员的表演提供动作支点,由演员的身段表演和唱词推动观众的想象,实现由“物象”到“心象”的转化,呈现出“物象的超越”的审美特征。江苏省昆剧院三十年打磨《桃花扇》,也反映出从“以西鉴中”到回归中国戏曲美学精神的本体转向。
结 语
创新的前提永远是继承。文化自信视域下的回归、继承不能只是动作、形式等技术性的继承,还应建立在对昆曲艺术理解的基础上,新时代的昆曲传承不在于舞台视觉上的令观众眼前一亮,而是通过表演让他们心头一动,被文化的魅力所吸引。《桃花扇》令人触动的是读书人在国破家亡时爱情的无法选择,政治立场的无法选择,身归何地、心归何处的惆怅与悲悯。昆曲的现代演绎、舞美空间设计应该立足于昆曲本体,不是以形式的精美取胜,而是重在以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立体化的人物形象、情感空间的深入展开来取胜。三个不同版本的《桃花扇》的舞台空间设计折射出一代代昆曲人对昆曲传承的思考与实践。从向西方学习、追求话剧化“摹真”的演剧空间到回归中国戏曲“空灵”的表演空间,意在阐明戏曲真正的美学意蕴。处于转型时期的昆曲,如何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展开舞台设计,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
——对孔尚任《桃花扇》中道具“桃花扇”运用的解读
——以国家大剧院舞美布景设计制作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