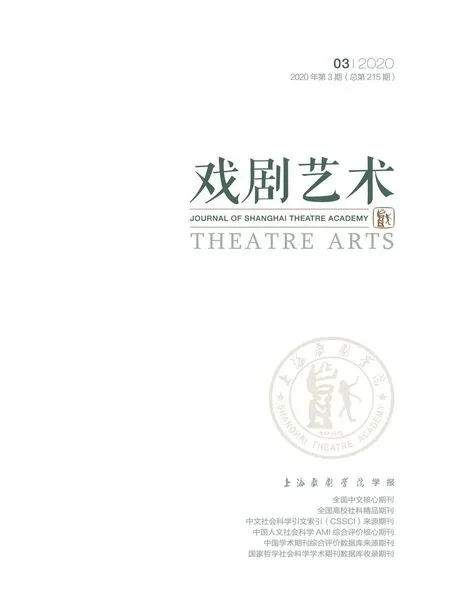论南戏、传奇声腔的三个问题
解玉峰
南戏、传奇的声腔问题,似为南戏、传奇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大问题。钱南扬先生《戏文概论》专立“三大声腔的变化”一章讨论海盐腔、昆山腔、余姚腔、青阳腔、弋阳腔等声腔,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中描述明清戏剧的第三编题为《昆山腔与弋阳腔诸戏》。近些年来声腔类专著也有不少,如林鹤宜《晚明戏曲剧种及声腔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94年)、苏子裕《中国戏曲声腔剧种考》(新华出版社,2001年)、流沙《明代南戏声腔源流考辨》(施合郑基金会,2009年)、曾永义《戏曲调腔新探》(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年)、廖奔《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余从《戏曲声腔剧种研究》(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等。
南戏、传奇的传播演出究竟使用了哪些声腔?各声腔之间是何种关系?每一声腔是否有相对应的南戏、传奇剧本?每一声腔与“剧种”是否有对应关系?上述问题可能是南戏、传奇声腔研究的根本性问题,学术界目前似尚未能达成共识。笔者不揣鄙陋,谨陈管见,敬请方家赐教。
一、声腔之种类
南戏、传奇的传播演出究竟曾使用了哪些声腔?这一问题虽较难有确切的回答,但我相信即使是初学者,也会知道所谓“四大声腔”,甚至也能说出祝允明《猥谈》中那一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字:
今人间用乐,皆苟简错乱……自国初以来,公私尚用优伶供事。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也。若以被之管弦,必之失笑。而昧士倾喜之,互为自谩尔。(1)(明)祝允明 :《猥谈》,(明)陶铤编《说郛续》卷四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我们不能确知祝允明写成这一文字的写作时间。祝允明为江苏长洲人(今吴县),生于明天顺四年(1460年),嘉靖元年(1522年)为应天府通判时称病还乡,嘉靖五年(1527年)去世,故我们姑且假定其《猥谈》成于1520年前后。祝允明《猥谈》之后约四十年,明嘉靖时某文人(今人多误为徐渭)所撰《南词叙录》也提到这几种声腔:
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嘌唱,即旧声而加以泛艳。(2)《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页。
《南词叙录》书前有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小序,彼时的“昆山腔”与祝允明时代已大不相同——“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祝允明为明弘治、正德年间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其《猥谈》一节文字,可能《南词叙录》的作者也读到了。祝允明《猥谈》,再加上《南词叙录》的引述,此后四五百年中,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乃成为知名度最高的声腔,乃至被今人归为“四大声腔”(3)洛地先生怀疑“四大声腔”的说法出现在上世纪50年代。邹青在《“明代四大声腔”说的源流及其学术史检讨》(《戏曲艺术》,2017年第3期)中说,廖辅叔编著《中国古代音乐简史》 (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最早明确提到“四大声腔”。。
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外,近百年来学界关注较多的似为青阳腔。最早提及青阳腔的文献似为著名传奇家汤显祖(1550年-1616年),其《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云:
此道有南、北。南则昆山、次之为海盐,吴浙音也,其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江以西为弋阳,其节以鼓,其调喧。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我宜黄谭大司马纶闻而恶之。自喜得治兵于浙,以浙人归教其乡子弟,能为海盐声。大司马死二十余年矣,食其技者殆千余人。(4)(明)汤显祖 :《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汤显祖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128页。
胡文焕明万历中期所编大型《群音类选》收当时流行戏曲演出或清唱曲目,其类别上有“官腔”“北腔”“诸腔”“清腔”四类,其所谓“官腔”所收皆出自戏文、传奇的一些折子,“北腔”收北曲杂剧及散套,“清腔”所收皆散曲,其所谓“诸腔”有自注云:“如弋阳、青阳、太平、四平等腔是也。”这里“青阳腔”位置仅次于“弋阳腔”。
自1942年傅芸子先生发表其著名文章《释滚调:明代南戏腔调新考》以来(5)参见傅芸子 :《释滚调:明代南戏腔调新考》,原载《东方学报》(京都)第十二卷(1942年),收入傅芸子 :《白川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学界对“青阳腔”颇多关注,1992年在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青阳腔学术研讨会。但由于“青阳腔”自文献记载来看,稍晚于“四大声腔”,很多人以为“青阳腔”乃“弋阳腔”之流变,其声腔地位颇为尴尬。
由于学界多以为南戏发源于温州,文献中有所谓“温州杂剧”“永嘉杂剧”,故“温州腔”也颇得关注,叶德均先生即力主“温州腔”与“四大声腔”并列为“五大声腔”。《南词叙录》有: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6)洛地先生《戏文辨正》文提出,“鹘伶声嗽”即“鹘”地伶人之“声嗽”(演戏时的言语音韵声调)。鹘,苍鹘,亦鶬鸹,即鸹鶬。鸹鶬可指括苍一带(今浙南温州、丽水、台州)伶人演戏时的言语音韵声调。。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7)《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39页。
永嘉戏子或温州戏子以其方言入唱搬演戏剧,自然会有“永嘉腔”或“温州腔”。祝允明《怀星堂集·重刻中原音韵序》亦云:
雅部祗日用十七宫调,识其美列是非者几士?数十年前尚有之,今绝矣!不幸又有南宋温浙戏文之调,殆禽噪耳,其调果在何处?噫嘻陋载!(8)(明)祝允明 :《怀星堂集》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明中叶苏州娄江(太仓)人陆容(1436年-1497年)与祝允明的生活年代基本相当,其所著《菽园杂记》云: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倡优者,名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女不耻为之。其扮演传奇无一事无妇人,无一事不哭,令人闻之,易生凄惨,此盖南宋亡国之音也。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士大夫有志于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绝之。(9)(明)陆容 :《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页。
既然如此,似不必怀疑“永嘉腔”或“温州腔”的存在,而且应增加“慈溪”腔与“黄岩”腔了。
学术界也有力争将“泉潮腔”与“四大声腔”并列为“五大声腔”者,这主要出自福建梨园戏、莆仙戏的研究者们,如刘念兹《南戏新证》(中华书局,1986年)、王爱群《泉腔论》等。(10)参见王爱群 :《泉腔论》,福建戏曲研究所编 :《南戏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福建梨园戏、莆仙戏多存早期南戏风貌,为“活化石”,“泉潮腔”为独立于“四大声腔”外的自成系统的声腔,为南戏形成的始创声腔。福建梨园戏、莆仙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存早期南戏风貌,我们姑且不论,泉州、漳州、潮州福建沿海一带自南宋代起经济文化日渐发达,与浙江台州、温州相连,其地自亦应有戏班演出,也即应存在“泉潮腔”。明末莆田人姚旅所著《露书》卷九载万历四年(1579年)萧崇业任正使、谢杰任副使册封琉球时所看到的福建戏曲的演出情况有:
琉球国居常所演戏文,则闽子弟为多,其宫眷喜闻华音。每作,辄从帘中窥。宴天使长吏,恒跽,请典雅题目, 如《拜月》《西厢》《买胭脂》之类皆不演; 即《岳武穆破金》《定远破虏》亦以为嫌。惟《姜诗》《王祥》《荆钗》之属,则所常演,每啧啧羡华人之节孝云。(11)(明)姚旅 :《露书》,刘彦捷校点,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
又明万历间泉州晋江人何乔远(1558年-1631年)所撰《闽书》卷三十八“风俗”云:
(漳州)地近于泉,其心好交合,与泉人通,虽至俳优之戏,必使操泉音,一韵不谐,若以为楚语。(12)(明)何乔远 :《闽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46页。
据此,“泉腔”“潮腔”或“泉潮腔”的存在当为不容置疑的事实。
除以上提及的几种声腔(包括“太平”“四平”“乐平”“慈溪”“黄岩”诸腔)外,古人提及的声腔还有不少。如王骥德《曲律》“论腔调”节有:
世之腔调,每三十年一变……旧凡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故是南曲正声。数十年来,又有“弋阳”“义乌”“青阳”“徽州”“乐平”诸腔之出。今则“石台”“太平”梨园,几遍天下,苏州不能与角什之二三。其声淫哇妖靡,不分调名,亦无板眼,又有错出其间,流而为“两头蛮”者,皆郑声之最,而世争羶趋痂好,靡然和之,甘为大雅罪人,世道江河,不知变之所极矣!(13)(明)王骥德 :《曲律》,《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17-118页。
这里王骥德一下子新提供了“义乌”“徽州”“石台”三种声腔。此外,魏良辅《南词引正》还提到“杭州”腔,明末人熊文举《雪堂先生诗选》提及“宜黄”腔,清康熙时人刘廷玑《在园杂志》提及“京腔”“卫腔”,清乾隆时人严长明《秦云撷英小谱》提及“枞阳腔”(自注即“石牌腔”)、“襄阳腔”(自注即“湖广腔”)、清乾隆时人李调元《雨村剧话》则提及“清戏”,等等。
至于近现代人,“昆腔”则有“南昆”“北昆”“湘昆”“晋昆”“永嘉昆曲”,“高腔”中较知名的则有安徽的“岳西高腔”、江苏的“高淳高腔”、浙江的“松阳高腔”、“西安高腔”、“(新昌)调腔”、湖南的“常德高腔”、“辰河高腔”、湖北的“麻城高腔”、江西“孟戏高腔”等,简直不胜枚举。
所以,试图把南戏、传奇演出曾使用的声腔进行确切的统计,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南方的十几个省、七八百个县,只要其地有戏班,伶人自然会以其方言土语演唱戏剧,理论上便可能产生七八百种腔,甚至更多(因为南方即使一个县也可能方言差异很大)。
但古人以及今人提及的三十余种声腔,实际可分两大类:一类为“高腔”——“一唱众和”或“一人吟唱、众人帮腔”,以锣鼓伴奏(不入管弦)(14)近代以来,有些“高腔”戏班大约受 “昆腔 ”或 “乱弹 ”的影响,亦使用管弦伴唱。管弦的出现对 “接腔”每有所削弱,以至于有替代“接腔”成为过门之势。;一类为“依字声行腔”——一人依汉字四声咏唱,以笛相和,以板节奏。(15)洛地在《戏曲音乐类种》(艺术与人文科学出版社,2002年)中提出,“南北曲腔”可分为“昆腔”与“高腔”两大类,本文此处也基本依从洛先生的分类。
以上提及的三十余种声腔绝大多数实为“高腔”,而其中严格意义的“依字声行腔”只有魏良辅改革后的“昆腔”。此外,“海盐腔”“泉腔”也似有“依字声行腔”的发展阶段。
自前引祝允明《猥谈》的文字看,他在1520年前后看到的“昆腔”“海盐腔”皆为“高腔”,但四五十年后,魏良辅、梁辰鱼等改革后的“昆腔”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走到“依字声行腔”的道路,对此学界已有讨论,本文不拟赘述。值得关注是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海盐腔”的变化。明万历年间南京江宁人顾起元(1565年-1628年)所撰的《客座赘语》提及“海盐腔”云:
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则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阅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后则又有四平,乃稍变弋阳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昆山较海盐又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长延至数息,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16)(明)顾起元 :《客座赘语》卷九“戏剧”,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3页。
明万历(1573年)以后,昆山腔已在文人阶层取代“海盐腔”而成为“官腔”(《群音类选》),但引人注意的是顾起元这里说到的“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这说明海盐腔也曾走到以“官语”入唱、也即很有可能走到“依字声行腔”。更值得注意的是明莆田人姚旅《露书》卷八中描绘的“海盐曲”:
歌永言,永言者,长言也。……故古歌者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今唯唱海盐曲者似之:音如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近一刻,不背于永言之意。(17)(明)姚旅 :《露书》,第191页。
按,姚旅生活在明万历、天启年间,生平事迹不详,其《露书》所载事晚至天启三年(1623年)。如果姚旅所说“海盐腔”能“音如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近一刻”属实,我们不能不说彼时“海盐腔”已基本上是“依字声行腔”。
又如明万历时南昌人陈宏绪(1597年—1665年)《江城名迹》所载南昌王府女优演唱海盐腔云:
匡吾王府,建安镇国将军朱多某之居,家有女优,可十四五人。歌板舞衫,缠绵婉转。生曰顺妹,旦曰金凤,皆善海盐腔,而小旦彩鸾,尤有花枝颤颤之态。万历戊子(1588年),予初试棘闱,场事竣,招十三郡名流,大合乐于其第,演《绣襦记》,至斗转河斜,满座二十余人皆霑醉,灯前拈韵属和。(18)(明)陈宏绪 :《江城名迹》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46页。
据陈宏绪《江城名迹》,海盐腔女优“歌板舞衫,缠绵婉转”,似非一般高腔那样率真质朴。再联系前引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说海盐腔“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我们有理由相信有的与文人接触较多的海盐腔戏班其演唱已很讲究,已与一般粗质的“高腔”颇有差异。但从《金瓶梅》等文献反映的情况看,海盐腔至少在明嘉靖时仍未“被诸管弦”,与昆腔仍有很大距离。
福建梨园戏分“七子班”“上路”“下南”三路,其中的“七子班”有生、旦、净、末、丑、外、贴七门脚色,常用勾栏式的小舞台,表演精致细腻,其基本动作被称作“十八步科母”,从各方面看,“七子班”明显为古代家班遗存。故梨园戏演唱使用的“泉腔”讲究四声,有“依字声行腔”的特征。由于漳、泉一带的文人参与不像苏州一带那样深入,其文人化的程度自然也不及昆腔。
那么,以上提及的声腔是何种关系呢?窃以为诸腔之关系主要是两种。
一是如“昆腔”或“海盐腔”那样,其在苏州一带或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浙一带得到文人阶层的关注和参与,走到以官语入唱、“依字声行腔”的道路。那么这种声腔在传播过程中,势必会对各种地域色彩浓厚的各路“高腔”产生影响,正如通语或官话始终在影响各地方言一样。假如其传播到各地而落地生根,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地人加入戏班者渐多,不免会沾染地方色彩,不得其正,故古人有所谓“四方歌曲,必宗吴门”,今人过于强调各自“地方性特点”,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
第二种情况是,各路“高腔”受官腔化的“昆腔”或“海盐腔”影响以及彼此间的影响,也会逐渐摆脱其初始的地域性,在更大区域流播,有趋同之势。这正如各地方言不断为通语或官话侵蚀以及受近临方言的影响、方言个性逐渐消失一样。近代以来,主要受古人言论的影响,很多学者试图探索出各种声腔纵向的变迁关系,或归于弋阳腔之变,或归于海盐腔之变,在文献上缺乏实证,在理论上也大有问题。(19)如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长编》中说: “弋阳腔亦已南北通行,并且在某些地方因与当地土戏相互结合,随地发生变化。最显著的事实,如安徽的‘徽池雅调’‘青阳时调’‘四平腔’‘太平腔’之类。……至于流传到其他地区的‘弋腔’,或名‘高腔’(如四川、湖南)。”
二、“声腔”与剧本
近代以来,很多学者认为各种声腔与具体的南戏、传奇作品有对应关系,有些剧作被归为某类声腔的剧作。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完成于1930年,该著作首次在中国戏剧史的撰写中突出声腔的意义,其第三篇题为《昆曲昌盛期》、第四篇题为《花部勃兴期》。《昆曲昌盛期》论述自明嘉靖至清乾隆时李开先、汤显祖、李渔、洪昇、万树等传奇家及其作品。1939年,傅芸子先生在东京访书,最早提及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新刻京版青阳时调词林一枝》《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新簧》等曲选有“滚调”,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释滚调:明代南戏腔调新考》,认定这些曲选为“青阳腔”的曲本。(20)傅芸子 :《释滚调:明代南戏腔调新考》。1954年9月,山西万泉县(今万荣县)文化馆畅明生先生在该县百帝村发现《三元记》《黄金印》(即《金印记》)、《涌泉记》(即《跃鲤记》)、《陈可忠》四个道咸间艺人抄本,据说是青阳腔的剧本,赵景深先生不久写下了《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一文,发表在《复旦大学学报》上。(21)参见赵景深 :《明代青阳腔剧本的新发现》,赵景深 :《戏曲笔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1974年,戴不凡先生在阅读《古本戏曲丛刊》(初集、二集)时,发现其中的《玉丸记》《樱桃记》《锦笺记》《蕉帕记》有绍兴方言的印迹,认为它们都是“迷失”的余姚腔剧本,并得到著名戏剧家马彦祥(马彦祥是宁波人,与余姚相邻)的肯定。(22)戴不凡 :《论“迷失了的”余姚腔》,《戏曲研究》,1980年第1期。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在“昆山腔的作家与作品”一章讨论汤显祖、沈璟、李渔等作家及“四梦”、《长生殿》《桃花扇》等作品,在“弋阳诸腔作品”一章讨论《破窑记》《金貂记》《珍珠记》《荔镜记》等作品。
梁辰鱼《浣纱记》一向被认为昆剧史上特别值得关注的作品,陆萼庭先生在《昆剧演出史稿》中说:“(梁辰鱼)编制了第一个昆剧剧本《浣纱记》。”(23)陆萼庭 :《昆剧演出史稿》,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21页。
如果说声腔与具体的南戏、传奇作品有对应关系,很多现象可能无法解释。
如胡文焕明万历中期所编的大型书籍《群音类选》,其中收录当时流行的戏曲演出或清唱曲目,其类别上有“官腔”“北腔”“诸腔”“清腔”四类。其所谓“官腔”所收皆出自戏文、传奇的一些折子,“北腔”收北曲杂剧及散套,“清腔”所收皆散曲,其所谓“诸腔”有自注云:“如弋阳、青阳、太平、四平等腔是也。”而“诸腔”类所收亦为戏文、传奇,如《金印记》《破窑记》《白兔记》《跃鲤记》《织锦记》《卧冰记》《劝善记》《东窗记》等。那么,这至少说明“弋阳、青阳、太平、四平”这四种声腔可以共享这些戏文、传奇。
又如很多晚明曲选,如《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新选南北乐府时调青昆》《鼎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新镌南北时尚青昆合选乐府歌舞台》等。其书题都反映了“昆(腔)”可与“池(州腔)”“青(阳腔)”“徽(州腔)”共享同类文本。
1957年,在皖南山区发现王右生藏同治八年抄本《白兔记》《云亭相会》,抄本《白兔记》与明万历间刊刻的曲选《新锓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所收《白兔记》散出《出猎》《回书》《磨房会》等相对照,其词、白是完全相同的;又与岳西高腔散出对照,也无差异。(24)刁均宁 :《青阳腔戏文三种说明》,刁均宁辑 :《青阳腔戏文三种》,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1999年,第12页。据刁均宁先生介绍说,原收藏者王右生先生“既演高腔,又演徽戏与目连。《云亭相会》在解放前曾由歙县高腔与徽班合班演出过”。(25)班友书 :《从〈高文举〉戏文谈及皖南抄本〈云亭相会〉的发现》,《南戏论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226页。学界多以为抄本《白兔记》《云亭相会》为青阳腔剧本,而《白兔记》《云亭相会》显然也可用“池(州腔)”“徽(州腔)”“岳西高腔”“歙县高腔”演出,大名鼎鼎的徽班也能搬演,至近代犹然。
浙江高腔流传已久,至上世纪50年代仍有十余路,大体可分三支:绍兴、台州、宁波、温州四府为一支;金华、建德、衢州三府为一支;丽水为一支。其中前一支可称“调腔”,包括“新昌调腔”“宁海平调”“台州高腔”“温州(瑞安)高腔”,此四路高腔演出均有元杂剧《汉宫秋》(《游宫》《饯别》,即刊本第一折、第三折)、《西厢记》(《游寺》《请生》《赴宴》,即刊本第一本首折、第二本次折、第三折、第四本首折)、《单刀会》(第四折、第三折[残])。(26)参见洛地 :《现今浙江高腔(调腔)中的〈北西厢〉〈汉宫秋〉〈单刀会〉及其他》,《洛地戏曲论集》,2006年(台湾出版),第200页。其中的“新昌高腔”可演《牡丹亭》的《闹学》《游园》《惊梦》《寻梦》《跌雪》《冥判》等6折、《玉簪记》的《偷诗》《吃醋》《秋江》《追舟》等4折。这些折子戏演出使用的念白与作家原本有较大出入,但其唱词与原本出入则不太大,明显沿袭原本。众所周知,《单刀会》第四折《刀会》、《西厢记》的《游殿》一折、《牡丹亭》的《闹学》《游园》《惊梦》《寻梦》《冥判》、《玉簪记》的《偷诗》《秋江》等折,均为所谓“昆剧”传统折子戏,而这些折子竟然也是“调腔”的传统折子戏。
自浙江调腔的情况看,调腔戏班有“雅”“俗”两路,有些高腔戏班或演员(因文化所限)只能扮演通俗易懂的、也常常是自家戏班独有的剧目,有些高腔戏班或演员则可能搬演一些“雅”的文人传奇,也就可能因此与其他戏班共享一些剧目。
自江南传入北京的高腔也与浙江调腔相似。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文献来看,高腔于明万历时已传入北京,其唱渐改为官腔入唱,故清康熙时有“京腔”之称,也仍有称“弋阳腔”或“高腔”者。值得注意的是,京城“京腔”演唱的文辞有很多与“昆腔”同。长期生活在北京的晚清人震钧(1857年-1920年)所著《天咫偶闻》卷七有云:
京师士夫好尚,亦月异而岁不同。国初最尚昆腔戏,至嘉庆中犹然。后乃盛行弋腔,俗呼高腔。仍昆腔之辞,变其音节耳。内城尤尚之,谓之得胜歌。(27)(清)震钧 :《天咫偶闻》,《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219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本,第524页。
近人夏仁虎(1874年-1963年)《旧京琐记》卷十“坊曲” 亦云:
都中戏曲向惟昆、弋, 弋腔音调虽与昆异, 而排场词句大半相同, 尚近于雅。(28)夏仁虎 :《旧京琐记》,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130页。
由此可见,京中昆腔、高腔也可以共享同一剧本。
同一剧本可以不同声腔演唱,此种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最著名的是汤显祖的“四梦”。自现有材料看,《牡丹亭》等最初可能由“宜伶”以“宜黄腔”演唱过,对此徐朔方、曾永义等学者都有很切实的论证。(29)考虑到“四梦”、特别是《牡丹亭》(1598年)的创作年代,“体局静好”的“海盐腔”正值流行,笔者颇怀疑“宜伶”的“宜黄腔”不可能是很土的“宜黄腔”,而可能是“海盐腔”化的“宜黄腔”。但明万历以后,江浙昆班以“昆腔”演唱“四梦”无疑最为风行,直至今日。当然也有一些偏于“雅”的高腔班继续演唱“四梦”,如浙江的“调腔”。
凡此种种,都说明声腔与具体的南戏、传奇作品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同一作品可以不同声腔入唱,反过来,同一声腔也可唱不同结构体制的作品。这正如同一首杜诗,不同地方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读音去吟诵,反过来,某地流行的吟咏调子可以套吟不同诗人的诗作、词作。
其道理既如此简单,为何人们会普遍将声腔与具体作品对应起来?这就不能不说到“声腔”与“剧种”的关系。
三、“声腔”与“剧种”
“声腔”与“剧种”是何种关系呢?我们不能不援引《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戏曲声腔剧种”条:
区分中国戏曲艺术中不同品种的称谓。……戏曲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别,体现在文学形式及舞台艺术各个方面,但主要表现为演唱腔调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戏曲剧种”的概念被确定下来,同时,“戏曲声腔”也成为从腔调和演唱特点区别戏曲类型的一种概念……(30)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戏曲声腔剧种”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年,第465-466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中“戏曲声腔剧种”条的释文当然是一种权威的解释,至少反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编成的上世纪80年代普遍流行的观念。
在这样的“剧种”观念之下,一种“声腔”便是一种“剧种”,“四大声腔”也就是“四大剧种”。人们也很容易将“声腔”与剧本联系起来——一种声腔对应特有的戏剧作品,也很容易把某地戏班以某种声腔演唱过的某作品归为这种“声腔”的剧本,《浣纱记》是为“昆腔”而作。人们也不会去注意:同一剧作,各戏班完全可各以其“声腔”演唱,也同样留下很多烙印。
在笔者看来,《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所收的317个“剧种”,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使用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过去一般被称为“大戏”者;一类是两三个演员当场的过去一般被称为“小戏”或采茶戏、花鼓戏、灯戏、二人转者;三是驱邪祈福的一种宗教活动,如各地被称为傩(戏)、端公戏、神戏等。这三百多个“剧种”也大都要使用某种“声腔”歌唱的,如果我们以“声腔”作为区分戏剧的标准,以上三类不同性质的活动或戏剧,都会被混称为“戏曲”,其彼此之间乃成大小、兄弟关系。
各种“声腔”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地方性”或“地域性”——伶人以其方言土语演唱戏剧。故按照“剧种”论,只要某地有戏班或剧团,只要这一戏班或剧团在当地得到合法身份——被登记或管理,即有可能成为一个“剧种”。《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所收的三百多个“剧种”,有很多是1950年代“造”出来的。比如黑龙江、吉林一带本来没有使用生、旦、净、末、丑等脚色的戏班,只有二人转一类的活动,而黑龙江省文化部门把二人转的演员组成一个剧团,便产生了一个新剧种“龙江剧”,吉林省文化部门把二人转的演员组成一个剧团,便产生了一个新剧种“吉剧”。县市一级行政单位,如果竟然没有剧团,当然不利于文化建设和宣传,所以1950年代一些县级剧团也纷纷组建,也因此产生了很多新“剧种”。据说,我国大约有近百个稀有“剧种”,因为全中国只有一个戏班(剧团),故称“天下第一团”,如江苏丹阳市的“丹剧”、河南内乡县的“宛梆”、河北唐山市的“唐剧”等。这些被誉为“天下第一团”的“剧种”,大都是如此建立的。(31)1992年,文化部艺术局举办了全国“天下第一团”优秀剧目展演活动,展演分南、北两片,分别在福建泉州和山东淄博进行,32个稀有剧种参加汇演。南方片的18家剧团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白剧团、安徽省徽剧团、湖南省岳阳市巴陵戏剧团、福建梨园戏剧团、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漫瀚剧团、福建省泰宁县梅林戏剧团、福建省闽西龙颜山歌剧团、江苏省丹阳市丹剧团、江苏省苏昆剧团苏剧队、广东省紫金县花朝戏剧团、广东省海丰县白字戏剧团、广东省陆丰县正字剧团、广东省海丰县西秦戏剧团、浙江省温州市瓯剧团、浙江省新昌调腔剧团、浙江省湖州湖剧团、四川省梁平县梁山灯戏剧团、四川省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花灯歌舞剧团。北方片的14家剧团为吉林省扶余市满族新城戏剧团、青海省平弦实验剧团、陕西省渭南地区富平县阿宫剧团、宁夏回族自治区秦腔剧团夏剧队、河北省唐山市唐剧团、山东省淄博市五音剧团、山东省菏泽地区枣梆剧团、山西省大同市耍孩儿剧团、山东省柳子剧团、山东省莱芜市莱芜梆子剧团、山东省即墨市柳腔剧团、河南省太康县道情剧团、河南省内乡县宛梆剧团、河南省沁阳市怀梆剧团。
全中国两千多个县、几万个乡镇,如果当地也组建了戏班或剧团,理论上就可以产生上千或上万个“剧种”。但由于“剧种”(戏班)成立与否,最终要取决于是否被某地方政府部门登记认可,本来有戏班活动的地方,也未必有隶属于该地的“剧种”——正因为如此,华东、华南、华中、西南曾经戏剧演出繁盛的很多县市并没有自己的“剧种”。
1950年代前,中国各地祈福驱邪的傩仪非常普遍,但到了1950年代,傩仪一般被视为封建迷信,也是研究禁区。1980年代初,以《中国戏曲志》《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等大型志书的编纂为契机,很多文化系统研究人员下乡调研,在“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下,各地的傩仪纷纷被发现而被申报和登记为新的“剧种”,如安徽贵池傩戏、贵州安顺地戏、陕西汉中端公戏、青海藏剧等。
一方面是很多所谓“大剧种”,如京剧、川剧、汉剧、婺剧、柳子戏等都是“多声腔剧种”,另一方面是同一种“声腔”,1950年前活动范围基本相同、可相互搭班演戏的同一大类演员,却可以被组建到不同的剧团、成为不同的“剧种”演员。如流行于鲁、豫、苏、皖四省交界处的梆子戏,分别被归为“枣梆”“豫剧”“徐州梆子”“淮北梆子”等多个“剧种”。
1950年以来,很多剧作确实是单一使用或主要使用某种“声腔”的。但1950年以前,很多剧作在搬演时也可能使用多种“声腔”。胡忌先生曾著文说:“直到近代,我们还能看到《白蛇传》。全本有这样格局的演出 :《游湖·借伞》或唱皮黄、或唱昆曲,《成亲》主要唱二黄,《盗草》《水斗》主要唱昆曲(有南北曲),《断桥》唱昆曲,《祭塔》则又为二黄。那么这种办法演唱的《白蛇传》就是‘花雅同本’,两者几乎是各半的演出分量。稍往前些,在抗日战争时期,流浪于太湖地区的‘国风’苏昆剧团,团里上演的不少小本戏,如《风筝误》《牡丹亭》《十五贯》等,都是以几出唱昆的南北曲,夹杂在几出唱苏州滩黄的小调里。那也属于‘花雅同本’之类。至于更往前推到百年左右,在北京,既有‘昆乱不挡’的名演员如杨小楼、陈德霖、何桂山、王长林等能擅‘花雅同本’之戏,更有外地晋京的非京剧演员也偶有演‘花雅同本’的,如蒲州梆子的乔国瑞(艺名狮子黑,1881年—1957年),他在山西介休县梆子科班出科后,再拜名师专学昆腔戏,艺成后到京演剧,昆梆‘两下锅’,誉满都城。至于在湖南的湘昆、四川的川昆、浙江的甬昆等剧目中这样的例子更多,浦江乱弹曾有一本《别母乱箭》,居然为‘昆头、乱身、昆尾’。”(32)胡忌 :《从〈钵中莲〉传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菊花新曲破——胡忌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5页。清乾隆中叶以来,“昆、高”合班、“昆、高、乱”合班、“昆、乱”合班的现象日渐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剧作被不同“声腔”扮演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
2006年9月14日至17日,柏克莱加州大学组织了“《牡丹亭》及其社会氛围——从明至今昆曲的时代内涵与文化展示”研讨会。据吴新雷先生说,会议期间,旁听席上有位洋人突然举手发问,他说:“中国戏曲的剧种太多,什么‘Kun Opera’(昆剧)、‘Peking Opera’(京剧)、‘Cantonese Opera’(粤剧)等等数百种,把头脑都闹昏了,能不能创新,把‘Kun’‘Peking’‘Cantonese’之类的头衔全都去掉,创造一个全新的剧种,一统天下,就叫做‘Chinese Opera’(中国式歌剧)?”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主持会议的人惊讶莫名,只得连声说:“No!No!No!”(33)参见吴新雷 :《昆剧史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52页。
我个人读到这则消息,深思良久。这位洋人因为中国戏曲有太多的“剧种”,“把头脑都闹昏了”。那么我们中国人自身,是否会因如此多的“剧种”而头脑不清?人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为了从整体上更好地理解这一事物。“分”的目的在“合”,而不是为“分”而“分”。中国民族戏剧的繁荣可以表现为有很多专业戏班或剧团,但不一定要表现为很多“剧种”。我们划分出了三百多个“剧种”,那么“中国民族戏剧”(Chinese Theatre)其总体特征或根本特征是什么?是在使用歌唱或“声腔”吗?
洛地先生在回顾过去百年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缺憾时,指出其首要的缺憾是“以曲腔史替代戏剧史”:
以曲腔史替代戏剧史,在我们研究中是普遍且又贯穿的。述说我国戏剧, 是:以“歌舞”为源头; 以“相和歌”“唱赚”“诸宫调”等为其过程;以“北曲”“南曲” 作为戏剧形成的特征; 再往下的“明清戏曲史”,则皆以所谓“四大声腔”为启端, 接着是所谓昆腔与弋阳腔的“昆弋之争”;再接着是乱弹与昆腔的所谓“花雅之争”。再下来, 就是所谓“声腔剧种”了。(34)洛地 :《中国传统戏剧研究的缺憾》,《社会科学研究》 ,2000年第3期。
笔者近来在梳理近代以来相关南戏、传奇声腔方面的研究时,也深感我们很多研究者可能不自觉地过高地估计了“声腔”研究在整个南戏、传奇研究、乃至中国民族戏剧研究中的意义。
窃以为,就南戏、传奇研究而言,与其关注各种“声腔”,不如关注“声腔”背后的戏班及其活动——因为所谓“声腔”不过是各地戏班以其方言咏唱而已。“弋阳”“余姚”“海盐”“昆山”四地的戏班是否是最为“活跃”的前“四大”,可能大有问题。
单就“声腔”作为一种“音乐”或“歌唱”而言,与其试图将各种“声腔”做纵向的各种牵连(如某某声腔为某某声腔之遗存),不如将各种“声腔”做共时的类别的区分,因为前一种研究可能过于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