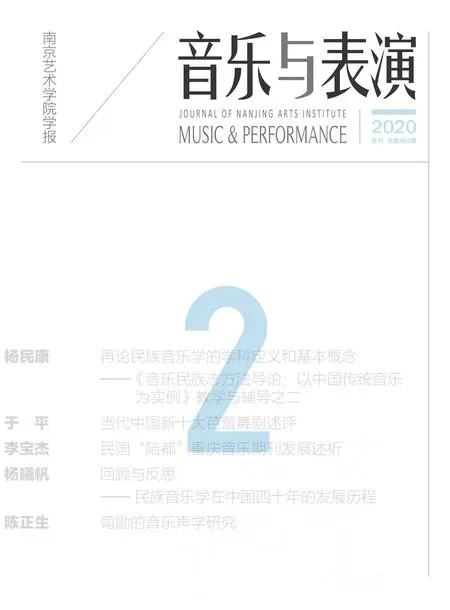帮派文化·边缘族群·认同焦虑
—— 论张作骥早期电影中游走于社会边缘的帮派/青年男性
孙力珍(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引 言
作为“后新电影”导演的代表,张作骥曾以副导演的身份跟随侯孝贤完成了《悲情城市》等多部影片的制作,也帮助虞戡平解决过很多片场出现的难题。他不仅“从侯孝贤那里学习到了如何挑选和处理演员,让演员的表演充满真实感到几乎纪录片的风格,也从虞戡平导演和香港电影导演那里学到了非常专业而有效的排片方式”[1]。但是张作骥首部电影《暗夜枪声》(1994)的拍摄并没有那么顺意。在与香港导演张之亮的合作中,张之亮因考虑到商业因素而要求干预影片后期制作,并主张把香港人难以听懂的闽南语换掉。也正是这个原因,张作骥强烈否认《暗夜枪声》是自己的作品。此后,张作骥开始拍摄一些台视的系列纪录片。其中“《烈火青春少年档案》,是关于青少年犯罪实际案例探讨……后来他继续追踪这些犯罪的青少年真实的生活和环境,于是被他们带到了关渡平原,有了拍《忠仔》的灵感”[1]。
从《忠仔》开始,帮派文化与边缘族群是张作骥试图平衡商业卖点与艺术追求的重要元素。在《忠仔》(1996)《黑暗之光》(1999)《美丽时光》(2001)《蝴蝶》(2008)等表现社会边缘群体的影片中,帮派文化始终充斥其中。但与传统帮派电影不同,张作骥电影的帮派角色,既不像吴宇森的《英雄本色》中因对抗“邪恶势力”而携手共进的“兄弟情谊”,也不像弗朗西斯·科波拉的《教父》中呈现出固定的类型特征——个人自由与权力腐化之间的对抗,更不像日本导演北野武《四海兄弟》中强调忠诚与勇武的男性气质。相反地,张作骥电影中所呈现的帮派叙事,一方面承袭了台湾电影中惯用的“社会写实”元素,以写实主义为影像基调呈现台湾底层族群社会;另一方面以帮派作为社会底层的唯一生存途径,呈现出帮派斗争为边缘族群生存困境的微型寓言,从而折射出20 世纪90 年代台湾社会面对政治、文化、经济的巨大变革,彰显台湾不同省籍族群的生存困境与认同危机。本文试图从帮派文化、边缘族群和认同焦虑三个层面,深入检视张作骥早期电影中,帮派文化与边缘族群之间纷争关系,及其背后所映射的社会文化意涵。
一、“另一种电影”:写实主义与帮派文化
什么是“另一种电影”?1987 年,台湾“当局”正式宣布解严,台湾不仅在政治上脱离了近四十年的钳制,更使得“社会与文化获得了重新思考与定义的机会,呈现出了面对自由所产生的骚动与实践的能量”[2]。同年年底,台湾新电影也在媒体人与影评人的拉锯中落幕,由詹志宏起草的《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①该宣言于1987年,53位新电影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所起草并发表,该宣言宣称了“新电影”的结束,也宣告了“另一种电影”的兴起。不仅可以视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结束,也宣布了“另一种电影”的诞生。如果说“台湾新电影”中流露出的是导演们对“历史的执着感受与忠实记录,使电影落实到个人人生与台湾社会的共同经验”[3]之上,那么,“另一种电影”则把镜头伸向台湾社会的边缘角落,“进一步揭示出了台湾过往与当下所不可触及的议题与黑暗面,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界限”[2]。张作骥不仅承袭“新电影运动”写实主义影像风格,也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视听风格与叙事象征,将台湾帮派文化与写实主义结合,派生出反映台湾边缘族群的“另一种电影”。遗憾的是,关于台湾电影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于“台湾新电影”,而“另一种电影”在风格与内涵上的“迥异”之处却鲜有提及。张作骥的电影可以说充分发展了“另一种电影”所具有的批判社会黑暗面、挑战社会主流文化,并将帮派文化融于写实主义影像中,揭示“解严”后台湾社会乱象丛生的社会现状,并以“魔幻式”的“光明结尾”②“光明结尾”是台湾学者廖金凤在其文章《张作骥的独家秘方——“光明写实”》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此概念指出张作骥电影中底层角色“死而复生”的结尾具有“化解黑暗沉重结局、拥抱光明面向”的特征。[4]给予观众以精神层面的想象与慰藉。
自“光复以来”,台湾电影中“写实主义”因政治意识形态而被赋予了很大的“弹性”。如20 世纪50 年代,台湾电影盛行“通俗剧”,像《王哥柳哥游台湾》《台北发的早班车》《高雄发的晚班车》等,这一类电影中“写实主义以愈来愈强烈的手段组织时间和空间,试图用电影来化解现代性的僵局,努力舒缓电影与‘国家’的紧张关系”[5];60 年代,台湾政治局势相对稳定,文艺创作受到西方“现实主义”影响,影视行业也开始制作具有“写实主义”的影片。中影老总龚宏受到李行导演的《街头巷尾》的启发,于1963 年提出具有“过滤”现实的“健康写实主义”,并由李行拍摄出《养鸭人家》《柯女》等大量“健康写实”的影片。而后,“台湾文坛与影视界均受到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逐渐形成台湾电影‘现代主义’化的趋势”[6],80 年代初期,《儿子的大玩偶》(1983)以一种全新的视听语言开启了“新写实主义”的滥觞,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电影运动的浪潮。不同于健康写实主义,“台湾新电影用极简的风格,坚持呈现不加修饰的现实”[5],如《小毕的故事》(1983)《风柜来的人》(1983)《我这样过了一生》(1985)《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1986)等。如果说80 年代台湾新电影的发生仍然处在“戒严”期,其创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保守观念,那么90 年代,台湾电影中的写实主义“试图突破1980 年代写实主义的风格,并尝试关注社会边缘题材。[6]以张作骥为代表的“后新电影”导演则将镜头对准当下的台湾底层社会,并将写实主义与帮派文化相结合,成为此一时期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与人文关怀的影像表达。从《忠仔》(1996)开始,导演就以边缘社会的少年为主要表现对象,并将其成长经验放入底层社会与帮派纷争中。而与常见的成长电影中反应青少年懵懂与苦涩青春不同,张作骥电影中的青年男性则是“直视社会弱势阶级的无奈与别无选择,愠怒与隐忍成了成长过程中的必然”[7],这也影射了边缘角落所存在生存困境与认同问题。
帮派电影又称“黑帮片”,“一般认为,黑帮片脱胎于警匪类型片”[8]。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电影类型,不同文化背景下帮派电影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含义。如日本的帮派片强调帮派角色之间的忠诚、信用;中国香港帮派电影则多呈现为兄弟情谊、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而美国的帮派电影则表现对自由、权势的争夺……然而,中国台湾电影中的帮派角色中既没有特定的叙事惯例(包括人物模式化的设定、虚拟空间的营造、激烈地复仇情节),也没有明确的价值观念取向。取而代之是对台湾社会底层各个族群的关注,反复呈现的是时代遽变下,台湾社会文化脉络中人物生存的艰难与人性的挣扎。因此,比起其他具有叙事程式的帮派电影,台湾电影中的帮派更像是一种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它不仅深深地扎根于台湾动荡的现实社会,而且“反映了该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氛围对于权威、秩序与善恶等概念的不同态度,由此显现出该社会脉络下不同的集体困境。”[2]
纵观张作骥所执导的八部长片中,从《忠仔》开始,社会底层青年在“孤立、乱伦、神秘的宗教仪式和帮派文化所包围的暗黑迷宫中前行。”[9]时隔三年,他的第二部长片《黑暗之光》(1999)中无家可归的青少年阿平,亦无法逃出帮派之间的冲突与暴力,最终惨死港口码头;2001 年,荣获台湾金马奖的影片《美丽时光》,影片从“安稳的自家庭院出发,抵达阴暗的台湾黑社会。”[9]当小伟的双胞胎姐姐与病魔做死亡斗争时,他与阿杰因误杀黑帮老大,而遭到其他帮派成员的追杀……2007 年的《蝴蝶》更像是《美丽时光》的一种延续或者说故事的外延。影片中的帮派大哥一哲在《美丽时光》中就已经以帮派角色出现,到了《蝴蝶》中,曾一哲的身份不仅是一个帮派头目,而且还隐藏着关乎其复杂身世的认同焦虑……
二、边缘族群:人物图像与底层空间
在张作骥的影像当中,导演使用写实主义的手法,以“仿纪录片”[10]的形式呈现底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他们要么是90 年代“关渡平原”中被迫跳八家将的阿忠,要么是遭外省父辈遗弃的少年阿平,要么是挣扎在边缘社会与帮派群体的阿杰和小伟……这一类遭遇相似经历的青年男性和帮派角色构成了张作骥电影中的边缘群体图像,导演也不断深化对这一群像的探索,呈现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外省子弟;其次,张作骥电影中通过使用缓慢的影调——长镜头/景深镜头、画外音、黑幕等方式——强化真实的底层社会空间,试图以此探索更加深刻的社会内涵与文化议题。
(一)人物图像:边缘化的青年群像与草莽式的帮派角色
提起帮派/黑帮电影,映现在脑海中的便是身穿黑色西装,手戴金戒指,再加上一副黑色墨镜,手夹一根雪茄。这样的人物图像便是传统帮派电影中对帮派老大的形塑与刻画。图像研究(iconograph)起源于1939 年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19 世纪末,潘诺夫斯基在其唯一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电影中的形式和媒介》中,尝试将“图像”这一概念应用于电影的研究领域。他指出“早期电影中的出现的‘定型化’外表、行为和标志对观众的提示作用:‘两撇黑胡子和一根手杖代表坏人……’”[11]因此,图像学在影视中的应用便具有了归纳类型电影中特定的人物类型、道具以及场面调度中的视觉要素的安排。“图像学”除却归纳整理的功能之外,“更是探讨电影图像安排与组成的象征意义与诠释。”[2]虽然张作骥的电影并不能被直接归类为“类型电影”,但是他影像中的青年男性无疑具有表征时代的意义。本文所探讨的人物图像是以张作骥的电影为检视对象,考察具有相似社会地位与个体经验的青年男性与帮派群体,之于台湾社会的象征意义。
对处在成长阶段的边缘青年男性来说,张作骥电影中的青年男性有着相似的边缘处境——生存的绝境与身份的迷思。如《忠仔》当中,阿忠辍学后被迫去学八家将,希冀以“敬畏神明”的方式来改善家庭霉运状况,但是他却在学习八家将的过程中,不断承受来自家庭、帮派、社会各个面向的磨难与苦楚。《黑暗之光》中的阿平,在母亲死后愈发堕落,从士校辍学后,被父亲委托给曾经的战友、现今的基隆帮派大哥照看。从表层来看,阿平因其孤僻的性格,不仅无法融入帮派团体,还因与康宜相爱而卷入与他营帮派的纷争中;从深层角度来看,造成阿平悲剧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地缘关系上的弱势”——从花莲(一个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相当落后的东部区域)到基隆(以本省人为主,且以闽南语为主的强势族群)的外省子弟,无论是在日常生活或帮派交际中,“阿平形同失语与失能,在此环境的社会阶级脉络中,沦为边缘中的更加极端之边缘位置”[12]。《美丽时光》中的阿杰和小伟,因找不到“正当”工作,而替黑道老板收钱谋生。在一次要债过程中,阿杰因遭到对方帮派老大的侮辱,而意外开枪打死帮派头目,引来杀身之祸。《蝴蝶》当中,曾一哲代替弟弟坐牢刑满,归来后再次陷入更大的精神困境中——不仅无法获得父亲的认同,也无法寻回自己的乡音……纵观张作骥的电影,边缘且无助的青年男性群像成为他影像中突出的人物图像。他们具有共同特征:不仅无法跻身于主流社会之内,而且也无法获得帮派大哥(类父角色)的认可。此类“游荡”在社会边缘且无法以正当手段谋生的青年男性,成为90 年代映射台湾弱势阶级的一个脚注。
除了无归属感且最终丧生的青年男性以外,张作骥电影中出现大量粗莽且无能的帮派角色。按照传统的帮派电影惯例,该类型电影对帮派男性的形塑阳刚且果断、潇洒且理性、沉稳且冷血。也正是这一特质,使得帮派电影中的男性有着统一且易识别的男性气质。而张作骥电影中帮派角色不但抛弃了这一形塑惯例,而且影片中的所呈现的帮派形象,从其外在的穿着到内在帮派的理念,展现的是平民化的外在形塑,以及为谋生而四处奔波的帮派理念。因此张作骥电影中的帮派角色既没有果断沉稳的帮派大哥和阔绰潇洒帮派小弟,也没有做事干练且有勇有谋的体面人,有的是以最原始的粗莽与暴力,为琐碎的小利与冲突四处晃荡奔波的边缘角色。
从其外在的衣着上来看,张作骥电影中的帮派角色无一例外地是身穿花褂衩、脚趿拖鞋,毫无气派可言。如《黑暗之光》里面,帮派大哥身穿白色褂衩,还经常光着膀子四处闲逛,而小弟的外在形象更加寒酸。从阿平的住处来看,他们不仅蜗居在一间杂乱的多人宿舍,而且在衣着上也仅仅是最普通平常的汗衫与长裤。这一帮派形象在《美丽时光》中有着延续性的发展。当阿杰和小伟去帮派老大家要债,跟随小伟和阿杰进入视觉框架中的不是琳琅满目的高档饰品,也不是气派的帮派家族,而是家徒四壁的普通居所,帮派大哥在房内光着膀子斥责老婆,为了赖账对前来要债的阿杰和小伟破口辱骂……从内在的帮派理念上,张作骥电影中的帮派角色既没有“宏观”帮派家族意识,也没有统治一方社区的远大理想。《黑暗之光》中帮派大哥除了“赛鸽赌博”之外,影片不仅没有展现有关他任何的“生意”(经济)行为,而且经常遭遇地方警察的打压与剥削。反倒是他对康宜一家的无私帮助却赢得了底层民众对这一帮派大哥的认可与认同。从这一层面上来讲,张作骥电影中的帮派角色几乎都是在为基本的谋生而四处奔波。作为帮派的大哥,他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拉拢一些“小生意”来维持小弟们的生存状况。比起传统帮派电影所建构的帮派传奇,或通过讲述帮派传奇来营造一个可供观众幻想的帮派间的兄弟情谊,张作骥电影中的帮派角色,更像是在族群纷杂的社会中为谋求生存而与其所盘踞的族群区域与城中区域的居民产生利益关系,同时他们也希望证明自己是在为这个‘命运共同体’效力”[13]。张作骥电影中的帮派角色不仅以其外在的表征解构了传统帮派电影中的形塑惯例,而且其内在理念凸显的是此一时期台湾电影中帮派文化成为台湾底层族群竞相争夺生存空间的一种现实映射。
(二)底层空间:纵深感的营造与现实社会的映射
电影理论家马尔丹认为处理电影空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再现性空间,另一种是构成性空间。前者按照“复原现实”的原则,通过移动摄影使我们去感受空间,后者则是按照“蒙太奇”的方式,将零散的空间段落“并列——联接”[14]。张作骥电影以大量移动摄影、缓慢的影调——长镜头/景深镜头、画外音、黑幕等方式——“再现”底层社会的空间形态,以表现更加深刻的社会内涵与文化议题。
首先,家庭空间是张作骥电影中不可忽视的空间形态。在其早期的电影中,在影片开头,导演通常以同期声代入,继而再现家庭空间。如《黑暗之光》当中,张作骥以一对视障夫妇拍结婚照开场,而后影片正式开始于李康宜背对固定镜头,面朝基隆海港的窗户画乌龟。在同样镜框大小的镜头转换中,李康宜转身朝着镜头走过来,镜头伴随着人物的缓慢行走向后拉去,李康宜继续朝着镜头走过来,此时,家庭空间的纵深感被呈现出来。当李康宜与弟弟的拌嘴时,门铃响起,李康宜又开始从餐桌位置朝着门口走去,这样的纵深空间在张作骥电影中反复出现;《美丽之光》导演以娴熟的镜头技法呈现了“非列管眷村”①1949年,国民党迁台,因“国防部”对眷村的管理有限,把村分为“列管眷村”与“非列管眷村”。这一边缘与落后的家庭空间。影片开头以小伟一家饭前的生活状态展开,先是利用横移镜头呈现家庭内部结构,以及生活在家庭中的人——年老的阿婆、生病的姐姐,爱玩的弟弟……而后,影片采用固定镜头呈现家庭空间的纵深感,前景中身患绝症的姐姐坐在鱼缸面前,后景中阿杰与小伟在讨论什么,而后,阿杰朝着姐姐走过来变魔术。在下一个镜头当中,影片镜头深入到外省父亲的房间,他被阿婆叫出去,顺便带上门,此时镜头特写一张“中华民国九十万寿贺”的纸张,这时,镜头很快横移到由门框形成的景深镜头,前景中小伟在挂条幅,中景是阿杰,后景也是在挂条幅。影片使用接近两分钟的长镜头展现一个家庭空间结构,这样的家庭空间不仅营造出一种真实且有“意味”——暗示家庭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阶级——的空间形态,也“呈现这些人物彼此间的宗族关系或家庭关系,包括社经背景、语言族权的隶属区分,甚至角色的性格特质”[15]。
其次,除却家庭空间所呈现的宗族关系以及家庭所处的社会阶级之外,张作骥电影中较多出现帮派角色所处的“地下空间”。这里的“地下空间”并非是指地理学上处在地表之下的地域空间,而是指帮派团体因其所从事的职业性质——“盘踞于民间、对抗官方政府,并且非法占据当地公共资源”[16]——而无法“光明正大”地在“地上”浮现的空间状态,如帮派角色经常出没的台球厅、非法交易场所、赌场、昏暗居所等。传统的帮派电影中的“地下空间”往往是一个具有严格秩序/规矩的空间。在这个有序的空间当中,帮派大哥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帮派小弟无一例外地处于被支配的状态。不同的是,张作骥电影中的“地下空间”充斥着无序、叫嚣、失败的和解与隐忍式的暴力。导演常采用固定长镜、静默的画面与黑幕等方式,来呈现这个“失序”的地下空间。《黑暗之光》里在“和解”的饭桌上,阿平不断地遭遇警察/组长的侮辱与鄙视,场面也因和解的失败而一度失控,此时双方扭打的混乱场面只有八秒的时间。随后,镜头切换至灰蒙蒙的港口海面,一艘有着启明灯的航船向远处驶去。而后,固定镜头再次切换至打斗场面,此时后景中的打斗已经明显处于虚焦状态,前景是阿平血淋淋的一只手撑在门框上。近景长镜头跟随他来到港口,阿平的主观镜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绝望与凄凉的氛围油然而生,画面随着阿平倒下去的身体而结束。而在《美丽时光》小伟和阿杰被送回台北,两人穿过长长的街道,来到那条暗长的胡同口,却发现仇家已经找上门,这时阿杰和小伟为躲避帮派仇家,穿梭在破旧且阴暗的眷村小巷中。这一底层空间中夹杂着边缘族群与帮派势力。如果说,帮派势力所盘踞的“地下空间”因其非法行为而经常遭遇警察的盘查与压榨,那么小伟和阿杰这一边缘群落则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他们在信仰“道路真理”的逼仄空间中长大,但是又因无意犯错之后,很快被黑帮势力围堵枪杀。这一段落的空间安排,呈现了更加明显的阶级对立,即帮派势力既可以为其所盘踞的区域谋取利益,也能够为了复仇而随意伤害更加弱势的群体。
对边缘族群的关注与底层空间的再现成为张作骥电影中重要的两个面向。边缘族群的形塑构成了张作骥电影中的具有图像化意义的边缘人物,而底层空间的再现提供了阶级对立与暴力发生的场所。
三、认同焦虑:挫败的男性,失败的认同
90 年代初期,民进党“利用掌控行政资源与媒体,挑起省籍对立,撕裂台湾族群……统独成为台湾社会最大的焦虑。”[17]这也使90 年代的台湾社会充满了动荡与不安的情绪。认同焦虑的产生也使得过去以“巨父”形象为最高表现意志的政治话语开始走向瓦解。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张作骥电影中呈现出大量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挫败男性。他们试图通过叫嚣与谩骂、爱与性的补偿、故地重游/寻找过去等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他人的认可,建立自己的主体性。但由于历史经验的不可磨灭与当下社会处境的尴尬,使得这一行为带来的不仅是生存的挫败,而且也是引发认同失败的深层原因。
权势地位与掌控力是男性在社会中所追求的优越特质。尤其是在帮派文化中,帮派男性向来以阳刚的男性气质、优越的经济地位和出众的外貌体魄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相反地,张作骥电影中的帮派角色/青年男性既不具备优越的经济地位,也不具有阳刚体魄。他们试图通过叫嚣与谩骂、爱与性的补偿、故地重游/寻找等方式,来确认自己作为男性的身份与特质,从而获得他人认可。如《忠仔》通过画外音的方式,不停地抱怨外界体制对自身情绪的压迫,并以自我戕害的举动发泄对父亲行为的不满;《黑暗之光》中,刚加入帮派组织的小弟阿平,通过接受并拥有康宜(女性)的恋爱来证明自己强于他营帮派小弟(男性阿麟);《美丽时光》中,当小伟和阿杰的“讨债”工作初步得到老板认可,并赏赐他们一把枪时,阿杰总是把枪插在腰间,动不动就拿没有子弹的枪“吓唬”别人,从而树立自己的气势与尊严;而到了《蝴蝶》当中,作为帮派大哥的曾一哲重回故乡,但是却发现再也没有人记得自己……这一系列的行为反映出涉世未深的边缘青年男性总是极力表现出自己作为“男性”的特质,并试图通过这一男性特质来获得外界/他人的认可,从而获得身份/文化的认同。但是实际上,这一行为的后果不但没有为其树立起男性身份,反而因其“出格”的行为陷入挫败与绝望当中。如阿忠退出八家将之后,只能默默地看着母亲成为逗笑观众的“小丑”;《黑暗之光》中,阿平因为“抢”了阿麟的女友,引起各帮派争斗而失去年轻的生命;《美丽之光》阿杰因误杀帮派老大而招致帮派的追杀,最终被乱棍打死;《蝴蝶》中,一哲因保护弟弟打死对方帮派老大而被刺死在迷幻的丛林中……
由外在环境引起的挫败感直接导致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失败。这一失败的认同感也致使他们在产生自我怀疑。因为“人总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框架中建立对自我的认知……假如人的群体归属感失效,人作为个体对自我认同也会遭遇挫折。”[18]张作骥电影中无法通过他人认可的底层青年男性,皆无一例外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然而,需要探究的是,在政治与文化相对开放的90 年代,为什么台湾电影中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如此多的底层/帮派男性在社会阶级中的挣扎与无奈。如《少年叱,安啦》(1992)《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南国再见,南国》(1996)《忠仔》(1996)《黑暗之光》(1999)《美丽时光》(2001),等等。
解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检视90 年代台湾社会环境,更需要追溯其历史经验。众所周知,1949 年,蒋介石携近120 万“军公教”迁进台湾。大规模的迁台并非仅是空间地理上的位移,而是一次复杂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汇。为了安置军队,台湾出现了大量的“眷村”居所。“至1982 年左右,全台约879 个眷村,约98535 户”[19]。因对眷村的管理有限,管理者把村分为“列管眷村”与“非列管眷村”。“眷村所处区域以及是否为“列管眷村”即代表了居住其中的外省人所属之社会与经济阶级”[12]。而张作骥电影中的眷村明显处在社会边缘的“非列管眷村”。如果说生活在“列管眷村”因社会阶层的优越与生活的富足而不会引起对现状的不满,那么,处边缘社会的“非列管眷村”不仅无法享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也无法从事正当的社会职业。因此,他们不但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且也常常因“失意”的情绪而产生怀旧的情感。问题是,对于有“家乡”的第一代“非列管眷村”的荣民而言,他们可以通过对大陆/故乡的思念或归返,来获得精神层面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但是对于出生在台湾的“眷村二代”来说,他们“自己把自己看作是台湾人,但他们又被台湾人称作外省人,这种身份的困惑伴随着外省二代的成长,像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迫使他们不断面对这个身世之谜”[20]。如《黑暗之光》中,“外省二代”阿平的父亲离开台湾后,他因违反军校纪律被除名,而后加入黑帮团体。阿平不仅无法融入黑帮团体,也无法获得黑帮老大(代偿性的认父)与他人的认可;《美丽时光》中阿杰与小伟“闯祸”后,(黑帮)大哥立刻与其断绝关系,阿杰因此被仇家开枪打死;而《蝴蝶》中,一哲在身份的错乱与“寻找乡愁”的失败中,做出“弑父”的举动,而“弑父”的行为并没有使得一哲获得解脱,而是陷入更大的精神困境中。
如果说“身份主体性”的建构与“去殖民化”成为台湾本省人强化“在地性”的方式的话,那么到了90 年代,“外省二代”在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男性之后,则处在一个相对尴尬的位置。他们既无法自觉地融入其中,也无法获得他者/本省人的认同。张作骥影像当中的“外省青年”与“本省帮派”之间的冲突与决裂都呈现了身份的尴尬。在“父辈”寻找“在地性”主体身份失败后,“子辈”则陷入了更为惨淡的境地——漂浮的文化身份。这一漂浮的文化身份一如前文所述:既无法与“父辈”乡愁呼应,也无法获得“在地性”的认同。因此,在无法完成的“自我认同”当中,青年形象要么在混沌的生活中继续挣扎,要么丧命于帮派的暴力之中。但导演总是在主人公丧命之后,以“鬼魅”的方式来使死者获得重生。导演意不仅“构造了一种联结现实主义和后殖民的新模式”[21],而且以悲悯的心态给予了“这些道德世俗式的边缘人物得到精神层面的拥抱与救赎,让普世众生皆有机会能够被平等的对待”[22],这也许就是导演张作骥以“光明结尾”的温情方式对90 年代的台湾边缘族群的呈现与思考。
结 语
在美学形式上,张作骥继承并发扬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美学形式,在内容呈现上,他则更加深入地呈现台湾边缘族群的生存困境。导演把写实主义与帮派叙事相结合,颠覆传统帮派电影中具有主宰性的霸权男性气质,塑造出具有图像意义的边缘化青年/帮派男性形象,并在具有象征性的底层空间中,再现了边缘族群的生存状态与身份难题。总而言之,张作骥影像中的边缘族群不仅指向了20 世纪90 年代台湾社会的乱象,也反映出底层社会的生存困境与族群认同的焦虑与迷茫。
——以《台北人》与《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