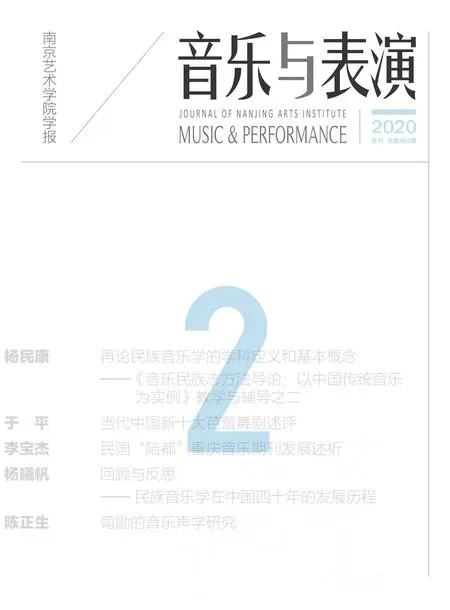再论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
——《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教学与辅导之二
杨民康(中央音乐学院,北京 100029)
本讲将继续讨论《导论》①下文将把《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一书简称为《导论》。第一章“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
第一讲说过,《导论》的上篇涉及了“一论两史”,分别涉及了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学和学术史两个基本的方法论侧面。其中第一章主要是侧重学科学的讨论。在初版中该章分为三节,在修订版中扩充为四节:一、常规方法论层面: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二、研究音乐是否需要“语境”或文化支点;三、对认知民族音乐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接纳与应用(新增);四、常规方法论与文化哲学观:学科理论的转型与分层。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去展开讨论:第一,民族音乐学暨音乐民族志的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包含了常规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两个基本层面;第二,两个层面之间涉及了实践经验(与音乐民族志相关)与哲学思想(与音乐人类学相关)的层次性差别以及外显、内隐和下位、上位等二分关系;第三,两个层面的出现有先后之分,可以视之为当代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两次转型。
在《导论》第一章里,已经对音乐民族志暨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做了力所能及的介绍和分析。作为导读文章,本文除了将从元理论层面予以进一步归纳、梳理、解读和总结外,还将对其中所涉及的一些人文社科跨学科学术背景进行阐释性分析,并对原书中未能尽言的一些新的个人理解和设想略做补充性陈述。
一、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的两个基本层次及其学理脉络
在《导论》第一章,笔者提出,在当代民族音乐学暨音乐民族志的学科定义和基本概念里,包含了常规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两个基本层面的观点。在本文里,将提出并讨论当代民族音乐学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曾经历了与其学科定义变迁同步相关的两次基本的学科方法论转型:一次是它作为经验性、实践性学科,于民族志与常规方法论自身层面的转换,具体体现出由客观事实性到兼纳客观事实性与主观意义性,由文本间性到兼纳文本间性和主体间性以及由描述性书写到兼含描述性、阐释性书写等几方面转换特点。另一次是在它由经验性、实践性学科转型为兼含理论性的综合性学科的过程中,从常规方法论到兼含常规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的复合层面的转换。这里先谈前者。
(一)五个基本学科定义、两大学术研究阵营与两种不同学术观点
在《导论》第一章中,围绕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定义,举了众多的例子,其中最为关键的有五个基本定义,均不同程度与“音乐学派”和“人类学派”两大阵营的学术论争相关。其中前三个学科定义分别是:
1.胡德提出的“民族音乐学是对一切音乐(any music)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它不仅研究音乐本身,而且也研究这种音乐周围的文化脉络(cultural context)”。[1]与此相关的是,利斯特(List,1969:195)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传统音乐的研究……”。[2]
2.梅里亚姆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3]
3.梅里亚姆将民族音乐学定义改为“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4]
上述三个定义,都紧紧围绕常规方法论及音乐民族志的书写等基本问题。对此,不仅可以从民族音乐学层面,而且可以从音乐民族志的层面加以理解。若论其中有何不同?日本民族音乐学家山口修评论说:“实际上他(胡德)的研究成果在有关音乐自身的构造分析方面倒是比较显著。”[5]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涅特尔(Bruno Nettl)则认为:“这样的民族音乐学乃是‘作为音乐的研究’”(the concept of ethnomusicology as the study of music)。并且认为至少就主旨和重点而论,胡德的这个定义同梅氏的定义是完全不同(quite different)的两种观点。[6]1311980年版新格罗夫音乐辞典的“民族音乐学”条目则进一步提出:“也许是由于民族音乐学同时作为音乐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分支存在的原因,有关它的定义彼此各不相同。”该论还将梅里亚姆和利斯特分别指为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的代言人。由此可见,上述学者将梅、胡为代表,分别为民族音乐学所下的“作为音乐的研究”或“作为文化的研究”两种定义看作是分别代表音乐学和人类学“两大学术阵营”的,“完全不同的两种观点”,是没有异议的。
另外两个与之密切相关,目的又略有不同的定义,一个是梅里亚姆基于音乐民族志书写思维方式提出的“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亦即为今天许多学者所熟知的,民族音乐学“涉及三种分析层面上的研究——关于音乐的概念,与音乐相关的行为和音乐的音声本身。”[7]另一个是安东尼·西格(Aathony Seeger)在《音乐民族志的风格》一文里,通过对音乐民族志和音乐人类学所做的比较,给出了“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阐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历史”[8](Seeger,1991)的定义和结论。关于后两个定义的特别之处,将在后文予以讨论,在此拟先交代一下与上述两种不同观点相关的人文社科学术语境与时代背景。
(二)与两种民族音乐学不同观点相关的学术语境和时代背景
若进一步考察上述民族音乐学学科定义得以产生的学术语境和时代背景,可以看出,它们虽然表面上涉及音乐学派与人类学派之争,实则体现了以“音乐”(或艺术)为象征的客观事实性与以“人和文化”为象征的主观意义性两者的对立、交替与融合关系,其中处处透现出 “主观—客观”及“主位—客位”二元对立关系的交织、影响以及人们对于主位文化观的取舍态度。
由此看《导论》的各章节中,笔者曾经多次谈到20 世纪中下叶,因认知人类学、阐释人类学等人类学学科对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导致形成了以梅里亚姆、布莱金等为代表的,以“认知民族音乐学”所彰显的当代民族音乐学研究观。而这类学术观念,又继承、来源于更早发生自欧洲的一些社会学学术传统。比如,按美国社会学学者彼得·L.伯格(Peter L.Berger)和托马斯·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1966)一书中所说,早期宗教社会学家涂尔干所提倡的、最基本的社会学原则是:“把社会事实视为物”,另一位社会学家韦伯则观察到:“行动的主观意义丛结是历史学与当前社会学的认识对象。”该书作者认为,“这两种表述并不矛盾。社会确实带有客观的事实性,但它也确实是由表达主观意义的行动所建立起来的。由客观事实性和主观意义性所构成的二元特征恰恰使得社会成为一种‘自成一类的现实’”。[9]24然而其中一种较为明显的趋向却是,韦伯所谓的“行动的主观意义丛结”已然成为最受当代学者青睐的,“历史学与当前社会学的认识对象”。此类学术观念在其后辈学者伯格、卢克曼、格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学术著作中反映出来,并且在同时代的梅里亚姆、涅特尔等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论争中,通过以“音乐”(或艺术)为象征的客观事实性与以“人和文化”为象征的主观意义性的对立、交替与融合得以明确体现。而梅里亚姆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和提出了“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则为当代民族音乐学同样比较重视韦伯提出的“行动的主观意义丛结”的做法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注脚。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界,20 世纪80、90 年代也开始将该类学术观念引入国内,甚至也有人将它拓展到中国音乐学研究的“元理论”层面,并提出了如下问题,“我觉得将目前我们的‘音乐研究’扩大成‘音乐文化研究’是适时的,也就是说逐渐将我们的研究视点由‘人的创造物’(把音乐作为一种人的活动结果)转移到‘人的创造’(把音乐作为一种人的活动方式)上来,或者说扩大我们已有的研究视界,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10]然而,当时这样的话题,在具体研究的层面上还有些“曲高和寡”,更多停留在观念性讨论之中。在民族音乐学界也是这样,尽管当时大家对梅里亚姆提出来的“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及“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已经并不陌生,但却很少有人真正从音乐民族志书写和思维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地揣摩它的具体含义,而能够像布莱金那样将其具体应用到研究和分析实践当中,就更不容易了。
二、常规方法论的第一重拓展——“文化(语境)中音乐的研究”
音乐学(艺术学)或早期民族音乐学的形单影只,主要体现在它更多强调、倚重的是形态学分析。就此,梅氏提出民族音乐学是“文化中音乐的研究”,而在其身后的诸多民族音乐学著作里,这个定义又被延伸为“文化语境中音乐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当时有关该学科的诸多学术贡献里,这类定义从符号学的角度,把民族音乐学的形态学研究与语用学,亦即韦伯所言“行动的主观意义丛结”联系起来,为民族音乐学拓宽了学术道路,从而体现了当代该学科方法论层面的第一重拓展。
这里,顺便提一下在新版的《导论》第一章里,新增加了第三节“对认知民族音乐学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接纳与应用”。增加这一节的原因,是由于笔者通过多年的学习与研究实践,越来越感觉到,对于当代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学科内容不断拓展的状况,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去解释,其中较为可行的一种就是用文化符号学的方法原理去进行读解。一般来说,符号学可分为形态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语境学)三个分支,其中,形态学作为三个分支之一,居于系统的表层,语义学和语用学居于隐层。从研究对象看,形态学和语义学分别涉及符号的形式和意义内容,语用学主要涉及符号生存的语境及人——符号的使用者两个要素。
(一)语境在符号学——语用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代民族音乐学学科主旨和定义中体现出的某种由较单纯的“音乐研究”转向“文化语境中音乐的研究”的学术转向,若从研究者,或客位、局外的角度看,这就涉及音乐民族志学者怎样去书写和分析的问题。倘若从局内人或主位观的角度看,便是一种将客观事实予以内化的过程。关于前者,在新版《导论》第一章里,笔者在提出上述转型趋向的同时,还提出此期音乐民族志书写亦曾经经历过两次方法论转型:第一次转型(1960-2000),主要体现为(比较音乐学时期的)宏观比较向(现代民族音乐学时期的)微观个案研究方法的转换和过渡;第二次转型(2000-),则体现为由定点个案研究延伸至多点音乐民族志研究。其中,音乐民族志书写的第一次转型与民族音乐学学科主旨和定义的第一次转向同步。这也即在第一章中笔者提出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是否需要“语境”或“文化支点”的问题。这里,将从这个概念的源头说起。
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又称“文化的上下文语境”。仅从“语境”一词的符号学原意看,是指一个意指不清的名词,可以借助其在句子中的上下文来获得意义的解释。比如下面这句话:“这个国家叫中国,在亚洲。”其中,“国家”为无意指名词,整句话即上下文语境。而在具体的音乐研究课题中,将较单纯的“音乐研究”置入上下文语境,首先是指表演场域,然后才是社会文化语境。就此来说,一般的西方音乐学学者、早期的比较音乐学学者和以梅里亚姆为代表的当代民族音乐学学者,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课题的不同性质,对文化语境的需求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们尝试以莫扎特《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布朗族民歌这样两个较极端的研究对象为例,看看西方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两类学者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学术局面和能够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手段。
(二)客位视角——社会文化语境下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思维和方法手段
对于前一类研究对象来说,由于身为纯音乐(或“无标题音乐”)类型,意义(语义)的解释无关紧要,也就无需求助于上下文语境。至于其中人与环境的因素,虽然与表演行为相关,但是在研究者开始这项研究时,从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到协奏曲的一般音乐特点以及民族文化特点,可以说都有前人研究为依据,在此研究者要想通过研究获得的,仅只是该曲的音乐个性特点,以为表演所用而已。至于早期比较音乐学的学术状况,该类学者一般沿用了西方音乐学的学术观念和研究目的,即使在面对非西方音乐时,也往往会较多出于物质性或艺术性的目的,主动去选择乐器为主的考察和研究对象,而对语义性较强,对文化语境依赖程度较大的民歌弃而不顾。
比之而言,当带有人类学目的民族音乐学学者较主动地去面对后一类研究对象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笔者所选择并面对的布朗族民歌这样的少数民族传统民歌,往往带有较强的整体性特点。其中包含的不同民歌种类,因其具有的不同的文化性质和功能作用,对于语境和乐讯使用者的依赖程度也大小不一。其民歌具有的不同语义功能,可以看作是在其符号通讯过程中,以音声符号作为载体,负荷并传送各种艺术或社会文化内容的不同方式类型。依语义功能与语境结合的不同方式,具体可分为四种:
1.以再现社会内容和意义为主旨,符号内容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传载功能,比如叙事史歌;2.抒表发乐者的感情、心志,发乐者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抒表功能,比如儿歌;3.向受乐者传达讯息,受乐者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传讯功能,比如情歌;4.符号本身不再现社会内容,符号形式在其中起重要作用的趋美功能或娱乐功能,比如抒情性舞歌。[11]
据我自身的学术经历,在我20 世纪末叶开展布朗族民歌课题时,除了对其中所包含的一般民族特征已经有人研究过之外,对于这类富含历史、民俗、宗教意味的民歌,从表演语境到文化语境,几乎是一片空白,都要从头开始考察和研究。并且由于文化多样性的原因,我们对于每一个民族、族群的民歌开展研究时,都很难去完全借鉴以往的经验和阅历。这时,把音乐置入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研究,就成为一个非常具体的任务和目的了。事到如今,学者们已经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既然布朗族民歌研究需要考虑文化语境,难道研究莫扎特《e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就不需要结合文化语境吗?对此,于润洋先生在他提出的“音乐学分析”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有关心此事的读者,可以继续循此深入追踪和观察。
(三)主位视角——社会文化语境下客观音乐事象的内化、外化和客体化
民族音乐学具有的意义和功能作用绝不仅限于音乐或艺术层面,这是肯定无疑的事情。但是,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而并非是唯一主旨)和物性依据却主要是音乐。当我们将它放置到语境(或语用学)层面看待时,它仅是整体性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功能主义研究话语中,也仅是一种局部功能类型。实际情况则是,在社会个体所依存的客观世界或整体性文化语境中,音乐与其他文化事象总是融为一体,并且同时针对个体产生内化、外化和客体化作用的。
前文曾经述及,当今人文社科理论中已经呈现出“由客观事实性和主观意义性所构成的二元特征”。而韦伯早已观察到的“行动的主观意义丛结是历史学与当前社会学的认识对象”这一学术现象,后来为伯格、卢克曼、格尔兹等社会科学学者及梅里亚姆、涅特尔、布莱金(John Blaking)等民族音乐学学者所继承。关于民族音乐学学者所关心的音乐与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如同伯格和卢克曼所看到的:“在社会个体来说,也即体现了其外化、客体化和内化的过程。”作者并且认为,“外化、客体化和内化”这三类现象,在人类现实生活中是同时并存和并举的。换言之,对于社会中的个体成员来说,“他在社会世界中外化自身的存在,同时把社会世界作为客观现实予以内化。”[9]161若我们同意上述观点的话,那么对于本文所论及的,当代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两重拓展之一——梅里亚姆等人将音乐与文化语境和人联系起来看待和讨论的做法,或许应该视为他们关注到了社会个体将音乐——一种“客观现实予以内化”的一方面;至于第二重拓展,即梅氏提出的另一个“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可说他们同样注意到了社会个体“在社会世界中外化自身的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行为活动。就此而言,后者乃是在前者持有的文化本位分析思维和方法论基础上的继续和延伸。
三、常规方法论的第二重拓展——“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
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定义中对于学科方法论的第二重拓展,即通过提出“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模式,释放出“主观意义性”外化的三层含义:首先,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中,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或“主观意义性”,亦即相对于其所创造的文化产品所具有的主观能动作用;其次,指出了发挥这种作用时所具体遵循的“个体外化”——“主体→行为→客体”具体活动路向;再者,事关本学科的尤其关键的一点是,在这种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维和方法的启示和触动之下,民族音乐学的形态学分析也发生了相应的嬗变,出现了一系列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为了达到上述研究目的,或有必要将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对象一齐纳入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对它进行一番以惯例化、制度化、正当化和层次化为对象和标尺的学术考量。
(一)惯例化、制度化、正当化——乐人音乐文化概念模式的形塑及过程
依据社会学理论,每一位内文化持有者在其一生中,都将出现并拥有由内化、外化和客体化构成的一系列社会化经历和体验。首先,他在幼年时期认识和接受传统和外来知识,都将被汇聚入一个惯例化、制度化和正当化的过程,也就是在“社会传统”的既定轨迹里,社会个体将世界社会的客观现实予以内化的过程。按伯格的说法,即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人类有机体完成了自身的发展,这一过程恰恰也是人类“自我”的形成过程。[9]66在此过程中,首先,“所有人类活动都有可能被惯例化(habitualization)/任何一种行动在被不断重复后都会被铸成一种模式(pattern)。”其次,“当不同类型的行动者之间的惯例活动呈现为交互类型化(reciprocal typification)时,制度化就出现了。换句话说,所有这种类型化都是制度。”[9]70-71再者,“只有当一个人的内化达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才成为社会性的一员,这种个体发生过程就叫社会化。”[9]163
而后发生的是,“制度世界也需要正当化(legitimation),即它需要被解释和被证明。……精巧的理论正当化……是一个社会中‘人尽皆知’的事情的总合,包括准则、道德规范、智慧箴言、价值与信仰、神话等事物。要把这些事物全部理论化,需要极其繁复的智力工作,就像从荷马到眼下的社会系统建构者所做的事情那样。”[9]80-84无疑,音乐作为局部性知识和一种“角色化”类型,一样被纳入这样一个“精巧的理论正当化”体系,并且从梅里亚姆等众多学者所言及的音乐与文化的概念化系统中部分地体现出来。按照社会学家的说法,这种“精巧的理论正当化”——有关内文化的概念化系统(或文化模式)是隔代完成的,并且在每一位新生的社会个体心中塑造成型。其后,在其成年期或次级社会化期间,其主观意义性产生外化,并通过“主体→行为→客体”(亦即“概念→行为→音声”)的具体活动路向得以外向释放和发挥。
(二)正当化之后:“观念、学统、方法”层次观与“观念→行为→产品”运行论
在上述学科发展过程中,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内部形成了“观念、学统、方法”三个范式层次。其中,往往由哲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母学科提出的一般方法论占据了引领地位。而在民族音乐学内部,同样居于上位及观念层的音乐人类学,通过与其他母学科之间的跨学科互动交流,产生、形成了自己本学科的思想、观念元素。同时,各种经验学科层次(如音乐民族志、音乐形态学)和地缘、对象学科(如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流行音乐研究)还在传统的学科分类思维影响下发展和运作,为母学科和子学科观念层的锻造过程贡献了具体思路和实践案例,由此在各子学科内部形成了自己由“观念→行为→产品”的体系性研究范式。据此,若将音乐民族志方法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对象相结合,或许能够在人文社科及民族音乐学的学统层、方法层有所作为,创造出民族音乐学及音乐民族志的中国经验乃至中国范式。
(三)“主观意义性”外化:“概念→行为→音声”的理论模型与分析实践
在上述学界大趋势的影响下,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体性转向和“人的外化”趋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在民族音乐学领域,梅里亚姆比较敏锐,在认知民族音乐学的学术语境下,率先提出了“概念→行为→音声”的研究话题,但由于他英年早逝,这个话题被布莱金、赖斯等学者接了过来。在更新一辈学者的手中,这类研究话题更是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层面被逐渐推向和延及音乐形态学分析领域。在此研究阶段,民族音乐学的形态学分析思维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嬗变。音乐民族志书写的思维方式从以往突出(音乐)文本间性向更加突出主体性和主体间性过渡;音乐概念和音声在符号学意义上得到有效的鉴别和区分,出现了一系列基于结构主义——符号学方法基础上的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后者如“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简化还原分析法”和“转换生成分析法”等。对于此方面的研究状况,笔者已有另文介绍。[12]更为具体的案例介绍、分析和理论构想,将在本导读系列的后续文章及《音乐民族志书写》《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等拙著中再予进一步展开。
四、民族音乐学学科方法论的第二次转型:“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
《导论》第一章里,作者提出当代民族音乐学继在常规方法论层面完成了由客观事实性到兼纳客观事实性与主观意义性的第一次方法论转型之后,又曾经历了由常规方法论向兼纳常规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层面的第二次方法论转型。而梅里亚姆于1977年将民族音乐学定义为“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可以视为这次转型的风向标。
关于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第二次转型中兼纳常规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层面的情况,可以参考安东尼·西格在《音乐民族志的风格》一文里对音乐民族志与音乐人类学所做的学科性质的区分:“音乐人类学是应用一套特殊的理论,去阐释人类行为和音乐发展历史;而音乐民族志则是如实记录对人群音乐的认识,它不需要任何理论的演绎,而只需要假定对音乐进行描写是可能的和值得的。”[8]随着研究对象和学科自身的快速发展,如今这个定义也在发展和变化中。
首先,民族音乐学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以“音乐人类学、音乐民族志”亦即文化哲学观与常规方法论的两层区分方法,以及“观念、学统、方法”三个范式层次构成的、完整的方法论范式体系。对此,除了西格外,涅特尔也认为梅里亚姆的定义“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是历史和民族志研究的常规方法,“音乐作为文化的研究” 则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专门研究。[6]131-132
其次,两个学术层次都同样注重去致力于主体性或主观意义性的思想观念建设。其中,音乐人类学从观念和学统层面着手,关注于解决主观意义性——主体、客体的关系及主体间性——主位、客位的关系问题。比之而言,音乐民族志则更多是从常规方法论及实践、操作层面去解决实际问题。
再者,在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民族志两个学科方法论层次及三个范式层面之间,存在着相互贯通,密切结合的特点,很难将它截然区分开来。以音乐民族志为例,虽然它不主张做过多的理论上的演绎,但却非常强调在音乐人类学及观念层理论方法的指引下,去结合使用描述性与阐释性描写手段。其阐释的对象是主位文化观,致力于“内文化持有者阐释的再阐释”。
结 论
究其实质,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都是以实践、经验(体验)为根基的学科,亦是强调从主体——(音乐)符号使用者和主位——人(或乐人)出发,去兼纳客观事实性与主观意义性的学科。这两方面特点一直都较为集中地体现在(音乐)民族志方法身上。如今在民族音乐学里,一直居于上位及观念层的音乐人类学,由于与其他相邻学科——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的融合交流、互补互渗,导致了其自身学术面目越来越趋于模糊性和复杂性,拥有了更多的跨学科关系性质。而在研究实践方面,其重心越来越向音乐民族志偏移,越来越强调音乐民族志的作用,而使以往仅作为民族音乐学属下一个学术层面存在的音乐民族志,如今也逐渐具有了准学科的学术性质。本书以《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为书名,便因此有了“正当化”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