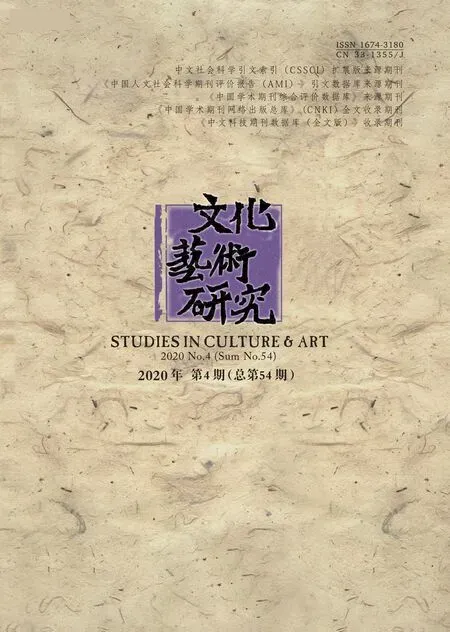柳亚子“捧角”之辨正
周逢琴
(西南科技大学 文学与艺术学院,四川绵阳 621010)
南社是一个革命文学团体,柳亚子乃南社的灵魂人物。1912年春,柳亚子主持《民声日报》文苑,为伶人冯春航捧场,又在《民立报》《太平洋报》等报刊上发表短文,揄扬冯春航,并带动南社社友多人,成为冯春航的拥趸,俨然“冯党”。1913年柳亚子推出《春航集》,1914年又出《子美集》,为另一位新剧家陆子美张目。有人认为,南社人捧角,关注的是“独立的人”的艺术,不同于视伶人为“物”的赏玩式的“捧”,“无疑是具有现代色彩的”。[1]也有人认为,南社文人把捧角作为倡导政治革命与戏剧改良的手段,捧角的实质是以此形式倡导一种戏剧新理念、新观念,是对封建“捧旦文化”的一种超越。[2]还有人从南社词作印象出发,指出柳亚子等人的捧角仍是无聊的旧文人劣习,虽然冯春航、陆子美等也曾演出一些“革命”性质的新剧,但这是柳亚子等为自己捧角的辩护。[3]166孰是孰非,需要仔细辨正。
一、捧冯春航
冯春航(1888—1941),名旭初,江苏吴县人,师从沪上名伶夏月珊,9岁登台,人称“小子和”。柳亚子早在1902年就观看冯春航演戏a冯春航时年14岁,柳亚子也不过年长1岁。少年时代的记忆鲜明难忘,所以柳亚子在结识了冯春航后,作诗云:“相思十载从何说,今日居然一遇君。”寄尘:《〈春航集〉纪事一》,载柳亚子:《春航集》“杂纂”,广益书局1913年版,第56页。,“余初识春航,在丙午年(1902年),时春航方在大新街丹桂茶园。所演《百宝箱》《刑律改良》诸剧,观之使人肠断”[4]121。《百宝箱》即《杜十娘》,《刑律改良》即《贞女血》,这两部剧有人称之为新戏,但从内容看,乃是新编之戏,应属传统戏曲范畴。在柳亚子回忆中,这一年冯春航还演出了《玫瑰花》一剧。这部剧的题材、表演形式、戏服,都有浓厚的改良色彩。《玫瑰花》以“玫瑰村”的被占据和复得,隐喻中华民族的命运。剧中饰演主人公玫瑰花的,就是冯春航。署名“裴郎”的作者回忆说:“春航以夏氏高足,久从潘月樵、刘艺舟诸子游。英发高华,不同凡俗。犹忆十年前,在丹桂茶园演《玫瑰花》革命新剧,一时名士,皆目为法国自由女神,即其身价可想矣。”[5]24《玫瑰花》外,冯春航还演出了不少革命新剧。据欧阳予倩在《自我演戏以来》一文中回顾:“南市新舞台是在中国第一个采用布景的新式舞台……他们最受欢迎的戏有《新茶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惨》之类,当时种族观念正从国民间苏醒过来,这种戏恰合时好,如潘月樵的议论,夏月珊的讽刺,名旦冯子和、毛韵珂的时装、苏白得成为一时无两。”[6]
从编演的多部新剧剧目看,冯春航虽善演旧剧,其实也是当之无愧的新剧家。《中国戏曲志·上海卷》有载:“新舞台建立后,(冯)又排演《妻党同恶报》、《新茶花》、《恨海》(一名《情天恨海》)、《江宁血》、《贞女泪》(一名《刑律改良》)、《黑籍冤魂》、《冯小青》、《红菱艳》、《杜十娘》、《花魁女》、《孟姜女》、《薄汉命》等‘醒世新剧’。”[7]综观各方旧闻,自1902年起,新剧发展起伏颠扑,冯春航至少主演了《玫瑰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惨》《血泪碑》《惠兴女士》等剧,并且很可能是他亲自编演的。这些新剧长演不衰,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都活跃于上海各大舞台,被不同的剧院和演员重新演绎。
因为接触了刚刚兴起的“新剧”,柳亚子对于戏剧改良的热情被大大激发。他对戏剧界的改良充满期待,希望能真正通过新剧,用时装新剧、洋装新剧的形式,表现排满光复的思想精神,借戏剧将世界眼光和光复思想输入国民脑中。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柳亚子热情地呼号:“今当捉碧眼紫髯儿,被以优孟衣冠,而谱其历史,则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尽印于国民之脑膜,必有欢然兴者。此皆戏剧改良所有事,而为此《二十世纪大舞台》发起之精神。”[8]少年柳亚子的戏剧观念,必与其观剧经验相关。可以说,从冯春航表演的新剧中,柳亚子受到了某种情感的震动和思想的激发。
尽管如此,柳亚子之捧冯春航,也有不少传统文人积习。据胡寄尘《〈春航集〉纪事一》记载:“亚子之识春航,在清末乙丙之间,至庚辛而倾倒益深,此时已有赠春航诗矣。”[9]541909年11月,冯春航在苏州演出《血泪碑》,时值南社第一次虎丘雅集,柳亚子观戏成痴,为赠诗一律:“黄歇江边旧凤雏,无端乞食到姑苏。蛾眉谣诼声何苦,翠袖飘零怨岂芜。别有伤心看宝剑,那堪多难识明珠。狂生旧是陈阳羡,也许云郎捧砚无?”[10]此诗只是与同人风流自赏,但以陈维崧与云郎的关系,喻自己与冯春航,不能不说是以名士自命且有狎昵之心。在《箫心剑态楼顾曲谭》剧评中,柳亚子多次称冯春航为“美人”,也很刺目,如“春航工颦善笑,如百面美人”,“今革命功成,美人无恙。久宜重排旧剧,纪念前徽”。[4]124在致友人书中,也有狂言:“春航近日排戏劣丹桂,主者可磔也。小云(与冯春航搭戏的龙小云)亦从未登台,广陵散从此绝矣。弟有十万金,当收此两人为家伶……”[11]可见,柳亚子的旧文人心态,并未完全去除。
妇人醇酒,似乎是柳亚子一班人逃脱政治打击的灵丹妙药。柳亚子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颓唐生活,说:“在《太平洋》专编文艺,替冯春航捧扬,一面和曼殊、楚伧大吃其花酒。曼殊常叫的倌人是花雪南,楚伧是杨兰春,我却是张娟娟。记得有一首绝句道:‘花底妆成张丽华,相逢沦落各天涯。妇人醇酒寻常事,谁把钧天醉赵家? ’颇有英雄末路的感慨。”[12]同一时期捧冯春航,何尝不有耽于声色之娱的意味?但是,这一“捧角”心态在“二次革命”爆发后,出现了明显转折。如果说,《春航集》出版之前,柳亚子的捧角有旧文人遗习的话,那么随着“二次革命”的形势进展,出版《春航集》以对抗《璧云集》,也确实可以视为一次政治对抗,只是偏于消极而已。
关于冯党、贾党之争,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回忆说:“北伶贾璧云南下,《小说时报》出版《璧云集》,我便出版了《春航集》以为对抗,于是冯党与贾党的斗争颇烈,甚且含有南北斗争的意思。”[13]持有这种看法的并非柳亚子一人,“《中华民报》管义华君谓冯、贾之争,实含有南北新旧之关系。仆谓,岂唯南北新旧,即民党与官僚派之奋争,共和主义与专制主义之激斗,皆于是观胜败焉,可矣”[5]24。而今之学者说:“非常时期政治上的南北之争居然可以通过这种无聊的捧角活动来表现,如果不是柳亚子后来的自我拔高,那真可谓革命党的堕落了。”[3]165笔者认为,捧角活动既不完全“无聊”,也并非柳亚子的政治性自我拔高,彼时南社的革命活动趋于消沉,视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可以的,视为革命党的堕落,则言过其实了。
柳亚子等人早有为冯春航编小册子的想法,1913年6月,因为《璧云集》的出版,同人更觉出版《春航集》刻不容缓。胡寄尘云:“亚子于夏初来海上,以稿付余,偕同人访春航于其寓,春航出小影二十余枚赠之。亚子‘相思十载从何说,今日居然一遇君’者,即成于此时也。”[9]56可见,柳亚子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结识冯春航,此前只是以粉丝身份为其摇旗呐喊罢了。所以,柳亚子与好友数人捧冯春航,虽未能摆脱传统捧角文化的影响,在心态上起初未始没有一点狎邪之意。但与冯春航接近之后,柳亚子反而摆正了心态,冯春航也得以加入南社。吸纳冯春航入社,是对冯春航人格的最大肯定,也是一份宣言,宣告冯春航与南社社员有着同等的“士”的身份。南社另一位社友作《冯春航传》,则点明了这一点:“呜乎,阛阓之间,歌舞之地,讵不乏士哉!若春航者,其殆伶而士者欤?”[14]1366
二、独推《血泪碑》
柳亚子在民国元年(1912)春,主持上海《民声报》文苑栏目,“日日于报上扬春航”,零星文字悉编入“上天下地”小栏目,即诸贞长所谓“上天下地说冯郎”。彼时,柳亚子逗留上海,几乎观遍了冯春航所演的戏剧,对冯春航所演新剧旧剧,柳亚子都有详评,但都不及对待《血泪碑》之兴味盎然,百看不厌且津津乐道。柳亚子自言:“余于斯剧,雅有嗜痂之癖。”[15]140对于《血泪碑》的反复观看和谈论,向南社友人推介该剧并交流观感,并在日报和《南社丛刻》上写诗吟词,扩大冯春航和《血泪碑》的影响,已使柳亚子从单纯的捧角者演变为新剧的直接参与者。从捧冯春航,到推《血泪碑》,看似一致,其中却有微妙的差别,可以说,对于“剧”的重视和品评,逐渐偏离了以“角”为中心的旧式捧角文化,从而赋予了“捧角”以新的内涵。
柳亚子曾作《血泪碑本事》,收《春航集》中,我们也因此可知剧中细节。柳亚子为什么对《血泪碑》情有独钟呢?《血泪碑》8本,敷演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男女青年石如玉和梁如珍同学相爱,互赠信物。但两人命途多舛,屡遭奸人陆文卿陷害,梁母和梁父先后惨死,如珍两次系狱。姐姐如宝与陆文卿私通,如珍遭受百般折磨后被卖到妓院。死前与石如玉相见,嘱其复仇,石如玉斩二仇人,祭奠于如珍墓前,头触墓碑而死。
首先,《血泪碑》被誉为“哀剧中之杰构”[4]120。柳亚子认为冯春航最宜演哀情剧,以悲剧擅长,在这部剧中做到了人戏合一。一般认为冯春航新、旧剧兼善,而亚子说:“顾冯长新剧者,于旧剧略逊。而新剧中,尤以悲剧为最。往观所演《血泪碑》,真使人回肠荡气,不可抑制。”[16]92并作《海上观剧赠冯春航》二首,其一为:“一曲清歌匝地悲,海愁遐想总参差。吴儿纵有心如铁,忍听尊前《血泪碑》。 ”[4]123此时的柳亚子,在南京国民政府任了三天的秘书,抱病而还,又逢南北议和,革命走入低谷,柳亚子自诉“这时候,我是无聊极了”。冯春航之于柳亚子,更像是李延年之于杜甫,有“落花时节又逢君”之慨;所谓“长歌以当哭”,哀情剧《血泪碑》,则与柳亚子此时的心境相同,成为柳亚子心中的一首诗,借以发泄他心中的积郁和愤懑。
以柳亚子至情至性的性情,不但自己嗜观《血泪碑》,也经常拉朋友一起,他拉林百举,拉俞剑华,拉苏曼殊,拉马小进,并乐于看这些朋友观剧时的反应,如见多情之曼殊泪湿罗巾,“掩面不忍观”。俞剑华则在《与柳亚子书》称赞《血泪碑》:“殆如正则《离骚》,长沙惜誓,美人香草,寄托遥深。”[14]将一部新剧比拟诗骚,这是对新剧美学功能最大的认可。由此也可证,处在革命低潮时期,柳亚子与友人们追逐哀情剧的行为,有着政治文化上的映射,与旧文人醉生梦死的捧角行为有本质的差异。
其次,在《血泪碑》中,冯春航的表演符合了柳亚子对旦角表演的理想。“神情、口白,处处高尚、纯洁,乐而不淫。”[4]132在剧中,梁、石的爱情,表现得纯洁浪漫。柳亚子描述了剧中一细节:如珍以指环赠石生为纪念,并奏琴演唱——“按批雅诺(piano音译),唱外国歌。珠喉一啭,清响遏云”。冯春航通西洋音乐,会演奏钢琴,非旧派艺人所能比拟。更难得的是,冯春航的表演不假造作,出落大方,没有当时伶人的“时下气”。“时下气”,是对旧剧习气的批评语,在上海新剧兴盛的氛围中,旦角的杨柳春风之姿,反而被鄙弃。当姚鹓雏评春航“举止草率,乏生动之致”时,柳亚子则谓“不然”:“春航之所以为春航,正在落落大方,无寻常扮旦角者习气。故纯任自然,不加造作,而愈形妩媚。此幽兰静女所由异于浪蕊浮花也。”[4]133在柳亚子的影响下,南社文人多以冯春航自然得体的表演艺术为尚,并与贾璧云等伶人对照,突显其高尚。
再次,《血泪碑》反映旧家庭制度和刑律不合理酿成的悲剧,也有一定的醒世意义。在柳亚子看来,新剧须有高尚之格调,激扬世道。柳亚子说:“以剧本而论,《血泪碑》之价值,实高出于《新茶花》等倍蓰。”[15]92《新茶花》也是一部新剧,本赛金花事改编,其中女性附属男性的意识十分明显,柳亚子这一批评,透露出对男女平等意识的期待。在介绍《合浦还珠记》的附识中,柳亚子说:“覆雨翻云,颇伤人格。抑一夫一妇,世界公理。今日提倡新剧,不宜复杂以《珍珠塔》《双珠凤》之陋习。”[18]又如《梅龙镇》,柳亚子认为“是剧为专制历史之遗影”。引友人止斋评曰:“此等剧本非民国所宜保存。”[4]127南社“冯党”重视新剧的思想内容,不止此例。另一南社成员庞树松,也是冯迷,在其所作《冯春航传》中说:“偶与春航谈,作语颇明隽,以是疑春航非无学者。嗣春航之师夏月珊语余,以春航在学之成绩,余以是重春航。欧风东渐,新剧盛行,春航所编之《血泪碑》,《惠兴女士》诸剧,先后出世,春航隐隐以改良社会教育为己任,人亦以是益重春航。”[14]1365-1366可以说,“以改良社会教育为己任”,提升了冯春航新剧的意义,也是对冯春航的一种激励。
三、捧陆子美
也是缘于《血泪碑》,柳亚子结识了另一位新剧家陆子美。陆子美(1893—1915),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名遵熹,字焕甫,江苏师范高才生,丰姿俊朗,投身新剧活动,曾演《血泪碑》,也为柳亚子激赏,名重一时。姚鹓雏曾著《菊影记传奇》,取材于南社诗人柳亚子与陆子美、冯春航之实事,此戏共6出,载于1914年10月至1915年正月刊《小说丛报》第4—7期。虽说是传奇,也是传当代之奇,其中真人真事、时间地点,全以真名出现,并有大量诗词书信的引用,看作是对柳亚子捧陆子美的写真集,亦未尝不可。
《菊影记》叙柳亚子与陆子美遇合因缘,颇生动。第一出“忆梦”,写柳亚子在黎里愁闷无着,得胡寄尘书,知《春航集》已杀青。又与夫人佩宜、子无忌闲谈春航。第二出“闻歌”,写陆子美来黎里演剧,柳亚子在刘东海、黄病蝶的强邀下观陆子美演《血泪碑》之梁如珍,端娴流丽,举止不凡,不禁心中称奇。第三出“琴心”,柳亚子与陆子美已结缟纻之好,陆子美为柳亚子绘《汾湖旧影(隐)图》,柳亚子访子美寓所,恰好听到子美弹琴,亚子发现子美将其所赠诗谱入琴歌。第四出“离筵”写柳亚子劝陆子美折节读书,束身坟典,并在江亭治酒,与东海、病蝶一道,为即将离沪的陆子美饯行,子美感伤离别。第五出“停鸿”,写柳亚子得姚鹓雏信,鹓雏居然有论冯春航、陆子美,使柳亚子有吾道不孤之感。又得子美信,知子美又至沪江,梦子美。第六出“赋甄”阳湖汪兰皋访柳亚子,柳亚子允诺编《子美集》,正是“黄鹤还需崔灏题,华黍由庚一例依”。
比起冯春航,陆子美似乎更像是理想中的“紫稼云郎”,但柳亚子却在和陆子美邂逅交谈中,了解了他的身世,同情于他的遭遇,并与之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林一厂有诗《题〈菊影记传奇〉,用亚子〈梦春航〉韵》,算是澄清了世人的猜疑,对柳、陆交往做了公正的评价。原诗如下:
莫当高唐是梦思,闻歌情绪似桓伊。
湘君信怨长捐佩。山鬼应悲俗好祠。
舞鹤铩翰空白惜,驯龙生性实难知。
有音弦外深深托,哀乐中年仗勉持。[15]
林一厂还指出陆子美有名士气:“紫稼本来名士气,庭兰岂负相公知”[19],可谓知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南社精英的柳亚子,并不真正看重陆子美的演剧,反而希望他离开演艺界,以读书治学为正业。他说:“我看子美,天资既优,性情尤厚,真乃吾辈中人,艺事犹余技耳。”[19]中年柳亚子回忆起这一段往事,仍然说:“他年纪很轻,又曾进过学校,人颇聪明,而性格则甚懦弱。在这种走江湖跑码头的新剧团中打滚,在我看来,是很不适宜的。我于是劝他弃剧就学,他也答应了。为了这件事情,也闹了一些小风波。但他还是舍不得浪漫的生活,索性跑到上海民鸣社登台献技,颇出风头。我也只好将错就错,出版起《子美集》来,这大概已是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的事情吧。”[20]
这里的“将错就错”,很耐人寻味。似乎是中年之后的柳亚子,意识到当年捧角确有过火之处。可以理解为,先是陆子美错了,错在舍不得浪漫的生活,不能悉心读书;再是柳亚子也错了,错在不顾南社社友的感受,大张旗鼓地捧陆子美。也可以理解为,出版《春航集》,引起了不少非议,柳亚子颇有后悔之意,但既然已经为人误解,不妨将错就错,再为陆子美冒一大不韪。
陆子美演《血泪碑》,柳亚子称之曰“纯粹新剧”:“兹为纯粹新剧,无唱工。”[15]138朱双云《新剧史》为新剧家做传,也有《子美本纪》,称陆子美“以哀情剧名于时,骚人墨客,颇加激赏,而以吴江柳亚子为尤甚云”[21]117。比起冯春航,陆子美是一位更纯粹的新剧家,但他依然难逃被歧视和误解的命运。对比海上隐身剧界的新剧家们,可以说,陆子美投身剧界,亦颇有“伶隐”情怀,是朱双云所谓“忧国之士”,“忧国之士,慨于世道陵夷,志切移风易俗,第以手无寸柄,不能偿其宏愿,乃从事于粉墨场中,将以感人性情,生公说法,石可点头,广长谭禅,佛甘摩顶,此盖大有功于世道”[22]23-24。从陆子美身上,柳亚子看到了新剧家不为名利、舍身殉志的精神,他在《陆生传》中说:“风会既移,用夷变夏,谓法语不如巽言,经训不如谣俗,耳提面命不如悠游浸润,则有良家子弟投身菊部,高自标榜,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者。”[23]这样的认识,体现了对新剧家的理解和同情,无疑高出于那些贱视俳优的南社同人。
新剧界虽然一直呼唤中国的莎士比亚,但在大多数文人那里,鄙视伶人的传统心理却很难扭转。柳亚子的行为引起南社某些成员的强烈不满,如蔡哲夫发表《致叶楚伧书》,指柳亚子“乃韩、董之徒耳,为人柔曼便辟,美丽自喜,弄脂傅粉,朋比伶人,烛房寻类,得侣冯、陆,以为荣幸,固其宜也。但竞阿所私,而假《南社丛刻》以表扬之,表扬不已,复援引入社。孰甘与为伍耶?”[24]这种攻击和误解在当时不算鲜见,于今也很难说没有。有人说:“其实他们演出新剧不过是一种追逐潮流之举,所以一旦新剧过时了,他们便又重操旧业。冯、陆又都是南社社友,但是吸收他们入社本身就是一种‘捧’。”[3]166将援引冯、陆入社贬为“捧角”的一种形式,实在是很不公正的。吸纳冯春航和陆子美入南社,为陆子美做传,署“友人柳弃疾”,本身即有一定的超越世俗的意义。
结 语
在观《血泪碑》中,柳亚子记录下苏曼殊的观感:“春航数年前所唱西曲,无如今日之美满。实觉竿头日进。剧界前途,大有望于斯人云。”[4]120可见,对于新剧界的前途,柳亚子等南社文人并非无心。可以说,柳亚子“捧角”,起始未尝不存有一定的旧文人积习,但在与冯、陆的交往中逐渐超越了庸俗的捧角心态,由捧角而转为捧新剧作品,实有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主观意绪。柳亚子揄扬冯、陆的表演艺术,编印出版《子美集》《春航集》,客观上也宣传了新剧,促进了新剧的“甲寅中兴”,柳亚子可以说是新剧热心的推波助澜者。学界对新剧演剧的意义一向有所忽视,对柳亚子热心参与新剧之举,以“捧角”一言以蔽之,是极为偏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