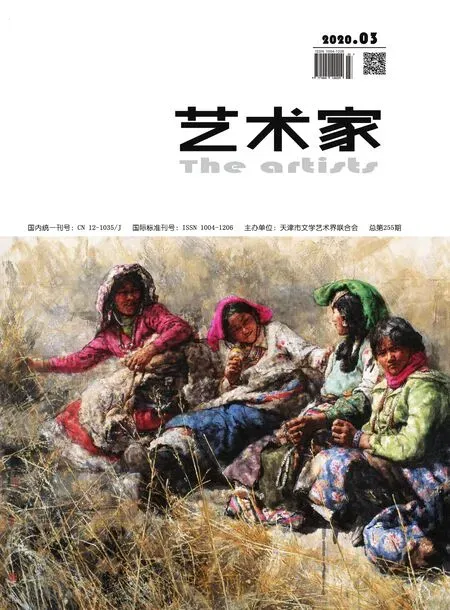寺庙经济体制下元代酒楼剧演场所运营
□丁 一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
酒楼演唱兴起于宋代,至金元戏曲兴起之后,酒楼演唱内容就从说唱扩展到杂剧清唱,也就是选取杂剧套曲加身段表演,用乐器伴奏,省却舞台装扮和角色扮演,既适应局促的场地限制,也可以以曲为单位缩短演出时间,以点戏方式提供服务,给酒馆流水客人更多的选择。酒楼多为“唱”杂剧,因此,在大量诗歌中也将酒楼称为“歌馆”,如《八声甘州燕山雪花》(宋·赵功可)中的“•漾天街晴昼,料酒楼歌馆,都是春回”,又如《代上陈给事二首 其二》(宋·林亦之)的“良辰歌馆声声起,明月妆楼夜夜开”。无名氏的元杂剧《拘刷行院》散套对酒楼杂剧演出有着生动的描写[1]。
一、元代酒楼剧演场所形制
在元代,人们把酒楼秦台、歌楼妓馆、歌棚舞榭这样的地方称为“章台”,把美女云集的游乐场所称为“洛浦”。元代酒楼与音乐表演息息相关,是都市中高且显眼的固定建筑,《喜寿里客厅雪山壁图》(元·萨都剌)中言“秦淮酒楼高十层,钟山对面如银屏”,《分题得车摇摇送方叔高之官》(元·陈旅)中写道“蓟门南头卢水流,燕姬十五居酒楼。弹筝唱歌《折杨柳》,落日车前劝郎酒”[2]。酒楼中歌舞音乐不断,是辅助宴乐消费的重要方式,这个现象遍布大江南北尤其是重要的都会城市,例如,《青楼集》记载“廉野云朝卢书斋、赵松雪饮于京城外之万柳堂。刘(歌妓,艺名为解语花)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亦出现在边疆之地,是普通官员文人娱乐消费的常见方式,如《长洲行送黄茂宰之官长洲》(元末明初·张羽):“阊门大道多酒楼,美人如雪楼上头。争唱吴歌送吴酒,玉盘纤手进冰羞,劝人但饮不须愁”,元代许多诸名文人重臣都毫不掩饰对酒楼娱乐消遣的流连与喜爱,如王恽《清明日锦堤行乐》中写道:“花翻舞袖惊歌板,柳隔高城暗酒楼。”又其《清霜怨(赠吴省参君璋)》描写酒楼与朋友宴乐解忧:“西风巷陌尘障面,酒楼寂寂空箫笳。”
元代不仅配有“秦台”以供演唱之需,还提供住房延长宾客消费时间,酒宴场所、表演的戏台和宾客住房是酒楼形制的三大组成部分,有许多元代诗歌可以彼此印证:有元刘敏中的《鹊桥仙·书合曲诗卷》:“无情枯竹,多情软语[3]。谁按梨园新谱。邻舟余韵遏云声,只认作、珠绳一缕。秦台风物,当时几许。扇影春风解舞。客愁都向坐间空,问谁管、西窗夜雨。”有元末明初郭钰的《寄刘渊茂才》:“多情指画秦台近,一曲鸾笙月下闻。”及其《和袁方茂才秋夜宴集》:“杨柳舞低牙板促,木犀香满羽觞飞。袁郎自是风流客,旧约秦台愿不违。”正如《牡丹亭》二十三处冥判《哪吒令》中提到的,元代的秦台,和之前诗歌中提及的花台、酒台、歌台、舞台、楚台一样,都是酒楼附属的表演场地:“瞧了你润风风粉腮,到花台、酒台?溜些些短钗,过歌台、舞台?笑微微美怀,住秦台、楚台?” 明代天启《慈溪县志》亦提及酒楼剧演的形制安排:“东西廓皆有酒楼……宋元以来皆为戏台,歌鼓之声不断。台之四面皆楼,楼前商泊云屯,往往于楼上宴乐。”
二、元代酒楼剧演消费水平
酒楼往往消费不菲,一掷千金,“已将万事归诗帙,苦乏千金醉酒楼”(元末明初李延兴《舟次龙江》)虽为夸张说法,但也从某种程度上暗示酒楼消费金额之巨。《大都赋》中也写道“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佇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消,褰绣幌而云暖。一笑金千,一食钱万,此则他方巨贾,远土谒宦,乐以消忧。”大都名妓张怡云歌唱一曲《水调歌头》之后,得到二锭赏银作为酬金,这是极为昂贵的价格,还不包括宾客酒饭住宿开销[4]。
略微小结,元代酒楼是杂剧清唱演出的重要表演场所,以酒宴住宿业务为主,歌唱娱乐表演业务为其助兴,消费高昂。元代酒楼特设“秦台”这样的专门表演场地,与勾栏剧场一样目的和用途明确。不同的是,酒楼消费水准远超过市井勾栏,是元代文人社交场所,也是文人与有名望的杂剧艺人近距离交流的场所,曲作家和文人争相赠曲、题诗,出现了同题竞争的“次本”现象,也出现了跨界层合作剧本的情况,是元杂剧剧本重要的酝酿生产场所[5]。
三、寺庙经济制度下酒楼剧演管理
种种迹象表明,元代酒馆的运营及其利润归属可能与元代特有的寺庙经济有关。元上都有过寺院管理酒楼和政府经办酒楼的记载:“寺家合得钱物,官为支付”,即成宗元年(1295年)元朝政府闰四月的圣旨中规定,上都大乾元寺以及其他地区寺院的酒楼、湖泊课税交归有司。元代寺院作为合法的独立经济体存在,进行光明正大的商业运作[6]。从中统四年(1263年)世祖诏寺院“种田入租,贸易输税”开始,寺院只要按章纳税,经商就是合法的。至元元年(1264年)巩固这一政策,要求“儒、释、道、也里可温、达失蛮等户,旧免租税,今并征之”。李•在《元代民族经济史》中将“寺院”部分列在“经营商业的特权阶层”一节中进行讨论,指出皇帝赐寺院以邸舍、解库、酒馆等加以保护,使得寺院经商比一般商人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寺院经济规模之庞大远超现代人的想象,程钜夫描述仅大护国仁王寺一处的产业写道:“凡径隶本院若大都等处者,得水地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三顷五十一亩有奇,陆地三万四千四百一十四顷二十三亩有奇,山林、河泊、湖渡、柴苇、陂塘、鱼竹等场二十九,玉石、银铁、铜铁、硝•、白土、煤炭之地十有五,栗为株万九千六十一,酒馆一。(凡径)隶(本院)河间襄阳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者,得水地万三千六百五十一顷,陆地二万九千八百五顷六十八亩有奇,江淮酒馆百有四十,湖泊、津渡六十有一,税务闸、•各一。内外人户,总三万七千五十九,实赋役者,万七千九百八十八。殿宇为间百七十五,灵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牛具六百二十八,江淮牛之隶官者百三十有三。”
从土地、田亩、鱼塘、树林、煤矿、盐铁这样的原始生产资料与资源,到茶楼、酒馆、占星堂这样的商业运营店铺,再到税务端口、贸易港口,一应俱全,如此,寺院就如有着完整产业链条、多种业务跨地区经营的大型企业,他处沽酒、买卖之利尽归寺院所有,同时也承担着重要的税赋职责,“其僧道种田营运者,依例出纳地税商税,其余杂泛科差并行免放”,同时也承担着吸纳富余闲散劳动力的作用。人们投奔寺院早已超出敬奉朝拜神灵的意义,更多为了在各种经济阶层盘剥之下能在寺院有栖息容身之地,除了因为寺院可以提供足够的居住工作条件外,还因为寺院劳作可免沉重的徭役,否则便不会有大德八年(1304年)的诏书提出整治:“军占民匠诸色户计,近年以来往往为僧为道,影敝门户,苟避差徭,若不整治,久而靠损贫下人民。”
寺院有着成熟而合法的雇佣方式,对僧尼的文化水平有一定的要求,“僧人每三年一次试五次大部经,仰总统所选择申通经义有名师德,于各路置院选试僧人。”若想离开寺院也有条文规定,“遇有僧尼还俗者,仰元礼师长追取公据、加沙,牒,送本处官司,与民一体应当差役,无至两身。”僧尼与寺院的经济关系非常明确,僧尼依靠寺院的资源生存,有责任劳作运营从增加寺院收入,寺院扣押僧尼的身份证明文件,对院中僧尼有管理权,可按商业经营的要求差派僧尼前往不同的岗位劳作[7]。
综合寺院相关史料,以及《青楼集》中大量杂剧艺人以寺院为最终出路的记载,寺院与元杂剧演出运营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复原出来:
受不了教坊盘剥的元杂剧艺人们借着三年一次的机会终于考到了“僧尼”的身份,身份文书由寺院扣押,即人身从属关系由教坊转移到寺院,为寺院服务。元杂剧艺人有时在寺院演出,有时为了商业运营需要前往隶属寺院的酒馆演出,但不管在哪里演出都由寺院按需要差派调遣,目的都是为了增加收入以应付缴纳商税[8]。没有演出任务时,艺伎人则与其他僧尼一样劳作。
出于经济目的,寺院也经营妓院,重价购入女子充当“圣女”,取悦前来朝奉的男人,但这类女子的地位应与靠才艺谋生的元杂剧艺人有所区别,实际情形可能就如多桑蒙古史所言,“当时诸大城市礼拜堂、道院、居民左右,曾见有娼妓居留。其开设此种妓院者,以重价购入女奴以营贱业……合赞曾云,此种妓院不应存在,宗教与道德皆所不许。顾其存在既久,不能一时废止,应渐禁之,先应救出不愿为妓之妇女。由是禁以不愿为妓之妇女售入妓院,其已在妓院者可以自由脱离,用公帑赎之,以配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