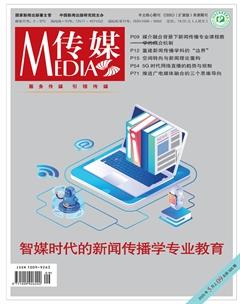进化:短视频大潮中媒体人转型痛点研究
马昌博
摘要:随着中国短视频大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加速转型投入短视频行业。转型的媒体人需要面临从“手艺作坊”思维到工业化内容产品方法论思维的转变,以及对内容行业组织系统之间竞争本质的认知更新;同时,转型的媒体人也面临数字衡量、管理杠杆、制度遵从和信任力驱动几大痛点。针对上述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内容机构和个人的OKR(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法则,即目标与关键成果(行动)法,为机构和人的转型提供系统性推动。
关键词:媒体人 短视频 转型 OKR法则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短视频内容创新和创业成为风口,从2012年到2019年7年间,越来越多传统的媒体人转型投入短视频创新创业大潮,“在传播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在传播形态不断迁徙流变的今天,媒体人创业的结构性机会已然出现”。其中有成功案例,也有更多失败的教训。自2019年始,短视频行业重新洗牌,出现越来越大的头部集团和越来越难的中小机构,这都对短视频创新创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转型要求。
笔者从事内容行业超过15年,有着从传统媒体人转型为新媒体创业者,再聚焦转型到短视频创业者的经历,在短視频行业拥有超过8年的经验。本文以短视频创新创业者的视角,从个人认知和组织管理角度出发,探讨媒体人转型的本质、痛点和可能的改善方式。
一、转型的本质是改变内容生产模式及对组织系统竞争的认知
媒体人转型,首先普遍着力的是改变内容输出语态,简单说是努力让自身的表达有“网感”。但从笔者近8年的转型经验看,表达方式的改变只是转型的浅层次,转型背后是内容生产模式和组织系统的改变。
1.从手工业的“手艺作坊”思维变为工业化的内容产品方法论思维。传统媒体人转型,首先要理解目前短视频行业内容创作的标准性、可复制性和追求规模化生产的特点:内容优劣不单凭个人主观判断,还有一个清晰、可描述、可执行的标准,而且基于该标准可进行质量可靠的规模化生产。
就笔者所在的视知(北京)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知)而言,转型的过程其实是区分创作和创业,即作品和产品的过程。视知认识到,不能过分强调自己所在内容行业“创意”的特殊性而掩盖对内容产品方法论的工业化构建。这就要求媒体人要从手工业的“手艺作坊”思维转变为标准化的内容产品方法论和大规模品控思维,从追求模糊的少数“最高分”,到追求高质量的大规模“平均分”。
2.内容行业竞争的本质是组织系统能力的竞争。在上述要求下,短视频内容的升级为内容产品系统能力的竞争。与此对应的趋势是,自2019年以来,短视频的每个垂直领域都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头部集团,从各大平台的排行榜可见,中国短视频领域的头部机构已经稳定在30到50家左右。这些头部集团收割了更多的流量、用户和商业收入。反之,这些因素又倒逼头部集团不断进行系统性优化,提供数量更多、创新更快、质量更稳定的内容服务来支撑业务发展。
由此,内容行业最终的竞争变成了组织系统之间的竞争,是公司或机构的组织、战略、效率等一系列现代商业机构元素的综合竞争。从这个角度衡量,中国的大部分内容公司都不是合格的,其缺乏作为一个公司应有的产品标准和工业化模式。
视知在建立之初,制作团队最高曾达45人,但每个月生产视频不超过20个。现在视知的制作团队缩减到20个人以内,但是通过工业化的制作系统和外包系统,让每个员工都成为产品经理,最终单月可以实现的产量提高至少5倍。而媒体人的转型,就是从单纯的内容创作者,到工业化的内容创作模式构建者,再到一个公司化(机构化)的系统管理者的进化。
二、媒体人转型的痛点:数字衡量、管理杠杆、制度遵从和信任力驱动
如前文所述,传统媒体人角色单一,更像是一个专业的“手艺人”,但是短视频时代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背后需要公司(机构)的系统支撑。“媒体人身份从单一的新闻报道者,转为兼顾媒体创始人、内容提供者、服务商、生产商、甚至商人的多重角色。”而这些,本身都是转型的痛点。
1.从擅长文字到擅长数字,对商业模式要精确衡量。公司作为一家商业机构,核心目的是“能够持续盈利”,这就需要数字思维。而文字思维(图像思维)和数字思维的不同,在于是否有“数理模型验证”本身,媒体人转型面临的首要改变是要从擅长文字到喜欢数字,并从数字出发建立思考模型。
笔者创业之初,曾经很困惑为何公司的报表上有盈利但经营中却很艰难,经过细致的数字分析,发现当时公司旗下的某几个产品模式会经常面临客户收款未到,但是公司却已有大量支付成本的情况,这就使得公司现金流压力巨大。现实是,大多数企业并非死于亏损,而是死于没有现金流。
转型过程中,商业模式是核心问题,最基本的则是要做清晰的财务穿透,建立成本模型。成本不仅仅是一般印象中的人员工资、稿费等,还包括公司额外的社保成本、房租分摊、人力行政等管理成本分摊、销售成本分摊、固定资产等折旧分摊。成本穿透后,可能很多看起来有毛利率的项目实际是亏损的。
同时,商业模式的天花板也很重要:如果内容机构基本靠制作收入,没有附加的IP溢价,收入增加的同时成本也同比例线性增加,甚至成本增加比例高于收入增加,越扩大生产利润越薄,就是个很难做大的商业模式,一般而言必须要努力结合垂直产业链找到纵深的持续性收入。简言之,媒体人转型要做一个有数字化商业觉醒的人。
2.要承认管理更要科学管理,要追求制度更要喜欢制度。传统媒体行业中,“记者这个工作有个体劳动者的特征,行动起来像独行侠,大多不需要坐班。这跟创业所要求的纪律性、规则性是相冲突的”。
传统媒体产出一篇报道通常只需要单独或少数几个人行动,不需要或只需要少量系统支持,受的制度管束也较少。
然而短视频内容生产是规模化和标准化的,这就需要发挥管理杠杆和制度推动——内容创新创业已经从公众号时代的单打独斗变成大规模系统能力。但限于之前的工作习惯,部分媒体人不擅长科学管理;而对于制度,媒体人往往认可公共利益层面的制度,却不习惯企业制度本身对自己的管理,认为它代表着对创意的“约束”。
但就笔者的创业经验而言,一个内容机构中,合格的管理和制度本质上从来不是为了约束,而是为了形成认知、组织和行动上的共识,并实施它。制度和管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它无法保证创造“最优”,但能创造长期稳定的“次优”。对一个组织系统来说,稳定的“次优”往往就是“最优”。
3.从善于提出质疑到善于“信任力驱动”,擅长“破”更要善于“立”。作为媒体人,其通常习惯的新闻立场是质疑,在质疑中寻找真相,包括可能的公共风险,是“破”;但转型后,作为一个创业者,更需要看到机会,看内容创新的缝隙和机构竞争的可能性,是“立”。
以视知为例,内部有一个评估机制:面对短视频市场的极致竞争,作为一个创新和创业者,如果看到30%的可能(对应着可能有70%的未知失败风险),就需要乐观地相信这件事情能做成,当然前提是面对这30%的机会,视知本身有区别于其他竞争者的独特性,而不是一般优势。
而从组织管理的角度,作为一个转型的内容创业者,不仅要“我相信”,还要确保能驱动一群人相信,要擅长“信任力驱动”。“信任力驱动”一方面要通过数理模型推演,从产品模式和商业模式上确认未来的可能性,说服员工;另一方面,要从价值观和积极性上进行感染。这其中,媒体人不太习惯的“打鸡血”,有时恰恰是转型的创业者和机构本身的催化剂,也是“信任力驱动”的一部分。因为转型者一定要從渺茫中寻找机会,否则创新和创业本身就不会开始。
三、转型的工具性方法:建立内容机构和个人的OKR法则
就笔者转型多年的经验,在以人为核心的内容机构中,个人目标和机构目标的统一,是该机构管理水平的核心。当前,一种目标管理工具——OKR,正受到国内外创新型企业的推崇,如谷歌、华为和今日头条与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等。笔者所在的机构也连续两年进行了实施,发现OKR对内容机构也很适用,适合更多的媒体人作为个人和机构转型中的管理工具。
1.OKR法则适合内容机构和人的转型现实,并产生系统性推动。OKR法则即目标与关键成果/行动法,是一套定义和跟踪重点目标及其完成情况的管理工具和方法。Objectives是目标,Key Results是关键成果/行动。OKR要求机构、部门、员工不但要设置目标,而且要明确完成目标的具体行动,并能够将目标管理自上而下贯穿到个人。
此前传统的绩效工具KPI(Key Performace Indicator),往往建立在对固定数字指标的追求上,但实际上内容机构并不是总能用数字衡量,甚至对很多数字本身的重要性都需要清晰认定——因为数字不简单等于媒体或内容机构追求的影响力。单纯的KPI,对内容机构而言往往制造的是无意义动作和无效数字。这一过程中,内容型人才的自我成就感和能动性也会急剧减少。
OKR不仅仅强调“数字”,也强调一个状态性目标,如“成为头部视频账号,具有业内影响力”。所以相比KPI,其也更适合内容机构。以视知运营部门的OKR为例,衡量账号IP运营结果的不是简单的粉丝和阅读量等数字,而是帮助IP账号更好地实现商业化影响力。以此为衡量,如果运营的IP账号粉丝一个月增长了100万,流量增长了一个亿,但都是泛粉丝、泛流量,对商业化没有意义的话,则判定没完成目标。反之,如果IP账号粉丝只增长了10万,流量增长了100万,但粉丝和流量精准,行业影响大,最终商业化增长强劲,则判定为完成目标。上述OKR的目标方式,一方面让数字有意义,另一方面也能让内容机构和个人从商业结果思考问题。
虽然OKR的目标设置未必是数字,但拆解目标的“关键成果/行动”却一定是可执行可量化的。举例一个IP运营的目标是“成为头部视频账号”,拆解后,这个目标的关键成果或行动之一是“账号全年有效流量达到10个亿”,然后再继续拆解:什么是有效流量,如何才能找到有效流量。
上述做法保证了目标不会流于形式,而且拆解目标为行动对实现目标的关键过程进行指导、管控和考核,让员工在实现中不走型,进而保证结果。其结果之一是,通过对OKR目标和过程的层层拆解,倒逼媒体人从“大而化之”的管理,变成结构化和数字化管理;从用感觉管理产品和机构,到靠数字和“目标—行动”逻辑来管理产品、机构和个人(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理解的OKR不仅仅是一个目标管理系统,它还作为一种“角色定位系统”,让全体人员清楚自己在目标下的角色、位置以及衡量标准。
2.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管理,鼓励激发更多人的制度。对于转型创新创业的媒体人和机构而言,由于新媒体尤其是短视频行业的不断变化,新边界不断拓展,模式调整是常态。因此,既要保证战略的确定性,又要保证创新的广泛性和执行的适配性。
前者可以通过机构层面的战略方针、目标管理、制度建设来框定,后者则需要部门和员工的自我驱动,提出更多解决办法。由此,内容机构在制定OKR时,需要遵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方式,保证在目标和执行现实中找到合适的均衡地带。其中目标“O”是从上往下拆解的,而实现目标的关键“KR”,由部门和员工自己思考制定。让其在大目标下,拥有充分的解决方式自主权,以增强成就感和舒适感。
以视知为例,OKR分为几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公司战略方针;第二层级年度目标(O);第三层级年度关键结果或行动(KR);第四层级工作计划P(Plan,具体工作打法和任务)。为了平衡公司战略的稳定性和一线部门与员工的能动性,规定公司战略目标年度内不更改;年度目标(O)除非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一般不更改,但每半年检讨一次;年度KR确定后每季度评估一次,经过协商上下一致后可进行季度更改;计划(P)可以根据月度甚至周进行频繁调整适配。事实上,新媒体内容机构创新性要求极高,一线员工对具体问题往往更有解决办法。
需要说明的是,OKR制定不仅针对部门,最终也落实到每一个员工身上,从CEO到最基层。所以,OKR也是个人“进化”的管理工具。更重要的是,每年、每季度、每个月、每周都会有ORK的进度会,都是对个人和机构的提醒与推动,让整个系统一起转型进化。
OKR最后的考核则按照结果和过程两种不同模式,笔者所在的视知,以目标实现的结果衡量部门,以目标实现的关键行动过程衡量个人。因为对部门而言,没有结果(O),过程没有意义;对个人而言,执行者首先要确保关键结果或行动(KR)过程的到位,最终才能形成系统结果。
需要明确的是,虽然笔者一直强调管理和制度,但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成机构的目标,只有人可以做到这点,而不是管理和制度本身,尤其内容机构是由人生产的产品去影响人。所以对内容机构而言,最大的管理就是发挥人的能动性的管理,最好的制度就是鼓励激发更多人的制度,这也是OKR法则的本意。
作者系视知传媒创始人、中国应急管理学会舆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参考文献
[1]叶铁桥.转型与创业:从翻过山丘到跨越山河大海[J].新闻战线,2019(01).
[2]曾娅洁.从“单位人”到“创业者”:离职媒体人的数字化转型与现实隐忧[J].编辑之友,20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