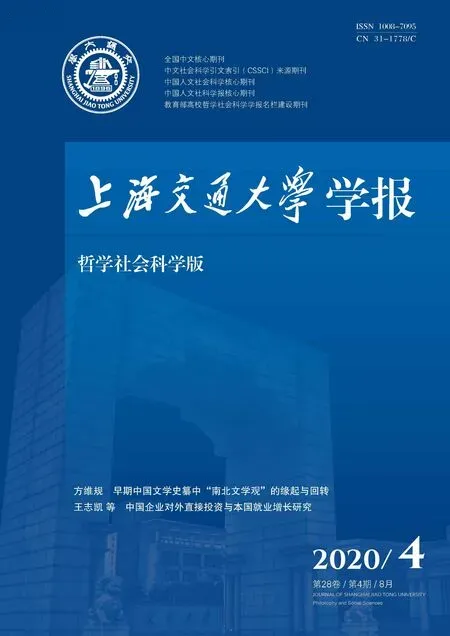论英美意象派诗歌对视觉艺术的汲取与整合
梁 晶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310018)
作为“现代诗歌起点”的英美意象派,(1)语出T·S·艾略特。参见: [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4.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不遑多论。意象派诗歌的一大共性是对“视觉”的倚重。诗人弗莱彻曾说:“意象派诗人应从最具想象的层面上对待其诗歌题材,并且从视觉上呈现它。”(2)Edward G. Fletcher. Imagism—Some Notes and Documents [J]. Studies in English, 1947(26): 201.依据意象派思想主要奠基者休姆的说法,“意象”所指就是“精确的视觉形象”。(3)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7.这里休姆之所以强调“视觉”,一方面固然由于“意象”一词源自拉丁语“imago”,意指为图像;另一方面,英美意象派诗人们一向推崇艺术,其形成发展与同时期艺术尤其视觉艺术的变革密不可分。
美国著名艺术史理论家潘诺夫斯基在《视觉艺术的含义》一书开篇,曾将雕塑、绘画、建筑统归为自古典时代至文艺复兴时期“视觉艺术的三种姊妹形式”。(4)[美]E·潘诺夫斯基.视觉艺术的含义[M].傅志强,译.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9.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二十世纪视觉艺术》中,爱德华·路希·史密斯又进一步将摄影等涵盖在20世纪视觉艺术的门下。(5)[英]爱德华·路希·史密斯.二十世纪视觉艺术[M].彭萍,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而对英美意象派诗人而言,20世纪初叶的绘画、雕塑、摄影、电影显然是极其重要的灵感之源。可以说,每位意象派诗人都与同期视觉艺术有着难分难解的渊缘。因此,从同期绘画、雕塑、摄影、电影等视觉艺术入手,全面理解与把握英美意象派诗歌的视觉特质无疑是必要且必行之举。
一、 诗/画/乐的交融“呈现”
20世纪初叶,“大范围的叛逆意识”弥漫在整个欧洲艺术界:“画家、作家、音乐家、雕塑家们感到自己正处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上,哲学思想与社会生活同样处在决定性转向上。转变正在逼近。这种情绪激发了大范围的叛逆意识,人们随时准备迎接大事件的到来……艺术界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采取行动。”(6)Daniel Aaron. America in Crisis: Fourteen Crucial Episodes in American History [M]. New York: Knopf, 1952: 205-6.柏格森直觉主义的传播、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欧洲各色艺术思潮的涌现,以及摄影、电影这些全新视觉艺术的诞生令人目不暇接。这其中,以塞尚、莫奈、杜尚、毕加索等为代表的欧洲现代派绘画的离经叛道同样影响深远。
众所周知,自文艺复兴时期始,西方传统的作画方式强调画面的再现与镜像式精确描摹。而现代派绘画则一反此传统,重在呈现物体的色彩、结构、体积。如果说塞尚的静物作品开风气之先,尚且属于温和的有悖传统的现代绘画,那么,1913年纽约“军械营展览”以及1917年杜尚以《泉》命名的男用小便池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视觉艺术的三观。
处在这样的“叛逆”与变革大潮中,以庞德、休姆为代表的英美意象派诗歌应运而生。这些诗人们或由于自身热爱与家族熏染,直接从事或参与绘画等艺术创作;或以旁观者的视角,一边撰写着现代派绘画的艺术评论,一边将其创造性呈现或重构在自身的诗歌创作中。譬如诗人威廉斯就曾宣称:“我尝试将诗与画融为一体……我在写诗中,有时并不想说什么。我只想呈现。”(7)Linda Welshimer Wagner.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Speaking Straight ahead”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6: 53.其代表诗作《红色手推车》就是将三个普通的视觉意象(wheelbarrow, rainwater, chickens)加以巧妙并置,通过对每个意象色彩、体积以及意象间结构的精心“设计”,一帧栩栩如生且极富视觉美感的现代派绘画跃然“呈现”于纸面。
事实上,倘细察英美意象派相关宣言,不难发现“呈现”(presentation)一词被屡次提及。早在1913年弗林特发表的《意象主义》一文中,就将“呈现”明确纳入意象主义的三大创作规则:“1.直接处理‘事物’,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2.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8)[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03.而在1915年4月出版的《意象派诗人们》的“序”中,“呈现”一词更直指绘画:“呈现一个意象(因此我们的名字叫‘意象主义’)。我们不是一个画家的流派,但我们相信诗歌应该精确地处理个别,而不是含混地处理一般,不管后者是多么辉煌和响亮。”(9)[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12.不难看出,意象派所谓的“呈现”与彼时“画家的流派”心气相通,即重在以所谓“精确”的方式“呈现”现实之物,而非“一般”的“含混”概念。这不免让人联想到威廉斯在其《自传》中的表述:“(文学作品)据此开始触及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脱离开纯粹想法之上的文学表达使诗歌与绘画创作得以更紧密的结合。”(10)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67: 236.
那么,意象派所信奉的“脱离开纯粹想法之上”的“呈现”是否仅仅是物的单纯客观呈现,而不掺杂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呢?对此,《意象派诗人们》(1916)的“序”给了我们比较明确的解答:
“意象派”并不仅仅意味着画面的呈现。“意象主义”指的是呈现的方法,而不是指呈现的主题。它意思是说要清晰地呈现作者想表现的一切。他也许会想表现一种犹豫不决的情绪,在这种情形下,诗也应该是犹豫难决的。他也许想要在读者眼前唤起那在一片风景上不断地变换着的光,或一个人在激烈的情绪中变化着的思想的不同姿态,那么他们的诗也必须不断转换变化着,来清楚地呈现这一点。(11)[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14.
可见,强调“呈现”并非意味着创作主体自身情感的消泯,创作者的“情绪”依然主导着作品的“呈现”。只不过,这种情感的表征是主体借助对客观物的精心“设计”而“呈现”。这在意象派诗人们的宣言中同样可窥见一斑。譬如庞德对“意象”的经典定义:“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12)黄晋凯,张秉真,杨恒达主编.象征主义·意象派[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35.威廉斯的客体主义诗学信条——“思在物中”,以及D·H·劳伦斯“第四向度”对主体想象的推重。事实上,这与现代派绘画大师们对时下绘画的界定同样不谋而合:“我们对于绘画有着更崇高的概念。它是画家体现内在感觉的工具。”(13)[法]亨利·马蒂斯.画家笔记[M].钱琮平,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3.
诗人与现代派画家们的诉求既然如此契合,那么,对于意象派诗人而言,又该如何在诗歌创作中更好地“呈现”主体的“理性和感情”,抑或画家们所谓的“内在感觉”?除了挣脱传统诗歌固有形式、韵律的束缚,意象派诗人们的一个重要“设计”就是将诗的视觉意象构筑在主体内在听觉之上,形成视觉与内在听觉的联动机制,并辅之以时空、动静的多方位作用,从而更好地“呈现”诗“思”。
意象主义在成立之初,就已意识到诗歌音乐性的重要。弗林特在1913年提出意象主义的三大创作规则,第三条指涉的就是诗的音乐性:“用音乐性短句的反复演奏,而不是用节拍器反复演奏来进行创作。”(14)[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04.但彼时意象派诗人们急于挣脱的是抑扬格五音步这类传统“节拍器”,至于如何表现自身诗歌的音乐性,意象派诗人们并未言明,这也成为意象派诗歌常为人所诟病之处。庞德在1915年2月曾给出进一步说明:“一个人摒弃韵律,……是因为有一些特定的情感或能量不能被过于熟悉的策略或模式所表达。”(15)Ezra Pound.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Ezra Pound 1907-1941[M]. D.D.Paige (ed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1: 345.落实到现代派绘画,体现主体“情感或能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绘画的“内在音乐”,正如歌德所预示的,“绘画要将与音乐的内在关系当作自身的基础”。(16)[俄]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M].余敏玲,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73.
绘画与音乐的相通由来已久,尤其是绘画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绘画的抽象与模糊使其愈发具有音乐的特性。譬如当欣赏立体主义绘画时,其碎片化的拼贴杂糅,使得视觉产生运动的效果,观者的内心同时听闻绘画引发的乐感,从而达成与画家情感的同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画作精髓。与之近似,意象主义诗歌着力唤醒的,也正是读者的内在听觉,即心耳听音。兹以威廉斯短诗《南塔基特》(“Nantucket”)为例:
窗外的花朵
淡紫明黄
在白色的窗帘后变幻—
爽洁的气息—
午后的日光—
玻璃盘上
一个玻璃瓶,酒杯
倒置,旁边
一把钥匙——还有那
洁白干净的床(17)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909-1939 Vol.1[M]. Walton Litz & Christopher MacGowan (ed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 372.
单从视觉上看,全诗犹如塞尚的静物画。“白色的窗帘”将整首诗分隔为窗外与室内两个空间,其中,掩映于窗外的是“淡紫明黄”的秾艳“变幻”,室内则是多个物体的静态呈现,有玻璃制品的盘子、瓶、酒杯,还有钥匙和床。在午后日光的辉映下,玻璃制品反射出的透明澄澈与“白色的窗帘”“洁白的床”相交融,凸显了室内的爽洁柔和。从窗外的色彩浓烈转向室内的淡雅平和,随着视线的挪移,读者的内心也不由荡起内在音响,仿若乐曲从跌宕渐趋平和。显然,这样的阅读经历与传统的英诗格律抑或朱光潜先生的诗乐同源,亦即诗歌通过“文字意义”如重叠、和声、衬字等展现诗的节奏全然迥异。(18)朱光潜.诗论[M].北京: 中华书局,2013: 126.
再比如诗人兼画家的D·H·劳伦斯在1928年创作的《亲吻》(“A Kiss”)一诗:“一朵红花落向它红色的倒影,/倒影向上浮动,充满深情,/两者融合成甜蜜的整体,/——再也听不见一丝声音。”(19)[英]D·H·劳伦斯.灵船——劳伦斯诗选[M].吴笛,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47.这里,极具画面感的“红花”与“红色的倒影”相互映衬,在静与动的交织作用下,最终定格成一图像“整体”,由是,瞬时意象被巧妙地并置于空间之上。而全诗读来,宛若一首深情低吟的小夜曲,在破折号的延展中,缓缓地滑至寂音——“再也听不见一丝声音”,从而于无声处见有声,诗人的创作意图即恋人间亲吻的“甜蜜”亦浮出水面。至此,一个富于层次变换的诗的立体画面完满地“呈现”出来。
劳伦斯在总结自己绘画经验时曾慨言:“一幅画是活的,是因为它与你投入的生命同在。如果你没有把生命注入——没有激动,没有视觉发现的欢欣或狂喜凝聚其中,那么这幅画就是死的。”(20)[英]D·H·劳伦斯.劳伦斯文集(第10卷)[M].毕冰宾,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49.意象派诗歌的创作亦如是。其精确而直接的客观“呈现”背后,委实蕴含着创作主体浓浓的情思,只不过,这种情思隐匿于诗、画、乐相交融的独特视觉“呈现”中,亟待欣赏者调动自身的感官去体悟、发掘。
二、 诗/雕塑的视觉形象立体化
在《文学理论》一书中,韦勒克曾如是论及诗歌与雕塑的关系:“诗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传达类似希腊雕像的效果: 由白色的大理石或石膏引出的那种清冷、那种安宁、静谧以及鲜明的轮廓和清晰感。”(21)[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141.韦勒克之语俨然是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的旁白。正如多年以后,当回顾意象派诗歌创作时,庞德说:“在这种诗歌中,绘画和雕刻似乎‘正在变为言语’。”(22)[美]J·兰德.庞德[M].潘炳信,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4.
英美意象派诗人对雕塑大都怀有由衷的热爱。早在1912年,年仅20岁的意象派诗人理查德·阿尔丁顿就在《诗刊》上发表诗歌《致一尊希腊的大理石雕像》(“To a Greek Marble”),诗人徜徉于博物馆内,为一尊希腊大理石雕像所深深吸引,并在内心与之进行情感交流。同时期现代主义雕塑家高狄埃-布热泽斯卡、雅各布·爱泼斯坦更是意象派诗人庞德、威廉斯的至交。休姆对意象派诗歌的评注也是直指雕塑这门视觉艺术:“这种新诗不像音乐,更像雕塑,它竖立起一个石膏似的意象,并把它交给读者。”(23)[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8.
与铺陈于画布上更加注重色彩的绘画不同,雕塑是一门立体造型艺术,“是形式或设计在三个平面上的构成”,(24)Ezra Pound. Gaudier-Brzeska: A Memoir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92.也是艺术家用具有一定硬度的物质材料制作出具有实体形象的艺术过程。故而,立体空间与对材质的触觉感知构成雕塑的两大主要特征。这两大特征运用到诗歌实践中,使得意象派诗歌的视觉“呈现”变得更为立体化和可视化。譬如威廉斯诗歌《刺槐花开》(“The Locust Tree in Flower”)。单从视觉上看,诗中的每一单词成一诗行,竖直排列,诗体本身就颇似一簇盛开着白色刺槐的花枝:
在 Among
那 of
亮绿色 green
僵的 stiff
裂开的 old
老 bright
枝 broken
间 branch
洁白 come
芳香的 white
五月 sweet
再次 May
来临 Again(25)William Carlos Williams. The Collected Poems of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909-1939 Vol.1[M]. Walton Litz & Christopher MacGowan (eds.).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91: 379.
事实上,“硬朗”(hardness)一词在意象主义宣言中出现的频率同样不低,素被视为评判意象派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尺。在《意象派诗人们》(1915)的“序”中,意象主义的六条原则之一就是“写出硬朗、清晰的诗,决不要模糊的或无边无际的诗”;(27)[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13.庞德在评价阿尔丁顿的诗歌时,也曾指出其诗歌“真正的中心”是做到了“硬朗”;(28)[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21.同样,在和F·S·弗林特围绕后者的代表作《天鹅》发生论争之际,庞德强烈反对弗林特对意象主义创作法的强调,认为这阻碍了诗歌通向一种“希腊式的硬朗”。(29)[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13.联系到上文庞德和休姆等人对雕塑与意象派诗歌的表述,“硬朗”一词显然与雕塑材质带给人的通感意识即触感的可视化密切相关。
作为感知觉的两大组成部分,人的触感或触觉与视觉既相异又相通。通常来讲,视觉是一种“观看”行为:“观看是为实践活动指引方向的基本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观看,就是通过一个人的眼睛来确定某一件事物在某一特定位置上的一种最初级的认识活动。”(30)[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滕守尧,朱疆源,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7.可见,视觉需要与其对应的器官——眼睛来发生关联,没有这一对应的器官,也就没有视觉。但是,触觉意识的发生则没有与其对应的器官(说皮肤是器官显然存有争议),人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或者任何一个器官,都可能发生触觉感知,而“雕塑主要是通过一种视觉引起一种触觉感受,而带有强烈的物质上的接触感……正因为材质性质通过视觉心理化和精神化,我们才能超越触觉的直接反应,而把雕塑的物理性转化为审美属性”。(31)王林.美术形态学[M].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1: 66.这也正是雕塑区别于绘画的重要艺术特性,即触觉的可视性。
意象派诗人们对绘画、雕塑等视觉艺术大都有着极强的鉴赏力,他们深知:“概念是人为的,知觉方是本质的。”(32)[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7.这里的知觉不仅涵纳视觉,更有视觉与触觉双重层面上的交互感知。以意象派诗歌的典范之作——庞德的《地铁车站》(“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为例:“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33)[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00.在《高狄埃-布热泽斯卡》这部回忆录中,庞德曾述及该诗的创作缘起:“在当时的情境下,色彩是主要颜料,我是说色彩是最先进入意识当中,并与意识构成充分的匹配。”(34)Ezra Pound. Gaudier-Brzeska: A Memoir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101.但倘若细察,会发现全诗不仅由“色彩”构成,传导出诗人主体“意识”的,还有触觉上的可视化感知,即叠加于色彩之上的“脸庞”“树枝”“花瓣”以及“湿”且硬的“树枝”,并藉由“脸庞”打造出三维空间凸隐的艺术效果,从而在立体化和可视化上,极大地开启和丰富了全诗的想象空间。
意象派诗歌与雕塑的不解之缘还延续在后期庞德的漩涡主义诗学中。漩涡主义是1915年由庞德与雕塑家高狄埃-布热泽斯卡、画家温德汉姆·路易斯共同发起的,是庞德对早期意象主义的修正和延伸。在回忆录《高狄埃-布热泽斯卡》中,庞德多次将漩涡主义等同于意象主义。经由漩涡主义,庞德的意象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他认为,意象不仅是静态的,还是由头脑中“漩涡似的画面”形成的“一个充满能量的漩涡(vortex)或观念束”,(35)Ezra Pound. Gaudier-Brzeska: A Memoir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106.并通过形式的组合,在艺术家强烈情感的驱使下,最终达到使意象流动不居而“充满能量”的动态“呈现”,从而延长意象诗的长度,强化意象的空间视觉效果。
尽管漩涡主义诗学演变至后来,庞德对“漩涡”的表述愈加玄奥和令人费解,譬如在漩涡主义思想汇聚的主阵地《飓风》(Blast)杂志上,庞德曾指出:“漩涡是一种形式,一种形式演变的系统或者说是一个能量系统,它围绕某个中心旋转,不管什么东西只要靠近它,都将被卷入其中。漩涡是词群,是词的网络,通过辐射中心聚于一处。”(36)马金苗.埃兹拉·庞德漩涡主义思想的特点——以Ezra Pound英译《月下独酌》为例[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36(5): 119.这一方面固然贴合了漩涡主义绘画和雕塑秉持的漩涡式创作理念,但另一方面,也似乎与意象主义诗歌素来倡导的“明晰”和“精确”的原则大相径庭。即便如此,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庞德自始至终坚信,雕塑与绘画是意象派诗歌创作的两大重要灵感来源,意象派诗歌应注重汲取雕塑对“形式美”(beauty of form)的强调与“多重平面的关联”(planes in relation),只有基于此的“安排或‘和谐’”才是意象派诗歌的“根基”与活力所在。(37)Ezra Pound. Gaudier-Brzeska: A Memoir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0: 147.
三、 诗/电影/摄影的多元“呈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照相或摄影步入了全新的时代。自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生产出柔软、可卷绕的新型感光材料——胶卷,并研制出第一台可携式方箱照相机以来,1906年闪光灯在摄影上开始被首次运用,摄影遂成为现代视觉艺术的新风尚。而世纪之交的另一大盛事则是电影的普及,对此,1907年11月的《星期六晚报》(TheSaturdayEveningPost)曾有详述:“三年前,美国还没有五分钱影院,现在已经有四到五千家,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这是电影工业的繁荣时期。”(38)George C. Pratt. Spellbound in Darkness: A History of the Silent Film [M]. Rochester: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1966: 46.巧合的是,摄影、电影的勃兴恰与英美意象派诗歌的萌蘖相重合。
事实上,巧合的不仅仅是时间点,还有诗人与艺术家们彼此的互动与惺惺相惜。譬如意象派诗人威廉斯与20世纪前半叶蜚声美国的摄影大师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雷兹(Alfred Stieglitz)的密切交往。(39)有关威廉斯与斯蒂格雷兹的交往,详见: 梁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一位寻求并体验“美国性情”的作家[D].黑龙江大学,2003.在诗歌创作中,威廉斯也广泛借鉴了摄影中的“直接”“聚焦”等技法,将现实经验世界的瞬时图像忠实还原于笔端,即便这图像不过是散布于医院后墙不起眼的炉渣,抑或伫立路旁并小心翼翼拔去鞋中钉子的农妇。这也正是其“思在物中”诗学的精髓:“在‘物’的自行言说中,思想亦随之自明显现。”(40)梁晶.现象学视阈下威廉斯诗歌美学研究[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126.
如果说摄影更多是从静观的层面给诗人以灵感,那么,由一系列动态画面构成的电影与意象派诗歌更有着难解难分的夙缘。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摄影是“电影的基石”。(41)Stanley Cavell. The World Viewed: Reflections on the Ontology of Film [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1: 26.电影的构成就是将一帧帧静态的画面或镜头并置、叠加、回放、特写、编辑,进而动态呈现为一部影片。譬如庞德的名诗《一个姑娘》(“A Girl”):“树进入我的手,/汁液升入我的臂,/树长入我的胸——/向下长,/树梢从我身内长出,像手臂一样。”(42)[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06.整首诗动感意味十足,树的蓬勃滋长中孕育着个体“我”的生生不息。不仅如此,倘若读者对古希腊罗马神话略有所知,心中定会浮现另一幅画面,即达芙妮为躲避太阳神阿波罗的追逐而幻化为树的场景。这里,“树”/“我”交叠,古今时空的叠映交会,都令该诗油然生发出电影的画面感和无限美感。
对意象派诗歌与电影的关联,裘小龙先生在其翻译的《意象派诗选》一书中尽管并未论及,但作为该书的译者,他显然对此有所感悟,正如他在“译者附记”中所言:“意象派诗人是让一个个意象自行排列着,诗人仿佛是拍一部纪录片,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整部片子看完,总的印象也出现了。”(43)[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248.在笔者看来,“纪录片”一词并不足以体现意象派诗歌的动态画面特色,除却纪录片的写实,意象派诗歌更长于运用电影的表现手法如蒙太奇、交叉剪辑等。兹以D·H·劳伦斯诗歌《沉思中的痛苦》(“Brooding Grief”)为例:
中国足球就悲剧在,它似乎只有有限游戏。所以,许多人一再说中国足球没有文化。文化的核心不是学习什么与不学什么,也不在于学习了多少课时,更不在于有没有学习记录,而在于有没有发现与进入无限游戏。正因为如此,中国足球才习惯于争夺现有资源;才眼里只有出线与夺冠,才“窝里斗”得欢,一出门就丢人现眼。
来自黑暗中的一片黄叶,
在我前面跳跃——就像一只青蛙——
为什么我要吃惊,猝然站停?
我曾凝视着那个生育了我的妇人
在病房杂色斑驳的黑暗中
直挺挺地躺着,因为死的意志
全身僵硬——
那片急速逝去的黄叶曾把我
带回到我前面肮脏的积雨坑似的
混杂的落叶、路灯和车辆中。(44)[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166.
这里,“黑暗中的一片黄叶”引发诗人“跳跃”的联想,随后镜头快速切换到过往的另一时空——“病房”,诗人的母亲“直挺挺地躺着”“全身僵硬”。眼前的黄叶幻化为曾经母亲躺在病房中僵硬的身形。在色彩、光影的斑驳流转中,现时与过往、现实场景与诗人此刻内心活动都悉数内化在“黑暗中的一片黄叶”之上。这不正是电影蒙太奇的叙述与呈现?
论及电影对意象派诗人的影响,最突出的范例莫过于美国女诗人H.D.。H.D.酷爱电影,她不仅是风靡一时的电影杂志《特写》(CloseUp)的创办人之一,还亲自撰稿,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影评。并且,饶有趣味的是,因其相貌出众,她还多次被导演选中,担纲女主角出演过多部电影。电影对H.D.的影响至深,某种程度上,她的诗更像是流淌跃动的电影画面。譬如那首被庞德推崇不已,誉为意象派诗歌的典范之作《奥丽特》(“Oread”):
翻腾吧,大海——
翻腾起你尖尖的松针,
把你巨大的松针
倾泻在我们的岩石上,
把你的绿扔在我们身上,
用你池水似的杉覆盖我们。(45)[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99.
大海的惊涛骇浪恰似“巨大的松针”在“翻腾”,这浪涛不单倾泻在岩石上,也倾泻在驻足海边的“我们身上”。这里,由白色的巨浪、绿色的松针构成的极富动感的画面仿若电影镜头的快速切换,最终合二为一,以特写的镜头对焦主体“用你池水似的杉覆盖我们”。置身诗中,不仅感受到浪涛如杉般的繁茂绿意,以及海浪奔涌不息的流动画面,更唯美的,仿若电影中蒙太奇画面的合成,在水/杉叠映的合流下,伫立岸边的“我们”此刻化身为电影中守护山林的女神奥丽特,守护着这海、这浪、这“池水似的杉”。
H.D.的很多首意象短诗都袭用电影的表现手法。对此,学者莱依蒂曾用“意象/电影眼”一词形象地道出H.D.的意象诗与电影的相通:“H.D.在诗中频频使用意象/电影眼(imagist/cinematic ‘eye’),她的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的创作手法——特写、蒙太奇、镜头的快速切换。”(46)Cassandra Laity. T.S. Eliot and A.C. Swinburne. Decadent Bodies, Modern Visualities, and Changing Modes of Perception [J]. Modernism/Modernity, 2004,11(3): 426.在莱依蒂看来,不仅H.D.,还有庞德也非常擅长使用“意象/电影眼”,譬如《地铁车站》中,庞德就借用了蒙太奇手法与电影镜头的快速切换。据此,莱依蒂认为,在H.D.和庞德的诗中,充分验证了“现时电影模式的备受关注”。(47)Cassandra Laity. T. S. Eliot and A. C. Swinburne. Decadent Bodies, Modern Visualities, and Changing Modes of Perception [J]. Modernism/Modernity, 2004,11(3): 426.
尽管莱依蒂颇为精当地指出H.D.和庞德诗中蕴含的电影特性,但对电影为何受意象派诗人青睐的成因却语焉不详。在笔者看来,将电影的表现手法沿用到意象派诗歌创作中,和二十世纪初电影体量精短的现实状况不无关联:“1913年以前,电影的标准片长一直为一卷盘,就是说,电影放映不超过15分钟。”(48)[美]让-米歇尔·拉巴泰.1913: 现代主义的摇篮[M].杨成虎等,译.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16.有限的片长意味着电影制作人必须将事件尽可能压缩以呈现其精髓,那些冗长的、不利于传达主旨的情节只能被舍弃。这与同时期意象派诗人们信奉的“绝对不使用任何无益于呈现的词”以及“凝练是诗歌的灵魂”等创作原则恰巧吻合,(49)[英]彼得·琼斯.意象派诗选[M].裘小龙,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 313.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电影这一新兴视觉艺术才受到意象派诗人们的格外关注。
作为二十世纪初新兴的视觉艺术,摄影和电影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与同时期绘画、雕塑一道,共同构筑了意象派诗歌全新而独特的视觉特质。遍览古今,无论诗画一律、诗画异质的歧见,抑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评鉴,诗与画的话题可谓常青不衰。如何把握和解读诗与视觉艺术的关联?叶维廉先生的一席话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发:“现代诗、现代画,甚至现代音乐、舞蹈里有大量的作品。在表现上,往往要求我们,除了从其媒体本身的表现性能去看之外,还要求我们从另一媒体的表现角度去欣赏,才可以明了其艺术活动的全部意义。”(50)[美]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00.横看成岭,侧观成峰。作为一名攀登者,“明了”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全部意义”或许只是山巅处可望而不可即的美景,但从视觉艺术的“表现角度”对意象派诗歌加以重新审视,或许未尝不是“从不同角度向它无限趋近”的一种努力。(51)彭青龙,易文娟.科技人文、思维比较和人类精神——访谈钱旭红院士[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3.毕竟,我们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