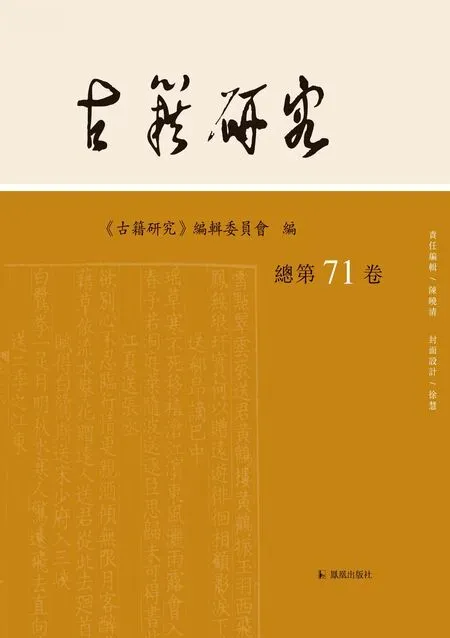劉績《三禮圖》内容考論*
喬 輝 張曉寧
關鍵詞:劉績;三禮圖;考證
劉績,史書無傳。《四庫全書總目》“《三禮圖》四卷”提要下云:“《三禮圖》四卷,明劉績撰。績字用熙,號蘆泉,江夏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鎮江府知府。”(1)(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76頁。劉績爲明朝人,“宏治”當爲“弘治”,爲明孝宗年號,其在位時間爲1488—1505,庚戌進士,即1493年進士,其撰《三禮圖》當在1493年後。
劉績撰《三禮圖》之本旨在於糾舊圖之失,匡舊注之謬。《三禮圖》卷一序《三禮圖説》言:“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天人而流於異端矣。績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勿泥舊説,見舊是者,今不復圖。”(2)(明)劉績:《三禮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5頁。其體例亦由此得知:凡舊圖誤者,則撰新圖;凡舊圖是者,則不復圖。
其《三禮圖》内容,《四庫全書總目》“《三禮圖》四卷”下有云:“是書所圖一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諸書,而取諸《博古圖》者爲尤多,與舊圖大異。”(3)《四庫全書總目》,第176頁。觀其書所依之作,其内容多依《博古圖》《禮書》而作,今結合其文,參照禮之經文、注疏,結合相關禮圖文獻,兹取數例,考察其内容之真僞。
一、 内容考釋(上)
卷二之“總”云:

劉績以“總” 爲幘巾髻籠所以韜髮。《禮記·内則》:“笄、總。”鄭玄注:“總,束髮也,垂後爲飾。”孔穎達疏:“總者,裂練繒爲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5)(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461頁。《説文·糸部》:“總,聚束也。”段注:“聚束也,謂聚而縛之也。悤有散意,糸以束之。禮經之總,束髮也。禹貢之總,禾束也。引申之爲凡兼綜之偁。”(6)(清)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47頁。《釋名·釋首飾》:“總,束髮也,總而束之也。”總爲束物之組,故翟車謂之組總。《詩·鄘風·幹旄》:“束絲組之。”毛傳:“總以束絲而成組也。”可知,“總”乃束髮之物,垂後爲飾。《説文·巾部》:“幘,髮有巾曰幘。”《玉篇·巾部》:“幘,覆髻也。”《廣雅·釋器》:“幘巾,覆結也。”《方言》卷四:“覆結謂之幘巾。”《後漢書》卷十一《劉盆子傳》:“俠卿爲製絳單衣、半頭赤幘。”李賢注:“幘巾,所謂覆髻也。”(7)(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81頁。可見,“幘”乃覆髻之物,與“總”實爲二物。《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0册P.2967之《喪禮服制度》亦有“總”圖(8)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78頁。,其圖“總”之形與劉績“總”圖不符。《居延新簡》亦有“幘”,經學者考證,其功用爲“裹頭的長條形布袋”(9)聶丹,聶淼:《〈居延新簡〉中的“行幘”》,敦煌研究,2016年第1期,第23頁。,不爲“束髮”,劉績所言與《居延新簡》所載不符。要之,劉績以“總”爲“幘巾”, 與禮文、傳世文獻皆不符;其圖“總”亦作“幘巾”狀,甚失之。清黄以周《禮書通故》“名物圖一”之“服”亦言劉績圖“總”之失,另撰“總”圖。黄圖與《敦煌西域文獻》載“總”圖形制亦有異,不知孰是,兹存二圖。
卷三之“圭瓚”云:
按九寸七寸之璋,中皆射四寸,圓爲槃,則圭瓚當倍之,射八寸矣。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鄭玄引叔孫通之作而誤以鼻爲龍頭流。若云瓚勺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八寸,則義自明矣。(10)《三禮圖》,第375頁。
劉績以爲鄭玄所言“圭瓚”之形制有誤。筆者以爲鄭玄所言有理,劉績之言有待商榷。
《周禮·考工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鄭注:“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11)(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周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922頁。《詩·大雅·旱麓》:“瑟彼玉瓚,黄流在中。”毛傳:“玉瓚,圭瓚也。”鄭箋:“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黄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12)(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829—830頁。鄭玄言“瓚”之形制甚明:瓚形如盤,呈圓形,其後有柄,以圭爲之,其前有流,乃出水處。《玉人》又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黄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鄭注:“勺,故書或作約。杜子春云‘當爲勺,謂酒尊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衡謂勺柄龍頭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横,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13)《周禮注疏》,第923頁。鄭玄以爲圭瓚之制,猶如三璋之勺形,且謂鼻爲勺流也。其説與先鄭所云“鼻謂勺龍頭也”有異,當《漢禮》所爲。又由《玉人》言“鼻寸”,若如先鄭所云“鼻爲勺龍頭”,則不知“寸”是言寬狹,亦或言長短,無從所定,若如鄭玄所言鼻爲勺流則知寸爲勺之長。故鄭玄所云有理。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十四《尊彝圖》之“圭瓚”所畫之圖與鄭注所言相合。
《周禮·春官·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注:“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劉績以爲鄭注言“瓚槃大五升”當爲“瓚勺大五升”。聶崇義則以爲“瓚槃大五升”當爲“瓚大五升”。《禮記·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鄭注:“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爲柄,是謂圭瓚。”鄭注《玉人》《明堂位》所言“瓚如槃”“大五升”,筆者以爲十三經注疏本《周禮注疏》言“瓚盤大五升”,當爲“瓚,大五升”, 乃衍一“盤”字。《左傳·昭公十七年》:“鄭裨灶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杜注:“瓚,勺。”(14)(晋)杜預注,(唐)孔穎達疏:《左傳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084頁。劉績以爲“瓚盤”當作“瓚勺”與上下文辭及文獻所載不符,失之;劉績言“下有槃,口徑一尺”,此槃爲盛圭瓚之槃,與“勺”乃爲二物,劉氏混而言之,不當。
據出土實物,玉瓚之形制與鄭注、劉績所言皆有異。1976年陝西扶風雲塘銅器窖藏出土的兩件戰國伯公父“玉瓚”,又輝縣固圍村 5號戰國墓出土的陶瓚和當陽趙家湖 CM3出土的木瓚、商周時期的婦好墓和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兩件銅瓚,器柄均作尖首圭狀,當屬於圭瓚之屬。
上述出土“玉瓚”之形制未見鄭注所言“流爲龍口”,或許漢代“玉瓚”形制確有“流爲龍口”這一新變化,然尚無漢代出土實物佐證,故鄭注所言闕疑。劉績所繪“玉瓚”與出土實物更是大相徑庭,甚失之。
又“燕几”云:
《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校在南,禦者持之。古几猶今道家之几,形如半環,三足,坐則曲者向身,可以憑。以曲者兩端著地,故綴足。禦者一人坐持上足也。《語林》曰:直木横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以蹯鵠膝、曲木抱腰?則直几,後世之制也。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15)《三禮圖》,第388頁。
《儀禮·士喪禮》:“綴足用燕几。”賈公彦疏:“燕,安也。當在燕寢之内,常馮之以安體也。”(16)(漢)鄭玄注,(唐)賈公彦疏:《儀禮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129頁。“燕几”乃靠着休息的小桌子。劉績以爲“燕几”(附圖)乃古几,阮諶等言直几乃今几。

劉績“燕几”圖
關於劉績“燕几”形制之説,後世學者各有説辭。《儀禮·既夕禮三》:“綴足用燕几。”清胡培翬正義:“今案:劉氏績云:‘古几猶今之道家之几,形如半環,三足,坐則曲者向身,可以憑。以曲者兩端著地,故綴足,禦者一人坐持正足也。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劉云三足,與賈又異,今並存俟考。’”(17)(清)胡培翬:《儀禮正義》,江蘇: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21頁。清黄以周《禮書通故》卷第四十五“名物圖二”:“阮諶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黑。’賈公彦云:‘几兩端各有兩足。’聶崇義云:‘司几筵掌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是無兩端赤中央黑矣,蓋取彫漆類而髹之也。’以周案:古人執几,倏縱倏横,必無五尺之長。馬融以爲三尺,近是。據賈疏,几四足。或説几曲其兩端,居足各一,劉績以道家半環几三足當之,不足信。”(18)(清)黄以周:《禮書通故》,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927頁。
劉績言“憑几”,文獻有載。《魏志》卷十二《毛玠傳》:“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19)(晋)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75頁。“憑几”即古之“隱几”。其形制,南朝謝朓《烏皮隱几》詩爲證:“蟠木生附枝,刻削豈無施。取則龍文鼎,三趾獻光儀。勿言素韋潔,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謝朓所言“隱几”之特徵:一則“三足如鼎”,二則“曲躬”即形體呈弧曲狀。劉績引《語林》則進一步説明“憑几”乃“曲木”,非直木;施用時則“曲木抱腰”,即弧曲的弧面向外,人坐時憑几高度如腰處,人可憑隱其上。據出土實物,20世紀60—70年代,南京象山王氏墓群出土有陶憑几,其形制如劉績所述。《文物》(1973年第4期)之《南京大學北園東晋墓》載東晋墓出土器物中有憑几3件,几面弧形條狀,下有三獸足。弧面長74、寬9釐米。背面呈凹槽狀,中部厚2、四邊厚4釐米,几高24釐米。
又《文物》(1986年第3期)之《安徽馬鞍山東吴朱然墓發掘簡報》言出土漆木器中有“憑几”,“木質胎,髹黑紅漆,扁平圓弧形几面,下有三個蹄形足。弦長69.5、寬12.9、高26釐米”。
杜佑《通典》卷八十六《凶禮八》“喪制之四”之“薦車馬明器及飾棺”:“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漆屏風一,三穀三器。”(20)(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325頁。《士喪禮》言“綴足用燕几”,燕几乃明器,即爲《通典》言“憑几”。據文獻及出土實物,劉績言“燕几”形制爲是,黄以周駁斥劉績之説失當。
《文物》(1986第4期)載包山一號墓出土拱形足几長72.4、寬22.4、高33.6釐米,又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一號出土木漆憑几長63、高43、寬34釐米。考古資料表明,先秦時期出土的“几”面分爲直形和曲形,其長度、寬度、高度皆不相同。《文物》(1955年第8期)之《南京附近六朝墓葬出土文物》載南京趙士岡晋太和元年墓出土灰色陶几,長106.4、寛24、高19.3釐米,附圖。

南京趙士岡晋太和元年墓出土灰色陶几
據漢代一尺約爲現代的22釐米,則阮諶言“几長五尺”相當於現代的110釐米,與南京六朝墓出土“灰色陶几”長度相當;馬融言“几長三尺” 相當於現代的66釐米,與包山一號墓出土“几”等長度相當。可知,阮諶、馬融所言皆有理,黄以周言“馬融‘几長三尺’説爲確”有待商榷。劉績存其二説,爲是。
二、 内容考釋(下)
卷四之“鼎”云:
《考古圖》有牛首爲足,鼎容一斛,則《三禮圖》謂牛鼎受一斛,羊鼎受五升,豕鼎受三升,皆爲首飾足,必有所授矣……其正鼎無蓋,止有扃、羃……凡鼎不鈛耳皆然。鉶鼎、膷鼎鈛耳則有蓋,不用扃、羃……按圖云:蓋則陪鼎無扃羃。可知鈛耳則自不能容扃矣。鄭氏以膷鼎有扃,非也,世儒無有知也。(21)《三禮圖》,第404頁。
劉績所言三鼎之容受、形制,援引《三禮圖》之言。四庫全書本聶崇義《三禮圖集注》卷十三《鼎俎圖》所言牛鼎受一斛,羊鼎受五斗,豕鼎受三斗;四部叢刊本《三禮圖集注》所言三鼎之容受爲:牛鼎受一斛,羊鼎受五斗,豕鼎受三斗。劉績所引《三禮圖》内容與聶崇義《三禮圖集注》不符。
牛鼎受一斛,文獻有載,如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七十三《雜器物部》之“鼎”云:“《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22)(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252頁。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二《珍寶部》一一“銀”云:“阮諶《三禮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錯以白銀’。”(23)(宋)李昉:《太平御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年,第3608頁。然“羊鼎”“豕鼎”之容受,除聶崇義《三禮圖集注》有載外,明以前禮圖之作皆不載,又劉氏徵引《三禮圖》與聶圖亦不符,其援引内容失當。
劉氏之言“羊鼎”“豕鼎”之容受與四部叢刊本《三禮圖集注》、四部全書本《三禮圖集注》皆異,有待考釋。據《三禮圖集注》言,天子諸侯以牛鼎,其口徑、底徑及深度俱一尺三寸三;大夫以羊鼎,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一寸;士以豕鼎,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强。牛、羊、豕三鼎有等級之别,且其大小、容受之數亦有等級之别,然就其所言數字,三鼎之容受相差不大。又言抬三鼎之“扃”,長度分别爲三尺、二尺五寸、二尺,亦可説明三鼎形制大小相差不大。《説文·斗部》云:“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又云:“斛,十斗也。”按《説文》,四庫全書本《三禮圖集注》所言爲是,劉績所言失之。
又劉績以爲正鼎無蓋有扃,陪鼎諸如鉶鼎、膷鼎有蓋無扃,鄭玄所言陪鼎有扃爲誤。筆者以爲劉績所言有待商榷。
陪鼎爲盛膷、臐、膮之鼎。陪鼎對牢鼎而言。陪鼎所盛爲加饌,故陪鼎亦稱羞鼎。《儀禮·聘禮》:“飪一牢,鼎九,設於西階。陪鼎當内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設扃鼎。膷、臐、膮,蓋,陪牛、羊、豕。”鄭玄注:“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聘禮》又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鄭玄注:“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聘禮》言牢鼎有扃,不言陪鼎有扃,蓋以牢鼎况之,陪鼎略而不言。
《周禮·考工記·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三個。”鄭注:“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賈疏:“云‘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者’,亦《漢禮器制度》知之。膷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膷鼎,據陪鼎三膷、臐、膮而説也。”鄭注之言扃之大小,是就牢鼎、陪鼎而言,故知鼎大者爲牢鼎,鼎小者爲陪鼎。膷鼎等陪鼎之扃是據漢法而言,其上當有扃可知。劉績以爲陪鼎有蓋,有蓋即不會有扃,以陪鼎鈛耳無法容扃,其説不知其據何,實爲臆測之辭。據《説文·鼎部》,鼎有三足兩耳,其耳即爲穿扃之用,何來“鈛耳則自不能容扃”之説?由鄭注《匠人》言知,扃有大有小,是專爲大鼎、小鼎而設,故鈛耳無法容扃一説不當。
結 語
明代,禮學衰微,三禮圖文獻甚少,劉績《三禮圖》可謂這一時期三禮圖文獻的代表著作。然是書多本陸佃《禮象》、陳祥道《禮書》、林希逸《考工記解》,取《博古圖》尤多,與舊圖大異。今核之相關文獻及出土實物,我們以爲劉氏一書多有因襲,存在一些訛誤,雖有創新之説然多未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