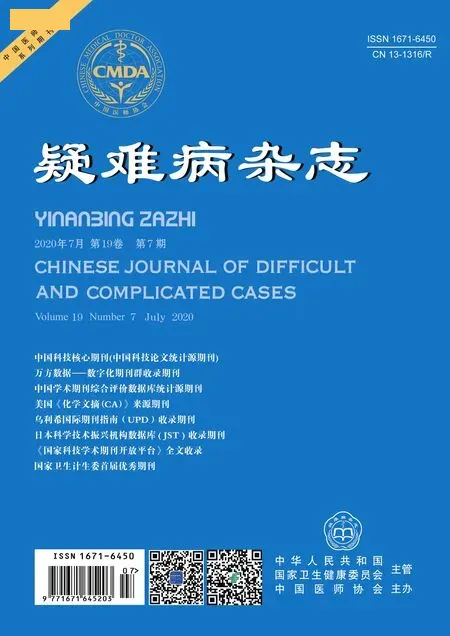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炎性因子风暴与房颤的关系
贾茹,尹德春综述 曲秀芬审校
最近由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世界蔓延。大多数患者病情稳定,预后良好,但部分感染患者快速进展为重症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或多器官功能衰竭(MOF)并最终死亡。炎性因子风暴是导致病情恶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大量炎性因子引起体内严重的炎性反应状态,而炎性反应与心房颤动密切相关。
1 炎性因子风暴概述
炎性因子风暴(又称细胞因子风暴)是一种以全身性炎性反应、高铁蛋白血症、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和MOF为特征的临床症状。目前为止,有Toll样受体(TLRs)、核苷酸寡聚化结构域样受体(NLRs)、视黄酸诱导基因-I样受体(RLRs)、C型凝集素受体(CLRs)等4种模式识别受体参与炎性因子风暴的发生[1]。当病原微生物进入人体时,激活TLRs,而后激活各种信号介质级联反应,最终使核转录因子κB(NF-κB)诱导多种炎性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干扰素调节因子3(IRF3)和激活子蛋白-1(AP-1)等的大量生成[2],引起机体损伤。多种疾病的进展机制中都有炎性因子风暴的参与,涉及多个系统。因此,不能把炎性因子风暴认定为是一种疾病,它是不同初始损伤的共同终点,其本质是机体免疫系统功能失调,炎性因子会对其自身的产生起正反馈调节,级联产生大量的炎性因子最终导致机体损伤[3]。
2 新型冠状病毒中的炎性因子风暴
近期对入院时新冠肺炎感染患者血液的实验室检查发现,大部分患者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及血清铁蛋白增高,淋巴细胞绝对值降低,该结果表明,SARS-CoV-2可能主要作用于淋巴细胞,尤其是T淋巴细胞,病毒颗粒通过呼吸道黏膜传播并感染其他细胞,在体内诱发炎性因子风暴,产生一系列免疫反应,并引起外周白细胞和免疫细胞(如淋巴细胞)的变化[4]。流式细胞术分析发现,外周血CD4+和CD8+细胞的数量大大减少,而其状态却被过度激活,CD4+T细胞中具有高度促炎效应的CCR4+、CCR6+、Th17细胞增加,此外,发现CD8+T细胞有高浓度的细胞毒性颗粒[5]。T细胞的过度活化,促炎因子的大量释放,这些都说明了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体内,出现了炎性因子风暴。并且,与未进入ICU的患者相比,ICU内的危重患者血浆中IL-2、IL-7、IL-10、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SCF)、单核细胞趋化因子(MCP-1)、TNF-α等细胞因子的水平更高[6],也证实了这一点。
3 新型冠状病毒增加房颤易感性
Yao等[7]研究发现,心肌细胞中NLRP3炎性小体在房颤中的作用,通过免疫印迹法评估了阵发性房颤(pAF)和持续性房颤(cAF)患者心房全组织裂解液和心肌细胞中NLRP3炎性小体的活性,并建立了表达组成性激活NLRP3的心肌细胞特异性敲入(CM-KI)小鼠模型,结果显示,pAF和cAF患者的心房肌细胞中NLRP3炎性小体的活性增加,且NLRP3的特异性抑制剂MCC950可以减弱CM-KI小鼠的自发性房性期前收缩和房颤的发生,这项实验证实了炎性反应与房颤息息相关。最近的一项研究,利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测恶性肿瘤患者心房18F-氟脱氧葡萄糖(FDG)的摄取,与对照组相比,恶性肿瘤伴房颤的患者,心房FDG摄取率增高,且恶性肿瘤伴房颤组中4例尸检心脏的病理证实,在FDG摄取区域有血管外巨噬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8]。说明心肌局部炎性反应与房颤的发生关系密切,可能通过局部炎性介质的增多,影响心脏电活动,诱发房颤。
SARS-CoV-2与SARS-CoV的基因组具有较好的序列同源性[9],通过对121例SARS患者的研究发现,心动过速是SARS-CoV最常见的心血管并发症,并且有1例患者出现阵发性房颤[10]。与SARS-CoV相比,人群对SARS-CoV-2普遍易感,患有潜在慢性心血管病者更容易感染SARS-CoV-2,也更容易出现并发症和危急情况,甚至死亡[11]。在感染SARS-CoV-2患者的临床特征描述中,感染者除了有呼吸系统症状外,16.7%的患者出现了心律失常[12],虽然没有提供心律失常的明确分类,但SARS-CoV-2有可能通过以下机制,影响心房的电重构或结构重构,增加房颤易感性。
3.1 炎性因子风暴引起心房电重构 在临床研究中曾发现,炎性介质与心房电学性质有关,可以引起心房电重构。有文献报道,物理刺激后P波平均持续时间增加,CRP、IL-6、TNF水平瞬时升高,但心房容积无差异,提示炎性因子的急性改变与心房电传导及AF易感性有关[13]。COVID-19患者体内T细胞过度活化,重症患者短时间内发生炎性因子风暴,IL-2、IL-6、IL-7、IL-10、TNF-α等炎性因子大量释放,其中多种炎性因子已被证明与房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经IL-6预处理的大鼠心房组织,即使轻微的张力也可以导致房颤的发生[14]。与窦性心律组相比,房颤患者心房组织中TNF- α表达水平升高,T型钙通道亚基mRNA表达水平降低, TNF-α可能凭借通道功能损伤和下调通道蛋白表达的方式,降低心房肌细胞T型Ca2+电流,参与房颤的发生[15]。
3.2 心肌损伤 SARS-CoV主要通过刺突蛋白(S蛋白)与细胞膜上表达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蛋白结合侵犯人体[16],与SARS-CoV相比,SARS-CoV-2的S蛋白与人类ACE2有更强的结合亲和力[11]。研究发现,ACE2在心肌细胞及周细胞等心脏细胞中均有表达,且ACE2在心脏的表达高于作为该病毒主要靶器官的肺,表明心脏可能存在感染易感性[17],是SARS-CoV-2导致心肌损伤的关键。在疫情初期的COVID-19患者临床特征描述中发现,有12%的患者出现了急性心肌损伤也证实了这一点[4]。心房心肌病可由炎性反应引起,重症COVID-19患者体内发生炎性因子风暴,强烈的炎性反应状态很可能导致心房心肌病的发生发展[18]。研究发现,有基础心脏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心肌病)的患者,在感染SARS-CoV-2后,更易发生心肌损伤,使TnT水平升高,患者可有更严重的呼吸功能障碍和更低的氧分压[19],这些基础心脏病本身已经对心脏结构产生影响,而COVID-19患者体内严重的炎性反应状态甚至是炎性因子风暴和低氧血症等,都会加重心房心肌病。近期,在对感染者进行的病理解剖中,发现了心肌间质中有少量单个核细胞的炎性浸润[5],表明COVID-19患者存在心肌局部炎性反应,它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影响心房重构,诱发房颤。COVID-19患者发病时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4],发热可以使患者心率加快。快速房性心动过速可导致钙超载,介导氧化应激、细胞凋亡、膜功能障碍、能量消耗和低度炎性反应的发生[20],这些均是导致心房重构、诱导房颤发生的危险因素。而房颤可能是在剂量—反应关系中被触发的,全身受累及感染越严重,房颤的发生率越高[21]。COVID-19患者免疫系统过度激活,血清中促炎因子水平升高,并级联释放大量的炎性因子,引起全身性炎性反应,或炎性因子聚集于心房,引起心房心肌病,增加房颤易感性。
3.3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改变 ACE2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同工酶,裂解血管紧张素Ⅱ(AngⅡ)产生Ang (1~7),发挥抗炎和抗重构的作用[22]。SARS-CoV-2通过病毒表面的S蛋白与ACE2结合而入侵人体,使ACE2的表达减少,进而导致AngⅡ局部升高。AngⅡ可以通过刺激促炎细胞因子(如IL-6、IL-8和TNF-α)的产生和直接激活免疫细胞来增加炎性反应,而TNF-α、IL-2、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等细胞因子可以调节钙稳态,引起肺静脉异常触发,缩短心房动作电位持续时间[13]。经AngⅡ处理的小鼠,依赖CD11b和CD18整合素,使心房中性粒细胞浸润增加[23],心房的局部炎性反应,也会导致心房重构,最终引起房颤。AngⅡ也是引起纤维化的复杂信号系统之一,尤其是AngⅡ 1型受体,属于主要的促纤维化细胞膜受体,也可以产生活性氧[24],当AngⅡ局部升高时,促进心房纤维化的发生发展,增加了活性氧的产生,而心房纤维化是导致房颤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活性氧也被认为在心房纤维化和电重构中起着潜在的重要作用,是导致房颤的重要介质[13,24]。
4 房颤的治疗
4.1 抗炎药物干预治疗 类固醇类药物是临床上常用的抗炎药物,临床试验表明,围手术期内短期应用类固醇后,在房颤消融术后前3个月内,类固醇组的早期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25]。他汀类药物具有包括抗炎在内的多种作用,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使用他汀类药物预处理,可以显著降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房颤的发生率[26]。秋水仙碱可以缩短炎性反应期,是预防心脏手术术后房颤发生的有效药物[27]。除此之外,噻唑烷二酮、罗格列酮及醛固酮受体拮抗剂等药物,通过其直接或间接的抗炎作用,可以调节炎性反应与氧化应激,减轻心房重构及纤维化,对房颤产生有利影响,减少房颤的发生[20]。
4.2 精准治疗 当前,射频消融手术是治疗房颤的重要策略,然而这一过程会引起一定的组织损伤。在传统手术与抗炎药物预防及治疗房颤的基础上,也可以利用炎性细胞因子的特异性拮抗剂,尝试开展对房颤的精准预防或治疗。例如,在对全身性幼年特发性关节炎(JIA)疾病的研究中,发现了细胞因子IL-1β的失调,并成功将IL-1受体拮抗剂阿那白滞素应用于治疗,并在随后的的临床对照试验中,证实了其有效性[3]。通过精准抑制导致房颤的主要炎性因子来预防或治疗房颤,是一种治疗房颤的新思路。
5 总 结
大量的基础及临床研究表明,房颤与体内的炎性反应状态密切相关。病原体入侵人体,激活机体的免疫系统,释放促炎因子,当机体免疫系统失去负反馈调节时,导致炎性细胞因子大量释放,最终引起炎性因子风暴。体内大量的炎性因子引起全身或心房局部炎性反应,使心房电重构或者结构重构,最终导致房颤。COVID-19患者体内炎性因子水平高,重症患者体内发生炎性因子风暴,且病理解剖结果证实了患者心肌间质中有少量炎细胞的浸润,SARS-CoV-2病毒与ACE2结合,使AngⅡ水平升高,这些均促进了心房电重构或结构重构,因此应该对COVID-19患者进行密切的随访,警惕远期房颤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