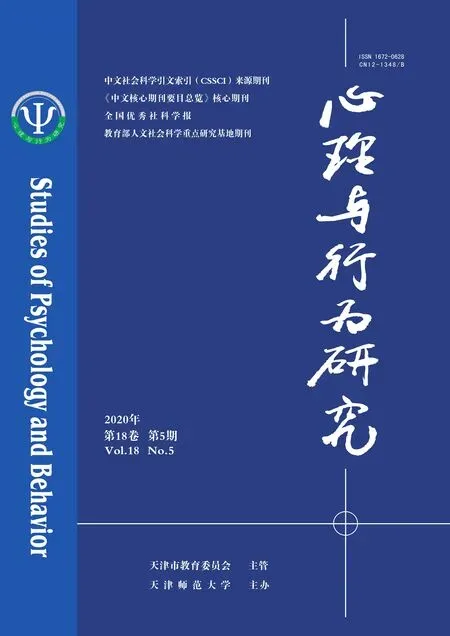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孤独感与正念的作用 *
黄明明 赵守盈
(1 内蒙古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呼和浩 特 010020) (2 贵 州师范大学心理学 院,贵阳 550025)
1 问题提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发布的第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 年3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 亿,同时手机互联网行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也出现上升势头。然而,过度使用手机会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手机成瘾倾向(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MPAT),又称手机依赖,是指个体过度沉迷于以手机为媒介的活动,对手机使用产生强烈、持续的渴求感与依赖感, 并导致个体出现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Yen et al., 2009),已经成为当前严重的青少年公共卫生问题(黄俊霞, 梁雅丽, 陈佰锋, 陈玉娟, 宋建根, 2018)。大学生是手机使用的主力军,也是手机成瘾的高发群体,有必要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发生机制进行探究。
1.1 述情障碍与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
述情障碍(alexithymia)是指个体难以向他人表述自己的情感,并且以缺乏想象力、缺乏内心世界关注等为特点的适应不良心理现象(Griffith,1998)。述情障碍是一种稳定的多维人格结构,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述情障碍是“时代人格”的一个组成部分(陈奕荣, 邵华, 2019; 张春雨, 张进辅, 张静秋, 张苹平, 2011; Sifneos, 1996)。诸多研究发现,述情障碍不仅可以通过抑郁、焦虑等间接影响大学生的手机依赖(Gao et al., 2018),也对大学生网络成瘾和手机过度使用具有直接影响作用(Craparo, 2011; Demirci, Akgönül, & Akpinar, 2015)。最近,国内有研究表明,述情障碍的水平可以显著预测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甚至可以直接引发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陈奕荣, 邵华, 2019)。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理论认为,个体适应不良容易引发个体的手机成瘾(陈秋珠, 2006; Davis,2001),揭示了手机成瘾倾向形成的认知机制,而互联网具有补偿功能,在频繁使用手机后,述情障碍的心理状况将会获得病理性补偿,最终引发个体对补偿物(智能手机)的过度依赖。在日常生活中,述情障碍会导致人际适应困难(张亚利等, 2018),大学生为了补偿自己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的不满足感,避免人际不适应感,会通过频繁使用手机的方式与外界取得联系,由此引发手机依赖(徐 宏图, 杨琪, 汪海彬, 2018; Schimmenti et al., 2017)。因此,本研究假设(H1):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1.2 孤独感在述情障碍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
孤独感(loneliness)作为一种负性情感体验,是指个体体验到个人预期交往和实际社会关系不一致的痛苦(Cacioppo & Patrick, 2008)。当个体感到自己的人际关系单薄,并且与自身理想状态差距较大时就会产生孤独感(Henwood &Solano, 1994)。大学生时期是个体情绪情感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主要发展任务就是避免孤独感、培养亲密感,建立自我统一性。如果未能顺利度过这一时期的心理危机,就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Erikson, 1950)。实证研究表明,述情障碍可以预测和解释个体的孤独感水平和成因(Frye-Cox & Hesse, 2013; Qualter, Quinton, Wagner, &Brown, 2009)。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孤独感是预测个体手机成瘾倾向水平的主要指标(刘红,王洪礼, 2011; Öztunç, 2013)。互联网使用-满足理论指出,个体使用某种互联网媒介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Dunne, Lawlor, & Rowley, 2010),从大学生使用手机行为来看,述情障碍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由于存在一定程度的情绪加工和共情缺陷,自己不能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引发了孤独感,而个体频繁使用手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需求。平时,大学生频繁使用手机与外界建立亲密关系,当大学生体验到了使用手机带来的良好体验,便会沉浸在这种使用行为中,形成手机依赖,这与沉浸感理论观点保持一致(Csikszentmihalyi, 2014)。因此,本研究假设(H2):述情障碍通过孤独感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
1.3 正念在孤独感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调节作用
正念(mindfulness)是指个体全身心地聚焦于当下体验和活动,并对自己的体验和活动持一种非批判性的接纳态度;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它能够使个体聚焦于当下,缓解负面情绪的困扰(Shapiro &Carlson, 2009)。最近的研究发现,正念可以有效缓解孤独感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作用(Murat, 2019),并有效调节大学生压力知觉与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关系(Liu et al., 2018)。根据特质正念理论观点可知,正念水平较高的个体,对自己当下的状态接纳程度更高,不会为了改变某种境况而去频繁地使用手机,手机成瘾倾向不明显,而正念水平较低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回避的应对方式,不愿接纳,而是试图改变当前的状态(Bishop et al., 2004),更倾向于通过手机网络等途径寻求满足和改变,这样更容易产生手机依赖行为。同样,正念将个体注意力引导至当下的体验之下,阻断负面情绪情感对其他负面心理特质的形成途径(Kabat-Zinn, 2012),从而有效避免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引发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设(H3):正念在孤独感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由此可见,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形成同时会受到大学生对手机使用、认知和情绪体验的影响。使用-满足理论、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理论、沉浸感理论分别从大学生的行为、认知和情绪体验揭示手机成瘾倾向的内部机制,而特质正念理论则针对以上内部机制提供了有效干预的理论基础。因此,结合已有研究结论,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究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过程机制及正念调节机制,以期为防范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提供理论指导。

图1 假设模型图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以整群抽样的抽取方式,抽取来自江西省五所高校的1342 名大学生进行测验。由课题组成员担任主试,经过培训后,随机分派到这五所高校中,并在任课老师或班级辅导员的协助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剔除明显不认真作答的被试后,回收有效问卷1224 份,回收率为91.2%。其中,男生682 名(55.7%),女生542 名(44.3%);理工类490 名(40.0%),文史类571 名(46.7%),艺体类163 名(13.3%);独生子女414 名(33.8%),非独生子女810 名(66.2%);农村生源935 名(76.4%),城市生源289 名(23.6%);大一355 名(29.0%),大二441 名(36.0%),大三224 名(18.3%),大四204 名(16.7%)。参与调查的被试年龄在1 6 ~2 5 岁之间,平均年龄20.17±1.38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
采用姚芳传、徐长宽、陈启豹、彭昌孝和王春芳(1992)修订的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 TAS-20),该量表共20 个条目,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进行Likert-5 级计分,有5 个条目是反向计分,有三个维度,分别是辨别情感困难、描述情感困难及外向性思维。测验总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述情障碍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82,CFA 拟合结果良好(χ2/df=4.411, GFI=0.947,NFI=0.958, TLI=0.935, CFI=0.947, RMSEA=0.074)。
2.2.2 手机成瘾倾向量表
采用熊婕、周宗奎、陈武、游志麒和翟紫艳(2012)编制的手机成瘾倾向量表(Mobile Phone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 MPATS)。该量表共16 个条目,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进行Likert-5 级计分,有四个维度,分别是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总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手机成瘾倾向的程度越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4,CFA拟合结果良好(χ2/df=4.876, GFI=0.966, NFI=0.985,TLI=0.958, CFI=0.972, RMSEA=0.058)。
2.2.3 孤独感量表
采用Russell(1996)编制孤独感量表(第三版)(UCLA Loneliness Scale Version 3, UCLA-3),该量表共20 个条目,Likert-5 级计分,11 个正向计分和9 个反向计分,单维度量表。该量表在我国大学生中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刘红, 王洪礼,2011),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是0.71,CFA 拟合结果良好(χ2/df=4.024, GFI=0.969,NFI=0.983, TLI=0.965, CFI=0.976, RMSEA=0.061)。
2.2.4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
采用陈思佚、崔红、周仁来和贾艳艳(2012)修订的中文版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indful Attention Awareness Scale, MAAS),该量表共15 个条目,Likert-6 级计分,单维度量表,总得分越高,个体正念觉知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是0.86,CFA 拟合结果良好(χ2/df=3.472,GFI=0.983, NFI=0.969, TLI=0.979, CFI=0.986,RMSEA=0.051)。
2.3 数据处理
利用SPSS21.0 对研究中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积差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AMOS21.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中介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 单因子方法对测验结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出了8 个特征值大于1 的公因子,其中,首因子对总体解释率为18.68%,远低于40%的测验标准(Podsakoff, MacKenzie, Lee, &Podsakoff, 2003),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述情障碍、孤独感及手机成瘾倾向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对本研究中的述情障碍、孤独感和手机成瘾倾向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结果如下表1 所示。结果显示,大学生述情障碍、孤独感及手机成瘾倾向的得分彼此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可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
3.3 孤独感和正念在述情障碍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作用
3.3.1 孤独感在述情障碍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
利用AMOS21.0 建立以孤独感为中介的中介效应模型,在分析之前,将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然后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rap 法,重复抽样3000 次,对中介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该中介效应模型拟合良好(χ2/df=4.08, GFI=0.93, NFI=0.97, TLI=0.96, CFI=0.96, RMSEA=0.08)。其中,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直接效应显著(c’=0.47,t=7.19,p<0.05; 95%CI[0.34,0.73]);述情障碍对大学生孤独感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a=0.68,t=15.09,p<0.05; 95%CI[0.45,0.83]);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b=0.15,t=2.97,p<0.05; 95%CI[0.11,0.49]);其中,孤独感的中介效应值是0.11,95%CI 是[0.05, 0.24]。所有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孤独感在述情障碍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与相关性统计结果(n=1224)
3.3.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根据本研究假设,利用AMOS21.0 构建了如图2 所示的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估计方法与3.3.1 相同,并采用相关研究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对该模型进行检验(温忠麟, 叶宝娟,2014)。结果显示,该模型的拟合情况良好(χ2/df=3.37, GFI=0.95, NFI=0.95, TLI=0.97, CFI=0.97,RMSEA=0.06)。

图2 述情障碍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机制(标准化)
该模型结果显示,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预测效应(β=0.45,t=5.81,p<0.01; 95%CI[0.31, 0.59]);述情障碍对大学生孤独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β=0.66,t=11.88,p<0.01; 95%CI[0.58, 0.73]);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β=0.15,t=2.57,p<0.01; 95%CI[0.01, 0.30]);孤独感在述情障碍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的中介效应也显著(β=0.10,p<0.01; 95%CI[0.02, 0.19]),以上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具有统计意义。由此可见,孤独感在述情障碍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此外,正念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β=-0.15,t=-2.90,p<0.01;95%CI[-0.25, -0.04]);孤独感与正念的交互项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β=-0.13,t=-3.15,p<0.01; 95%CI[-0.29, -0.02]),以上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正念可以对孤独感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为了更深入地探究正念对孤独感和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关系的调节效果和机制,本研究以一个标准差为界限,将正念分为高分组(M+SD)和低分组(M-SD),并绘制出简单斜率检验图(simple slope plot),如图3 所示。结果显示,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正向预测效应在高水平正念组不显著(β=0.09,p>0.05),而在低水平正念组却显著(β=0.25,p<0.05)。这说明,正念可以缓冲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预测效应,即降低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

图3 调节变量(正念)的简单斜率图
4 讨论
4.1 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述情障碍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验证了本研究假设H1,结果与前人相关研究保持一致(陈奕荣,邵华, 2019;徐宏图等, 2018; Gao et al., 2018),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认知-行为理论和沉浸感理论基本观点也相符合。述情障碍水平较高大学生的情绪加工能力有明显的缺陷,在人际交往时出现适应困难而不能建立自己所需求的友谊(Parker, Taylor, & Bagby,2001),手机使用恰好满足了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得到满足的广泛人际交往需求,成为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现实基础。日常生活中,如不能满足大学生人际需求,缺乏倾述对象,则大学生会倾向于通过手机网络等媒介与外界建立联系,获得亲密感,逐渐对手机形成依赖。
4.2 孤独感的中介机制
本研究表明,孤独感在大学生述情障碍和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本研究假设H2。孤独感的中介作用可从两个方面阐释:其一,述情障碍使得大学生不能灵活地与外界进行交流,对现实人际环境适应困难,导致社会化进程受到阻碍,这是引起个体孤独感的客观因素。以往研究表明,虽然述情障碍严重的个体情绪表达能力较低,人际适应较差,但他们依然具有灵活的思维和强烈的社交欲望(Wastell &Taylor, 2002),这使得他们“机不离身”,最终导致了手机成瘾倾向。其次,述情障碍引发大学生对自己当前社交活动不合理认知,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Parker et al., 2001; Wingbermühle,Theunissen, Verhoeven, Kessels, & Egger, 2012)。此时,述情障碍严重的大学生由于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情感需求,不能在现实中与他人积极互动,进而引发孤独感,转而使用手机与外界联系,试图摆脱自己的孤独感。大学生在孤独感水平较高时,往往主动通过手机发展亲密感,而当注意力控制方向指向手机信息时,就容易导致较高水平的手机成瘾倾向(连帅磊, 刘庆奇, 孙晓军, 周宗奎,2018)。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大学生人际互动遇到阻碍时,应该主动与老师、同伴等互动,参与团体活动,避免独处,以免引发严重的手机成瘾倾向。
4.3 正念的调节机制
本研究发现,正念调节了孤独感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关系,即在高正念水平下,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不显著,而在较低正念水平下,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显著,验证了本研究假设H3。高水平正念可以降低不良认知内容和认知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预防大学生不良行为的发生发展(王玉正, 齐臻臻,刘兴华, 2017; Creswell et al., 2012)。当大学生情感需求不能表达时,会引发孤独感,进而导致大学生对述情障碍处境的不良认知图式。正念水平较高时,这种不良认知图式给手机成瘾倾向带来的启动效应和诱发作用则会被阻断或缓解(Flink et al.,2018)。而低水平正念的大学生往往会对自己当下经历的孤独处境做出批判性的评价,不愿意接纳自己的处境,并试图通过手机等媒介与外界互动的方式来避免当前的孤独感,进而引发手机成瘾倾向。此外,正念具有去自动化的功能(王岩等,2012),可以阻止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自动化联结作用,进而减少了孤独感对手机成瘾倾向的持续诱发作用。因此,引导大学生接纳当前的处境,提高大学生正念水平,是预防大学生手机依赖的重要途径。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虽然本研究假设得到论证,但从数据采集面来看,本研究取样过于集中,与其他地域的大学生样本存在差别。手机成瘾倾向表现可细化为社交成瘾、游戏成瘾等各类亚型,限于研究工具,本研究未能全面考察不同类型的手机成瘾倾向。此外,未对大学生述情障碍进行阴性和阳性的临床检验,而是以平均水平衡量大学生整体述情障碍情况,需要进一步根据阴性和阳性的结果区别对待。本研究中的横断面研究结论还需要后续不断追踪验证。后续进一步深化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发生机制的实验与追踪研究,应广泛取样,并采用分类技术划分不同类型的手机成瘾,考察阳性和阴性述情障碍对不同亚型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机制。
5 结论
(1)孤独感在述情障碍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2)正念显著地负向调节孤独感对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的影响,正念与孤独感在述情障碍与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之间起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